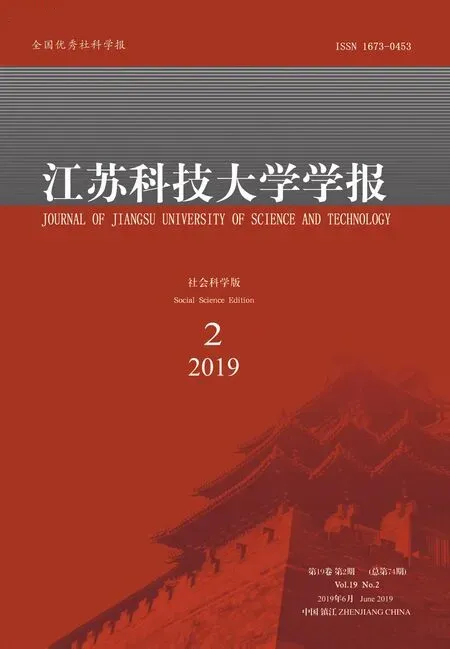论屈辞的“南方”空间书写
2019-03-05王亚男
王亚男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道:“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刘勰认为,屈原作品能够充分传达情感,形成独特的风格,一定程度上受南方环境风物的直接影响。这一观点受到了学界的普遍支持,前辈学者也针对其作品的南方文化特征留下了很多经典论述。如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提出,“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屈原的文学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2]。杨海明在《试论宋词所带有的“南方文学”特色》一文中梳理“南方文学”线索,认为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楚民族崇拜英雄与女性的信仰,使其代表性文学《楚辞》“富有浪漫的色彩和婉丽的风格”[3]。
的确,屈辞中“南”也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方位。对“南方”的表现贯穿了屈原许多作品。可以看出,屈原对于“南方”拥有特殊的执念。这在创作中既表现为他对荆楚之地的地理环境与巫教风俗气息的客观呈现,同时还表现为对“南方”进行了自己的主观建构。他擅长展现不同的地点、环境与风物,构造出包括神话与现实在内的极为广博的宇宙空间。在建构过程中,他特别突出空间与人之主体的互动,既使得空间被人赋予了价值与美感,又使得人之主体被空间影响,加载了特殊的气质与诉求。人与空间的相谐,共同构成屈辞中独具魅力的空间书写。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展开了讨论。如施仲贞《论〈离骚〉的空间意识》一文特别提出《离骚》中有南方和西方两种取向,他认为前者代表“故土”,后者代表“乐土”[4]。又如刘彦顺的《楚辞中的“江南想象”及其空间感——从人文主义地理学观念来看》一文则从水道、屋宇、芳香植物等江南意象切入,探讨楚辞赋予江南的文化意义和想象。还有一些针对《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具体研究中也涉及到南方方位的讨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屈原“南方”书写的讨论还可以继续深入。屈辞中的“南方”有哪些丰富的含义?屈原对于“南方”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他又是如何建构出作品中的“南方”?他与“南方”又有怎样的互动关系?这些都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屈辞中的“南方”意象
(一)客观地理意义的“南方”
屈原笔下的“南方”,从客观地理环境的视角来看,大概可以有五种意义指向:
第一,它直接表示现实中的“南方”方位,当为相对于郢都而言的南方楚地,例如《哀郢》中的“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怀沙》中的“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等。对于屈原的流放路线,从古至今众说纷纭。王逸的《楚辞章句》承继《史记》对屈原的表述,认为屈原在怀王时被疏而作《离骚》,顷襄王时迁逐江南沅湘之间,《九章》《九歌》等作品均作于屈原被迁江南时。这种看法对后代影响十分深远。明清到当代,对屈原的流放经历的研究逐渐深入,尤其是对流放“江南”的问题有着详细的讨论。其中,“东迁”与“南迁”成为重要的关注点。《哀郢》中“方仲春而东迁”、“当陵阳之焉至兮”成为“东迁”说的重要论据。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认为“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中记录的是东南方向,“南渡者,陵阳在大江之南矣”[5]。对屈原流放的路线,笔者采用蒋骥的说法,将现实中的“南方”方位理解为笼统的“大江之南”。
第二,神话语境下的“南方”,即舜为地方神的九嶷山、苍梧之地。《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记载,虞舜葬于湘水流域:“兕在舜葬东,湘水南……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6]《离骚》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敶词”。此“南方”虽有对应的地理位置,但却存在于《离骚》抒情主人公神游的语境中,因而并不是真实的地理方位,而是一种想象中的“南方”。
第三,它可以作为楚国的指代。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楚国位于南方。屈辞中指代楚国时,常常以其地理位置的南方指代国家社会本身,例如《橘颂》中的“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涉江》中的“哀南夷之莫吾知”等。
第四,它也可以作为楚国政治中心郢都的指代。这主要体现于被认为是屈原流放汉北时所作的《抽思》之中,如“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汪瑗注曰:“南,指郢都也。汉北,指当时所迁之地也。屈原所迁之地,其在鄢郢之南,江汉之北乎?”[7]王夫之《楚辞集释》也认为“有鸟自南兮,南集汉北”是“追述怀王不用时事,时楚尚都郢,在汉南。原不用而去国,退居汉北”[8]。汉南郢都相对于汉北而言是南方,屈原流放怀念国都,思念君王,便以“南方”指代眷恋的故土。当然,对屈原是否有流放至于汉北经历,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对《抽思》的解读,一以王逸、朱熹为代表,王逸注“屈原自喻生楚国也”[9]113,朱熹注“屈原生于夔峡而仕于鄢郢,是自南而集于汉北也”[10]。另一以姚鼐为代表,认为“有鸟自南兮”之“鸟”指代楚怀王,“来集汉北”是指楚怀王入秦至汉北,而非屈原流放于汉北。姚注云:“怀王入秦,渡汉而北,故托言有鸟而悲伤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虽流放,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11]此两种观点可备为参考。
第五,指代极南蛮荒之地,主要来自《招魂》中“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此“南方”或实或虚,综合了现实与传说之中的南方荒蛮之特性,是一个遥远的无法到达的地方。
屈辞中对客观地理意义上的“南方”的表现可以总结出以上五种。除了客观地理意义的指向之外,屈原还善于借助神话构写与隐喻,表现另两种特殊的空间意蕴,即神话的“南方”与带有隐喻意义、半实半虚的“南方”。
(二)神话圣境的“南方”
《离骚》中主人公的第一次神游,就是“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敶词”。其目的地是舜所葬的苍梧大地,也就是楚国的南方一带。这次“南征”之后又有三次神游,分别是向西前往昆仑仙境,上天到达天宫,最后再向西前往西海。对比四次神游的表现方式,关于南方之行的书写与后面三次有很大不同。首先,比起后面几次游历有各种飞鸟仙兽同行,南方之行显得孤独而简单。主人公并未借助任何力量,而是独自一人直接前往苍梧大地。其次,南方之行有明确的目的,即向舜陈词,因此它没有繁复迂回的路线,也没有徜徉游览中生发的各种心绪。第三,南方之行的目标完全达成,并不像后面几次游历遇到各种困难且最终没能彻底完成自己的愿望。在天宫之行中,主人公希望能面见天帝,然而“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守门人不允入,使得“求贤不得,疾谗恶佞,将上诉天帝”[9]24的愿望无法实现。而南方之行中主人公“跪敷衽以陈辞”,作为倾诉对象的舜也是不出场的,但从主人公大段的诉说话语可以看出,他完成了个人情感的倾诉。可见,屈原在文本中建构的这个“南方”空间,和后面向西、向上再向西的神话空间完全不同,它是一个无所阻碍的圣地,是一个可以寻找到共鸣、宣泄内心的苦闷、得到灵魂皈依的地方。忠贞高洁之士可以在这里和南楚之神虞舜产生灵魂的互动。
屈原为什么要在《离骚》中建构一个与后面天马行空的神话想象有明显区别的“南方”空间呢?因为这个“南方”空间承担了主人公最真实的个人情志。主人公对舜的陈词篇幅很长,有三十多句,采用的是直抒胸臆的写法。这与后来三次神游中隐晦的“求女”和其他各种象征意象进行组合是完全不同的。主人公从夏代开始讲起,虽有“启《九辩》与《九歌》”的大禹盛世,然而好景不长,太康误国,社会清明被彻底打破。主人公又接连诉说了羿、浞、浇、桀、纣等众多荒淫之人的行为与下场,言语中传达出指责与愤怒,与后面表达的对于现实的愤懑与悲伤相互呼应。虽然在陈词中主人公也提到夏禹、商汤、周文王能够任用贤人,获得上天的支持,但提到他们的例子只是传达主人公在历史之中感悟到的社会发展规律和教训,以揭示自夏以来乱世形成之理。这一大段关于乱世之思考的陈词,也只适合向舜之灵魄陈述。在夏代之前的唐尧虞舜之世,是忠贞高洁之士所向往的圣贤清明之世。舜死后,夏朝好景不长,很快就在太康的手中出现“失国”,进而又涌现出许多昏庸残暴的掌权者。主人公向舜的长篇陈述,正是对舜之世的追忆和呼唤。而舜对于抒情主人公的意义又不同于其他先贤。在后面的几次神游中,主人公也提到了帝喾、少康等先贤。但他们只是用来构造主人公的神游想象,并不突显其崇高的历史地位。舜则不然,虽然他没有出场,但主人公对舜拥有绝对尊重与真诚的态度,二者之间实现了毫无障碍的情感与灵魂互动。这个“南方”空间也因此显得格外神圣。
对楚国人而言,舜不仅是一位圣贤,还是南楚的地方之神。根据史料记载,帝舜一直被奉为荆楚地区之神,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望祀虞帝于九嶷山”[12]。马王堆汉墓所出古长沙国南部地图,九嶷山旁也注有“帝舜”二字[13]等等。这种既来自地理环境影响,也来自个人品性追求的虔诚尊敬,使得舜在《离骚》奇妙的神游空间里成为重要的情感寄托。《九歌》中《湘君》与《湘夫人》二诗所写两位神灵的身份虽引起诸多猜测,但它们也似与舜有着密切的关系。舜所在的沅、湘以南之地,在屈辞的神话空间中成为表达尊崇、敬仰的纯洁神境。
(三)充满隐喻的“南方”
如果说《离骚》中的“南方”是一个带有神话想象色彩、用于情感陈诉与寄托的抽象空间,那么在《招魂》与《九章》等作品中,屈原就表现了既带有客观描写又充满隐喻的半实半虚的“南方”空间。
首先,它象征着善与美的存在。《招魂》与《九章》中常常描写到江南一带的风物。例如《招魂》中的乱词以首句“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领起下面南行的旅程。在旅程之中,这位悲伤的行人看到了很多江南的风物,例如“箓苹”“白芷”“长薄”“皋兰”“枫”。对比屈原的其他作品,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典型的“香草”意象。例如《离骚》中有“杂杜衡与芳芷”、“纫秋兰以为佩”,《九歌·湘夫人》有“沅有芷兮澧有兰”、“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等等。这些“香草”在屈原的作品中一贯被赋予品质高洁、善良正直的意味。那么,在香草遍布的南行之路所指向的“南方”,也一定是一个充满善与美的所在。
《九章·橘颂》也是表现江南风物的重要作品。“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橘树是天地孕育的植物,它生来就适应着南方的水土。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中,它“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展现出优雅动人的外表美和砥砺志节的品质美。当然,也只有坚定固守在南方,它才能保持这样的美丽与高洁。倘若它“种于北地,则化而为枳也”[9]134。可见它的生存与生活环境是紧密相关的。它所身处的“南方”,正是能赋予它一切美好品质的直接来源。因此,在《橘颂》中,作者自比橘树,并又一次建构了一个温暖美好的生长之地“南方”,这个“南方”既可以实指,指向橘树生长茂盛的楚国,或是其流放的南方之地;又可以虚指,指向赋予自我美好品质的一切外在因素,可能包括儒家经典的教育、来自宗族血统的影响等等。而他作为一棵“橘树”,就坚守于这样的“南方”之中不愿离开。
其次,屈辞中的“南方”也并非都是美好之地。它也可以是环境恶劣、难以生存的地方。同样是南行的旅程,《涉江》中这样写江南的风景:“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这里的风景是晦暗、深邃而寂寥的,人身处于此就是和野兽同处,风景呼应着人物内心中“哀吾生之无乐兮”的感叹。这个“南方”既是主人公实际身处的地方——在他“旦余济乎江湘”之后“入溆浦余儃佪”,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又是实际的生存状态——孤独地在偏僻的地方流浪,“愁苦而终穷”。
而《招魂》中又有一个更加恐怖的“南方”:“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归来兮!不可久淫些。”这个“南方”是极其危险的,那里是野蛮人、毒蛇与毒虫的居所,还有各种原始且凶残的生活方式,是个不可以停留的地方。这个“南方”呼应诗中西、东、北、上、下各处恶劣之所。它并不单独作为一个文学建构的“南方”意象,很有可能是楚地民间招魂词中常用的手法。
二、人与“南方”的互动
“南方”这一空间意象,还与人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在方位上它是相对于某一参照物的位置从而成为“南方”的,那么这一参照物是什么?“南方”与其参照物之间被赋予了怎样的关系?而空间是属于抒情主人公的空间,其必然有着“出”与“入”的问题,人物对“南方”的前往、停留与离开,这些互动中又可以表现出怎样的情感态度?
(一)方位的相对性
方位是相对的,有“南方”则必然有东、西、北其他方位,以及它们所参照的“中央”。屈辞中虽也出现东、西、北的方位,但都没有南方出现的频率高。从地理位置来看,屈原最典型地表现了郢都—“南方”这一相对的方位关系。而这一关系的背后,又有着权力中心与权力边缘、恶与善、禁锢与自由、悲伤与快乐等等复杂且相背离的意义对立。
权力中心与权力边缘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屈原贬谪流放的《涉江》《哀郢》等纪行作品中。屈原在这些作品中表达了作为臣子离开国都时流连哀思的伤痛,突出展现了他的政治身份。例如《哀郢》中主人公离开郢都踏上南行的旅程,在他自己看来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导致的结果:“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所以,他在南渡之行所感知到烟水缥缈、前路迷茫,一定程度上正是政治权力缺乏、个人被强权支配而失去行动自主性的生存状态的外化。而从权力中心走向权力边缘,又可以照见郢都的未来——“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他可以预见到郢都宫殿为墟、楚国强权沦落的未来,就像他现在所在的南行之路一样,背离了权力与繁华而走向放逐与边缘。
恶与善的对立也是方位相对关系下表现的重要意义。屈辞中的“南方”一定程度上有着美与善的隐喻意义。屈原虽然被流放,但他始终高举着君子有节的道德旗帜,坚守自己的心灵品质。“南方”相对于中央郢都而言,反而成为了一个忠臣贤士的去所,相对应地,郢都则成为一个奸臣当道、藏污纳垢的所在。然而他的本心是热爱郢都、热爱国家的。他在《离骚》中借抒情主人公之口追溯自己的祖先,在《橘颂》中歌颂为橘树生长提供良好环境的“南国”楚国,都表达了其内心中无比向往个人与国家的“共美”。因此他遭受放逐,前往那个遍布香草芳花的“南方”,他的心绪十分复杂:自己所标榜的美好却成为放逐的代价,本心所认同的“共美”已经消解。他只能通过继续坚守自己良好的品质修养,向尧舜禹等先贤看齐来对抗这种悲伤。
郢都是权力中心与恶的代表,而“南方”则是权力边缘与善的代表,它们在屈原身上形成了情感的悖论。作为忠臣,他期盼能够在权力中心为君分忧,报效国家,然而他却壮志难酬,难觅知音。因此“南方”是对快乐的背离,在那里他感受到深深的痛苦。但同时,他又愤恨郢都道德的沦丧,在“南方”的香草世界中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因而又获得了挣脱恶之牢笼、实现本我之善的主体自由。所以“南方”与郢都对他而言都具有两面性。这种不安的心态,使得他对于郢都与“南方”这两个空间都有着选择与逃离的想法。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人物对空间的出与入的问题。
(二)空间的出与入
在屈辞提到“南方”的句子中,“南”通常是和动作连在一起的。例如《离骚》中的“济沅湘以南征兮”、《哀郢》中的“淼南渡之焉如”、《抽思》中的“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怀沙》中的“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等。“南方”多是行动的目的地,人物常常在“向南”行走。屈原“向南”的旅程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南行,即他被君王放逐而向南行走的客观现实;另一种是主动南行,即“自疏”的个人意念。这段违背屈原的政治愿望、给他带来极大痛苦与迷茫的被动南行,又伴着主动的“自疏”与告别的信念,使其并非完全消极而展现出主体对现实的积极超越。
“自疏”意味着离开故土去往远方的行为来自抒情主人公的个人选择,而非全由外力的强求。《离骚》中的四次神游都是主人公主动离开其所在的生活环境去往神话的世界。尤其是南行一段旅程,是出于主人公个人意愿才去往苍梧之地寻找舜作为他的知音。除了借神游来实现“自疏”之外,屈辞在表现现实生活放逐南行、被迫远离故土的行程中,也有明显的“自疏”意识。在《思美人》中,屈原以“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窃快在其中心兮,扬厥凭而不俟”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既然悲伤的现实无法改变,那么只能姑且逍遥,将愤懑置之度外,毕竟高洁的花草最终会卓然自现,芳香必然远扬,而贤士只要能够保持自己高洁善良的品节修养,他最终也会战胜困难,扬名立万,实现个人的价值。虽然这种自娱的心态在悲伤面前仍然是勉强的,但它代表了人物主体适应生活现实并坚守高尚情操的态度。流放远走的被动性逐步消解了,追求个体生存意义的主动性则逐渐加强。又如《招魂》中最后的乱词部分,展现了一条“皋兰被径兮斯路渐”的香草之路。这段远离郢都、远离权力中心、远离恶的旅程,正代表了对自我的追寻,因而也是一种“自疏”的态度。我们还会发现,除了《离骚》中抒情主人公“南征”有着明确的目的地以外,其他作品中抒情主人公“自疏”的目的地是虚幻不明的。“南方”对于他来说,可以是一个正在经过的空间,也可以是一个没有具体名称的目的地。从他离开郢都,离开权力中心与恶的空间开始,他就进入了“南方”的空间,这个空间随着他的行程逐渐扩大。他迷茫地走向远方,但何处为止步之所却并未言明。由此可见,“南方”于他又是一个想象的、不切实际的远方,是一个召唤着他不断远行、流浪的地方。他的“自疏”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象征着他对于个人品行修养的坚守永无止境。
南行的过程中,对郢都的怀念与对国事的担忧使得屈原与抒情主人公又常怀有回归的愿望。例如《哀郢》中就有“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的回顾、遥望动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的梦归家乡,以及“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回归意愿。《招魂》一篇更是以自招魂魄的方式,呼唤停止流浪,魂归郢都。现实中的人物是不能回去的,但在招魂词的语境之下,它提供了一种可以回归的可能。《招魂》借用了楚地民俗仪式的招魂词格式,首先用序词介绍招魂的缘起,接着在招词的部分告知灵魂四方环境之恐怖危险,铺叙楚国郢都之繁华快乐,最后在乱词的部分既点出本篇是春天南征之作,又回忆了从前君臣相处的生活,表达“哀江南”的痛苦。从篇章结构来看,招词为虚,而乱词为实。招词借巫阳之口,以对魂魄的召唤来表达人物内心的诉求。招词中同样建构了一组“中央”与“四方”的方位关系。“中央”拥有着奢华的宫室、娇艳的美人、丰盛的宴席、欢乐的歌舞,是人间之乐境;而四方则充满了蛮族、野兽等令人畏惧的恐怖存在与各种危险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不可停留的所在。这个超现实世界里的方位对比,正照应现实中的郢都与主人公流放的“江南”之所的对比。但从乱词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现实中主人公流放的“南方”并不恐怖,反而遍布各种象征着美好的香草。因此就出现了超现实与现实照应不合的情况。正如乱词中“魂兮归来,哀江南”中用“哀”一字,屈原对于所处“南方”的认识和体会也是复杂的:他始终保持着“自疏”意识,但在招词中却借本我幻化的巫阳之口,呼唤自己的灵魂返回那个充满了罪恶的郢都,而到乱词中又恢复“自疏”的意识,继续远行。那么主人公到底是归去还是远行?他又该如何解脱与超越当下?招词与乱词的矛盾,实际上寓意着他行走的方向出现了错乱。或许这也提供了一种理解方式:对他而言,正身处的这个“南方”其实是难以停留的,他身处“南方”却不知所往,这便是“哀江南”之“哀”的情感原因。
三、南方地理因子的文学投射
屈原选择“南方”作为书写的对象,这当然与屈原的贬谪经历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屈原对于“南方”的关注与选择,一定程度上也是南方地理文化因子的启示。现实南方所具有的各种地理特征,经过艺术的抽离与引申,在其建构的文学作品中的“南方”集中表现出来。而随着对现实“南方”与文学“南方”的呼应,那些南方的地理特征与艺术隐喻也实现了双重的加强。
从自然地理来看,楚国是南方国家,它有着温和湿润的气候,易生长各种植物尤其是很多美丽的花草。这些物象给予了屈原“香草”的创作启示。而越往南走,气候越加湿润,行途中江水河流边会生长更多的花草,这对于因德行而被贬又同时内心“自疏”的屈原来说,无疑会引起越来越强烈的心灵共鸣。另一个重要的自然物象便是水道。无论是《九章》与《招魂》中现实的“南行”还是《离骚》中神游的“南行”,作者都提到了水道,例如《离骚》之“济沅湘以南征兮”,《涉江》之“旦余济乎江、湘”、“乘舲船余上沅兮”,《哀郢》之“上洞庭而下江”,《怀沙》之“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惜往日》之“临沅、湘之玄渊兮”等等。刘彦顺在《楚辞中的“江南想象”及其空间感》一文中认为:“作为故土的郢都越来越远,致使原来那些流畅贯通、联系四面八方的水路系统,都因为遥遥相距而变得不相通了;同时,也使用这一水道的变化作为喻体,来表现自己心绪的杂乱与郁结。”[14]楚国本就是沼泽遍布、江河罗织的江南泽国,使用舟船通过水路是行远途必须的交通方式。河流的漫长无尽呼应着人物绵长的愁绪,也指引着看不见尽头的未来。不管人物是顺着河流飘远,还是渡过河水向南行进,它们都代表着对原始地的远离,象征着放逐与流浪。此外,作品中美好或又恶劣的“南方”,也与客观的南方环境有关。南方的地理环境本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气候温暖、水分充足、适合万物生长的地方,《橘颂》中就赞扬了这一片水土对橘树生长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过分炎热湿润的气候、毒虫毒蛇的生长、比较原始奇异的生活习惯,这在屈原离开繁华的郢都前往山林荒泽的途中必然带来与繁华都市反差极大的不适感。《招魂》中上下四方之恶劣可怖的地理特征,可以说正是这种不适感的极端化表现。离开拥有着宫室之美、服饰之盛的郢都,走向山川河流,屈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楚地地理文化的返璞归真。也正是因为他走向自然,他的感官变得十分敏锐,使得他能够感知到自然对他心灵的呼应,并在创作中使万物皆着“我”之色。
综上所述,屈原在其作品中建构了一个意蕴丰富的“南方”空间。在实际流放所至的现实空间之上,叠合信仰、权力、道德诸多抽象意义,使其既成为屈原高洁品性与悲伤心灵的外化,又呈现了楚地自然与文化对人物主体的呼应与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