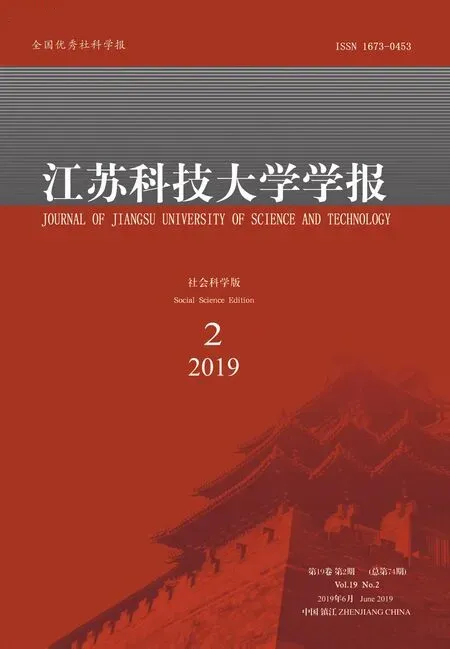论《异邦客》凯丽形象的文化身份建构
2019-03-05王雪瑶
张 媛,王雪瑶
(1.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2.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异邦客》是赛珍珠在母亲凯丽(Carie S.Sydenstricker)1921年去世后为其精心撰写的一部传记,也是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七部作品之一。相较于《大地》《母亲》等获奖小说,国内学者对此展开的专题研究并不是很充分。其主要原因与其传主的传教士身份有关,19世纪末美国派驻中国的传教士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形象带有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的色彩。从1999年到2016年,陆续发表的相关论文近10篇,研究主题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赛珍珠母亲凯丽身份相关的宗教研究;二是与赛珍珠精神追求及文化认同相关的文化研究。
纵观现有对《异邦客》的研究,少有研究者从身份叙事的角度、从人物形象的文化身份建构入手,探究其叙述策略对于叙事文本呈现及人物形象塑造的效果及影响。
一、凯丽形象的文化身份建构:难以规避的殖民主义色彩
人物形象塑造是文本分析的核心。作为《异邦客》主人公的凯丽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关于凯丽的形象建构,最能代表其形象特质的是《异邦客》开篇和结尾处旁观者视角下简洁平实的描述。
在传记开篇,赛珍珠在记忆中留存的凯丽生平几十幅画面中选取了最能代表其特质/状态的一幅画像:
她就站在长江边一座中国城市阴暗中心的美国式花园里。[1]3
如果对这一主旨句作语法分析,主干是“她……站在……美国式花园里”,修饰限制成分是“长江边一座中国城市阴暗中心”。虽然背景是“长江边一座中国城市阴暗中心”,但主人公却是站在“美国式花园里”。对照艺术原则下凸显出来的中国城市“阴暗中心”、美国式“花园”,形成了巨大的视角反差,为主人公形象定下了基调,也为读者展示了多方面的象征意义与人文主题,同时间接透露出赛珍珠内心作为美国人的骄傲和优越感。
在传记尾声,赛珍珠给予凯丽盖棺定论的评价:
对于她以多种方式接触的无数中国人来说,她是美国。我多次听他们说,“美国人好,因为他们和善。她是美国人。”对于孤寂的海员和士兵,对于所有的男女白人,她由衷的愉快和乐于相助的友谊代表着家——代表这方国土上的美国。对于孩子们,在最遥远的外国环境中,她设法而且有时不惜代价地为他们提供美国背景,使他们成为自己国家的真正公民,给予他们对美国不朽的爱……这个妇人就是美国。[1]180
这是读者准确把握凯丽形象的一把钥匙:对于中国人而言,凯丽的社会身份是随丈夫到中国传播福音的美国传教士;对于所有漂泊异邦的男女白人而言,凯丽与他们同为“异邦客”,所扮演的角色代表在异邦这方国土上的美国;对于孩子们而言,凯丽念兹在兹的是对美国文化认同,因此不惜代价地为他们创造与提供美国背景。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就其社会身份和角色而言,凯丽是传教士和“异邦客”,就其自我认同而言,凯丽始终认同的是其美国文化身份。
(一)社会身份:传教士形象
传教士形象是凯丽的社会身份,而传教士形象是贯穿《异邦客》文本的意象线索:上溯凯丽祖辈从荷兰来到美国,一直到凯丽出生、成长,下至其随丈夫到中国的传教生涯。一些《异邦客》研究者对此作过梳理和研究,如刘丽霞认为,“母亲凯丽身上清教徒的一面被否定”[2],刘丽霞还对赛珍珠的传记与冰心、包贵思的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3]。侯郅玥以赛珍珠父母的生命历程为线索,对在华传教士埋骨不在故土、放逐却在他乡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展示[4]。杨坤在硕士论文中对赛珍珠创作中的宗教意识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梳理[5]。朱骅认为,“《异邦客》典型地再现了一位来华美国女传教士在跨国空间中与故土文化、宿主文化、职业、信仰博弈却最终客死异乡的生命史,揭示了女性离散者身处的文化困境和离散状态中男权体制的进一步加强”[6]。
1880年,凯丽(1857-1921)与赛兆祥结婚后就来到中国传教,一直到1921年在镇江去世,陆续在中国度过了近40年的传教生活。赛珍珠在《异邦客》中对凯丽女传教士形象的刻画栩栩如生,既是对母亲的珍贵记忆书写,也具有重要的宗教学与社会学史料价值。
因其作为传教士和传教士妻子这种特殊身份,凯丽形象可以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凯丽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地帮助需要救助的人:她帮助王阿妈走出失去孩子的阴影及疾病的困扰;为美国流浪汉提供宿食,抚养一个丧母的孩子——宝云;准备食物让背井离乡的美国士兵和水手大快朵颐;中国闹饥荒时,凯丽将自己的东西分给穷人;通过说服白人,将美国运来的那些中国人吃不惯的救济奶酪变为大米和面粉供给难民;向中国妇女和孩子讲授卫生清洁相关的知识,等等。“在安德鲁布道的地方,她就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一群群的女人和孩子,教他们识字、唱歌、编织和手工,在教这些的同时也讲授基督教徒的生活和行为的简单基础知识。”[1]159凯丽尽职尽责地履行作为一个传教士和传教士妻子的义务。在传教与救助工作中自然流露的善良热情、坚定务实,使她在教区民众中大受欢迎。在这一点上,凯丽与赛珍珠40年代作品《群芳亭》中刻板教条、狂热传教从而惹人反感进而避而远之的夏修女有着天壤之别。
从社会、文化层面分析,传教士这种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本身就与西方向东方输出文化、价值、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带有“文化帝国主义”色彩[7]204。凯丽每到一处,就将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带到那里,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无形当中以一种美国人的姿态去影响他人。西方的上帝文化已深深地烙印在凯丽的骨子里:“至于她……却不知道她便是美国,无论她到哪里,就把美国带到哪里——带给她所遇到的人。”[1]139凯丽所到之处,她身上所具有的美国文化也随之而至,感染和教化身边的人。她是“做好事的美国人”[1]88,“她是美国活生生的象征”[1]141。有学者认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思想和观念进行有目的的侵略就是文化帝国主义”[8]363-364。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载体的凯丽在中国的传教,无论身处何处,凯丽总会宣扬上帝,教导中国民众去追随上帝。凯丽在与丧女的王阿妈的对话中就存在明显文化殖民的痕迹:“‘我们的国家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她说,‘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上帝教我们要仁慈’,凯丽犹豫了一下,开始告诉她……上帝一定存在的。”[1]79包括凯丽在内的传教士群体在中国遭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及其他针对外籍人士的不友好待遇,可以从社会文化层面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其中有两个场景尤其值得玩味。其一,由于凯丽是异乡人,邻居将长时间的干旱怪罪到凯丽身上,想杀死凯丽和她的孩子,凯丽在大伙冲到她家中之时,用一首中文的《耶稣,我爱你的名字》感化了大家,自己也成功脱险。其二,在凯丽的家中,凯丽倾听中国妇女的烦恼,给予她们以安慰,其中有些人已经秉持着这样的心态:“你(凯丽)信仰什么我就信仰什么,因为它既然能使你这样——即便对我也仁慈,那它一定是真的!”[1]89在西方文化的感染下,女人们的精神得到升华,愈发地想要向上帝靠近。凯丽向中国民众宣扬的美国式精神、美国文化,无疑是对中国民众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殖民,旧时期以王阿妈为首的许多中国民众在凯丽和上帝精神的感召下,其文化属性逐渐开始发生转变,中国民众开始自愿接纳上帝和西方文化,王阿妈等人就是被改造成受西方文化接受者的典型代表。
西方向中国输入传教士的海外传教事业,本质上是对他国/另一民族输出文化、科学、价值、信仰,其初衷、结果甚至行为本身不可避免带有文化侵略、文化殖民色彩。作为传教士和传教士的妻子,凯丽的一生确如很多论者阐述的具有悲剧性。她没有赛兆祥的宗教狂热,却付出了失去4个子女的代价并客死异乡。
(二)实际角色:“异邦客”形象
《异邦客》作为书名,贴切地概括了传主凯丽异国传教实际扮演的角色,是她一生最为形象的写照。虽然从时间上比较,凯丽生活在中国的时间超过在美国的时间,但凯丽在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与异教、白种人与黄种人、文明与落后的对立冲突中,始终认同的是前者。虽然身在中国,但她却始终秉持美国立场:“就出生和爱而言,她的根在这个国家,美国。”[1]99凯丽缺乏中国文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从容与淡定,身在中国,心在美国,这种身心分裂的状态使她与身处的中国环境格格不入。中国的一切都令她反感,刚到杭州,当地人和环境留给她的印象就非常恶劣:“他们看起来多么可怕、小眼睛多么残忍、好奇心多么冷酷……那儿房子如此密密麻麻地挤在运河的两岸,以致它们好似从边上溢了出来,用柱子支撑着整齐地站立在水中一样。”[1]56-57这种对“异邦”环境和人物的厌恶以及不适应几乎贯穿凯丽早期传教生涯。
1.对“异邦”生活环境的厌恶
凯丽对于“异邦”的居住环境极为不满,这在凯丽向赛珍珠讲述往事部分特别明显。
在南方城市杭州,“拥挤而不卫生”的城市让“凯丽感到压抑、无法忍受”:
城市狭窄弯曲的街道、乞丐、拥挤而不卫生的生活使凯丽感到压抑、无法忍受。而且在街上无论走到哪里,就有密密麻麻的人群跟在后面,这也令人不快……最令她难受的是见到那些悲惨的景象,或许特别是瞎子。[1]62
在北方沿海城市烟台,她为看不见脚下中国城“拥挤的街道和瞎眼的乞丐”[1]77而庆幸。
在江边城市镇江,到处是“挣扎、下沉的男男女女的恐怖情景”[1]83。她为她的孩子叫屈:“他们没有花园玩耍,而街道邪恶又拥挤。”[1]85“堆满垃圾的街道上,臭味飘到三间房子里……半腐烂的污秽经过烈日熏蒸,吸引着一群群的苍蝇。”[1]86
在运河边的清江浦(淮安),家外充满嘈杂与喧嚣:“有城市的吼声、小商贩的叫卖声、抬轿子的苦力在人群中挤过时的吆喝声、手推车刺耳的咯吱咯吱声。”[1]87干旱的夏天也似乎故意与她为难:“空前干旱的夏天。整个春天日复一日不见下雨……幼小的庄稼枯死。仲夏到来,天热得令人难以置信……稻子丰收的希望没有了。”[3]89
在中国传教的早期,无论是在南方的杭州还是在北方的烟台,无论是在江边的镇江还是在运河边的清江浦,凯丽无论走到哪里,对于“异邦”环境都感到不适应和厌恶。
2.对“异邦”民众精神状态的鄙视
凯丽对这一个时代“异邦”中国民众的懒散与下流、嘈杂与混乱、邪恶与残忍、愚昧与迷信等精神状态,既鄙视又怜悯。
懒散与下流:“一个懒散的中国园丁倚在她近旁竹林的一颗竹子上,他……腰间松松地系着带子,一顶竹编的宽边帽在他剃光的头顶上裂开了。”[1]4“那地区尽是些下流人出没的处所……门里坐着懒洋洋的、衣服穿得半拉拉的各式各样的女人。”[1]116园丁也好,各式各样的女人也好,懒散与下流无处不在。
嘈杂与混乱:“每位中国妇女的面孔变得紧张而激动……比赛开始了。每个人都尽其可能地唱得又快又响,而且从板壁那边传来的吼声可以判断,男子那边也是同样的情况……谁也不按调子而只顾自己唱……老妇人前后摇晃并用假声高嗓门吱吱地叫,以可怕的速度咕噜着,同时长长的指甲移动着指着书上的字。”[1]60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抑或是老人,即使在唱圣歌的庄严时刻都仍旧是不讲规则、自行其是、乱作一团。
邪恶与残忍:这在王阿妈刚出生的女儿被自己父亲打死的人伦惨景得到活灵活现的展现:“母亲的膝上正躺着一个小死婴,头颅里渗出了脑浆。男人躺在木板床上,脸色阴沉地咒骂着……凯丽……倾吐她深切的愤慨。”[1]78“头颅里渗出了脑浆”的惨烈场景令人心悸、目不忍睹。
愚昧与迷信:女性缠小脚的习俗反映了中国人愚昧的野蛮陋习,以致使凯丽“看见她们的小尖脚”感到“恐怖”[1]60。宿命论使中国人毫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些具有古怪东方宿命论的人们却驾着各式微小的船只定期往返于危险的水面上。”[1]83甚至干旱这种自然灾害也要归因于像她这样的外国人,以至于王阿妈提醒凯丽不要上街:“人们说,因为外国人到城里来,老天爷恼怒了。”[1]89
凯丽与传教地中国的环境、民众格格不入,与其客居“异邦”置身度外的他者心态相关,也与其在落后中国传播福音的社会身份相关,更与其自我认同的美国优越的思想相关。
(三)自我认同:美国人形象
在《异邦客》的结尾,赛珍珠对凯丽的美国人身份、美国认同作了画龙点睛的总结:“这个妇人就是美国。”[1]180
凯丽对美国故土的思念贯穿整部作品,相较于对“异邦”中国的不适应,故乡美国是传主凯丽心中的天堂——美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这种对美国文化与文明的自觉认同与绝对推崇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美好的回忆中倾吐对故土美国的赞美。凯丽总是想起“家乡的教堂钟声”[1]17,想起她成长的自然环境那“灿烂而凉爽的阳光……纯洁的、银色的雾霭”[1]23,想起她成长的社会环境的“美好、光明”[1]71,“美和洁净,美和正直”[1]102。特别是对美国饮食卫生的赞美更是溢于言表:“她谈到……摘来就吃的新鲜水果……它们是那么甜美洁净。对这些白人小孩来说,这听起来就像天堂一般……对于这些孩子……美国一直是一个魔幻的国家,那儿的水不需要煮沸便可以喝,那儿的苹果、梨和桃可以从树上摘下来就吃。”[1]80-81
凯丽还对孩子如数家珍地回忆家乡的果树、果实、草地、山丛等自然美:
比音乐还美的是:看绿树成荫的群山从肥沃、安宁的地上凸起。[1]98
蓝色天空下铺满了粉色的苹果花;秋天清凉的葡萄摘下后“就那么”吃,不用洗;地上的苹果拾起就算你的,可骑的马、可以赛跑的草地、从大树制成的槭树糖,这种树在秋天转变为金黄色——所有这些,再加上许多别的,便是美国,她们自己的美国……属于她们的广阔国家。[1]127-128
对美国现代文明创造的物质财富更是满心自豪:凯丽“对自来水、电灯和雄伟的高大建筑物的惊人魔力感到无限自豪”[1]134。
二是在“异邦”中国尽量保留故土美国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中,弹奏从美国带来的风琴;而美国国庆日更是凯丽家庭永远的节日:“7月4日一直是他们欢庆的节日。她自己制作了一面旗帜,还放鞭炮并围着风琴唱《星条旗》。在孩子们见到美国之前许久,便学会了把休假称之为‘回家’。”[1]80
三是在子女的培育过程中坚持美式教育。这是作为母亲的凯丽最为重视的,就是希望子女不忘美国文化的根,不被异邦中国同化。“出于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感和对教化的热忱,许多传教士尝试将美国的教会结构和家庭文化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亚洲文化中来”[9] 3。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精心为孩子们在中国大地上营造出一个美式家庭。在家庭布置方面,每次搬家,凯丽都会随身带有玫瑰花种或天竺葵枝条,打造属于她自己的美式花园;凯丽还将中国的家进行美式布置与装饰,在上海旧货店购买与美国家中相似的椭圆形餐桌,“她想将这餐桌当作链环把我们一点一点地与她自己的国家连接起来”[1]21。在家庭饮食方面,凯丽在中国厨房中烘烤可可饼、馅饼等美式家常点心。在家庭教育方面,凯丽教孩子们讲英文,用风琴教孩子们学习音乐,她还告诉孩子们如何感受美,给孩子们讲述自己在美国的家等。从布置到饮食以至于日常教育,凯丽尽己所能让孩子们感受美国氛围。
其二,言传身教美国的价值观。凯丽身体力行地展现并传播美国价值观,使其子女免受异邦落后思想影响。一是教育子女热爱劳动,热爱工作。中国历来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儒学传统,对于体力劳动存在偏见和歧视。凯丽不但身教、管理着“一个节俭的美国菜园”[1]149,“她……一直在园里挖地哩……上面留下了许多劳动的印记”[1]3,而且言传美国的价值观,“我们国家没有苦力……正因如此人们很快乐。每个人都工作……我们美国人工作!”[1]134-135二是教育子女树立男女平等的现代观念。在中国,重男轻女思想在上层精英与普通平民心中根深蒂固:“让长子做事是可耻的。女孩子,可以,但儿子不行。”[1]107针对这一非理性的落后意识,凯丽教育孩子:“在美国男孩和女孩都一样受教育,一样受重视。”[1]107三是不愿子女受到异邦中国逆来顺受、软弱无力性格特征与思维定势的负面影响。她担心孩子的成长:“东方人的逆来顺受仍会钻进她孩子们的心灵,使他们变得软弱无力。”[1]106凯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继承并秉持坚强勇敢的美国精神。
其三,送孩子回美国接受系统教育。凯丽对美国人的善良、勤劳、生气勃勃、男女平等等优良品质和社会习俗津津乐道,生怕孩子们忘掉了美国的根。“她经常担心她不能使孩子们够上他们自己国家的生活和思想标准……”[1]106在儿子埃德温回归美国之际,凯丽因儿子离开中国消极的成长环境、回归自己的祖国而感到激动:“她的儿子已离开东方那懒惰、梦幻的气氛而进入他自己国家敏捷、生气勃勃的生活中。”[1]115出于同样的考虑,赛珍珠和妹妹也先后被送回美国接受系统的大学教育,最终赛珍珠于1914年与1926年分别获得美国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学士学位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
凯丽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始终坚持其美国人身份,宣扬、推广美国文化传统和美国精神,以实际行动表现出精神诉求、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方面的美国文化身份认同。
综上所述,凯丽形象的文化身份建构,在社会身份、实际角色、自我认同诸方面,无论是其传教士身份、异邦客身份,抑或是美国人身份,都与殖民主义色彩难逃干系,明显带有浓重的“西方特权视角下的世界”“西方文化下的种族优越论”殖民主义色彩。
二、赛珍珠的叙事策略:对文化殖民色彩的淡化与消解
凯丽形象的文化身份建构,与赛珍珠在其笔耕不辍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领域一直致力于倡导民族平等与对话融合以及文化多元的主张明显存在抵牾。作为人物传记的《异邦客》,对中美环境、人物、文化等方面的对比呈现与《大地》等其他诺贝尔获奖小说“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多彩和史诗般的描述”也明显不同。
传记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小说,传记作者必须遵循一切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传记文体决定了作者没有创造事实的自由[1]34。但在叙事语言、叙事风格上,赛珍珠摒弃冷静超然的“零度风格”,而选用对比色彩强烈、充溢强烈爱憎情感的词汇与表述方式,对传主凯丽眼中、心中的中美环境、民众、观念等国风民俗着力描述,在刻意的比对中生成并强化其震撼人心的叙事张力。在凯丽传教的1880-1921年代,中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国别差异是不容回避的现实,这是凯丽产生“西方文化下的种族优越论”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凯丽的传教士、异邦客、美国人心态,又是凯丽“西方特权视角身份”的主观因素。
为了淡化和消解《异邦客》中凯丽形象建构流露出的 “西方特权视角下的世界”“西方文化下的种族优越论”痕迹,赛珍珠只能在不违背传记真实性基础上对事实进行取舍:在叙事内容(主旨与材料)、叙事形式(结构与视角)上进行精心选择与设计,并采用相应的叙述策略对凯丽形象建构中不可避免的文化殖民色彩予以淡化,并进行某种程度的消解。
(一)叙事内容的选择与设计
叙事内容作为呈现给读者的文学成品在读者接受与评价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关涉主旨的确立与材料的选取。传记作品更是要求其叙事内容既不能违背传主形象的真实性,又要淡化与消解其文化殖民色彩。这其中的取舍斟酌显示出赛珍珠用文字重塑母亲形象时的选材能力与良苦用心。
1.鲜明的叙事主旨
主旨是文章的灵魂。关于《异邦客》主旨的确立,可以从赛珍珠选用的标题中寻找到其立意的蛛丝马迹。《异邦客》英文书名为TheExile,有“流放”“放逐”之意,因此也有其他中译版本将其译为《流亡者》《流放》或《放逐》。
凯丽是位多重意义上的流放者:在宗教信仰上,被上帝放逐;在现实生活中,被自己的祖国放逐;在婚姻家庭中,被丈夫放逐。她的一生是被放逐的一生。
凯丽也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异邦客:在美国,她的家族是从荷兰、法国避难来到美国的异邦客;在中国,她是从美国来到中国传教的异邦客。
因此,从立意上说,《异邦客》作为“凯丽的传记”,主人公虽然有“西方文化下的种族优越论”痕迹,但作为“放逐者”和“异邦客”,其悲剧性命运与凯丽的传教士身份、美国人认同形成明显的背离与反讽,无形中对凯丽身上存在的文化殖民色彩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淡化与消解。
2.精心选择的叙事材料
叙事材料的选取必须围绕主旨展开。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叙事材料的取舍,一是叙事材料的详略。
在叙事材料的取舍方面,在凯丽(1857-1921)长达64年的一生中,可资书写的素材甚众,不可能巨细无遗地将所有材料都写进作品中。赛珍珠在材料选取上围绕要表达的中心意象“流放者”“异邦客”进行了精心选择,主要选取了两种材料:一是家族从荷兰到美国的流放,成为美国的“异邦客”;一是凯丽从美国到中国的流放,成为中国的“异邦客”。
在叙事材料的详略方面,家族从荷兰流放到美国成为“异邦客”作为背景材料从略,凯丽从美国流放到中国成为“异邦客”作为人物传记的主体从详。特别意味深长的是,赛珍珠对凯丽在美国成长阶段做了虚化处理,在家族流放史与凯丽流放史中间,“这时两岁”直接跳到凯丽在异邦中国向子女们讲故事,留下了凯丽生活的空白(2岁到23岁)。这样的处理特别耐人寻味,凯丽在美国的成长阶段没有直接展开,凯丽一直津津乐道的美国作了虚化处理。这显示了赛珍珠的艺术匠心和价值取舍。因此,在叙事材料的选择与详略的处理上,“流放者”“异邦客”对凯丽身上存在的文化殖民色彩同样进行了淡化与消解。
(二)叙事形式的合理设计
叙事形式包括文本结构的组织与叙述视角的选择。《异邦客》是赛珍珠在母亲去世的1921年就开始构思的一篇传记,是赛珍珠写作的第一部书,1928年失而复得,直到1936年才由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公司(Reynal &Hitchcock)出版,历经15年。该作品结构的完整与多变的叙述视角都可以视作赛珍珠文学创作的艺术结晶,同时反映出赛珍珠淡化与消解凯丽身上存在的文化殖民色彩的写作基调与良苦用心。
1.完整的文本结构
《异邦客》的文本结构完整,主要表现在文本总的组织构架与部分/要素间的关联方式两个方面:
一是总分有序,首尾照应。整部书开头的画面选取,结尾的总结,对于母亲作了总的定调:虽然作为“流放者”“异邦客”,凯丽却对放逐自己的祖国痴心不改。
二是过渡自然,章法严谨。整部书由两部分组成,分三个环节展开。
其一,家族的放逐史。由“事情总得从头说起”领起,到造就凯丽“这美国妇人的一个因素”结束[1]4-16。
其二,凯丽的放逐史。分为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凯丽的自述,由“按她自己记得的讲述往事”[1]16领起,到“第一次她来是为了上帝。现在她来是为了这些人”[1]104结束,贯穿了凯丽早期到中国生活的片段,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些事实,几乎可以还原凯丽早年的生活轨迹,将其看作凯丽在异邦中国早期的编年史:
1880年7月8日赛兆祥与凯丽成婚,1880年10月21日来到上海,月底,赛兆祥到达杭州。
1881年6月,赛兆祥派往苏州接替回国休假的牧师杜布西(H.C.Du BUSE)传教,是年7月15日,凯丽在上海生下了他们的第1个孩子(男)埃德加(Edgar)。
1883年12月28日,凯丽在苏州生下了他们的第2个孩子(女)莫德(Maude)。
1884年夏,赛兆祥夫妇到日本度假,9月15日,莫德在回来的船上死在一位传教士马丁博士怀里,将莫德带回葬在上海的教会公墓里,两个月后赛兆祥又被调回杭州。
1885年,赛兆祥再次被召回苏州,12月中旬举家前往山东芝罘(烟台),王阿妈开始跟随赛家。
1886年5月13日,凯丽在芝罘(烟台)生下了他们的第3个孩子(女)伊迪斯(Edith),不久被派往镇江,赛兆祥去苏北里下河各地、徐州一带传教,在清江浦(淮安)建立分站。
1887年夏天在镇江,秋天一家人前往清江浦。
1888年4月,《中国记录者》发表了赛兆祥评述一个新的《福音书》的中译本。
1889年1月23日,凯丽在清江浦生下他们的第4个孩子(男)阿瑟(Arthur)。
1890年8月21日,阿瑟病倒,同期伊迪斯在上海感染霍乱,9月5日阿瑟去世,赛兆祥将其送去上海,与莫德、伊迪斯一起葬在上海的教会公墓里。10月11日,赛兆祥与凯丽启程离开上海,开始还乡之旅。
1892年6月26日,凯丽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生下他们的第5个孩子(女)珍珠·康福德·赛登斯特里克,中文名为赛珍珠。
1893—1894赛兆祥夫妇在清江浦。
二是赛珍珠的叙述,由“我现在可以自己叙述这个故事的某些部分”[1]104领起,到“对了解她各方面的我们来说,这个妇人就是美国”[1]180结束。主要叙述1894-1921年凯丽在“异邦”流放的晚期生活,略写清江浦,详写镇江的生活。
围绕“流放者”“异邦客”结构文章,以达到淡化与消解文化殖民色彩的目的。
2.多变的叙述视角与多重叙述声音
胡亚敏在《叙事学》中将叙述划分为“视角”与“声音”:“视角研究谁看的问题,即谁在观察故事,声音研究谁说的问题,指叙述者传达给读者的语言,视角不是传达,只是传达的依据。”[10]20
叙述视角的特征通常由叙述人称决定,对叙事文本的构建以及叙事效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异邦客》在叙述视角的选取上同样体现出赛珍珠淡化与消解文化殖民色彩的主观努力。叙述视角也称叙述聚焦,是指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通常将叙述视角分为三种形态:全知视角、内视角、外视角。
赛珍珠的《异邦客》书写,在文本的不同部分、叙事的不同时段明显选用了不同的视角:全知视角(祖辈从荷兰移居美国到凯丽2岁的1859年)、内视角(凯丽的自述,1880-1894在中国做异邦客)、外视角(赛珍珠的叙述,凯丽从1894-1921年在中国做异邦客)。通过对不同叙述视角的灵活使用,控制叙事节奏以达成真实客观而又不乏情感色彩的传记叙事效果,建构起传主凯丽形象的文化身份,实现了对叙事文本的重构。
视角转换导致文本中出现多重叙述声音。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将声音看成是叙事“为达到特殊效果而采取的(修辞)手段”,探讨声音在叙事交流中所起的作用[11],区分出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
多重叙述声音在全知视角、内视角、外视角的转换中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或者采用的是“不充分报道”,或者采用的是“不充分解读”,或者采用的是“不充分判断”方式。多变的叙述视角与多重叙述声音的完美结合产生的阅读效果,使《异邦客》传主凯丽所秉持的后殖民主义取向与作者赛珍珠的多元文化观念杂糅、混淆在一起,达到两者融为一体、难以辨识的艺术效果。
(1)全知视角
全知视角又称为零视角,叙述人称一般以第三人称为主。叙述者洞悉一切,凌驾于整个故事之上,随时对人物的思想及行为做出解释和评价。这是一种比较传统和自然的叙述视角,叙述者>人物。赛珍珠在追溯凯丽家族史的时候就采用了这种叙事视角。赛珍珠由“事情总得从头说起”[1]4总领,以大体封闭的叙事形态,按照自然时序延伸扩展,交代了凯丽祖孙三代的家族起源及发展演变情况:“她出身于一个殷实、小康而独立的荷兰世家”,接着简要陈述她的祖父、父亲、母亲从旧大陆的荷兰、法国辗转来到新大陆的美国的艰辛历程,家族先辈同样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异邦客”。
用概述方式采用全知视角对于家族史的回顾,其叙述声音所起作用是“不充分报道”。历史背景叙事部分虽然篇幅不多,但蕴涵赛珍珠创作的多重匠心:一是剖析造就凯丽“这美国妇人的一个因素”[1]15,更深的用意在于平衡凯丽在中国做“异邦客”的经历:凯丽自认为的美国故乡、美国的根,其实就其根而言,凯丽的故乡与根并不在美国。作为在美国的“异邦客”,凯丽的祖父、父母在美国最初的境遇并不美好:“一旦到达美国海岸,他们的困难就开始了……纽约人贪婪而精明,当这一船节俭的荷兰商人和手工艺人进入港口时,他们就成了再好不过的牺牲品”[1]11,当“他们坚强地忍受了这一切,并立即前往宾夕法尼亚州,找到了他们根据书面介绍购买的那片土地……才发现那完全是一处什么也不适宜、压根儿无法耕种的沼泽地”[1]11。凯丽在美国家乡度过的时光,即1857-1880年间的生活作者选择性地进行了省略,留待凯丽对孩子们的讲述中进行交代。
这种全知视角的选用,因其只有作者的一个声音,一切表诉与意义都是作者意识的体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与消解了凯丽关于美国故乡、美国天堂的神话。
(2)内视角
对于赛珍珠出生前以及未懂事前的凯丽情况,即1880-1890年间凯丽在中国做“异邦客”的情况,赛珍珠采用凯丽“自己记得的讲述往事”方式展开[1]16。叙述者=人物,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内视角。叙述者所知道的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叙述者只借助主人公的感觉和意识,从她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
采用内视角,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赛珍珠出生以及未懂事前的凯丽情况只能选择由凯丽本人讲述,二是有利于真实再现人物,因为采用这种视角,凯丽既是主人公又是讲述者。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她”或者凯丽展开叙述,因而在叙述声音上就只是凯丽的声音,这种“不充分报道” “不充分解读” “不充分判断”,使赛珍珠与母亲凯丽有了某种程度的区隔,也就淡化了文本呈现的西方优越和西方中心的殖民色彩。
对于1880-1894年这10多年间的情况,是《异邦客》浓墨重彩展开的地方。这15年间,凯丽跟随丈夫赛兆祥奔走各地传教,赛珍珠研究者大都熟悉其行旅,凯丽对于美国的热爱,对于异邦中国的隔膜与不适应,与其生活的颠沛流离相关,也与其子女在中国相继夭折相关。这在前文赛珍珠对凯丽的形象建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出。
赛珍珠在结束母亲凯丽故事的自我讲述时,对此作出目的论意义上的总结:“第一次她来是为了上帝,现在她来是为了这些人。”[1]104展示了凯丽从隔膜到逐渐适应、融入“异邦”中国的过程,同样淡化与消解了“西方文化下的种族优越论”。
(3)外视角
赛珍珠对于自己开始记事后的情况,对凯丽的叙述又转向外视角,“在适当地熟悉这位美国妇人之后,我现在可以自己叙述这个故事的某些部分”[1]104,这主要反映在赛珍珠一家人从清江浦到镇江定居以至于凯丽去世,大致涵盖凯丽从1894-1921年的近30年间的生活经历。
外视角,简单说叙述者<人物,叙述者对其所叙述的一切所知有限,也就只能“叙述这个故事的某些部分”,相较于第二部分凯丽自己的讲述,受到的局限性相当大。这与小时候的记忆遗忘有关,也与赛珍珠后来离开母亲回美国留学、婚后于1917年离开母亲随同布克去往宿州这些客观因素相关。其叙述声音“我”做出的仍然也只能是 “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解读”“不充分判断”。这一部分的叙述,相较于第二部分对于中国的负面描述、凯丽对于美国的向往有明显的减少。当然在结束部分,赛珍珠还是对于母亲的一生做了高度总结:“对了解各方面的我们来说,这个妇人就是美国。”[1] 180
由于传主传教士身份的特殊性,也由于传主与赛珍珠的天然亲密关系,赛珍珠在真实展现凯丽的一生时,运用叙述策略淡化与消解了凯丽形象建构的殖民色彩,多少撇清了自己与母亲凯丽身上文化殖民色彩的关系,在客观效果上达到了书写目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赛珍珠在《异邦客》中进行凯丽形象的文化身份建构时,难以完全撇清作为传记作者的自己与“西方特权视角下的世界”“西方文化下的种族优越论”之间的干系;在其中国言说中不可避免地进行西方和东方价值体系对比,进一步将中国与中国书写演化为想象的地域及其表述[12]。这种言说方式,与赛珍珠本人文化认同困惑的主观因素不无关系。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有陈静《从〈战斗的天使〉与〈异邦客〉透视赛珍珠的文化身份》(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吴碧玉与陈泽星《异国的灵魂栖息在何处——论〈异邦客〉中关于精神自我的追寻》(《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第9期)、张倩《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论赛珍珠三部传记的写作主题》(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朱春发《移情与认同:论〈异邦客〉中的边缘人》(《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等诸多研究,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