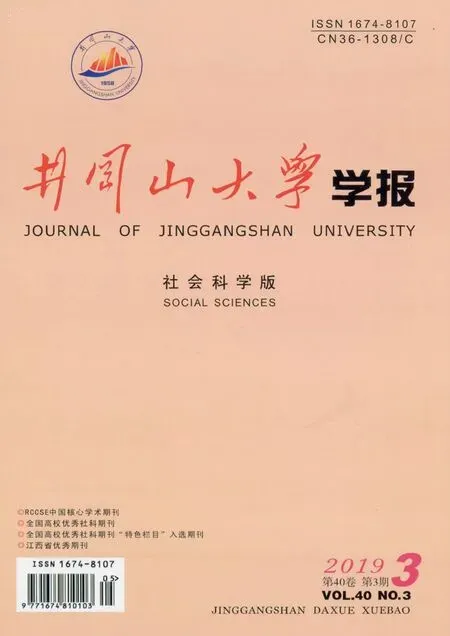论谭嗣同的仁学创新
2019-03-05唐春玉
唐春玉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仁是传统儒家实践哲学的主导,也是传统儒家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而仁论一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议题。近代以降,西学涌入、社会危机深重、革命风潮高涨,传统儒家思想在面临时代未有之大变革的历史时刻,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社会转折、文化转型的历史关头,如何回应时代之变化、西学之挑战,便成了时代向知识分子提出的迫切任务。以谭嗣同为首的志士仁人,一方面承继了儒家仁学的精华,另一方面借用西方的平等、自由、博爱等近代观念,以实现儒学的自我革新为旨归,建构了一套指导政治实践的新仁学体系。谭氏之新仁学,“它要在思想上打倒不合潮流的偶像,冲决束缚人们的一切网罗”[1](P272)。 谭嗣同的仁学凝聚了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融合古今中西之作,更是近代仁人志士探寻救亡之法、启蒙之方的一个历史缩影。
一、以太释仁——仁学本体论的革新
近代以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遇、碰撞、交汇已是无法规避的历史事实。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今说”中国哲学,以“古话今说”之方式对以往哲学进行重新理解、逻辑重构,实现中西哲学的互动、交融,便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延续、发展的重要特点[2](P10)。 以谭嗣同为首的志士仁人,为实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革新,把西方自然科学“以太”同中国哲学“仁”相比附,建构起新仁学的哲学体系。
为此,谭嗣同对囊括天、地、人的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背后的本原进行了探索,进而把宇宙天地万物背后的超验存在和本原依据归之为以太:“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管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 ”[3](P10)透过谭嗣同对以太宇宙本然体段的把握和叙述,可知以太遍润一切,化在三界万物之中,是事物普遍性的超越存在。以太之大用流行,体现为仁、兼爱、佛海、灵魂、爱力多重向度,体现出涵盖儒释道三教,且沟通中西哲学的特征。在中西交融的视野下,谭嗣同接着用中国哲学注重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体用关系来说明以太在现象中的显现,他说:“由一身而有家、有国、有天下,而相维系不散去者,曰惟以太。身之分为眼耳鼻舌身,……曰惟以太。 ”[3](P10)
透过谭嗣同关于以太的论述,可知以太是一个维系人、社会、宇宙的“道”本体。谭嗣同借由对经验世界的演绎推导出以太为世界的本体,在肯定以太超经验性的同时,他还推断以太是“不生不灭”的。为了说明以太的“不生不灭”,谭嗣同以佛教名词“微生灭”来论证物质世界的“不生不灭”。谭嗣同把物质世界“不生不灭”称之为“微生灭”。这种“微生灭”“求之过去,生灭无始;求之未来,生灭无终”[3](P36),而且“旋生旋灭,即灭即生”,“密之又密,至于无可密”。谭嗣同认识到事物的“生灭”跟以太是分不开的,正是不断的“旋生旋灭,即灭即生”,才有“不生不灭”的永恒存在,“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宇宙因此也“不生不灭”地永恒存在。由此观之,以太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根,同时也是宇宙间一切存在总体生生不息的助力。对以太宇宙本体的性质定位,以及以太的“不生不灭”,谭嗣同是为了进一步建构起以太与仁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在西方哲学范畴对以太的思考之后,谭嗣同回到中国哲学的历史总体中找到了仁,并把本体以太等同于仁来实现仁学本体论的革新。仁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自孔子创立仁学伊始,孔子将仁诠释为以“爱人”为本的宗法血缘联系,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伦理实践,进一步将仁化为普遍的伦理金律。这是仁体发显的基础阶段。不过孔子未能直接就本体来揭示仁,而是在德性求境界、工夫和本体中达至仁的境界。孟子承接孔子,将“仁者爱人”的伦理规范进一步扩大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磅礴境界,并进一步提升为仁政的政治诉求,以心、性、天的下学上达的圆融论证,把道德自觉与普遍必然性融合为一。孟子从内外两方面扩大了仁学内涵,多方面显示了仁体本有的维度。但是无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或者孟子爱民爱物的仁政,无不是在说明仁所具有的政治以及伦理意义,并没有完成仁学形上学。汉儒在“仁者爱人”的基础上,以博爱论仁,肯定了泛爱、兼爱、博爱的表述,使仁爱包含了先秦儒、墨各家之仁,进一步扩宽了仁的伦理内涵。在宇宙观上,董仲舒首次明确以仁为天心,且以生释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无穷极之仁也。 ”[4](P402)“天,仁也”,这一命题已经接近了仁体的思想。就自然界而言,天之仁体现在覆育万物、化生万物、养而成之、有功无己。仁深入到儒家的宇宙论建构过程之中,仁上升为形上学之实在,已经具有了仁学形而上的意义。宋儒继承了董仲舒以生释仁的路数,提出了“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是互为补充的,“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 ‘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 ”[5](P33)“生生”与“一体”,都是关于仁的实质性的解释,于是“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在孔孟仁学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扩充,仁学形上学得以完成。
谭嗣同继承了“生生之仁”与“一体之仁”的理解,但是作出了一些转换和改变。如上可知,一方面,谭嗣同以以太的“微生灭”来论证世界的“不生不灭”,以“不生不灭”来解释天地氤氲、万物化生、生生不已的“日新”变化,而“日新”是“斯可谓仁之端也已”[3](P62)。以太“日新”为仁,“日新”为生。质言之,生是仁之根据,即为“生生之仁”。另一方面,以太是世界统一性的物质本原,以太之用具有“以太有相成相爱之能力”[3](P26),“格致家谓之 ‘爱力’、‘吸力’”[3](P12)。 “以太之用至灵而可征者”,于人身为脑,于虚空为电,“而人知脑气筋通五官百骸为一身,即当知电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也。”[3](P15)谭嗣同将以太理解为把事物联系为一体的媒介,由以太而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体的 “爱力”、“吸力”作用,是仁的体现。以太“日新”的生生之理为仁之端,以太的“相成相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人物交融的仁爱伦理,“日新”的生生之理和以太的“相成相爱”即为仁学形上学,从哲学意义上而言,仁指向的是本体意义。
为了进一步说明仁的本体意义,谭嗣同借助元、无的本体诠释方法来解释仁、元、无的内在关联,“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3](P4)。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仁,亲也,从人二”。清代学者阮元特别说明,仁字左边是人,右边是二,仁的原始精神是人与人之间在我—他的场域中的亲爱关系,注重的是交互性特质的阐明。“元”字的结构是“从二从儿”,“无”字许慎认为通“元”为“无”,也是属于“仁”的意义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元是宇宙万物萌发初始之义;无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是万物的本原,“有生于无”,而仁的功用可穷尽于无。通过仁、元、无的内在一致性,可见,仁已经超越了政治、伦理层面而指向本体之域。能达于仁、元、无的学说有三种:佛教、孔教与耶教。谭嗣同把儒之“仁者爱人”、耶之“爱人如己”、佛之“慈悲”融会贯通,使仁学合乎逻辑地发展成统摄儒、耶、佛在内的哲学体系。
谭嗣同将仁提升和改造成精神性实体,进一步,他将中西方哲学传统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以太—仁的哲学架构。他以仁与以太相配,一方面,“夫仁,以太之用”[3](P14),“其显于用,谓之‘仁’”。仁是以太之用,以太是仁之体。仁之发显流行依赖于以太;另一方面,作为以太之用的仁,充塞宇宙全体,是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3](P14)之本原,“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3](P8)。 按照此逻辑推导,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由以太而生,此处又说仁生天地万物,以太和仁同为万物的本原、依据,以太和仁的差别就大大减少,甚至二者等同了。换言之,就宇宙本体论意义而言,作为抽象存在之以太等同于精神性实体之仁,形成了哲学上的“二元论”观点。
那么,谭嗣同建构两个超验本体,并让以太等同于仁的意义何在?究其缘由,谭嗣同对以太本体的论述,其指归还在于强化仁是万物的本体依据。谭嗣同借鉴西方自然科学“以太”一词,并对其予以抽象和提升,将其革新为世界的本体。对以太本体的论述实为对仁进行重新理解、逻辑重构,用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实证性来论证仁作为万物本体的合法性。
关于仁本体,谭嗣同从几个方面加以界定:其一,“夫仁,以太之用”,“仁为天地万物之源”[3](P8)。这说明在谭氏仁学思想的逻辑链条上,仁是以太之用,又是万物存在的本根、本因。其二,“智慧生于仁”,“不生不灭,仁之体。 ”[3](P8)以以太的不生不灭界定仁,仁成为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其三,仁之属性为通。他在强调仁为以太之用时,又以“通”来规定仁的内涵,强调通是仁的第一要义,是故仁与不仁即为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与不仁……苟仁,自无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 ”[3](P13)通则仁,不通则不仁,“不仁则一身如异域,是仁必异域如一身……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也”[3](P13)。 其四,仁与耶之“爱人如己”、墨之‘兼爱”、佛之“慈悲”、格致家之“吸力”、“爱力”实为相通,仁学成了会通儒、佛、耶,贯通自然、政治、伦理的终极依据。
谭嗣同将西方自然科学以太和中国传统哲学仁比附起来,并且让本体以太等同本体仁,这是他建构仁学的创造性一举。以太由质点分割,至于“一”,而仁的特征也是“一而已”。以太和仁都是“一而已”,故“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3](P8)。以太是“不生不灭”,仁成为“生气流行”的永恒存在。“仁以通为第一义”[3](P7),通的意义为“道通为一”,通体现在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内外通,终括其义,三教之公理又可为人我通。“通之象为平等”[3](P7),平等是仁最重要的社会属性。概括而言,平等是仁的题中之义和价值指归,通是架构仁与平等的桥梁,“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3](P8)谭嗣同借由概念的层层演绎,推导出以太—仁—通—平等的仁学体系,仁学在以仁为基础的前提下开出了平等的近代意义,这就不同于古代讲万物一体所指向的是兼爱、博爱的伦理境界,为儒学仁学的近代发展,特别是仁学指向政治思想的路径提供了一些方向。因此,谭嗣同把仁学中的“生生之仁”与“一体之仁”,转换成近代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自由等价值伦理精神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儒家仁学思想也因此从旧有之古义展开为近代社会价值。一般而言,平等在中国近代社会最为贫乏,因为平等与君主专制制度相悖逆,与封建等级社会相抵触,故以平等是当世最缺乏者。不过,平等也因此成为政治变革最主要的政治诉求。根据谭嗣同以太—仁—通—平等的逻辑思维,并将之贯彻于政治、伦理领域,那么,凡不符合仁学价值指归的政治、伦理规范及要求,就必须加以冲决。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实现仁所指向的平等的人间秩序,他们在新仁学的指导下去批判封建礼教,推翻不合理的政治体制。
二、心力行仁:仁学价值观的建立
谭嗣同转入对心力的研究是在维新事业陷入低潮之后。这一时期,他提出“以心挽劫”的口号,用心力代替了之前的以太,形成了心力—仁的唯意志论见解,使以仁为主导的哲学体系从理论走向实践。
谭嗣同执着于“以心挽劫”,还在于“心”的积极能动意义。宋明心学,是“心”作为道德内倾之源的本体地位被确定下来。“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作为万物之本体,具有至善的德性,“至善是心之本体”[6](P29),“心”既是万物之本体,亦为至善之根源。“心”之所以为至善,乃是因为“心”先验地拥有了“天理”,“夫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6](P203),“心” 确立为传统道德的内在根据,传统道德也因“心”而凝聚成完整的道德体系。于积极意义而言,“心”被确定为道德价值根据,所有德性都是“心”的发显与流行,所有的伦理秩序体系是本体“心’的外在投影和推演。“良心”作为先天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善性种子,相当于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人之本性的自我立法,对于加强人们的道德实践的自觉有着积极的意义。
不过,“心”作为道德价值内倾之源从一开始就遗留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尤其到明清以降,道德本体“心”遭到了历史性的危机,直至最终瓦解。原因有:其一,把“心”或“良心”作为道德本体,有可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的倾向。无论是主体之“心”还是本体之“心”,都带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而且“良心”本体的最大特点是封闭性、自我性、内在性,每个人都有一套道德准则,而且随着“心”的无限膨胀,使得“心”的本体地位让人质疑;其二,“良心”的泛化与普遍化,使得道德本体“心”对于世俗人的惩戒作用减弱。人人皆有良心,物物皆有良心的平民化、普遍化趋势,使“心”从天上被迫拉回到人间,其神秘性、绝对性、超验性的内涵少之又少;其三,“良心”与仁、义、礼、智、忠、孝等德性,是“一”与“多”的关系。 “一”的绝对与神秘与“多”的相对与实在形成了巨大的张力,难以调和。于是,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良心善性”的多角度的反复论证、批评之下,“心”的超越性、终极性、神秘性逐渐消失,最终崩溃与瓦解。至此,人们德性生活的本体依据——内在“心”或“良心”自明清之际就被消解了。以至于到了晚清,已有的伦理道德规范遭到了普遍化的破坏,人心的狡诈、虚伪、自私、腐败、贪婪等非道德行为开始沉渣泛滥。如何寻回道德意义的本体依据,近代的思想家对“心”投入了积极的关注。
从洋务运动至维新变法,思想家们已经逐渐从器物层面开始深入到制度层面以及思想道德层面的改造上。时有龚自珍的“自尊其心”,大谈心力的巨大作用,强调“以教之耻为先”的道德教育;魏源的“平人心之积患”,以道德教化正人心、沥德性;康有为的“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以恢复孔教来提升社会风气,拯救人心等命题。谭嗣同的“以心挽劫”可谓是对这一社会思潮的响应。而他所谓的心力不再是中国传统伦理意义上的“良心”。就本质上而言,谭嗣同的心力一方面承继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某些因素,一方面又融入了西方近代伦理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价值融为一体而形成的精神力量,兼具本体与功夫的双重性格。在客观性方面,心力是以太的精神性实体,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 ”[3](P7)就主观方面,心力乃是宇宙最具平等之仁赋予个体的自由意志,具有实现“仁”的方法意义,“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3](P96)。不过心力可善可恶,其中,“机心”为恶,“愿力”为善,能解救社会劫运的是“愿心”,也就是“慈悲之心”。
既然心力分为“机心”和“愿力”,那么促使心力中的“机心”隐而不发,“愿力”发挥作用的方法,谭嗣同认为是 “何莫并凹凸而用之于仁”[3](P106)。“天地间仁而已,无所谓恶也”[3](P26),仁是宇宙个体应有之德性,仁是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谭嗣同以仁来规范和引导心力,把心力引向正确的方向,使心力趋利避害,且朝着对社会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样一种以仁为价值取向的善良意志可以感化他人,净化道德,发挥个体的意志自由。于是,本质上为善良意志的心力,就成了社会进步的的动力因,“天下皆善其心力也,治化之盛当至何等地步? ”[3](P108)于是,谭嗣同的“以心挽劫”就成为了一个唯意志论的伦理学命题,强调主体的自由意志是成就道德的内在动因。谭嗣同“以心挽劫”的唯意志论见解,在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 “三纲五常”为底色,兼具政治结构和伦理秩序的社会形态。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的本质获得了形上超越“天道”的依据,人的生命价值唯一的源头是由最高的道德本体“天理之善”给予的。但是,这种将形上道德本体直接等同于具体的三纲五常的做法,迫使人丧失了追求至善本体之动力,成为依附于现实政治统治的奴隶。谭嗣同“以心挽劫”的唯意志论见解,恰恰破解了这一桎梏。既然作为宇宙精神实体的心力流行于“人道”之中是具有平等之义的仁,而仁的根本特点为通。据此,君主专政的政治政体,儒家的三纲五常都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与人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仁之境界背道而驰。那么以心力去破除旧有之道德,使人性从封建政治体制下剥离出来就获得了合法性的形上依据,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获得重新定义。
谭嗣同还进一步指出,若能求得人类的心力相通,那么仁所指向的平等而融洽的人间秩序就可以实现。谭嗣同将心力的实体归为“慈悲”,“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3](P97),把修炼“慈悲”作为拯救社会危机的根本方法。换言之,谭嗣同用佛教之“愿心”所含有的平等、无畏之新道德去破除“机心”之旧道德。究其底奥,谭嗣同所谓的心力就本质而言是要为他的政治理念服务的。由于近代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是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双行并轨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谭嗣同的“心力说”对新道德人格的诉求,体现的是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旧有道德的批判,对人民、国家应有道德的近代转型提出的新任务。在他看来,封建专制社会网罗重重,要突围这根深蒂固的网罗禁区恐怕一时难以实现,唯有个体坚守“心力之实体”,方能让维新志士满怀信心去冲决社会重重之网罗。这是谭嗣同在近代伦理革命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可贵之处。为此,谭嗣同直指人心,从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来解决人心问题。
个人方面,他要求人们“断意识,除我相”。谭嗣同要求克服人所具有的局限性和奴性,以主体人格精神的自我塑造来解决机心所造成的劫运。他循着陆王心学的思辨路径,以“内返”的形式,从本源上“断意识”,以内倾之源“明觉之心”的发动来摒除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对立、痛苦。在“外绝牵引,内归易简”[3](P108)的路径和条件下,心不为外物所役,断除种种社会意识。惟其意识断除,“我相”的决然断裂,个体才能以慈悲之心待人。而“众心一源”,“我之心力,能感人使我同念”[3](P12),慈悲之心的传递、辐射、感化,彼此休戚与共,才可以达到了无彼此、人我不分的境界。而仁就是人我的互相感通,慈悲之心的增长,“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3](P98)。
从“我之心力,能感人使我同念”所指向的伦理实践逻辑出发,你若看到有人对你使用机心,那么你先去掉自己的“机心”,重重地发起一种“慈悲心”,自然就察觉不到别人的“机心”了,“人之机心为我忘,亦必能自忘;无召之者,自不来也。 ”[3](P97)“慈悲之念”的博大情怀,能化解他人之“机心”。感觉不到别人的算计心,那么别人就不会对你使用“机心”,自我也就无畏了。总之,他是要人自觉地忘记别人对你施加的压迫、侵犯等种种苦难,尔后就不会觉得有压迫、侵犯之苦了。人把现实的一切苦恼都抛之脑后,也就了无自我,达到“除我相”的境界,于是“异同泯”“平等出”,达“仁矣”。
在国家方面,谭嗣同意识到国家的自强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责任在己而不在人”。这种“责任在己而不在人”的说法,实为对“君主专治”的古典政体的悖逆,是对“民主群治”近代政体的倾慕。在他看来,国家之自强不只是圣君贤臣的责任,它更是人类群策群力、自由合作之结果。换言之,国家自强独立的理想,是建立在“民主群治”的基础上。可见,民主之原动力在于人民对自我权利的觉醒,在其意志和行为自由统一基础上所衍生的道德责任感。这种将自我提升为国家、民族命运之上的责任意识,使得当下的国人为国家之自强而焕发出高度的自觉。就此,谭嗣同提出用“合心力”的方法来达到国家之富强。
人人激发潜在之心力,以心力参与社会之改造,那么内在的精神力量就可转化为外在的物质力量,“心之力量虽天地不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 ”[7](P460)个体内在的精神力量的觉醒,可以唤起国人为国家独立、自强的责任心、自信心。人人增进心力,心力“骤增万万倍”,则可达到“一切众生,普遍成佛”的治化之盛。这种“一切众生,普遍成佛”的治化之世已经超越了种族、人群、国界的樊篱,不仅能挽救劫难,普度众生,还可以拯救全天下,乃至整个宇宙。“一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以此为心,始可言仁,言恕,言诚,言絜矩,言赞天地,赞化育。以感一二人而一二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3](P97)谭嗣同认为,心的巨大功力好比佛教“普度众生”情怀。人心存关怀,普度众生,有助于人们建立起终极关怀的信念,而践行仁、忠恕、笃诚等诸般德行亦因心而显发。谭嗣同“以心挽劫”之仁学具有博大的人文胸怀,使得谭嗣同的仁学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依托,更是一种新型的道德本体,“天地间亦仁而已矣”[3](P14)。
以上可知,谭嗣同借助心力的巨大能动来革新仁学世界观,使得仁学既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又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谭嗣同把中国社会现实与佛教“普度众生”联系起来,同时又从中西方借鉴有益的思想资源,把仁学熔铸成涵盖中西、古今的既理性又超越的信念体系。“以心挽劫”背后,是依托佛教超越一己的宇宙关怀的信仰力量,是谭氏构建仁学的理论初衷,是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积极探索与思考。“以心挽劫”的背后,是谭嗣同对以“心”解决社会危机的倚重,同时也证明了仁学的心学特质。
三、余论
在民族灾难与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时刻,谭嗣同建构起涵盖中西,容纳各家学说的仁学思想。然而紧迫的社会现实,致使谭嗣同对一些外来知识没有来得及完全吸收与消化,故遗留下不少矛盾和问题。不过,谭嗣同整合中西文化以变革社会危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尝试论之,谭嗣同之仁学是兼具认知和实践的新仁学,新仁学相较以往之仁学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色及时代精神。总归其旨,仁学是谭嗣同后期思想之主体,也是其哲学、伦理思想之终极归宿。它凝聚了志士仁人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哲学思考,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会通中西、熔铸古今之方式来反思当下时代问题的理想追求和实践路径,是对儒家仁学的一种创造性阐释。举其要旨,谭嗣同对仁学的创造性阐释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仁学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哲学。谭氏之仁学不同于旧有之仁学,他扬弃了仁维护等级制度的礼的内容,将仁提升和改造成精神性实体,将中西方哲学传统融为一炉建构起以太—仁的哲学架构。谭嗣同建构仁学的初衷和宗旨之一是“以心挽劫”,以回应近代中国遭受劫难的时代难题。因此他的仁学无疑是对时代问题的哲学构思,是谭氏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反思和觉醒。仁学遵循的仁—心—识的相互统摄的路径使谭氏之仁学独具特色,成为中国哲学、伦理史上最完备、系统的仁学体系。
第二,仁学是具有多元视界的新儒学。谭嗣同之仁学,亦可谓将古往今来之儒家发展为一新儒学的哲学体系。谭氏之仁学具有大境界和大视野,拥有以往儒学无法企及的广博和高度。在他的仁学中,既有平等、自由、博爱等西方近代伦理精神,也有西方自然科学的缩影,同时还有孔孟陆王代表的儒家主流,佛、道、墨的综合。就以太之用仁就涵盖了墨之兼爱,佛之慈悲、轮回,耶之灵魂等统摄中西方传统文化在内的统一体。这种会通中西以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儒学的做法,可以说是对儒学的一次伟大的革新和创举。
第三,仁学是具有世界关怀的新人学。在《仁学》中,谭嗣同自信地说:“孔教何尝不可遍治地球哉!”可见,谭氏追求的仁之境界乃是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大同治世,它已超越一家、一国之疆界,乃是宇宙众生的平等境界。梁启超评论《仁学》时说到:“《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8](P170)可见,中国哲学、伦理学中的仁的广博境界和宏大气象在谭嗣同的仁学体系中得到了全新的提升,使之不仅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救士与启蒙)休戚相关,更与西方列强及一切“含生之类”有关。他将仁与平等、慈悲接通,且其仁所具有的天下胸怀,俨然已超越了国界走向世界,从而使古旧传统中的仁真正开出了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