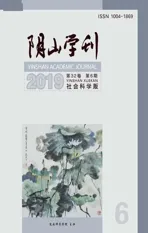史达祖《双双燕》词燕子意象的象征意义*
2019-03-03许兴宝
许 兴 宝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双双燕》一词是两宋词坛上的著名之作,下面是全部词作的内容: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稍,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史达祖《双双燕·咏燕》)
历史上曾经有过作为韩侂胄堂吏的史达祖与词人史达祖是否为一个人的争议。但从总体上看,将词人史达祖认定为韩侂胄堂吏的人为多数。可以列出如下几家:王士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冯煦、刘永济等。由此可见,没有必要再用功夫去考证相关的争议问题。有了上述依据,就有理由将《双双燕·咏燕》中燕子意象的象征意义追问下去。
一
多数诠释者不重视“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这个对创造燕子意象具有关键意义词句中所包涵的意蕴,只是就字面意思给予诠释就了事。如有人说,这个句子写燕子“傍晚归来,双栖双息,其乐无穷。……在双燕归来前,以为天涯游子曾托它俩给家人稍一封书信回来,它们全给忘记了”(高原语)。[1]1814有人在注释的时候说:“这句是说燕子忘了给思妇带回征夫的讯息”(唐圭璋语)。[2]从如上两个例证中可以看出,诠释者无疑将《双双燕·咏燕》这首具有言外之意的燕子意象词,完全当作不包含任何言外之意的单纯咏物词看待了。根据史达祖的生平与特定时期的创作倾向来看,史达祖通过《双双燕·咏燕》来创造燕子意象,寄托着没有将出使金国时对敌情准确判断的信息提供给韩侂胄,致使韩侂胄在不能全面了解敌情的情况下,作出了北伐的决策,以至于使自身受到连累的懊悔意味。
史达祖《梅溪词》中,除了上述燕子意象之外,燕子意象共出现12首次,占《梅溪词》总数的十分之一稍过。就这个倾向来关注,几乎与晏殊词完全等同。统计可知,晏殊《珠玉词》里面,约有30余次燕子意象,于他本人词中鸟类意象的占比半数还强。词中燕子意象出现较多,是由晏殊的部分词学思想所决定。晏殊的部分词学思想是,作词要以吟咏富贵为主,但不是说仅仅描写金玉锦绣,而是要将富贵气象展示出来。晏殊的这种词学思想,是通过他人之口转述出来的: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3]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帘幕中间燕子飞”是出现燕子意象的典型诗句,恰好是被晏殊确定为表现富贵气象的证据之一。从中是否可以看出,晏殊在诗中创造燕子意象,就是显示富贵气象的表现?应该肯定地说,晏殊在词作里面,出现较多燕子意象的根本缘由正在这里。作为少见的太平宰相,晏殊尽享富贵人生不说,即使在审美追求上,必然也要表现出超过普通人仅仅寻求物欲满足的精神审美。作为韩侂胄堂吏的史达祖,曾几何时的富贵生活,与晏殊没有任何区别。史达祖在词中创造燕子意象,还有创造燕子意象成为名篇的成果,这种审美追求与晏殊的审美追求也应该如出一辙。史达祖《双双燕·咏燕》词以“(燕子)度帘幕中间”作为开首句,不是套改晏殊诗中“帘幕中间燕子飞”的情景描写,那又将是什么?即使将史达祖的《双双燕·咏燕》词判定为是受晏殊如上诗句启迪的结果,也不能视为纯粹的荒诞之举。另外可以见到史达祖接受晏殊影响的例证是:在《玉楼春·社前一日》词中,通过“明朝双燕定归来,叮嘱重帘休放下”与“处处旗亭堪系马”的情景描写,与晏殊“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存在着互为影响的关系;在《解佩令》一词当中,除去珠帘意象与燕子意象和谐组合而成的意境,就是接受晏殊“帘幕中间燕子飞”的影响之外,晏殊《无题》诗中“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情景描写,对于《解佩令》词中“淡月梨花,借梦来、花边廊庑”的情景描写,同样具有明显影响。
推陈出新于史达祖的表现是,将燕子意象创造带来的富贵气象,给予了规模化的扩展。其具体表现是,将晏殊以特定审美观照对象作为目标而形成的理论适应范围,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给予了扩大,形成了创作规模。这个问题在上面的意象数据统计中,已经有了清楚的说明。下面要说的问题是,晏殊追求富贵气象的词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影响到史达祖,是因为史达祖作为堂吏的身份和出生地域与晏殊具有特定因缘。作为堂吏的史达祖,无疑在充满富贵气象的氛围里面生活。这种生活对于有创作激情的词人来说,必然要起到激励作用。史达祖在《双双燕·咏燕》词中出现的由柳昏花暝、红楼、雕梁等因素和合而成就的自然环境,燕子理所当然是出现在富贵生活场景中的活物。从史达祖的出生地(安吉)来看,接壤于晏殊的家乡抚州,这是史达祖接受晏殊影响的地缘方便。
史达祖在四十多岁受到刑贬,此时方为创作的旺盛时期。所以在受到刑贬之后仍然可以创作,并且有作品传世,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满江红·中秋夜潮》词就是刑贬之后的词作。对史达祖刑贬之后依然有创作实践的判断,要看程千帆给出的结论:“现存《梅溪词》包括了史达祖晚年的作品,可见张鎡在嘉泰元年作序以后,其词集又经过重编。”[4]从程千帆的如上结论当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史达祖续编的词作中,完全可以断定《双双燕·咏燕》词是被刑贬之后的暮年之作。为人熟知的规律是,于人生的晚年回忆年轻的时光为常见,前车之鉴的朱敦儒词可以作为范例来看。史达祖对往日“辉煌”的回顾,也只能是在韩侂胄被诛杀以及本人被刑贬之后。史达祖以晏殊“吟咏富贵气象”的词学思想作为创作指导,创作出以回顾往日“栖香正稳”、“轻俊”的富贵得意之时,没有能够为韩侂胄提供准确而有益的信息,那就是“便忘了、天涯芳信”的词句,无论如何都是符合规律的。
史达祖被刑贬之后,与董如璧、耿柽无异,都是被全面否定的对象。处于如此情境中的史达祖,与无辜纯粹无缘吗?对往日的工作疏忽是否有所忏悔?史达祖在特定的情境当中创作《双双燕·咏燕》一词,虽然词题使用的是传统创作理论上的咏物说法,但在实际上是寄托着词人内心苦衷精神信息的意象创造法。
二
之所以在词中道出“忘了”转达准确而有益的信息于韩侂胄的懊悔,是因为由史达祖被刑贬前的地位所决定,与此同时也由韩侂胄仓卒发动北伐的行为所决定。史达祖刑贬之前的重要地位,从史书的记载与陈自强经常称“堂吏史达祖为兄”[5]的表述中,均可以得到证实。主子与堂吏的关系非同一般。中书吏职名当中有堂吏一说,实际上是“制敕院五房堂后官”的别称,拥有的权力非常大,行使五房群官管辖的权力,为五房群官的首长。五房群官直接为皇帝服务,其中有人掌承受皇帝言语,及进书草,有人掌点检书写熟状及进呈,有人掌敕命用印下发,等等[6],已经是权力非常大的官吏,更何况是群吏首长的堂吏史达祖。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有史料将史达祖描述为“事皆不逮之都司,初议于苏师旦,后议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职”与“事无决,专倚堂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具出其手,权炙缙绅”。
堂吏的特殊地位必然会受到韩侂胄的信任,因此也就有借庆贺金章宗生日的机会,随礼部侍郎李壁出使金国去打探金国国情殷虚的行为。还应该指出的是,随李壁出行还有在完成使命的同时,带有监视李壁的使命。李壁之所以被委派出去打探金国国情的殷虚,是因为邓友龙于嘉泰三年十二月出使金国的时候,有人通过贿赂驿站官的手段,请求接见邓友龙于深夜之际。在接见的时候,给邓龙友汇报了金国困扰于蒙古,再加上饥荒连年,面临着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处境,如果宋朝军队能够适时驾临,摧枯拉朽之势必然如愿。邓友龙将得到的如上情报如实向韩侂胄作了汇报,随即将出兵金国的倡议,以奏疏的形式传递上去,于是在朝廷左右便形成了北伐金国的议论。李壁在北伐金国的议论出现之后,被选派出使金国,韩侂胄的目的无疑是出于谨慎,以求更进一步地确认邓友龙之前带回情报的可靠性。李壁出使回来所带情报与邓龙友无异,但韩侂胄于此依然心存狐疑。因此再派陈景俊出使金国以祝贺元旦的名义,以便再加确认。陈景俊同样带回的是与李壁基本相同的“金主本无意用兵”情报。陈景俊得到情报的记载没有李壁所带情报的记载详细,但可以明确的是,“金主本无意用兵”说对韩侂胄北伐金国决心的最后下定,所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是无可疑虑的。李壁具有坚定不移的北伐金国信念,具体表现是先行主动进上要求追贬秦桧的奏疏,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激励举国上下收复中原的信心;其次还主动接任叶适直学士院的职务,将讨伐金国的诏书进行了全面起草;第三是初次北伐金国兵败后,为了迎合韩侂胄将过错归咎于苏师旦将自己引上邪路(指北伐金国)的胃口,有意识地在韩侂胄面前摆出严厉唾骂苏师旦的造作姿势,并且提出流放荒野以谢天下等建议。实践证明,李壁做的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并不是韩侂胄的爪牙。有据可以证明的是,李壁后来凭借着参知政事的高位,不止一次地秘密告诫诛杀韩侂胄的密谋者,行动必须火速进行,否则将会出现机密泄露的失误,并且当即秘密下令殿前司中军统制权主管本司公事夏震带兵随时准备实施刺杀。这一系列事实说明,李壁是参与诛杀韩侂胄的直接策划者。上述事实的摆出,让人们看得非常清楚,韩侂胄在当初不信任李壁,是确切存在的事实。
史达祖肩负着重大责任伴随李壁出使金国,得到了什么样的情报?史书不见记载。但完全可以预想的是,绝对不可能带回令韩侂胄变更北伐金国决心的情报。就这一点来说,从词人所作《龙吟曲·陪节欲行留社友》词中的“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栏杆静、慵登眺”句子里面表现出“壮怀无挠”积极北伐金国的坚定意志来加以关注,完全可以证明史达祖是一个全面支持韩侂胄北伐金国的人。从出使金国回来的时候,路过汴京写的“天相汉,民怀国”(《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词来看,在史达祖心目中,丧失天意的金人,在我军到来之时,必然不堪一击。对于韩侂胄发动的这场理由不充分、准备不足因而失败随时都有可能的北伐,持有意见不同者并非一人。其中就有丘崇,他的意见是:
中原沦丧且百年,在我固然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战危,若首倡非常之举,兵交,胜负未可知,则首事之祸,其谁任之?
丘崇出于善意还进一步满怀信心地分析形势,确认在金国人没有破坏盟约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应该拿出应有的气度,不要一惊一乍,而是要趁机在加强军事实力建设方面下大功夫,以便占有主动权,在金国挑起事端的前提下,加以北伐就有充足的理由了。丘崇的如上善意见解,不仅没有被韩侂胄当做善意加以采纳,反倒却被视为处心积虑忤逆自己意志的敌意加以排斥。类似于丘崇者,一律被韩侂胄视为异己。史达祖为韩侂胄的心腹人物,如果于出使金国回来之后,能够提出与丘崇相类似的善意见解,韩侂胄于悬崖将要坠马的时候,回头急转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在韩侂胄恶性膨胀的时候,史达祖只是一味地迎合,这种行为与周筠、苏师旦等人极力要求起兵伐金,最终却以丧师失地告终还不完全相同。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伐金失利的起初,史达祖没有被韩侂胄确认为祸端引起的首恶分子。在韩侂胄面前,史达祖可谓是一个情感与生命双双能够赢得的幸运者。在主子最犯糊涂之际,作为心腹的史达祖,没有及时加以提请注意,不是因为主子淫威所逼,而是身在此山的结果所造成。有据可证的是,倪思在苏师旦受到处罚以后,将造成失误的韩侂胄论为“明有余而聪不足”,还以晚年的杨国忠与李林甫作比,危言耸听的劝谏意味十分明显,但得到的打击报复不过是由试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改任为宫观官而已。这个事实表明,在认识到自身确实有所失误以后,韩侂胄对于他人的善意劝告,还是能够部分地加以接受的。史达祖作为堂吏,与主子朝夕相处,如果不清楚韩侂胄的如上表现,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对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韩侂胄北伐金国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史达祖了解得十分清楚。对于金人内心中生出的厌战情绪,但不欲先开和议之口,意在想等待机会占得主动权,以及宋军在屡次战败的情境中,士气落到最低程度的事实,史达祖了解得十分清楚。韩侂胄后悔以前用兵决策轻率,是在从金人韩元靖那里得知金国也有和议意向以后的事。正是因为有所后悔,所以才有了拿出自家二十万钱财主动去补助军需,意在通过这种方式来博得世人对过失决策宽宥的举动。与此同时还要求丘崇派人带着官方文书与金将布萨揆主动和谈。布萨揆感觉到了有机可乘,于是装出一副强者姿态,提出了割地、称臣、献首谋之臣的苛刻要求作为议和条件。其中要求宋方交出韩侂胄的用意十分明显。对于这个暗含杀机的苛刻要求,朝廷中的人无所不晓。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史弥远即在应允布萨揆的苛刻要求之下,将韩侂胄谋杀。在这一年之内,韩侂胄是事实上的强弓之末,唯恐残喘都来不及。对于上述情况,史达祖同样是应该有所了解的。
自从进入中枢以来,韩侂胄的劣迹就是人们经常谈起的事实。只从树敌过多这个方面来加以关注,就可以见到“始则朝廷施设,悉令禀命,后则托以台谏大臣之谏,尽取军国之权决之于己”,“立椒殿皇后,韩侂胄反对”[7]等多个事实。如此作恶,一点都没有觉察,对于史达祖这样的位置,就有些不可想象了。两旁外人对韩侂胄的行为都看得非常清楚,能够作出“逊以相位,乞身告老,为绿野之游,易危为安”的劝告,史达祖难道还一无所知?韩侂胄被诛的密谋,不可能让史达祖知晓,是为理所当然。但韩侂胄自开禧以来的作孽,自己都清楚居相位的所作所为是“谬当国秉”,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迟早都会到来。与韩侂胄不沾边际的旁人,对其所处境遇,都以善意的方式给予提醒。史达祖是其心腹,再任期间却不见有挽救危局的丝毫见解提出。史达祖在与主子同时接受刑罚后,通过在词中创造意象的方式,隐隐约约地表露出没有将危险信号先见地传递给韩侂胄的懊悔,是有良心的反映。关于史达祖对韩侂胄所为知情的实际事实,刘永济给出的明确认可是:
史为韩侂胄中书省吏,凡韩有所作为,史无所不知者,其间不少“昏”、“暝”之事,皆所“看足”者。(刘永济《微睇室说词》)[8]
如上认可与我们坚持的上述观点完全合拍。为了进一步表达相同观点,在同一本书里面,刘永济还指出,虽然对主子的“昏”与“暝”有所看足,但史达祖不想自行引退,以至于在主子身败名裂以后,因此受连累而受到黥面的刑辱。刘永济这个说明的言外之意是,史达祖在遭受到黥面之辱后,内心当中应该存在着未能及时向韩侂胄提供有益信息的懊悔意绪。史达祖内心当中存在的懊悔意绪,在刘永济与俞平伯一同选注的《唐宋词名篇》一书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证之以作者(史达祖)另一首《满江红·书怀》词‘一钱不值(贫相逼)’之句,则其悔悟之心亦盛深刻。”[9]
由上述可以看出,史达祖对以往所为有所懊悔的判断,既有内证依据,也有外证依据。
三
要想证实史达祖通过创造燕子意象,来渗透自身懊悔意绪的精神信息,还要从纪实倾向在史达祖词中的实际存在来加以关注。从《梅溪词》的查阅可知,纪实词中的部分,有些为主子被诛杀之前的作品,有些则是主子被诛杀之后的作品。大凡有小标题的纪实词作,为前期的作品,可以举出的词例如随李壁、林仲虎贺金章宗天寿节随行覘国途中创作的所见所闻作品即是。在《宋词系》一书当中,夏承焘认为,如下一些作品,当是如上出使途中创作出来的作品:《龙吟曲·陪节欲行留别社友》《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齐天乐·中秋宿真定驿》《鹧鸪天·卫县道中有怀某人》《惜黄花·九月七日定兴道中》。[4]413除此之外,《鹊桥仙·七夕舟中》《玲珑四犯·京口寄所思》也被确认为随行途中作品。这些作品创作年代的确认,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将词中小序及词之内容、李壁、林仲虎的事迹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梅溪词提要》综合在一起,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分晓。但通过词作中的内容分析,来判断与史达祖特定时期身份一致的题旨表现,仍然是最为关键之处。如对《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词创作时间判定,就是从“出京怀古”词题以及内容分析,得出是随李壁、林仲虎使金归途经过北宋旧京汴梁时创作的结论。再根据词中“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的内容来加以关注,人们认为史达祖与多数北上覘国者带回来的情报没有两样。
作为一个一身兼有双重任务使命出使金国的史达祖,带回迎合韩侂胄蓄意北伐意愿的情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合之以史达祖所具有的抗战意愿来看,从如上举出词中抽吸出来关键表述,不可能存在表达上的歧义,也不可能引出读者领会上的歧解。与史达祖一同出使金国的全体成员,在坚持抗战的思想上,没有意见不一致之处。可以见证的是,李壁在《使金诗》诗中同样表达了“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风残照懒回头”的抗战思想。由此可以看出,抗战思想对于在史达祖词中的表现来说,绝对不可能是孤弦幺韵。
受刑贬以后史达祖创作的词,确认具体创作时间的难度较大。一方面是由于几乎见不到有关于标明或暗示创作时间的小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作品题旨表现不透明,再合之以受刑贬之后的生活状况以及为堂吏之前的生活状况,能够发现的记载极为有限,所以难以考订具体创作时间。而对于史达祖来说,为堂吏之前的生活处于潦倒状态,受刑贬以后的生活更是处于潦倒状态,而且在刑贬以后,内心当中还充满着不可自我化解的矛盾。
通观史达祖的全部词作,能够发现其中有部分作品记录了自身内心中的矛盾以及生活的潦倒状况。以“书怀”为词题的《满江红》词,是为这个类型作品的典型。这个判断的作出,需要我们来看程千帆的论断:“从所作《满江红·书怀》‘三径就慌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看来,他后来的生活是潦倒的。”[10]程千帆论断中“他后来的生活”,就是指刑贬以后的生活无疑。下面我们再来看杨海明针对上词发表的论断:“总观全词,它尽情地抒发了自己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感情:有怀才不遇的愤懑”。“总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而在两种理想无法实现之前,他就只能借艺术(文学)去暂时地摆脱和渲泄自己的苦闷”![1]1842无需发问,杨海明将这一首词作确认为于堂吏任上创作的作品。程千帆与杨海明发论的根据不是史料,而是根据作品的内容所进行的推定。推定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诚如王朝闻在给王大有的两封信之一中所说的那样:“只要揣测不脱离历史发展规律而且符合特定过程和方面的独特性,不是以揣测代替可能存在的存在,那么揣测不只是可以的,而且在特定条件之下是有必要的。”[11]有如上两位学术大家符合逻辑的推定,对更为清晰地认识史达祖《满江红·书怀》词的主旨,无疑会起到引导作用。有这样的逻辑存在,对其余一些词的主旨,以词中的内容作为依据推定出来的结论,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全面承认。雷履平将以词题为“白发”的《齐天乐》词推定为“在贬逐期间”作,所凭借的根据除了张鎡为《梅溪词》于嘉泰元年辛酉作的序文当中有“余老矣,生须发未白”的话语之外,以词的内容作为推定的根据,仍然是主要手段。“涅不重淄,搔来更短,方悔风流相误”这样的词句,以“词人初依主战派韩侂胄为掾吏,‘权炙缙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韩被杀后,身亦牵连遭贬,故有‘风流相误’之语”[1]1833这样的诠释来加以了结。如上所给出诠释的意思为,受到刑贬的黜置以后,史达祖对过去与韩侂胄结交之事方才生出了懊悔。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看,完全能够把“渐疏了铜驼,俊游俦侣”一句当中所包涵的意蕴,推定为被贬出朝廷以后内心中存有的不堪回首懊悔之感。王步高将《秋霽》一词考订为创作于被贬江汉时期的作品,而且给出具体的创作时间,即大约在嘉定五年之前的某一个深秋之时,考订的根据是“谁是、脍鲈江汉未归客”这个句子。而这个句子的造出,是化用杜甫在江陵期间作诗将自己称为“江汉思归客”而来。(杨海明将词题为“中秋夜潮”的《满江红》词里面“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一句中所包含的意思确认为“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出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昭雪冤愤。按嘉泰四年五月,韩侂胄在定议伐金之后上书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史达祖身为韩侂胄的得力幕僚,他在词里写伍子胥的沉冤得以洗雪,恐即与此事有关。”[1]1838杨海明对如上词句意思的确认,完全依据的是词的内容,而不是史料。
正是建立在可以按照词的内容进行推定的基础上,词学研究专家刘永济对《双双燕·咏燕》词才果断地作出如下诠释:“其词曲尽燕子之情状,然非纯咏燕,乃托燕以写闺情,写闺情又即自抒情也。但观其‘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之句,言外盖有所指。考邦卿为韩侂胄中书省堂吏,凡韩有所作为,邦卿无不知者,其间不少昏暝之事,皆邦卿所‘看足’也。又邦卿‘看足’此种昏暝之事,乃不早自引去,卒与同败,实由‘归晚’。观此语,则邦卿亦非全无感觉者,但意志不坚耳。此等处是否作者无疑流露心事,虽不可知,然证以作者另一首,《满江红·书怀》词‘一钱不值’之句,则其悔悟之心亦甚深刻。”[9]如上这种诠释词的手段,对领会《双双燕·咏燕》词的内涵所能起到的指导作用十分明显。尤其可贵的是,其中出现的“悔悟之心”云云,成为从创造燕子意象的关键句子“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当中寻找象征意义的重要依据。
在作为堂吏的史达祖内心中,出使金国要为韩侂胄带回有益信息,是他本人的使命所在。这个愿望在作于随李壁出使金国途中作词题为“京口寄所思”的《玲珑四犯》词里有表白:“待燕来、先寄新词归去,且教知道。”让燕子带给主人“且教知道”的信息,无疑是与北伐抗战相关的信息。这时的史达祖在内心里面,充满了完成使命的迫切感。通过如上论述,可知史达祖出使金国所带回来的信息,与李壁等人所带回来的信息,没有丝毫不同,由此导致了韩侂胄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制定了草率的北伐计划。在遇到打击之后,史达祖有“悔悟之心”,是一个具有良知的正常人的表现。史达祖的“悔悟之心”,通过创造燕子意象的方式,向世人做出了坦白,正是词人的高明之处。发现史达祖给燕子意象渗透词人懊悔的精神信息,无疑是切中实质的精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