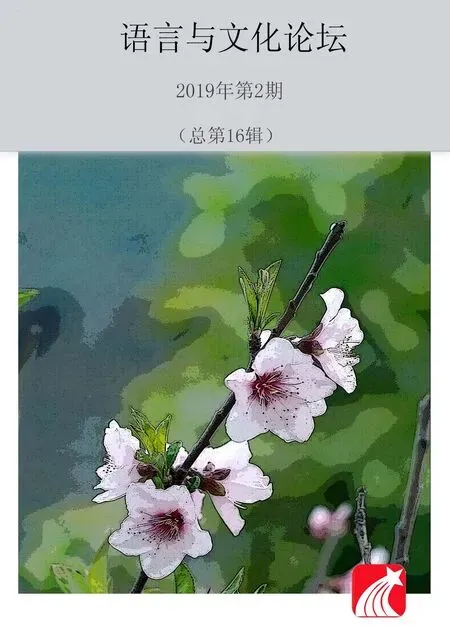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
——试谈非马诗歌艺术追求与思想内涵
2019-03-03何与怀
◎[澳]何与怀
非常有幸,由于参加一些国际文学会议,很多年前就结识了非马先生这位享誉世界华语文坛的“业余”诗人。私底下,我们不时电邮往来,通常是他传来诗作让我欣赏,我则传去文章向他请教。记得相处最密集的是2008年3月那次。他与夫人应邀一起到悉尼访问,立时掀起一阵旋风。应文友们要求,我在《澳华新文苑》刊发了一期“非马专辑”,并与澳洲酒井园诗社以及“彩虹鹦”网站一起举办了几场座谈会、聚餐会,以欢迎他们的光临。其情其景,正如悉尼诗词协会会长乔尚明以金代刘著《月夜泛舟》、清代姚鼐《金陵晓发》、宋代王沂孙《高扬台》《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以及唐代高适《别董大》各诗集句所描绘:
浮世浑如出岫云,风烟漠漠棹还闻。
如今处处生芳草,天下无人不识君。
多年结交证实,这位“天下无人不识”称为“非马”的诗人,的确,此马非凡马。这是一匹长途奔驰而壮心不已的骏马。早在1978年,他在《马年》一诗曾经这样写道:
任尘沙滚滚
强劲的
马蹄
永远迈在
前头
一个马年
总要扎扎实实
踹它
三百六十五个
笃笃
这是自信,也是自许,更是自励。风入四蹄轻,现在又过了几十年,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笃笃马蹄声,总是不绝于耳,总是在我们心房回响。
一、反逆思考:非马诗作的重要特色
最初看到“非马”的名字——好像是30多年前了,总之是认识非马本人之前许多年,首先进入我脑海里的自然是“白马非马”这个典故,是战国末年名辩学派的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公孙龙和他的著名哲学论文《白马论》。我自然想到“白马非马”那个众多哲学家特别是先秦哲学家探讨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继而我又知道非马这位诗人是一位高尖端核工博士。他在台北工专毕业后,于1961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马开大学机械硕士与威斯康星大学核能工程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能源部属下的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能源研究工作多年。
因此,我一直最感兴趣的是:经严谨而又长期科学工程训练的这位诗人与众不同之处何在?
的确,正如许多论者所言,对于许多诗人与诗论家来说是尖锐对立的诗与科学,在非马那里却得到了和谐与统一:文字简洁,旋律短促,是非马诗句的特征,十足表现科学家的干净利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以对科学无穷的探求的姿态写诗。他的诗既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又结合现代文学的先进的表现手法和批判精神,用凝练浓缩的语言营造惊奇的意象,表达具有多重内涵和象征的内容;他不但对社会人生热切关怀而且以冷静的哲理思考见长,两者相得益彰;人们特别用一个常常形容科学家思考方式的词来评论他的一些诗作:“反逆思考”。
试看非马写于1976年的《共伞》这首诗一个片断:
共用一把伞
才发觉彼此的差距
但这样我俯身吻你
因你努力踮起脚尖
而倍感欣喜
短短5行,34个字,却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塑造了一个饶有趣味而耐人寻味的意境。这种艺术魅力除了取材立意外,应归功于“先抑后扬”的突转结构法。恋人无意中发现“差距”,有些扫兴;但当读者正要顺此思路往下走时,突然出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差距”,一人低头俯就,另一人踮脚趋迎,爱情经过“差距”的验炼而愈显纯真,自然使人得到一种特殊的审美愉悦而“倍感欣喜”。这就是非马的“反逆思考”,先将读者的思路引向与主旨相反的方向,然后突然扭转到诗人力图表达的正确的方向上来,因而获取新奇独特、深刻有力的效果。
这种手段在《鸟笼》一诗中用得最为精彩:
打开
鸟笼的
门
让鸟飞
走
把自由
还给
鸟
笼
谁读了此诗都会极其惊奇和感叹。采用笼中鸟以喻失去自由是一个相当古老而平常的意象,但在非马看来,把鸟笼打开,让鸟飞走,这不仅是把自由还给鸟,更是把自由还给鸟笼。诗人怎么想到强调后者,而且这么强烈?!这真是画龙点睛的惊人的神来之笔!这样寓意不凡的“反逆思考”,真让人叫绝。
这就开拓了审美与思考的另一空间。这是一种双向的冷静的审视。在一般人的眼里,“鸟笼”是自由的、主动的、掌握别人命运的。但现在非马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浅薄的。事物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又互相制约的动态系统,而不是绝对单一固定、不与他者发生任何关系的存在物。鸟被关在鸟笼,鸟固然失去了自由,鸟笼也失去了自在的自由,不自由是双方的。许多论者都指出,以此哲理来审视人生现象,便会因诗人新奇的想象的触发而引起多重的联想。可以把“鸟笼”和“鸟”的形象看作哲学上的代号,象征两个互为依存互为对立的事物,并尽可以见仁见智,将它们解读为诸如灵与肉、理智与感情、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奴役、社会与个人、人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的自足的本性、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等相反相成的概念。的确,顺着这个思路,人们其实可以恍然大悟:当社会中的某一层次、某一部门、某一领域的人自觉或非自觉地担负起监视、限制、管教另一层次、另一领域内的人时,实际上他们也走上了自身的异化,他们同时也失去了本身应得的自由。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非常清楚,禁锢的施加者在钳制他人的过程中,其实自己也往往陷入无形的囚笼;唯有松解禁锢,还他人自由,禁锢者也才能走出自囚的牢笼。没有自由便没有和谐——这是起码的真理。
非马诗歌意象简练,却又内涵深广丰富,决定了人们对其诠释和演绎的多元化,《鸟笼》一诗是一个最好的标本。这首杰作写于1973年3月17日,在台湾地区《笠》诗刊第55期(同年6月15日出版)发表后,在台湾引起轰动,后来还入选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编注的《国文选》。此诗一直是海内外论者品评非马作品的一个重点,被看成是“反逆思考”或“多向思考”的经典性作品。
许多年之后,非马又写了两首相关的诗。前者是写于1989年4月27日的《再看鸟笼》,同年7月1日发表于《自立晚报》副刊。他这样再看鸟笼:
打开
鸟笼的
门
让鸟飞
走
把自由
还给
天
空
另一首是《鸟·鸟笼·天空》,写于1995年2月2日(同年10月发表于《新大陆》诗刊第30期;10月21日发表于“中央”副刊)。诗这样写道:
打开鸟笼的
门
让鸟自由飞
出
又飞
入
鸟笼
从此成了
天
空
关于《鸟·鸟笼·天空》,非马告诉我,这首诗是为一位在美国南部一个小镇上经营杂货店的诗友写的。他为日夜被困在店里而烦躁痛苦不堪,我劝他调整心态,打开心门,把它当成观察社会人生的小窗口,同时偷空写写东西。后来他大概还是受不了,干脆把店卖掉搬离小镇,到休士顿去过寓公生活。在《再看鸟笼》附记中,诗人让人很出乎意外地写道:多年前曾写过一首题为《鸟笼》的诗。当时颇觉新颖。今天看起来,仍不免有它的局限。因为把鸟关进鸟笼,涉及的绝不仅仅是鸟与鸟笼本身而已。非马何以将业已还给了鸟笼的自由收回,改而还给天空?正如居住旧金山的美国华裔诗人刘荒田认为,非马是把鸟笼放到广大的背景——天空去了,天空的自由,是靠鸟的自在飞翔来体现的。因此,鸟笼剥夺了鸟的自由,归根到底是剥夺了天空的自由。
非马原名马为义,取笔名“非马”,是开玩笑说自己是人不是马,也免不了让人联想到“白马非马”这一个典故,但最主要的是含有跟他诗观相关的更深层的意义。他希望“在诗里表现那种看起来明明是马,却是非马的东西。一种反惯性的思维,一种不流俗的新诗意与新境界的追求与拓展”。他对自己诗写的追求就是:“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
所谓“比现代更现代”,我觉得主要是他营造意象的手法非常现代、非常新颖独特。人们发现,非马诗中的意象大都单一、纯净,他绝不做烦冗的堆叠,他执意让意象压缩、跳接,让意象产生非确定性与多层意义,使他的诗歌获得外部形貌简约而内部意蕴丰富的诗美。顺便说,正因如此,他的诗译成外文时,可以和中文原诗一样完美,既没有杂质糅入,也不会让原味消失。还有,他有意识地反逆人们平常的观物习惯思维习惯,这是他求新的独特方式。他要从平凡的事物中找出不平凡,从而制造惊奇。创新虽为艺术的普遍法则,但通向“新”的道路却因人而异,从这里往往显示出作者的独特风貌,其高低雅俗,深刻或平庸,一比便了然于心。刘荒田说,他在解读上述这三首诗时,不禁想起了禅的三个境界,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确,就这三首诗来看,通过诗人营造的意象,诗的意境,诗的境界,层层递进,每层都有独特的风光,实在是迭生惊奇,令人把玩不止。许多人都说了,非马的诗歌作品都充满着强烈的生命感及隽永的哲思,简洁纯朴的形式,负载着多重含意及可能性,常予人以意料不到的冲击。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专有名词:“非马意象”。
二、民族悲剧深深渗透的诗心
非马的价值,在艺术手法技巧之上的,是其“比写实更写实”所表达的深刻的思想性。就让我们从他写于1981年的《罗湖车站》(返乡组曲之八)说起。当年,他经过中国广东省深圳和香港边界的罗湖车站,写下这首兼具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诗篇: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她老人家在澄海城
十个钟头前我同她含泪道别
但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
像极了我的母亲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他老人家在台北市
这两天我要去探望他
但这拄着拐杖的老先生
像极了我的父亲
他们在月台上相遇
彼此看了一眼
果然并不相识
离别了三十多年
我的母亲手挽包袱
在月台上遇到
拄着拐杖的我的父亲
彼此看了一眼
可怜竟相见不相识
非马1936年生于台湾台中市,不久随家人返回祖籍广东潮阳,1948年再到台湾,1961年到美国,迄今一直住在芝加哥。而他的双亲,至写此诗时已经离散30多年,一个住在台湾台北市区、一个住在广东澄海县城。显然,他的家庭,又是时代悲剧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正如《罗湖车站》所揭示的深层含义。
非马在罗湖车站看见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像极了他的母亲父亲。这也许不过是他潜意识的幻觉。因为他多么希望他们是他的父亲母亲,多么希望他们能在同一个月台上相遇。但是,他立刻想到,他父母亲即使真的相遇,彼此也只会视同陌路,失之交臂。全诗语言通俗浅显,但意境却非常深沉凝重;白描淡写的诗艺相当传统;亦幻亦真甚至荒诞的意象却很现代。虽是写一家平民百姓30多年的离愁别恨,但是,谁又能认为诗人仅仅是表现自我一家的命运呢?诗人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希望和失望、无奈和悲哀,显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代表了由于两岸分离而骨肉长期离散的千万个家庭。这一幕以边界的罗湖车站大舞台演出的悲剧,饱含着诗人真挚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
《罗湖车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文坛兴起的“探亲文学”热的先声之作,堪称“探亲文学”的序诗。而在写作《罗湖车站》之前,于1977年,也就是非马在刚刚跨过40个如梦春秋之后,诗人更写出曾被许多浪迹天涯的华夏游子奉为抒吐乡愁的经典之作的《醉汉》:
把短短的直巷
走成一条
曲折
回荡的
万里愁肠
左一脚
十年
右一脚
十年
母亲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来
此诗把醉态十足的写实与乡愁无限的写意巧妙地结合起来。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这个借酒浇愁的游子,离家门近时却寸步难行。“短短”的巷子,竟然有“万里”愁肠的心酸。“巷子”与“愁肠”的比照,把走近门口将要与亲人相见的一段历程强化了。诗末尾的一字一句,更暗示了步履的艰难,以及路程的遥远和时间的流逝。这种近乡情怯的醉态,极为令人黯然神伤。
非马特能致力于刻求表象以外的意境。因此,一条巷子竟是万里愁肠,一脚竟然十年,这是超现实的非写实,但又比写实还写实。人们不禁对这首诗作多重意义的理解。所谓“醉汉”,可以是真正醉酒后酒入愁肠而怀乡,也可以是表现因思乡情切以致迷离恍惚,如醉如痴;其醉态可以是实写走近家门的一种心情,也可以是表现醉汉般恍惚迷离的幻觉。许多人更是把《醉汉》看成一首寻根诗,诗中的“母亲”象征诗人魂一夕而九逝的祖国。这样,“醉汉”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流落异乡的游子,这还只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而这表象的内涵是抒发和反思民族分裂的乡愁。人们阅读此诗时,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当时已经冰封了几十年的台湾海峡。这“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的漫长艰难的步伐,正是动荡年代的象征性意象,蕴含着咫尺天涯的悲剧意识。而“我正努力向您走来”,是对母亲的倾诉,也是对祖国的倾诉,倾诉抑制悲情叩开乡关的努力,倾诉摆脱内心困境和外界现实阻挠的曲折的努力,倾诉时代的悲剧、人生的悲剧……
非马一次回答提问的时候,说出一段意味深沉的话(贝《答问》,刘强著《非马诗创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写诗是为了寻根,生活的根,感情的根,家庭和民族的根,宇宙的根,生命的根。写成《醉汉》后,仿佛有一条粗壮却温柔的根,远远地向我伸了过来。握着它,我舒畅地哭了。
《醉汉》这首仅仅只有40个字的小诗,正是诗人洒下的一枕怀乡梦国的清泪,这首经典式作品的每一个字,都具有金石般的分量。甚至可以说,它的意境和象征,堪比一部史诗,一部长篇巨著。它把具体的现实性与严酷的历史感深刻地统一起来,那种酸甜苦辣的心头滋味,那种回肠荡气,直达心灵,震撼心灵。
非马写作《罗湖车站》时,罗湖车站几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接触的仅有的交汇点,而事实上那时海峡两岸的亲人还得不到从这里进出的“来去自由”。至于写《醉汉》时,中国“四人帮”刚刚倒台,开放改革的国策更是连影都没有。今天,三四十年过去,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怜竟相见不相识”的现象可能没有了——该相见的大都早就相见了,或者来不及相见早就去世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远未结束。“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这种悲剧还在继续。澳华作家杨恒均曾在北京当时的《天益网》上发表了一篇他于2007年12月29日在台湾台中市亲身实地考察后写就的随笔,标题是《台湾海峡为什么越来越宽?》,这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的文章对台海两岸状况感慨万千。因此,即使今天,相信每一位吟读非马《醉汉》和《罗湖车站》等诗作的人,还会禁不住低回反思,感叹不已。
三、民族苦难的根源何在?非马的探问
黄河与中华民族紧密联系。这条古老的大河承载着华夏历史,也见证着中国人的苦难,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和苦难汇聚的河。我注意到,非马作了两首《黄河》。
前一首溯“源”,作于1983年4月5日,最早于当年7月22日发表在台北的《联合副刊》:
溯
挟泥沙而来的
滚滚浊流
你会找到
地理书上说
青海巴颜喀喇山
但根据历史书上
血迹斑斑的记载
这千年难得一清的河
其实源自
亿万个
苦难泛滥
人类深沉的
眼穴
此诗两节,第一节运用极为写实的手法描绘了黄河挟泥沙滚滚而来的气魄,但在第二节诗结尾处却用超现实的幻觉手法,把黄河的源头写成亿万个人类苦难泛滥的眼穴。地理书上的“源”和历史书上的“源”,两相比较,得出诗人的独特发现——发现被俗常目光埋葬了的诗意。这样,如论者指出,就跳出了“实像”的河,不落于一般写黄河的旧窠臼,甚至包括习惯的“母亲”意象,而进入了“灵”的层次:人类苦难历史之“河”,出“虚”,肉眼不可见。原来,“苦难”之“源”,如“眼穴”意象所喻示,是“人为”的,是历史上各种腐朽罪恶的专制制度造成的。
后一首析“流”,反而是先作的,1975年1月12日写成,最早发表在《笠》诗刊第70期:
把
一个苦难
两个苦难
百十个苦难
亿万个苦难
一古脑儿倾入
这古老的河
让它浑浊
让它泛滥
让它在午夜与黎明间
辽阔的枕面版图上
改道又改道
改道又改道
诗人不直接写从黄河中看到了苦难,而是“把”苦难“倾入”,突出了苦难的积压,突出表明了这条河自古以来就是一条承受苦难的河。“苦难”的量化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数的量化。从“一个苦难”到“亿万个苦难”逐渐递增,表现了从个人到民族,从时代到历史苦难的普遍和久远。“苦难”的反复重叠几乎就像一座在成长的大山压过来,最后发展成一个种族的记忆,让全世界的华人都会联想起母亲河的灾难,灾难的场面与情绪:战争烽火、黄水患难、流离失所、无穷哀怨……
第二节则突出剖析“苦难”之“流”。这里用了三次“让”这个词,就像上节“把”苦难“倾入”一样获得同样的效果。诗末“改道又改道/改道又改道”的意象叠加最为使人震撼。这不仅仅在于抒发情感,而是要唤起读者强烈关注问题的严重性。自以为是的人类把追求表面的发展看为第一要务,一直在糟蹋黄河一直在糟蹋自己的居住环境。这个叠加的意象,紧扣历史和现实。对“苦难”实行“改道”的苦难,只是使“苦难”一再加码,而“改道”却不改其“辙”,只是重复历史的回头路。真是令人深思!
两首《黄河》是大气深沉内涵丰富的诗章,具有雄性的美学特征,具有厚重的时代感和历史感。非马在1982年还写了一首题为《龙》的诗,外表看来和《黄河》很不同,但我发现其思想内涵是共通的:
没有人见过
真的龙颜
即使
恕卿无罪
抬起头来
但在高耸的屋脊
人们塑造龙的形象
绘声绘影
连几根胡须
都不放过
非马这首《龙》,是一首小诗,仅有10行共49个汉字,但它显示了非马诗作强烈的社会性,而且别具一格,而且甚具深意。如论者所言,诗一开头,诗人便以突兀峭拔的否定语式将龙这一千古神物推上了曝光台,这种开门见山式的表达,如一把利剑,一下子戳穿了东方文化尤其是华夏文化的神秘面孔。的确,只活在古老的传说之中的“龙”,有谁见过它的真容呢?即使是“恕卿无罪”的所谓真龙天子,也只是古代和现代的迷信而已。然而,构成强烈的反讽的是,人们却偏偏四处塑造龙的“光辉”而且具有威吓性的形象,连“几根胡须都不放过”,就像世人创造“神”然后对其顶礼膜拜,中国人也创造“龙”以作为顶礼膜拜的神物。这不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异化吗?今天“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尊贵的图腾。虽然“龙”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积淀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但谁能否认,“龙”最重要的是象征权力、专制、绝对命令——龙是天上的权威,自命的真理,高高在上。如果说古老的华夏历史最初有一个自由的龙羊对立而又共处的时代,那么,后来就进入了龙愚弄、统治、奴役羊的大一统时代。非马这首诗,如一声洪亮的警钟,将人们从以“龙”为内核的那种负面传统文化所衍生的虚妄与自傲中震醒过来,让人仿佛觉得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都在震颤。诗人在这里赋予诗的意象以民主与科学的哲理思考的内涵,对迷信和愚昧予以鞭挞,毫无疑问具有值得称赞的时代精神和当代意义。
四、弘扬人道主义 承传终极关怀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说说。
1978年,非马从美返台,在一次谈及“理想中的好诗”时,明确指出:“对人类有广泛的同情心和爱心,是我理想中好诗的首要条件……对一首诗我们首先要问,它的历史地位如何?它替人类文化传统增添了什么?其次,它想表达的是健康积极的感情呢?还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对象是大多数人呢?还是少数的几个‘贵族’?”(贝莫渝:《诗人非马访问记》,《台湾日报》副刊,1978年9月1日;《笠》诗刊第89期,1979年2月15日)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非马通过自己的作品建立了一个值得称颂的艺术世界,这是一个富于正义、充满人性的世界。
让我们读读他写“给濒死的索马利亚小孩”的《生与死之歌》:
在断气之前
他只希望
能最后一次
吹胀
垂在他母亲胸前
那两个干瘪的
气球
让它们飞上
五彩缤纷的天空
庆祝他的生日
庆祝他的死日
这首写于1992年8月15日,同年首先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0月号和台北10月27日《人间副刊》的诗,是一篇催人泪下的作品。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饥荒中的非洲儿童,那种眼大无神,形销骨立的画面,使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睹。非马的这首诗,正是以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为主题。这个索马利亚小孩临死前,渴望母亲的乳房能胀满奶水,甚至饱满得像要腾空高飞的气球。把乳房比作气球,真是奇思妙语,却符合小孩天真的幻想,表现了他对果腹、对生存的强烈渴望。诗最后用“生日”和“死日”对称,从而把悲剧气氛推向高潮,成为撼动读者情感的巨大的冲击波。诗人写出一个天真却是濒死的小生命,那么渴望美好却又那么幼小、孱弱,那么短暂的生命,充分显示了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非洲儿童的深切同情,深刻地实践了自己对诗歌的“社会性”的承诺。
由于地理条件的恶劣,再加上人为的因素,特别是统治者贪婪腐败又治国无能的因素,非洲一些国家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战乱频繁,饥馑连年,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人们说,非洲是“被上帝遗忘”的地方,那么,像是美国,这个“上帝给以青睐”的地方,就没有悲伤吗?居住在这个国家的非马,以他的诗歌明确告诉我们,悲剧到处都会发生。
这是他写于1985年的《越战纪念碑》:
一截大理石墙
二十六个字母
便把这么多年青的名字
嵌入历史
万人冢中
一个踽踽独行的老妪
终于找到了
她的爱子
此刻她正紧闭双眼
用颤悠悠的手指
沿着他冰冷的额头
找那致命的伤口
这是一个具体的场景:一位老妇在碑石上寻觅无可寻觅的爱子,她把冰冷的大理石幻觉成爱子的“冰冷的额头”,而且硬不死心地要找出“那致命的伤口”。这种哀伤臻于极顶时的痴心妄想虽然无言可是却发散出强大的控诉力量!正如论者说,这首诗所突现的心态情感极富现代人的时代特征,又由这时代特征而在历史进行中获得了时空纵深感,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这首具有“现代感”与“历史感”双重性质的诗章,统领大时代的风雨硝烟,统领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统领无数亲情的悲歌。
如果说,非马对母国文化的无限依恋凝成他创作心理上的民族情结,那么这种对全人类的关切热爱意识便是他的“人类情结”。他的诗中,常常出现意蕴的层层递散与深化,由一己、一家而推及全民族以致全人类,这不但是民族情结的漾散、扩张,而且是它的升华与入化。
对于人类,为祸之烈,莫过于战争了。诗人对于人间这个散布仇恨、自相残杀的魔鬼深恶痛绝。《越战纪念碑》是对于“人类文明一种自身反省”的卓越贡献。它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它像警钟一样将告诫悬挂在人类的头顶之上:远离战争,不要以任何借口去触摸战争。
非马以《电视》荧光幕隐喻人类奇诡并可悲可叹的记忆——即使对最受诅咒的战争:
一个手指头
轻轻便能关掉的
世界
却关不掉
逐渐暗淡的荧光幕上
一粒仇恨的火种
骤然引发
熊熊的战火
燃过中东
燃过越南
燃过每一张
焦灼的脸
荧光幕上一粒小小的荧光,会逐渐展现世界,而一粒“仇恨”的火种,也会“骤然引发熊熊的战火”。战火会燃至世界任何一个地域,这些会不断地改变,但只有一种是不受肤色、种族、国籍的限制而改变的,那就是“每一张”受难的焦灼的脸。这是“关不掉”的真相。但是有些人就是想关掉,像关掉电视机一样,动用一个手指头,轻轻便把“世界”关掉。事实就这么残酷。人类就这么愚蠢。《电视》这首诗的讽喻,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社会的关切和批判。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倡导“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是对人存在的根本关怀,同时也体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它与自由、民主、博爱、科学等当今普世价值是相通的,都是超越一切民族、语言、肤色的差异,超越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和社会体制的差异,超越一切时代和地区的差异。我们从非马的诗章中,也分明看到中华文化的终极关怀的承传与当今普世价值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