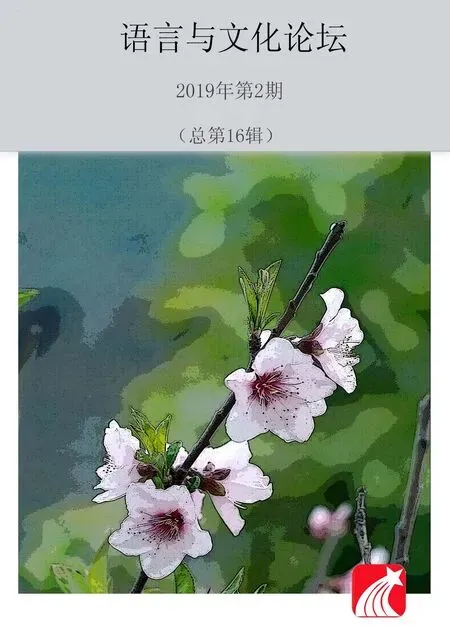植物·器物·人物
——毕飞宇《枸杞子》的生态解读
2019-03-03闫建华王旭群
◎ 闫建华 王旭群
无论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还是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都是典型的文学地理景观。毕飞宇在《枸杞子》中描绘的王家庄同样也是如此。尽管《枸杞子》(1994)只是作者发表在《作家》杂志上的一个短篇,但若将其置于作者构建的王家庄这一整体文学地理空间中来看,它除了首次推出带有毕飞宇标签的王家庄这一地理景观之外,还与作者后来专注“文化大革命”和“鬼文化”的王家庄系列作品(如《地球上的王家庄》《玉米》《平原》等)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比照。相照之下,《枸杞子》中的王家庄还透着一种厚重的生态关怀,并通过植物、器物、人物的交织互动来表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所经历的生态困惑与抉择。本文拟紧扣植物、器物与人物,从原生态自然的再现与破坏、探索者的盲目与悲剧以及自然的“复魅”与未来乡村的生态之道等三个方面对毕飞宇的《枸杞子》进行解读。
一、原生态自然的再现与破坏
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说:“《枸杞子》是色彩斑斓的。汪政晓华说我喜欢炫技,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小说给他们的印象。我喜欢华美,用华美去展示悲剧,有一种说不出的凄艳。”①作者所“展示”的“悲剧”之一便是王家庄原生态自然的破坏。在被破坏之前,王家庄的生态自然就像是一幅风景画,村民就是风景画上的人物。小说题名中的枸杞子和小说人物父亲从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示”出王家庄美丽的自然风景画卷:
父亲进城以前采了两筐枸杞子,他用它们换回了那把锃亮的东西。父亲一个人哼着《十八摸》上路,鲜红透亮的枸杞子像上了蜡,在桑木扁担的两侧随父亲的款款大步耀眼闪烁。枸杞是我们家乡最为疯狂的植物种类,有风有雨就有红有绿。每年盛夏河岸沟谷都要结满籽粒,红得炯炯有神。大片大片的血红倒映在河水的底部,对着蓝天白云虎视眈眈。②
蓝天白云、清澈河水和鲜红透亮的枸杞子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风景图,再加上肩挑桑木扁担、一路山歌不断的父亲这一人物,王家庄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枸杞子,其明艳的色彩和生机勃勃的长势通过“耀眼闪烁”“炯炯有神”和“虎视眈眈”这样的字眼得到形象地呈现。这样的“华美”除了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之外,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唤起读者的文化认同感。从《诗经·小雅》的“言采其杞”到陆龟蒙等人先后所作的《枸杞赋》,枸杞子所代表的采集文明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生态自然一代代延续至今,它貌似原始落后,实则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活力的根源所在。
与枸杞子的透亮和亲切形成对比的是父亲用枸杞子换回的“那把锃亮的东西”,也就是小说中象征工业文明的重要器物——手电,它的金属外壳给村民一种陌生的冰凉感,并为勘探队的到来和盲目开采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就手电本身而言,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王家庄的原生态自然造成不小的冲击。当村民们得知父亲从城里换回了手电,便纷纷聚在皂荚树下想看个究竟。当手电在“每一颗星都干干净净”的清爽夏夜被打开时,这道不属于自然的光“横在了院子中间,穿在大门钉在院墙的脊背上”,吓得皂荚树上的栖鸟“带着长长的哨声彗星一样划过”夜空,冲击着乡村夜晚的自然静谧。③
手电的光束除了惊吓到皂荚树上的栖鸟,还给王家庄村民带来某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当母亲问父亲手电里头是什么的时候,父亲回答说:“是亮。”④对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而言,手电所指涉的另一个“亮”的世界无疑充满了诱惑,尽管这仅仅是一个有局限的光。这也就是说,虽然村民们从手电照亮的夜空中瞥见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希望,但在希望之余,他们又体会到一种“面面相觑”的、无知、无能和无助的沮丧。⑤
但与勘探队带来的冲击相比,手电对王家庄自然和人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支所谓的石油勘探队在抵达王家庄的当天就开始轰炸钻井,可在这之前他们并没有经过任何调研和实地勘察。尽管村民们对此十分不满和不解,但勘探队队长为他们描绘的愿景消除了他们的不满和疑虑:“村子里到处是电灯,像枸杞树上的红枸杞子一样多。”⑥就连水里都可以装上电灯,届时“每一条河都是透明的”。⑦这就是勘探队队长所说的“科学之光”,而这“科学能使每一个人都变成神仙”。⑧受其蛊惑,王家庄人开始想象电气化时代的美妙前景,父亲还因此对勘探队队长说:“你们随便打,除了大闺女的床沿,你们哪里打洞都行。”⑨勘探队队长的盲目自夸和村民的盲目崇拜,最终导致了王家庄原生态自然的严重破坏:“即将收割的水稻和正值成长的棉花被踩得遍地狼藉”,⑩清亮透明的河水变成了深不可测的墨绿色,鲜活的水生动物逐一死去,以致“河里没有再死鱼,因为河里已经没有鱼可以死了”。[1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依据科学的解释,勘探队四处寻找的石油本身也是源自自然生命的产物,是植物和动物经过千年万年的沉积形成的产物。勘探队的盲目开采貌似与自然毫无关系,实则也是一种离不开自然的“科学”行为。
同《枸杞子》中的王家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在《平原》里描绘的王家庄,那里的“水稻长势更好”,人们更加讲究“天时”,井然有序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和收获。[12]吴景明指出:“生态文学观念下的文学图景可能不再是矛盾深重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和谐共存。”[13]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在《枸杞子》中还体现为人与动植物之间的那种“共通”性:大哥追求北京的神态像一颗麦穗,北京在柔桑下撒播着狐狸一般的目光,她在夜里的游走如同鱼一般,甚至连村民们对高楼大厦的想象都“永远离不开水稻生长的姿态”[14]。遗憾的是,这种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和谐共存”在《枸杞子》中却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一旦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态也会遭到相应的破坏。我们看到,在河水被污染之后,王家庄村民“以恐怖和绝望的心情看着河里的墨绿光慢慢地变暗,最后消亡”。[15]随后,小说中唯一有名字的人物北京也在这条被玷污的河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进一步表明人类与自然之间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依存关系。
二、探索者的盲目与悲剧
王家庄的自然生态之所以遭到严重破坏,这与探索者的盲目是分不开的。吴义勤在论及《枸杞子》时指出:“《枸杞子》中的生存‘错位’始于勘探队的到来和父亲的‘手电筒’,而北京的与人私通以及被谋杀则是这出‘近乎无事的悲剧’的‘死水微澜’,它对应的是人性的麻木与萎缩。”[16]文中提到的勘探队队长、父亲和北京这三个人物不仅折射出整个王家庄的生存“错位”,而且也表征着中国乡村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走过的那段并不平坦的探索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三位人物也堪称中国乡村的探索者,尽管他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我们先来看两位男性探索者。总的来看,他们都是王家庄在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蒙昧与科学发生直接或间接碰撞的核心人物。有学者将《枸杞子》中的父亲形象与《写字》《地球上的王家庄》等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混为一谈,认为他“受权力压制且处于极度压抑和沉默寡言的状态”。[17]《枸杞子》中的父亲显然并非如此。他不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杀过人而在村里颇有威信,而且还因此成为披红戴绿的“英雄”。当勘探队刚到村里开采石油时,村民们坚信“只有杀过人的父亲能够阻止他们”,于是父亲又顺理成章地成为王家庄的代言人。[18]起先,父亲对勘探队的态度也是拒绝的,可当勘探队队长“用科学论证了石油和马路汽车的关系,尤其强调了石油与电的关系”之后,父亲对勘探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他开始意识到,石油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它所发出的科学之光是一切追求的精髓所在。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父亲对科学的认知完全来自勘探队队长这位科盲,一个看似掌握着科学但却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外乡人:
他说,石油就是电。有了石油,村子里的所有树枝上都能挂满电灯,也就是手电。月亮整个没用了。村子里到处是电灯,像枸杞树上的红枸杞子一样多。电在哪里呢?——电在油里头;而油又在哪里呢?——油在地底下。队长说,这是科学。[20]
对于连手电都没有见过的王家庄村民来说,勘探队队长讲述的“科学”道理和描绘的光辉前景无疑迎合了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希冀。他们对科学的无知和憧憬充满了民间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殊不知这位画了“大饼”蓝图的勘探队队长自己却是一位盲目的践行者。他未经科学论证,在进驻王家庄的当天就带领勘探队打洞“开采”,此后一直没有停歇,致使王家庄的庄稼、河流、生灵遭到涂炭,而他所吹嘘的神奇的石油却始终不见踪影,“只剩下孤寂的爆炸和伤感的回音。”[21]
勘探队队长的所作所为及其必然的失败使王家庄人逐渐从懵懂中醒悟过来,他们对电气化的热情也开始消退,唯有父亲依然站在勘探队一边,对其毫无章法的开采行为深信不疑,即使当他在“黑洞洞的井底”看到的是“一无所有”的、黑暗的“科学”时也是如此。[22]这种“黑洞洞的井底”或曰“黑暗科学”不正是父亲和勘探队队长盲目探索的一种写照吗?父亲所理解的科学无疑是十分幼稚的,而仅凭“电”和“石油”等科学术语忽悠村民的勘探队队长也是一个十足的科盲。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父亲和勘探队队长不仅对自己所理解或掌握的科学深信不疑,而且还以权威的身份来左右其他村民,使自己成为王家庄理所当然的、盲目而可悲的探索者。与其说他们比其他人更迫切地希望实现用电灯代替月亮的“宏伟”蓝图,毋宁说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也使之骑虎难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毫无成效且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现实面前依然坚持“探索”的理由所在。
父亲与勘探队队长盲目的个人英雄主义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开发矿业”运动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对它的一种遥响。据记载,彼时的地质工作者都把“为祖国寻找宝藏”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红遍大江南北的《勘探队员之歌》就是最好的明证。如果说彼时的地质工作者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在《枸杞子》中,读者看到的却是勘探队对地质勘探工作的盲目蛮干。正因为如此,披着科学主义外衣的勘探队注定要被拉下神坛,因为他们与父亲对科学的认知实质上并无区别。勘探队队长只看到石油开采带来的好处,却全然不懂科学开采之道,更无视盲目开采对乡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退一步讲,即使他们侥幸找到了石油,但如果因此让王家庄付出惨痛的环境代价,使其从此与青山绿水“绝缘”,那么这样的成功也是一种失败的成功。
我们再来看北京这位女性“探索者”的处境和命运。《枸杞子》中描绘的人物并不多,都是通过未曾露面的叙述者“我”来讲述,其中除了父亲、母亲、大哥、勘探队队长、山羊胡子老爹以及鬈毛小子等极具城乡特质的人物指称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这位女性人物。她是王家庄唯独有名字的人物。村民们用首都来为这位姑娘命名,是因为她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是“学校里作文写得最好的”。[23]这说明北京是一位既漂亮又聪明的姑娘。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首都北京对村民而言是严肃而荣耀的字眼,是落后的乡村只能在广播中听到的神圣之地。这种向往跟青年男子对村里最美的女子的向往和追求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北京的名字不仅彰显的是北京的个性,而且也凝聚了王家庄村民的集体想象:“‘北京’在我们想象力的最顶端,一过了‘北京’,想象力只能逃回原地。”[24]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北京被勘探队的鬈毛小子“开了”的时候,大哥以及村民们是多么震惊、愤怒和绝望!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被“开”与乡村原生态处女地的被“开”是何等的相似!北京是村里第一个试探与城里人交往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她付出的代价与王家庄的河流、鱼儿、植物(尤其是庄稼)付出的生命代价并无二致。
毕飞宇在小说中并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北京的外表有多么出众,而是反复用“狐狸一样的目光”来描绘她。[25]狐狸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并不陌生,如在《写字》和《是谁在深夜说话》等作品中,作者都对狐狸有着极为生动的描写。不论是童年经验的天真回忆还是成人深夜的哲理思考,狐狸都是一种灵性的存在,一种质疑和挑战的象征。如此看来,作者用狐狸的目光来描摹北京自然有其用意。通过人物的动物化描写,作者将北京的清纯目光与王家庄的自然生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北京的“堕落”也与王家庄自然生态的破坏之间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当北京与鬈毛小子私通被发现时,她眼里的狐狸“说走就走光了,两只眼睛变成了手电,除了光亮,别无他物”,与此同时,王家庄的自然生态因为勘探队的盲目开采也到了临界点。[26]令人玩味的是,当大哥用手电讨好北京时,北京对这发光的器物漠不关心;可当她与鬈毛小子好上之后,她眼里的狐狸竟变成了她所不屑的手电之光;而当北京眼里的“狐光”被“科学”之光所代替的时候,北京的灵气也就丧失了。
北京对王家庄的青年男子是一视同仁的,她的目光是“等距离”的,[27]也是“均匀”的,[28]独有勘探队的鬈毛小子得到她的青睐。吸引北京的或许不是鬈毛小子自身的能耐,而是他留着城市标志的发型及其所指涉的城市生活与外部世界。这与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笔下的母亲何其相似,后者把脱离小镇的梦想寄托在寄宿旅馆的男客身上,这与北京将脱离王家庄的梦想寄托给鬈毛小子的做法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母亲变成了心灵扭曲的畸人,而北京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三、自然的复魅与未来乡村的生态之道
“九十年代以后发生在乡土大地上的经济变革,使乡村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全面转型,乡村的文化形态也由此发生重要变迁,复杂的现实为当代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9]发表于1994年的《枸杞子》正是取材于中国乡村转型时期的一篇佳作,这一历史语境不仅给作者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也赋予他一种超前的批判意识,对转型时期的乡村及其生存现状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便是对乡村的盲目发展予以否定,并就中国乡村正确的发展之道予以形象的揭示。
那么作者是怎样揭示这一点的呢?我们且从贯穿小说始终的枸杞子这一重要的植物意象谈起。枸杞子是国内常见的茄科落叶灌木,其果实早在先秦时期就被广泛食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对枸杞子的药用价值有明确记载:“补精气诸不足,易颜色,变白,明目安神。”[30]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枸杞子“明目”的原因和功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枸杞子的“明目”功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手电的照明功效。手电虽然在小说中多处出现,但它并未起到真正的照明作用,而是起到一种“瞎亮”的、“盲目”的作用。小说中有两处可以说明这一点:当父亲用手电察看勘探队打出的深井时,他发现除了黑暗,井里“一无所有”;当手电掉进黑魆魆的河水中时,村民们立马认识到了它的“盲目”功效。而当手电的光照变得“盲目”起来时,阳光下的枸杞子却“红艳艳”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发挥着“明目”的作用。[31]这一点在打捞北京尸体的一段描写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当村民们“把目光从北京的尸体上转移开之后,枸杞子被一种错觉渲染得血光如注”。[32]北京的悲剧象征着整个王家庄城市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但在城市理想破灭的同时,枸杞子鲜艳的自然光亮却始终没有泯灭,亦即其“明目”功效始终没有减弱。
除了“明目”,枸杞子还具有自我修复或自我恢复的能力。在小说结尾,勘探队队长所许诺的“科学”之光已经被“祛魅”,因而他离开王家庄的“背影成了王家庄最动人的时刻”。[33]作者紧接着说:当勘探队不见踪影时,“枸杞子被浓雾乳得干干净净、水灵活现”。[34]这说明,曾经一度被忽视、遭破坏的枸杞子又一次得以“复魅”,其“水灵活现”的样貌表明,以枸杞子为代表的王家庄的自然存在具有一种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勘探队孜孜以求的宝藏并不在地下,而是在王家庄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态中。这也应了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所说的话:“技术并不能把我们从对自然的依存中解脱出来,而只是转变了这种依存的方式和特性:它使我们从某些对自然的依存中解脱出来,但是马上又建立起一些新的依存关系。树可以伸到土壤上面,但它往上长得越高,它的根在土壤中就扎得越深。”[35]
毕飞宇的小说不论是在描写都市还是乡村,都在城乡互照中探求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的理想生活。《枸杞子》如此,其他作品也是如此。在毕飞宇看来,未来乡村的理想图景并不是王家庄村民所期盼的那种三十八层高的、辉光无限的玻璃大厦,也不是以科学名义对乡村进行盲目开发的所谓的发展,而是像枸杞子一般生生不息、自然而又生态的田园画卷:
我对21世纪的希望是简单而又基本的,21世纪的水是水的样子,风是风的样子,草像草的样子,天像天一样蓝……我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每一个人都像棕榈树的叶子那样,舒展、自然、常绿,在风中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的模样。不要为了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叶子,拼命指责别的叶子没有到天空去翱翔。21世纪的太阳在天上,水在脚下,风在枝梢上荡漾。[36]
综上可见,毕飞宇在《枸杞子》中呈现出来的王家庄原生态自然的破坏及其修复并不是一曲简单的哀歌或颂歌,而是中国乡村在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发展之道的一个缩影。尽管探索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如果没有经历这样的探索创痛,人们就不会对乡村乃至整个中华大地上的青山绿水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强烈的诉求。当王家庄所经历的探索创痛最终在蓝天白云和繁星闪烁的自然生态中得到治愈时,作者其实已经形象地昭示出中国乡村在当下和未来的发展之道。这便是《枸杞子》所昭示出来的全部意义所在。
注释:
①姜广平,毕飞宇:《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花城》2001年第4期,第189页。
②④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③⑤[18]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⑥⑨[19][20][23]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⑦⑧[25][27]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⑩[14][26]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11][21][33][34]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12]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13]吴景明:《生态批评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15][32]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16]吴义勤:《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毕飞宇论》,《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第53页。
[17]鄢青:《论毕飞宇小说的权力书写》,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报告,2014年6月。
[22][28][31]毕飞宇:《冒失的脚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24]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明天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29]赵允芳:《寻根·拔根·扎根——九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流变》,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30]《中华医学名著》编辑委员会(编):《本草纲目(上下)》,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2页。
[35][美]霍尔姆斯·洛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36]毕飞宇:《沿途的秘密》,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