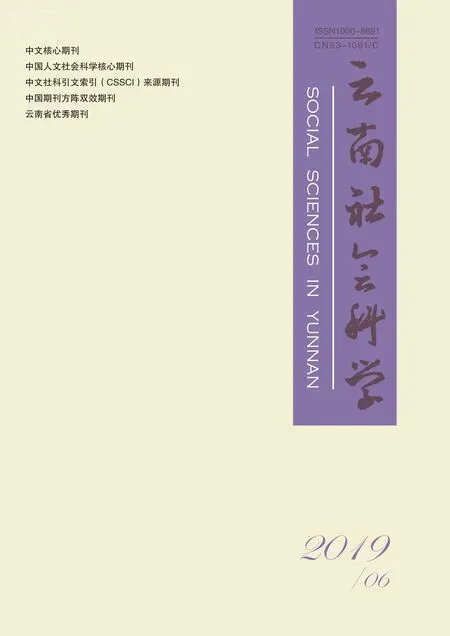公民健康权实证化的困境与出路
2019-03-03李广德
李广德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作为中国卫生与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保障公民健康权一直是这部法律的核心出发点,并在其草案中明确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权,从而即将开启中国公民健康权实证化的步伐。立法者以健康权的方式坦率地承认政府在保障公民健康需求上的国家义务,以立法决断的魄力开启了中国社会权行政法以及行政诉讼保护的先河,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在保障人民利益上的责任担当,为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卫生理念之转变以及健康中国战略建设提供了以权利为抓手的法治手段,意义深远。然而,作为传统社会权具体类型之一的健康权,因其内在权利属性和可诉性难题等理论争议而在实证化方面备受挑战,①李广德:《健康权如何救济?——基于司法介入程度的制度类型化》,《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因此,健康权的实证化首先需要面对其内涵确定性的理论挑战,这是通过立法保障公民健康权的认知前提。此外,尽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行政基本法律和行政诉讼的方式为公民的基本健康需求提供保障,无疑具有充分的政治正当性,但也必须夯实这一法律权利的宪法依据以充实健康权实证化的合法性根基,以体现“依据宪法,制定本法”②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法学家》2013年第5期。的立法原则要求。而中国宪法中是否存在健康权规范以支持法律的具体化,这也是一个需要证成的规范命题。
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公民健康权即将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所实证化,但健康权的理论基础和宪法依据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由此带来理论上的挑战和认识上的困境。为了不至于让这部基本法律中的核心概念变得空洞,避免成为仅仅只是停留在文本上的法,能够切实指导未来公民健康权的立法构建、执法实施以及司法保障,推动健康中国战略法治化建设,就很有必要对健康权实证化的困境进行梳理,为消除健康权实证化困境提出相应的理论支持,并为相关制度的设计提供必要的启示,本文就是对此的一个尝试。
一、公民健康权实证化的两重困境
从实施立法行为的形式上说,根据中国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权力结构,制定基本法律的权力是中国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基本职权,因此,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权,是其立法权的正常表现,理论上全国人大可以为公民创设任何权利义务,并不会存在正当性的危机。那么,为何要特别强调健康权的宪法基础?亦即探寻中国宪法中公民健康权的宪法基础之缘起或者必要性何在。这是因为一方面,健康权一直是一个颇受理论质疑的概念。即健康权概念本身的理论争议导致健康权实证化和法律化的正当性困境;另一方面,肯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立法原则之效力,就意味探寻宪法中的依据是立法的基础,而问题恰恰在于中国宪法文本中是否存在健康权规范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因此,健康权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依据问题,给健康权的实证化带来合法性的困境。
(一)正当性困境:健康权的概念争议
健康权的理论争议首先体现在它是否能构成一项真正的权利这个根基性问题上。学者和人权理论家们主张健康权不应被当作是一种人权,因为健康权难以被详细地定义,其权能边界的“最低标准”不明晰以及缺乏义务和社会责任的对应主体,且健康权的概念没有充分考虑到个人自身对身体所负的责任。他们进一步指出理论上,“权利”应当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相关主体需要不惜代价来维护权利;二是它是一个需要由司法机关来进行定义和解释的概念。若健康权成为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花费很多资源为民众提供此种服务,而以有限的资源来为每个人提供健康保健会使经济崩溃。因此,健康作为一种权利是不可行的,追求健康保健的财政和物资负担根本无法满足,资源的约束使得旨在无限延长寿命的权利难以证成。①See Berkeley John,Health Care Is Not a Human Right,British Medical Journal,4 Aug ,1999.大都认为提高人群健康的目标应该通过社会经济政策而不是一项正式的健康权来实现。②对健康权理论争议的详细梳理与评论,参见高秦伟:《论作为社会权的健康照护权》,《江汉论坛》2015年第8期。
此外,主张健康的权利化,也就意味着健康保障的司法化,因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既是法谚的经验表达,也是逻辑的法理穿透。司法救济是权利救济的典型方式,而这意味着法院必然会对健康资源的分配指手画脚,首先此举将导致对民主原则和分权原则的破坏。因为实施公民健康保障所需的资源分配在传统上属于立法机构的权力范围,司法机关的介入首先会侵犯立法机关的职权,其次因为法院不是民选机构,法院对立法权的侵犯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民主原则的破坏。再次,在资源分配决定的执行上,这是一项需要非常专业化的机构才能实施的事项,法院因此被认为不具备应有的专业能力,因而引发执行能力的质疑。③对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可诉性的质疑,参见秦前红、涂云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研究——从比较宪法的视角介入》,《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
(二)合法性困境:中国宪法中的健康权争议
对于中国现有宪法中是否存在公民健康权的问题,首先应当澄清的是,在中国现有宪法文本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健康权”的基本权利。因为根据现有宪法文本第三章基本权利章节的内容,除了第36条宗教信仰自由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活动之外,均无其他直接的健康有关内容。因此,中国宪法文本中是否存在现代人权意义上的健康权?即是否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和教义学构建的方法推导出中国公民享有健康权?对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有少数学者依据中国宪法文本中没有相关内容而直接否定了健康权的存在,因而进一步主张通过立宪的方式,在中国宪法中将健康权予以明确化。④参见田开友:《健康权的贫困:内涵、根源和对策》,《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杜承铭、谢敏贤:《论健康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实现》,《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多数学者主张健康权可以构成中国宪法上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在推论和主张的证成思路上,主要存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直接列举相关条文作为中国公民健康权的规范依据,如现行宪法第21条、第26条第1款、第36条第3款、第45条第1款等等。①例如王晨光:《论以保障公民健康权为宗旨 打造医药卫生法治的坚实基础》,《医学与法学》2016年第1期;焦洪昌:《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等。这种方式直接认为前述条款是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健康权条款,即通过对这些条款的体系解释,可以建构出中国宪法对公民健康权相关内容的宪法确认,从而将其确定为中国公民健康权的文本规范。但这种通过直接列举相关宪法条款作为健康权的文本规范的方式,略显简略和生硬,使得相应的宪法文本依据与健康权规范之间缺乏合理的关联;二是认为健康权是中国宪法上的一项未列举的基本权,需从其他条文中推导出来。②例如张卓明:《中国的未列举基本权利》,《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杜承铭、谢敏贤:《论健康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实现》,《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等等。而对于如何推导,解释建构的理论依据都没有进一步的展开,从而使得健康权的文本依据和规范内容更显空白。
二、正当性困境的突破:健康权的官方定义
尽管健康权遭受多种理由的质疑和责难,但滥觞于国际人权界肯定健康权的努力,在证成健康权的研究上,同样取得了很多共识性的理论,并反映在相关国际人权的文件中。③对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可诉性的质疑,参见秦前红、涂云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研究——从比较宪法的视角介入》,《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其中,联合国专门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机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即OHCHR)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08年发布的第31号情况说明书(Fact Sheet No.31)④Fact Sheet No.31: Right to Health,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Factsheet31.pdf.专门以健康权(Right to Health)为标题,对它的核心要素、规范内容以及一般争议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集中反映出了理论界对健康权的理论共识。该官方文件延续了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中的健康和健康权的定义,认为“健康不仅仅只是没有疾病或者体弱的状态,而是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福祉健全的状态……享有可获得的最高水准的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类似于“享有可获得的最高水准的健康”表达构成了健康权的实质内涵。具体而言,官方将健康权的实质内容概括为五个核心要素:
首先,健康权是一项总括性的权利(inclusive right)。它的作用范围和制度功能首先指向能影响人体健康生活的潜在因素,如食品安全、饮水安全、营养充足、卫生条件充分、工作环境友好、健康教育信息可及以及隐含的性别平等。其次,健康权包含自由权(freedoms)的面向,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免于未经同意的医疗诊断,如医疗试验;免于肉体折磨和其他非人道的、非体面的惩罚和对待。再次,健康权包含着权能和资格(entitlements),如有权获得健康保护系统为每个人所提供的平等机会来享有最高可获致水准的健康,享有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的权利,获得必要医疗的机会,妇幼保健健康,平等、及时地获得基本卫生服务,在国家和社区层面对做出有关健康决议的公众参与权等。复次,健康权本身含有不受歧视的内涵。亦即健康服务、产品和设施必须对所有人无歧视地提供。最后,所有的服务、产品和设施必须保质保量地可用(available)、可及(accessible)和可接受(acceptable)。⑤See Fact Sheet No.31: Right to Health.
根据上述对健康权的定义和内容阐述,健康权并不是要求国家直接确保每个人的身体都处于健康的状态。个人的健康状态受诸多内外因素影响,如个人的生物基因和社会经济条件等,都不受外在力量尤其是国家的直接控制。健康权指向的是要国家和政府确保人们都能享有一个健康的环境,从而为健康状态的享有提供最基本的可能和保障,如提供药品、健康设施、医疗服务等。换言之,健康权的作用方向是对人所生存的生活和生存环境进行直接调整以间接地实现人人身心健康的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健康权既具有工具性的意义,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追求。上述定义还从健康和健康权机理的角度指出,“我们自己的健康以及被我们所照护的那些人的健康是人类日常关注的焦点,健康也是所有人的最基本和最必不可少的财富”,而赋予人人享有最高能获得的健康标准的健康权,则构成人权的基础部分。因此,健康是人之所以具备权利能力的基础,健康权则构成其他人权甚至所有法律权利的基础性权利。
在健康权的权利性质和价值取向上,传统的理论常把基本人权划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健康权属于积极权利。积极权利(在宪制形态上又被称之为社会权)的定位又带来了两个对健康权的误解:一是把最高可获得的健康标准当作是一项国家长远的纲领性目标(即宪法规范类型中所谓的政策条款),国家没有法定的直接义务为本国公民提供健康保障;二是健康权的实现取决于国家的财政状况,因此对公民健康保障负担不起的国家对本国公民的健康的不负有义务。针对这两个误解,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委员会和世卫组织都予以了回应,指出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采取措施和步骤尽可能地、毫不犹豫地为本国公民提供健康保障。从原理上而言,社会权所追求的目的旨在维护人类尊严,甚至有学者指出:“社会基本权利之重心,并不在于保障人民自由,而是在保障社会安全。”①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34页。作为保障和体现人类尊严的社会基本权,自然就是国际人权条约和各国宪法文本的应然内容,而作为社会权之一的健康权“是实现公民权与行使其他基本权利的有效工具”②See M.David Low,et al.,Can Education Policy be Health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esearch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Policy and Law,Vol.30,No.6,2005.,而不健康的身心状态则会使个人的自由、自治以及其他权利的行使受到克减。健康作为公民个体的基础要素,在现代政治功能的意义上,发挥着夯实民主参与的价值。因此,健康权是人格尊严最核心的要素和前提,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心理是人拥有尊严的最起码的标志,它“通过为公民提供健康,促进了更大规模与数量的公民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促使国家治理得以有效实现”③高秦伟:《论作为社会权的健康照护权》,《江汉论坛》2015年第8期。。这种意义上健康权具有了社会治理的功能,因为健康权为公民形塑了现代政治参与中机会平等的秩序功能。如果公民因为缺乏健康医疗而导致身体或精神不适,这就在制度上“人为地”导致不平等的出现,也就在结果意义上带来社会的制度不公正、不平等。④关于健康权的法理及其价值,参见李广德:《健康作为权利的法理展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正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权的健康权对自由权的享有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健康权的国内化、法律化和国家义务的法定化才具有意义。
三、合法性困境的突破:公民健康权的宪法依据
笔者认为健康权构成中国宪法中的一项未列举权,因此,将从未列举权的角度展开对中国宪法中的公民健康权的规范论述,通过未列举权与健康权之间的关联论证,运用文本解释和教义学建构的方式,推导出中国宪法中的公民健康权之文本与规范内涵。
美国宪法第9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对于一定权利之列举,不得解释为否定或者轻视人民所享有的其他权利”,它是法官援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后宪法依据,这被认为是未列举权(unenumerated rights)理论的滥觞。不过美国宪法语境下的未列举权更多是司法操作尤其是宪法解释意义上的概念,是通过法院的解释适用发展出来的未列举权体系。⑤郭春镇:《从“限制权力”到“未列举权利”——时代变迁中的〈美国联邦宪法第九修正案〉》,《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2期。同样,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项,即德国基本法上所谓的“兜底条款”,成为保障基本权利秩序和价值的最后屏障,构成德国基本法上未列举基本权的概括和推断依据。此外,日本宪法第13条有关公民幸福权的规范也与德国类似,构成日本宪法上的“概括性基本权”⑥[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3-110页。,都是对未列举权理论的发展。
据有关学者的主张,宪法之所以在明文列举的权利之外还能推导出未列举的基本权利,是由基本权利的先验性决定的。公民的权利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法律层次、宪法基本权利层次和固有权层次。⑦李震山:《多元、宽容与人权保障——以宪法未列举权之保障为中心》,台北: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第13-15页。宪法基本权和一般法律上的权利都是对人固有权利的实在法确认,二者的区分在于各自的重要性上,而重要性的判断既取决于立宪者的主观意图,也受制于制宪时的理念和物质所能提供保障的水平,即立宪时能为宪法文本所列举或者承认的基本权利总是有限的。但本质上,基本权利“既不是造物主所赋予的,也不是国家或宪法赋予的,而是人本身所固有的”①林来梵:《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许崇德主编:《宪法学》(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宪法对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障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基本权利的不受侵犯性,换句话说,“基本权利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生命力,并不依存于宪法”②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7年,第419页。。而人民的固有权利具有自然权利的属性,应当受到宪法的保障,而这部分没有为宪法所列举的人民固有权利构成未列举的基本权。前述所揭示的健康权对于人以及人的尊严所具有的重要性表明,公民的健康权益毫无疑问应当成为宪法所保护的固有权利。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公民健康权的文本依据。
因此,如何建构中国宪法中作为未列举权的健康权的问题,就转换为如何寻找健康权的宪法文本依据问题,即现有的宪法条款中哪些规范和条文包含有健康权的规范。确定未列举权的规范内容既需要依循概念即健康权的一般理论和共识,又需要符合未列举权作为基本权的特性,前者构成确定未列举权文本的意向要素,即未列举权的规范是由作为基础概念的意向所决定的,即健康权的概念基础决定了健康权文本的意向;后者规定了未列举权文本的语境要素,即未列举权的规范是在基本权的语境之下所产生出来的,即健康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定位决定着健康权文本的确定与范围。③在哲学解释学上,意向和语境都是理解文本意义的两个标准,意向提供了文本的主体意图,语境限缩了语义的理解范围。探寻宪法文本中的健康权规范,健康权本身的法理意向和健康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功能语境相互关联,循环理解,既确立了健康权的规范依据,又限制了宪法文本空间,使得理解公民健康权规范的认识论依据建立在合理和合宪的理想基础之上。总而言之,建构中国宪法中公民健康权,须将意向要素与语境要素相互集合,循环理解。
从未列举权的作用机理来说,如果把基本权利当作一种基础性的社会资源分配资格,④秦小建:《宪法为何列举权利?——中国宪法权利的规范内涵》,《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那么一项权利之所以需要被确定为未列举权,其本质就是要使这项权利获得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参与资源分配的资格以及由此获得的配套制度保障,从而获得等同于明文列举的基本权所具有的法律地位和制度保护。换句话说,未列举权的作用逻辑和作用机制是一种拟制,即把某项未列举权拟制为列举的基本权。而这种拟制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基本权利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是因为未列举权亦要获得列举权的同样功能,才选择了赋予一种未列举权拟制的基本权利资格。故而,作为未列举权的健康权,其实质是赋予健康权以基本权利的功能,赋予公民健康权的基本权利地位,进而使得公民的健康权益能够参与国家基本权利资源的分配。那么反过来,宪法文本中能够满足健康权作为基本权利之功能内容的相关文本,在与健康权的一般法理内涵进行关联的基础上,都可以构成健康权的宪法依据。问题进而又转化为确定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在传统的基本权利理论看来,基本权利被划分为自由权和社会权。前者是消极权利,国家尊重而不得侵入,后者是积极权利,得国家主动介入和积极作为。德国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发现自由权和消极义务与社会权和积极义务两者之间的理论鸿沟,并不符合现实的情况。自由权同样需要国家履行积极义务,比如提供司法救济;对于社会而言,由于基本权利最初的制度目的是确保公民的权利免遭国家侵害,故而社会权也就天然地有着抵抗国家侵害的意义。⑤张翔:《基本权利的收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因此,任何基本权利既具有自由权面向的消极功能,也具有社会权面向的积极功能,只是不同的权利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已。功能体系的描述既适合于整个基本权利秩序,也适合于每一项单独的基本权利。因此,任何一项单独的基本权利,既具有主观法性质的防御权功能(即当国家侵害基本权利时,个人得请求国家停止侵害,且此项请求可得到司法支持)以及受益权功能;还具有客观价值秩序的功能,如制度性保障(立法机关必须通过制定法律来建构制度)、组织与程序保障(国家要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组织上和程序上的保障,建构组织体系和程序制度来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实现和救济),狭义的保护义务(即国家保护公民免受来自第三方的侵害义务以及基本权利具有对私主体之间的第三人效力等)。①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作为中国宪法中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的公民健康权,自然具有作为基本权利的上述功能体系,从而构成推导中国宪法文本中公民健康权的语境要素。又结合前述一般健康权的理论共识这一意向要素,笔者认为,中国宪法文本中的以下条款构成中国公民健康权的宪法规范依据。其具体的语境与意向相互关联的推论思路详见下表1。
由此,中国宪法中的公民健康权规范得以依循未列举权的思路和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得之关联而证成。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是:第一,上述关于健康权的内容是中国宪法文本中最广泛的健康权概念,包括了环境健康在内的内容,从而会与环境权的概念在未列举权的意义上发生一定的竞合。而在具体化的意义上,健康权的范围需要由立法者进行限缩和选择,到底选择保护多少健康权的范围,是《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所要面对的任务。第二,上述很多条款并不是基本权利规范,而是国家目标或者政策条款,而对于国家目标条款或政策条款能否推导出主观法性质的基本权利,是一个在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德国法上所谓客观法的主观化理论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目前国内公法学者尚未对此展开研究和译介。这也从侧面说明,本文对未列举基本权的论证思路,会受到宪法规范理论的挑战,从而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不断做出修正。
四、公民健康权实证化的制度表达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作为宪法中健康权规范的具体化,毫无疑问得以宪法中健康权的规范内涵为依据和合法性来源。宪法中的健康权作为基本权利,可视为一项公法上的请求权,从而可借用请求权的体系思维对上述宪法中的健康权条款所具有的规范内涵做出体系性的建构,以此作为基本医疗卫生立法中的健康权相关制度设计的依据和内容。公法中的请求权分析框架包括三个方面:请求权的主体(基本权利的享有主体)、请求权的对象(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以及请求权的内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②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落实公民健康权的相关制度亦应当包括这些方面。
(一)权利主体制度
健康权的主体问题无疑首先是公民。根据《宪法》第33条第1款,公民的宪法定义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那么问题在于: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能否在中国享受健康保障的问题。尽管中国宪法第32条第1款规定了在中国的外国人之合法权利应当得到应有的保障和保护,但健康的保障以一国公民的纳税为基础,如何合理划分外国人在华所能享受到的诸如医疗保健水准等健康权益,就需要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作出合理科学的设计,既需要照顾人道主义精神,又不违背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法律原理。此外,根据健康权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的实践,健康权除了实质内容上的最高可能获致的健康水准之外,还包括对弱势群体的肯定性权利内容。在中国宪法健康权规范上,多为对普遍公民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规定。但第45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了国家和社会保护残废军人和盲、聋、哑等残疾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等。这里的“生活”应当包含基本医疗服务在内的最低要求。残疾军人和公民构成中国公民健康权的特殊主体。这些群体的健康权需求需要得到特别的立法确认和保障。
(二)义务主体制度
与基本权利所对应的概念就是国家的基本义务,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即公民基本权利的请求对象,乃国家。这就决定了政府在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的主要责任与义务,①陈云良、何聪聪:《新医改背景下政府公共医疗服务义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这也是目前立法的基本共识。但中国健康权义务主体的特殊性表现在:第21条规定国家鼓励三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医疗卫生设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情况下,可向“国家和社会”请求物质帮助,以及“国家和社会”负有保障残废军人、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生活等保障的义务,因此,这里的“社会”是否是健康权的国家义务的主体?在“社会”的性质问题上,“社会”的实质内涵主要指社会组织,它并没有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义务,②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75页。这里把“社会”列为义务主体,应当解释为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事业,即国家和社会一起为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等,是其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应该赋予相应的经济主体权利保障的制度地位。因此,《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需要为社会组织等力量参与公民卫生和健康照护事务提供制度性的赋权,比如吸收社会资本办医和公益慈善资本参与医疗服务,开放非政府公益组织(NGO)、福利院、宗教组织等主体的办医资质等。
(三)权利内容制度
公民所能够享有的健康权利作为公民健康权的实质内涵,《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的公民健康权,应当包含以下权利内容:
第一,应当规定公民的身心健康不受侵犯。公民的身心健康不受侵犯既包括不受国家的侵犯,也包括不受其他任何第三人的侵犯;既包括身体的健康(physical health)不受侵犯,也包括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不受侵犯。在国家义务上,既要求国家尊重公民的身体健康,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侵犯公民健康的消极义务,还包括国家要建立法律制度保护任何第三人对公民身体健康的侵犯,这也是目前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有关健康权的宪法依据所在;也包括保护公民精神健康,就政府而言,主要应确保公民免于恐惧的权利。《基本医疗生与健康促进法》应当主要规定国家对公民身心健康的尊重。
第二,公民享有获得健康照护的权利。公民在疾病的时候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就是获得健康照护权的宪法依据。宪法第45条规定的“获得物质帮助”应当解释为获得医疗健康照护、医疗费用给付和其他健康服务等。对于疾病来说,必然需要获得专业人员的帮助,通过药物和诊疗技术的介入来恢复健康。因此,获得物质帮助主要指获得医疗照护和医疗费用给付。这是健康权最为核心和最实质的内容之一。医疗保险要解决的就是公民享受医疗服务对价给付的问题,通过保险的方式来为公民提供可支付的甚至免费的医疗服务。因此,《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应当规定公民的健康照护权利,并通过医疗保险制度、现代医院制度、医生制度、药品管理制度、疾病防控制度等制度加以保障和实现。
第三,公民有获得公共卫生福利的权利。宪法第21条规定了国家有义务发展医药事业和体育事业,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尤其是鼓励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从主体维度而言,这一条的规范意义已经超越了个人主体的维度,包含了宪法中公共卫生的基本要素。③See Lawrence J.Gostin and Lindsay F.Wiley,Public Health Law: Power,Duty,Restraint,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pp.1-38.因此,《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应当对公民的公共卫生权利做出确认,夯实相关内容表达。
第四,公民享有健康生活环境的权利。健康权的确立并不是要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和维护每个人都是健康的状态,而是要基于预防的角度确保健康的可能以及基于救济的角度确保不健康的状况能够得到救治和恢复,毕竟个体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的机理和规律,这也为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建设要求将卫生工作的理念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健康为中心的宪法要求。因此,提供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对于预防和保障健康而言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应当对此进行明确的宣示,以作为未来相关立法的根据。
第五,公民参与健康卫生事业管理的程序权利。宪法规定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社会事务。公民的健康权利涉及方方面面的制度设计、立法和政策制定等,必须充分保障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利。公共卫生同样需要公民参与,需要国家做出程序保障。中国未来卫生基本立法“应该注重程序性健康权的规定,保证公民的参与性”①谭浩、邱本:《健康权的立法构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为对象》,《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本文的结论在于,健康权是可以实证化的。具体来说,健康权尽管内涵丰富,存在着消极尊重和积极履行的双重面向,但健康权作为一种权利类型,完全具备实证化所要求的规范内涵,立法者的选择和立法表达足以消解其正当性的困境。就中国的具体语境而言,健康权是中国宪法文本中的一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中国公民健康权的实证化具备充分的宪法基础,从而消解中国公民健康权是实证化的合法性困境,并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相关内容提供了宪法依据和参考。
随着《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公民健康权的正式确认,明确政府基本医疗服务义务,为有关的国家机关保障公众健康权提供执法前提,为司法机关救济健康权利提供法理依据,尤其是确立以基本法律保障公民健康权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模式,将会开启全球范围内公民健康权保障的新范式。这部法律将构成了中国公民健康权法治保障的制度基础,将有利于落实宪法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的国家义务。不论是确认健康权本身的法理基础,还是评价这部法律立法的宪法依据,以及在实施这部法律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和合宪性解释,本文的工作都为未来中国公民健康权的法治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智识参考。但对于健康权具体化后的制度实践问题,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救济模式等复杂问题上的考虑,这仅仅只是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