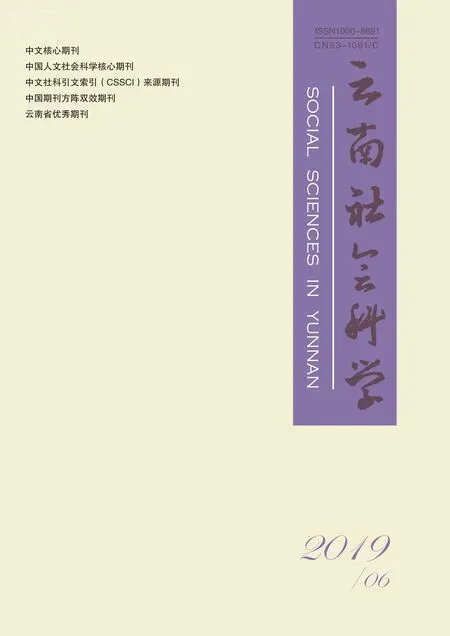论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机制
2019-03-03沈寿文
沈寿文 李 俊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修改之后,自治州不仅拥有了自治立法权,而且获得了与设区的市同等的一般地方立法权;与这种“二元”立法权相适应,存在着“二元”的立法监督机制,即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监督机制①鉴于篇幅限制和写作目的,本文讨论的自治州立法的批准与备案审查对象限于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立法,而不涉及自治州的政府规章。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监督机制。然而,2017年9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做好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撰写自查和清理的函》(法工办函〔201〕297号)要求各地要抓紧组织开展“专项自查和清理工作”,杜绝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法规(特别是单行条例)“与上位法不一致、故意放水”。其中,该函附件《有关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与国务院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不一致的情况表》涉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6年5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2016年5月)、《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2年3月)、《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1年3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松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1999年3月)、《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1997年3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1992年7月)等7部单行条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所发的函中,自治州制定的单行条例,在备案审查上被等同于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审查的是“合法性”问题(所谓“与上位法不一致、故意放水”)。这一做法是否具备法理基础,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需要在分析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监督和自治立法监督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立法监督目的的关系基础上加以解答。
二、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的规范依据
中国现行《立法法》第72条规定了自治州与设区的市享有同样的一般地方立法权,因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法律法规关于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监督的规范内容,自然适用于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监督,这些规定涉及设区的市(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批准、备案审查与撤销等内容。而自治州自治立法监督的规范内容主要体现在现行《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和国务院《法规规章备案条例》、一些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法规等法律规范中。①涉及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法规规章备案条例》以及辖有自治州的省(自治区)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程序规定或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报批程序规定。
(一)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之事前批准
一方面,就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批准的规范依据看,根据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规定,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事前(地方性法规生效前)批准,包括批准主体、批准内容、批准程序等内容。关于批准主体,与设区的市相同,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地方性法规)的批准主体是其所在省或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审查的内容,与设区的市相同,《立法法》第72条规定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自治州地方性法规是否“合法”(即与上位法是否相抵触)进行审查;关于具体的批准审查程序,一般规定于各省级具体的立法程序中,其与设区的市的立法批准程序相同:一般是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具体承担审查任务,提出审查意见,最终由省级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另一方面,就自治州自治立法批准的规范依据看,涉及批准的主体、对象、内容、程序等规定。首先,批准的主体同样是其所属的省级人大常委会,这与其一般地方立法的批准主体一致;其次,批准的对象是自治州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再次,关于批准审查的内容,自治州自治立法的批准审查的内容虽未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但根据现行《立法法》97条第二项的规定,可以推导出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批准审查的内容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违反宪法的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果存在“变通规定”,其条款是否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是否对上位法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做的规定作出了“变通规定”。该内容在一些民族地区省级的《报批程序规定》或《立法程序规定》中有所规定,比如《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定》(2016年修订)第48条的规定。②《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定》第48条第一款规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审查其是否违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是否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对不违背上述原则和规定的,应当予以批准。”第二款规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认为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行政法规、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作出的变通规定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或者违背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做的规定需要修改的,可以由有关专门委员会修改,修改稿应当征得报请机关的同意;也可以退回报请机关修改后再报请批准。”最后,自治州自治立法的批准程序规定主要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规定,一般分为党内批准和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两个步骤。
显然,从法律文本的字面上看,自治州地方性法规制定的批准规定与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的批准规定,尽管批准的主体都是所在的省级人大常委会,但是在批准审查的内容上确实存在重大区别:前者批准审查的核心是“合法性”问题,即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是否存在“抵触”上位法的情形;而后者批准审查的重点,是“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问题,即可以“抵触上位法”,但不得违背现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然而,该条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事实是否就是如此?如果就是如此,那么前文提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做好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撰写自查和清理的函》(法工办函〔2017〕297号)要求各地要抓紧组织开展“专项自查和清理工作”涉及自治州的7部单行条例,清理的重点就是“抵触上位法”,而不是“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的问题,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做法便存在问题;反之,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做法没有问题,那么该条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便不能按照字面含义进行解读。因此,该条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可能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特别需要对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机制的整体作一体系性解读,这就涉及作为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机制组成部分的备案审查规定的内容。
(二)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之事后备案审查
一方面,就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的规范依据看,首先,关于备案主体,虽然《宪法》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以及自治州的一般地方立法均没有规定备案要求,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第43条和《立法法》第98条第二、三项明确规定了由其所在的省级人大会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国务院《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3条和第6条则专门规定在其公布后30日内,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国务院备案。其次,关于备案审查的内容,按照《立法法》第72条第二款、第96条的规定,备案审查的重点是“合法性”问题,即“不抵触上位法”。再次,关于备案审查的提出与审查。《立法法》第98条规定了其应在公布后30日内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立法法》第99-101条详细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的内容。备案审查可以依职权审查也可以依申请审查,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主动审查,也可以由法律规定的主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其是否与宪法或法律抵触进行审查。最后,关于审查结果,若未违背“抵触原则”,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书面告知常委会办公厅即可;若违背了“不抵触原则”,则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向自治州地方性法规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如果制定机关按照审查意见进行修改或废止的,审查终止;如果制定机关拒绝修改的,则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撤销议案。
另一方面,就自治州自治立法备案审查的规范依据看,无论是备案审查主体、备案的提出主体与时间、备案审查的提出与程序均与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规定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备案审查内容。从现行《立法法》的规定看,自治州自治立法后的备案审查内容似乎既包括审查“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也包括“不抵触上位法”的情形。然而,如果结合现行《立法法》97条第二项隐含着的关于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时批准审查遵循“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的原则,那么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生效后的备案审查内容应当与其一致,备案审查的重点应当是“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而不是“不抵触上位法”。然而,现行《立法法》第96条又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果存在“超越权限”“违反上位法”或者“违背法定程序”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这一规定,明显是强调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备案审查内容同样包括“合法性”问题,即“不抵触上位法”。不过,一波三折的是,如果备案审查发现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内容有本条“合法性”问题,采取立法监督的措施却又回归到现行《立法法》第97条;而97条第二项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第75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则又回归到现行《立法法》第75条第二款——这一款规定的就是“可以抵触,不得违背”内容。
显然,这种绕圈子式的立法条文援引,带来两种可能的解读:一种是对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生效后的备案审查与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生效前的批准审查一致,即审查的重点是“可以抵触上位法,但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另一种则是,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生效后的备案审查与生效前的批准审查内容不一样,前者既审查是否“抵触上位法”问题,也审查是否“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如果按照前一种解读,则前文提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要求就是否“抵触上位法”专项自查和清理涉及7部自治州单行条例似乎便存在问题;但如果按照后一种解读,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这种做法便有了法律依据。实际上,上述两种解读,涉及到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的目的、立法监督难题的根源等内容。
三、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的目的
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的目的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放置到中国立法体制上讨论才能得出较为有说服力的解释。在中国这种“分工型”立法体制之下,除了特别行政区之外,中国所有地方事务均属于中央事务的范围,中央均有权介入,并不存在地方与中央在立法权限上的“分权”(Decentralization)。①沈寿文:《“分工型”立法体制与地方实验性立法的困境》,《法学杂志》2017年第1期。因此,包括自治州在内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自治州的一般地方立法(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地方立法;对自治州两种立法进行立法监督,有其共同的目的,当然也有其侧重要求。
(一)共同目的: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在“分工型”立法体制之下,整个立法体制呈现出体系严密、等级森然的金字塔结构特征,为了维护法制统一,低位阶的法律性文件不得与高位阶的法律性文件相抵触是一项核心原则。国内学术界达成共识的是包括自治州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般地方立法,应当遵循“不抵触上位法”原则,以维护国家法制体系的统一。然而,争论较大的是包括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在内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是否只是遵循“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的原则,还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应当遵循“不抵触上位法”原则。在一些学者看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不仅不用遵守“不抵触上位法”原则,而且还可以变通规定上位法,只要遵循“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的原则即可。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倒因为果,恰恰是因为现行《立法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变通规定上位法,因而,既然自治州立法可能存在抵触上位法的情形,为了防止这种变通规定(抵触上位法)超出必要范围,才需要对“变通规定”进行限制,也才有“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的规定。实际上,一方面,强调法制统一,是现行《立法法》的核心要求。就法律文本看,现行《立法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立法的法制统一原则;2001年的《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1条也强调了备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加强对法规、规章的监督”。另一方面,从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主体、立法程序等角度看,之所以将自治州自治立法的主体限制在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扩充到常委会,是因为自治立法属于自治州重大事项,只能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而客观上,人民代表大会一年通常只能召开一次,会期短,需要审议的重大事务多,自治立法仅仅是其中重大事务之一,因而,这种制度设计意味着自治立法以需要自治立法的事项重要且必要为原则。此外,自治立法的批准程序通常需要经过党内审批程序,也是表明进行自治立法需要十分慎重,更何况这种自治立法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变通规定”上位法。
按照“因为赋予自治立法以一定条件下变通规定上位法,因而自治立法时遵循‘可以抵触上位法,但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的逻辑,自治立法(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便需要考虑两种情形:(1)一种是自治立法(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条例文本内容没有“变通规定”上位法内容的情形;(2)一种是自治立法(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条例文本内容存在“变通规定”上位法内容的情形。对于前者(1),如果立法时依然遵循“可以抵触上位法,但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的原则,便与现行《立法法》第4条法制统一的原则相背离,也与中国“分工型”立法体制强调下位法不得抵触上位法的原则相悖,因而,对于第一种情形,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与一般地方立法一样仍然应当遵循“不抵触上位法”原则。对于后者(2),则应当在内容上进一步划分两类不同的条文:一类是自治立法(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文本中“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款(个别条款),自然存在合法“抵触上位法”的情形,只要遵守“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的原则即符合立法目的;但是,自治立法(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文本中还有大量没有“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款,这些条款如果也按照“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的原则进行审查,则显然违背立法目的。因此,整体上看,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是包括一般地方立法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在内的所有地方立法共同的、也是根本的目的。当然,具体到自治州的一般地方立法和自治立法的监督目的上,二者各有侧重。
(二)各有侧重:自治州一般与特殊的立法监督目的
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监督目的,是应对地方立法扩容、保障地方立法水平,从而在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的同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一方面,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后,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自治州)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立法主体剧增,①朱宁宁:《“管法的法”施行四年扫描》,《法制日报》2019年6月25日。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省级人大常委会进行事前事后把关,主要目的是“考虑到设区的市的立法主体众多、为了维护法制统一”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31-232页。。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有件必备,有备必审”的要求,使得设区的市、自治州的地方立法的备案审查处在“设区的市扩容立法”与“加强备案审查”的制度叠加区域。③郑磊:《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权:制度需求与规范空间》,《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2期。另一方面,中国地方立法的水平不平衡,需要省级人大常委会对其立法质量进行把关。④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0年,第248-249页。经过多年的实践,原先一些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立法经验,立法水平有很大提高,但立法扩容后,许多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一般地方立法还缺乏经验,立法主体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立法水平的差异。因此,对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进行事前批准与事后备案审查也是为了保障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的立法质量、立法水平,维护法制的统一。
对于自治州自治立法监督目的来说,规范自治州自治立法权、为变通规定上位法把关是自治州自治立法监督的侧重点。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权在本质上是中央(国家)对特殊地方以一般地方所没有的优惠照顾的权力(权利),自治立法权是一般地方所没有、而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之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所拥有的权力,因而,一方面,赋予权力,同时也必须予以监督和约束,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也“必须受到严格的和实际的控制”⑤秦前红、姜琦:《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立法监督》,《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行使自治立法权、尤其是在自治立法文本中“变通规定”上位法时,也应当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
显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这一立法监督的根本目标决定了无论是对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监督,还是对自治州自治法规的立法监督,重点其实都定位为“合法性”问题,即是否存在“抵触上位法”问题。对于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这种立法监督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自治州的自治立法(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监督,如果该自治立法文本中没有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文,这种立法监督的目的同样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该自治立法文本中存在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文,针对这些变通规定的条文,立法监督的侧重点应当是“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因而这种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为根本目标的立法监督在这些条款上便是特殊的例外;但是,应当强调的是,即使存在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文的某部具体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其文本中绝大多数条文并没有变通规定上位法,因而,这些部分(绝大多数内容)不能与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款一样成为这种立法监督目的的例外,它们同样应当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为根本目标。按照这种的思路,则前文提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要求就是否“抵触上位法”专项自查和清理涉及7部自治州单行条例,在原则问题上便不存在问题。但是,由于单行条例中可能存在“变通规定上位法”的例外情形,因而,实务中在对自治州单行条例的立法监督上,在区分单行条例是否存在“变通规定上位法”的前提下,如果存在“变通规定上位法”,则针对这些“变通规定”的个别条文内容,还有进一步聚焦与澄清的必要。为了进一步聚焦和澄清单行条例文本中这些个别的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文,需要进一步梳理目前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中的难点:即自治立法中的变通规定上位法应当如何进行立法监督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前提是正确理解“变通规定”在中国立法史上的变迁及其后果。
四、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难题的应对:变通规定的变迁及立法监督重点
如前所述,自治州“二元”立法监督中,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监督与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一样,重点审查“合法性”(不抵触上位法)问题;而自治州自治立法(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监督较为复杂,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关于自治立法(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文本中如果存在“变通规定上位法”情形时,应当如何进行立法监督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澄清,则涉及“变通规定”的立法史,其中《立法法》的制定和修改是其中两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性节点;按照这两个关键性节点,涉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上位法”情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前的阶段;二是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后到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前的阶段;三是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后的阶段。
(一)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前的“变通规定”及其立法监督焦点
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历部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宪法相关法都没有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变通规定”上位法的内容。“变通规定”最早出现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7条第二款中,该款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或省人民政府得依据当地少数民族婚姻问题的具体情况,对本法制定某些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提请政务院批准施行。”这一规定,开了一些单行法律(《刑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继承法》《收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森林法》等①张殿军:《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规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页。)授权民族地区(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和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份)必要时对该法律做变通规定的先河。正因如此,在学术界,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将“变通规定”作为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相并列的一类立法表现形式;②参见张殿军:《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规定研究》,第30页。而且许多学者对一些单行法律授权时条文规定的内容的混乱提出了批评。③吉雅:《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5-28页。可以说,在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前,通过一些单行法律的授权,的确存在一种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相并列的“变通规定”的立法表现形式;④张殿军教授认为,变通规定要么属于自治条例,要么属于单行条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没有除此之外的第三种法律形式(张殿军:《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规定研究》,第29-30页。)这种观点,如果指的是在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后,则是正确的;如果包括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前的情形,则是错误的。应当承认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前,由于立法行为还没有统一的规范,的确存在一些单行法律通过授权的形式产生了“变通规定”这样一种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列的法律表现形式。在立法实践中,一些民族自治地方也往往以“某某变通规定”的法规标题出台这种对单行法律某些条款的“变通规定”。
从立法监督的角度,这种直接冠以“某某变通规定”法规标题形式的立法监督,给立法监督带来了便利,即无论是生效前的审议批准,还是生效后的备案审查,重点都是在这些“变通规定”条文上。当然,前文提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要求就是否“抵触上位法”专项自查和清理涉及的7部自治州单行条例,并不存在标题上直接冠以“变通规定”的法规。
(二)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后到2015年修改之前的“变通规定”及其立法监督难题
2000年《立法法》制定后,对“变通规定”进行了规范,其结果是“变通规定”不再是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列的立法表现形式,而仅仅是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两种立法表现形式的具体内容之一。⑤沈寿文:《“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下的单行条例功能》,《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也就是说,“变通规定”仅仅是在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如果有必要,才在具体条文上“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某一规定或某些规定——尽管实践中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后,仍然有个别地方以“变通规定”的题目进行立法,对上位法内容进行变通规定,但这种冠上“变通规定”标题的立法表现形式,在性质上仍然是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比如2004年6月3日批准生效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实施〈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变通规定》,在性质上仍然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人大制定的单行条例。2000年《立法法》规范“变通规定”的意义在于:它是对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前存在的“变通规定”混乱局面的一次清理和规范。但如此一来,也导致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中,“变通规定”基本上不再出现在单行条例的名称上,而是隐入具体条文之中。由于2000年《立法法》没有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在备案时应当对“变通规定上位法”作说明,即变通规定的必要性(拟解决的实际需要)、变通规定的内容等做说明,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在立法监督时,难以直观了解到该部自治立法文本是否变通规定了上位法的条文;反过来,也导致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该部自治立法存在“抵触”上位法的情形,而且“抵触”的内容不属于2000年《立法法》第75条第二款规定的“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对上位法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的内容时,是否便可以认定为是在“变通规定”上位法,因而非属于立法备案审查应当予以纠正的内容?
显然,一方面,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出发,尽管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要求民族自治地方“变通规定”上位法时在备案时要做说明,但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机关自然并无此义务要求;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那就意味着,只要经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最高立法机关之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便是承认(确认)这种“变通规定”;而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形:如果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抵触的是省级地方性法规这样的上位法的话,只要经过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便承认(确认)这种“变通规定”;然而,如果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抵触的上位法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尽管经过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生效,但这种承认(确认)“变通规定”的行为,仍然留下危及国家法制统一的漏洞:省级人大常委会有与本省(自治区)的自治县和自治州“合谋”的可能、以“变通规定”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形式破坏国家整体利益、攫取地方特殊利益。正因如此,前文提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要求就是否“抵触上位法”专项自查和清理涉及7部自治州单行条例便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假设在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前的单行条例存在抵触上位法的情形,如果他们不是属于“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的内容,是否便可以认定为违法?可能得进一步讨论:讨论的着重点是自治州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存在变通规定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也就是说,从实务上看,对自治州自治立法(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监督的重点是,看是否存在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情形中的变通规定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
(三)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后的“变通规定”及其监督重心
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后,立法者在原先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上位法”的行为。该法第98条第三项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这一规定既是强调“变通规定不代表法外特区,它们同样应当受到备案审查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同时也是为了方便事后立法监督,“在卷轶浩繁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为了更有效率地对变通规定进行立法监督,本次修改专门增加了作出说明的要求”。①冯军主编:《新立法法·条文精释与适用指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356页。然而,这一规定,如果真的仅仅是因为“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往往条款较多,其中某些条款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出的变通规定‘隐藏’在其中,备案审查机关不易发现、比对和审查。为了提高备案审查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立法法专门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报送备案提出了说明变通规定的要求。”②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305页。从理论上说,并不必然要求民族自治地方在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制定报送批准时(比如自治州的单行条例制定后报省级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时),需要事前(生效前)专门向批准机关作变通规定的说明;但是,这一规定事实上也倒推审议批准机关在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如果有变通规定上位法时,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提供必要的说明,作为针对变通规定这个部分的内容是否审议批准的重要依据(其他非变通规定的部分,按照是否存在“合法性”问题,即是否存在抵触上位法的情形进行审议)。因此,这一规定,实际上同时在审议批准和备案审查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后,除了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因而立法监督更为严格,①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第304页。无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之外,自治州和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凡是没有在备案时“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的,可以推断为由于立法上没有变通规定上位法的主观愿望、不具备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构成要件,便可以一律视为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存在法定的“变通规定”上位法,如果条文有抵触上位法的,无论是省级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时,还是备案审查机关在备案审查中,一律按照“合法性”问题进行处理。因此,前文所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就是否“抵触上位法”专项自查和清理涉及的7部自治州单行条例中,有两部单行条例是在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后制定的,便可以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侧重于“不抵触”上位法的原则进行审查。
五、结 语
自治州尽管存在“二元”立法监督机制,但是,不仅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批准和备案审查应当遵循“合法性”的审查原则,而且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和备案审查,主要遵循的也是“不抵触”的审查原则,只有当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存在变通规定上位法时,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文才是例外——遵循的是“可以抵触上位法,但不得违背《立法法》第97条列举的情形”,而大量非变通规定的条文仍然应当遵循“不抵触”(“合法性”)的审查原则。
一方面,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批准与备案审查遵循的是“不抵触”原则。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批准的审查内容主要包括不得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应当符合适当性等要求。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批准审查遵循的是该法规与上位法的“不抵触”原则。该不抵触原则不仅包括单纯地“与上位法已有的明文规定相抵触”②周旺生主编:《立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还应当包括不得与上位法的立法原则、立法意旨等相抵触。其形式上的抵触认定应看其是否与上位法规范、原则所冲突,而实质上还要看其在实施过程中和事实范围上是否与上位法相冲突。③彭振:《设区的市立法抵触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9年第7期。
另一方面,自治州自治立法的批准审查原则,在两种情况下也同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一样遵循“不抵触上位法”原则:一种情况是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没有变通规定上位法,应当遵循“不抵触上位法”原则;另一种情况是尽管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存在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文,但是其他没有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文仍然应当遵循“不抵触上位法”的原则。④沈寿文:《“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下的单行条例功能》。值得强调的是,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不必然要“变通规定上位法”——也就是说,“变通规定上位法”仅仅是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的特殊情形,在实践中,大量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内容并没有“变通规定上位法”内容;即使在某一部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中对某上位法的个别条文作了“变通规定”,其他没有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文依然占多数。
此外,虽然自治州立法备案审查的立法目的均为维护法制统一,且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内容等均大体一致,但仍然需要区分对二者的审查内容。对自治州自治立法中的立法变通规定上位法的部分,在批准审查环节遵循的是“不违背”而非“不抵触”原则,这在备案审查部分同样适用,即对自治立法变通部分的备案审查倾向于维护其“优惠照顾”内容基础上,维护法制统一。因为对于同一部立法,批准审查是“事前监督”,而备案审查为立法的“事后监督”,二者具有承接关系,后者为前者做最后的把关。《立法法》第92条第二项规定反映了这一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经过“审查”之后,有权撤销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即在事后通过备案审查的方式对前述批准立法进行把控。若后者的审查内容、标准与前者不一致,那么将难以维持这一立法监督体系。因此,对自治州立法的备案审查,在总体上应当以国家法制统一为原则,对“依照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作为有条件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