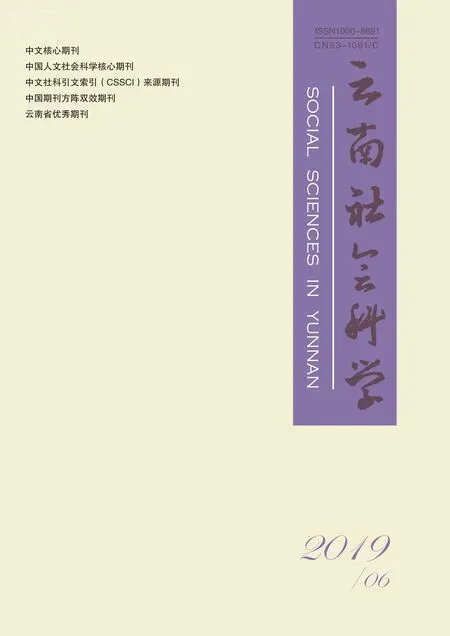技术革命演进中企业劳动关系范式的变迁与对策
2019-03-03马国旺刘思源
马国旺 刘思源
一、技术革命与劳动关系范式
劳动关系是指雇主(或雇主组织)和雇员(或工会)双方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劳动关系最早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或企业之中,即企业劳动关系。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合同逐渐普及到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导致在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和社会组织之中也出现了劳动关系。但是,时至今日,企业依然是经济社会中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因此企业劳动关系也是最主要的劳动关系形式。并且,在劳动力在产业部门间的流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机制以及劳动法规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劳动关系也会对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和社会组织中的劳动关系产生影响,使它们向企业劳动关系靠拢并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因此,下文所提到的劳动关系主要指企业劳动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核心,①范春燕:《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因而劳动关系由生产力决定并对生产力起反作用。劳动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概括为:一方面,重大科技创新会重塑生产方式,进而塑造劳动关系的具体模式。另一方面,劳动关系会制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当劳动关系和谐时,持续的技术进步、高速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而当劳动关系紧张时,劳动者或工会就会全力抵制新的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也会因罢工、怠工等大幅下降,从而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新熊彼特学派将重大的科技创新称为“技术革命”,它具有重塑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具体模式的作用。从1771年英国工业革命爆发至今,人类社会共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即工业革命(18世纪70年代-19世纪70年代)、电气革命(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和信息革命(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们即将步入的智能时代是信息革命深化发展的新阶段。人工智能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其核心投入要素仍是信息、芯片等;并且智能时代仍要继承、发展信息革命中的“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的制度体系。①马国旺、刘思源:《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机遇与中国创新政策转型》,《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年第23期。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譬如工业革命催生了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电气革命催生了福特制的生产方式,信息革命催生了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塑造了不同的劳动关系模式。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笔者将之称为劳动关系范式。每种劳动关系范式都由技术、市场和政府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塑造,并在这三方面因素的推动下演化发展。劳动关系范式既能提高企业内的劳动效率,又能确保全社会总体上的劳资和谐,因而它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和“良好的工作场所实践”等概念,以及欧洲提升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提出的“工作和雇佣质量模型”,②渠邕、于桂兰:《劳动关系和谐指数研究评述》,《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年第15期。笔者将劳动关系范式的具体内涵界定为六个方面:工作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主要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社会福利。
劳动关系范式具有共识性、相对稳定性和示范性的特征。首先是共识性。劳动关系范式是劳、资双方妥协的结果,它的六方面内涵必须有一部分有利于劳动者,另一部分有利于雇主,否则它就很难被广泛认可。其次是相对稳定性。劳动关系范式是一组制度安排,是生产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一旦发展成熟就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没有一种劳动关系范式能够永久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每种劳动关系范式都会经历探索、巩固和衰退的生命周期;旧范式的衰退阶段和新范式的探索阶段会重合。最后是示范性。在一种劳动关系范式使其领先国家取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后,其它国家纷纷模仿、效法这一范式。尽管不同国家的国情各异,同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在不同国家可能会有不同表现,但它们总体上是相似的。因此,可以参照每次技术革命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国家来归纳相应的劳动关系范式。
本文基于相关历史事实,从工作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六个方面入手,依据“生产力-生产方式-劳动关系范式”的基本框架,来论述三次技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变迁,并针对当今电气革命劳动关系范式和信息革命劳动关系范式并存的现状提出几点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今后劳动关系调节制度的转型升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
在工业革命中,生产活动一方面引入结构精巧的工具机来模拟传统手工工匠的操作,大幅减弱了对工匠技艺的依赖,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另一方面使用水力、风力、蒸汽力等替代人和牲畜的肌肉力,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妇女和儿童能够承担之前成年男性工人才能从事的工作。这种生产方式塑造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该范式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发展得最为典型,这里就以英国为例具体探讨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大致于1771年在阿克莱特的克罗福德纺纱厂中萌芽,在1847年《十小时工作制法》颁布后发展成熟,并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衰落而衰退。该范式主要具有以下六点特征。
第一,劳工被迫接受不稳定的工作,工人时刻处在对失业的恐惧之中。工作的不稳定性可归因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首先,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积累而提高,导致资本雇佣的边际劳动递减,劳动需求随之减少。譬如在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铁路公司经营每英里已完工铁路平均需要雇佣18人,但是随着铁路运营里程的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末,运营每英里已完工铁路平均只需雇佣11人。③[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51页。其次,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譬如1825年的经济危机使英国兰开郡的9万工人失业。①刘金源等:《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3-244页。但由于技能退化、工人同质化和劳工之间的竞争等,劳动者只能接受不稳定的工作。
第二,劳动收入增加,实际工资上升。从1755年到1851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34%,不同工种工人的实际工资都显著增加。在1824年《反结社法》被废除以前,英国工资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增减,增长相对缓慢。1781、1797、1805、1810、1815和1819年的英国实际工资指数分别为:39.24、42.48、40.64、39.41、46.71和 46.13。而在1824年以后,由于工会的崛起,工人的实际工资快速增长。1827年、1835年、1851年的英国实际工资指数分别为58.99、78.69和100。②赵虹、田志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从实际工资角度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尽管实际工资的增速比资本利润的增速慢得多,但是实际工资的上涨的确调动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第三,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首先,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普遍每天需要工作15-16个小时,有的工人甚至每天工作19-20小时,每周工作90-100小时。③[美]摩尔根:《劳动经济学》,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年,第167-177页。1847年《十小时工作制法》颁布后,法定工作时间仍在每天10小时以上。其次,劳动强度没有因机器的使用而减轻。尽管机器减轻了工人的体力负担,但却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去操作和看管机器。在计件工资体制下,哪怕一个走神都有可能给工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机器使妇女和儿童变为成年男性劳工的对手,迫使成年男性劳工同时操作更多机器,承担更繁重的工作。譬如19世纪30年代的普通纺纱机要求每个成年男性工人每天完成大约2200次提拉纱线的动作;而自动纺纱机则要求每个成年男性劳工同时看管两台机器,每天要完成大约4400次提拉纱线的动作。④[美]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4页。最后,工作环境恶劣且危险,“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0页。1842-1848年英国先后颁布了《矿业法》《10小时工作制法》和《菲尔登工厂法》等,这些法案限制了工时、规定了最低工资、优化了劳动环境等。⑥荣兆梓等:《通往和谐之路: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85页。但在实践中,这些法案只保护部分劳工,且经常得不到严格的执行,因而它们对劳动者的实际保障有限。
第四,管理方式采取“转包制”的模式,其典型例证是英国纺织业中的“机器操作工-接线工”制度。纺织业的工厂主直接同资历高、技术好的机器操作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支付工资,然后由机器操作工自行雇佣接线工和帮工进行生产,这些接线工和帮工通常是机器操作工自己的亲戚、邻居、孩子等。这一举措有助于解决机器大工业中的劳动供给不足问题。在生产活动中,机器操作工指挥、监督接线工和帮工的工作,并要对错误的操作所造成的损失负责。机器操作工可以通过解雇、暴力等方式威胁接线工和帮工,以确保他们的工作效率。接线工和帮工的工资比机器操作工低得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他们也可能成为机器操作工,这种对未来的期望成为接线工和帮工努力工作的动力。
第五,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让位于工厂中的“干中学”和学徒制。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孩童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形同虚设:学校教育的学习时间被灵活地安排在工闲期内,学生很容易忘记之前学过的知识;学校教师的水平也不足以承担教学工作,许多教师甚至不会拼写自己和学生的姓名;童工很早便进入工厂,其父母也要在工厂中从事繁重的劳动,这导致孩童的家庭教育缺失。在如此糟糕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条件下,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却在稳步提升,这要归功于工厂中的“干中学”和学徒制。譬如在英国的纺织业中,机器操作工要负责将生产技术教给他所雇佣的童工和少年工人。
第六,政府的福利制度缺位,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承担起福利保障职能。在工业革命时期,贫穷被看作是懒惰、酗酒、生活不节制等劣根性习性的结果。受这种观念影响,英国政府的福利制度具有惩罚懒惰的性质。1785年的《吉尔伯特法》允许农场主以极低的工资(通常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雇佣等待救济的穷人。1834年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取消了之前斯品汉姆兰制济贫法的场外救济原则,规定穷人要取得救济,就必须进入济贫院从事繁重的劳动。济贫院被马克思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其中的工作条件比一般的工厂还要恶劣,劳动报酬也十分低下。这样的政府福利制度在整个19世纪都没有明显的变化。①王章辉:《英国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14-319页。由于政府的福利制度严重缺位,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承担起福利保障的职能。譬如机械工人混合工会在1851-1889年为会员提供各种互助金和补助金,累计支出高达298.8万镑。19世纪40-60年代英国相继建立了450余个消费合作社。以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为例,工人社员们以认购股份的方式集资创办零售商店,社员凭借其在合作社商店中的消费获得凭证。每隔半年,商店在支付完经理和店员的薪水后,会将结余的利润按持股比重和消费凭证数量返还给社员,作为“分红”。
总之,上述六个特征规定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范式,即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实际工资的上升确保了机器大工业中的劳动力供给;不稳定的工作使劳动力成本不致过快上涨,并使工人被迫接受长时间的工作、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劳动环境;工厂中的“转包制”管理方式和“干中学”、学徒制的教育模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厂法案、工会补贴和消费合作社将劳资矛盾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从而避免了社会革命。这种劳动关系范式曾一度促进了英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并促成了英国在19世纪40-6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衰退、蒸汽动力甚至电力的应用、生产自动化程度提升、工厂规模的扩大,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能力大幅提升,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容易遭到雇主的侵蚀。这破坏了劳资双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并推动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走向分裂和衰退。
三、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
在电气革命中,电能逐渐成为工厂生产活动的主要能源,这对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首先,电灯、电车和高架起重机等使工厂更干净、更明亮,工厂的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都提高了。其次,工厂能为每个设备单独供电,免去了巨大的蒸汽动力中心和复杂的传动机构,生产设备不需再按轴承位置摆放,这催生了生产的流水线。流水线细化了劳动分工,使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使生产管理更加严格,并使技术工人的控制能力大幅减弱。最后,电力易于传输,且电报、电话等方便了远程通讯,这些都导致工厂的规模经济、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垄断组织发展壮大,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控制能力大幅提升。这样的生产方式催生了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或称福特制劳动关系范式),该范式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发展得最为典型,这里以美国为例具体探讨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在美国,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萌芽于1875年电气革命爆发之际,在1935年《瓦格纳法》和《社会保障法》颁布后发展成熟,并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电气革命的衰落而衰退。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主要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第一,就业的稳定性增强。在电气革命中,工厂的规模持续扩大,雇佣工人数量大幅提升,譬如福特鲁日汽车城曾雇佣八万多名工人。对于规模如此之大的工厂而言,过高的工人流动率会带来巨大损失:一方面,搜寻和培训大量技术工人需要付出巨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当离职的工人过多且劳动供给有限时,生产活动就有可能中断。为了降低工人的流动率,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通过提供高工资、工作福利和开通内部晋升渠道等举措培养劳工的忠诚度,使工作的稳定性增强。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月均流动率从1919-1923年的5.4%下降到1924-1929年的2.7%。
第二,劳动收入进一步增长。在电气革命中,优势产业(包括汽车、橡胶、玻璃、石油精炼等)的垄断大企业普遍为工人提供较高的工资,以吸引更多工人、提高劳动效率并抑制工会力量等,譬如1920-1929年美国汽车工人的工资增长了23.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优势产业中的高工资推动总体工资率上升。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1948-1969年美国劳动者报酬的年均同比增长率达到7.05%。因为垄断大企业具有价格控制能力,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上涨的工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劳动收入的增长不仅未对企业利润造成过多不利影响,而且还增加了消费,并促进了企业利润的实现。
第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改善。首先,每日工时下降到8小时左右。1890-1920年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周工时从54.4小时下降到45.7小时。1933年的《美国工业复兴法》和1938年的《联邦公平劳工标准法》等法律规定每周的基本工时为40小时,企业应为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上的工人加薪。到1963年,在美国的印刷、酿酒、服装、煤矿等产业中,有相当多的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其次,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大,工作乏味且单调。流水线将生产活动细分为许多工序,并严格规定了每一道工序在单位时间内要完成的工作量。一方面,工人在流水线上从事的工作通常仅是简单、重复、乏味的机械操作;另一方面,每道工序在单位时间内的工作量一般是根据泰勒和吉尔布雷斯的“时间-动作”构想制定的,普通工人通常要尽全力才能完成它。最后,工作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车间更加明亮、干净、整洁,工厂也配套设置了绿地、体育设施、学校等。但这些都是惠而不费的“花边福利”,其目的是提高工人的忠诚度,并在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抑制工人的不满。
第四,企业管理采取“科学管理+科层制+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模式。首先,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包括:对工作任务进行科学分析,为每一项工作制定标准化的劳动过程和努力程度;根据工作能力来雇佣和培训工人;通过制定工作计划、组织技能训练、提供休息时间和劳动工具等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并让工程师监督工人劳动。①Casteel P.D.,“Taylorism,Fordism, & Post-Fordism”,Research Starters Sociology,No.4,2018,pp.1-6.其次,科学管理催生了金字塔形的科层制管理结构,决策权随着层级的上升而增强,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随着技术能力和资历的提高,劳工有可能被从车间提拔到管理层,因此科层制也为工人提供了晋升渠道。最后,大公司尤其垄断公司普遍建立起内部劳动力市场,允许工人在公司内部轮换岗位。这降低了技术工人的离职率,节约了企业的培训成本,也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五,规模化、标准化的学校教育取代工厂中的“干中学”和学徒制。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需要大批量、同质化的工人。工业革命时期工厂中的“干中学”和学徒制的教育模式难以承担培训如此大规模劳工的任务。于是,美国建立起规模化、标准化的学校教育体系,它独立于工厂体系并成为一项社会事业,为美国工厂源源不断地输送技术工人。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公立学校运动中,美国普及了小学教育,1852-1918年美国各州又相继普及了义务教育。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对技术培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890-1930年美国高等教育为美国产业提供的各类人才从1.7万人增长到接近14万人,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都增设了科学训练系科。
第六,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提高,逐步建立起“福利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纷纷通过改善工头的管理、实施有序的雇佣与解雇程序、提供工资激励、提供保护性保险福利、营造积极的车间文化、改善体力劳动环境和安全、增强雇员话语权等方式构建“福利资本主义”,②[美]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超越社会契约:西欧和美国福利国家的重构》,《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以赢得工人的忠诚并提高生产效率。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府通过联邦法律对最低工资、加班费、失业保险、社会保障体系等作出规定。1935年颁布的《瓦格纳法》规范了集体谈判制度,鼓励工人成立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在《瓦格纳法》的授权下,1938年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后来它逐渐发展成为主导美国劳资谈判、维护美国工人利益的重要力量。③[美]约翰·W.巴德:《劳动关系:寻求平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78页。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全国性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正式在美国建立,这标志着美国成了福利国家。
总之,上述六个特征阐明了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的基本内涵。规模经济、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导致大企业的崛起,生产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劳动需求,增强了工作的稳定性;企业引入科学管理、科层制、流水线和内部劳动力市场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通过缩减工时、提高工资、构建福利资本主义等方式来提高工人的忠诚度;教育发展成为一项独立于工厂体系的社会事业,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规模庞大的教育体系为工厂输送源源不断的技术工人;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支持建立工会并构建了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险项目不断完善。这种劳动关系范式曾帮助美国在20世纪彻底地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滑入“滞胀”、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的发展、“弹性专业化”的中小企业联盟或网络组织取代科层制的大企业、“无人工厂”的出现、经济全球化等,不仅雇主的劳动需求降低了,而且雇主对雇员的控制和监督能力也增强了。这导致劳资力量再一次失衡,破坏了电气革命时代劳资双方达成的默契,并推动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走向分裂和衰退。
四、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
自20世纪70年代初信息革命爆发以来,基于微电子的信息技术和远程通讯技术主要给生产方式带来了以下五点影响。第一,信息的传播、运算和交换速度大幅提升,催生了跨国公司及其全球生产网络。第二,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更加自动化、数字化甚至智能化,对体力劳动和普通脑力劳动的需求都在减少。第三,计算机辅助企业管理,促使企业精简管理层级,并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监督和控制。第四,个性化、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迫使企业持续创新,更强调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第五,互联网和物联网创造了大量线上工作,并使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空前扩大。截至目前,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业已展现出许多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将有望在智能时代真正发展成熟,并引领一段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协同增长。这里笔者结合智能时代的发展趋势,从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六个方面考察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或称后福特制劳动关系范式)。
第一,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随着工业智能化技术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者和许多从事程序化的、枯燥的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将被机器人和计算机取代。但与此同时,随着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扩张、线上工作的崛起、自主创业成本的降低、兼职工作的倍增,将为劳动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就业方式更加灵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2017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显示,美国劳动力中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从1960年的14%上升到2015年的16%。其中,经济因素导致的兼职工作比例仅为3%-4%;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兼职工作比例在12%左右。特别是从2010年开始,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经济因素导致的兼职工作比例明显下降,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兼职工作比例反而上升。这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兼职工作和灵活就业是劳动者的自愿选择。另外,自主创业在许多情况下增强了劳动者工作的稳定性。有实证研究表明,自主创业提高了美国弱势群体参与劳动的热情,并抑制了劳动参与率的下降。①Taehyun A.,“The Employment Dynamics of Less-educated Men in United States:the Role of Self-employment”,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No.1,2015,pp.110-133.另一项基于韩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自雇者更不容易因市场冲击而沦为失业者。②Taehyun A.,“An Analysis of Employment Dynamic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Role of Temporary Work and Self-employment”,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No.4,2016,pp.563-585.
第二,劳动者收入多元化,主要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其中,工资收入既包括劳动者从事全职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也包括劳动者从事兼职工作、线上工作或个体经营的副业等获得的收入。资产收入主要指劳动者用自己的收入投资金融资产所获得的收益和分红。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层出不穷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如众筹、基金等)大幅降低了投资门槛。基金公司为风险偏好者、风险中立者和风险规避者都设计了相应的理财产品。劳动者用自己的收入投资金融资产,就不再是无产者,其可以凭借自己的金融资产获得企业利润的分享权。更广泛、更稳定、更高效的金融体系能使劳资双方共赢:一方面开拓了劳动者分享企业利润的新渠道,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募集更多资金。有实证研究证明,在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下,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可以通过金融发展得到改善。①Yi-bin C. & Chien-Chiang L.,“Financial Development Income Inequality and Country Risk”,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No.1,2019,pp.1-18.
第三,劳动条件更加人性化。工作时间更有弹性,劳动强度减轻,工作环境改善。首先,工作时间更有弹性。在智能时代,物质的生产更依赖于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而精神消费品(包括物质商品的设计元素等)的生产更依赖于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有研究预测2017-2037年人工智能将使27%的制造业工作、22%的交通运输和仓储工作、13%的公共管理和国防工作、9%的金融和保险业工作、4%的建筑业工作、4%的批发零售业工作、2%的行政管理工作消失,但会增加8%的教育工作、8%的酒店服务业工作、9.5%的通信业工作、18%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23%的健康行业工作。②Bolton C.et,al.,“The Power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usiness Automation,and the Smart Economy”,Economics,Management,and Financial Markets,No.4,2018,pp.51-56.这些新增工作的绩效大多并不会因更长的劳动时间和固定的工作日而提高,所以企业为了激发雇员的创造力,将允许劳动者相对灵活地安排劳动时间。其次,劳动强度减轻,生产活动更加安全。在智能时代,与其说“机器换人”,不如说“人机协作”。人工智能可以进一步增强人的体力和智力水平,进而全面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活动的安全性,并使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③[美] 凯文·凯利:《必然》,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29-60页。最后,劳动环境也将明显优化,危险系数高、劳动环境恶劣的工作将快速被机器人取代。譬如早期汽车制造业的喷漆车间采用人工操作,其中的劳动者要忍受刺激性气味和高温作业。现在,多数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喷漆车间实现了无人化运作,这不仅大幅节约了劳动力成本,而且提高了生产线的运转速度,汽车喷漆的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原来的喷漆工被安排到装配、质检等环节工作,他们的劳动环境得到了改善。
第四,管理方式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④于显洋:《组织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3-381页。以充分调动和利用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劳资合作将取代劳资冲突。首先,中间的管理层级逐步消失,科层制的管理方式将被扁平化的管理方式取代,这能够加快企业和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换速度,使企业和组织更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其次,企业管理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实施,这非常适合互联网公司和大型跨国企业的发展需要。譬如自由工作者之家Elance网站上拥有970万名自由职业者,他们曾为全球超过380万家企业提供过服务;Elance对注册会员的管理就是通过虚拟的互联网实现的,这极大地提高了Elance的经营效率。⑤[美]约翰·布德罗等:《未来的工作:传统雇佣时代的终结》,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63-65页。再次,管理方式更加民主,劳动者获得更多参与企业管理和提出产品质量改进建议的途径。最后,管理方式更加弹性化,企业和组织内部的岗位调动更加频繁且更加灵活,劳动者不再长期隶属于一个固定的上级,而是经常根据工作需要被灵活地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团队之中。
第五,人才培养个性化,线上教育和顶尖大学的慕课(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将得到更广泛的认可。线上教育和慕课允许学员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专业、知识模块、课程和教师等,这对于培养个性化、多样化的人才至关重要。线上慕课服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它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因顶尖师资力量不足而造成的教育条件不均等问题。譬如佐治亚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在线硕士课程以较低的费用提供高质量的学位教育,它使得美国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年产量至少提高7%。⑥Joshua G.et,al.,“Can Online Delivery Increase Access to Education?”,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No.1,2019,pp.1-34.另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购买世界优秀中学和顶尖大学的线上慕课服务,为本国人民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不需要独立建设世界顶尖级的学府(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独立建设世界顶级学府超出了它们的能力范围)。这样,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将有望大幅减小,进而促使跨国企业向更多国家投资,并为全球协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六,社会福利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包括政府以转移支付形式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各类社会保险计划以及公共财政支持的就业保障计划等,政府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首先,在智能时代的知识经济中,成熟、稳定的新劳动关系范式需要劳资双方的协同和妥协,这需要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以及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基本的收入保障是一种可行的经济政策,它能消除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产生的不稳定性,并通过网络学习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①Lucarelli S. & Fumagalli A.,“Basic Income And Productivity Cognitive Capitalism”,Review of Social Economy,No.1,2008,pp.71-92.其次,到目前为止,多数发达国家和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私营和公立社会保险体系,为劳动者提供失业、医疗、工伤、生育、养老等方面的保障。最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应当为每一个想要工作的劳动者提供公共部门的就业岗位,以避免失业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和其它社会问题。②[美]兰德·雷:《现代货币理论:主权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90-325页。在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政府有条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一方面,政府推动的新基础设施(物联网、大数据中心、高速交通网络等)建设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许多公共服务岗位(如社区医疗等)并不需要很多财政投入就能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收益。
从上述六个方面的特征可以看出,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可以进一步减弱异化劳动的程度,构建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部门可以为有意愿就业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就业保障,并为低收入者和无劳动能力者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基本生活无忧的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学校或通过互联网慕课学习知识和技能,成为高素质、个性化、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力,并根据自己的所学在线上或者线下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就业方式更加灵活、更有弹性,企业不必为僵化的长期雇佣合同支付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劳动者也可以随时从不喜欢的就业岗位离开,并有权规划他们的劳动时间。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劳动强度由于智能机器人的引入而大幅减轻,劳动环境明显改善。企业为了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采用更加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的管理方式。劳动者的收入更加多元化,包括工资和理财收益等,通过用工资购买金融资产,劳动者不再是无产阶级,劳资双方的关系从互相对立走向互利共生、互相合作。可以预见,这种新型劳动关系范式能够有效地缓解劳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引领新一轮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当然,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仍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才能真正成熟。
五、新、旧劳动关系范式重叠的现实与因应之策
当前,我们正处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重叠期。旧的电气革命劳动关系范式已经衰退,但仍占据较大比重;新的信息革命劳动关系范式蓬勃发展,但尚未取得主导地位。譬如:即便在制造业非常先进的德国,依然有65%的工作不允许工人拥有自由裁量权,且临时工作岗位还在持续增多;即便一些企业赋予劳工自由裁量权并允许他们参与企业管理,但这种赋权通常只是名义上的而非实际的;雇主允许劳工提意见,但多数情况下并不按照工人的意见行事。因此,根据前文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的梳理,笔者认为,当前新旧劳动关系范式重叠期的突出特征是经济社会中存在两种互相竞争的劳动关系范式。
当前由于新旧两种劳动关系范式并存且互相竞争,所以不同国家、产业和职业之间的劳动关系范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工作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工作时间、管理方式和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第一,在工作的稳定性方面,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5年全球职业与社会问题展望》指出,全球只有1/4的就业者与雇主签订了长期合同,超过60%的劳动者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越来越多的人以非正式工、临时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参与工作。第二,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拉大。美国商务部普查数据显示,美国全部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9上升到2017年的0.48。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加拿大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26上升到2010年的0.337,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91上升到2010年的0.421,法国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308上升到2012年的0.331,印度的基尼系数从1983年的0.311上升到2009年的0.339。第三,不同工种的工作时间差异较大。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4月,美国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批发业、仓储运输业和公共事业中的平均周工时较长,分别为46.7小时、39.1小时、40.7小时、39.0小时、38.8小时和41.9小时;零售业、信息业、金融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教育和医疗业以及休闲和酒店业的平均周工时较短,分别为30.7小时、36.6小时、37.7小时、36.2小时、33小时和26小时。第四,在管理方式方面,只有极少数的数字工作才比福特制的工作更具自主性、自我组织、多样性和创造性。除了少数高技能工人变得更富创造力以外,大部分工人没有获得更多的决策权和自主权。第五,在社会福利方面,“自由福利国家”制度在很多发达国家取代了“福利国家制度”,这加重了福利制度的不平等。在“自由福利国家”制度下,社会福利项目转由私营部门经营,社会保险项目和税收减免政策取代了政府对穷人的转移支付等。政府通过只保留最低保障和补贴私人福利计划等方式推进福利制度的市场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社会福利项目的目标是使其参与者获益,而非普遍地接济穷人。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贷款利息的所得税抵扣政策)被收入较高的个人和家庭不相称地享受了;许多私营的福利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也由相对富裕的阶层享受。
可见,要从当前新旧劳动关系范式重叠,即电气革命劳动关系范式和信息革命劳动关系范式并存且相互竞争的状态迈向巩固的信息革命劳动关系范式,可能仍要经历相对漫长的时间。鉴于劳动关系范式的巩固能够促进劳资和谐,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笔者认为:政府应当更积极地调节劳动关系,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就中国而言,具体的对策建议涉及技术、市场和制度三个层面。
首先,在技术层面,既要重视鼓励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又要重视培育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进而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促进劳资力量的平衡。具体而言,政府可实施以下两个方面的政策:第一,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支持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并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使国内的产业结构逐渐向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上端移动,从而提高产业附加值和企业的盈利能力。这是中国劳动关系范式转型升级的源泉所在,须知,没有经济发展就谈不上劳动关系的改善。第二,改革当前以培育同质化劳动力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体系,更加注重素质教育、个性化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基础教育应当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育,以便为富有发展前景的文化创意产业输送人才。高等教育应当重视培养个性化的人才,这可通过加大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增加高等学校的教师数量、进而提高高等教育院校的师生比来推动。同时,应重视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培育适合信息和智能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级技术人才和创新应用人才。
其次,在市场层面,应重视调节市场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促进劳动力相对平稳地从旧产业向新兴产业流动。劳动力从旧产业向新兴产业流动不仅关乎中国的产业升级,而且关乎中国的劳动关系范式转型。但是,劳动力从旧产业流向新兴产业是需要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的,如果政府不能帮助劳动者从低端产业流向高端产业,那么产业升级和劳动关系范式转型就将面临巨大挑战,并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具体而言,政府可实施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第一,破除不必要的“编制”、户籍限制等,消除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地区间流动的障碍。第二,适当提高劳动者参与失业保险的缴费费率和补偿金额,使劳动者转换工作没有后顾之忧。第三,提高正在接受技能培训的失业者的生活补贴,从而提高失业劳动者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技能的动力。第四,促进和规范各类人力资源中介平台的发展,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缩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相匹配的时间。
最后,在制度层面,政府应做好民生兜底工作,积极应对劳动关系范式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摩擦和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劳动关系范式相对平稳地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政府可实施以下两个方面的政策:第一,直接增加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中的无编制就业岗位,或者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增加公共部门中的就业岗位。这些新增的就业岗位可以成为劳动者从低端产业流向高端产业过程中的中转站,进而避免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造成的人力资本浪费。第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健全社会再分配制度,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再分配制度的改革来提高普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福利水平,使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及其子女有更多的机会接受素质化、个性化、专业化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从而使他们更容易在相对高端的产业中择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