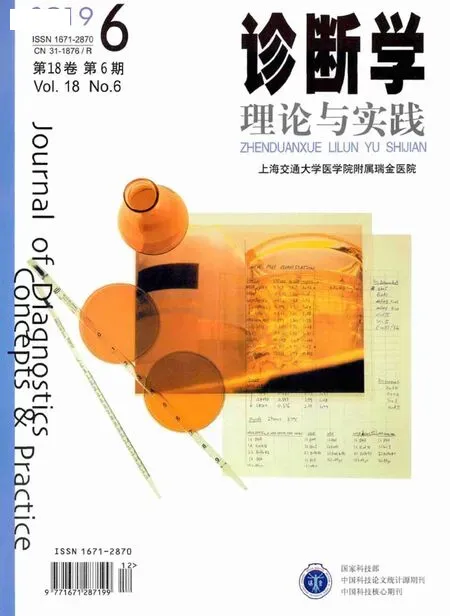新生物标志物在胃肠道肿瘤中疗效预测和预后价值的研究进展
2019-03-03陈海燕杨小宝许大康
陈海燕,杨小宝,许大康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医学检验系,上海 200025;2.西安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癌症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00)
从肿瘤细胞到肿瘤微环境的研究是肿瘤研究领域相当重要和关键的部分,对认识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在肿瘤的诊断、防治和预后评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肿瘤细胞是生长不受控制的细胞,可通过基因突变加速细胞分裂或抑制正常控制系统(如细胞周期停滞或程序性细胞死亡)从而导致癌症。在肿瘤组织中,除了肿瘤细胞外,其他成分还包括间质细胞和细胞外基质,而间质细胞又包括成纤维细胞、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CAF)、内皮细胞、炎症细胞、脂肪细胞等,这些共同构成了肿瘤的微环境。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众多成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肿瘤细胞周围的间质细胞状态对肿瘤的转移有重要影响,甚至可以用来预测肿瘤复发。免疫治疗彻底改变了人类癌症的治疗方法,然而只有15%~20%的患者对免疫疗法有反应[1],如果有可筛选适合免疫治疗者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则可通过筛选,对部分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免疫治疗,其疗效可能会更显著。
生物标志物被定义为正常或异常的、客观且可量化的生物指标,可以帮助疾病诊断、预后判断和治疗反应评价等[2]。生物标志物分为七大类,包括易感性及风险生物标志物、诊断生物标志物、监测生物标志物、预后生物标志物、预测生物标志物、药效学及反应生物标志物、安全生物标志物,其可用于肿瘤诊断、预后判断或者治疗反应评价等,是实现肿瘤个体化治疗的关键步骤之一。目前临床已应用了几种胃肠道恶性肿瘤的生物标志物,以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靶向治疗方案和用于监测治疗反应和复发。现随着免疫疗法时代的到来,迫切需要能够指导肿瘤免疫应答的生物标志物。目前已探索了来自肿瘤微环境、肿瘤基因组和来自液体活检的特征性生物标志物,但单一的生物标志物诊断价值有限,而与传统的单一生物标志物相比,多重生物标志物的使用具有提高判断准确率的潜力。另外,尚需要对免疫生物标志物进行全面分析,以揭示动态和多方面的抗肿瘤免疫力,并进行合理的设计,制定组合策略,同时开发新型的生物标志物。
本文总结了生物标志物在胃肠道肿瘤中的应用,重点介绍新生物标志物的开发在癌症治疗中的预测和(或)预后价值。
传统生物标志物在胃肠道肿瘤中的临床应用
一、诊断及预后评估
1.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在 结直肠癌等肿瘤中的应用:目前在临床中使用的胃肠道肿瘤标志物如表1 所示。CEA 是胃肠道最常用的肿瘤标志物之一[3],其过度表达发生于>90%的结肠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和60%的其他类型的癌症,包括胃癌、肺癌和胰腺癌[4],故一直被广泛用作血清肿瘤标志物。CEA 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不高,特别是在疾病的早期阶段[5],因此不能作为筛选早期胃肠道癌症的生物标志物。然而,在确诊疾病的患者中,血清CEA 的绝对水平与其疾病负担呈相关[6-7]。研究显示,CRC 肝转移患者的平均血清CEA 水平为(64±1.6)ng/mL,而CRC 无肝转移患者的平均血清CEA 水平为(2.6±0.8)ng/mL,2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CEA 具有一定的预后评估价值。

表1 主要生物标志物在临床上的应用
2.糖类抗原在胃癌中的应用:糖类抗原(carbohydrate antigen,CA)72-4 是目前诊断胃癌最佳的标志物之一[8],对胃癌有较高的检出率(93.83%);而CA19-9 在胰腺癌辅助诊断方面起重要作用,但都特异度不高,中位特异度为82%(68%~91%)[9]。因此,在对消化道肿瘤患者进行随访的过程中,常需要将CEA、CA72-4、CA242、CA19-9 这4 个指标组合在一起,综合分析,动态观察。对肿瘤标志物的连续监测、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诊断的灵敏度(53.2%)[10],从而帮助肿瘤的早期诊断。
二、指导靶向药物应用
近年来,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发现与传统的放、化疗相比,肿瘤分子靶向治疗的特异性更强,效果更显著,毒副反应也较小。
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作为胃癌的治疗靶点:HER2 是一种酪氨酸激酶受体,属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家族,是已知的胃食管交界处(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GEJ)腺癌的治疗靶点和预后因素[11]。HER2 二聚体与各自的配体结合后,通过激活下游信号通路,包括膜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信号途径(RAS/RAF/MAPK)和磷脂酰肌醇-3 激酶/蛋白激酶-B/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PI3K/AKT/mTOR),可促使HER2异常扩增或过表达,导致细胞周期进展不受控制,研究提示7%~38%的GEJ 腺癌患者存在HER2的扩增和(或)过表达[12]。单克隆抗体曲妥珠单抗可用于治疗HER2扩增和(或)过表达的晚期胃或GEJ癌症患者,且当曲妥珠单抗和顺铂合用时效果更好,可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单独化疗组为5.5 个月、联合用药组为6.7 个月)和总生存期(单独化疗组11.1 为个月,联合用药组为13.8 个月)延长[13]。
2.以间质表皮转化因子作为胃癌的治疗靶点:胃癌靶向治疗的另一种生物标志物是间质表皮转化因子(cellularmesenchymal to 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c-MET)。有研究显示,10%~20%的胃癌患者中存在着MET 基因扩增的现象[14-15]。激活的c-MET 信号转导可使癌细胞增殖、存活和侵袭的能力增强,是一种独立的生存预后因素[16]。MET 基因扩增可见于61%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和35%的小细胞肺癌患者[17-18],且MET 基因拷贝数较高的NSCLC 患者的预后相对较差[19]。MET 拷贝数≥5 的人群中位生存期(25.8 个月)明显短于MET<5 拷贝/细胞的人群(中位生存期为47.5 个月,P=0.004 5)。因此,阻断这些靶点,可有效抑制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
三、生存预后
1.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K-RAS):在转移性CRC 中,K-RAS 突变状态已被广泛报道为预后和预测肝脏转移的生物标志物,可以在12%~75%的结肠癌中被鉴定,并在大多数研究中显示出与较差的预后相关[20]。由于小GTP 结合蛋白(RAS)致癌基因位于EGFR信号通路的下游,即使EGFR 被阻断,K-RAS 突变也可导致该途径的激活[21]。因此,K-RAS 突变状态可作为对抗EGFR治疗无反应的生物标志物。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成功研制出KRAS 靶向药物,绝大多数药物仍处于一期临床研究阶段。
2.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和错配修复功能缺陷(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dMMR):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指DNA 甲基化或基因突变致错配修复基因缺失,从而导致微卫星重复序列长度的改变,表现为同一微卫星位点在不同个体之间或同一个体的正常组织与某些异常组织之间,微卫星位点的重复单位的数目不同,使其不能正常地发挥调控作用,导致细胞增殖及分化异常,促发恶性肿瘤的形成。大量研究表明,MSI 与CRC、胃癌等的发生密切相关,提示MSI 检测具有多重临床病理意义。为了防止MSI,机体自然进化出了一套对抗系统,能修复DNA 错配,即DNA 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其由一系列特异性修复DNA 碱基错配的酶(由错配修复基因编码)组成,能够查出MSI 并进行修复,保证复制的精确性。如果MMR 修复机制出现故障,即dMMR,参与MMR 修复基因发生了突变,MMR 修复能力下降或缺失,个体的自发突变率将明显增加。dMMR 在所有CRC 中占15%~20%,在胃癌中占8.5%~20.0%,在食管及胃食管腺癌中占3%~7%,在胰腺癌中占2%~3%[22-23]。一项针对2 630 例癌症复发患者的多变量分析显示,MSI/dMMR 肿瘤患者相比于微卫星稳定/错配修复MMR 完整患者的复发后生存时间更长,调整后的风险比(hazard ratio,HR)为0.82;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0.69~0.98;P=0.029[24]。dMMR 已被证明对结肠癌、胃癌和胰腺癌患者的生存有积极的预后[25],例如根据MSI 状态估计250 例胃切除术患者的卡普兰-迈耶(kaplan-meier)生存率,微卫星稳定肿瘤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26.7 个月(95%CI 为20.8~32.5 个月),而MSI 肿瘤患者的中位生存期超过观察期[26]。此外,dMMR可以预测PD-1 抑制剂的抗癌疗效[27]。突变频率增高会导致肿瘤免疫原性增强,因此dMMR 患者对免疫疗法的敏感性较高[28]。
综上所述,传统的生物标志物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靶点及靶点标志物以指导肿瘤的诊断和治疗。
生物标志物的新发展
前文已经总结了传统生物标志物的特点,下文将阐述近年在生物标志物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总结见表2)。肿瘤微环境、肿瘤基因组学、液体活检将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诊断、疗效监测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一、肿瘤微环境中的生物标志物
1.PD-1/PD-L1:在活化的淋巴细胞(包括T 细胞、B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上表达的PD-1 限制了组织内T 细胞效应子的功能。通过上调PD-1 的配体(PD-L1),肿瘤细胞可诱导效应T 细胞凋亡[29]。据报道,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PD-L1 的表达率各不相同(14%~100%),无论这些肿瘤是否对PD-1/PD-L1 治疗有反应[30]。早期研究表明,PD-L1 阳性可以增加患者从PD-1/PD-L1 抑制剂治疗中获益的概率[31]。然而,最近有更多学者质疑了PD-L1 作为有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准确性,因为多项研究均显示,免疫疗法的效能与PD-L1 表达水平无关[32]。

表2 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开发
研究者利用携带人类免疫球蛋白基因座的转基因小鼠,首次开发出抗PD-1 [纳武单抗(nivolumab),也称为ONO4538、MDX-1106 或BMS-936558]的完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mAb)。纳武单抗的同型IgG4 使补体活性或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最小化[33]。该抗体在IgG4 恒定区的228 位进行丝氨酸到脯氨酸的替换,使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对活化T 细胞的作用最小。纳武单抗的临床试验于2006 年在美国开始,2009 年在日本开始被应用于临床。纳武单抗的一期临床研究显示,其对NSCLC 的累积有效率为18%,黑素瘤为28%,肾癌为27%,14%的患者出现3 级或4 级药物相关不良事件[34]。值得注意的是,与细胞毒性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 的单抗伊匹单抗相比,纳武单抗作为单一药物已显示出持久的临床活性,且不良反应要少得多[34-35]。
迄今为止,超过500 项使用PD-1 信号抑制剂的临床研究已经在至少20 种实体和血液恶性肿瘤上使用了8 家制药公司的9 种抗体[36]。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管理的临床试验数据库显示,全世界受试者总数超过20 000 人(https://clinicaltrials.gov/[CTG])。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于2014 年批准纳武单抗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素瘤患者,2015 年批准其用于NSCLC 患者,2016 年批准用于经典霍奇金淋巴瘤和肾癌患者。FDA 还于2014 年批准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用于治疗黑素瘤,并于2015 年批准其用于治疗NSCLC。抗PD-L1 于2016 年被批准用于不能切除的膀胱癌和NSCLC。
然而,目前的研究仍有一些局限性。PD-L1 阳性仅是派姆单抗治疗NSCLC 患者的必要条件,免疫组化检测PD-L1阴性的患者仍可以通过抗PD-1 或抗PD-L1 治疗获得临床疗效。在大多数研究中观察到,PD-L1 阴性肿瘤患者的反应通常在11%~20%之间,纳武单抗单药治疗的总反应高达41%。由于肿瘤具有异质性,例如同一个病灶的不同位置以及不同病灶之间的PD-L1 表达不同,治疗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治疗方式均会影响PD-L1 的表达。此外,不同平台检测PD-L1 水平不一致性,检测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现如今尚未有统一的方案,仍需进一步探究。更为严重的是PD-1 阻断治疗带来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包括间质性肺炎、伴有胃肠道穿孔的结肠炎、1 型糖尿病、严重皮肤反应、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皮质类固醇治疗后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败血症、脑病和神经后遗症、格林-巴利综合征、脊髓炎、重症肌无力、心肌炎和心功能不全、急性肾上腺功能不全和肾炎等[37-40]。综上所述,PD-L1 因其局限性不是一种完备的预测免疫治疗的生物标志物,但其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2.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TIL)代表具有抗肿瘤潜力的适应性免疫的有效机制,已显示其与各种类型的癌症预后及对免疫疗法的反应相关[41]。自体TIL 的过继细胞治疗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转移性黑素瘤患者中具有丰富的临床应用。TIL 治疗利用了肿瘤中的天然存在的肿瘤反应性T 细胞,代表一种个体化治疗,因为TIL 是从患者自身的肿瘤组织中分离出来的,并在体外激活和扩增后重新注入。在进行TIL 输注之前,需先进行预处理——淋巴清除化疗,然后输注白细胞介素2。多个独立的研究中心报道,10%~20%的患者肿瘤完全消退,且客观反应率高达50%[42-45]。先前针对TIL 治疗其他实体瘤的试验显示其成功率有限,但免疫治疗策略的最新进展激发了人们对开发这种方法用于其他适应证的兴趣。TIL 治疗现已在其他选定的实体瘤中显示出临床活性[46-47],并在其他组织学中进行了测试,包括卵巢癌、肾细胞癌、CRC、胰腺癌、肝细胞癌、胆管癌和胃癌。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卵巢癌和肾细胞癌作为实施TIL 治疗的候选。在CRC 中,免疫细胞的类型、密度和位置,特别是细胞毒性和记忆T 细胞(HR=0.585,95%CI 为0.362~0.946,P<0.01),能比TNM 分期(HR=3.803,95%CI 为1.179~12.274,P<0.05)更好地预测生存期[48]。在T 细胞浸润程度相似的CRC 中,CD103+记忆T 细胞比例最高的肿瘤预后最好[49]。CD103+CD8+T 细胞高度浸润患者与低度浸润患者相比,总生存期显著延长(HR=3.418,95%CI 为1.020~11.45,P<0.05)。
为了标准化评估CRC 中TIL 的方法,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测量单核细胞在苏木精-伊红染色区间基质区域所占面积的新方法。这种方法的结果证实,TIL 的密度是CRC 中有用的预后因素[50]。肝癌TIL 中自然杀伤细胞比例[(11.8±8.1)%]显著低于周围组织[(18.0±7.9)%]。癌巢浸润密度低者的无瘤生存率(P=0.027)及总生存率(P=0.005)明显低于密度高者[50]。在Epstein-Barr 病毒(EB 病毒)相关的胃癌中,证实了肿瘤内高TILs、低PD-L1 表达与更长的无病生存期之间的关联[51]。最近有结果显示,利用18 个基因特征的T 细胞炎症基因表达谱评分与胃/GEJ 癌症的派姆单抗治疗疗效显著相关[客观缓解率(P=0.012,n=203),无进展生存期(P=0.017,n=203)][52],在T 细胞炎症基因表达谱评分和PD-L1 表达之间发现显著但非线性的关联(r=0.40,P<0.001)。这些结果表明,与PD-L1 表达相关的T 细胞炎症基因表达谱分析有作为胃/GEJ 癌症中选择治疗的生物标志物的可能。
3.免疫抑制性骨髓细胞:肿瘤相关的髓样细胞不仅会产生抑制或无反应的环境,阻断T 细胞功能和增殖,还可通过加速肿瘤干细胞生长、血管生成、基质沉积、上皮-间质转化和转移促进癌症。肿瘤内和循环骨髓来源的抑制细胞的积累已被证明与胃癌的疾病进展及预后相关。例如一项54 例胃癌患者研究发现,外周血CD4+CD25+Foxp3+Treg 细胞与CD4+T 细胞的比率与胃癌临床分期、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相关(P<0.05)[53]。
骨髓细胞对先天免疫反应也很重要。单一骨髓标志物不可能预测免疫反应疗效,需要开发多重生物标志物分析,用于标记临床试验前的免疫抑制性骨髓细胞,以预测其免疫疗效。
二、肿瘤基因组学中的生物标志物
1.基因panel:基因panel 靶向测序是一种用于鉴定可能靶向基因组的新兴方法,并与治疗相匹配。基因panel 同时检测多个位点、多个基因,而这些位点和基因需要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选择和组合,从而构成一个检测panel,目前仍存在着一些挑战。例如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CancerCenter)开发了一种靶向基因测序panel,最初包括341 个基因,现已扩展到410 个癌症相关基因。然而研究的225 例需要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中,只有3 例(1%)与基于测序结果的治疗相匹配[54],2 例无益处,1 例患者反应不明确。将测序结果实际应用于指导个体治疗,目前仅限于胰腺癌患者,其他肿瘤中的应用尚未成熟,未来可以在其他肿瘤中进行尝试。
2.肿瘤突变负荷:研究显示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与各种类型癌症的免疫检查点阻断的临床获益显著相关[55],TMB 越高,患者从免疫治疗中的获益可能越多。然而,大多数胃肠道癌症的突变负荷较低[56],但MMR 缺乏者除外。一项包含了1 375 例各种胃肠道肿瘤患者的研究显示,结肠癌具有高的TMB、MSI-H 和(或)微卫星稳定性,而那些突变频率较高的人被发现肿瘤特异性新抗原具有更丰富的CD8+T 淋巴细胞浸润和更高的调节分子表达(细胞毒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PD-1、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 和吲哚胺2,3-双加氧酶1)[57]。在晚期胃癌患者中,TMB是接受PD-1 单抗治疗的潜在疗效预测标志物,高TMB 患者(位于前20%的TMB≥12 muts/Mb)的有效率(33.3%对7.1%,P=0.017)及总生存时间[14.6 个月对4.0 个月,HR=0.48 (96%CI 0.24~0.96),P=0.038]均明显优于低TMB 患者(TMB<12 muts/Mb)[58]。因而,含有TMB 的患者更易受益于免疫疗法。
三、液体活检中的生物标志物
明确诊断需要肿瘤组织活检,但其并不能用于监测治疗反应[59]。外周血生物标志物的分析,包括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和外泌体,其采用的非侵入性方法称为液体活检,已成为克服肿瘤组织活组织检查限制的一种方法,并在监测复发和治疗效果方面显示出巨大潜力。有研究调查了原发性胃癌患者8 个原癌基因中的68 个ctDNA 突变热点后发现,疾病晚期ctDNA 与5 年总生存期显著降低有关(5.6%比31.5%,P=0.028)[60]。
1.ctDNA:ctDNA 主要由活跃生长的癌细胞死亡而释放,也可直接从循环肿瘤细胞中分泌[61]。值得注意的是,ctDNA 可以为肿瘤进化和动态疾病监测提供全面的基因组分析[62]。在CRC 中,ctDNA 已被证明能成功地收集EGFR 靶向治疗患者的实时进化分子。ctDNA 分析不仅可以识别可能导致EGFR 阻断抗性改变的基因,还可以指导选择可能对靶向药物有反应的罕见患者群体。在确诊时可检测到ctDNA水平的3 例患者中,手术切除后其水平降低,而姑息治疗期间复发或进行性疾病同时升高。在另一个队列中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4 例患者术后等位基因突变频率下降[63]。因此,治疗期间ctDNA 水平的变化也可能是评价临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效果的指标。
2.CTC:CTC 是血流中的循环肿瘤细胞。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经过治疗的25 例Ⅰ~Ⅲ期CRC 患者中,ctDNA阳性患者的2 年无复发生存率(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为66%,而阴性者的2 年RFS 为100%[64],进而表明其存在与患者的总生存期或无进展生存期降低相关。此外,还有研究报道了CTC 作为监测治疗反应和检测复发的治疗靶点的价值。然而,鉴于该患者群体中CTC 的稀缺性,CTC 的预后和预测作用尚未在非转移性环境中建立。
3.外泌体:外泌体是内体衍生的细胞外囊泡,直径为30~120 nm,携带一批蛋白质、代谢物、RNA(包括mRNA、miRNA、lncRNA)、DNA(包括mtDNA、ssDNA 和dsDNA)和脂质[65-66],是液体活检标志物作为生物标志物的重要来源。据报道,首次将外泌体作为生物标志物是在8 例肾细胞癌患者和8 例健康志愿者的样本中进行的[67]。Zhang 等[68]研究了胃癌细胞的外泌体,发现肝转移者体内的外泌体水平升高。胃癌患者的血清外泌体水平比健康受试者高,且血清中的外泌体数量与胃癌分期呈正相关。尽管外泌体在非侵入性早期检测和潜在治疗方面具有很大前景,但仍具有一些局限性。外泌体生物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准确测量外泌体的数量和纯度。只有一小部分细胞外囊泡携带相关的通讯内容,因此其实际效率难以检测。此外,需要更多地了解细胞外囊泡亚型的特定标志物和每种类型细胞外囊泡的基本作用,以更好地了解其在各种疾病环境中的应用。
生物标志物研究的前景
在临床中仅有少数生物标志物可用于治疗胃肠道恶性肿瘤,尽管目前已经鉴定了许多用于胃肠道恶性肿瘤的新的生物标志物,但尚未得到相关临床试验的验证。另一方面,指导患者选择适当的治疗,进行生物标志物测定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未构建适当的生物标志物对患者进行选择,会导致实验疗法的临床试验终点时未能满足要求。因此,在建立适当的生物标志物测定之前,不应推进实验性治疗剂的开发。因此,在未来生物标志物的开发应与药物开发同时进行,每当确定潜在的治疗靶标时,应伴随开发生物标志物测定法。
对于免疫疗法,单个生物标志物通常不足以预测治疗反应。免疫生物标志物的综合分析不仅可以提供组合免疫疗法的合理设计,还可以鉴定多种免疫生物标志物,并随后开发多重检测,以共同评估多种免疫生物标志物。肿瘤标志物的开发、组合亦对精准医疗、诊断大有裨益。遗憾的是,目前的生物标志物检测方法缺乏必要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的无创、特异且灵敏的生物标志物,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并能更有效地追踪临床疾病的发展过程及治疗反应。综合应用多个标志物会比单方面标志物更为全面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