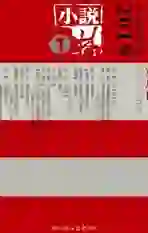鸟类报告
2019-02-28智啊威
前言
双腿带我回到生养我的那片土地时,正值傍晚。我走在浓雾掩映的故土上,渴望以一种地质勘探、走访调查的方式,劈开眼前浓雾,以此来完成这篇报告。然而由于资料欠缺,证言模糊,这篇报告的写作过程尤为艰难。很多时候,我只能茫然地站在豫东平原的阡陌上,听鸟雀衔来一两句内幕,顺藤摸瓜但最终两手空空。因此,在这篇报告中,我拒绝说教,指引,甚至拒绝事件背后的意义提供。我将努力用一种客观方式,呈现我所看到的小羊庄、鬼仔岭以及整个豫东平原的真实状貌,以供未来的调查者们参考。
一 是谁把咬牙切齿砸在了我的后脑勺上
人言闪烁与史料欠缺,使我对鬼仔岭的调查,时常陷入绝望的泥沼中。每当这时,我手夹着烟,踏着月色、暮霭、细雨或烈日,走出小羊庄,在豫东平原上走来走去。田间偶遇归村的人,递上根烟,无话。那人也无话。不待烟燃尽,我又迈开腿,没走几步,那人便把咬牙切齿砸在了我后脑勺上。我一个趔趄,恍然回头,那人的身影已消融在浓雾中。那一刻,我呆愣在淫雨霏霏的阡陌上,从后脑勺传来的剧痛,电流般涌向全身。我感到身子一抖,眼前翻起一股黑云……
醒来时,看到母亲坐在床头,她眼圈黑紫,一脸倦容。而父亲正蹲在地上喷云吐雾。我声音微弱地叫了声娘,她先是一愣,继而伏在我胸口上哽咽了起来:“阿伍,娘说多少遍啦!说多少遍啦?你咋就是不听?你为啥非要去鬼仔岭?”她在哭声里责备我的同时又补充道:“有些事情,能是该你知道的吗?”。
“要不是个二百五,他不会干这些糗事儿!”父亲从云雾中站起,把烟头摔在地上,火星在脚下迸溅。他瞪着我,撂下这句话,便向屋外走去。门挡了他的路,他没用手推,而是一脚把门踹得震天响。那一刻,我感到房子摇晃得厉害,仿佛要塌下来了一般。
村长来时,身后跟了一群人。那时我头上缠着绷带,疼得厉害,但还是努力支起上身,赫然看到人群中有几个狗头和狼头……它们一个个长在人的身体上,站在村长身后,对着我和母亲龇牙咧嘴。一时间,我被眼前的场景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躺下去,拉起被子蒙住了头。
我以为缩在被窝里就安全了,可村长的声音却穿过空气,穿透棉被,洪水样朝我耳朵里灌:“阿伍,你是小羊庄的一分子,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一点儿政治觉悟你都没有吗?俗话说得好,出头的椽子早烂。有些事你可要掂量清楚。昨天,有人朝你的后脑勺上拍了一砖头,这种事在咱们这不是第一次,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你觉得拍在你头上的那一砖头是伤害,我反而觉得那一砖头是对你的温馨提醒,是爱意表达的最高形式。你要想想,在那个时候,要对你有多么深厚的爱和关心,才会咬牙切齿拍下那至关重要的一砖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一砖头拍得恰到好处,那一砖头如果拍醒了一个梦中人,这事难道不值得祝贺吗?”
村长讲罢 ,我把被子掀开一条缝,看到村长带领着那几个动物脑袋正要离开;在他们转身之后,我看到他们各自屁股上的尾巴,在裤子外面摆动着。这一发现令我震颤不已。我早时在村里见到他们,他们屁股后面的裤裆里鼓鼓的,那是它们的尾巴!那时他们还藏起尾巴做人,可这才几天啊,他们已经堂而皇之地把尾巴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觉羞耻,反而觉得是一种荣耀。
人群散后,我从被窝里探出头,看母亲还坐在那,便把刚看到的那些脑袋和尾巴讲给她。我以为她会和我一起喟叹,然而没有。她用手抚摸着我的脸说:“阿伍,那一砖头是不是把你拍傻了,你咋开始说胡话了呢?”说着,泪珠从她眼角爬出来,“啪嗒”一声,石磙样砸在了我的胸口上……
二 报告人阿伍的材料补充
鬼仔岭位于小羊庄东南三公里临河之地,本该成一块肥田,但从我记事起,那里便是一块荒地,无人开垦种植。早年,鬼仔岭还有一些残垣断壁,站立在荒野中,饱尝风雨吹打。如今,已彻底倾圮,只剩下一片隆起的土堆,像一个巨大的坟墓,静卧在那里。
幼时,大人们明令禁止我们去鬼仔岭玩耍,他们用带着死亡气息的话语无限渲染鬼仔岭,使鬼仔岭终年蒙着一层阴森而恐怖的面纱,导致很多孩子谈鬼仔岭色变。然而在我八岁那年,由于好奇心的强大驱使,我决定去一趟鬼仔岭,这决定得到了好友铁头的积极响应。
那是1978年的一个夏天,我和铁头一人脖子上挂一壶水,怀里各揣一块玉米面馍,站在了鬼仔岭高大浓茂的荒草前(鬼仔岭就在这荒草的掩映中)。
时值中午,日头毒辣,我跟铁头站了一会儿后,相互递个眼神,便一头扎进了荒草中,向鬼仔岭的中心走去。草叶划在脸上火辣辣的,草籽掉在脖子里奇痒难忍。我微眯着眼,把草丛扒开缝,艰难前行;草丛里闷热难耐,且有很多不明颗粒被吸进鼻孔,我感到呼吸紧迫,不得不张着嘴,不明颗粒便跑进了我的嘴里,我一边吸一边吐,那感觉糟糕极了,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我们走出荒草,眼前忽然开阔,只见鬼仔岭上空乌云低垂,几个瘦弱的龙卷风在鬼仔岭的皮肤上游来荡去,一股阴寒之气扑面而来。
铁头见我呆愣在那里,回头催道:“快点阿伍,来一趟不容易,四处转转,看能捡到什么宝贝不。”我追着铁头的声音往前走,一只黑鸟突然从断墙上惊飞,拍打着翅膀向鬼仔岭上空射去。我赶紧停住脚,抬头望着那只黑鸟。正当这时,走在前面的铁头突然从一面断墙后跑出,一脸惊恐地喊道:快跑阿伍!快跑!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便看见一群黑鸟像一块巨大黑布从铁头身后涌来,迅速遮掩了我们头顶的天空……见此光景,我和铁头尖叫着在鸟群的阴影中仓皇奔逃,像两只被猎狗追捕的兔子……
等我俩气喘吁吁跑出荒草丛时,一起回头,看到身后疲软的草叶折射着耀眼的日光,瓦蓝的天上连只鸟毛都没有。铁头抹了一把额头上密集的汗珠,喊了声:我的妈呀!然后便失魂落魄地往小羊庄跑去。
回小羊莊的路上,铁头心神不宁,他嘴里喃喃着说:好多骨头,好多眼睛,胳膊,嘴唇和手臂,血糊糊的,好多啊!我不知道铁头在说什么,当我问他在那面墙后究竟看到了什么时,他先是沉默片刻,继而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说道:阿伍,好多骨头,好多眼睛,胳膊,嘴唇和手臂,血糊糊的,好多啊……
见铁头如此神经兮兮,一路上我也没再跟他说话。
然而,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从鬼仔岭归来后的第三天傍晚,铁头就出事了。
那天傍晚,晚霞血水般从西天流淌下来,顺着小羊庄的大树和高墙往下淌,我跟着村里人的脚,踩着黏糊糊带着血腥味的霞光涌到南沟的时候,看到铁头骑在一棵高大杨树的枝干上,鼻孔眼睛嘴巴里都插满了铁丝样的细木棍,那是鸟雀搭窝用的木棍。他的血顺着木棍流出,从木棍的另一端一滴滴往下掉,几十根细小的木棍被染成了红色,导致他的脑袋远远看上去像一个猩红的刺猬,诡异而惊悚。
那棵大树,要两个人伸开双臂才能勉强合抱住。这么粗大的树,一个九岁的孩子是怎么爬上去的?众人在树下叽叽喳喳,议论不止。而正当大家抓耳挠腮之际,人堆里一个嗓子炸声道:看!铁头的头顶上那是啥!一时间,众人的目光被那个嗓子牵引着,顺着铁头的头顶往上爬,爬着爬着,在铁头上方约一米处的枝叶间,一个脸盆大的鸟窝在晚风中若隐若现。霎时,众人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没了声。只有铁头他爹娘的号啕,在人堆里奔来撞去。
村长来时,树下已围了很多人,村长身后那几个动物脑袋,像拔萝卜一样,抓住围观者的头发或肩膀,给村长闪出了一条路。村长站在树下,被铁头他爹娘的哭声笼罩着,一时间神情凝重。他命令身后的狗头和狼头们,想办法把铁头的尸体取下来。说罢,村长蹲在铁头爹娘面前,轻拍着他们的肩膀,语带关切地说:别哭啦,都这样了,看开点吧。
说罢,村长从地上站了起来。
这时,树下的杨贵往人群外走,边走边说:自己人都杀!自己人都开始杀了哩!村长闻声,愤怒地转过身,对着杨贵砸去一句:杨贵,出头的椽子早烂!
杨贵轻哼了一声,匆匆走了。
杨贵走后,村长对着另外几个动物脑袋说:“快把孩娃们赶走!”听到这句话,我们心里十万个不情愿。直到那几个狗头、狼头对着我们怒吼,伙伴们才悻悻离去。我假装扭伤了脚,走在最后,又听到村长对众人说:不能让孩娃们知道,有些事永远不能让孩娃们知道。听到这里,我的脚步更慢了。还没等我听清后一句话,屁股上就莫名其妙挨了一脚,整个人差点没一头栽在地上。我回头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狗头,它上来还要踹,我爬起来伸手护着屁股,贼一般仓皇逃了。
三 掠过窗前的飞鸟像一声叹息
下葬那天,哭声熄了,铁头的棺材被两个人抬着,铁头爹娘目光呆滞,相互搀着,跟着铁头的棺材往东地走。两人抬棺,爹娘随后,四个人,一具棺,走在豫东平原溽热的阡陌上。村长不让哭,也就不能再哭哩,这些都是规矩。小羊庄不大,但规矩不少,“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村长的嘴边话。在小羊庄熬日月,谁能不按照小羊庄的规矩来?不让人哭,那就让风代替着哭,不让泪流,那就让汗代替着泪流吧。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哩?
那一天平原烫脚,汗落下去,伴着“嗞”的一声,像落在烧红的铁板上,紧跟着从汗水消失的地方,腾起一股微弱白烟,那白烟歪歪扭扭,继而消散无踪,像一个人的死。
铁头的死因,在小羊庄大人的嘴巴和嘴巴之间来回咀嚼,但真相,是永远不可能传到孩子们的耳朵里去的。 那一年,当我满脸困惑,向娘问起铁头的死因时,她总是一脸惊恐,转而怒嗔道:小孩子家不要乱打听!
时至今日,我依旧常常去想,铁头的死跟他头顶那个鸟窝有什么关系?那个鸟窝跟鬼仔岭有什么关系?鬼仔岭为什么成了一片废墟?曾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为什么突然变成一群鸟雀飞走了?他们为什么会变成一群鸟雀?而村人为什么阻挠我去调查这些事情?这些神秘事件的背后,跟小羊庄里的人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问题至今还困扰着我。
然而,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那一天,在豫东平原迷雾笼罩的阡陌上,是谁把咬牙切齿砸在了我的后脑勺上?是小羊庄里的一个人,又好像是小羊庄里的所有人……我不能再往下想了,我的脑袋疼得厉害。如今,我只能死尸般躺在床上,侧过头,把目光扔向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掠过窗前的飞鸟像一声叹息。
四 我的大脑和双腿开始不稳固了
伤痊愈后,我走在村子里,众人看我,像看一个怪物,迎面走来也不再跟我说话,我主动招呼他们,他们最多“嗯”一声,然后目不转睛盯着我。那目光令我如坐针毡,难道我长了两个脑袋八只眼不成?我回到家,对着镜子端详很久,鼻子眼睛耳朵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头没扁,脸没丢,但他们为什么看我像看一个怪物?
屋漏偏又连阴雨,那段时间里,父亲对我的态度也骤然转变。平日里,无论他在干吗,哪怕正在与人谈笑,只要看到我,便立刻收起笑,一脸冰霜地瞪着我。“爹,为啥这么恨我?”那天,我向着他的一脸冰霜走去,他迅速抽起猪圈上那把明晃晃的砍柴刀,从牙缝里迸出一个“杀”字,然后举起刀,对着身边那棵手臂般粗细的柿子树就是一刀。柿子树被拦腰砍断的同时,我惊出一身冷汗,连连后退。这时,母亲从屋里跑出来,夺过他手里的刀扔进猪圈的粪堆上,然后指着我对父亲吼道:那不是你的亲骨肉?父亲双眼通红,像陷入了魔怔一般,那个字又从他嘴里发出,子弹般朝我射来:杀!
父亲的变化令我心寒,一直以来,他生性木讷,踏实肯干,对我和母亲也是关爱备至。然而那一刻的父亲表情狰狞,行为极端,和以前的那个温和寡言的父亲判若两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从一开始他就强烈反对我调查鬼仔岭,却又不善言说,很多不满情绪淤积在心,挤压久了,便成了这般模样。
那段时间,母亲担心我与父亲之间,因这事而起隔阂,产生敌对情绪,因此她总在临睡前来我屋里,开导我:
“他怕你有个闪失,他就你一个儿子。”继而又说,“鬼仔岭的事儿……你想知道,但村长会让你知道吗?你非要知道,那将会有多危险你知道吗?我们就你一个儿子……”说着说着,母亲哭出了声。
在母亲的抽泣声中,我再次忍不住问道:“娘,你们为什么对鬼仔岭闭口不言?鬼仔岭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给我讲讲吧娘!”
听到我的恳求,母亲赶紧从床头站了起来,摇着头,哽咽着走了。
母亲走后,我辗转难眠,月光从窗缝间爬了进来,在床上缓缓移动。我从床上下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推门而出。
村子十分静寂,月光哗哗啦啦地在地上流着,我走上田野,走在小羊庄的皮肤上,走在小羊庄的肠子里和血管中。我感到双腿间像安装了一台动力强劲的马达般在了无边际的平原上走来走去,我感到身后有无数块砖头和冷笑尾随着我。但我沒有丝毫恐惧,依旧走啊走啊,越走越快,困扰我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的后脑勺开始隐隐作痛:我感到空,我感到冷,我感到我的双脚里有另一双脚……
作者简介:智啊威,1991年出生于河南周口。有小说刊发于《天涯》《山花》《作品》《青年作家》《文艺报》《广州文艺》、“大益文学”第三辑《寓》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