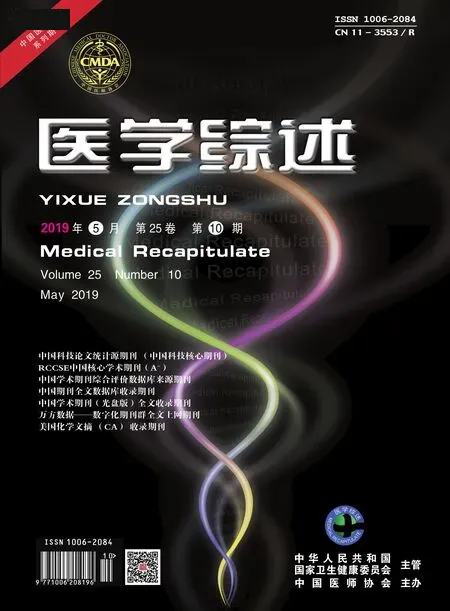脑脊液酶谱在脑血管疾病中的进展
2019-02-27许清源颜立娇刘辰庚王培昌
许清源,颜立娇,刘辰庚,王培昌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检验科,北京 100053; 2.首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北京 100053;3.青海茫崖石棉矿区中心医院检验科,青海 海西 816401)
近年来,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上升,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脑血管疾病根据病因和发病机制不同可分为出血性脑血管疾病和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两类,急性脑血管疾病又称脑卒中,中医称作中风。目前,脑卒中是全球第一大致残原因,也是我国的首位致死原因,具有高病死率和高致残率等特点,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的负担[1]。大脑处在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包围的环境中,CSF对脑组织有支持、营养和保护的作用,并与脑组织的细胞外液处于动态平衡中。发生脑血管意外时,脑组织缺血缺氧或被压迫,导致神经细胞损伤、坏死、细胞膜通透性改变,从而使脑细胞、脑血管中的物质(包括一些酶类)进入CSF,因此 CSF中的酶可出现质或量的改变。血脑屏障是脑组织的天然屏障,使血液物质很难通过血脑屏障影响CSF的成分,同时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可能标志物向系统血液的迁移也减少,因此CSF中酶的变化能更精确地反映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情况,并使脑脊液酶分析成为评价中枢神经系统各种病理改变的方法,可在脑血管疾病早期协助诊断脑血管疾病,对其严重程度、预后等进行判断。现就近年来脑血管疾病的CSF中酶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血红素加氧酶
血红素加氧酶(heme oxygenase,HO)是血红素降解过程的限速酶,哺乳动物细胞表达诱导型HO(HO-1)和结构型HO(HO-2)两种同工酶。最初被描述的第3种同工酶HO-3事实上源于HO-2[2]。HO-2在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分布广泛且表达稳定,糖皮质激素是唯一诱导因素[3]。正常情况下,脑内HO的活性主要表现为HO-2的活性,而HO-1只表达于部分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在脑中很难被检测到。仅在高氧、缺氧、热休克、脑缺血、脑出血、脑外伤、某些药物刺激等应激状况下,HO-1才在神经胶质细胞大量表达[4]。
脑血流持续中断5 min,神经细胞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出现脑梗死。对转基因鼠的实验发现,脑缺血后6 h、24 h及发生永久局灶性脑缺血损伤时,过量表达HO-1的转基因鼠的梗死灶体积和脑水肿程度均较非转基因鼠明显缩小或减轻,梗死灶周围的缺血半暗带也明显缩窄[5]。另有研究发现,大鼠脑缺血后HO-1表达增高,缺血再灌注后HO-1表达也增加,并在血管再通后48 h达到高峰[6],以上研究都表明,HO-1的表达增加能保护脑组织,减少神经细胞的损伤和死亡。有实验研究发现,HO-1的过表达可使大鼠星形胶质细胞的蛋白和脂质过氧化,导致细胞死亡,HO抑制剂能减弱这些作用[7]。可见,若能使HO-1适量表达则可为脑梗死的治疗提供帮助。
脑出血后大多数脑组织的损伤不能直接归因于缺血,可能是血肿释放的毒素引发的损伤级联反应,导致细胞丢失和预后不良。体外实验发现,在含有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的初级细胞培养物中,与血块共培养的大多数细胞损失可归因于血红素介导的氧化应激和兴奋毒性[8]。Chenroetling和Regan等[9]对血液注射性脑出血模型的实验研究发现,用胶质原纤维酸性蛋白基因启动子驱动转基因小鼠表达人HO-1,血液注射7 h后,转基因鼠组同侧纹状体HO-1表达量超过野生型对照组鼠7倍,主要定位于血管周围星形胶质细胞,结果显示转基因鼠组死亡率显著降低(34.8%比0%),这与纹状体细胞活力增加、血脑屏障破坏和神经学缺陷减少有关。实验证据表明,HO-1升高对脑出血的良好预后有重要作用[10-11]。此外,Wang等[11]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大鼠对照组比较HO-2基因缺失大鼠,脑损伤的体积在脑出血后第1天和第3天分别增加30%和67%;神经功能的损伤在第1天和第3天分别增加26%和38%。由此可见,HO-1和HO-2在脑血管疾病以及再灌注损伤的治疗中起重要作用,可作为药物作用的新靶点,改善患者预后。
2 超氧化物歧化酶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SODs)是生物体内重要的抗氧化酶,能催化超氧阴离子O2-发生歧化反应,清除体内氧自由基,平衡机体的氧化与抗氧化系统,保护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害。SOD有3种同工酶,分别位于胞质[分子量为32 000的CuZnSOD(SOD1)]、线粒体[分子量为85 000的MnSOD(SOD2)]和细胞外[分泌性EC-SOD(SOD3),分子量为135 000]。
在缺血性卒中期间,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在急性期和神经炎症阶段受到损伤,其中活性氧类的产生和活化免疫细胞的侵袭是导致神经变性的重要原因。对急性脑卒中患者临床CSF样本的SOD水平进行检测发现,发生脑缺血的时间越久,CSF中SOD水平越高,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害的程度越重;急性期CSF中SOD水平较高患者的预后往往较差;SOD在CSF中的消除时间较短,提示它可以是急性期中枢神经系统受缺血影响细胞数量的定量标志,但可能不是细胞功能永久性丧失的良好标志,对预后判断有一定的作用[12]。Davis和Pennypacker[13]的研究指出,SOD3过表达作为神经保护策略的有效性源于其在大脑中低水平的基础表达,SOD1和SOD2在基础条件下就处于高度表达状态,但SOD3仅在损伤期间神经元中被诱导表达。以上数据表明,SOD3的上调在脑缺血期间可能具有强大的神经保护作用,氧化应激在不同疾病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在神经系统疾病中,其对神经元的损伤作用应引起关注。在大多数情形下,由于CSF中较完善的氧化还原缓冲体系,使其处于合理范围内,但在某些疾病中,尤其是脑血管疾病等急性神经系统疾病,其平衡遭到破坏,故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监控。
脑卒中只造成局部的脑组织缺血,缺血区常围绕受缺血影响小的水肿区,可能由氧化应激损伤导致。有实验表明,脑卒中伴有或不伴脑水肿患者的SOD水平均升高,但不伴脑水肿患者的SOD水平更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4]。由此可见,SOD可阻止脑卒中后的继发性脑损伤,具有治疗卒中后脑水肿的潜在价值,但应建立在患者梗死灶大小相似的条件下,才可将脑水肿组和无脑水肿组进行比较,与前述脑梗死灶越大,SOD水平越高,预后越差的结论不相斥。
3 烯醇化酶
烯醇化酶是催化2-磷酸-D-甘油酯和磷酸烯醇式丙酮酸在糖酵解途径中相互转化的二聚酶,可根据所含的亚单位分为αα、ββ、γγ、αβ、αγ五种同工酶。在神经系统中,神经胶质细胞只含αα烯醇化酶,而γγ烯醇化酶只局限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内,因此γγ烯醇化酶又称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NSE不与细胞骨架相结合,易于释放,当发生脑损伤时,CSF中NSE可发生显著变化,能灵敏地反映脑损伤程度。研究显示,脑梗死患者CSF中具有免疫活性的α、γ烯醇酶浓度都随梗死灶体积的增大以及神经系统功能性损害程度的加重而升高,且α值与γ值的升高具有强相关性,α烯醇酶上升的速度是γ烯醇酶的 4.8倍[15]。CSF中的烯醇酶水平与临床预后有关,α烯醇酶与γ烯醇酶浓度之和越高(>50 μg/L),预后越差;所有预后较好患者的CSF总烯醇酶<50 μg/L。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患者CSF中的NSE均会升高,但Brouns等[16]测定89例卒中后8.7 h的CSF中NSE水平的研究发现,NSE水平与卒中严重程度、位置和预后无相关性,可能是CSF样本抽取时间过早,NSE还未释放到CSF中所致,有数据显示,CSF中NSE的显著升高一般发生在脑缺血后24~48 h[17]。此外,对比观察脑出血患者与正常体检者发现,脑出血组血清NSE水平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和病灶大小呈正相关,即NSE水平越高,病情越严重,神经功能损伤越严重[18]。NSE主要存在于神经细胞中,血清NSE升高是血脑屏障破坏使NSE从脑细胞中逸出进入血液循环所致,故可推测,CSF中NSE对评估脑出血病情和预后更具价值。除脑血管疾病外,脑肿瘤、脑炎、脑膜炎、痴呆、癫痫、脑外伤以及多发性硬化等可引起脑组织损伤的疾病中,患者CSF烯醇化酶都会升高。烯醇化酶虽然对脑血管疾病的诊断没有特异性,但它对病情评估,调整治疗方案,判断预后有重要作用,在不同神经系统损伤中,烯醇化酶水平或活性的差别是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4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Lp-PLA2)是血管内膜中巨噬细胞、T细胞和肥大细胞分泌的炎性标志物,可特异性催化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中磷脂酰胆碱水解,生成溶血磷脂酰胆碱和氧化非酯化脂肪酸等脂类促炎物质,进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19]。
Lp-PLA2的数量和活性与种族、性别、脂质代谢以及他汀类降脂药和新型Lp-PLA2抑制剂的应用有关。在平衡这些因素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尤其是复杂斑块和易破裂的纤维帽中仍发现Lp-PLA2活性上调。有研究表明,血浆中Lp-PLA2活性和浓度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急性卒中患者神经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或复发性脑卒中的短期风险相关[20-21]。另有实验发现,伴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脑卒中患者,尤其是颈内动脉或大脑中动脉闭塞患者,对静脉溶栓有抵抗作用。大量研究表明,Lp-PLA2是冠心病和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22-29]。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批准LP-PLA2可用于预测冠心病和缺血性卒中风险[30]。有文献报道,血浆中Lp-PLA2的活性是女性患无症状性脑梗死的重要预测因子,但对男性并无此作用[29]。
脑血栓形成是脑梗死的主要发病机制之一,其病变基础是脑动脉粥样硬化,可见,CSF中Lp-PLA2水平与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能密切相关。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CSF中的Lp-PLA2几乎全部来自脑血管,故CSF中的Lp-PLA2能否准确预测脑梗死,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对脑血管疾病患者CSF中Lp-PLA2的研究有限,对Lp-PLA2的研究几乎都是采用血清学样本,Ye等[31]第一次报道有关测定CSF中Lp-PLA2活性的研究发现,CSF中有Lp-PLA2存在,且可测量,这将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5 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天冬氨酸转氨酶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能催化肌酸和ATP发生可逆反应,形成磷酸肌酸和ADP。磷酸肌酸可被视为“高能磷酸盐”的储存库,能够按需供应ATP,对有间歇性高能量需求细胞的能量稳态起重要作用。CK是由2个亚单位组成的二聚体,形成CK-MM、CK-MB和CK-BB三个不同的亚型,CK-MM主要存在于骨骼肌和心肌中;CK-MB主要位于心肌中;而CK-BB主要分布于脑组织中,CSF中测得的CK几乎都是CK-BB[32]。乳酸脱氢酶是一种在糖酵解酶和糖异生过程中催化乳酸和丙酮酸之间氧化还原反应的重要酶类,广泛存在于机体各种组织细胞的胞质中。当脑细胞损伤时,乳酸脱氢酶可从细胞内渗出而被检测到。天冬氨酸转氨酶是催化L-门冬氨酸与α-酮戊二酸之间氨基转移反应的酶,主要分布于心肌与肝脏的线粒体内,临床常作为肝实质和心肌损害的辅助检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属于血管内皮细胞膜结合酶,广泛分布于人体各组织,以肺中含量最高,能催化血管紧张素Ⅰ转化为血管紧张素Ⅱ,使缓激态失活,导致血管收缩,增加血管压力。
6 小 结
脑血管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包括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动脉栓塞、动脉狭窄和闭塞、脑动脉炎、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瘤、颅内血管畸形等,最终引起脑组织缺血或出血,因此,能反映以上病理变化的CSF酶谱可对脑血管疾病有预测和诊断作用。目前,对脑血管疾病的诊断主要依赖患者症状、影像学检查和脑电图,而用于测定CSF中酶的实验室检查尚不完善。影像学技术在脑血管疾病的诊断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不可缺少的检查之一,但并不适用于生命体征不稳定或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当患者出现症状并在影像学检查表现出异常时,往往疾病已经进入晚期,甚至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和死亡。因此,探测脑血管疾病生化指标的改变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现已对CSF中一些与脑血管疾病有关的酶进行研究,但尚未找到特异的酶,这与CSF中酶的检测方法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关系。在未来研究中,若能在CSF中找到可灵敏反映脑血管疾病早期的某种特异酶或在脑血管疾病未发生时进行风险评估,将为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并大大减少脑血管疾病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