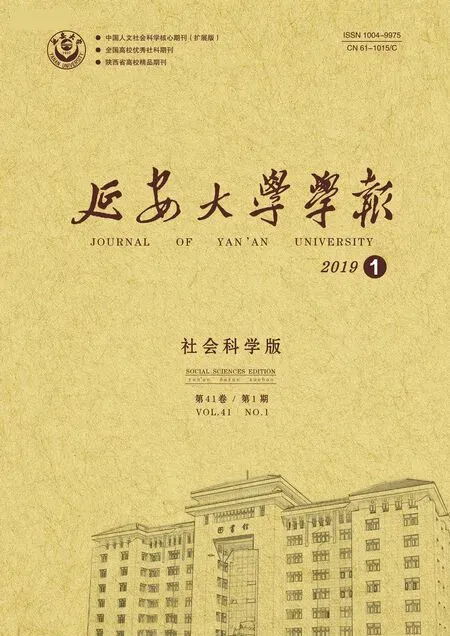论曹禺戏剧与延安时期的“大戏热”
2019-02-26王俊虎
王俊虎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从1940年开始到1942年初,延安所演出的国统区的戏剧作品共有十部,其中曹禺个人的剧作就占了四部,分别是《日出》《雷雨》《北京人》和《蜕变》。这四部剧作与抗日战争内容直接相关的只有《蜕变》。在当时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与抗战无关的国统区的曹禺的这些“大戏”,之所以会形成一股热潮,并在解放区民众中广为流传,这与延安时期的文艺环境、曹禺本人的生活经历及其剧作的艺术魅力等是密切相关的。
一、延安时期的“大戏热”与曹禺戏剧的艺术魅力
(一)延安时期“大戏热”的原因
延安时期“大戏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时高质量的话剧剧本比较匮乏,一度甚至出现“剧本荒”的现象;二是人民群众对抗战以来千篇一律的抗战剧、阶级斗争剧产生了审美疲劳。
自抗战爆发以来,延安几乎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投入满腔的热情进行文艺创作,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都基本与抗战相关。在严峻的战时环境中,大部分文艺工作者来不及仔细揣摩作品的艺术质量,当时虽然出现了数量不少的抗战剧作,但大部分作品难免粗制滥造,以至到1940年,抗战已经持续了三年,文艺工作者把能想到的、能创作的题材都进行了挖掘,但很多文艺工作者还是感到能够进入创作的东西越来越少。因此,话剧剧本创作的数量日渐减少,一度甚至出现剧本荒现象。如《中央日报》在1939年9月30日星期六第四版刊登王潔之的《谈今日戏剧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提到了戏剧的“剧本荒”问题,“至于戏剧,因要求者的量的增加,表出的形式比较复杂,具体,而且严正,剧本的产量反而减少了。剧本荒这现象自然是更明显的”。[1]
另一个原因,是人民群众对抗战以来的戏剧作品千篇一律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疲惫之感,渴望艺术水平更高的剧作,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讲话》中所说:“但是普及工作与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普及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总是一样的『小放牛』,……,那么普及者与被普及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岂不又变成没有意义了吗?”[2]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看到了文艺普及的必要性,同时也清楚文艺提高的重要性。解放区文艺不能一味地只抓普及而忽视提高,人民群众对于文艺作品的欣赏水平和对艺术作品的要求也自然会逐渐提高的,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因此,在毛泽东的发起和支持之下,延安从1940年开始至1942年初,形成了一股演出大戏的热潮。
(二)曹禺戏剧作品缘何成为“大戏热”的焦点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之下,国统区作家曹禺的戏剧在延安解放区成为戏剧舞台演出的焦点而备受关注。曹禺戏剧作品缘何成为延安时期“大戏热”的焦点?这与曹禺本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剧作本身的艺术魅力有很大的关系。
曹禺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对封建制度的感受比其他家庭出身的作家自然要深刻。曹禺自幼便生活在带有浓厚封建专制色彩的家庭,官僚家庭的专制、腐朽、堕落,他均耳濡目染,也甚为熟悉,这也成为他日后戏剧创作的主要素材。在童年时期,曹禺的养母经常带着曹禺去看戏,“他不但看到京剧,还看到不少地方戏,如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等”。[3]5这些经历都对曹禺产生着深远持久的影响,也使得他日后的戏剧更“接地气”,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
1922年,12岁的曹禺在南开中学读书。南开中学自由轻松的学习环境与浓厚的校园戏剧演出氛围使得曹禺的戏剧天赋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不仅是《南开周刊》的戏剧编辑,而且还是话剧排演的主要演员。曹禺在创作戏剧、演出戏剧的过程中更能体会到观众的观剧心理和情感,他特别重视观众的欣赏趣味和习惯,这也是曹禺的剧作深受群众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扩及全国,身在南开中学的曹禺直接或间接地都深受影响。正如田本相在《曹禺剧作论》中所说的:“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使年青的曹禺看到反动统治的黑暗,共产党人英勇牺牲献身解放事业的精神,更使他心中升腾起反抗热情,加强着改变社会的责任感。”[3]7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曹禺不论是行为还是思想上,都同共产党更为亲近,特别是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统区人民在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统治下民不聊生,使曹禺更加坚定了走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决心。正如曹禺在《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和田本相同志的谈话》一文中所说:“从抗战开始,我同共产党人接触越来越多了。一九三八年,在重庆见到周总理,谈的就更深了,周总理是十分坦率的,他给我多年的教育和帮助,是我终身难忘的。”[3]372-373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战积极性远不如抗战开始阶段,同共产党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并故意制造一些摩擦事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曹禺的戏剧如《雷雨》《蜕变》等,遭到国民党的严格审查甚至禁演。曹禺在其剧作中对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讽刺,戳到了国民党的痛处。延安解放区之所以对国统区禁演的曹禺的剧作非常欢迎,不仅是因为曹禺本人的进步思想符合共产党的需求,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争取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到民族抗战的正义事业之中,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国民党的丑恶嘴脸。因此,1940年至1942年延安出现了演出曹禺剧作的热潮是不奇怪的。
延安时期上演的曹禺剧作,虽然大部分剧作的内容与抗战无关,比如《雷雨》《北京人》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曹禺的剧作在民众中备受欢迎的程度。例如,《解放日报》于1942年1月26日星期一第四版的《科学园地》第九期刊登李直的《谈谈雷雨》一文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民众对曹禺剧作的喜爱。这本是一篇科学性很强的文章,主要讲述的是在打雷下雨时,如何避免遭到雷劈,但文中一开头却写到:“你看过《雷雨》吧!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反映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话剧。”[4]一篇科普性很强的文章,却以一部文学性的剧作作为科学论证的切入点,从中可以看出曹禺的剧作受欢迎的程度以及被民众认可的程度都是非常高的。
曹禺剧作所具有的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剧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情感不仅符合边区民众对高质量、高水准剧作的渴望,而且也契合毛泽东后来在《讲话》中所提到的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文艺思想。正如《新华日报》于1941年1月7日星期二第四版刊登惊秋的《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上)》一文,文中在提到延安演大戏、洋戏的原因时说到:“……曹禺的『日出』『雷雨』等等。在抗战空气最强烈的延安,演出如上述的与抗战无直接关系的戏,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反映抗战现实的剧本荒,但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在延安戏剧水准的提高,以及使观众从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的历史的认识里,更深的去了解抗战的现实这一意义上。”[5]曹禺的《雷雨》与《日出》虽然与当时抗战的时代内容联系并不密切,但其剧作所具有的反封建的思想,有助于使人民群众更好地珍惜解放区开明、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动员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而且,相比于抗战初期一些“急就章”、来不及进行艺术雕琢与加工的戏剧作品来说,《雷雨》与《日出》不论是在人物刻画、语言提炼,还是在谋篇布局、艺术结构等方面,都是艺术水准高并值得戏剧工作者学习与借鉴的优秀作品。
《蜕变》是一部与抗战密切相关的剧作,完成于1939年,1940年首次在重庆上演,却遭到国民党的审查与刁难,勒令修改剧本,最后又遭到蒋介石的禁演,这是因为《蜕变》对国民党的腐朽与黑暗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与讽刺,对共产党等“新生命”“新生力量”进行了歌颂与赞扬。1940年延安的陕北公学文艺工作队首次演出了《蜕变》,好评如潮,正如《新中华报》于1940年11月10日第四版刊登叶澜的《略谈<蜕变>》一文中所说:“《蜕变》是一面说明了目前阴暗正是为黎明前‘新陈代谢’的必然过程,……走向光明的途径。”[6]《蜕变》具有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抗战的作用,而且“《蜕变》这样的好剧本只有在追求真理与爱护真理的延安才能上演了十一天之久……”。[6]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曹禺的《蜕变》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延安在抗战时期反复上演曹禺的“大戏”,不仅显示出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文艺氛围以及共产党宽广包容的胸怀,而且《蜕变》在延安反复上演,也说明了剧作的受欢迎程度和剧作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北京人》与前面三部剧作不同的是,这部剧作从开始构思到最后的完成、演出,都与共产党的影响密不可分。研究曹禺的专家华忱之在《曹禺剧作艺术探索》中说:“《北京人》创作的成功,首先是和党的关怀教育,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作者的启迪帮助分不开的。”[7]185周恩来多次接见曹禺,不论是从创作还是思想上,对曹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得曹禺对抗战的形势、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作者在江安创作《北京人》的过程中,随时都得到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支持”。[7]186正是在共产党的支持与关怀之下,曹禺在创作和思想上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他本人对革命、对抗战、对共产党都充满了希望。《北京人》虽然没有对抗战的时代内容进行直接的描写,但“剧本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大家庭内部的种种倾轧,揭露了封建阶级精神的空虚、生活的腐烂,以及他们的无法挽救的没落、死亡的命运”。[8]《北京人》相对于曹禺之前的剧作,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又进了一步,对革命的方向也更加坚定和明确,又加上这部戏从创作到完成,都有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正如《解放日报》于1942年4月27日第四版刊登矛盾的《读<北京人>》一文中所说:“绝不能低估《北京人》的价值,低估他的社会意义。”[9]因此,演出《北京人》在延安形成了热潮,1942年5月,西北文艺工作团接连多天演出《北京人》,得到观众和延安文人的喜爱。
二、对曹禺剧作成为“大戏热”演出的焦点剧目的反思
国统区作家曹禺的剧作在延安解放区引起关注并得到大范围的演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艺现象。曹禺剧作成为延安时期“大戏热”演出的焦点剧目可以带来如下影响与启示。
首先,有助于广大民众认清政治形势,坚定抗战决心。曹禺的剧作《蜕变》多次上演,好评如潮,深受解放区军民的喜爱。地理环境极为闭塞的边区军民可以通过《蜕变》了解到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与腐败,有助于认清国民党“嘴上一套,背地一套”的虚伪嘴脸。与此同时,也有益于团结更多真心抗战的人士,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其次,有助于拓宽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与普通民众的艺术视野。曹禺戏剧不仅满足了当时解放区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水平剧作的渴望,而且也有助于戏剧工作者、群众等学习和借鉴曹禺戏剧的经验,提高剧作的艺术质量。延安时期,戏剧的专门人才相对比较匮乏,戏剧工作者的专业知识、艺术素养等并不高,通过反复演出大戏,使他们从不断的实践之中,学习和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艺术素养。
最后,有助于加深文艺工作者对戏剧民族化、大众化的认识,而且在面对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选择时,曹禺的剧作作出了很好地示范以及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曹禺的剧作,不论是《雷雨》,还是《北京人》,在如何借鉴外来文化和继承发扬本民族文化,以及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怎样充分地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平和习惯等方面为延安的戏剧工作者甚至边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例如《雷雨》,曹禺在一定程度上有吸收和借鉴外国戏剧的地方,但突出和强调的是本民族自己的特色,并没有因为借鉴外国戏剧而丢掉自己本民族的东西。由于曹禺本人有过演出戏剧的经历,他知道和了解观众的口味和需求,比如在《雷雨》的创作主旨上,曹禺采用的是普通百姓熟悉的主题和内容;在情节结构上,他深知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他们喜欢看有故事内容、有情节穿插和矛盾冲突性强的剧作,正如曹禺自己所说:“他们要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10]502因此,在安排和组织故事的情节结构时,曹禺站在观众的角度和位置去进行谋篇布局。另外,在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方面,《雷雨》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的艺术,为剧作营造出一种诗意的氛围和风格。比如《雷雨》第三幕中对鲁家屋外情形的描写:“渐渐乘凉的人散了,四周围静下来,雷又隐隐地响着,青蛙像是吓得不敢多叫,风又吹起来,柳叶沙沙地。”[10]71这种诗意氛围的营造,是和本民族的文化艺术相融合的产物。除此之外,《雷雨》在语言的选用上,具有日常化、个性化的特点,善于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提炼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人物的语言和自己的身份、文化素养、社会地位等都是相吻合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
曹禺是一位善于从观众、普通民众的角度和立场去进行戏剧创作的剧作家,而且也善于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并从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并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在戏剧、诗歌等领域的创作。比如,“大戏热”之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成立、延安街头诗运动,还有文艺家们对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如对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的重视和发掘,创作出至今仍广为流传的《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等艺术水准高又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这些优秀的、带有民族风格的文艺作品的出现与“大戏热”中曹禺的剧作被频繁上演是分不开的,或者可以说曹禺的剧作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文艺工作者对普通民众欣赏趣味的重视以及对本民族文化和文艺优良传统的发掘热情。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延安时期“大戏热”聚焦于曹禺剧作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反复演出的曹禺剧作,与现实抗战生活密切相关的只有一部《蜕变》,而缺少正面反映边区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动人事例和人物形象,而且演大戏对演出地点、服装舞台等的要求很高,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物质并不发达的边区来讲,反复演出大戏,会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再加上当时有些剧团以演出大戏为荣,摒弃“小戏”,各个剧团之间也相互攀比,形成一股不良的社会风气。正如《解放日报》于1942年6月28日星期日第二版刊登的一则报讯《延安剧作者座谈会商讨今后剧运方向》中所说:“塞克王震之等同志,谈及延安过去只演大剧只演外国戏,看不起自己写的小戏,是一种应纠正的偏向。”[11]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延安时期的“大戏热”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结语
从1940年至1942年初,不仅延安演出曹禺的剧作,而且前线部队也进行演出,并且很受观众的欢迎和喜爱,比如“贺龙军队的战斗剧社,曾在山西为部队官兵演出了各种内容的话剧,包括《雷雨》……”。[1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曹禺剧作的文学受众是广泛的,不仅普通市民、知识分子喜爱看,前线战士也喜爱看。透过这股演剧热潮不难看出曹禺剧作高超的艺术水准与迷人的艺术魅力。曹禺剧作不是脱离群众与现实生活而高高在上的“供奉之物”,而是与观众的欣赏趣味相契合,善于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汲取营养,无论是剧作的内容、语言,还是情节、结构等都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环境下考察曹禺戏剧热的原因和影响,不仅可以领会曹禺剧作所蕴含的艺术魅力与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理解延安时期的文艺氛围、文艺政策、审美趣味等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