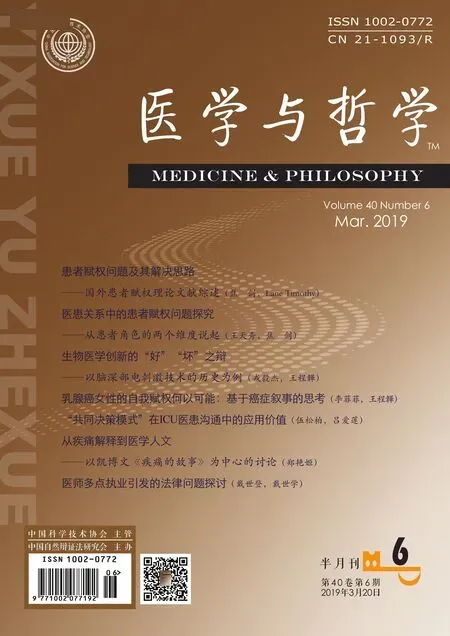乳腺癌女性的自我赋权何以可能:基于癌症叙事的思考
2019-02-25李菲菲王程韡
李菲菲 王程韡
疾痛叙事(illness narratives)强调病人的声音,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生物医学专家话语体系的表达个体苦难与经历的方式[1]。尤其是对慢性病患者而言,其所遭受的折磨除了来自于疾痛,慢性病本身作为破坏性事件造成的人生进程的中断(biographical disruption),更构成了他们深层次的痛苦根源[2-3]。面对慢性病所带来的身体、自我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叙事可以通过疾病归因、消解死亡恐惧等方式帮助病人重新建立起秩序感,病人的“正常”身份认同也在叙事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重塑[4-5]。癌症作为一种严重的慢性病,经常伴随着复发转移的高风险,因此也就更容易导致病人的失序感。癌症病人的叙事对于他们自身也就十分重要,更是获得了医学人文学者的普遍重视[6]。
医学人文学者对于疾痛叙事的关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宏大叙事的生物医学话语日渐式微,大众媒体的发展却使得病人能够便捷地获取疾病相关的知识以挑战医生的权威[7]。早期的疾痛叙事研究探索了医学专业知识所塑造的医生的权威与病人的服从。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Mishler[8]分析了医生与病人话语互动中的规范与秩序,认为医生控制了与病人间的谈话以确保生物医学模式的主导地位,指出了区分病人视角的“生活世界的声音”(voice of the life world)与“医学的声音”(voice of medicine)的重要性。后来的疾痛叙事研究更加聚焦在病人身上,注重体察病人的情感,并结合年龄、社会性别、阶层等因素考察疾病对其人生进程的破坏[9]。Kleinman[10]沿此方向,更加明确地指明了disease与illness的不同,认为前者指向医学上诊断的疾病的病名,而后者更多强调病人的疾痛感受的表达,病人的苦难境况不应再被忽视。Frank[11]66-108则主张进一步结合病人的生活经历来考察疾痛与苦难。同样作为癌症病人,他撰写自传亦分析其他病人的回忆录,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了叙事类型学研究的典型代表。对叙事类型的划分,体现了病人身体、自我与社会的互动及相应的身份认同,也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理论关怀,在疾痛叙事研究的诸多传统中是最具生命力的一条进路。
1 癌症叙事的类型学
Frank[11]67将癌症病人讲故事的方式总结为三类,分别是“恢复叙事”(restitution narrative)、“混乱叙事”(chaos narrative)与“探寻叙事”(quest narrative)。“恢复叙事”最为常见,也往往遵循着“昨天我很健康、今天我生病了、但明天我会重获健康”的模式展开,叙述者也常怀“我会好起来的”信念与心态。这实际上也是Parsons等[12]“病人角色”(sick role)概念的延伸。在结构功能主义者看来,疾病意味着对正常秩序的偏离。病人虽短暂享有卸下工作、生活重任的权利,同时又肩负着努力寻求医疗机构的帮助、让自己尽快好起来的义务。在“病人角色”中,医生作为社会控制的代理人[13],既负责在诊断过后给就诊的人“发放”病人身份,又在鉴定病人是否回归正常方面担任守门人的角色。“病人角色”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那些认为自己着实受身体之痛而又无法获得医学诊断的人,积极地与医生建立联系,行走在为自己(甚至可能并不存在)的疾病寻求医学诊断、争取病人身份的道路上[14]。与“恢复叙事”相反,“混乱叙事”的故事情节为“生活永远不会好起来了”,这种缺乏有序结构的叙事通常只有在回忆起极具破坏性的事件(如大屠杀)时才会出现[11]81。“探寻叙事”则是直面苦痛,对疾痛表现出接纳的态度,将疾痛视为人生中能促使自己成长的财富而不尽然是需要“好起来的”坏事情[11]94。
当然在疾痛叙事的类型学划分上并不存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Robinson[15]就曾以叙事情节为基准,将叙事归纳为“稳定”(stable)、“进步”(progressive)和“退步”(regressive)三种类型。相比之下,Hydén[1]则从讲述者、疾痛与叙事三者间的关系出发,将叙事分为“作为叙事的疾痛”(illness as narrative)、“关于疾痛的叙事”(narrative about illness)、“作为疾痛的叙事”(narrative as illness)。其中,第一类叙事多发生在病人自主表达疾痛感受与经历的情况;第二类则更多出现在医患互动的场景中,如病人表述疾痛以便于医生诊断时;第三类叙事则是无法如常叙事的罕见情况,如脑部受损导致叙事能力的丧失等。除了确定具体叙事类型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叙事类型间的关系亦是探讨的对象。又如Coll-Planas和Visa[16]分析了7位患乳癌的博主在博客中写下的故事,发现在她们的叙事中兼有Frank所说的几种不同的叙事类型,这些叙事类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不过始终需要承认的是,更多的学者是站在Frank的肩膀上不断反思,才将疾痛叙事类型学发展出更为广泛的脉络。
除了展现叙事类型为何(what),包括Frank在内的更多学者也愈发关注起叙事类型何以为是(how)的问题。受到福柯等的影响,“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被认为是导致叙事主体叙事类型多样化的根源[13]。按照福柯等[17]的理解,“自我技术使个体能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或者在他人的帮助下,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进行一系列的操控,完成自我的转变,进而达到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想要达成这种理想的状态,病人需要改变自己“不良”的生活方式,控制饮食和体重并加以锻炼[18];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自我控制和管理[16]。以癌症叙事为例,Thomas-Maclean[19]认为,用Frank叙事类型中恢复叙事的框架来考察癌症叙事并不恰当,因为癌症几乎不可能达到完全康复的状态。一来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复发转移的风险,二来癌症治疗本身也大程度上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如接受了乳房切除术的女性,无论在身体感知还是身份认同方面,都无法恢复如初。只有戴上义乳、穿上衣服的时候,她们才看起来跟其他人“一样”。既然这种恢复难以达到,Thomas-Maclean因此主张用“重建叙事”(reconstruction narrative)来替代“恢复叙事”的表述。类似地,Hansen和Tjørnhøj-Thomsen[20]也认为恢复叙事强调的“生病-接受帮助-治愈”的思路并不成立,而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生病-接受帮助-仿佛治愈”的康复叙事(rehabilitation narrative),这种叙事则通过国家康复机构所提供的“自我技术”话语得到强化。
“自我控制和管理”的叙事背后,是话语秩序的社会控制与国家治理术的整体逻辑[21]。甚至可以认为,是在对多重结构性逻辑的顺从或是抵抗的过程中,个体叙事才成为了可能。例如,在典型的医患二元关系中,医生被认为拥有着更多的专业知识,缺乏专业知识或仅有外行知识(lay knowledge)的人在生病后应积极地寻求医生的帮助,被期待遵医嘱尽快“好起来”,进而才产生了恢复、重建或是康复叙事。殊不知以医生为代表的专业群体,正是现代国家规避高福利负担困境的代言人。叙事的归属终将是权力而不是他们自己。
2 接受抑或拒斥癌症幸存者身份
对于癌症病人而言,“好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获得某种“幸存者身份”。身为医生的Fitzhugh Mullan首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使用了“幸存者”这一提法描述了自己的患癌经历。此后,他更是倡导把幸存者的定义提前到癌症得到确诊的那一刻,并建立起国家癌症幸存者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Cancer Survivorship,NCCS),致力于推动癌症“受害者”(victim)观念向“幸存者”转变[22]。无可否认,“幸存者”叙事是百分之百符合“病人角色”期待的。但“幸存者”的表述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比起“受害者”、“病人”、“得癌的人”(person with cancer)等身份,“幸存”暗示着面对疾病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抑或用专业的话讲“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23]。事实上,“幸存者”一词常常与“战争”这个极具男性气质的隐喻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癌抗争被誉为跟自我的战斗,身体被比作战区,癌症是敌人,医学专家则扮演着英雄的角色[24]。
然而,“像男人一样战斗”并不总会得到人们的接受。例如,在很多社会中,女性总是被要求遵从独特的女性气质的规范来要求自身以符合社会性别的秩序[25]。女性气质并不天然地等同于男性气质的反面,但却大概率与战争的隐喻无关。如在Mathews[26]观察的北卡罗莱纳州一个名为H.E.L.P的乳癌互助小组中,小组中的成员就拒绝用“战争”来形容自己的癌症经历。比起乐观、感恩地接受“幸存者”的身份,她们更乐于以一种女性独具的方式直面患癌后的负面情绪。
但始终不可否认的是,负面情绪的产生根源于女性角色和病人身份的天然对立。毕竟乳腺癌对女性气质的威胁,会直接地体现在女性身体和家庭职责的层面之上。一方面在男性霸权的文化当中,女性气质强调女性的附属地位以及身体特殊部位,如胸部和毛发特征的性吸引力[27]。得了乳腺癌,可能意味着头发脱落、失去乳房,手术部位甚至会出现癌性伤口、散发出阵阵恶臭。残缺的身体一方面可能令她们的伴侣望而生畏,同时“治疗又会带来雌激素分泌减少,导致提早绝经和其他妇科疾病,从而影响性生活的满意度”[28]。即使存在乳房重建的选项,但正如Ericksen[29]的被访者所描述的那样,“重建后的乳房无论是从外观抑或主观感受上,都与手术前不一样”。被访者中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提到了做完重建手术后乳房依旧难看,而丈夫对这一点显然很介意,“他假装(重建的乳房)没有使他丧失性趣,但是他不会去摸(重建的乳房),他说他不摸是因为我不想让他摸”。另一方面,女性长久以来持家者(homemaker)的形象本身就意味着自我牺牲。因而当女性的家庭角色发生转变,即患癌后不但不能照顾家人,反而需要家人照顾时,这样的变化通常会使很多女性感到不适应[30]。罹患癌症也会使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工作甚至失去工作,她们会因既不能供养家庭反而给家庭增添了经济负担而觉得歉疚[31]。
但这样的冲突似乎又是无解的,毕竟医学的逻辑贯穿在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中[32]——经前综合征、怀孕、分娩、更年期……即便是正常的女性也是如此。
3 残缺的身体与抗争的可能
改变的契机在于身体,以及身体与其嵌入的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与环境的耦合——医学人文学者如是发现。当不再试图隐瞒癌症对身体的影响时,乳腺癌女性也就真正地被自我赋权了。
拒绝佩戴义乳是最常见的一种抵抗。比如Frank[13]就援引Lorde的回忆录,讲述了她去医院随诊,不戴义乳时受到护士说教而感到愤慨的经历。在Lorde看来,护士在极力说服自己佩戴义乳时,自己好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作为女权主义者,Lorde甚至借用达荷美亚马逊女战士切除一侧乳房以便射弓的传说,将自己比作“独乳女战士”[11]104。身为作家的Lorde的确能够引经据典,将自己的不满与抵触书写下来直抒胸臆。但对大多数女性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却很难产生如此的勇气。然而,有着包容各种异类的长尾的虚拟网络空间却给她们提供了自我描述、铭刻和重写她们身体的机会,让一个一个孤立的女性联合起来,获得了“解放”和重塑自身的机会。对此,Pitts[33]也认为互联网的匿名性保证了乳腺癌女性可以肆意地分享现实生活中社会要求其必须遮掩的部分,如残缺的身体,以及内心的悲痛与委屈甚至对医学权威的不满等情绪。这种现代性的自我披露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反抗形式。
呼应传统也是乳腺癌女性自我赋权的一种方式。如Kaiser[22]在研究患乳腺癌的女性时发现,这些抗议者不但会反对穿宽松的T恤来遮掩身体的残缺,而且会在一些活动中特意展示女性术后带有疤痕的身体,鼓励大家谈论死亡,表达愤怒、焦虑等情绪。其中的一个名叫Joanna的受访者更是直言自己对“幸存者”身份的排斥:我们是因为污染和(政府)缺少对人类的关爱才患上了癌,现在政府、医疗机构却又给我们贴上“幸存者”的标签,好让我们顾不上思考自己为什么患癌的事情。作者坦言Joanna是田野中唯一一个将“幸存者”标签政治化的报道人。Joanna本人也坦言这种独特的归因模式和她“部分的美国土著血统”有关。Joanna说在美国土著的太阳舞仪式中,人们会刺穿自己的胸部来证明对他人的爱以及他们有能力忍受和去爱。对于Joanna而言,癌症是她的重构装置(reframing device),是她的太阳舞仪式。“我活下来了,我现在更强壮了。”胸口的伤痕就是证明。
无论是“没有人知道你是乳腺癌”,还是Joanna,都向我们展示了生活世界中通过多重结构性逻辑潜在冲突而非单纯调和而被赋权的可能。认同某种角色的正常,就可以坦然接受或者对抗“病人角色”、“女性角色”上世人所认为的不正常。
4 结语
癌症无疑是一种人生进程的中断,但癌症叙事的意义却远不止如此。例如,看了于娟“活着就是王道”的博客(后结集出版为《此生未完成》),很多读者就会留言感慨“在这里,会停下来想,什么才是生命中真正不能割舍的东西?”[34]
实际上,“不能割舍”的本质就是包含“病人角色”在内的各种社会角色的正常。在现代国家规避高福利负担的诉求之下,借助医生的医学凝视[35],病人自发地产生了恢复、重建或是康复的叙事。但我们却认为,作为自我技术的叙事背后存在着包括决定“病人角色”的多重结构性逻辑。而正是对这些的顺从或是抵抗,才使得多样化叙事成为了可能。比如H.E.L.P互助小组中的乳腺癌女性,由于坦然接受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角色”,也就不会再惧怕患癌后的负面情绪。于是女性角色和病人身份的天然冲突以及在女性身体和家庭职责的威胁就似乎没有那么可怕了。又如Lorde以及千千万万个匿名网络博主,当他们尝试以实名或者匿名“书写者”的身份来去标识自身的时候,主动暴露残缺的身体和不满的情绪亦并非难事。再如Joanna即便只是拥有部分“美国土著血统”,却可以直面割乳手术的伤疤,甚至将其作为重构自身的见证。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即便在国家倡导[20]、产业介入[36]所致使的“幸存者”话语流行的情况下,在男权主导的文化当中,乳腺癌女性依然存在着通过向某种结构性逻辑主动皈依从而自我赋权的可能。打开那扇门,美好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