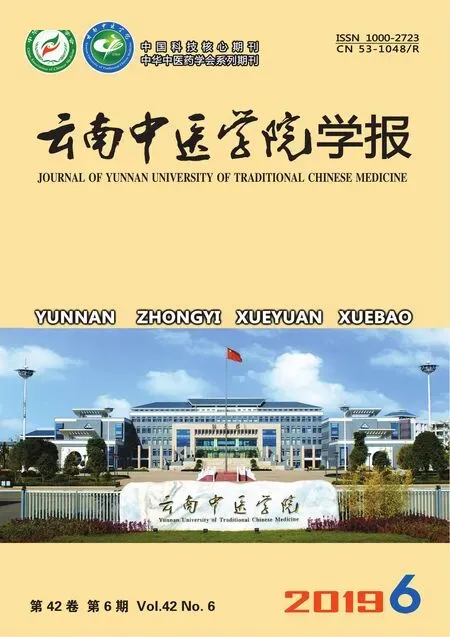黄芩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2019-02-24苏敏敏惠建萍刘越洋杜晓泉刘海涛
苏敏敏,惠建萍,刘越洋,杜晓泉,杨 莉,刘海涛△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2.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二科,陕西 咸阳 712021)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病变主要累及结肠、直肠的黏膜及黏膜下层[1]。该病具有缓解与发作相交替、病程迁延的特点,可以从无症状的炎症发展为广泛结肠炎,增加了患者罹患结肠癌的风险,被视为消化系统的难治性疾病[2]。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UC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不仅降低了患者的生存质量,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西医治疗UC的主要药物为氨基水杨酸类、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但其疗效存在显著个体差异,且不良反应及毒副作用较大[3]。UC归属于中医学“痢疾”“久痢”“肠澼”等范畴。中医药在治疗UC方面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改善临床症状,减少复发频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优势[4]。越来越多的研究为黄芩汤治疗UC提供了丰富的实验和理论依据。
1 黄芩汤的概述
黄芩汤首载于张仲景《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篇》:“太阳与少阳合并,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方中黄芩味苦性寒,是为君药,清泻阳明肠腑热邪,以达坚阴厚肠之效;芍药味酸性寒,是为臣药,可泄热敛阴、缓急止痛。炙甘草味甘性平、大枣味甘性温,共为佐使药,可以调和药性,益气和中以防黄芩败胃伤脾,与芍药相伍,酸甘化阴,增强缓急止痛之力。四药协力共奏清热止利,和中止痛之功,用于治疗腹痛,下利急迫,肛门灼热,舌红苔黄,脉弦数等症。后世治疗痢疾的复方,大多是从本方化裁而来,汪昂《医方集解》中称黄芩汤为“万世治利之祖方”。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黄芩汤具有抗炎、抑菌、调节免疫、保肝降酶、镇痛、减轻化疗药物对胃肠道的毒力等作用[5]。目前临床上广泛用于急性胃肠炎、细菌性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等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6]。中医认为外感邪气、饮食不节、情志内伤等是UC的主要发病诱因,素体本虚是UC形成的基础,病理因素有湿热、痰浊、气滞、瘀血、疫毒等[7]。无论饮食不节还是情志内伤,均可伤及脾胃,导致脾失健运,运化失常,致水湿内生,下趋于肠腑;或直接外感湿邪,湿邪滞留肠腑,日久化热。湿热之邪蕴结肠道,阻碍肠络气血正常运行,气滞血瘀,肠络失养,血败肉腐而形成本病[8]。湿热之邪留恋肠腑经络,也是本病反复发作,迁延难愈的主要原因。《丹溪心法》中明确提出痢疾的病因为“湿热为本”,并提出“湿热瘀积”之为病[9]。可见,在UC整个发病过程中,湿热是其关键病理因素。吕永慧[10]通过对110例UC患者采用系统聚类法分析,得出UC证型分布占比分别是大肠湿热证(25.5%)、肝郁脾虚证(12.7%)、血瘀肠络证(9%)、脾胃气虚证(16.4%)、脾肾阳虚证(9%),其中大肠湿热证占比最高,体现了湿邪与热邪对于UC的重要性。赵坤[11]通过计算机检索PubMed、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等多个数据库,共计309例患者,经Meta分析证实了黄芩汤治疗UC在高治愈率及低不良反应方面均明显优于柳氮磺胺吡啶。阎玲[12]将82例UC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美沙拉嗪)和观察组(美沙拉嗪+黄芩汤加减方),发现观察组在临床疗效及症状改善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血清免疫IgA及IgG的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有效减轻了结肠黏膜血管的炎性反应。由此可见,黄芩汤治疗UC的临床疗效是确切的,具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2 黄芩汤治疗UC的作用机制
2.1 调节免疫
2.1.1 炎性细胞因子 现代研究表明,促炎细胞因子与抑炎细胞因子之间的失衡会导致机体的免疫异常,这是UC发病的重要机制[13]。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量与UC的炎症程度呈正相关,它可以通过影响肠上皮细胞的分泌功能,促使内皮细胞发生水肿,增强细胞的通透性,并使肠道中的一系列活性物质被激活,从而促进肠道黏膜发生病理性损伤,诱导或加重UC的发生[14];抑炎细胞因子主要在UC发病过程中可以起抑制炎症反应,促进肠黏膜上皮损伤修复及愈合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细胞因子具有促炎与抑炎的双重调节作用。张天涵[15]通过对325例UC患者分析,发现大肠湿热证型患者的炎症活动性指标CRP、ESR、FC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证型患者,表明了湿热证型UC与炎症具有高度相关性。丁海荣[16]等将126例UC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黄芩汤颗粒+美沙拉嗪)与对照组(美沙拉嗪),连续治疗2周后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血清IL-6、IL-1β、TNF-α水平均有显著降低,IL-10水平显著升高,但治疗组炎症因子的改善较对照组明显。陈丽等[17]以复合法(三硝基苯磺酸+乙醇)制备的UC大鼠模型为载体,治疗1周后,发现黄芩汤各给药组与模型组相比大鼠血清IL-6、IL-1β、TNF-α 含量显著降低,IL-4 含量显著升高,且结肠的组织病理学改善明显,得出结论:黄芩汤主要通过调节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发挥抗炎作用,从而达到治疗UC的目的。迟宏罡等[18]发现黄芩汤可以有效降低TNBS诱导的UC模型大鼠血清中IL-17和IL-23的水平,并能够明显抑制结肠组织中IL-17和IL-23的mRNA表达。黄芩汤在治疗UC方面发挥抗炎作用的有效活性成份是黄芩苷、白芍苷、甘草酸等。实验研究发现黄芩苷可以降低UC患者血清单核细胞IL-6、IFN-γ等促炎因子的释放,白芍总苷可以降低大鼠血清 TNF-α、IL-6、IL-17、IL-23 的水平等,二者都可升高抑炎因子IL-10的水平,芍药苷还抑制UC小鼠结肠巨噬细胞中NLRP3蛋白表达和IL-1β的释放[19-22]。因此,通过使促炎与抑炎因子趋向平衡,抑制炎症反应,是黄芩汤治疗UC的机理之一。
2.1.2 淋巴细胞亚群 Th1/Th2是CD4+T细胞的2个主要亚群,Th1 可以通过分泌 IL-6、IFN-γ、TNF-α等因子介导细胞免疫和炎症反应,Th2可以通过分泌TGF-β、IL-13、IL-10、IL-5、IL-4 等因子介导体液免疫和抗炎反应[23]。当一方分泌亢进致使Th1/Th2平衡失调,会激活淋巴细胞并释放多种细胞因子,加重肠道黏膜的炎症反应,导致UC的发生[24]。实验研究发现,在TNBS诱导的UC动物模型中,Th1类细胞的水平升高而Th2类细胞水平下降[25]。因此,调节Th1/Th2的平衡,可能会达到减轻UC肠道黏膜炎症的作用。郑学宝[26]等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黄芩汤可以通过降低UC大鼠结肠组织T细胞活化共刺激分子CD28、OX40表达,上调CD4+T细胞活化抑制因子CD152的表达,从而下调过度激活的效应CD4+T细胞。邹颖[27]等发现黄芩汤可以降低UC大鼠结肠组织及血清中IFN-γ和IL-12的表达,提高IL-4和IL-10的表达,明显改善大鼠的症状,减轻结肠黏膜的炎性细胞浸润程度,进一步证实了调节Th1/Th2的平衡是黄芩汤治疗UC的免疫学机制之一。
Th17/Treg是继Th1/Th2之后发现的另一新的淋巴细胞亚群。Th17/Treg的转化平衡是维持肠道免疫稳态的重要因素,Th17细胞分泌IL-17、IL-22等多种效应因子介导炎症反应,IL-6、TGF-β可共同诱导RORyt表达,促进Th17分化,高浓度TGF-β又可以诱导FOXP3的产生,从而促进Treg的分化[28]。研究发现[29],黄芩汤能够降低UC大鼠血清或结肠黏膜IL-17、IL-6、RORyt的水平,增强 TGF-β、FOXP3 的表达,证明调节Th17/Treg的平衡关系也是黄芩汤治疗UC的免疫学机制之一。
2.2 调控信号通路
2.2.1 TLR4/MyD88/NF-κB信号通路 核因子-κB(NF-κB)作为UC发生、发展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转录因子,在调节炎症反应的相关基因表达中起关键作用[30]。TLR4是一种启动炎症反应、参与免疫应答的细胞跨膜受体,主要是通过与其下游的重要接头蛋白髓样分化因子(MyD88)相结合,最终激活下游的NF-κB,促使机体细胞因子的合成与释放,从而引起肠黏膜的炎症反应,导致UC的发生与发展[31]。实验研究发现黄芩汤具有降低 UC大鼠血清 IL-17、NO、PGE2,升高IL-10的作用趋势,明显降低了结肠组织中TLR4、MyD88蛋白的表达[32];黄芩汤还可以显著降低UC模型大鼠血清NO、TNF-α、IL-6和PGE2水平以及大鼠结肠组织NF-κBp65蛋白的表达[33]。因此,从以上可以推断出:黄芩汤治疗UC可能是通过抑制TLR4/MyD88/NF-κB信号通路的活化,进一步下调下游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来实现的。
2.2.2 IL-6/JAK/STAT3通路 JAK/STAT3是一条调控免疫及炎症反应的重要信号通路。IL-6是参与炎症反应的细胞因子,与UC疾病的严重程度、炎症等级及病变范围呈正相关。IL-6可以使JAK激酶活化,进而启动JAK/STAT3通路,调控下游靶基因的转录及蛋白表达,参与炎症调节[34]。研究发现[35],UC肠道黏膜中的IL-6、JAK、STAT3三种蛋白的表达显著升高,表明UC的发生及加重与IL-6/JAK/STAT3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密切相关。纪佳[36]等发现黄芩汤可以抑制 UC 大鼠 IL-6 mRNA、JAK mRNA、STAT3 mRNA,并显著降低了IL-6、JAK、STAT3的蛋白表达及血清中IL-6、JAK、STAT3的含量,得出结论:黄芩汤可以通过抑制IL-6、JAK、STAT3信号通路的激活,减轻肠道的炎症反应。
2.3 平衡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主要由有益菌、共生菌、致病菌组成,是组成人体肠道微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在正常机体条件下,各菌种之间保持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对宿主具有生物屏障功能[37]。而当肠道环境发生异常时,会导致大量条件致病菌在丰度、数量及结构上发生改变,转化为机会致病菌并在肠道大量繁殖,进而影响肠道的免疫调节系统,与此同时,机会致病菌还会释放大量肠毒素进一步增强肠道黏膜的通透性,使肠道内的抗原、内毒素等一些促炎介质更容易侵入黏膜固有层,升高肠道环境的炎症水平,诱发或加重UC发病[38-40]。徐航宇等[41]通过高通量测序研究技术发现黄芩汤可以使UC大鼠肠道的乳酸杆菌显著增加,理研菌属显著降低,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结构发挥治疗UC的作用。实验研究[42]发现黄芩汤可以显著增加DSS诱导的UC大鼠肠道中的有益菌(拟杆菌属、普雷沃氏菌属),使有害菌(大肠杆菌志贺属、毛螺菌属)显著减少,进一步证明适当提高肠道有益菌比例,恢复肠道菌群平衡是黄芩汤治疗UC的内在机制之一。
2.4 抗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OS)的过度激活被认为是UC发病的另一重要因素。氧化应激会导致大量氧自由基的产生,超出机体对氧化物的清除能力,引起脂质过氧化,进而损伤肠黏膜屏障的保护功能,在诱导UC发生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43-44]。氧自由基(OFR)是一类化学性质活跃的含氧基团,它可以通过氧化肠黏膜脂质,使肠黏膜结构和功能发生异常变化[45]。丙二醛(MDA)是结肠黏膜细胞中脂类物质发生氧化反应后的产物,其含量可以反映结肠黏膜脂质过氧化程度及黏膜受损程度[46]。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是机体氧化系统中两种重要的抗氧化酶,可以清除结肠组织中过多的OFR,使结肠组织免受氧化物的干扰及损害,保护结肠黏膜的屏障功能[47]。在UC发生的病理过程中,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炎症可以使氧化应激反应扩大化,氧化应激又可以诱导机体释放大量炎症因子,如此形成恶性循环[48]。因此,在UC的治疗过程中合理应用抗氧化治疗至关重要。实验研究发现[49],黄芩汤可以显著降低UC模型大鼠血清中MPO和LPO的含量,升高机体SOD、GSH-Px的含量,还可以通过调节Nrf2调控Ⅱ相解毒酶和下游抗氧化基因的表达,提示黄芩汤可以通过增强结肠黏膜的抗脂质氧化能力,达到治疗UC的目的。黄芩汤中的黄芩苷、黄芩素等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炎、抗氧化、免疫调节、抗肿瘤等作用[50-51]。刘萍[52]通过动物实验发现黄芩苷可以显著降低UC模型小鼠MPO酶活性及MDA的含量,升高谷胱甘肽含量,明显改善小鼠体重变化、结肠组织学形态表现,认为黄芩苷是通过抗氧化作用,而达到修复UC大鼠结肠组织黏膜目的。可见,黄芩汤发挥抗氧化作用主要与黄酮类化合物有关。
3 小结
综上所述,UC是一种与遗传、免疫、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的复杂疾病,具体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黄芩汤组方精简,疗效确切,治疗UC主要涵盖免疫机制中的炎性细胞因子、Th1/Th2失衡、Th17/Treg失衡、TLR4/MyD88/NF-κB 信号通路、IL-6/JAK/STAT3信号通路、肠道菌群失衡及氧化应激反应机制,具有多成份、多靶点、多途径等优势。然而,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中医讲求辨证论治,而黄芩汤只适用于湿热证型,故湿热证型UC动物模型的建立有待进一步完善,更好的实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粪菌移植虽已成为当前治疗UC的一种新型模式,但其缺乏标准化、规范性及安全可靠性,距离实际应用于UC的临床治疗还存在很多问题。微生态制剂虽然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达到治疗UC目的,但因其菌群种类有限,无法完全重建UC患者肠道微生态,黄芩汤与微生态制剂的联合应用是否会实现协同增效有待进一步研究;以上机制缺乏大规模的临床研究,应采取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为以后更好的研究黄芩汤治疗UC提供更完善、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此外,黄芩汤治疗UC作用机制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应结合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多种方法研究,为以后黄芩汤及其他中医药方剂更好的运用于临床提供更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