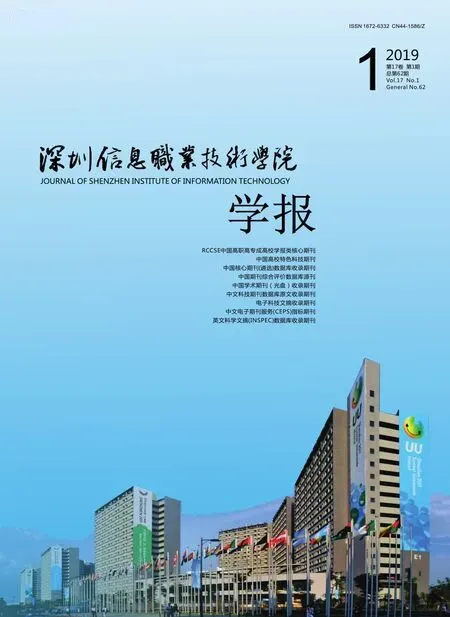美国小说《飘》五个译本的对比分析
2019-02-22刘英凯
刘英凯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1 关于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孰是孰非的现代翻译理念
王东风在其《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1]一文中简述了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之争的历史,他说:“在古代、现代和当代中国,归化与异化,作为翻译的两种策略,前后有三次大规模的论战。古代,归化异化之争的雏形是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到了近现代,‘质’译和‘文’译为‘直译’和‘意译’所取代,其第二次交锋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以鲁迅为首的一批左翼学者主张直译,而以梁实秋为首的一批右翼学者则主张意译。直译派认为意译让‘洋人穿了长袍马褂’,消解了原文的异国情调;意译派认为直译以辞害义,语言洁屈聋牙。……当代中国译坛归化异化之争可视为20-30年代那场直译意译之争的延伸。率先对在当代中国译坛归化翻译主流提出挑战的当数刘英凯的《归化一翻译的歧路》(1987)一文。……刘英凯对归化这一翻译方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归化会‘改造外国……的客观事实,抹杀其民族特点,迫使它们就范,同化于归宿语言,因此也就必然是对原文的歪曲’。”
以上观点中所谓“归宿语言”就是指翻译的“目标语言”,在汉译英中,英语就是“归宿语言”,在英译汉中,汉语就是“归宿语言”。下面我们讨论的几个不同版本的汉语译本《飘》,仍然坚持在归宿语言——汉语中,避免“归化”,避免消解原文——英语中的“异国情调”,避免改造外国(美国)……的客观事实,抹杀其民族特点,迫使它们就范,同化于归宿语言—汉语之中。这个道理是极其简单的,读者阅读美国人写的小说,就如同到美国旅游,他们希望看到的是美国的异域风情、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习俗时尚、宗教、地理、使用语言的习惯……了解的是小说中描述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画面。这样的文字翻译过来,只要译文忠实,也就会随处泄露该文字的“客籍”—其独特的外域民族风格。而不能是太多的中国化了的风情,不该像鲁迅所说的,让洋人“穿了长袍马褂”。
我在跟刘路易和李静滢合作翻译并出版、均由我写“翻译后记”的三本文学作品《夏季走过山间》、《大卫的伤疤》以及《简•爱》的翻译实践上一直坚持上述的方向:反对归化、努力异化。在这一次对美国小说《飘》的重译过程中,我跟合作者,我女儿刘路易仍然坚持这一“异化”的旨志。众所周知:译本对比是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下面的文字就是我把我们的译本跟其他四个译本所做的对比研究。国学大师章炳麟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我们可以从本文下面第2.5.1小节看到,前四个译本竟然对一个句子均彻底错误理解,因而陈陈相因,全部译错,这说明了重译的必要性,“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世界范围内的名著不断有重译本的根本原因;而本文中的其他章节则充分说明了异化原则的重要意义。简而言之,下面“刘译”和本文的写作均可视作我们呼吁巨细必究的认真翻译态度以及坚持异化理念,译出异国情调这一有现代性意义的翻译思想而做出的新一轮的努力。
《飘》据说有已经有了将近十个版本。《飘》的首译者为傅东华。傅译本是1940年出版,我手头有这个译本200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版本,其中标为1940年9月15日所写的“译序”讲到他“归化”原则的几个方面。
“即如人名、地名,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对话方面也力求译得像中国话。有许多幽默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语都用我们的成语代替进去……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这位译者确实把如上这一“归化”原则身体力行了:原属“客籍”的人名都改“入”了中国“籍”。主人公Scarlett O'Hara—斯嘉丽•奥哈拉,译者却把它“归化”成姓“郝”名“思佳”;男主人公Rhett Butler—瑞特•巴特勒则归化成姓白的“白瑞德”,“女二号”Melanie Hamilton—迈乐妮•哈密尔顿则归化成姓韩名媚兰,其哥哥,即“女一号”斯嘉丽的第一任丈夫Charles Hamilton—查尔斯•哈密尔顿则译成韩查理。斯嘉丽的第二任丈夫Frank Kennedy—弗兰克•肯尼迪译成甘扶澜;“男二号”Ashley Wilkes—艾什礼•威尔克斯的归化名字是卫希礼。Pittypat Hamilton竟然译成“韩白蝶”。也有极少数遵循姓氏和名字各一字的两字模式,如Jonas Wilkson译成魏忠。其余近一百个所有角色的名字大都遵循了中国姓氏外加两个字的三字格模式,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而他坚持“中国化”、“用我们的成语代替进去”以及随意“删节”的错误翻译思想所造就的归化指数高、异化指数低,缺乏认真态度,缺乏表现“异国情调”效果的译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译者。
下面将要对比研究的是包括傅译本在内的四个版本和拙译本。它们分别是:1)傅东华译《飘》(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简称“傅译”);2)李美华译《飘》(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简称“李译”);3)陈良廷等译《乱世佳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简称“陈译”);4)黄健人译《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简称“黄译”);5)我们的“刘译”(译毕正待出版)。
其中李译在人名音译中的归化指数仅仅次于傅译。在这个译本中,虽然次要人物的汉译名都避免了汉语人名模式,但是傅译中的郝思嘉、白瑞德、韩媚兰、卫希礼等主要人物的三字格名字在李译里尽数保留。这就生动证明了傅译的错误理念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2 五个译本的对比研究
下面我们在词汇、修辞等美学范围、语法和文化等层面上对五个译本进行学术对比的分析。英语原书是Margaret Michell所著的Gone with the Wind,是Pan Books出版社的1936年初版1988年重新印刷的版本。从学术的严谨性考虑,我们把原文和译文的分析中所引用的原书和前四个译本中的例子都按照各本书的页数做了标识。
2.1 词汇学层面
现代词汇学包括词汇(如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复合词)、短语、成语和谚语等层面。
2.1.1 词汇
2.1.1.1 动词
例1. Timidity and embarrassment swept over her and waves of color mounted her cheeks as he came up the walk. (P.915)
傅译:所以当瑞德走上台阶来时,她脸上不觉泛过一阵红晕。(P.955)
李译:他从小路上走上前来时,羞怯和尴尬袭遍她的周身,脸颊不禁涨得通红。(P.1091)
陈译:当他沿着门前小路走来时,她只感到战战兢兢,十分尴尬,两颊不禁泛起阵阵红晕。(P.911)
黄译:眼见他走上甬道,梅丽提心吊胆,好不自在,脸也刷地通红。(P.935)
刘译:他走上便道的时候,胆怯和尴尬扫过般地遍布她的身心,一波波的红晕爬上了她的双颊。
傅译放弃对Timidity and embarrassment swept over her整个句子的翻译,符合此译本过于随意的惯例。陈译的“她只感到战战兢兢,十分尴尬”和黄译的“提心吊胆,好不自在”各用的两个四字格成语的语义强度都大大超过Timidity and embarrassment的一般性说法,因为timidity的语义是胆怯和羞怯,哪里到了“战战兢兢”和“提心吊胆”的程度?而embarrassment的语义只是尴尬和不自在,“十分尴尬”和“好不自在”都是程度大大拔高的语义偏离。李译的“羞怯和尴尬”以及刘译的“胆怯和尴尬”才是恰如其分的原文语义再现。而waves of color mounted her cheeks在傅译里是“一阵红晕”,在李译里是“脸颊不禁涨得通红”都指的是一次性行为,显然与waves的复数形式不相契合,倒是陈译的“阵阵红晕”最贴近正确的语义理解。刘译“一波波的红晕”既与其复数形式相合,又展现了形象思维的“波”,显然最为妥贴。关于“一波波”在汉语人群中的可接受性,请见下面第2.1.1.3小节,此处不赘。这一小节里最重要的讨论是动词在译本里的正确使用,第一个讨论的动词词组swept over her 在傅译和黄译里被彻底忽略,在陈译里只是加了个 “感到”。李译和刘译都尝试再现这个动宾结构。由于英语her的特殊用法,在做宾语的时候,一般的翻译处理规律是增加词语,李译的处理是“她的周身”,刘译则处理成“她的身心”,哪一个处理更好一些,并没有定于一尊的标准。但是考虑到主语是Timidity and embarrassment—胆怯和尴尬,是既可以表现在表情和动作上,也可以体现在内心深处。所以刘译采取的是“她的身心”。重要的是动词swept(是sweep的过去时,语义为扫、扫过)如果能给予形象的再现,是应当尝试的。刘译处理成“扫过般地遍布”。这在翻译技巧上被称为“直译”(“扫过般”)加增补(“遍布”)是当代文学翻译常用的翻译技巧。鲁迅说:“凡是翻译,它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2]。直译是旨在“保持原作的风姿”,增补是“力求其易解”。类似的例子还包括讨论的第二个动词词组mounted her cheeks。其语义是刘译所采取的“爬上了她的双颊”,这是抽象名词做主语时的拟人修辞格,理应在译文中得到再现。与此对照,处理mounted时,傅译的“泛过”、李译的“不禁涨得”、陈译的“不禁泛起”以及黄译的“刷地通红”都显示了不同程度地不遵照原文的随意性。
2.1.1.2 分词
严格地说,分词应该列入动词之下的类别,但是我们不想再列出2.1.1.1.1那样过于细碎的分类。因此处理成让它跟动词并列。
例2. …would only bring more barbed remarks from him.(P.594)
傅译:都适足以引出他的更加锋利的评论来。(P.615)
李译:那只会让他说出更能讽刺人的话来。(P.704)
陈译:都只能引出更加刺人的话来。(P.579)
黄译:只会招来他更多的挖苦。(P.606)
刘译:只会从他那里引出更像倒钩般刺人的话来。
在原句子里,more是修饰barbed,不是修饰remarks的,所以黄译本翻译成“更多的挖苦”就显然是强调了数量,这个译文是最离谱的。分词Barbed原初的名词Barb意为鱼钩和箭头的倒钩,动词的语意则是:装上倒钩;使……带有讥讽、讥刺。文学的形象思维要求译者尽可能地表现出文学的形象,因此刘译本的“更像倒钩般刺人”最有形象思维的特点,又能够把深层语义“刺人”再现出来。其余译文只译出了深层语义,忽略了表层形象。
2.1.1.3 名词
例3. Melly was hurting so bad—there were hot pinchers at her and dull knives and recurrent waves of pain. She must hold Melly’s hand.
傅译:媚兰正在受煎熬,仿佛被煨红的铁钳子在那里钳,被钝刀子在那里刮,一阵又一阵地痛。(P.949)
李译:梅利是这么痛苦—火热的钳子在烫着她,还有钝的刀子,阵痛又一阵一阵来临。她必须抓住梅利的手。(P.1084)
陈译:玫莉在忍受着痛苦—一阵一阵的疼痛,仿佛有许多人拿着通红的铁钳和钝刀对她施以毒刑。她必须抓住玫莉的手。(P.906)
黄译:梅丽疼得厉害—火红的钳子、钝刀子在拧她、割她,一阵紧似一阵地疼。她必须握紧梅丽的手。(P.930)
刘译:迈莉正痛得那么厉害—好像有几把热热的钳子在钳她,还有几把钝刀子在割她,还有一波波反复的疼痛。她必须抓住迈莉的手。
原句里的so,只有李译和刘译没有忽略,但是描述的事情发生在过去,李译的“这么”就不符合回忆的场景,刘译的“那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原文的hot,傅译译成“煨红”,陈译译成“通红”,黄译译成“火红”,都造成了语义距离过远,而李译的“火热”比前三个译版要好,可是“火”字出现的缺点是语义过量。对She must hold Melly's hand整个一个句子的信息,傅译和黄译竟然都彻底漠视,译文中不予再现。这不是严肃译者的正确态度。Recurrent一词除了刘译之外,所有的其他四个译文都没有翻译,造成语义流失。陈译的“有许多人”以及“对她施以毒刑”是毫无依据的语义添加,不是翻译正道。这里重点要强调的是复数名词waves,所有前4个译本都处理成“一阵又一阵”,这显然是忽略形象思维的保守译法。正如思果所说,“有些生硬的洋话,经过时间这个熨斗熨来熨去,也渐渐变得自然了。三十年前特异的说法因为一再为人采用,已经成了‘土产’,再过一两代也许给人视为陈腐。”[3]事实上恰恰由于翻译工作者的贡献,“一波激动的情绪袭来”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的句子早已为汉语受众所欣然接受。所以译者完全没必要受保守思维影响过重,而不敢移植原文形象思维的“一波波”。
2.1.1.4 形容词
例4. …they've got younger and more peppery.(P.732)
傅译:他们……就都像返老还童一样,到比以前更加泼辣了。(P.765)
李译:他们变得更年轻,活得更有滋味了。(P.867)
陈译:他们变得更年轻,更泼辣了。(P.719)
黄译:他俩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P.747)
刘译:他们变得更年轻了,像胡椒辛辣一样更有活力了。
傅译中的“返老还童”是四字格意识过于强烈,“返老”之信息是原文所无。李译的“活得更有滋味了”是想当然的理解,与peppery的语义距离过远,黄译的“越活越”结构是凭空添加,原文如果有the more …the more 结构,那样翻译才有依据。须知:peppery是名词pepper派生的形容词,名词原意是胡椒、胡椒粉,引申义中之一是活力、劲头。所以黄译的“越有劲”和刘译的“更有活力”之译是有根据的。但是刘译把表层的形象思维信息“胡椒辛辣”和“有活力”这一深层含义均忠实再现,做到了形神俱现,骨肉两全。
2.1.1.5 副词
例5…he had said, sheepishly…(P.583)
傅译:他也曾羞答答地告诉她们,……(P.607)
李译:他还忸怩不安地说过,……(P.695)
陈译:他也曾羞答答地对人说过,……(P.572)
黄译:他本人还腼腆地说过,……(P.598)
刘译:他曾经像绵羊一样腼腆地说过,……
一个译者如果有足够形象思维的文学意识,应该随时随地对形象性语言有清醒的认知,因此sheepishly如果能够移植,会让中国读者了解中西方修辞形象的差异。可是前四个译文全部抛弃形象思维,把“绵羊一样的”形象给抽象成“羞羞答答”或者“腼腆”,于是原句的异域风情凋谢失落了。刘译把表层的“绵羊”形象和深层的“腼腆”语义均予揭示,更符合现代翻译思维。
顺便提及:前四个译文中的“也”和“还”都是没有原文支持的信息添加,非翻译正道。严肃的翻译表现在每一个细节之中,不可过于随意。
2.1.1.6 合成词
在下面的 the ill-starred foray(P.701)短语中,刘译的“这次灾星照过,注定倒霉的袭击”,把合成词ill-starred的表层形象“灾星”和深层语义“注定倒霉”形神俱传地予以再现。而傅译的“这场事变”根本漠视了ill-starred这个形象思维方面生动的合成词,李译的“这次注定没好结果的突袭”(P.915),顾及了深层语义,而表层“灾星照过”就未予考虑。陈译的“那次倒霉的袭击”(P.761)和黄译的“这次倒霉的行动”(P.761)均比李译更为有欠忠实,连英语原词包含的“注定”语义都彻底忽略了。
2.1.2 短语
例6. Melly, what a tempest you make in a teapot,…(P.830)
傅译:媚兰,你自己在这里小题大做呢。(P.873)
李译:梅利,你干吗大惊小怪的,……(P.984)
陈译:枚莉,你实在是小题大做呢,……(P.819)
黄译:梅丽,真是小题大做。(P.846)
刘译:迈莉,你多么像在茶壶里兴起了个大风暴一样,小题大做了呀。
拜翻译之所赐,现在来源于a storm in a teapot的汉语短语“茶杯里的风暴”已经为广大受过教育的汉语受众所接受并使用。a tempest in a teapot不过是风暴规模更大了一点而已。如果说1940年就出版了的傅译本还不敢直译尚情有可原,而21世纪后出版的其他译本理应移植以形象思维为特点的 “茶壶里兴起了个大风暴”的这一生动信息。可是,遗憾的是,其他四个译本都把这一信息抽象化,译成“小题大作”,这在论翻译的著述中被称为 “抽象法”。四个译文都用了抽象法。这一方法的滥用到了何等程度,于此可略见一斑。抽象法没能像移植法那样“传真”,而是“失真”的译文,是不该提倡的。事实上,如果进一步抛弃保守的翻译思维,刘译基于直译加增补方法的后半部分的增补“小题大做”即使删除了,也是可以为汉语受众所理解并接受的。顺便提及几个枝节问题:傅译的“自己在这里”、李译的“干吗”、陈译的“实在是”以及黄译的“真”都与原文的what语义距离遥远,均违反当代翻译理念。刘译的“多么”才与what语义契合。
2.1.3 成语、俗语和谚语
例7. That was the last straw.(P.643)
傅译:这不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P.672)
李译:这是不堪忍受的最后一击了。(P.763)
陈译:这可叫她忍无可忍了。(P.630)
黄译:这对她可是沉重打击。(P.655)
刘译:这像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是对她的最后一击呀。
前四个译文竟然毫无例外地放弃了“最后一根稻草”这一生动的形象思维。其中傅译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是持自给自足的态度,用带有完全不同形象思维的自家语言品种“山穷水尽”代替异文化“株体”。这种抹杀翻译独创性的译法称为“替代法”。失去了真也就失去了美,因此替代法绝不宜提倡。其他几个译本都没能翻译这个形象思维的元素,只是译出深层语义,则属于 “抽象法”。在替代法和抽象法的译法之下,原作的异国情调均彻底凋谢了。刘译采取的仍是直译加增补方法。其实,其中的“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已成了受过教育的汉语人群所广泛接受的表达方式了。前四个译本中的后三个都是近十年来出版的,不能或不敢移植原句妙趣,是翻译理念落伍的产物。再如,本着尽可能移植的原则,在该翻译成“爱我就要爱我的爱犬”,而不应该按代替法翻译成“爱屋及乌”(李译P.1072、陈译P.894)或者按抽象法翻译成“爱我就得爱我朋友”(黄译P.920)。在此我们严肃指出:傅译由于态度过于随意,此处没有译文(P.941)。
可是与此相反,原文没有相应成语等语言成分的地方,我们的如上译者却常常由于四字格成语或者汉语俗语和谚语意识过强,强行换上或甚至是无中生有地强加有不少例子,强加的例子如下面第2.4小节黄译的“顺手牵羊”。再如You turned me out on the town while you chased him,陈译是“你为了追求她,把我甩在一边,逼我去寻花问柳”(P.884)。其中的“寻花问柳”信息为原文所无,纯属随意强加。此处相应的刘译则是平实的“你追他的时候,却把我撵到城里”。上面我们提到傅译说过的“有许多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语都用我们的成语代替进去”,其实其他三个译本何尝不是这样随意归化的呢?下面的例子无需对照原文,读者都会认为,这些成语、俗语和谚语不可能是外国小说中出现的表达方式。傅译中的“小娘子”(P.947)、李译中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P.12)、“菩萨心肠”(P.947); 陈译的“你算老几”(P.104)、“急惊风碰上百个慢郎中”(P.321)、“披麻戴孝”(P.534)、“我的小姑奶奶”(P.424)、“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P.537)、“乌龟配王八”(P.883)、“小巫见大巫”、(P.889);黄译中的“人老珠黄”(P.130)、“陈谷子烂芝麻”(P.287)、“穷得叮当响”(P.644)、“狗嘴里吐出象牙”(P.651)、“拒人于千里之外”(P.791)、“七大姑八大姨”(P.824)、“母夜叉”(P.875)、“一丘之貉”(P.880)以及“把芝麻当西瓜”(P.933)等等。读着美国的小说,却看到归化—中国化指数达到如此高度的汉语表达方式,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2.2 美学层面
翻译中涉及到的美学元素包括意境美、音韵美和语言形式美等,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语言形式美传递过程中的语言推敲和锤炼的必要性。
2.2.1 修辞层面
上述2.2小节无不涉及到词汇的修辞效应。这一节我们探讨的是作者刻意使用的修辞格。
2.2.1.1 排比
例8. The South was too beautiful a place to be let go without a struggle, too loved to be trampled by Yankees who hated Southerners enough to enjoy grinding them into the dirt, too dear a homeland to be turned over to ignorant negroes drunk with whisky and freedom.(P.588)
这里有too …to (太……以至于不)句型的三次重复,是作者刻意使用的排比句。译者应该有发现语言形式美的慧眼。可是请看如下的四种译本的处理:
傅译:(可能由于这属于译者所述的“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而未予翻译)(P.644)
李译:南方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决不能不做抗争就拱手相让。南方太令人珍爱了,不能任由北方佬肆意践踏。北方佬恨南方人,恨不得把他们碾成尘土而后快。南方还是个可爱的家园,不能把它交给被威士忌酒和自由思想灌得醉醺醺的无知的黑人。(P.734)
陈译:南方这片美丽的土地怎么能不经一番斗争就放弃呢?南方太让人爱恋了,怎么忍心把它任凭北方佬蹂躏呢?这些北方佬对南方人恨之入骨,巴不得把他们碾成粉末呢。南方这块乡土太宝贵了,怎么能把它交给沉醉于威士忌和解放之中的无知黑人呢?(P.605)
黄译:美丽的南方怎么能拱手相让?亲爱的南方怎能容忍仇恨南方的北佬横加蹂躏?这片宝贵的土地怎能交给被威士忌和自由弄昏了头的愚蠢黑鬼?(P.605)
刘译:南方是太漂亮的一个地方,不能没有抗争就把它放弃;是太让人爱恋的了,不能让北方佬践踏,这些北方佬痛恨南方人,恨不得把他们碾成泥土;南方是太亲切宝贵的家乡,是不能交给那些被威士忌和自由弄得醉醺醺的无知黑人的呀。
以上几个译文中,“太”字句型,李译本使用了一遍,减少了两个,却又随意给增加了“拱手”、“肆意”和“还”的信息。陈译本把“太”字句型使用了两遍,减少了一个,却无端增加了“入骨”的信息。黄译本根本漠视其排比形式之美,随意把排比的陈述句换成疑问句;随意添加信息,如“拱手”和“横加”;随意减少信息,如“家乡”(homeland);随意更改信息,把drunk—喝醉的信息更改成“弄昏了头”。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这已经不属于翻译,而沦于编译。刘译本把三个排比忠实再现,是尊重原文审美格局的正确翻译思路。顺便提及的是too dear a homeland中的dear,就人心中的价值而言是“宝贵”,就情感而言是“亲切”,理应都表现出来。
2.2.1.2 比喻
例9. …you gwine sour yo' milk an' de baby have colic, sho as gun's iron.(P.711)
此例是模仿没有文化的黑人嫲嫲发音和语法不规范的讲话,其标准英语当为you are going to sour your milk and the baby will have colic, sure as a gun's iron.作者用连词as作为比喻句的显性提示。
傅译:你的奶汁一准会变酸,孩子就要发绞肠痧了。(P.743)
李译:你的奶就会发酸,孩子就会患急腹痛,他会送命的。(P.842)
陈译:你的奶就会变酸,娃娃会肚子痛,肚子硬得像铁。(P.698)
黄译:你那奶可要变酸啦,宝宝吃了会闹肚子痛,这俺可错不了。(P.726)
刘译:你的奶就要酸了,孩子吃了要得肚子绞痛急病,像炮上的铁一样保准儿喔。
傅译忽略句子里的修辞信息,却把sure的信息转移到上一句中,用了个“一准”试图再现这个sure的语义。而李译也彻底忽略句子里的修辞信息,未提供翻译,或者把as a gun's iron 完全错误地理解成“他会送命的”。陈译错误地理解了as a gun's iron这句话,把上一句得急腹症的语义错会成跟这句构成语法和语义关系,因此翻译成“肚子硬得像铁”。这是理解错误导致的严重错译。黄译“这俺可错不了。”成功表达了sure的语义。但是,傅、黄两处译文都回避了as gun's iron这一形象思维的修辞信息,是一大不足。刘译:“像炮上的铁一样保准儿喔。”移植了“炮上的铁”这一信息。至于把sure译成口语化的“保准儿”,跟嫲嫲没有文化的特点相互吻合。顺便提及:语气助词“喔”符合作为斯嘉丽上下三代人的保姆和斯嘉丽道德监护人的慈爱身份。
比喻是所有语言中最重要的修辞方式,我们这里再举一个例子:By morning she would have thought up some excuse to offer, some defense that might hold water. (P.882). 傅译:“到了明天早晨她就会想出替自己辩护的理由来了。”(P.919);李译:“等到早晨她就可以想出一些理由来,一些站得住脚的开脱之词。”(P.1045);陈译:“到了明天早上,她就能想出一些借口了,也许能够把这件事儿掩饰过去。”(P.872);黄译:“明天早晨也许能想出个好借口,站得住脚的借口。”(P.899)。以上四个译文均无视that might hold water—“像容器盛水不漏一样”的形象化信息,李译和黄译用代替法“站得住脚”替换,傅译和陈译用抽象法敷衍过去。另外some的两次使用后面均跟着单数名词,因此其语义是“某种”。李译和陈译竟然把原词理解成“一些”,错误之大令人惊愕!另外,would have thought up是过去将来完成时虚拟语气,其意的理解必须是“将会已经想出来了”,而不应该理解成一般将来时。因此前四个译文的错误也属于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纠正以上几个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译法,刘译是:“到早晨她将会已经想出了某个借口给提供出来,是像容器盛水不漏一样可以经得起考验的某种辩解。”译文对比会让人思索翻译的原则和认真态度的重要性。
形象思维的努力贯穿到刘译的全书翻译中,例如遇上原文makes a mint of money,别的译文或者不予翻译(傅译P.696)或者译成“赚了很多钱”(李译P.808)、“发了大财”(陈译P.669)、“赚大钱”(黄译P.714)。刘译移植成“赚上了造币厂那么多的钱”。刘译在别的译文不敢移植的情况下,移植原文形象词汇的例子数以百计,仅仅再举一个例子,刘译:“啄了个吻”。而傅译“将自己的嘴唇放上去点了一点”—P.714;李译“吻了一下”—P.808;陈译“匆匆忙忙亲了亲”—P.669;黄译“轻轻一吻”—P.696。其中的“啄”字直译自原文的pecked,简洁到一个字,生动形象,别的表达法都显得不同程度地啰嗦,而且缺乏形象思维的特点。
2.2.1.3 借代
例10. I'd have stayed there like a fool and probably had my neck stretched by now. (P.613)
傅译:我一定还像个傻子似的待在那里,怕到现在,已经直了颈梗了。(P.641)
李译:我还会傻乎乎地呆在那,很可能现在已经被绞死了。(P.729)
陈译:我肯定还像个傻子似的呆在那里,这会儿恐怕已经直了颈梗了。(P.601)
黄译:我也许还傻瓜似的待在家,这会儿脖子也多半套上绞索啦。(P.628)
刘译:我会像个傻子一样待在那里,兴许到了现在,我已经脖子给抻长了,人被绞死了呢。
句子里的had my neck stretched(把我的脖子让人抻长)属于用现象指代实质(绞死)的借代修辞格。傅译和陈译都译成“直了颈梗了”,其绞死的语义表达得并不清楚。李译直接说“被绞死”,缺乏借代辞格的更为具体的形象思维,但是比傅、陈译文语义清晰是毫无疑问的。黄译的“套上绞索”,虽然有形象再现,但是没能表现出“绞死”的结果,国外小说提到“套上绞索”进行威吓,最后并不绞死的例子并不少见。刘译本既有“脖子让人抻长”的形象表述,又提及“绞死”的结果,才不会产生误会。顺便提及:李译中“很可能”里的“很”以及黄译本“待在家”里的“在家”都属于信息过量。
2.2.1.4 夸张
例11.Tonight, she was alive to her finger tips.(P.574)
这个句子属于修辞上的夸张句式。
傅译:(没有译文)(P.603)
李译:今晚她从头到脚都很有活力。(P.684)
陈译:今晚他完全生机勃勃。(P.563)
黄译:今晚她连手指尖都充满生机。(P.588)
刘译:今晚她一派生机,活跃到了她所有的指尖。
傅译随意性之大从此处的不予翻译上又一次得到证明。英语的脚趾是toe tips,因此finger tips只指手指尖,李译的“从头到脚”是没有原文依据的。陈译本把to her finger tips 的形象思维置之不理,而采取抽象译法,译成“完全”,过于敷衍。黄译和刘译都是考虑精细的合格译文。但是,原文没有even,黄译“连”的使用属于无源之水,是信息过剩。
2.3 译文语言的推敲和锤炼
对比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四个译本中出现不少有欠推敲的字句。我们在此特设一个小节略为揭示,为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做出呼吁。
2.3.1 译名的推敲
上面我们提到过归化成汉语三字格姓名模式。此处我们谈一下非归化名字的音译问题。人名翻译的原则是“名从主人”,按照源语的发音而不是拼写来确定译名。为节省篇幅,下面我们只论及女性名字(不包括姓氏),而且只举一个女士名字的例子:小说中有个女士的英文原名是India,刘译定名为“茵蒂娅”,不仅跟原名的发音最为逼近,而且也一眼看出是女士的名字,可是傅译竟然是“英弟”,让人怀疑是个男士;陈译的“印第亚”和黄译的“因迪”不像是人名;只有李译的“英蒂”像是个女士的名字,但是没能准确译出原名第二个音节的发音,是一个小小的缺欠。刘译在参照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译音原则的基础上,把小说中所有女性名字都按 “名从主人”的规定一一定名,取得了类似“茵蒂娅”的效果。
2.3.2 搭配的推敲
傅译的“他那被打的脸的记忆将要盘踞着她”(P.115)、“愤怒她自己,愤怒希礼,愤怒全世界”(P.116)、“害得我中觉打不成”(P.116);李译“脸上漾着怒火”(P.537)、“他心如火焚,快要融化了”(P.674);陈译中的“先不先她就会问我”(P.6)“究竟有什么法道”(P.551)、“裙子裹得紧紧的连腿子都看得出来了”(P.558);黄译本“滚烫的嘴唇”(P.617)、“掩盖了她怀孕的身段”(P.643)等有欠推敲的类似例子都有不少。因此我们要呼吁认真锤炼语言的精神。
2.3.3 口语化的推敲
在汉语中有些口语词汇例如“道牙子”或“马路牙子”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P.270、P.1490)得到了承认,即指马路和人行道相接的部分。这两个词恰好就是英语curb, curbing 和curbstone(必须是石头造的)的对等语。可能由于陆谷孙等词典把curb翻译成“路缘”,而“路缘”这个词不够通俗,所以四个译文碰上sat on the curbing(P.526)时,傅译的“坐在墙基石上”(P.556)属于理解和翻译全然错误,李译的“坐在街沿石上”(P.627)、陈译的“坐在路边石上”(P.514)和黄译的“坐在路边”(P.540)都表达得语义不清。刘译用的则是口语化的“坐在道牙子上”,做到了语义清晰而又通俗易懂。特别是在最具口语化特点的对话中使用书面语在四个译本中都有不少例子,我们分别予以简要例证。傅译在对话中使用“仿佛”(P.114)、“然而”和“倘使”(P.117);李译使用“结为伉俪”(P.39)、“施以暴力”(P.40)、“为之工作”(P.41)、“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P.42);陈译使用 “倘若”(P.447)和“别告诉任何人”以及黄译“他赖以糊口的土地就是他娘亲”(P.423)、“真是千古了”(P.174)都是斟酌和推敲不足的适例。
2.4 语法的特殊句型
例12. Scarlett, sick and miserab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pregnancy, alternated between a passionate hatred of the bluecoats who invaded her privacy, frequently carrying away any little knick-knack that appealed to them, and an equally passionate fear that Tony might prove the undoing of them all. (P.619)
傅译:斯嘉丽在怀孕的初期,一直都害着病、心气非常恶劣。所以看见那些穿蓝军服的闯进她私室来,并且经常要带点小东西走,他就觉得非常的愤恨,同时又怕东义要连累他们,一直都担着忧愁。(P.647)
李译:怀孕初期的斯嘉丽经常恶心想吐,非常难受。穿蓝军服的北方佬侵扰了她的清静和自由,经常是见到喜欢的小玩意就顺手带走。她一方面极为痛恨他们,另一反面又担心托尼会招供,毁了他们大家。(P.737)
陈译:斯嘉丽因为在妊娠初期,身子不适,心情也不佳。所以对那些穿蓝军服的闯进她的私室来见了喜欢的小摆设就拿走,一方面觉得可恨,另一方面因为怕汤尼的事儿会牵累到他们大家,心里十分担忧。(P.607)
黄译:斯嘉丽正处于早孕期,反应厉害,情绪低落。见北佬闯进来,还顺手牵羊,拿走喜欢的小玩应,真恨死了他们。同时又怕一家人会因托尼的事倒大霉,忧心如焚。(P.634)
刘译:斯嘉丽处于怀孕初期,感到恶心而且心里难受。她在强烈的憎恨和同样强烈的恐惧中交相轮换,憎恨的是那些穿蓝军服的大兵闯入她的私人空间,不管是什么小玩意儿,他们有兴趣,就经常给拿走了;恐惧的是彤尼的事会毁了他们大家。
从语法上讲,原句的重要语言点共有两处:一是特殊句型alternated between A and B(在A B两者之间轮流交替)是本小节意欲对比研究的重点,另一个是passionate 的两次使用。遗憾的是前四个译本都没有再现原文的这两个特殊的语言点。刘译把“她在……憎恨和……恐惧中轮流交替”的重点句型忠实译出,随后用“同样情绪激昂的”忠实再现原文的“equally passionate”短语的语义。
顺便再讨论一下重要语言点之外的几个问题。sick and miserable,傅译 “一直都害着病、心气非常恶劣”中的“一直”是随意的语义添加,“害着病”是多义词选择失误,此处显然应该选怀孕期间的“恶心”语义;李译的“经常”也是随意的语义添加;陈译用“反应厉害”翻译sick,随意性更加离谱。有关the bluecoats who invaded her privacy,李译的“穿蓝军服的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从修辞现象的翻译角度,属于借代翻译中的“直译加增补”,是无可指摘的,但是,此处可以删掉,因为北方军人身穿蓝色军服,上文已经提过数十次,此处完全没有必要加进这一信息。黄译的“北佬闯进来”有两处语义缺失,一是作为借代修辞格的the bluecoats(穿蓝军服的)指的是北方军人,不是泛指意义的“北佬”;二是“闯进来”没有提到闯进什么里,漏掉了her privacy的信息。黄译过于喜欢使用四字格成语,其中的“顺手牵羊”是随意添加了一个成语的信息,而“忧心如焚”中的“如焚”则是随意添加形象方面的信息。至于equally passionate,前面四个译文均没能置于翻译思维之列,是缺乏精细态度的表现,都令人遗憾。
英语语法的特点之一是常常使用汉语几乎不使用的长句。长句子是翻译的难点之一。认真推敲,调度连词是严肃译者的责任。可是译者一旦偷懒就会“生造”括号,逃避推敲的责任。仅举一例:Just a little over a year ago, she was dancing and wearing bright clothes instead of this dark mourning and was practically engaged to three boys(P.153)黄译是:“一年多前,她还打扮得花枝招展(瞧如今这身打扮的黑丧服),纵情跳舞,起码有三个男孩子想和她私定终身呢。”(PP.154-155)分析表明了:这个译文漏译了Just a little(刚刚……多一点)和practically(实际上),多译出了“纵情”、“起码”和“私定”中的“私”。“打扮得花枝招展”跟原句的wearing bright clothes(在穿着鲜艳的衣裳)语义相比,信息大为“超载”!刘译是:“刚刚一年多一点以前她还在跳舞,还在穿着鲜艳的衣裳,而不是这件黑色丧服,并且实际上等于跟三个小伙子订了婚。”只用了“而不是”就把上下文的信息联系到一起,避免了括号的随意添加。括号的无端增加,还包括李译的P.747、P.1080;陈译的P.440、P.469、P.593、P625、P.797以及黄译的P620、P651、P.958等等。
2.5 文化层面
2.5.1 圣经
例14. I'm sure the woman the Pharisees took in adultery didn’t look half so pale. (P.884)
傅译:衙门拿到的通奸犯绝没有面孔白惨惨的。(P.922)
李译:我敢肯定,一个女人若跟自以为讲道德的人通奸 他的脸色看上去也不及你这样一半的苍白。(P.1048)
陈译:我敢肯定,同道貌岸然的法利赛人通奸的女人,脸色准不会这样惨白。(P.874)
黄译:我敢肯定,与一本正经的法利赛人通奸的女人,脸色不会这么苍白。(P.901)
刘译:我肯定,法利赛人抓住的那个通奸女人(the woman the Pharisees took in adultery.法利赛人标榜自己遵守传统道德礼仪,曾把一个通奸女人抓住后送到耶稣那里,要求耶稣按摩西律法把那女人用石头砸死。此事的细节请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2-11节—译者注)脸色也不会有一半这样的苍白。
这个小节主要谈文化现象的翻译原则。在进入这个部分之前,先讨论一下语言理解的问题:从语法上讲,the Pharisees took in adultery 是修饰主词the woman的,那个女人在跟别人行淫通奸时被标榜自己讲礼仪的法利赛人抓住了,并不是法利赛人跟那个女人通奸。而《圣经•新约•约翰福音》所描述的事实也是这样:法利赛人把这个女人带到耶稣那里要求评断。可是李、陈、黄三个译者都没有吃透原文,而是错误地理解了上句话中的语法关系,又一律没有到《圣经》上查阅一番的认真精神,因此翻译都出现了严重错误,而且凭着一般英汉词典上Pharisees的负面形象的定义,把“自以为讲道德”之类的定语错误地写进译文中。傅译的“衙门拿到的通奸犯”令人莫名其妙:“衙门”在原文里完全没有依据;通奸犯是男是女,法利赛人跟女人的关系都完全没有交代。以上四个错误的翻译生动证明了:缺乏一个认真的态度,译者所犯的理解和表达错误以及随意在正文中加进原文没有的负面色彩的定语可以达到何等令人惊骇的程度!刘译用注释介绍圣经和法利赛人负面形象的事实,避免在正文中随意添加定语,这种处理才符合翻译的忠实理念。另外,陈译的“同……通奸”和黄译的“与……通奸”都不如李译的“跟”字更合乎口语习惯。有关口语化的文字推敲,请参阅上面2.3.3小节。
我们这里想强调的是:在面临地球村的当下,对于文化现象的翻译应该采取的移植态度。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态度,汉语读者已经都很熟悉的“潘朵拉盒子”、“阿基里致命的脚后跟”、“犹大的亲吻”、“维纳斯”、“邱庇特”、“缪斯”、“伊甸园”、“多米诺骨牌”、“特洛伊木马”、“诺亚方舟”、“阿拉丁神灯”、“达摩克利斯之剑”、“斯芬克斯之谜”、“鳄鱼的眼泪”、“皮格马利翁效应”等等又怎么能进入汉语呢?它们不都是经过翻译的移植到落地生根,从不熟悉到熟悉,近年来大量进入我们的文学语言,甚至进入汉语词典了吗?而翻译工作者要有鲁迅先生强调的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探索精神,通过注释介绍西方文化。有些译者认为,洋典故和西方历史地理知识读者不容易接受,加了注释又破坏阅读的连续性。这显然是保守的观点,试问,中文典故和历史知识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甘棠遗爱”、“箪食壶浆”、“庖丁解牛”等等,年轻读者最初遇到,没有注解或不去查阅,不也是不懂吗?通过读注释或查阅有关资料也就懂了;用得多,也就牢记在心,另一方面也会到处传开了。中文的典故可以有注释而不认为破坏阅读的连续性,对译文中设以注释为什么倒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呢?翻译史无数次地证明了,凡是成功的译文莫不极力依靠注释而大胆移植这类外域典故和其他类别的文化知识。翻译界有个趣谈:萧乾夫妇翻译的乔伊斯长篇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第九章的注释跟正文的篇幅差不多一样长,因此成为注释必要性的有力佐证。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
2.5.2 历史地理等知识
例15. Had she not been so surprised at Ashley’s windfall, Scarlett would have taken up the gauntlet,…(P.926)
傅译:斯嘉听说希礼有这笔意外横财不由得大吃一惊的话,她又要跟瑞德吵起来了,……(P.962)
李译:斯嘉若是对希礼得到的意外之财没有感到这么吃惊的话,她很可能接受这一挑战了,……(P.1099)
陈译:倘不是斯嘉丽为艾什礼这笔意外之财感到喜出望外,面对瑞特的这一这一挑战早就会奋起应战了,……(P.918)
黄译:天上掉下来一笔钱!斯嘉丽真为阿什礼感到喜出望外,不然,她又会为瑞特话中带刺和他吵起来,……(P.942)
刘译:斯嘉丽倘若不是对艾什礼这像被风吹落的果子一样的意外之财感到太惊讶,她本来是会已经接受瑞特这铁手套(guantlet, 中世纪骑士戴的金属片制成的手套—译者注)般的挑战了的,……
原句中windfall 的原初意义是:被风吹落的果子,引申的语义是意外之财,这同样是我们在前面谈过多次的表层和深层语义的关系,翻译时如果能把表层的形和深层的神同时再现是理想的翻译。翻译中的信息传递要尽量不多不少,傅译的“横财”中的“横”、黄译中的“天上掉下来一笔钱”没有原文依据,翻译得太随意;陈译和黄译中的“喜出望外”均属信息过量,是因为surprised的语义仅仅是吃惊,“出望外”是吃惊,而“喜”之译则是无端增加。汉语四字格成语的弊端在于信息的或增或减或变化,因此尽量避免使用。上文谈过,此处不赘。而taken up the gauntlet,从深层蕴含的语义来讲,确是指她跟瑞特吵架,但是表层含义既然是接受挑战,直译过来,读者都能看懂,理应直译,所以另外三个译文都移植了原文,只是陈译中的“奋起应战”信息过量,“奋起”之译没有原文依托。黄译中的“瑞特话中带刺”又是过于随意的信息添加。另外,从语法上讲would have taken表示的过去将来完成时态的虚拟语气,是“本来会已经接受了”(却没接受)之意,李译的“很可能接受”是对这一时态的理解不够。
西方中世纪骑士戴铁皮手套的历史知识,对于全面了解中世纪骑士精神有利无害,刘译加了个注释,给予介绍。别的译文完全无视taken up the gauntlet这一动宾短语,不足为训。
前面我们讲到,四字格成语、汉语俗语或谚语意识过强有害无利,可是,如果它们包含着特殊的汉语文化色彩,其荒唐性就更加出谷迁乔!我们就以“目不识丁”为例,这个成语在李译中的P.15、陈译中的P.16和黄译中的P.996中都曾出现过。须知:表示外国人未受教育,可以说“目不识ABC”,却不可以说“目不识丁”,因为“丁”是西方跨文化语言学所谓的culturally-loaded word(“文化负载词”)。“目不识丁”是汉语借代修辞格,借代的深层语义是:最简单的汉字都不认识,因此就是个文盲,但是在一篇外国文字中,除非有意使用,是绝无可能出现“丁”字样的。这个成语汉语民族色彩太强,用在西方小说的译文中都犯了所谓“文化因子错位”的大错误。其他例子如傅译的“这话是王八蛋说的了”(P.114)、李译的“稳如泰山”(P849)、“操你妈”(P.135)、“去他妈的”(P.528)、“去他娘的”(P.730)、“万贯家私”(P.807);陈译的“锱铢必较”(P.798)、“东山再起”(P.815)以及“泾渭分明”(P.894);黄译的“如意算盘”(P595)、“懂个屁”(P.618)、“狗娘养的”(P.630)以及黄译同李译文都出现过的“万贯家私”(李译P.807,黄译P.849)等等都是在中国地理、咒骂语、度量衡等方面的文化因子错位。
3 小结
以上四个译本,各有其长处,不容否定。傅译的筚路蓝缕之功尤其应予高度肯定。我们这里的讨论并非妄论高低,而是通过对比,讨论翻译原则的正确与否对于翻译质量的直接影响,从而为确立翻译的正确理念而做出呼吁。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熟就是俗。“熟”则没有创意,就会落入俗套,是一切创作包括翻译实践最应该警惕而尽力避免的。翻译中的归化程度高,异化程度低,就会满纸“熟”透了的四字格成语、俗语等俗套。以上四个译本中,黄译出版最晚,出版时间是2015年11月。如前所述,照理来讲,前修未密,后出转精,黄译本来应该后来居上。可是对比研究表明,黄译是21世纪后出版的三个译本中归化程度最高,异化指数最低,与原文疏离感最强,负载于语言形式之中的修辞元素和其他文学性流失最多的版本。严格来讲,它不属于符合现代翻译理念的翻译实践,应当列入“段内编译” 的范畴,但是深入讨论这一过程和结果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虽然黄译是在如上讨论中所涉及的各个层面的负效应例子最多的版本,但是限于篇幅和本文结构平衡的考虑,我们不能过多举证。这个结果表明了:建立一个尊重原文,尊重原作者,不是片面讨好中文读者,而是全方位保留“异国情调”的现代翻译理念是何等地重要!关于是尊重原作和原作者,还是用汉语人群熟悉到落入俗套的归宿语言去讨好保守的读者,请读者参阅拙作《试论奈达“读者反应”论在中国的负面作用》(《上海科技翻译》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