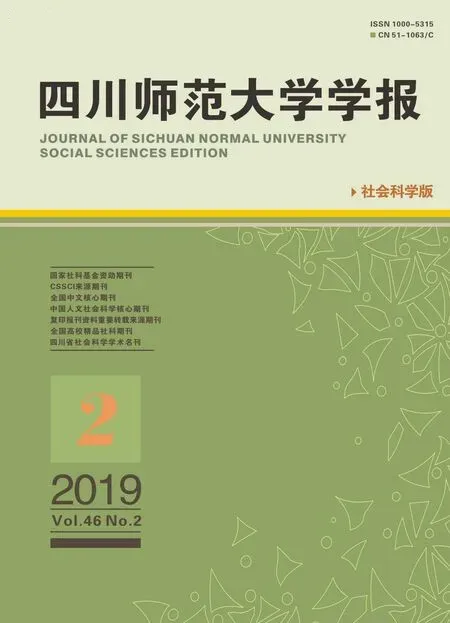以教翼政: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传昭布施
2019-02-22
(四川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66)
传昭布施,也称攒招布施、熬茶布施,是指藏俗每年传昭大法会期间,向齐聚大昭寺的数万喇嘛发放布施,一般为熬茶、放粥和发放藏银。传昭大法会,藏语称为“默朗钦摩”或“默朗钦波”大会,乃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宗教活动,是宗喀巴大师为纪念释迦摩尼而创立。第一次传昭大法会于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日举行,宗喀巴大师亲自主持。后格鲁派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将大法会的时间从15天延长到21天,在藏历新年之后进行。法会期间,藏区各地的僧俗群众向拉萨大昭寺汇集,诵经、辩经、迎请护法神、驱鬼、迎请弥勒佛等各种宗教法事活动和典礼一一举行。其中,藏历正月十五日为庆祝释迦牟尼与其他教派辩论胜利而举行酥油花灯节是整个法会的高潮。法会期间,“远近各地的大小施主都在此时来散钱布施”[1]78,清政府即有于藏历正月十五日开展传昭布施的传统。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中央政府派驻的西藏地方官员无法入藏,故其对藏传昭布施传统遂中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鉴于西藏地方宗教势力在西藏地方政治中的影响力及其亲中央的事实,为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统辖之下,中央政府在正面推行政教分离和“赋予西藏高度自治”遇阻的同时,也从侧面利用宗教改善双方的政治关系。其整体思路是:通过优崇藏传佛教,融洽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感情,进而增进地方的内向之心和国家认同感,恢复旧有的政治关系,最终实现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从国民政府存在期间对藏施政的具体情况看,布施西藏地方是其优崇藏传佛教的重要举措。
根据档案记载,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存在期间,持续开展了对西藏地方的传昭布施,但目前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对驻藏办事处的个别年份的传昭布施进行个案分析,二是在关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等较为宏观的研究中涉及到驻藏办事处传昭布施的内容①,尚未有直接以驻藏办事处传昭布施为对象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成果出现。本文试图做一尝试,对其政策背景、开展情况、政治意义等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 实施背景:国民政府的治藏困境与“以教翼政”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未能真正建立起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广州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据研究者考察,民国前期的西藏地方当局对这两种新的政治体制都不认同,认为此类政治体制“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西化,内中一些激进分子甚至有了离心倾向”[2]10。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中,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和中国的认同均逐渐削弱,开始将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定义为“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擅越关系,否认传统上的政治从属关系,并以此作为指导其与中央关系的基本准则”[3]228。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坚持“对藏固有之主权,决不放弃”,将明确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强化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作为对藏施政的中心内容。
为此,国民政府曾一度谋求改变西藏地方政教合一体制,在其地施行与内地其他省份一样的同质化统治模式,如1929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训政时期蒙藏委员会施政纲领》中提出“革新蒙藏旧行政制度”[4]169,但因建政初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整固党国和统合各派军政势力,尚无余力去解决僻处西部边疆的西藏地方问题。1934年,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就明确表示,国家解决边疆问题不外刚性的实力运用和柔性的政策羁縻两种,如实力充沛则以实力解决,如实力不济则以羁縻之策笼络,“吾人今当革命时期,实力不够,欲解决边疆问题,只能讲究政策”,蒋介石所称的“政策”,即“允许边疆自治之放任政策”,让“边民乐于自由,习于传统”,中央“犹有羁縻笼络之余地”[5]105。蒋介石关于处理边疆问题的这一阐述,“深刻反映了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在处理西藏等边疆问题上的力不从心”[3]218。事实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更加力不从心,“柔性的政策羁縻”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治藏的主导政策。
首先是由于“国民党人始终未能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坚固的政治结构”[6]197,加上地方实力派的挑战、国内革命战争的进行和西方势力的渗透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摆脱弱势政府的军政地位和时人认知。尤其是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随着内战的进行,国民政府内部政治腐败和经济危机日益暴露,其统治更是呈现出全面衰败崩解之势。
其次是西方势力对西藏地方的持续渗透。早在18世纪,英国即开始涉足西藏地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曾两次武力侵藏。1903年,时任英印总督寇松(Lord Curzon)提出宗主权的概念,否认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拥有。1921年,寇松正式提出“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②,作为英国对西藏政治地位认知的基本政策。正如梅·格尔斯坦(M. Goldstein)所言,英国对于西藏“最大兴趣在于,把西藏当成名义上的中国自治地方来看待,但要限制中国对西藏的影响”,即所谓的“西藏应当是在大不列颠监护之下的,名义上隶属中国的、拥有高度自治权的西藏”[7]31。20世纪40年代,英国调整其西藏政策,在《艾登备忘录》中提出支持西藏地方争取“完全自治”,以使西藏拥有“类似于主权国家的地位”③[8]165;英国印度事务部和英印政府建议英国政府“支持西藏(地方)对抗国民政府”和“出席国际会议”,英印政府中以黎吉生等为首的侵藏积极分子更是积极怂恿西藏“独立”[8]159,161。1946年,英国明确表示应“将西藏分离出去”[9]127[10]156,1947年又表示“大英政府将继续进一步关心‘西藏独立’的维持”④。此外,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主张“西藏在一种不确定的中国主权的形式下实行真正的自治”[7]543;二战后的美国虽然在官方渠道上没有改变尊重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的基本政策,但也开始“暗中半遮半掩地挑动和支持‘西藏独立’”[11]4。
再次,西藏地方亲英势力为寻求国际政治地位而积极活动。1941年,西藏地方亲英的达扎⑤活佛出任摄政,把噶厦地方政府“各主要部门中热振一派的官员全部清除,由达扎一派的官员所取代”[12]6。由于达扎昏聩无能,噶厦地方政府的“一切实权,皆落到索康⑥、噶蓄巴⑦、拉鲁⑧、夏格巴等亲英分子手里”⑨,其中“索康汪清⑩及葛须白实力最为雄厚”,而索康汪清之父索康·旺钦才旦则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从而形成一个以索康父子为中心的亲英势力集团,即亲英派。亲英派把持下的噶厦地方政府,在英、印等国际势力的挑唆、支持和策划下,开展了系列争取西藏地方国际地位的活动,如拒绝测修中印公路、擅设“外交局”、冲扰驻藏办事处、逮捕前任摄政热振活佛、出席泛亚会议、派遣商务代表团出访以及发动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等。
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蒋介石曾在1942年下达“对藏用兵”的命令[13]140。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国民政府无法调集军队对藏用兵。1942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奉蒋介石机密手谕拟订的《西藏之政治制度及其对于中国之关系》指出:恢复中央在藏主权,应以“先树立中央在藏之威信”为中心,采取“重实不重名”、“划分步骤,不求急进”的方略,稳步推进,以政治运用取代军事运作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方针。事实上,由于英国的干涉,国民政府还“对英国作出了不以军事手段解决西藏问题的承诺”[15]453。
国民政府也曾提出“赋予西藏高度自治”,以缓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逐步施行完整的治藏主权。“高度自治”是1940年代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中心议题[3]171。但由于国民政府内部对于“高度自治”没有完善的方案设计,西藏地方又表示实行自治的“时机未熟”[16]47,这一方案最后不了了之。在“高度自治”方案的研商中,国民政府放弃了最初“革新蒙藏旧行政制度”的设想,明确“西藏自治制度,系指西藏现行政教合一制而言”[4]262,这实际是国民政府在权力式微下为羁縻西藏地方的一种妥协。
在军事运用和政治革新均无法实施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只好持续采取“柔性的政策羁縻”,希冀以合法的利益给予与满足,融洽双方感情,强化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与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
藏传佛教在西藏地方经过数个世纪发展,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仰,对西藏地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力极大。尤其是拉萨三大寺,不仅宗教地位崇高,还拥有参与西藏地方政治之权,其僧人可以僧官的身份参与地方行政事务,其“堪布可代表寺院出席西藏政府各种政治及军事会议,并为出席民众大会之当然代表,其意见颇为政府所重视”,甚至有权否决噶厦地方政府的某些决议[17]162;而且,“三大寺拥护中央”,其喇嘛和噶厦地方政府中的僧官均是西藏地方势力中显著的“亲汉派”[17]69-71。因此,强化三大寺的内向之心,对于增强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并最终解决西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元明清时代统治者们注重利用藏传佛教维系和强化对西藏地方统治的根源所在。
国民政府履行对藏传昭布施举措,始于1930年代。1930年,蒙藏委员会拟派谢国梁为入藏特派员时,即提出“照旧熬茶布施一次”的建议:“按旧例,我国派员到藏,无不有熬茶布施之举”,“特派员到藏后,拟照旧例举行熬茶布施一次”[18]2515,后因谢国梁在入藏途中病逝而作罢。1934年,黄慕松入藏致祭,提出解决西藏问题“须从宗教入手,再从宗教上以推动政治”[19]36。黄慕松抵藏后,不仅规定向三大寺“每寺发基金以垂永久”,使每一喇嘛每年均可从基金中获得收益,还依据清代“驻藏大臣向例每年于正月十五日举行传昭一次”的传统规定传昭布施办法,以藏银691秤为传昭费,“由噶厦(地方)政府与大昭寺堪布负责保管”,以每年所得利息于传昭法会时向喇嘛布施,以“宣布中央德意”,使“喇嘛之倾诚内向可始终勿懈”[17]29。黄氏关于传昭办法的规定,对此后中央政府对藏布施的持续开展具有奠基意义和推动作用。1938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奉命入藏,认为三大寺“握有无上权威”,“喇嘛为社会上一种特殊阶级,具有操纵舆论,左右政治之魔力”[17]143,而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既无武力可以凭藉,复无感情可资维系,所欲赖以运用者,唯在结之以恩惠耳”[17]217,因此他指出,解决藏事只能从“政治方面善为运用”,即“动支巨款”,对西藏地方“僧俗官民给予赏赉,对其寺庙团体广予布施”和“在宗教方面,须由熬茶、布施等佛事,竭力联络三大寺及各寺院”[20]219-228。基于此,吴氏于1940年初在拉萨进行了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布施,使“全藏僧俗咸感中央重视佛教,优待僧民之德意”[21](三),430。
黄慕松和吴忠信入藏布施及其成效,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黄氏离藏内返后,对西藏问题发出“每觉从政治方面入手,不如由宗教关系因势利导,收效较宏”的感叹;吴忠信亦指出,宗教布施“对汉藏关系之改善实有莫大裨益”[21](三),430。基于黄慕松入藏政治交涉的失败和宗教布施的成功,以及吴忠信入藏大规模布施对融洽双方感情和借宗教事务推动政治事务的解决产生的积极影响,国民政府逐渐将对藏政治运用的重心转移到对藏传佛教的优崇上,形成了“以教翼政”的施政方针。蒙藏委员会出台了系列关于优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开展对西藏地方的宗教布施,是“中央对藏施政较具成效的典型之一”,也是“国民政府展开对藏政治运用的重要方面”;不过,在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相关文件中,很少有关于布施的明确规定,布施因此被称为“不是政策的‘政策’”[3]228,236。
二 竭力坚持:驻藏办事处对传昭布施的开展与实际困难
驻藏办事处成立于1940年4月,1949年7月从西藏撤离,共存在9年零3个月,先后经历了孔庆宗、沈宗濂和陈锡璋三位处长。驻藏办事处存在期间持续开展了对西藏地方的布施,包括传昭布施、对重要寺庙的特别布施和中央基金布施等内容,其中根据中央政府及蒙藏委员会指示定期开展的传昭布施是其主体内容。“蒙藏委员会向例于西藏新年三大寺传昭时,由中央拨款汇交驻藏办事处办理”,“为加强政教联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例于每年正月在拉萨传昭时,代表中央布施僧众”[16]46-48。
驻藏办事处先后举行了1941—1943、1945—1949年度传昭布施,而1940年驻藏办事处成立时,因传昭大法会已过而没有举行传昭布施,1944年则因传昭法会时驻藏办事处仍未收到中央拨付的布施经费,加上孔庆宗、沈宗濂之间的职位交替,也没有开展年度传昭布施。
驻藏办事处开展传昭布施的大致流程如下。
第一,与拉让羌锥接洽,确定布施日期和相关事宜。拉让羌锥平时负责三大寺日常所需的酥油、茶叶以及拉萨及附近主要寺庙的生活所需和供奉物品;传昭大法会期间,则负责大法会的开支和收入,安排各地前来布施的大小施主们的布施等事宜。噶厦地方政府通过拉让羌锥向驻藏办事处发出布施邀请,是驻藏办事处开展传昭布施的第一步,也是尤其重要的一步。收到邀请,驻藏办事处回复确定开展布施后,再派员与拉让羌锥接洽,商定具体布施日期,并衔请藏官帮忙。一般情况下,噶厦地方政府会指示拉让羌锥派出协助驻藏办事处办理布施的总管和人员。待总管派定,“彼即于藏历年前择日携带书记一二人来(办事)处筹备”。办事处在总管到来之前,需准备好现金、哈达、纸张(备作纸封用)、分装现金的口袋及装现金口袋的箱子等。待总管到来,共同分装布施当日所需之布施现金和酬谢各帮忙人员的现金,并分配确定布施当日大昭寺各门负责发放布施的人员。此项事务,拉让羌锥“总管来处一次或二次即可办竣,现金钱袋均由彼亲自装封盖印,装箱后仍由彼打漆盖印,直至传昭之日应用时再由彼等当面验开”[22](九),431-432。
第二,驻藏办事处筹备事项。上述事项完成之后,驻藏办事处开始进行其他的筹备工作,包括购买布施当日熬茶、放粥所需之物品,筹备布施当日的仪式等相关事宜,邀请帮忙的藏官、汉人等,以确保布施当日各项事务均能顺利进行。
第三,正式传昭布施。驻藏办事处开展传昭布施,大多会于布施当日先在大昭寺举行仪式。参加该仪式的人员,主要有达赖喇嘛、甘丹赤巴等藏中政教领袖人物,噶厦地方政府主要官员,驻藏办事处处长和部分职员等。如有仪式,则驻藏办事处人员先行前往大昭寺参加仪式,再前往大昭寺各门发放布施。如无仪式,则各相关人员待准备妥当后适时前往大昭寺各门,等到上午9时左右,大昭寺各门开启,众喇嘛鱼贯而出时,即向他们发放布施。传昭布施开展时,现金布施为必备内容,熬茶、放粥则视情况而定,或熬茶放粥,或放粥不熬茶,或熬茶不放粥。布施当日的现金布施,由办事处人员负责,并聘请帮忙人员在大昭寺七门同时发放,熬茶、放粥则由处中所请帮忙人员在拉让羌锥的统一安排下进行。
第四,受贺。现金布施发放完毕之后,“即有陆续献哈达送礼道贺者”,办事处对送礼道贺者均一一登记,并返还“份金哈达”,也一并登记在册[22](九),456。此类送礼道贺的有无及多少,则因驻藏办事处和噶厦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有所不同。而对于送礼道贺者,驻藏办事处接受与否、如何接受、如何还礼等,并没有一定之规,主要视该年度传昭经费多寡和送礼道贺者的身份地位而定。据戴新三《拉萨日记》记载,1943年,因经费困难,办事处“决定凡汉人来挂哈哒及送份子者均不收,以期节省糜费”。该年,因政治上已陷入僵局,布施结束后,前来道贺挂哈达者,与前两年相比少了许多。陈锡璋时期,相对此种冷清情形要好很多。如1947年,驻藏办事处向帮忙藏官及前来道贺的藏官、喇嘛等发出份金100余份,每份藏银5—100两不等,共计2800两,其中包括噶伦代表、总堪布代表、色拉寺堪布以及哲蚌寺、甘丹寺康村代表等[22](九),450-451;1948年布施后,驻藏办事处收到来自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十四世达赖新公馆,噶伦、孜本、堪琼等官员,以及总堪布、色拉寺杰扎仓,哲蚌寺、色拉寺部分康村等的贺礼,发出还礼份金共37份,每份藏银15—100两不等,共计2707.5两[22](九),456-460。
第五,收尾工作与布施结束。收尾工作,一是结算款项,与拉让羌锥派定之总管清算账目,确保手续完备,账目清楚;二是招待和感谢协助布施的藏官及其他帮忙人员;三是处理其他杂务,包括付给零星请赏者和帮忙之川回帮(在藏汉人)人员赏金、清点收入礼品和账目总结算等[22](九),435。
驻藏办事处的传昭布施,困难重重,如政治环境恶化、经费短缺、人员匮乏等,都直接影响传昭布施的开展。
决定传昭布施能否正常开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噶厦地方政府通过拉让羌锥向驻藏办事处发出邀请,而拉让羌锥是否派定总管和协助驻藏办事处邀请其他帮忙藏官,则是直接关系到传昭布施能否如期开展的关键点。1942年,由于刚成为摄政的达扎活佛及其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有较强的“独立”愿望,在拉萨主导了“外交局”事件和“藏警案”。鉴于西藏地方在此两次事件中表现出的“独立”倾向,中央政府竭力遏制其“独立”行径。时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虽是奉命与西藏地方交涉,但在交涉中表现得过于强硬,最终形成双方的政治“僵局”,以致驻藏办事处与噶厦地方政府之间“无法往返”[21](四),311-312。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3年。该年春节期间,“西藏举行各种典礼时,拒绝中央代表参加”[23]252。在这种情况下要开展布施,驻藏办事处就不得不顾虑噶厦不发出布施邀请、帮忙藏官请而不来等问题。尽管1943年的传昭布施最后得以顺利开展,但这些问题也着实让驻藏办事处苦恼了一番。关于1943年的政治“僵局”对传昭布施的影响,笔者曾有专文论述[24]92-101,此不赘述。
中央政府能否按期足额划拨布施经费,是决定驻藏办事处能否顺利开展传昭布施的另一重要因素。据戴新三日记记载,1941年,中央虽划拨约11万两藏银的布施费用,但没有在布施前及时拨付给驻藏办事处,驻藏办事处只得以每秤年息藏银六两的利息向拉让羌锥借款来开展传昭布施;1942年,中央汇款仍然迟到,驻藏办事处再次向拉让羌锥息借藏银10万两开展传昭布施。此两年传昭布施的总花费均为8万两左右。1943年传昭前,因为驻藏办事处与噶厦之间形成“无法往返”的政治僵局,加上办事处1942年布施时向拉让羌锥息借的藏银未全数归还,而无法再以借款的模式开展传昭布施。据当时的驻藏办事处科长戴新三日记记载:1943年1月29日,拉让羌锥回话请办事处速定布施日期时,特别提及“彼未提去年攒招办事处借用未还之五万元欠款,推其词意当有不能再借之意”。孔庆宗在1942年11月向蒙藏委员会请拨了次年传昭布施费用,迟至1943年1月中旬财政部才汇出牌汇10万元的布施费用,此时距离传昭大法会已不足一个月,而且因印币跌价,“每盾换藏银四两”,10万元牌汇“共仅换得66500两”,总额减少了33.5%;为如期开展布施,驻藏办事处多次召开处务会议,最后“觅汉藏各商家,洽卖印币”,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布施经费的兑换与筹措,并决定除现金布施外,“仅放茶一次,不放稀饭”,勉强完成了该年度的布施。陈锡璋时期,中央拖欠布施经费时间,少则1年,多则3年。仅就笔者查询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中,自1946年起至1949年驻藏办事处撤离前夕,陈锡璋催促、询问布施经费的电文就多达近30条。1946年,陈锡璋在没有收到布施经费的情况下,依靠借贷援例举行了该年度传昭布施,之后多次向蒙藏委员会催询这笔费用,但直到1947年10月行政院才核准1946年度的布施费用共计印币6万盾[22](十四),97,直到1948年6月驻藏办事处才收到其中的一半,剩下部分于1949年3月才收悉[22](十四),163,167。这笔费用的拖欠时间长达3年之久,可见驻藏办事处遭遇的经费困难情形之严重。1947年,驻藏办事处借支藏银7896.8两用于布施,该年布施共花去93781.8两[22](九),446,456,尚有近2万两的差额;而财政部核定的布施费法币5516万元(该年汉僧、布施、格西、捐修等费,共印币11.266万盾),直到1949年3月都没有到达驻藏办事处[22](十四),101,264,266。对于1948年的布施,蒙藏委员会在1947年12月直接电告驻藏办事处,“仍盼挪款办理”[22](十四),102-103。该年布施共花去藏银94946.1两[22](九),455,办事处在1949年1月才得知财政部核准了该年度的布施费,但仅为印币2289盾6安3派[22](十四),249。虽然驻藏办事处在该年3月收到了此项费用[22](十四),265,但实在少得可怜。1948年初,印币对藏银的折合率大约为1:3.7[22](十四),288,藏银94946.1两约相当于印币25661盾,财政部核准的费用还不到总花费的1/10。1948年底,蒙藏委员会指示照例开展布施,并确定布施经费为印币5.8万盾[16]48。但此时由于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再加上战争的影响,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驻藏办事处,经费都更加困难。驻藏办事处因会中长期拖欠各项经费,日常开销所需均赖借贷,至1949年处中积欠款项达70余万盾[22](十四),259。1948年下半年起,“债主纷来逼还债款”,陈锡璋称“实在无法应付”[22](十二),528。但是在经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驻藏办事处在1949年仍然“依照惯例,向各大寺庙发放布施”,并于布施期间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呈送份金,只是在费用上“已不似前些年那样显得手头阔绰”[25]85。
除经费问题外,人员不敷使用,也是驻藏办事处在传昭布施中面临的问题。根据1940年9月《修正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和1944年4月《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的规定,驻藏办事处的人事组织为处长1人、副处长1人、主任秘书1人(沈宗濂时期增设)、科长2—3人、汉文和藏文秘书2—4人、科员4—8人、办事员4—8人、会计员1人、医师1人、专门技术人员1—6人,以及咨议、雇员若干人等。按此计算,驻藏办事处的总人数最多可达36人。但因种种原因,驻藏办事处实际在职人员远未达到此数。孔庆宗时期,职员在职情况为:1940年11人,1941年17人(含驻印办事员1人),1942年16人(含驻印办事员1人),1943年15人(含驻印办事员1人、联络员2人),1944年沈宗濂入藏前16人(含驻印办事员1人、联络员2人)[21](四),31-81。1944年,因沈宗濂入藏对驻藏办事处进行人事调整,处内实际在职人员达20人(含驻噶伦堡和加尔各答联络员各1人),另有临时人员4人,总计24人,是驻藏办事处时期在职人员最多的一年,但1945年底就降为19人(1位藏文秘书和3位专员离藏,另有1名咨议离世)[21](四),498-501,535-538,579-590;(五),1-46。陈锡璋时期,处内在职人员最多的年份是1946年,计有副处长、秘书、科员、专员、办事员、医疗所主任和驻加尔各答联络员等16人;1946年以后,驻藏办事处辞职或请假离藏的职员增多,实际在岗人数逐渐减少,大致为1947年12—14人、1948年10—11人、1949年10人;这期间的驻藏办事处在人事上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在1948年上半年仅有的10人中,包括副处长兼代处长陈锡璋在内的3人已经呈请辞职获准,此后的时间只是在等待合适时机离藏[21](五),156-203。
开展传昭布施,各种事务繁多,以驻藏办事处这一二十人的规模,自然无法独自进行,即便仅为各项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员也不敷分配。所以,每年开展传昭布施时,驻藏办事处都要邀请藏官、川回帮保正、中央政府驻藏各机关职员、在藏汉商汉僧等协助办理,以确保布施的顺利进行。孔庆宗时期曾请过国民政府交通部拉萨电台(电报局)台长谭兴沛、军统拉萨站情报员胡明春、曹巽等人协助。陈锡璋时期,筹备阶段即“召集川回帮保正派定帮忙人员……一般川帮20名,回帮10名”;正式发放布施时,各门汉官“因人手不足,大约每门只得一人,余均请本地汉商帮忙”[22](九),432-433。如1947年,驻藏办事处开展传昭布施时,邀请川回帮保正派定20余人予以协助,这20人包括管厨3人、熬茶3人、管碗3人、伺候上座番官4人、招待滇平客商2人、招待番官随从4人、回教做咖喱饭9人[22](九),437,还请汉僧协助布施,如请自费汉僧张注汪“担任南门中队负责人”,请公费汉僧广润负责“招待事宜,收礼记录事项”[22](九),438-439。1947年,实际参与发放布施的29人中,仅6人为驻藏办事处职员,其他均为中央政府其他驻藏机关人员、川回帮保正和藏中商号派定人员以及在藏汉僧;1949年,实际参与布施的59人中,仅3人为办事处职员,帮忙藏官有16人,其余均为中央政府其他驻藏机关职员和在拉萨的汉人[22](九),464-465。此类事实,均反映出驻藏办事处人员严重不足。邢肃芝说,驻藏办事处布施时,“动员所有在拉萨的汉族官员出动”[26]248,所言不虚。
尽管在开展传昭布施时面临着种种困难,但驻藏办事处并未放弃布施。处长孔庆宗原是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1939年,吴忠信入藏时,孔为委员长行辕第一组组长,并作为先遣专员先期启程赴藏。吴忠信基于西藏地方宗教势力的分析而提出应重视对藏布施,如“三大寺握舆论中心,其喇嘛、堪布,均系富有智识、领导群众之人,凡熬茶、布施之厚薄,所给予一般之观感影响,关系甚大……乃西藏人心之所系及中央德意之所关,无论财政如何困难,亦不能不勉力从事也”[20]220-224,以及其在藏广予布施产生的积极效果等,都对孔庆宗产生了影响,使其有所认识和体会。孔庆宗领导下的驻藏办事处,在编制1941年度的行政计划时指出:“三大寺握西藏政治权利之重心,有喇嘛两万余,具有极大之潜伏势力。清例,年由中央发帑熬茶布施,崇其教,因辅其民。廿九年,吴委员长于传昭时,代表中央布施每一喇嘛藏银七两五钱,全藏僧俗咸感中央重视佛教,优待僧民之德意,对汉藏关系之改善实有莫大裨益”,提出了于“卅年正月间传昭三大寺喇嘛齐聚时,中央照例熬茶布施”的建议;在1942年度的行政计划中也明确指出:“中央于传昭时布施,不特符合多年之成例,且可深得佛教中心势力之拥护”,再次提出“于卅一年正月传昭,三大寺喇嘛齐集时,中央照例熬茶布施”;在1943年的行政计划中复又提出“三十二年度传统布施按援例办理”[21](三),430,520,665。正是基于对布施的重要性的认识,才使得孔庆宗在种种困难中坚持开展传昭布施。陈锡璋时期,开展传昭布施所面临的经费困难比孔庆宗时期要严重得多,尽管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陈锡璋对于传昭布施之重要性的直接表述,但仅从陈氏在驻藏办事处各项经费常年被拖欠、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开展传昭布施,即可见其对传昭布施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1949年2月初,陈锡璋在面临“债主纷来逼还债款”、已“无法应付”[22](十二),528之时,召集处中人员商议局势及应对办法,与会人员均表示:“同仁等但能支持一分,绝不愿透露倒台迹象,宁愿在经费未到期间一律暂不支薪,共撑艰局……无论如何艰窘,本年布施必须设法举办,以示镇静而期挽回藏人几分心理”[22](十四),254,清晰地展出了陈锡璋及处中职员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仍能心系国家主权,竭力维持,持续开展传昭布施,其精神实在值得肯定。
三 实际成效:驻藏办事处持续开展传昭布施的政治意义
1940年代,在西方国家对西藏地方积极渗透,西藏地方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强之时,中央政府虽然始终坚持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却无法以政治和军事措施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只好在“柔性的政策羁縻”之下开展政治运用,优崇藏传佛教,希冀以宗教为纽带关联西藏地方,将西藏地方置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防止其走向独立。
传昭布施在有清一代已成为制度化的举措。驻藏办事处代表中央政府开展对西藏地方的传昭布施,办事处人员身着汉式礼服,携带预先准备好的封盖印章的钱袋,在大昭寺各门向数万喇嘛发放藏银布施,某些年份还伴随着隆重的仪式,再加上拉让羌锥的事先安排以及公布的布施日程等,均能使领受份金的喇嘛知道布施来自国民政府,进而感念中央爱护佛教之德意。同时,盛大的布施场面及延续清代驻藏大臣布施的历史传统,加上深植于民众心中的“按班”形象,足以给拉萨民众留下良好观感。
于国家而言,传昭布施的举行,是以时间的重合、场景的重现和仪式的举行等物理化地宣示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表明西藏地方是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之下的一部分。而在国民政府行将败退大陆,西藏地方寻求“独立”和美、英、印等国试图支持西藏“独立”之时,援例开展传昭布施,更使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教联系在国民政府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得以继续维持,这既是对内的主权宣示,也是对外的主权宣示,对于抵制西藏地方和一些国际势力所谋求和推动的“西藏独立”活动具有积极意义。驻藏办事处在种种困难之下坚持开展传昭布施的精神和努力,尤其值得肯定和称赞。
就强化认同感而言,“从‘被给予’和‘选择’入手是两条必由之路。就‘被给予’而言,即是强化产生这一认同的‘历史记忆’;就选择而言,即从利益的驱动作用入手”[27]20。布施的开展,即是从后天利益驱动入手,以强化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感,当然同时也具有强化共同历史记忆的作用。
具体而言,持续开展的传昭布施,“使两万余僧众重感中央之深恩,各寺咸以中央尊重佛教,恢复清代旧例,亦皆表示感戴拥护”,就连曾因民初拉萨变乱、寺中喇嘛被杀而“深切仇汉”的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在驻藏办事处开展布施后,也“态度顿变”,与办事处联络“至佳”[21](三),665。可见,布施对于笼络藏中喇嘛僧众、争取宗教势力的内向以及强化他们对中央政府的认同,确有积极作用。
而事实上,布施不仅有助于争取僧众的内向,也有助于争取藏中官员的内向。驻藏办事处开展布施事务,均有赖于噶厦地方政府和西藏地方寺院的支持和配合。如前所述,在1943年的政治“僵局”之下,驻藏办事处在讨论是否要开展布施时,曾提出“往年例请藏官协助,现在僵局未开,藏官请而不来又将如何”,但事实是该年噶厦地方政府同样令拉让羌锥“协助办事处办理中央攒招(传昭)布施事宜”;1949年传昭布施时,更是得到了噶厦地方政府3孜本、1仲译钦波、3扎萨、2台吉以及代本、孜代表、雪代表等的帮助[22](九),464-465。其中,3孜本是当时噶厦地方政府4孜本中除夏格巴以外的3人;3扎萨包括擦绒·达桑占堆和阿旺坚赞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擦绒扎萨,曾任藏军总司令和噶伦,在40年代仍然保持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28]127;2台吉有桑颇台吉,他既是“第七世达赖的后裔”,也是“台吉中资格最老的”[29]116。此外,布施结束后,到办事处“送礼道贺”者,虽在某些年份会受双方政治关系的影响而有所减少,但也从未中断过。如在僵局之下的1943年,也有帮忙藏官、色拉寺拉基、堪布以及色拉寺、甘丹寺和哲蚌寺个别康村前往办事处道贺;1947年,布施结束后,噶伦代表、总堪布代表、色拉寺堪布以及哲蚌寺、甘丹寺康村代表等均前往驻藏办事处道贺;1948年,驻藏办事处收到了来自十四世达赖新公馆,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其他噶伦、孜本、堪琼等官员,以及总堪布、色拉寺杰扎仓,哲蚌寺、色拉寺部分康村等的贺礼。孔庆宗时期,在政治“僵局”之下的布施,仍能得到噶厦地方政府的援助;陈锡璋时期,在1949年的布施中还能得到藏中高级官员直接协助,以及布施结束后的送礼道贺和份金发还。这些均说明传昭布施具有一定的政治效用,有利于促进驻藏办事处与噶厦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藏中主要寺庙的良好关系和互动,争取藏中部分官员的支持与内向,进而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
但同时也要看到,传昭布施的政治效用也是有限的。如1943年传昭布施完成之后,“哲蚌各扎仓康村,铁棒喇嘛等,以及各藏官,汉商,汉僧均无一人来挂哈哒”,时任科长戴新三在其日记中写到,办事处“冷落情形,想较去前年相去远矣”。陈锡璋时期传昭布施结束后,三大寺堪布中,前往办事处祝贺仅有色拉寺堪布,哲蚌寺和甘丹寺堪布均未前往祝贺,该两寺康村也主要是其中的汉人康村派代表前往道贺,如哲蚌寺甲绒康村、甘丹寺甲绒康村。色拉寺一是因为驻藏办事处成立后广予布施,与办事处联络“至佳”[21](三),665;二是色拉寺作为热振活佛的母寺,在1940年代,随着热振与达扎矛盾激化及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需要中央政府支持,因之与驻藏办事处维持友好关系。
综上,在中央政府权力式微、无法以实力根本解决藏事时,持续开展宗教布施,对于增进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感情,树立中央政府的在藏威信,强化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驻藏办事处在存在期间,尽管面临人员不足、政治环境恶化和持续的经费困境,但也尽力持续开展布施,以推进藏事,应予以肯定。但也要看到,宗教布施和羁縻笼络并非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毕竟布施在强化国家认同感上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要切实解决西藏问题,不仅需要中央政府满足西藏地方合法的利益诉求,更需要以实力做后盾的强大中央政府给予西藏地方以“中国”身份和相应的观念意识,并进行相应的主权体制建设,变“异质化”统治模式为“同质化”统治模式,使国家权力能够最大限度地深入西藏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