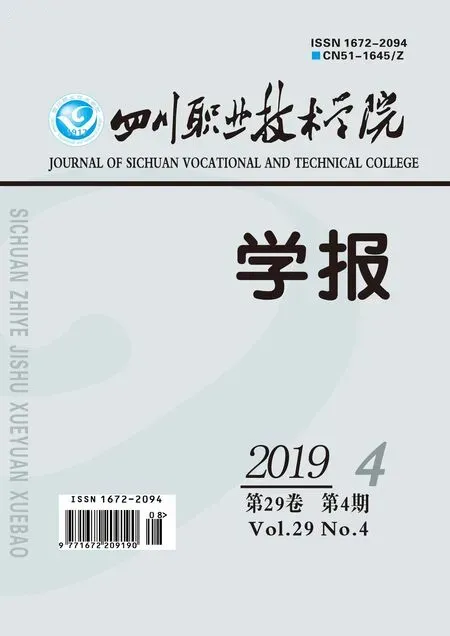梁实秋佚信释读及其思想观重估
2019-02-22施婷婷刘文辉
施婷婷,刘文辉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南昌 330013)
梁实秋一生钟爱写信,其书信的数量不计其数,诚如其女梁文蔷所述“写信是爸爸生命中很重要的一环。他爱收信、爱写信、爱发信、爱藏信……我常喜调侃爸爸,说他一辈子只会做两件事,一是写稿子,二是上邮局。爸爸写信之勤快,很少人能望其项背……”[1]。鹭江出版社2002 年10 月出版的《梁实秋文集》第9 卷书信集是目前为止有关梁实秋书信最为完整的辑录,但书信总计仅为404 封,仍有大量遗失的梁实秋书信尚未被发现。截至目前,经过学术界的不断努力,梁实秋的书信又有新发现,如段怀清发表于《新史料文学》2012 年第2 期的《梁实秋致陈纪滢书信四封及其他》,宫立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 年4月8 日的《梁实秋致弟函》给胡适的书信,宫立发表于《新史料文学》2018 年第2 期的《梁实秋佚简三通释读》致《复旦旬刊》编辑、刘英士和赵清阁(骚人)三人的书信。近来,笔者通过史料的发掘,也新发现梁实秋的书简一封,未被收录于《梁实秋文集》、陈信元编的《梁实秋文学年表》[2]和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年出版的《雅舍遗珠》,这就是1935 年3 月30 日发表于《华年》第4 卷第12 期的《关于青年思想问题》,是写给《华年》编者潘光旦的信简,涉及梁实秋与潘光旦的笔战及梁实秋在20 世纪30 年代的政治思想。笔者将通过对这这封佚信的考释来重估梁实秋的思想倾向。
一、佚信《关于青年思想问题》释读
佚信原文如下:
编者先生:
读贵刊四卷九期《再论青年思想问题》一文,甚佩高见。先生以为我“似乎并没有十分看准了这个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那么症结究在那里呢?先生说:“反抗情绪决不会无因而生;必有造成此种种刺激在。……第一步我们先得把这些刺激寻出来,然后再在去除此种刺激的一方面努力,这才是根本的建设工作。”其实那“刺激”倒底是些什么东西,先生并没有明白说出来,而我却说出来了,我说“因了外侮的煎迫和国内政治的窳败青年思想变成左倾……”。这一句话还经先生大文引录,怎么先生又说我“似乎并没有十分看准了这个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呢?
青年思想左倾,当然有根本原因在,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准这个问题的根本症结。不过这一问题有多少方面,有多少看法,我在大公报所作的文章是有篇幅限制的,不能把一个问题的各方面都讨论到,犹之乎先生的大作也并没有畅所欲言。假如要源源本本的讨论这样的一个大问题,不要写成几十万几百万字吗?
先生所说的“自由”与“公道”,甚是甚是。有一件小事我向先生报告:我在大公报发表的论文,是经过删削的,照原来的样子是不能在报纸上印出来的。这件事实,在我看来是“自由”受了侵犯,在先生看来,也是不合于“公道”的罢?公道不仅是自由,而自由之被人无理剥夺一定是一种不公道。争自由即是争公道之一端。我看现在左倾青年所受摧残,不能不出来说句公道话,所以才有大公报上那篇文章。先生还忍心说我是“只注重了自由忽略了公平”吗?
素仰贵刊持论稳健和平,故略申辩如上。其实我们的见解,诚如大文所说,“很相彷彿”的。我盼望贵刊多载几篇文章给左倾青年看,同时再多写几篇文章给压迫左倾青年的人看。现在有许多青年因思想而犯罪,当局对待他们的手段是令其“悔过”“宣言”,唉,这是惨痛的事实!主张“公道”的人现在应该出来说句话了!
潘光旦是梁实秋的清华学校校友,他于1932年4 月开始编辑期刊《华年》,《华年》属于评论性刊物。载文包括长短评、专著与译著、书报介绍、新诗与旧诗、讽刺漫画等。该刊作为一份评论期刊,其内容涉及国内外并着重于青年思想问题。
20 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先进分子。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处于灾难中的中国人挣扎着寻找救国之路,此时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并大量地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便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尤为动荡,特别是青年的反抗情绪甚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知识分子察觉到了青年思想中的过度左倾思想问题。针对这种青年思想中存在的极端左倾问题,《华年》的编者潘光旦在1935 年1 月26 日 的《华 年》第四卷 第3 期 发表了《青年的思想问题》一文,专门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青年左倾思潮如洪潮惊涛,以不可抵御之势冲到一般青年的心中…在背后都夹有极浓重的反抗的情绪。这种反抗情绪绝不会无因而生;必有造成此的种种刺激在。”[3]同时潘光旦还指出为纠正这种思想,应该“先得把这些刺激寻出来,然后再在去除此种刺激的一方面努力,这才是根本的建设工作。”[3]
而梁实秋在1935 年2 月24 日的天津版《大公报·星期论文》上也发表了相似的文章——《青年思想的问题》,他认为除了没出息的青年,其他一部分有出息的青年对于国事都有极度的悲愤,对民族前途抱有很大的忧虑,而青年思想变成左倾即是“因了外辱的煎迫和国内政治的窳败”[4]。梁实秋指出要合理处置青年左倾思想的问题,就要有“容忍”的雅量,“第一,在政府方面,应该给青年以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第二,在教育方面,应该给青年以完全的学术研究的自由……”[4]对于这篇文章中梁实秋解决青年左倾思想的办法,潘光旦提出质疑,他在1935 年3 月9 日的《华年》第四卷第九期的《再论青年思想问题》一文中批判梁实秋在解决青年思想问题时“似乎并没有十分看准了这个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5]。潘光旦指出人类文化的进步有两个主要的要素,一是自由,二是公平,而梁实秋“就只注重了自由,忽略了公平……而今日最紧要者尤其应该在公道一点上的努力”[5]。1935 年3 月30日,梁实秋在《华年》第4 卷第12 期以《关于青年思想问题》这封信来反驳潘光旦,说潘光旦没有说明白他文章中的“刺激”是什么。另外,关于潘光旦批评他没有看准“自由”和“公道”这一问题,梁实秋也辩白道:“公道不仅是自由,而自由之被人无理剥夺一定是一种不公道。争自由即是争公道之一端。”[6]这篇佚文一方面反映出梁实秋兼有公道的自由主义观,另一方面呈现了抗战前夕社会青年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左倾思想问题,侧面折射出当时激愤、动荡的社会状况。
其实,关于青年思想的问题,梁实秋曾多次撰文表达他的观点。笔者近日发掘到梁实秋的另一篇佚文《对青年谈自由问题》,其中关于青年思想自由问题梁实秋提出三个观点:“第一,思想不是信仰,是独特的贡献;不是人人能有的,不过应该培植它;第二,思想自由之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懒惰;第三,“左倾”“右倾”都是有作用的名词,制造出来骗诱人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任何“倾”,我们要有自由思想。”[7]梁实秋始终站在青年思想自由的立场上,反对阶级、反对“左倾”和“右倾”。正如梁实秋曾经的自述:“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8]
二、佚信中的思想观剖析
在现代文学史中,梁实秋一直以来都是以散文大家、风雅儒者的形象为人说道。但在抗战前,他也是一位热衷于谈论政治的政客。清华学校毕业后的1923 年至1937 年之间,梁实秋发表的大多是有关政治的政论及文学批评。梁实秋垂暮之年,回顾平生,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自已年轻时喜欢“谈”政治。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间,梁实秋在北京“谈”政治的热情,几乎与他谈学术的热情一样高涨。搜集到的这篇佚信中,最突出的是他倡导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
(一)以民族为根基的国家主义主张
作为一名国家社会党党员,梁实秋始终倡导“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在政治思想上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以民族的团结一体来作为一切的根据”,并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内外纷争;在文化上,不希望本土儒家文化被各种外来的文化冲击和左右。所以说,梁实秋从一开始就反对青年思想被社会动荡的气息所影响。
作为一个呼吸着五四新文化的空气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梁实秋的这种国家主义思想是由他的文化立场决定的。而他这种文化立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而大的时空背景。清华学校时期,学校的“国耻纪念碑”,引发了梁实秋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发扬,使他出国前就有了强烈的传统文化本位的国家主义思想,也奠定了他日后的国家主义倾向。后来梁启超在清华的国学演讲,更进一步推动了梁实秋的文学步伐,让他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清华期间,他参加“孔教会”,并且还“提倡国粹”,撰文强烈批评上海的西方化,甚至呼吁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子:“……我愿大家——尤其是今年赴美的同学——特别注意,若是眼珠不致变绿,头发不致变黄,最好仍是打定主意做一个东方的人,别做一架‘美国机器’!”由于留学前梁实秋的国家主义思想已深深扎根,这为他在留学期间的行为和思想导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赴美留学时,梁实秋在随身携带出洋的物品中,带了一面自制的丈余长的国旗,这在留学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之后,与清华庚款留学生校友于1924 年9 月初在芝加哥集会成立“大江会”,并创办《大江季刊》刊物,而这个刊物的主旨即为倡导国家主义——“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机处境,不愿意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闻一多也曾说:“大江会的创立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国内外维护传统文化富于国家民族观念的知识分子,纷纷以创会、办报、结社的方式,表达国家主义立场”[9],属于其中一份子的大江会,就此建立了与其他国家主义社团的政治文化姻缘,这就是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归国后,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的梁实秋,基于一贯的民族文化立场倡导一种国家主义的精神,在此种意义上并不是很赞同共产党的阶级观念,因此随之与共产党分流。
(二)以政治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倾向
梁实秋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身份标签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此标签印象始于《新月》时期。当时梁实秋与主张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知识分子胡适、罗隆基时常议政并联合出版了《人权论集》这一带有政治自由主义的论文集。此后,梁实秋也一直以自由主义自我标榜,遂使得自由主义这一符号标签如影随形的伴随梁实秋一生。但梁实秋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并非是完全西化的自由主义,而是站在儒家文化为根基的自由主义。
从横向看,梁实秋在文化方面不主张自由主义,而是以民族为出发点,提倡新现代的儒家文化,即提倡文化民族化。在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胡适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旗帜。而梁实秋与胡适在政治上大致有聚合的状态,但在文化立场上却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作为新儒学文化派的代表,梁实秋在文化上持有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他极力反对科学主义、反对民主,推崇文化的民族化。而一直以自由主义西化派为符号的胡适在对待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方面却不持保守的观点,他则一生坚持科学实证主义,主张西方文化的兼收并蓄。由此可以看出以梁实秋为主的新儒学文化派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共鸣中走到了一起,却在文化立场上最终分流。基于思想上与胡适的相异,梁实秋在回忆胡适时也与其刻意保持距离,如他在《怀念胡适先生》中所说“我认识胡先生很晚,亲炙之日不多,顶多不过十年,而且交往不密,连师友之间的关系都说不上”[10]。对于一些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将他描述为胡适所在的新月派成员时,他在《忆新月》中辩白到“我有时也被人称为‘新月派’之一员,我觉得啼笑皆非。如果我永久的缄默,不加以辩白,恐怕这一段事实将不会被人知道。这是我写这一段回忆的主要动机。”“‘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11]在政治方面,梁实秋主张英美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社会革命主张面前,自由主义政治的改良主义一派与梁实秋文化保守主义一派都推崇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认为社会各界人士在社会中不应被外在社会氛围所影响、所牵制,要依据自己的思想自由表达观点,享受自由言论的权利。这就使得梁实秋在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上与自由主义西化派不谋而合。正如高旭东先生在“梁实秋与中西文化”研讨会上做过《梁实秋:何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文人》的论文中所指出的,“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梁实秋说不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从政治批评的角度却体现出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因此,梁实秋所坚守的自由主义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而绝非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从纵向看,梁实秋的自由主义倾向不仅针对思想自由,而且还包括批评自由和议论自由。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梁实秋所追寻的自由,绝不是放弃责任和义务,自外于社会和人群;而是始终保持住个人自由思想、自由批评、自由议论的权利。1935 年11 月22 日,梁实秋一手创办了《自由评论》周刊,创刊号的《编者后记》中,揭示了他的办刊宗旨:“本刊没有照例的‘发刊辞’因为‘自由评论’四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明白的解释。本刊同人并没有任何全体一致的意见,不过我们都是爱自由的人,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我们是绝对保护的。”[12]在创刊号中,梁实秋发表了《算旧账与开新账》一文,他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13]文章大力呼吁政府当局开放党禁,还民思想自由,还政于民,实行法治。
(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契合
拥有两重身份——“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梁实秋,看似是一个矛盾体,实则凸现了梁实秋一直以来的新儒学的一个思想,而这种新儒学思想正是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梁实秋个体上的一个契合点。新儒学提倡“现代性”的儒家文化,这种现代性是基于儒家思想,借鉴白璧德人文主义,打造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化的途径。不管是国家主义抑或是自由主义,梁实秋始终站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立场去辨析。梁实秋对儒家文化的坚定信仰,使他在以孔孟之道为信仰的台湾成为“敦厚温柔之宝”。当然,作为一名留美归来的学者,他亦不同于像林纾一样的守旧派,他冲破了保守思想的束缚,坚定地支持当今社会特别是青年应该被赋予足够自由权利,而不是一味的接受,要站在儒家文化的根基上寻求思想上的自由。
梁实秋曾经说过:“我对梅花的冷峻怀有非常的向往。人之不可随波逐流,似乎也仿佛梅花之孤芳自赏。”[14]短短的一句话似乎一语道破了梁实秋早年的思想境界:犀利,锋芒毕露,对万事保持自己的人生见解且不被外物左右。而本文正是对梁实秋佚信中透漏出的这种思想境界的一种诠释。
当前,笔者搜集整理的有关梁实秋的佚简仅是一个开始,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笔者相信在此基础上会有更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书信资料将被发掘。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据,对于多方面、全方位感知作家,研究其他文人作家填补研究界的空白,甚至于深层次评估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