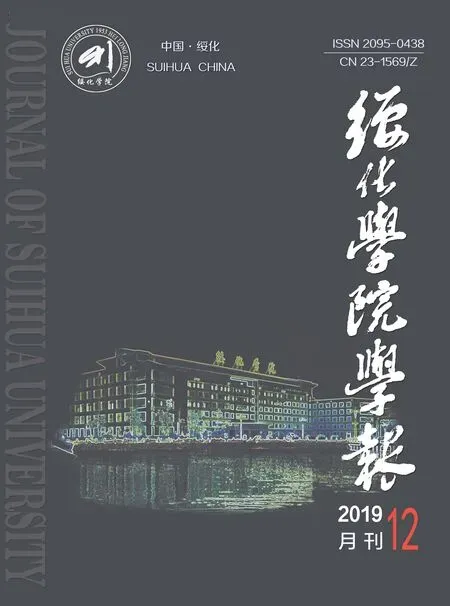融入与背离:新世纪以来文学中的贞操书写
2019-02-21李巧丽
李巧丽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一、失贞与堕落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或明或暗地就贞操展开了大幅度的想象,其中失贞后堕落的女性不在少数。孙慧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李平、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玉墨、关仁山《九月还乡》九月、铁凝《小黄米的故事》小黄米、魏薇《回家》小凤、孙频《隐形的女人》郑小茉、韩庆邦《月儿弯弯照九州》罗兰等。《我是真的热爱你》冷红在父亲病逝、母亲卧病、妹妹上学的情况下辍学离家打拼,即使在外工作相当不易,她从没有想过堕落,在骨子里她极度厌恶那些卖春的女人,所以,为了筹钱她不惜卖过几次血,但是她要守住底线的愿望因为方捷的设计失身而付诸东流。冷红还是沦落风尘,当冷红的妹妹冷紫得知姐姐的情况后,辍学来到姐姐身边监督姐姐,劝阻姐姐回归正途,可得到的只是冷红的鄙夷,在她看来“与其这么逼我去重做回那个流血的天使,不如就让我做一个健康的魔鬼”,冷红从一个受害者转变为一个害人者,其人性随着堕落的过程埋葬在这欢场中,为阻碍孪生妹妹的救赎计划,竟然伙同迫害害人者——方捷——又设计了一场失贞事件(显然,冷红知晓贞操对于良家女——妹妹的意义,因为她自己的堕落就与失去贞操密不可分,所以她才能够通过贞操完成对妹妹的“改造”),冷红与方捷的计划成功地逼迫冷紫加入了色情业,虽然冷紫进入色情业是怀着救赎愿望答应帮助姐姐实现挣100万的目标、但是冷紫终究也是在失去贞操后才进入的色情业。乔叶讲述的是两位坚决捍卫贞操的良家女堕落的故事。冷红冷紫两姐妹正是对妇女道德或曰贞操的坚守怀着强烈的愿望,才会有失去贞操后无能无力、自轻自贱沦的行为。
王梓夫《花落水流红》讲述了另类贞操的故事。在桃花冲这个贫穷的地方,高中生叶子纯洁美丽,家境殷实,又收获同乡杨小峰的爱情,两人即将结为夫妻;与叶子不同的是“小簸箕”,她在广州打工做了按摩女之后,接连将家财寄往家里,使原本贫穷的家庭立时成为村里的富贵人家,爸妈也在全村人面前直起了腰。从叶子身上,我们看出了她严守贞操,恋爱不乱性,这体现了她的自尊自爱,她的自尊自爱在即将转换身份之前,有过两次心理转换:第一次,她想寻找一个差不多的的男人为自己破身,可见于她而言,与不同的男人性交,是一个不谈处女、贞操的角色;第二次,她知道“破瓜”的费用,竟又听从表姐建议悉心盘算如何为自己的处女身/贞操买一个好价钱,处女、贞操真真在一个少女身上被想象成既无力又强大的怪物:无力体现在它对女性的控制权终究让位于强大的市场逻辑,强大则又昭示着它对妇女身体的规训与对男权社会的吸引力终究让贞操成为胁迫女性堕落的“催产婆”,这种堕落甚至表现为愉快地卖身。
失贞与堕落的促进关系在艾伟《小卖部》中被想象成另一个版本。小蓝谎称“读高中时,同她的生物老师好了......他几乎强暴了她......她还因此怀了孕......”道出自己无奈做发廊女的原因(然而她其实不是因为失贞后的悲惨遭际不得已堕落,“是她喜欢生物老师,勾引了生物老师。”)小蓝的良家女友苏敏娜听到了小蓝悲惨的遭遇对小蓝感到愤慨同时,又增加了一份理解和原谅,增强了前者对后者的救赎信心,这里,再明显不过地展示了贞操有无对发廊妹的促进作用,她们凭借该谎言掩盖自己为了欲望堕落的不齿动机,并且可以获得他人的谅解,可见贞操是多么容易就攫取了它对良家妇女的控制权,也多么容易为堕落女使用成为掩饰她们堕落的挡箭牌。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失贞女是如何堕落的叙述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贞操或曰处女身的丢失对这一身份的促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有逼迫的因素,但是贞操文化依然强势地成为女性堕落的一个助推剂,那些在城乡权力结构下苦苦挣扎的妇女在现实苦难面前不断向“钱”挺进的旅程中,她们原有的社会伦理、道德约束、价值诉求依然是她们在现实面前保持一副良家女的姿态,拒绝向灰色女性身份低头,在她们周围确实也环伺着各种性诱惑、性陷阱、性骚扰、性暴力、性剥削......她们一不留神就沦为他人捕猎的对象.....可是这些问题在贞操失去的女性眼中都“无足挂齿”,她们可以抗住生活的重压固守女性应该具备的贞操,这是贞操文化对他们的性期待、角色期待,她也一直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然而,悲惨的生活夺不去贞操之后,却要在失贞后给自己安上倚门卖笑的身份,还要盗用被害失贞人的身份,大摇大摆地享受他人的同情,省掉对自身的道德约束、自我反省,可见贞操对女性的控制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相反它成为堕落女与良家女身份转换的关捩,女儿们依然以保持贞操为中心,依然守着传统贞操过活,显示了传统贞操强大的生存力,但是就是这个强大的力量非但不能维护女儿家贞操反而促成女儿家堕落彰显了贞操文化在商业化时代的二元悖论。
二、从良与堕落
城市化的发展使农村人无限向往城市,于是他们纷纷逃离乡村,或为乡下的家人提供生活补给,或为了一种不同于乡村的别样生活等。乡下人进城往往与两性话题密切相关,作为乡下男人,进城之后往往与性饥渴、性压抑有关,女性则时常面临性诱惑、性骚扰、性陷阱等问题。男人们需要释放性能力、女人们又时常是性能量的释放地,但是仅仅从现实的两性天平出发尚不至于造就大批乡下“小姐”,然而,随着商业化大潮的袭来,“世俗的与物质的诉求成为社会大众的主导诉求”[1]。这一社会现状一方面带来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现实不能满足的问题,对这些缺乏生活技能,赚取生存资料有限的女性而言,市场提供她们的生存空间就变得狭窄起来,这时“她选择卖她的性服务或生育服务时,极有可能的是,她的选择更多的处于迫不得已,而不是自由选择,毕竟一个人除了自己的身体别无值钱的东西可卖”[2],作为“无可避免的成为商业化的对象”“商品社会不仅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而且是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必然再次以女人作为其必要的代价和牺牲”[3]。她们是乡村向城市缴纳的通往现代性的门票,这必然意味着,她们只能是以牺牲者的身份在现代性的进城中被城市“进入”,而她们“进入”城市的结果只能是为乡村/城市所见弃,成为一个“中间物”。
一直以来,“一个女性变成娼妓的过程往往叫做‘沦落风尘’‘跳进火坑’,走出色情业的过程则叫做‘从良’‘回头是岸’”[4],向世人传达出对从良的期待、宽容与接纳,然而商业化时代,于这部分女儿们而言:她们在衣食无着、子妹上学、父母患病等生存压力下选择进入色情业救家庭于水火,这样的悲壮与牺牲在她们看来是为人女、为人姊、为人妻、为人母理所当然的,甚至被自身视为高尚悲壮的,然而,一旦她们曾经的身份被曝光,迎接她们的只有回到贞操文化之下承受来自贞操、道德、伦理等的弹压,走向死亡或者远离家乡成为她们的归宿。这种对日常女性贞操的看重,残酷地剥夺女性的从良权力,更显出了贞操文化的残酷性、血腥性、迫害性......以及其在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的“顽固性”,昭示了打破传统贞操文化的必要性、艰难性、长期性......作家对从良女因妓女印记被社会伦理排斥的悲惨故事给予关注与同情,展现出作者对传统贞操文化的批判,呼吁着传统贞操文化的现代性转变。
何顿《蒙娜丽莎的微笑》金小平已经从良嫁人,从前的嫖客丁副镇长还是将她的身份戳破,随后,金小平的丈夫与她离婚,金小平也在愤怒与骚扰中砍杀了丁副镇长。孙慧芬《歇马庄的两个女人》李平的经历被抖落出来后,李平也不得不被丈夫请出婚姻关系。刘继明《送你一束红花草》樱桃为了贫困的家庭在外多年,终于用自己柔弱的身躯为家庭盖上了高楼,可是当染上性病回到家乡时,她的家人拒绝接纳她,村中人看她也不复往日赞美之词,留给樱桃的只有谩骂与指点,最后她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季栋梁《燃烧的红裙子》红喜在家庭围困之时做了“那种事”,后来在被警察遣送回家之后,曾经为家庭作出牺牲的红喜并没能获得家人的谅解,直至投河死去。不可否认的是,在商业化大潮的背景下,乡村社会亦生成“金钱至上”“笑贫不笑娼”等新的社会价值观念,但这种观念在实际的生活中,仍然只是向“金钱”看齐,对她们的认可也只是以她们的性别资本化为前提,赚钱能力成为她们被表面认可的依据,一旦脱出赚钱的范围,回归到正常的日常生活、伦理体系、价值观念当中,妓女曾经的身份印记并不会被磨蚀,相反,这个永不消失的印痕会成为妓女的又一重压迫,永远地失去获救的可能,这无不昭示着贞操对从良的制约作用。
三、背离贞操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指出:“有许多少女被随随便便一个夺走贞操后,便认为给献给任何人是自然的事。”[5]对她们而言,只要失去贞操便没了价值,或者说既然贞操失去了那么堕落于她们而言便无涉道德约束,何况又是被骗取的贞操,心中先认定自己受害者身份很快就会悬置了道德、伦理、性羞耻在行为选择、价值判断、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约束作用,加之能够通过身体换取钱财比之同等可以提供给自己谋生的生存方式简单轻松,于是,初次失贞非但没能引起女性不洁感、羞耻感,反而造就了一批边缘女性。
与此不同的是,有些虽然生活在底层,但是她们并不是因为失去贞操而沦落风尘,相反她们似乎一开始就看到了身体的价值,努力挖掘女性的身体资本,让身体资本化助益其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用‘身体’——其生育力、对身体的操纵、身体的内在性和身体的性愉悦取代‘劳动’或‘政治’而作为建造现代主体的场所”,尽管“构成了新形式的性别的不平等,虽然也是(更确切地说正是)这种差别激发了年轻妇女的兴奋”。[6]
《乡下姑娘李美凤》王手讲述了一个初来乍到在金钱与良家女之间简单直率得选择前者的故事。在她看来“钱对于乡下人来说是很大的,她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乡下人的身体算什么呢?反正迟早要被人睡的,在家里被一个没出息的人睡,还不如用身体换个靠山”,于是她轻松地同意了老板用钱买她的身体的建议,并且认定这样自己在鞋厂就有了靠山。李美凤用身体自然满足了她短浅的初衷,最终在鞋厂困难之时,老板抛出她来,她又用性替鞋厂要回欠款,最后,老板明示暗示李美凤陪自闭症的儿子睡觉。邵丽《明慧的圣诞》按摩女桃子的回乡带给没有考上大学的明慧极大地震撼,她不能不去羡慕这个曾经仰视自己的发小,于是18 岁的她和桃子一同来到省城,做了按摩女。
如果说,明慧们一开始就表现出身体羞感、贞操观念的丢弃,那么,对有些女性而言,她们对自身身份的骄傲、自得则意味着贞操观的彻底丧失,因而她们行为的干涉必然招致失败。《小卖部》小蓝在良家女面前总是把头抬得很高,“就好像她们做婊子是件伟大光荣的事。”她炫耀自己各式各样的人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且自认具有良家妇女所不具备的性资源,因而在良家女面前骄傲自得些,这均来自其对男性的魔力。“她们纵情的游戏:冒险性、刺激性、最重要的一点具有支配权。对一些工作者来说,看到对方眼中流露的渴望,感知到对方对自己的依赖和专注(不管这是多么短暂,转瞬即逝),使他投入金钱,自己也从给与和支配中得到片刻欢愉,此时此刻,自赏之感油然而生。”《发廊》细致描摹了发廊女方圆的心理地形,她的家庭虽然算不上富裕,但她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金钱去做发廊女。实际上,她做发廊女只是因为她看到了发廊女身上“一种她向往的生活”。作者虽未指出这种生活是什么,但显然是不同于她家乡西地的另一种生活,就连方圆做教师的哥哥都认为方圆的做派“纯属个人行为,跟道德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对卖肉谋生总是被动的、受到他人挟制的观点产生动摇,消解了有关“被侮辱者被损害者”“淫女荡妇”的固有想象,引向其他因素——即女性的身体权力,如李美凤、明慧、方圆、小蓝这样的单纯地为了背离一种社会伦理,走向疏离大众新式妓女。以上女性,她们堕落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将从她们自身寻找,物欲的追逐和性欲的看重遮蔽了传统的宗法伦理,道德约束,使自身在物欲与性欲的追逐中日渐迷失了作为人的尊严,沦为纯粹的“多阳具者”,但却未必产生20世纪90代以林白、陈染、王安忆三恋等为代表的书写女性“因欲望而获救,欲望成为女性获救的涉渡之舟”[7]的效果,她们日渐在“男性为性事支付”“和接受金钱”的便利中“丧失尊严”[8]。
在她们身上,传统贞操观念的影像消失不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冲破了男权社会的藩篱,相反正是她们出走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置藩篱的行为又造成了她们彻底沦为男权社会玩物的本质,不得不说,这是她们的悲哀。由此可见,被建构的贞操观念“不一定是被动的,消极的”[1],女性在商业化时代如何看待贞操仍然是一个缠绕多重的现代问题,因而,这些道德越位的女性自以为时尚的前卫观念非但未能实现其对身体的解放权,反而在其与传统贞操文化的斗争中失去了对身体的所有权。与此同时,作者的态度也发生了改观,无可否认作者是冷静地、平等地讲述故事,突破了有关固有的模式,并提供了大量的题材,然而作家悬置道德、弃置文学批判性的同时也让“此时艺术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升华、救赎功能,而外化为幸福和快乐的符号”[9],又造成贞操书写在当下贞操观念下的无力。
结语
行文至此,有一个再明晰不过的问题变得相当突出,那就是女性对贞操文化的融入(赞同)、背离(抛弃)最终均指向一个现代性问题,或曰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对贞操(性的开放度)的态度问题,以及此态度所关联的道德/伦理问题。
在第一种贞操书写中,女性一开始是主动融入贞操文化当中的,且表现出对贞操文化的强烈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显示出贞操对女性集体无意识的压制,这在她们不愿意背离贞操,死守贞操/道德/伦理的过程中均有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对贞操文化的认同,女性的堕落史才因为贞操的管制相对延迟了些。然而一旦她们失去贞操,那么女性的堕落卖肉史就彻底突破了传统的伦理要求向着堕落俯首称臣,体现了她们对贞操文化既融入更倾向于背离的意味。在这一个环节中,贞操又沦为她们的天然同盟,是失去贞操“逼”得女儿家以身体作为生存的资本操起皮肉生涯,如此一来贞操对女性的统治非但没有松懈,且这批女性自始至终都受到贞操的辖制,因而,对女性体内贞操文化的清理将变得刻不容缓。第二种叙事,则讲述了对大众贞操文化清理的必要性,作为从良幻灭的悲剧女性,她们承受了社会、男权文化的性政治,“一朝沦落,终身蒙尘”,她们大多怀着“百善孝为先”的心理动机,以崇高的人格背离了社会对女性的贞操期待,履行她们为人的“义务”,但强大的贞操文化压抑着集体大众,当她们完成任务,回到日常生活中,贞操文化的鬼影又以“万恶淫为首”拒绝了拒绝背离者的再次融入,显示出传统贞操文化的“吃人”的本质。以上两种叙事模式分别从边缘女性的贞操观、他人的贞操观两个不同方面入手,探讨贞操文化对现代性的阻滞性。至于第三种叙事,作者以平等的语调写出女性对传统贞操文化的主动背离,体现了女性拿回身体管理权的主观能动性。然而,那个叛离贞操束缚的女性应该成为个体的、具有个人能动性的“精神自我”,而不是以牺牲“精神自我”,“羞耻感”为代价,沦为“交换物质的生存条件”女性[10]。这种叙事模式,虽然作者的批判性相应地变得不那么突出,我们亦能从中读出,在现代性进程中全然丢弃贞操文化亦非正确之举,显示出作者对现代性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