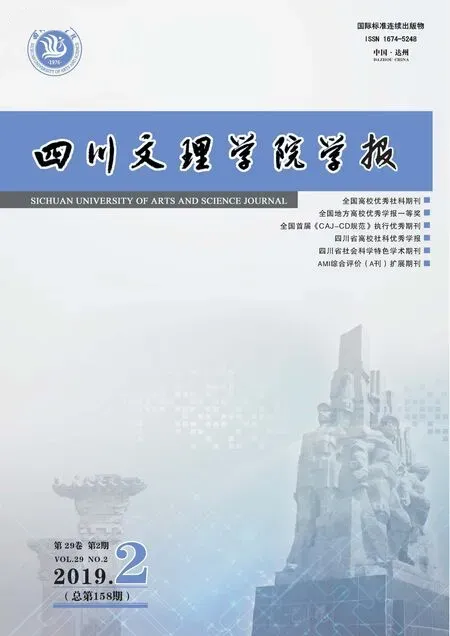《驴得水》:陌生化、隐喻与象征的符码世界
2019-02-21詹晓雨
詹晓雨
(四川传媒学院 数字媒体与创意设计学院,四川 成都611745)
青年导演周深、刘露导演的电影《驴得水》以1942年的中国农村教育生态为背景,讲述了以孙校长为首的一群农村教师因为一次虚假上报引发的一连串故事.本来自得其乐的一群农村教育知识分子,因为上级特派员的突然检查,而逐渐暴露出知识分子的性格缺陷.为了维护孙校长的“农村教育实验”梦,一群人撒了一个又一个谎,一句“做大事不拘小节”让他们的欲望、矛盾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最终酿成了张一曼自杀、众人受处分的悲剧.
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本片还有一个亮点——象征符号的建构.象征无处不在,任何事物除了自身具有的物理属性外,在表意层面都能发挥重大作用.形式主义试图探究艺术作品如何运用特殊的结构形式,为欣赏者延长艺术审美过程.陌生化理论强调文学的内部规律,它打破了象征主义一直致力于探讨文学的外部关系,从结构层面分析作品如何艰深化,从而延长欣赏者从物理属性到象征意义间的感知过程.电影《驴得水》中通过一系列象征符号的建构,形成自己的一条象征符号链,串起了人物之间关系,并对人物本质性格进行隐形喻指.在建构手法上,影片采用了异化能指、嵌入叙事、象征意义陌生化等方式,聚焦观众注意力,同时增强影片艺术性.
1 被陌生化的能指
维克多·什克罗夫斯基关于陌生化手法的探讨主要是能指层面的陌生化,他认为“奇异化”的形式体现更有利于帮助人们摆脱对事物的自动化认知,[2]而更加注重感知的过程,从而延长了感知过程,即审美过程.尽管什克罗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是针对文学的艺术性做的探讨,但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电影艺术,其艺术性是处于同一艺术层面的.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如果仅仅只是运用新的技术对现实进行简单的重现,无法称之为艺术.[2]电影艺术性的体现同样需要将人们对事物的感知唤醒,从与习惯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使人们“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使石头成之为石头”.
电影的能指除了指涉电影影像的物质存在本身还包含关于事物在人脑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特征的想象的存在,《驴得水》中构建的驴、貂皮大衣、头发、彩球等意象,虽在影片中的镜头不多,但在观众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想象的存在,这种想象的存在指向的是拉康“三界说”中的想象界.能指的概念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他认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能指是语言的声音形象.随着理论的变迁,能指一词被运用到电影符号学当中,并由此获得了在电影符号学中的新的意义.克里斯汀·麦茨的《想象的能指》一书中认为,电影的能指是为了让所摄之物成为隐喻或象征而存在的,而剧本要表达的意义与影像的符码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所指.
在《驴得水》中,驴、貂皮大衣、头发、彩球等意象形成组合关系构成一条异化能指链.影片中出现的第一个驴的镜头,是驴脖子上挂的写着“得水”的姓名牌的特写镜头.驴不会说话,电影中也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采取动物的叙述视角来进行异化,但影片中所有关于这头驴的镜头、台词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拟人化的“驴得水”的形象.孙佳在谈及驴的台词中多次进行了这种拟人化的处理.“驴棚没了得水住哪?”“得水不会说话了”“我给驴得水吃了响声散,现在驴得水能说话啦!”等将驴作为拟人化的形象进行的台词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影片中关于貂皮大衣、头发、彩球等形象也设计了专门的情景,采用一种轻松戏谑的方式进行符号建构.
与文学语言相比,电影语言在能指层面具有先天的陌生化优势.在《作为形式的艺术》一文中,什克罗夫斯基肯定了诗作为一种形象思维方式的存在,在阅读诗歌时,我们能产生“过程的相对轻松感”.[3]由于影像具有动态直观性,这种“相对轻松感”在电影欣赏的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影像符号与自然事物一样具有真实可观性,人们的观影过程与日常认知过程具有无比的相似性.这种形象感知对节约创造力这样的规律同样适用,但电影语言相对于自然事物的关系,与诗歌语言与一般语言的关系类似,电影语言具有某种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的东西.并非所有自然事物都能成为电影符号,并非所有电影符号都在自然中得以体现.电影语言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
首先,电影的编码过程同时也是影像语言的选择与组合过程.人的注意力有限,信息量并不能保证信息的接受率,相反地,冗余信息对信息的接受度可能起反作用.[4]一部电影的时长有限,能在有限的时长提供最多的信息并进行最丰富的表意行为,必须对影像语言进行选择并按一定的规则进行排列组合.对于影像语言的选择,爱泼斯坦将其称为“上镜头性”.
其次,作为蒙太奇理论支撑的格式塔心理学表明,人们可以根据给出的部分信息将剩余信息补充完整.[5]就叙事层面而言,为影片选取尽可能少的尽头完成尽可能多的叙事任务提供可能;从象征表意角度而言,象征符号的建构形式决定了形象背后更为深刻的表意目的和隐喻效果.叙事与隐喻是影片成为作品的关键因素,二者在影像符号的建构过程中相互交叉、相互促进.前者运用一般影像符号,对影片叙事人物、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形成总体性架构,叙事语言就像诗歌中的一般语言,是作为实际思维的手段.后者则需要构建独特的象征符号系统,通过转喻、隐喻等手法是影像符号陌生化,表达画面内容以外的意义.这种叙事语言与象征语言的划分有助于我们理解符号在影片中承担的不同任务,但从根本上说,不存在完全的叙事,也不存在完全的隐喻,即使是被认为最具有隐喻意味的诗的电影也依然或多或少包含叙事的成分,而在主流电影中,也不存在纯叙事的电影,符号的叙事与表意相辅相成,互为皈依.不管是叙事和表意,我们对符号的读解都服从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过程,至于自动补充的完整度则更多地取决于解码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在想象的能指的作用下,我们对于相同符号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再者,影像表现事物的特征更加的固定,这使得内容信息更加突出化.语言中关于事物的概念一旦转变为影像,概念的事物便转化为影像的事物,所指向的便不再是某个抽象概念而是具有有限的、固定的特征的具体事物形象.因此,电影进行的是比文学、诗歌更为具体的形象思维.
电影自身具备的一系列独特规律使得电影的影像符号获得了的天生的陌生化优势.陌生化又被称为奇异化,形式主义强调运用艺术性要从艺术自身的形式构成中进行探索,电影的艺术性便要从特殊的影像象征符号的建构中进行探索.作为一部优秀的影片,电影《驴得水》中尖锐的讽刺让人印象深刻,好的电影能将所要表达的意图藏于画面中,《驴得水》中建构了诸多具有隐喻色彩的符号,将创作者的话语很好地隐藏在影像背后.这些特殊的象征符号,同时也是影片艺术性的来源,诸多陌生化的处理使得观众的目光不知不觉投入到这些形象上,从而延长了影片的审美过程,达到了艺术性的效果.
2 嵌入叙事的象征
象征符号参与叙事的过程中,本身便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这种深深嵌入叙事中的整体感就是陌生化的自觉性.什克罗夫斯基提出“本事”和“情节”的概念,作为素材的一系列“本事”变成小说“情节”时,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变形,具有陌生的新面貌,作家越自觉地运用这种手法,作品的艺术性就越高.这种将现实加以陌生化的手法用于对象征符号的建构上更有利于符号及隐喻的突出.克里斯汀·麦茨也认为:“电影语言,首先是对一个情节的具体表述,而艺术效果即使在实体上与影片为我们交代故事时的语义行为不可分离,它仍然是另一个表意层次.”
在电影《驴得水》中,驴、貂皮大衣、头发、彩球等象征符号在叙事中承担起了重要作用,既作为故事的发展动力,同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
2.1 作为故事发展动力
故事由一头驴的赡养费开始,既缺钱又缺水的农村小学,不得不养驴给大家拉水喝.养驴的钱从哪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孙校长将驴上报为一名英语老师“吕得水”,并将“吕得水”老师的工资用来养驴.拿上面拨下来的钱养驴,学校老师们也是迫不得已,如果计划能一直正常进行下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上级特派员的视察却破坏了这个计划,为了不受惩罚,并继续拿到养驴的费用,大家决定让“铜匠”来冒充“吕得水”老师.
从此,驴的“真实身份”便成为大家拼命隐藏的对象,而孙佳一句无意的“驴得水能说话啦!”差点捅破了大家苦苦维持的谎言.就在所有人都在用一个谎来圆另一个谎时,本来为养驴而撒的谎最后却要杀驴来圆.
2.2 人物形象塑造与转变
《驴得水》中的象征符号建构不是独立于人物的,而是与人物个性、命运息息相关的.驴与铜匠形象的重合、貂皮大衣与裴魁山本性的暴露、头发与张一曼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彩球与孙佳周铁男纯真的性格.铜匠还是朴实的铜匠时,驴还是勤勤恳恳拉水的驴,铜匠被禁言时,驴也失声.铜匠被人说是“牲口”,他在接受教育之前确实如驴一样蒙昧,但同时也像驴一样朴实.铜匠彻底变成“吕得水”之后,驴被杀了,驴的消失同时带走了铜匠的质朴,是铜匠性格转变的另一种呈现.作为道具的貂皮大衣,就像一件兽性的外衣,将裴魁山本质中的残酷兽性彻底展现出来.失去了头发的张一曼,从那个想要过得自在点的女子变成了那个“什么都别听,什么都别管”的疯子.周铁男从那个送孙佳彩球的正直青年变成唯唯诺诺的跟班.
3 象征意义的陌生化
3.1 驴的拟人化
作为牲口的驴拥有孙佳给它取的名字——得水.对影片人物而言,驴是学校养得家畜,双方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学校喂养“得水”,驴“得水”给老师们拉水.然而这一正常的饲养关系在影片中却与正常情况不同,饲养驴的钱同样是以驴的名义获得的,学校老师们与驴“得水”之间的饲养关系存在异化现象,这也是影片矛盾的源头.
拿上面拨下来的钱养驴,学校老师们也是迫不得已,如果计划能一直正常进行下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上级特派员的视察却破坏了这个计划,为了不受惩罚,大家决定让“铜匠”来冒充“吕得水”老师.而就在大家一门心思训练铜匠的时候,驴突然不“说话”了.驴本不会说话,影片中强调驴的“失声”既是作为影片的笑料存在,也是将驴的形象进一步地拟人化.正常情况下,驴叫还是不叫本是生物自然的生理现象,而影片中的驴“得水”在被铜匠冒充之后,是作为一个被隐藏的对象,此时驴“得水”突然失声并非自然的生理现象,而是象征着驴“得水”被剥夺的身份和话语权力,以及自身被主宰的命运.随后,冒充“吕得水”老师的铜匠也被校长禁止说话.“驴得水”和“吕得水”的双重失声更进一步地将驴的话语权与人的话语权相连接,此时,驴和人都是被代表的对象.
而后,孙佳给“驴得水”吃了人用的响声散,驴能“说话”了,“吕得水”也能说话了.铜匠扮演的“吕得水”向特派员展现了惊人的“才能”,并获得了资助资格.铜匠以“吕得水”的名义给学校带来了利益,“驴得水”和“吕得水”都获得了说话的权利.然而,风波之后,铜匠依然是铜匠,却不再是原来的铜匠,驴得水依然是原来的驴得水.受过教育的铜匠丢失了淳朴的品质,想要彻底变成“吕得水”老师,他开始追逐利益并对张一曼疯狂报复,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为学校拉水的“驴得水”,在学校摆脱资金困境后,走向了毁灭的命运.
影片中通过铜匠媳妇之口说出:“你们才是牲口.”在《驴得水》中,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将利益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相反地,“驴得水”这样一只牲口,为大家带来了利益,为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最后还要被宰杀.这种泯灭人性的残忍就算以教育为目的也并不能合理化.
在《驴得水》这部影片中,“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形象,同时也是一个“拟人化”的形象,这种拟人化既表现在它在影片中被上报成一名老师,也体现在驴的命运与人物命运的高度重合上.“驴得水”经历了被赡养——被作为利益工具——被隐藏——被杀害的生命历程.观之女主角张一曼,同样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张一曼受恩于孙校长,她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为了学校的利益,她愿意用身体去“睡服”铜匠.尽管这种做法可能更多出于对自己欲望的满足,但也不能否认她被当做利益工具这一事实.不管是“驴得水”还是张一曼,当自身的存在与更大的利益相冲突时,他们便被隐藏甚至被毁灭.
什克罗夫斯基认为:“形象的目的不是使其意义易于被我们理解,而是制造一种对事物的特殊感受,即产生‘视觉’,而非‘认知’.”将这种结论用于电影批评中,很容易产生对“视觉”的误解.这里的“视觉”化并不是指将所有的形象都用镜头呈现,而是与诗歌的“视觉”类似,是指用能够形成想象的视觉形象,这种想象的视觉形象促使人们对于形象的进一步感知,察觉到与大家习以为常的形象的异样,形成想象的能指.
3.2 貂皮大衣:欲望化的符码
貂皮大衣作为象征符号进行陌生化建构的技巧之一是采取差异化手法.影片中以孙校长为首的四人为了理想中的农村教育实验才留在偏僻的农村,而就在大家都穿着清凉又朴素的夏天,裴魁山突然穿着华丽的貂皮大衣登场,成为其他三人嘲弄的对象,同时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貂皮大衣之上.影片前半段,四人为了教育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生活艰难到连喝水都困难,却没有人抱怨,依然固守贫苦.貂皮大衣的出现与以往的形象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此外,貂皮大衣的每次出现都伴随着人物的性格转变.与貂皮大衣直接关联的两个人分别是:裴魁山和铜匠.貂皮大衣首次出现在裴魁山性格转变之时,穿上貂皮大衣之后的裴魁山彻底撕去了之前伪善的面具,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而为了成就自己的利益,他的貂皮大衣被铜匠抢了过去.受教育之后的铜匠,也意识到这世界上的金钱权利如此诱人,那个朴实的铜匠已然死去,只剩下一个觊觎貂皮大衣并贪婪、残忍的“吕得水”老师.
貂皮大衣由兽皮做成,象征着财富、权利,同时也象征着残忍的兽性.影片中建构的貂皮大衣这一象征符号,它与剧中人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貂皮大衣不再只是作为装扮的衣物,而是作为一种被追逐的欲望化的形象.
《驴得水》中,差异化手法使得貂皮大衣成为一个醒目的形象,不仅剧中人物向它投向了或鄙夷或觊觎的眼神,坐在屏幕前的观众也形成感知的延续,对貂皮大衣所代表的野兽化、欲望化的含义进行思索.
3.3 头发:作为情感寄托符号
影片中出现了四次,每一次头发的出现都作为不同的象征符号,代表不同的含义.
第一次为驴棚着火,孙佳的头发被烧了一些,于是张一曼给她剪成了短发.孙佳是个纯真烂漫的姑娘,她努力地保护“驴得水”,却一次次地受到打击,驴棚被烧只是一个开始.她没有办法掌握驴的命运,更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二次是张一曼送给铜匠的头发,这一缕头发是张一曼的情丝.不得不说,张一曼是一个滥情的人,她的感情就像自己的发丝一样自由洒脱.铜匠回家之前想要确定与张一曼的关系,但想活得自在点的张一曼不能和铜匠确定任何关系,只能留下发丝给铜匠做个念想.这二人的感情也正是以张一曼剪下来的这一缕头发作为载体,一直存放在铜匠那里.
第三次出现是张一曼与铜匠感情破裂以后,铜匠丢弃了张一曼送的“情丝”.特写镜头中,张一曼呆呆地看着铜匠,她并不想出卖铜匠也不想如此狠心,但利益面前,根本由不得她选择.那缕头发慢慢从铜匠手中滑落,随之滑落的是铜匠最淳朴的心思.此后,铜匠彻底转变为一个冷酷残忍的利益追求者.
第四次是张一曼头发被剪,作为女人魅力象征的头发被一群男人残忍剪去,而这群男人曾经是张一曼身边最熟悉的人.张一曼失去的不只是自己一头秀发,更是失去了决定自己感情的能力.她最渴望的自由也已经成为不能实现的梦想.
头发作为意象四次出现,既是重复也是深化.四次重复,以及特写镜头的突出展现,将观众的目光聚焦到头发这一符号上.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刻意去感受头发的意义.正如什克罗夫斯基所说:“事物被感受若干次之后开始通过认知来感受:事物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这一点,但看不见它.”而通过在影片中的重复,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感知头发的存在.就如张一曼头发被剪得不堪入目时,我们会感到惋惜一样,头发这一意象开始引发我们一系列的情绪.头发对于女孩来说,是单纯、美丽的象征,而对于女人,头发还是情感的寄托.从孙佳到张一曼,头发展现了女孩到女人的情感变化.同样是剪发,第一次张一曼给孙佳剪发的画面是美好的、恬静的,而后来张一曼头发被剪时,画面却是残忍的、疯狂的.
3.4 彩球:作为理想追求的象征符号
彩球前几次出现都是作为周铁男与孙佳逗乐的道具,彩球鲜艳的色彩与少男少女之间的嬉笑打闹构成了衣服清新和谐的画面.耿直的周铁男与纯真的孙佳,青年男女之间简单情感不断滋生.
彩球与其他象征符号相比更具动态性,其质地具有弹性,充满生命力,就如同周铁男和孙佳,既年轻躁动又充满活力.而在电影最后一幕,彩球被磕绊了一下便散落在山坡.电影采用了慢镜头来展现彩球散落的画面,将彩球飞快的运动冻结,散落的彩球最终连这缓慢的跳动也会逐渐弱化,在这一刻,我们才恍然意识到,这动荡的彩球不只是感情的无处安放,更是理想追求的散落.孙校长、裴魁山、周铁男、张一曼四人的教育理想,张一曼的自由梦想都像散落一地的彩球回不到以前.
结 语
影片中通过对自然事物的陌生化编码而建构了一个个具有隐喻意味的象征符号.用陌生化理论对电影进行分析,对于电影艺术语言的发展有很好的指导作用,通过陌生化技巧产生的间离效果能帮助电影语言不至于落入对现实亦步亦趋的俗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