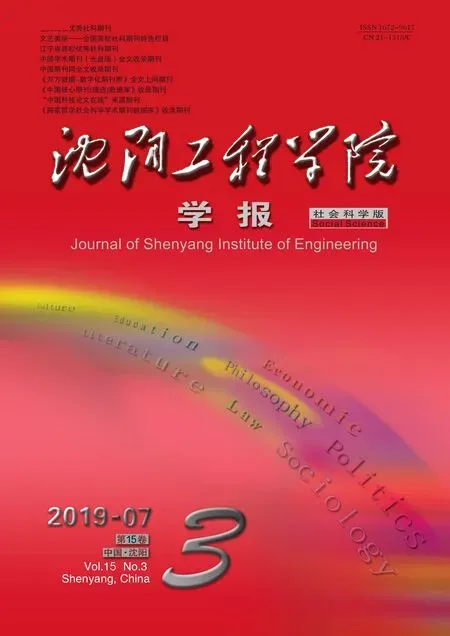文化维度理论视阈下的《最后的武士》解析
2019-02-21刘恒
刘 恒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最后的武士》是一部由爱德华·兹威克执导,汤姆·克鲁斯和渡边谦等主演的好莱坞巨作。在影片中,故事发生在19 世纪70年代的日本。明治天皇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他兴修铁路,效仿德意志的政治体制,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迫切希望将落后弱小的日本变成现代化的世界军事文明强国。然而,过快的现代化进程遭到了以胜元为首的传统武士阶层的强烈反抗。为了平息国内风起云涌的叛乱,内政大臣大村远赴美国,高薪聘请曾经的战斗英雄阿尔格兰来为日本政府训练第一支新式军队。但是,在新军训练尚不充足的情况之下,大村就下令让阿尔格兰率领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军进行与骁勇善战的武士集团的交锋对决。在这场冷兵器对抗热兵器的战役中,新军不堪一击,落荒而逃,阿尔格兰不幸被俘。作为一个俘虏,阿尔格兰丝毫没有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对待,反而得到了胜元与其妹妹多丽子的悉心照顾。在与武士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阿尔格兰不仅学会了剑道,还领会了武士精神。后来,在胜元处于危难之际,阿尔格兰联合其他武士冒死将他解救了出来。由此,他们再一次开始了与如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军的对抗。最后,武士集团中只有阿尔格兰幸存下来。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是荷兰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文化维度理论是霍夫斯泰德提出的一个用来衡量不同国家间文化差异的理论。他在《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中将文化差异总结为六个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以及放纵与克制。文化维度理论在跨文化交际领域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揭示了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而且为处理文化冲突提供了有效的准则。本文着重于解读电影中19 世纪后期的日本与美国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及放纵与克制三个维度中所展现的文化差异。
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霍夫斯泰德认为集体主义是指:“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到强大紧密的群体当中,这个群体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以换取人们对于该集体的绝对忠诚。”[1]81此外,他将个人主义定义为:“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的社会:人们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1]80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概念实际上反映的是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个体对集体所持的不同态度。尊崇集体主义的社会要求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集体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体必须为了集体舍弃个人利益来保全集体利益。个体需要履行对所属集体的道德义务,并且保持对该集体忠贞不渝的情感。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个体的集体意识比较淡薄,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身的利益,以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产生冲突时,个体往往会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虽然在19 世纪50年代发生的“黑船事件”后,日本被迫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但是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日本仍然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然而,与同时期的日本不同,位于北美大陆的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是一片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热土,更是一个高歌个人主义的国度。
武士道是当时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它对日本民族性的影响颇深:一个真正的武士必须恪守“名、忠、勇、义、礼、诚、克、仁”[2]15-16。严格遵守这一套道德规范正是作为个体的武士服从于社会集体的体现。受集体意识的驱动,武士会誓死捍卫自己所属集团的利益,英勇战斗,不惧生死。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切腹将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当自己效忠的君主死亡、国家灭亡或作战失败,武士都会选择切腹了结自己的生命。在与胜元领导的武士集团的交战中,新军士兵大败而逃。然而,作为全军统帅的长谷川将军没有逃跑,而是选择切腹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武士无法忍受失败的耻辱。同样是吃了败仗的阿尔格兰却没有选择自杀还当了俘虏,这让胜元的属下氏尾十分费解。为此,氏尾向胜元质问道,“主公,您为何饶他一命?他蒙受战败的耻辱,应该切腹自尽。”“那不是他们的习俗”,胜元淡淡地说。
美国信奉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认为自由、平等和人权是个体的政治诉求[3]23-41。个体进入社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个人利益的满足则是社会终极价值的体现。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其对个人利益的高度颂扬上可见一斑。出于对生命与死亡的敬畏,美国人在战场上遭受失败后,不会选择自杀来洗刷耻辱,而是大方投降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胜利的一方同样也会尊重失败者保留生命的权利。因此,阿尔格兰没有像长谷川将军一样在战败后选择自杀,他也无法理解胜元担当“介错人”斩下长谷川的头颅的做法。
阿尔格兰:我看到了你是怎样对待敌人的。
胜元:难道你们国家的战士不杀人吗?
阿尔格兰:他们不会砍下投降了的败将的人头。
胜元:长谷川将军请求我了结他的生命。武士无法忍受失败的耻辱。我很荣幸能砍断他的人头。
在与新军的最后一场对决中,武士集团不惧枪林弹雨,仗剑骑马勇往直前。浴血搏杀后,他们中只剩下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胜元与阿尔格兰。胜元恳请阿尔格兰结束他的生命,让他光荣地死去。阿尔格兰答应了胜元的请求,让胜元光荣安详地死在了战场之上。为武士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折服,新军士兵全体下跪表示恭敬。最后,阿尔格兰成了武士集团唯一的幸存者。
另一方面,影片中的人物对国家与家的情感也直接反映了日本与美国的文化差异。作为明治天皇的老师和大臣,胜元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发起的反抗并不是反对天皇的统治,反而是为了天皇,为了国家,为了整个大和民族。在他看来,明治政府在一味西化的现代化改革过程中,抛弃了传统,忘却了历史,而这与天下苍生的利益背道而驰,让他甚是担忧。为了能让天皇听见自己悲天悯人的呼声,他破坏铁路,抵抗新军,大胆谏言。胜元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唤醒明治天皇,使其终止了与美国军火贸易合约的签署。在信忠的村庄,房屋鳞次栉比,乡间路上熙熙攘攘,处处呈现着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村民们共同耕耘,邻里间团结互助;武士们则在一起练习剑术、射击与格斗。生活在那儿的每个人都属于这个集体的一部分,也都在为村庄的繁荣与和谐辛勤劳作。而贝格利、阿尔格兰和甘特三人不远万里来到日本,纯粹是为了明治政府给与的丰厚的酬金。为了谋求生计,为了追求财富,家国情怀寡淡的他们四处漂泊,四海为家。在信忠的村庄时,阿尔格兰在日记中写道,“17 岁那年离家后,这里是我呆得最久的地方。”最终,远离故土的他们都没有再回到美国。贝格利和甘特均死于战场,葬身他乡,而阿尔格兰也选择留在日本。
二、高权力距离与低权力距离
霍夫斯泰德将权力距离定义为:“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利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1]49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中,盛行家长式的权威以及独行专断的权力关系。换句话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或情感距离,但是人们对掌权者有着很高程度的依赖。下属往往乐意接受自己低级别的职位,并且不会直接要求和反驳上司。专断的领导作风促使上司享有最高的权威,而下属却无法参与决策过程。在低权力距离文化中,情感距离相对较小,人们对权力的期待与对权力的接受更为趋近。大众与掌权者相互依赖,权力分配不均的情况也较少。这也意味着上司和下属不会格外在意身份地位,决策责任的分配也较为广泛。权力分散、扁平化的管理结构普遍存在于低权力距离文化中,而“门户开放”政策更是备受推崇:上司愿意倾听下属的意见,而下属也能挑战上司的权威。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国。因此,日本是高权力距离文化国家,美国是低权力距离文化国家。
日本在历史上是一个神权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天皇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子孙,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日本臣民的心中,天皇不是凡人,而是神。凡是对天皇不恭敬的言行都被视作“忤逆不道”,而质疑、挑衅和命令天皇更是会受到严酷的惩罚。在去皇宫觐见明治天皇的途中,资深翻译葛兰对阿尔格兰与贝格利强调地说,“两千年来,天皇从未召见过平民。这可是你们前世修来的天大的荣幸。当然了,会有许多繁文缛节。你可以看他,但是他若没对你说话,你就不能讲话。他起身时,你要鞠躬;他鞠躬时,你要把腰弯得更低。”无论是在皇室寝宫还是在内阁会议室,所有人都对明治天皇毕恭毕敬。即使是向天皇谏言,胜元也不敢做出丝毫无礼冒犯之举。明治天皇向胜元问道,“告诉我该怎么做,老师。”胜元连忙下跪言道,“您才是天皇,我不是。您必须为天下苍生寻得良策。”在明治天皇之下,长谷川、大村和胜元也拥有很高的权威。身为曾经的武士和如今的新军指挥官,长谷川将军“个头虽小却不怒自威”。作为内政大臣,大村实际上扮演着明治天皇的发言人的角色,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不仅掌控新军,内阁会议上也能一人侃侃而谈。他命令下属软禁胜元和刺杀阿尔格兰时,几乎无人敢违抗他的指令。胜元是武士集团的领导者和决策者,有着崇高的威望。武士们都是无条件地执行他的决定,并且心甘情愿跟随他出生入死。当阿尔格兰刺死了胜元的妹夫,周围的武士们一拥而上准备杀死他的时候,胜元大喝一声“住手”,他们就都退了回来。妹妹多丽子向其抱怨道,“哥哥,请让他离开吧。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胜元正言厉色地说,“你要照我说的话做!”另外,深谙日本文化的葛兰也巧妙地利用了日本文化的高权力距离特质。为了营救被软禁的胜元,阿尔格兰求助于葛兰。面对守门士兵的阻挡,葛兰装腔作势厉声呵斥道,“大村大臣命令我们为叛徒拍照……你这个狗胆包天的乡巴佬……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堂堂的美国总统。他来率领部队击溃叛军!快过去帮忙搬摄影器材!”葛兰威严的神情使得日本士兵们听了后乖乖地就去搬器材并且放了他们两人进去。
美国是一个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就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所以它没有日本与欧洲社会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是平等且自由的个体,社会中不存在绝对的权威。在这种文化坏境下,上下级关系透明但不明显。尽管阿尔格兰上尉是贝格利上校的下属,但是他敢于挑战贝格利的权威并违抗贝格利的命令。在谈话中,他毫不掩藏自己对贝格利的厌恶与憎恨,并且直言不讳地对贝格利说,“给我月薪五百,我什么人都杀。但是,我要你记住:我很乐意免费杀你。”贝格利命令阿尔格兰率领新军镇压胜元叛军时,阿尔格兰并没有惟命是从,而是坦言:“他们还没准备好。”为此,他让一个新军士兵开枪射击他,以新军拙劣的射击技术来证明他的观点。到了与武士们交战的时刻,贝格利命令阿尔格兰和他一起躲到后方,因为他们只需为明治政府训练士兵不负责作战指挥。但是,这遭到了阿尔格兰的断然拒绝。出于作为一个军人的职业操守以及对士兵的责任担当,他毅然决然开始指挥新军做好战斗准备。作为阿尔格兰的下属,甘特中士同样也违抗上司的命令。
阿尔格兰:甘特中士,到后方报到,做好补给队伍的安置。甘特中士,你没听到我的命令吗?
甘特:我听到了,长官。
阿尔格兰:那就服从命令。立刻去!
甘特:恕我无礼,长官。但是我才不甩你呐!
在战场上,甘特中士对阿尔格兰的命令不屑一顾。这既是他对阿尔格兰忠心耿耿的表现,同时也是美国文化低权力距离的体现。
三、克制与放纵
霍夫斯泰德认为放纵表示:“人的基本需求与享乐欲望应当给予充分的满足。”[1]206而克制则要求:“需求和欲望的满足必须受到严格的社会准则的约束。”[1]206在放纵型社会,人们趋向于释放他们的原欲和本性,最大程度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在欲望的驱使下加之社会对任自放纵的允许度较大,人们会肆无忌惮地纵情于名利与酒色。在性格与态度上,他们外向热情、感情外露、渴望自由。在克制型社会,人们倾向于克制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由于受限于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人们对欲望的满足会加以限制。无论是在精神层面还是在身体层面,人们都克己守礼,不越雷池一步。在性格与态度上,他们含蓄冷静、内向沉稳、尊崇秩序。深受佛教和儒教熏陶的日本,在开放国门、全盘西化之前,是一个典型的克制型国家。然而,与日本不同,雄踞“新大陆”的美国是一个肃清了天主教的清规戒律的新教国家,属于放纵型社会。
日本是一个高度注重自我修养的国家。对日本人而言,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4]20-23。自我修养在日本文化中分为两类:培养能力与“圆通”。培养能力就是培养意志力。日本人认为精神能够战胜物质,精神可以驾驭肉体。通过对肉体的磨练能达到灵魂的升华,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会理会身体所遭受的损坏。“圆通”是破除无明和烦恼的障碍,恢复清净本性的境界,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因此,日本人重视沉思冥想,以此体验“人生的乐趣”。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胜元手握佛珠在空旷的山坡上打坐,超脱凡尘,进入忘我的境界。于冥想中,他看见了一只凶猛至极的白虎与武士们殊死搏斗。后来,阿尔格兰在树林里手持白虎旗拼死抵抗,这让他猛然想到阿尔格兰就是那头白虎。为了顺从天启,胜元没有怒杀阿尔格兰替其妹夫报仇。秉承天意和敬奉羯磨(Karma)的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杀念,将被俘虏的阿尔格兰视为座上宾。阿尔格兰与武士们切磋剑术,屡屡受挫。在一旁观战的信忠上前对阿尔格兰说道,“对不起,失礼了。太多杂念。刀法、人群的目光和敌人的战术。杂念太多了。你要心无杂念。”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年仅几岁的比健静坐在被积雪覆盖的庭院里。他用坚强的意念抵抗严寒对肉体的侵袭,以此来磨练意志力,消除杂念。日本同时也是一个恪守秩序与严于律己的国家。在武士及其家属聚居的村落与这些不同寻常的日本人一起生活了一个冬季之后,阿尔格兰自述道,“他们万分令人钦佩。从醒来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致力于把自己所从事的一切做到尽善尽美。我从未见过如此严明的纪律。”农民们在田地里埋头苦干,辛勤地打理耕地;铁匠们在铸剑房百般锤炼手中的武士刀,精雕细琢;武士们在练习场刻苦训练,一起比试剑术、射击与搏击;孩子们则在家里勤奋学习书法,精益求精。大家各司其职,敬畏神明,村庄里秩序井然。尽管阿尔格兰是多丽子一家的仇人,但是胜元仍然安排多丽子悉心照料阿尔格兰。后来,多丽子发现阿尔格兰如同父亲一般对待自己的孩子,温柔又体贴,还没有日本男人的大男子主义。她渐渐对阿尔格兰产生了微妙的情感,但是她又极力控制自己真实的感受。在阿尔格兰准备同胜元武士集团离开村落向东京出发时,这也许就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相见,她也没有出门送别阿尔格兰。
新教与天主教分庭抗礼,各据一隅。美国的清教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天主教的七宗罪:色欲、暴食、贪婪、懒惰、暴怒、嫉妒和傲慢,但是它更加注重民主、自由以及人性解放[5]35-40。新教精神也进而成了美国独特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之源[6]507。在《神曲》中,但丁认为“暴食”是“过度放纵食欲、酗酒或囤积过量的食物”[7]87;“贪婪”是“过度热衷于寻求金钱上、名声上或权力上的优越”[7]87;“暴怒”是“源自憎恨而起的邪恶的感觉,企图惩罚他人或复仇。”[7]88在美国时,阿尔格兰为战争创伤所扰,受梦魇所折磨,于是以酒解愁,成了个十足的酒鬼。因为嗜酒成性,阿尔格兰消极怠工,没有好好配合麦坎先生的表演,以至于丢了饭碗。为了功业与声望,贝格利不自量力,狂妄地率领211 名士兵攻击2000 名被激怒的印第安战士,导致无数士兵惨死。听到贝格利的名字时,胜元大加赞赏他是“一个很好的将领”。阿尔格兰愤慨地说道,“不,他不是个好将领。他傲慢还鲁莽。他是个自命不凡的杀人凶手。他的士兵因他而丧命。”为了复仇,为了雪耻,为了宣泄心中的怒火,贝格利带领军队血腥屠杀了一个印第安部落,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全是无辜的印第安妇女与儿童。
四、结语
作为一部将日本元素与美国元素相融合的历史电影,《最后的武士》不仅呈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的风貌,还反映了19 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与美国的文化差异。运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分析该影片,我们可以发现美日文化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权力距离以及克制与放纵三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虽然改革浪潮翻涌下的日本大开国门,对西方文明兼收并蓄,但是日本传统文化仍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君主制度、武士道精神和提倡自我修养的文化早已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美国是一个冉冉升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也是现代文明的典范。社会契约精神和清教主义奠定了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基础,铸就了美国的民族特性。阿尔格兰漂洋过海跨越太平洋,从现代的美国到了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日本。在此生活期间,由于文化差异,他有过不解,也有过彷徨。然而,真正让他着迷的不是现代的日本,而是传统的日本。他学会日语,掌握日本剑道,领会武士精神,身着铠甲手持武士刀与胜元并肩作战。和胜元有所不同,他是一个融合现代和传统的武士。最后,他选择回到那个让他获得重生的传统的村落,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享受到一份在现代文明中寻求不到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