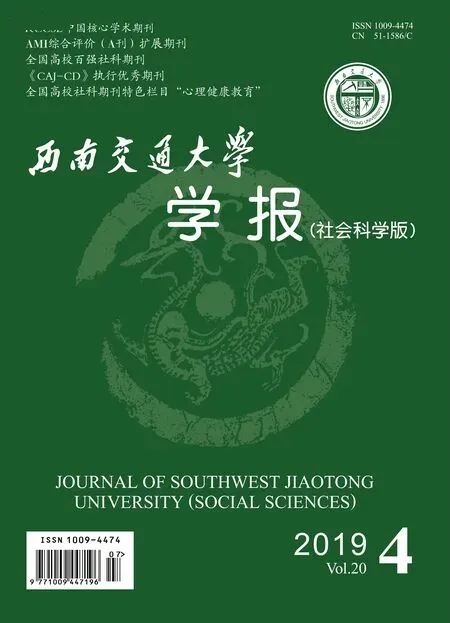史书自注对唐诗自注之影响
2019-02-20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史书自注是早于诗文自注出现的自注类别,初现于先秦史籍,两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成熟,至唐代而更加完善。刘知几在《史通·补注》中首次将史臣“手自刊补”的自注作为史注方法之一,这是史书自注具备独立属性的有力证明。史书自注的充分成熟,无疑为唐代始兴的诗歌自注提供了可鉴之资。此外,无论是基于修身治国之需还是科考的规则要求,精熟史书都是唐代文士的必备素质。唐代科举制度将三史科设为贡举十二常科之一①,考试内容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中;而春秋三传则是明经科必考典籍①。即使不是出于应试目的,这些经典史籍也同样是文人学士的案头必备。总之,作为业已成熟独立的注释体例,史书自注足以成为尚在起步阶段的唐诗自注的参考模式;而诗人对经典史籍的熟读,又使唐诗自注借鉴史书自注成为可能。
一
无论史书自注还是诗歌自注,都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内容——注释什么,体式——如何注释,形式——呈现面貌。就自注内容而言,其阐释对象及详略程度取决于被释文本的性质、内容及撰注者的考量,具有较强的主观针对性,故而很难为不同的自注撰者或不同文本类型的自注彼此仿效。而自注的体式与形式则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制于被释对象的文体及内容,而具有相对独立的模式,可适用于不同性质的文本。因此,史书自注的体式及形式成为对唐诗自注影响最深的方面。
史书自注体式即史书作者对己著的注解方式。古今学人大多将自注纳入宏观的史注法加以审视②,事实上,就史书自注本身而言,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亦逐渐形成了独立有效的阐释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训体自注
这类自注是对名称概念、字词义的解释说明,受经学注释方法的影响,注重意义阐释的精确性,与被释文本在内容边界上高度吻合。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1〕“夫文止戈为武”为插入正文的自注,用以训释“武”字之义。《史记·秦本纪》:“秦三将军相谓曰:‘将袭郑,郑今已觉之,往无及已。’灭滑。滑,晋之边邑也。”〔2〕末句亦为随文自注,是对“滑”这一地名的介绍。《汉书·艺文志》在“《平原君》七篇”条目下注“朱建也”〔3〕,朱建为西汉初人,高祖刘邦赐号“平原君”。《平原君》七篇为其所作,《艺文志》中特别以自注交代作者姓名,主要目的在于和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相区分,以免将两者混淆。
2.解体自注
此类自注是对文本信息的深入阐释或延伸补充。与训体自注主要针对被释对象的意义层面不同,解体自注更关注对史实及事实的延展细述。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杨氏》二篇”条目下自注“名河,字叔元,甾川人”〔3〕,是对篇目作者身份信息的补充介绍。再如《史记·田叔列传》有:“数岁,坐太子事。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2〕从“时左丞相自将兵”到“坐纵太子”是插入正文中的自注,进一步详述“坐太子事”的始末。又如《唐六典》门下省部分论及侍中对下呈于上的六类公文的处理过程为“审署申覆而实行焉”,句下注“覆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4〕,是对正文所言之“审署申覆”的具体步骤的说明。
由于解体自注不再囿于客观精确的意义训释,而立足于对史实人事的细化或扩充,这种注解思路更能代表史书自注的特色,所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逐渐成为史书自注体式的主流。
3.参见法自注
参见法自注指史书中后出自注的内容与已有正文或自注的内容恰好相同时,则后出自注仅交代重合部分内容的具体出处,而不对内容本身进行复述的注释方法。参见法自注最早见于《史记》,后世史书如《汉书》《隋书》《唐六典》等对此均有借鉴。此类自注一般不对文本内容进行直接的阐释说明,而重在发挥线索提示的功能,以引导读者串联史书中具有内在关联的记载,进行参照式的阅读。
参见法自注又细分为五类:书籍作者生平事迹参见、内容主旨类同书籍参见、古书今解本参见、史传人物及事件参见、典章制度参见。前三类已有文章专门论述,兹不赘言③。史传人物及事件参见指自注所释人事在史书中已有详载,自注需再次提及时,只交代史载之处而无需重复具体内容。此种情况多见于《史记》《汉书》的列传部分,并形成了诸如“事见某篇”“语在某篇”“语在某事中”“语见某传”等比较固定的提示语。如《史记·留侯世家》中云:“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语在《淮阴》事中”〔2〕。此处“语在《淮阴》事中”即为参见自注,提示韩信自立齐王的始末经过见载于《淮阴侯列传》,可与正文中受信印之事相参照。
典章制度参见集中体现在《唐六典》中,参见法自注约有20处。与《史记》《汉书》不同,《唐六典》中多使用“已具某处”“已详某注”“某注详焉”这类新的提示用语。如该书中书省部分,“右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句下自注“废置已详门下省左补阙注”〔4〕,中书省右补阙与门下省左补阙沿革废置的情况相同,撰者已在门下省左补阙自注中有详细说明,因而此处仅用参见自注加以提示交代。
二
以上三种史书自注体式均为唐代诗人借鉴运用,成为诗歌自注的基本阐释方法。
1.以明确概念及字词义为主要目的的训体自注在唐诗自注中得以沿用
唐诗中训体自注的内容主要包括训释人名与物名。人名训释如韦应物《送房杭州》题下自注“孺复”〔5〕二字,示以房氏全名。陶雍《和兵部郑侍郎省中四松诗》题下注“郑侍郎澣也”〔6〕,将诗题中的官职称谓明确为人名。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中的“常嗟李谪仙”句下注“贺知章谓李白为谪仙人”〔7〕,则是以姓名释别号。
物名训释又分三类:一是官职机构。如,李适《饯唐永昌赴任东都》中“翩翩矫翮度文昌”句下注“文昌即尚书省”〔6〕,元稹《上阳白发人》中“天宝年中花鸟使”句下注:“天宝中,密号采取艳异者为花鸟使”〔8〕。二是山河、城邑等地名。如皮日休《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慵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中“携将入苏岭”句下对“苏岭”的注释:“鹿门别名。”〔6〕李余《寒食》中“玉轮江上雨丝丝,公子游春醉不知”句下对“玉轮江”的说明:“汶江谓之玉轮江。”〔6〕三是亭台楼阁、寺观宅院等建筑形胜。如耿《题清源寺》题下注“即王右丞故宅”〔6〕;窦牟《奉诚园闻笛》题下注“园,马侍中故宅”〔6〕;李白《劳劳亭歌》题下注“在江宁县南十五里,古送别之所,一名临沧观”〔9〕。
字词意义的训解在唐诗自注中仍然存在,但比较少见。如杜甫《谢严中丞送青城山导师乳酒一瓶》中“洗盏开尝对马军”句下注对“马军”的解释:“军州对驱使骑为马军。”〔10〕又如智远《律僧》中“长长护有情”句下注“众生谓有情”〔6〕,阐释了“有情”作为佛教概念的含义。再如薛能《边城作》“管排蛮户远,出箐鸟巢孤”句下注“蜀人谓税为排户,谓林为丛箐”〔6〕,指出“排”“箐”两字在特定方言体系中的意义。
训体自注是对概念、意义的界定,注释内容与被注对象在内涵上的严格对应,是该自注体式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史书的训体自注中已出现应此原则而生的具体训释方法即互释法。所谓互释,指同义事物的相互阐释,被释者与解释者实为同质异名,两者对调位置后,训释关系依然成立。史书训体自注中的互释法往往使用肯定判断句,如前文所举《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自注“夫文止戈为武”、《史记·秦本纪》中的自注“滑,晋之边邑也”就分别采用了“A为B”“A,B也”两种典型的肯定判断句式,前者属于判断词居中结构,后者属于“……者……也”结构。在这两类句式中,A(被注释者)与B(注释者)的位置可以交换而不影响彼此核心内涵的高度吻合。
由此再审视唐诗中的训体自注,以肯定判断句为特征的互释法同样运用得相当普遍。前文所举唐代训体自注诗例中使用的判断句,有如下七类:(1)A即B;(2)A为B;(3)A,B别名;(4)A,B;(5)A,B也;(6)A,一名/一曰B;(7)A谓B④。第一、二、六、七类判断词虽不同,但均属于判断词居中的结构;第五类则是标准的“……者……也”结构;而第三、四两类虽缺少判断词及标志性结构,但具有明显的肯定判断性质,将其套入判断词居中结构或“……者……也”结构,均能成立。可见,唐代互释法采用的判断句式变体虽多,但基本句型不外乎判断词居中的“A为/即/谓/一名B”式以及“A(者),B也”式,这与史书训体自注互释法采用的判断句式一致。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史书自注与唐诗自注使用了相同的判断句式,而是以判断句为特征的互释法的使用,同时成为史书与诗歌训体自注的特色。因此可以说,是前者成熟的训释思路与有效的实现手段启发了后者,并为之提供了可供效仿的成功模式,从而使“判断句—互释法—训体自注”这一释解套路从史注转入诗注,这一推测是极有可能成立的。
2.解体自注在唐诗自注中大量出现,延伸阐释也成为唐代诗人自注其诗的主要方法
唐诗解体自注的延伸阐释分为内向延伸与外向延伸两类。内向延伸指自注对被释者显微、进深式的说明,是自注对诗歌内容的纵向深化,主要通过延展细节和揭示本事两种途径实现。
细节延展指自注对诗句中具有片段性与笼统性的人事信息进行缀补,言其所不能尽言之处,如独孤及《自东都还濠州奉酬王八谏议见赠》中“天地变化县城改,独有故人交态在”句下注:“天宝中,及尉华阴、郑县,别后经禄山之乱,郑县残毁,城移于州西”〔6〕。诗句的叙述仅反映出诗人居住过的城邑因战乱而引发重大变故这一现状,自注则不仅进一步明确所谓天地变化与县城改移的具体所指,还揭示出诗人与已面目全非的县城间的渊源,使诗句中概括式的书写因客观事实的支撑而更具充实饱满的情感张力。
揭示本事指诗歌避开对事实本事的直陈,而运用典故、比喻、象征等笔法曲折言之,自注则点明诗歌的实际指涉。如韦应物《将往江淮寄李十九儋》中有“燕燕东向来,文鵷亦西飞”之句,表面是写燕子与彩凤的东来、西飞,题下自注则点明暗藏之本事:“予自西京至,李又发河洛,同道不遇”〔5〕。诗人实以东来燕与西飞凤分喻自己和李儋行旅中的交错不遇。再如杜甫《奉赠萧十二使君》中“终始任安义,荒芜孟母邻。联翩匍匐礼,义气死生亲。张老存家事,嵇康有故人”六句下自注云:“严公既没,老母在堂,使君温清之问,甘脆之礼,名数若己之庭闱焉。及太夫人顷逝,丧事又首诸孙,主典抚孤之情,不减骨肉,则胶漆之契可知矣。”〔10〕诗题中的萧使君具体名字不详,原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幕府任郎官之职,不仅为严武属僚,且与严武私交匪浅。诗句中罗列任安拒投霍去病而始终追随卫青、张老悉心教导赵氏遗孤赵文子助其成材、山涛抚育培养嵇康临终所托一双儿女三个典故,自注则并非对典故本身进行阐释,而是指出其在诗歌文本中影射的实事,即萧使君在严武逝后对其家人的供养照料。诗句典故与自注内容间实则亦为类比关系,自注是在具体诗歌语境中对典故原有事义进行的叠加与延伸。
外向延伸是指自注对与诗歌或诗句相关的外围信息的补充说明,与内向延伸自注的纵向深化阐释不同,此类自注重在信息面的横向拓展,与被释诗歌或诗句的本事及内蕴关联不大。外向延伸自注一般以题下注居多,内容主要包括三类:(1)揭示诗歌创作原因,多使用“因以”“故以”作为提示语。如韦庄《伤灼灼》题下注:“灼灼,蜀之丽人也。近闻贫且老,□落于成都酒市中,因以四韵弔之。”〔6〕交代此诗的创作动机为感伤蜀地佳人灼灼贫老困窘的命运。(2)交代诗歌赠和对象。诗歌的寄赠对象大多在诗题中直接体现,以自注指明酬赠对象的情况较少,一般见于歌行体中。如杜甫《醉时歌》题下自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10〕,《徒步归行》题下自注“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途经邠州作”〔10〕,《丹青引》题下自注“赠曹将军霸”〔10〕;刘长卿《听笛歌》题下自注“留别郑协律”〔11〕;白居易《醉歌》题下自注“示妓人商玲珑”〔7〕。可见“某歌/行+赠/示某人”已成为唐代歌行体自注寄赠对象的常用书写格式。(3)陈述诗歌写作背景。如元结《欸乃曲五首》题下自注就该诗的创作经过进行了细述:“大历丁未中,漫叟结为道州刺史,以军事诣都使。还州,逢春水,舟行不进,作欸乃五首,令舟子唱之。盖以取适于道路云。”〔6〕由此可知,此篇的诞生与诗人一次公务出行中遇到的意外事件相关,实为缓解险途带来的惊惧与焦虑而作。再如杜牧《感怀诗一首》题下注“时沧州用兵”〔12〕,则交代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宗大和元年(827)八月,朝廷遣兵沧州,讨伐横海军节度留后李同捷,该诗正作于此际。
唐诗解体自注的延伸阐释分别从纵深细化和横向拓展两个维度增加了被释对象已有的信息容量,在本质上继承并坚持了史书解体自注以追求事实为本、以增补被释者既有信息为要义的阐释原则。换言之,唐诗解体自注两类延伸阐释衍生出的系列途径,均是遵循解体自注内容拓展原则的具体表现。
3.史书中的参见法自注在唐诗自注中得以继续沿用
唐诗自注中的“参见法”用例不多,仅见于以下六处:马怀素《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藩应制》中“空余愿黄鹤,东顾忆回翔”句下注云:“黄鹤见《汉书·西域传》,公主歌云:愿为黄鹄兮归故乡。”〔6〕张说《侍宴蘘荷亭应制》中“仙路迎三鸟,云衢驻两龙”句下自注云:“三鸟见刘向九辨惜贤篇,两龙出山海经。”〔6〕权德舆《八月十五日夜瑶台寺对月绝句》中“瀛女乘鸾已上天,仁祠空在鼎湖边”句下注云:“仁祠,寺也。见后汉书楚王英传。”〔13〕白居易《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中“愧无铛脚政”句下注:“河北三郡相邻,皆有善政,时为铛脚刺史。见唐书。”〔7〕郑嵎《津阳门诗》中“四方节制倾附媚,穷奢极侈沽恩私。堂中特设夜明枕,银烛不张光鉴帷”句下注云:“虢国夜明枕,置于堂中,光烛一室。西川节度使所进。事载国史,略书之。”又,“画轮宝轴从天来,云中笑语声融怡。鸣鞭后骑何躞蹀,宫妆襟袖皆仙姿。青门紫陌多春风,风中数日残春遗。骊驹吐沫一奋迅,路人拥篲争珠玑。”句下注云:“事尽载在国史中。”〔6〕
由上可见,唐诗自注中的参见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提示出处代替内容重述的注解方法。自注中需要解释的语典及事典在文献中已有极其详实的记载,诗人通过典故出处参见的方式,既实现了对典故的间接注解,又避免了对史载的重复叙述,这明显是对史书参见自注的继承。二是具有相对固定的参见提示语,即“某事/语见某书”“某事载某书”。这与史书参见自注的提示语基本相同,均先点明注释对象,继而指出其出处来源。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代诗人对史书参见自注用语的吸收与沿用。
三
除注释体例外,史书自注的书写形式对唐诗自注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书自注大致经历了直插入正文、“本注曰”提示、小字夹注三种形态的变化〔14〕。其中,以小字附注的形式对唐诗自注的书写体式影响最为深刻。
小字夹注形态的自注最早出现在魏晋史书中,实则是对佛经合本子注的效仿。佛经在传入中土后,同一经文译为不同语言或被不同译者翻译后,往往会形成表述各异的不同译本。而为了文献保存的完整性及对经意理解的全面性,注经者便将同一部佛经所有的翻译版本集中起来,以其中质量最高者为底本即母本,其余诸本为别本即子本,将译本内容按经意分割,母本中与之相匹配的译文以大字正文出之,诸子本的译文则以小字附于其后。这种附于母本正文之下的子本小字译文便是子注。子注与母本正文不是意义层面的阐释与被阐释关系,而仅仅是语词表述层面的“同本异译”。因此,其与史书自注对正文中史实的增补说明有本质区别。但佛经合本子注的小字夹注形式却深刻影响了史书自注的面貌。随着魏晋时期佛经翻译传播的日渐隆盛,合本子注的形式也迅速渗透到史书自注中,成为史书自注的固定形式。史书自注在兼收子注形式的同时,内容上仍保持了增补史实这一根本属性,从而实现了对佛经子注的吸收内化,建立起了史书自注新的书写范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便是魏晋时期子注式自注的典范。
唐人诗作的原稿早已亡佚不见,因此,对其自注的真实书写形式,只能通过以下两方面做出最接近真相的推测。
首先,从魏晋赋文中小字夹注的自注形式类推唐诗自注的书写形式。魏晋时期确切可考的使用自注的赋文作品有四篇:谢灵运《山居赋》、张渊《观象赋》、颜之推《观我生赋》和鲍照《芜城赋》。自注全部采用小字,附于题下或夹于文中。而这种小字夹注形式实为上述赋文自注的原貌。对此,有学者曾指出:
在史书中自注无论采用文中自注,还是“本注曰”的形式,都属于笔类。也就是说,这时的自注虽未采用小字标明,但其文体一致为笔类,仍然纯正可读。但赋中阑入之自注,诚以笔为文,如果不加以区别,则赋、注相互淆乱,文笔交错,则韵之句读,难以寻觅,几乎不能顺利阅读。从此不难看出,采用子注是赋的自注得以顺利传播的可靠途径。所以在沈约辑入《山居赋》之前,谢灵运采用子注体式书写其自注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大了。〔14〕
这段论述从文、笔差异及赋文与自注完整保存、传播的角度分析了魏晋赋文采用子注体式书写自注的必然性,推论十分合理。虽以《山居赋》为例,实则涵盖了赋作自注撰写的普遍情况。
用以上思路类推唐诗自注的书写形式,同样成立。诗歌与赋同属有韵之文,且比赋具有更严格的字句数、声韵、对仗等形式上的要求,加之古人行文无句读,若在诗句后仍采用史书自注的直插或“本注曰”两种传统书写方式,则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势必造成诗句与自注的相互夹缠肢解,不仅导致阅读障碍,也消解了自注对诗句信息增补细化的功能。如想既保证对诗句内容的补释阐解,又能在形式上与之区分独立,子注式自注无疑是最佳选择。因而唐诗自注的最初书写形式极有可能与魏晋赋文一样,采用的是子注体例。
其次,现存唐人诗集早期版本中的自注形式为推测唐诗自注的最初面貌提供了较可靠的依据。就现存集本而言,敦煌卷子中的唐人诗歌抄本最能直接体现唐诗书写的原始面貌;宋本唐人诗集,因时间相去不远,对唐集原貌的保存程度仅次于敦煌唐诗抄本。因此,笔者将以张锡厚先生编著的《全敦煌诗》及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宋本唐人集为例,对唐诗自注的书写形式进行分析。
1.《全敦煌诗》中唐诗自注的书写情况
《全敦煌诗》是目前所见辑录敦煌诗歌数量最多、类别最全面的敦煌诗歌总集,其中又以唐诗占主体。而在具体辑录过程中,则充分尊重遗书原抄格式,以忠实反映诗歌原貌为宗旨〔15〕。因此,其所呈现的唐诗自注书写形式具有极高的还原度。集中共有6处诗歌自注可确定出自唐人之手,现尽数列举如下:
孟浩然《梅道士水亭》题下注云:“亭金刚般若。”〔16〕该诗见于敦煌遗书伯二五六七《唐人选唐诗残卷》,自注呈单行小字排列,紧随题后⑤。
高适《同李司仓早春宴睢阳东亭》题下注云:“得花。”〔16〕该诗见于敦煌遗书伯二五二二,自注原抄格式为单行小字排列,紧随诗题之后。
李翰《李翰自注蒙求》以四言诗的方式撰写而成,是当时流行的蒙童读物。《全敦煌诗》本《蒙求》据敦煌研究所藏敦研〇九五、伯二七一〇、伯四八七七残片缀合为32句,除末句外,其余各句下均有自注,用以解释诗句中的典故,字数多达三四十字。所有自注为双行小字,每行十七至二十二字,字迹整齐清晰。
白居易《胡旋女》题下注云:“天宝年中外国进来。”〔16〕该诗见于敦煌遗书伯二四九二白居易诗残卷第十三题,自注原抄格式为单行小字,紧随题诗之后。
无名氏《赠阴端公》题下注云:“子侄逆遂成分别因赠此咏。”〔16〕另一首《军威后感怀》题下注云:“□□二年二月廿二日末,□□□身□人分□□。”〔16〕此二诗出自敦煌遗书无名氏诗十八首,前者见于伯二七六二,后者见于斯三三二九与斯六一六一的连接处。据郭炳林先生考证,无名氏诗十八首的作者是晚唐僧人悟真。笔者依此说,将其纳入唐代自注诗之范围〔17〕。《赠阴端公》题注的原抄格式为单行小字排列,紧随题后。《军威后感怀》题注的原抄格式为紧跟诗题下的双行小字排列,“□□二年二月廿二日末”与“□□□身□人分□□”各成一行。
可见,以单行或双行小字形式排列,紧随诗题之后,是上举敦煌遗书唐诗题下自注的通用书写格式,这基本上可反映出唐人自注撰写的原貌。
2.宋本唐人诗集中唐诗自注的书写情况
(1)唐人诗歌合集
《窦氏联珠集》与《松陵集》为现存唐代诗集中仅有的两部完整保存原集面貌的诗歌合集,两集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为宋本,故而其中的自注排布形式可以视为唐人自注书写的原始形态。储藏言所编《窦氏联珠集》现有的最早版本为南宋淳熙五年(1178)刻本。清代缪氏艺风堂影宋抄本、乌程蒋氏密韵楼影宋刊本、刘云份《中晚唐诗本》及《四部丛刊三编》本《窦氏联珠集》都保存了淳熙本的原貌〔18〕。
笔者以密韵楼影宋刊本《窦氏联珠集》为对象,考察了其中自注的书写面貌。集中共有自注诗13首,自注13处,其中题下注12处,句下注1处,均采用小字。12处题下自注中,单行排列式8处,包括2、3、4、6、7字句;双行排列式4处,包括7、9、12字句。1处句下自注为双行形式。
蔡景繁所藏北宋京都旧本为《松陵集》现存的最早版本,笔者所依《湖北先正遗书》本《松陵集》则属于北宋本一系,保留了此本的原貌⑥。集中共有自注诗127首,自注166处,其中题下注23处,句下注143处,包括124处文中句下注及19处文末句下注。所有自注均采用小字,题下自注单、双行排列式兼有,单行式自注5条,均为4字以内(包括4字)句;双行式自注16处,基本为5字以上(包括5字)句,仅一处例外,为2字双行句,即皮日休《临顿为吴中偏胜之地陆鲁望居之不出郛郭旷如郊墅余每相访欵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韵奉题屋壁》于诗题中“临顿”之下自注双行小字“里名”⑦。此外,该注出现的位置为题中,这与绝大多数自注紧随题后的情况亦有所不同。所有句下自注均为双行排列。
(2)唐人诗歌别集
敦煌唐诗抄本及两部唐人诗歌合集中的自注均以单行或双行小字附于诗题或诗句之下,这是唐代诗歌自注原貌最直接有力的实证。此外,宋本唐诗别集作为唐人诗集的早期版本,对唐人诗歌书写面貌亦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故而有必要对宋本唐诗别集中的自注进行考察,以为辅证。
为确保结论的准确,作为考察对象的宋本别集需满足下列条件:首先,入选诗人的时期分布相对均匀。其次,诗人自注诗数量在其所处时期属于高产群体⑧。第三,诗人曾亲编或保存整理过自己的诗歌作品。综合以上条件,笔者将对下列6部宋本唐诗别集中的自注进行考察。
①当涂本《李翰林集》。此本据清光绪年间贵池刘世珩玉海堂影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影印。集中有李白自注诗35首,均采用小字。其中3处为句下注,双行排列;其余为题下注,单、双行兼有。单行式多见于一字或两字自注;但也有字数较多的单行式个例,如《上崔相百忧章》题下注“四言,时在寻阳狱”〔19〕共7字,却以单行排列。双行式自注字数一般在5字以上(包括5字),最多可达30余字。《登金陵冶城北谢安墩》题下注“此墩即晋太傅谢安与右军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将营园其上,故作是诗”〔19〕,是李白诗歌自注中字数最多者,共计33字。
②《续古逸丛书》本《杜工部集》。该集以明末毛扆刊刻南宋影写本为底本,以述古堂另一影宋抄本加以增补而成。集中有杜甫自注诗115首,76处题下注与59处句下注均采用小字。题下注单行与双行排列兼有,4字以内一般为单行式;4字以上(包括4字)、10字以内(包括10字)的自注排列比较灵活,单、双行的切换没有固定的字数界限。10字以上题下注均采用双行式。句下注则基本采用双行排列,仅有两处例外,为单行形式:一处为《绝句四首》其一“松高拟对阮生论”句下注“朱阮剑外相知”;一处为该组诗的第三首“门泊东吴万里船”句下注“西山白雪四时不消”〔20〕。两处还均为文末句下注。
③《四部丛刊》影宋本《刘梦得文集》。该本有刘禹锡自注诗64首,46处题下注与29处句下注均采用小字。题下自注基本为双行式,有4处例外,为单行排列:《善卷檀下作》题下注“在枉山上”〔21〕;《闻董评事疾因以诗赠》题下注“董生奉内典”〔21〕;《早秋集贤院即事》题下注“时为学士”〔21〕;《三阁词》题下注“吴声”〔21〕。这几处基本为4字或5字注,而相同字数的其他自注则均采用双行排列。29处句下自注则均排作双行。
④宋蜀刻本《新刊元微之文集》。该本有元稹自注诗80首,51处题下注与43处句下注均采用小字。题下注单、双行排列兼有,以双行式为主,共36处,均为5字以上句(包括5字)。句下注基本采用双行形式,仅一处例外:《酬刘猛见送》中“江流初满槽”句下注“江槽楚语”〔22〕为单行排列。
⑤《四部丛刊》影宋本《樊川文集》。该本有杜牧自注诗46首,题下注11处,句下注50处,均为小字书写。题下注几乎均为单行排列,仅有一处例外,即《商山富水驿》题下注“驿本名与陈建议同姓名,因此改为富水驿”〔23〕采用双行式。句下自注则全部为双行排列。
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许用晦文集》。该本有许浑自注诗16首,题下注与句下注各10处,一律采用单行小字样式。
由上可见,宋本唐诗别集中自注书写形式有以下几个特点:从行式排布看,唐诗题下注形式比较灵活,以双行居多,单、双行排列兼具。句下注的排列则比较统一,基本为双行式。自注字体皆与正文相同,但字号偏小。从与正文的位置关系看,则分为自注缀于题下或篇末与自注夹于文中两种。以上六种别集中的自注并非唐诗自注之全部,但从中至少可以确定单、双行小字缀注或夹注应当是唐诗自注所采用的一种极为普遍的形式。这与《全敦煌诗》、《窦氏联珠集》及《松陵集》中唐诗自注原貌的特征相吻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以单行或双行小字的形式附于题、诗之末或诗句之中,是唐诗自注基本的书写样式。
若仅从小字缀注或夹注的形式来证明史书自注对唐诗自注的影响,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佛经合本子注乃至六朝赋文中的自注均有可能给唐诗自注的书写方式带来启发。而如前所述,唐诗自注虽以小字缀注或夹注的面目出现,但其所发挥的并非是对文本的翻译功能,而是对本事、诗意的增补阐释。显然,从内容的维度看,唐诗的小字夹注式自注与佛经合本子注有着本质区别。而以子注面貌承载释事解意之实,从而将佛经翻译校雠的手段彻底转换为注释的书写格式,则是从史书自注开始,也是史书中子注式自注与佛经合本子注的根本分野。在这个分界点上,唐诗自注恰与史书自注一脉相承。由此可见,于唐诗自注而言,史书中子注式自注的影响不仅仅是外在的书写形式,更是使用这一形式的目的与思路,因此更加彻底而深刻。
注释:
①详见《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第1159-116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刘知几最早将自注归为三类史注体式之一,详见白云译注《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第216-221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李绍平、杨华文将史注法分为两类自注与他注两类,详见其《历史文献注释论述赘言》,刊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75-78页。刘治立将魏晋至唐的史注体式归为七类,自注为其中之一。详见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刊于《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第45-48页;《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注三题》,刊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125-129页。
③详见那世平《〈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浅析》,刊于《图书馆学刊》1995年第2期第54页。此文虽以《汉书·艺文志》作论,但所归纳的三类参见法适用于其他史书自注中类似的情况。
④文中所举唐代诗歌中的训体自注虽非穷尽此类自注的全部例证,但所有诗例中使用的判断句类型都不出正文中的七类。因此,七类判断句句型可以代表唐诗训体自注判断句式的整体情况。
⑤六处自注行款的说明,分别依据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卷三五孟浩然《梅道士水亭》校记1,第1730页;卷三七高适《同李司仓早春宴睢阳东亭》校记1,第1904页;卷四五李翰《李翰自注蒙求》校记1,第2333-2335页;卷四八白居易《胡旋女》校记1,第2558页;卷七九无名氏《赠阴端公》校记1,第3542页;卷七九无名氏《军威后感怀》校记1,第3549页。
⑥《湖北先正遗书》本《松陵集》为汲古阁本《松陵集》的影印本,而汲古阁本又以北宋蔡景繁藏本为底本进行刊刻。因此,《湖北先正遗书》本保存了北宋旧本的原貌。关于《松陵集》收诗数量及版本流传情况,参见西南大学叶英俊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松陵集〉研究》第2-5页。
⑦参见《湖北先正遗书》本《松陵集》卷四,叶20b。
⑧依据笔者对唐代各时期人均自注诗数量(各时期自注诗总量/各时期自注诗诗人数)的统计,初唐为1首/人,盛唐为10首/人,中唐为12首/人,晚唐为8首/人。超过上述均值者,为各时期自注诗高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