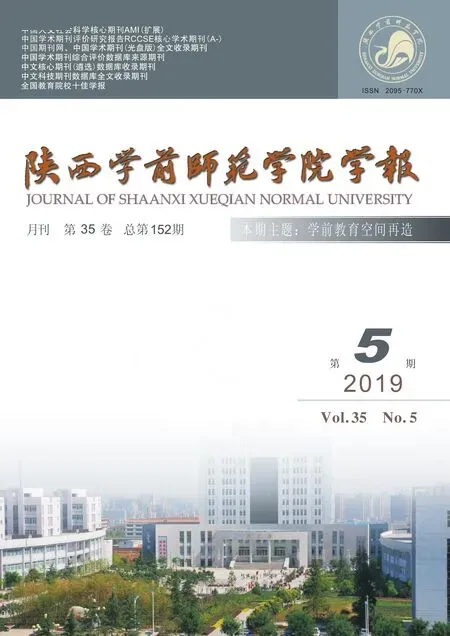儿童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关系的研究进展
2019-02-20吴念阳
安 茜,吴念阳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儿童在使用语言描述事物间关系之前就开始探索世界。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学会了描述空间关系的词。现代汉语中的空间语言主要包括空间方位词和空间维度词。空间方位词是确定事物空间关系的形式标记,包括五类:“上/下”类、“里/外”类、“前/后”类、“中/旁”类、“左/右”类[1]。空间维度词是对具有一定形状事物占据空间的量进行说明的词语,包括“大、小、长、短、高、低(矮)、深、浅、粗、细、厚、薄、宽、窄”等七对[2]。Cannon,Levine 和Huttenlocher(2007)为研究儿童在空间任务上的表现及与其父母空间语言产生之间的关系将英语中的空间语言分为空间维度词、空间形状词和空间指代词等八类[3]。
空间认知涉及物体的位置、形状、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移动的路径,与儿童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拼装玩具,参照地图到达目的地等,空间认知也与“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TEM)方面的成功有关[4]。
理论界对语言和认知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斯皮尔-沃尔夫假设(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主张语言塑造经验,不同语言间的结构差异导致认知差异。一个人所学的特定语言决定了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5]。反驳语言决定论的学者认为尽管语言之间的结构有很大差异,但它们并不能完全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看法[6]。几十年来,关于空间语言对空间认知是否起决定作用及二者之间的影响程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一、关于空间语言与空间认知关系的不同观点
(一)空间语言决定空间认知
语言是空间认知形成所必须的,语言能引导儿童关注空间信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对空间信息的处理[7]89-106。Casasola (2003)认为,如果在婴儿期获得了空间方位词,儿童将能辨析更多种的空间类别[8]。在发展早期,提示儿童使用特定的空间词汇可以提高他们的空间能力。例如,如果在短时记忆任务中使用了左(left)和右(right),学前儿童可以很好的保留关于颜色位置关联的信息[9]。Boroditsky(2001)发现,英汉两种语言使用的空间隐喻在时间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些语言使用者在认知加工过程中的差异。英语倾向于用水平词来表示时间序列,例如 ahead/behind (e.g.,putting hard times behind us,falling behind schedule),中国人倾向于用垂直词来表示时间序列,例如上/下[10]。一项对伊斯坦布尔失聪儿童的研究表明,没有接触过传统语言模式的聋儿很少产生传达两个物体之间空间关系的家庭手势。此外,在空间任务上,在控制了一般认知能力的影响之后,聋哑儿童的表现和听力健全的儿童相比表现不佳。这些发现表明学习空间语言在推理关系时能赋予认知益处[11]。空间语言之所以影响空间认知,是因为空间语言对空间关系进行编码,提高了人们匹配空间关系的能力。Loewenstein和 Gentner(2005)通过实验证实了空间语言对于空间关系匹配能力的影响[12]。有研究表明那些被教授并且后来在实验室中正确理解和使用空间语言“左”和“右”的4岁儿童在相同的空间重新定向任务中表现得比没有被教授这些空间语言的儿童更好,儿童对空间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是他们成功完成空间任务的预测指标[13]。
(二)空间语言是空间认知的工具
空间信息对儿童而言并非只有语言,还有感觉、知觉等。前语言阶段的儿童能够区别空间关系类别[14],六个月大的孩子可以基于“在……之间”关系(between relation)进行分类[15]。在空间关系不太容易辨别的情况下,对儿童进行空间语言的输入可以促进类别的习得。例如,训练“上”这一词后,儿童习得了这一关系,这种关系就难以习得,这表明空间语言可能对一些空间范畴的形成是必要的[16]。Szechter和Liben (2004)研究发现父母与孩子共读图画书时,那些父母使用空间语言强调空间关系(包括物体大小和位置)的儿童在使用空间信息完成图片排序任务时成绩较好[17]。
Li和Gleitman(2002)认为,空间语言和空间任务表现的相关性可以解释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空间语言引导空间认知;二是不同的文化群体对空间有不同的解释,对空间的理解指导了他们使用的空间语言。三是存在第三变量,如任务环境,导致空间语言与空间任务成绩之间的相关性。为验证第三变量的存在,Li和Gleitman进行了一系列控制任务环境的研究。为了控制任务环境对被试的影响,这些研究都是在同一语言社区进行的。研究表明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之的关系是复杂的,在某些情况下,空间语言似乎对空间认知有显著影响,但在其他情况下,空间语言可能不如其他因素重要,如来自同一语言社区的被试在不同的参照条件下使用的策略有所不同。在相对参照条件下使用相对策略,被试在绝对参照条件下使用绝对策略[18]。
(三)空间语言和思维同时发展
Dehaene等人(2006)对几乎没有空间语言文化的亚马逊部落的蒙杜鲁库人进行了研究,表明许多空间任务的解决可以没有空间语言的帮助,从而说明空间语言不是空间认知发展的必需品[19]。然而,数据的重新解读揭示了空间语言的重要作用[20]。除了测试蒙杜鲁库人,Dehaene等人(2006)用同一空间任务测试了美国儿童和成人,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成人比美国儿童和蒙杜鲁库人表现都要优异,表明经验与空间语言可能对空间认知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二者并非有谁占主导地位,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可能同时发展,它们可以通过日常经验相互建构[19]。
二、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关系研究范式
(一)跨语言研究
Choi,McDonough,Bowerman,and Mandler(1999)表明,18个月大的儿童,他们对母语描述这些关系的具体方式很敏感,并且能够识别属于他们语言中正确分类的情况。英语使用“in”来描述包容关系,使用“on”来描述支持关系。相比之下,韩国使用“kkita”(紧身)和“nehta”(宽松)来描述相同的空间关系。这就导致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分类。英语将“盖上钢笔盖子”和“把信放在信封里”归为不同的空间类别,分别表述为“put a lid on apen”和“put a letter in an envelope”;而韩语则会将这两者都归为kkita(紧身),将“苹果放在碗里”归为nehta(宽松)这一独立空间范畴[21]。Levinson和他的团队调查了24种语言如何表达空间关系,研究发现了各种语言表达空间关系的方式主要有:相对参考框架、绝对参考框架、内在参考框架;采用不同参考框架的语言的使用者认知到的空间关系是不同的。Levinson等人认为不同的语言会导致不同的概念识别,语言可以重新组织其背后的认知[22]。Johnston和Slobin(1979)对2到4岁母语分别为英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儿童进行了空间方位词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发现跨文化语言中儿童获得空间词的一般顺序基本保持一致[23]。
(二)空间语言线索对空间认知的影响
Casasola,Bhagwat,Burke (2009)发现,比起没有在任务中听到空间语言提示的儿童,听到空间语言提示的儿童会在空间任务中获得更好的成绩[24]。Loewenstein 和Gentner (2005)发现,那些获得主试提示目标物的方位(例如,我把这个奖杯放在箱子“上”/“里面”/“下面”)的学前儿童在空间任务中的表现比那些说些无关空间词的(我把奖状放在这里)的更好[25]。Dessalegn和Landau (2010)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复杂的空间匹配任务中,那些听到了描述方位的空间语言(例如,红色在左边)的四岁儿童,更倾向于去结合以及记住颜色和方位信息[26]。儿童能较早地在自己的语言中理解特殊的空间词汇的能力可能意味着儿童听到的空间语言从很早就开始调整儿童的空间认知。
(三)空间语言表达对空间认知的影响
Pruden,Levine和Huttenlocher(2011)的研究发现儿童在14个月和46个月时的自由游戏中空间词汇的产出数量可以预测他们在56个月时的不同领域的空间认知能力[27]。Hermer-Vazquez等人(2001)在与对“左”/“右”方位有关的空间任务中,5—6岁儿童能够说出特定空间词汇“左”和“右”可以帮助他们在任务中获得更好的成绩[28]。Simms和Gentne(2008)在与对“中间”有关的空间任务中,3—5岁儿童能够说出特定词汇“中间”可以帮助他们在任务中获得更好的成绩[29]。基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随着儿童使用空间词的经验的增加,他们在使用语言编码相关空间特征的表现会更好,这将提高其空间认知表现。
三、汉语儿童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研究
现有对汉语儿童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的研究,多集中在儿童方位词习得顺序的探讨上。张仁俊(1985)通过“被安放物”和“参照物”的实验任务考察儿童对空间方位词的理解和表达,结果发现儿童空间方位词的理解先于表达;空间词的习得顺序是:里、上、下、外、后、前、中、旁、左、右[30]。 孔令达(2002)依据儿童日常话语中的材料来描述儿童语言中方位词的发展面貌,并得出了儿童方位词发展的大致序列,与张仁俊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吴念阳(2014)聚焦儿童对维度词“高低”习得的先后顺序展开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儿童对空间维度词“高低”的先后习得顺序依次为“本体高”、“位置高”、“低”,即两岁儿童已经习得了“本体高”,四岁儿童习得“位置高”,而直到五岁他们才可以习得“低”[31]。有研究者依据儿童自由游戏的语料库对考察了儿童空间方位词表达能力的发展情况,研究发现幼儿能够使用所有类型的普通话空间方位词,使用频次最高的为“里”类,其次为“上”类[32]。
除上述有关方位词习得顺序的研究以外,目前国内对方位词的研究还有一个热点,即将方位词与儿童认知发展相联系,从心理认知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儿童的方位词习得问题。 王祥荣(2000)从垂直方位心理表征能力的角度对儿童掌握“上/下”类方位词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从句法和语义的角度描述了其发展过程,进而讨论了儿童“上/下”类方位词习得的机制和特点[33]。彭小红和李尤(2010)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两名1-3岁汉语儿童的方位词习得及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早期方位词的习得过程,他们认为幼儿方位词的习得受其早期认知能力、方位词的语义理解难度、语言输入频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34]。上述研究均强调汉语方位词习得与空间概念发展之间的关系,另外,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除了如上述研究那样从概念发展角度研究汉语空间方位词的习得以外,也有从方位词如何表达空间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如刘宁生(1994)从探讨语言如何表达物体空间关系的角度入手,讨论了汉语人群看待空间的特定方式并给予了认知解释[35]。
四、启示与展望
国内外的研究者对儿童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关系方面做了不少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的研究者更加关注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作用机制的探讨,有多种研究范式;国内关于汉语儿童空间词的研究更多的是通过个案或者借鉴国外心理实验的方法对某几类或者某几对空间方位词的理解与表达进行研究,对空间维度词的考察较少。
汉语空间语言无论从语义或语法上来说,与英语和其他语种有很大的差异,目前多数研究忽略同一空间词所表达的义项是不同的,只是做了笼统的论述。若仅将同一字形的方位词分为一类进行考察,容易忽视不同义项能反映不同概念发展水平的事实。如“上”类,在汉语表达中,“桌上有本书”和“上”及“墙上有幅画”的“上”义项均有所差异,“桌上有本书”的“上”表水平接触,“墙上有幅画”的“上”表表垂直附着,它们所表达的空间关系概念是不同的[32]。由此可见,现有研究模式并不能够全面反映儿童空间语言理解与表达的真实情况,对汉语儿童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的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