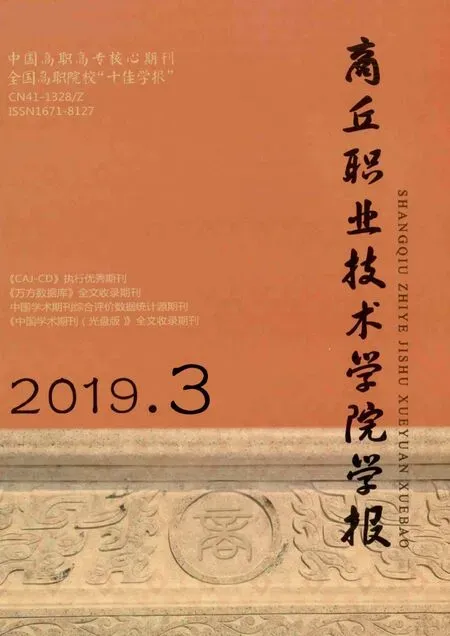《看不见的人》中间接的女性力量和艾里森的矛盾女性观
2019-02-20卫佳睿
卫佳睿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 1913-1994)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小说家之一,《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 1952)是其代表作。小说讲述一个不被看见的黑人男青年“我”在不断寻找被看见的过程,小说的开头与结尾相互照应,都是“我”回到一个封闭的空间。主人公“我”是历史这座巨型机器上毫不起眼的齿轮,齿轮离开了机器无法生活,而机器却可以有源源不断的齿轮来替代某个齿轮。在“我”寻找被看见的过程中,5位女性对“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针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国内外的关注点较少。最早关注《看不见的人》中两性区别的是西尔万德,她指出:“《看不见的人》中的黑人和白人女性都反映了美国白人男性所建立的被扭曲的刻板人物形象,”[1]并以艾里森本人在其论文集《影子与行动》中提到的“刻板人物”的定义,说明《看不见的人》是反对美国白人社会对黑人进行的“刻板”描绘,而女性的存在却是非人性化的和刻板的。斯坦福延续了西尔万德“刻板女性人物”的观点,并对这些人物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 “小说中黑人和白人女性都复制了描写女性的传统两分法——妇人或妓女,母亲或诱惑者。”[2]但她只是详细分析了玛丽这位人物的特征。刘晓洁沿用斯坦福的二分法,对5位女性人物进行了分类和解读[3]。许丽萍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4]。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拟在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这些女性在宗教、心灵和身份三方面所蕴含的力量对“我”的巨大的影响,并与艾里森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做对比,进而分析艾里森的矛盾女性观。
一、间接的女性力量
“我”把自己定义为看不见的人,一方面出于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另一方面为揭示黑人在美国白人文化中的地位。但“我”还是踏上了寻找身份的旅程,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最终是如何被看不见的。“我”经历过3次身份转变,这3次改变促使“我”不断向上爬,爬向别人能看见“我”的山顶。其间有5位女性在“我”3次身份转变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女性本身所隐藏的力量把“我”推向了寻找的高峰,转变了“我”寻找的方向,但最终却走向了深不见底的深渊。这5位女性角色影响了“我”的宗教观、心灵归属问题和身份建构与转变。
(一)“我”的宗教观
《看不见的人》创作历时5年,1952年完成,其间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覆灭后人们心灵、信仰和道德的崩溃与重建。1947年美国私刑迫害事件、种族问题愈演愈烈。一个致力于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对黑人却从没兑现过他们的诺言,黑人一直被排除在平等和博爱之外。美国内战结束后,“南方社会最大的变化是黑人奴隶身份地位的改变,奴隶制的废除使得将近400万的黑人奴隶获得了自由。自由的来临使许多的黑人相信上帝对黑人的拯救,认为这是上帝的仁爱与福音”[5]。解放后的黑人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宗教生活中,学习和阅读《圣经》,参与教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基督教已经融入美国黑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给予美国黑人希望和勇气,为无助的他们重燃生活的希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们精神造成的重创和美国私刑对黑人身体与心灵的毁灭动摇了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并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可以拯救他们。
小说通过一个老年妇女唱圣歌,反映出主人公矛盾的宗教观,即对上帝的怀疑。小说前言里“一个老年妇女在唱黑人圣歌”[6]9,这部分的字体是斜体字,从前后文的语境来看,该部分产生于“我”的想象。“我”通过听而超越现有的空间,进入一个想象的空间。在另一层空间的“我”与这位唱圣歌的黑人老妇女进行了实质性的交流。交谈内容涉及上帝:“‘孩子,我满心爱戴我的主人’她说道。‘你该恨他’我说。‘他给了我一个儿子,我爱这帮儿子,所以我虽然恨他,可我总得爱孩子的爹。’‘对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我也有体会,’我说。‘我此刻之所以在这儿出现,也就是因为这种矛盾的感情。’”[6]10-11。这段对话揭示出“我”精神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对上帝的矛盾心理。 “我急忙离开,听见老妇人还在低吟:‘诅咒你的上帝,孩子,然后就死去吧。’”[6]9。上帝本应拯救黑人兄弟于水深火热之中,但现实并没有。所以“我”代表黑人兄弟对上帝的存在和力量持怀疑态度。然而为了生存,“我”一直隐藏自己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只能通过和老妇人的对话表现出来。一个是怀疑,一个是坚信,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部分人仍然坚信上帝对黑人种群的拯救,但另一部分人质疑上帝的存在能否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此外,“我”对上帝的怀疑并未到此结束,与老妇人的对话唤起了一种类似答案的答案,指引了“我”对未来的寻找方向。在对话的后半段老妇人提到了“自由”,她用女性独有的细腻在“自由”和上帝之间形成一种比较,并表明他们两人都更爱“自由”,为后文奠定了寻求自由的基调。这位老妇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上帝比喻成儿子,把“我”精神中对上帝的矛盾心理和对自由的向往表达出来,把“我”从一个看不见的影子慢慢具化成一个实体。
(二)“我”的心灵回归
“我”是一个看不见的人,一直寻找不到自己的路。在大学里,遵纪守法,想要仿照布莱索博士,爬到高处,能够被人看见。布莱索博士是一名典型的黑人功利主义者,即通过攀附和奉承白人获取自己的利益。而“我”也照着布莱索博士的做法,巴结来参观学校的白人赞助者,以此作为爬高的阶梯。但“我”并没有做好,反而弄巧成拙。当“我”要被布莱索博士开除时,“我”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到不知往哪里走,心不知飘到了哪里,好像一切都是一场梦。“我”就要离开自己用命奋斗出来的上学机会。直到遇见唱诗班“瘦削的棕色姑娘”[6]116,她的声音和身体让“我”回归到出发的地方。这位女性是在布莱索博士找“我”谈话之前出现的,当时的“我”正在观察和叙述布莱索博士是如何走到现在的地位。叙述者只用了两个段落描写这位姑娘蕴含的力量。她的身体和歌声聚积着无法言说的悲伤。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到,在以菲勒斯语言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女性没有自己的语言,她们只有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语言:“它的肉体在讲真话,她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7]所以,这位姑娘用自己的身体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情感,尽管她还没有自己写作的机会。但是她的歌声让别人听到了,刺激了“我”的心灵。同时,歌声也给予“我”力量,让“我”想到曾经、父母和家乡。“我听不懂歌词的含意,但却能领略演唱时的那种凄楚、渺茫和超凡入圣的情绪。”[6]116姑娘的这种力量让“我”想到种种可怕的后果,包括父母的责备和不确定的未来。“这歌声,虽是眼前情景的一个有机部分,似乎有一种力量,比这情景更加咄咄逼人,于是我一下子被拉回到现实之中。”[6]117想到祖父的嘱咐,“我”决定直接面对未知的后果,尽自己努力继续往前走。
(三)“我”的身份转变
身份是“我”寻找的目标,目的是成为被看见的人。“我”从拳击场的受辱,大学时期的努力与奉承,到大城市纽约的奋斗,全部是为了能出人头地。但刚开始到纽约的“我”并没有什么机会,直到遇到了3位女性。她们用自己的女性力量为“我”的身份转变聚积了力量,点燃了导火索,最后找到了真正的意义,即自由。
玛丽·蓝博的关怀与言语为“我”的身份转变积聚了能量。正如斯坦福所言,玛丽是一种母亲式的形象。她不仅给“我”提供了安居之所,并且还能让“我”每天吃到热乎乎的饭菜。在“我”最落魄和无所事事的时候,玛丽给予“我”生活的希望。“我也不把玛丽当作‘朋友’看待;她不仅仅是朋友——她是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的、熟悉的力量,这力量像来自我的过去的某些东西,使我不致卷进我不敢正视的某种未知的境地中去。”[6]259玛丽对“我”的影响不只在这段特殊时期,她的力量和影响贯穿“我”今后的生活,让“我”能勇敢地去寻找一种改变。在纽约的这几个月,打破了“我”对现实与想象的界限。在以前,“我”尽量遵循别人的话,尤其是布莱索博士,但还是被他欺骗,被他所写的推荐信蒙蔽。在遇到玛丽之前,“我”在一个油漆工厂找到工作,却由于身体原因,无法胜任。我一直处于碌碌无为的状态。在靠着赔偿金度过艰难的日子时,玛丽时常提醒“我”,并且不断地督促“我”去做些事情以取得有新闻价值的成就。在玛丽的关怀和鼓励下, “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而这些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玛丽身上具有的女性力量,她不仅在生活上对“我”体贴入微,还在思想上激励“我”做一些事情。玛丽对“我”的影响是深远长久的,在“我”迷茫的时刻,玛丽的爱和力量充满“我”的内心,即使走投无路时,也是想着去玛丽家。“上玛丽家去,我只有这个念头,上玛丽家去。”[6]572
被白人赶出自己家的老太太是点燃“我”愤懑和身份发生质变转化的导火索。“我看见一群人面有愠色地朝一座房子看着,那儿有两个白人男子正在往外搬一张单人扶手椅,椅子里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正在用无力的拳头打他们。”[6]267事件开始时,这位老太太有两次直接面对“我”说:“只要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就够了。看一看就够了。”[6]268老太太的直视刺激了“我”。接着白人抢走了老太太的圣经,而且不允许她进房间内祈祷。白人的这些做法让围观群众奋起反抗,而当“我”在捡起抽屉里的东西,看到一张“自由身份证”[6]273时,想起了黑人的现实处境。这促使“我”在白人拔枪的时候走到黑人们面前,并说服他们用守法的方式与其进行对抗。这一行动标志着“我”被看见和被发现,为以后加入兄弟会埋下了伏笔。“而在整个过程中,那位年老的女性一直发出刺心的叫喊。”[6]271老太太的女性力量在无形之中刺激着“我”心底里潜藏的愤怒和不满,点燃“我”内心不断翻腾的火焰,从而使“我”在人群之中脱颖而出,寻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西比尔,一位白人已婚妇女,小说中她作为自由的化身触动了“我”的反叛和对自由的寻找。刘晓洁借用Stanford的两分法,把西比尔定义为诱惑者。但笔者认为西比尔对“我”来说是最后的醒悟和解脱。她其实是自由的化身,肆无忌惮地释放自己,用酒精和性爱麻痹自己以逃避现实。“我”接触西比尔是想学习赖因哈特,试图通过女性来获得兄弟会的内部情报。当“我”戴上墨镜时,人们把“我”认成赖因哈特,而“我”借此想象赖因哈特是怎样的人,并且把自己化身为赖因哈特,为获得情报而接近西比尔。但西比尔刺激了“我”对女性的同情和怜悯以及对自由的意义的寻找。尤其是在“我”送她走后,她又出现了。“她等在一座街灯下向我招手。我丝毫不感到奇怪;我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我慢慢走近时听到她在笑。她在我前面跑了起来,光着双脚,悠悠然地仿佛在梦中一般跑。东倒西歪,但是很敏捷。”[6]539-540这时的西比尔与第一位老年妇女所向往的“自由”形成了呼应,把“我”对女性的印象混杂在一起。西比尔给予“我”的力量不同于前几位女性,她让“我”把对女性的鄙视、厌恶、愧疚和同情等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带给“我”一种沉重感,使得“我”对兄弟会和整个社会彻底失望。她让“我”更加确定自己是看不见的人,一位无名的黑人而已。
这5位女性所赋予“我”的女性力量,让“我”想起了家人的嘱咐和初心,刺激了“我”一次次的身份转变。正如有学者说:“黑人女性形象在必要时可以为了黑人男性做出牺牲,为整个黑人所谓的黑人民族性付出全部的努力,而同时隐藏她们的自我和个体需求。”[8]142这5位女性就是这样的形象,为黑人而埋藏了自己。所以,这些女性所隐藏的特有的女性特质带给“我”力量,在“我”寻找身份的路上起到关键的作用。
二、艾里森的矛盾女性观
5位女性自身的力量无法直接改变黑人的现状,而是以“我”为中间者,或者说通过男性本身的性别优势,为黑人种群性运动发挥自己的微薄之力。但艾丽森对这些女性的片面描述又夸大了她们的缺点和劣势,揭示了作者的矛盾女性观。
文中所描述的女性力量并不能直接对外界产生任何作用,而是通过“我”的改变来显示,即这些力量是在“我”身上发挥作用。因为父权社会的压制,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而黑人女性又受到白人女性的抵制,其地位更是处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她们是男性的附属品,只能通过男性寻求自身在社会上的位置。例如,玛丽经常对“我”说:“只有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改变这个世道了,你们得带头,得斗争,使我们大家多少提高一点。”[6]255-256从中可以看出,玛丽作为女性的无能为力,她们只能在年轻男性的带领下,为自身和自己的种群争取平等的权利。而且无论是黑人老妇女还是跳舞的棕色女孩,她们都无法直接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她们的声音和动作只能选择性地被男性听见和体会。所以,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所起的作用永远是被动的,并受到种种限制,特别是黑人女性。而“我”在小说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女性的力量成为“我”的行动动力,刺激“我”不断寻求新身份,为改变黑人的现实境遇做出一些努力。
然而,这些女性形象在“我”心中却是不完整的。文中所论述的5位女性,只有玛丽和西比尔拥有自己的姓名,前面3位却无名无姓,只是“我”根据她们的特征给她们贴上相应的标签。第一位是“我”想象中唱黑人圣歌的老妇人,所以对她的描述仅仅停留在声音上面,一是她唱的歌,二是与“我”的对话。缺少对其具体面貌和表情的描述。第二位是唱诗班的棕色姑娘,她也是通过歌声和身体带给“我”无穷的力量,对她的长相和经历亦无从得知。第三位是被赶出家的老太太,她的叫喊、眼神和行为点燃“我”心中的火焰,但“我”并没有去描述其悲伤和愤懑的心理状态。玛丽和西比尔虽然有姓名,但是对她们的描述却仍然是片面的。玛丽第一次出现的形象是“那个大块头黑女人用沙哑的女低音”[6]253,还有“看着她那粗糙的褐色的手指拿着那只亮晶晶的玻璃杯”[6]253,而且其言行始终体现其对男性的依赖。西比尔对“我”的印象类似于色情狂,即使现在美貌依旧,但“她马上就会身材粗壮,有一个小小的双下巴,腰腹部得勒上三层紧身褟。……但是我同时越来越发觉她身上有一种女性美,暖洋洋的”[6]527。可以看出,文中的女性尽管各自拥有其独特的力量,但艾里森却没有全面完整地刻画任何一个女性形象。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男作家文本中的黑人妇女老套形象的刻画是文学上‘厌女症’的表现,这些文本并没有抓住黑人妇女的真实形象……尽管有些形象似乎是正面的,但黑人妇女不论以怎样的面貌出现,民族主义文学都没能刻画出黑人妇女的多重性格特点”[8]141。所以,艾里森虽然致力于跳出黑人的圈子,融合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学价值,但是对于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艾里森的观点依然是按照传统男作家对女性的刻板认识,女性是男作家们烘托男性优势的背景材料。但同时,艾里森也认识到这些女性所拥有的独特的女性力量。艾里森的矛盾女性观,表明了黑人男作家在逐渐打破性别的界限,并试图为黑人同胞寻找出路的努力与尝试。
三、结语
“我”在自我身份追寻的过程中离不开女性无形之中的力量,小说中的5位女性以女性独有的魅力和优势支持“我”在跌倒之后爬起来继续寻找自己的出路。而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片面描述反映其矛盾女性观。这既体现了艾里森对女性价值的认同及对女性现实遭遇的同情,又打破了黑人男作家固有的偏见,表明黑人男作家也在努力超越性别差异,为黑人种群的共同利益所做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