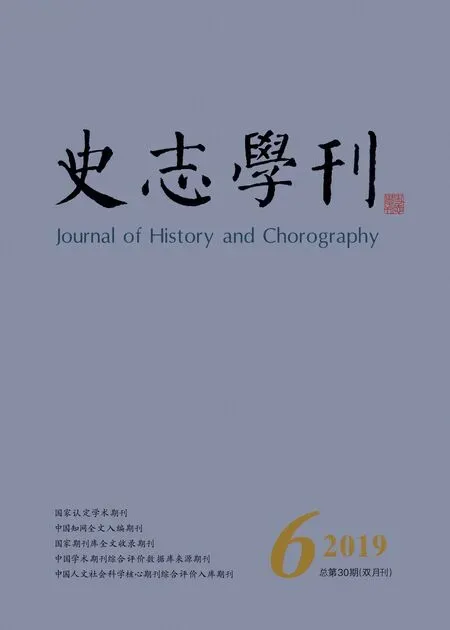古代草原丝路贸易流动性探梳
2019-02-20马晓娟
马晓娟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与社会学学院,乌鲁木齐 830017)
丝路学是当下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其中所包括的草原丝路及其贸易研究则颇为丰富。但是关于草原丝路贸易流动性,目前还无专文考察。正基于此,本文对此问题做了尝试性的综合探讨与梳理,以期对相关问题作以补充与丰富。
从实际考察来看,比起绿洲丝路相对固定的路线与站点,草原较为空旷的大漠、草场与森林区则决定了草原丝路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上的路线,以及人文族群间势力范围变动性较大,体现出了较强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也正是草原丝路贸易一个显著特点。由于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的差异,农耕区的物资比之草原区要丰富得多,故农牧贸易是草原丝路贸易一个最基本的支撑点。草原丝路贸易流动性具体实质也主要展现于此。
一、贸易对冲区的变动性
翻阅千年历史记载来看,农牧间贸易是在交往博弈中而进行的。故农牧对冲区或者说政治力量交界区的变动性,首先就是草原丝路贸易的变动性第一个实质体现。其主要表现于两个方向上的对冲区及变化。
1.南北对冲区的起伏。
历史上的南北对冲区分界线,既有草原内部的,也有南北农牧间的。但是游牧群体本身所产物资因有太多相类性,因此草原贸易最大对象还是农耕区物资。故这里主要来谈谈农牧间的对冲区。二者间最主要的体现是长城,它也是农牧分界线。正如西汉时汉文帝给匈奴冒顿单于的信中所言:“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902)依据文献看,先秦与游牧族群相邻的中原诸侯国均在边界区建立了长城,如史所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卻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885-2886)由此看出,各诸侯国不仅建立了长城,而且在长城一线还设置了郡县,起到“卫城”与“拒胡”之效应。当然,这些长城一线郡县也成为农牧经贸交流的最前沿地区。但是这种分界线随着时代发展是变化的。秦统一六国后,在原有诸国北部长城基础上不仅做了连接,也新修了不少长城,这一新形成的长城,即万里长城,成为秦与北部游牧族群的分界线。从东到西,这一北部长城大致经历了当时的辽东郡、辽西郡、渔阳郡、上谷郡、云中郡、九原郡。比对今天,大致经历的地区是丹东、沈阳、呼和浩特、兰州一线。比较战国时代北部所修长城位置,秦时所修北部长城已经是大幅度北移了。其原因,一如《史记》云:“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886)同时“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卻匈奴七百余里”[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80)。因秦原本就处于诸侯国西部,故北移中西北部长城所推动的幅度最大[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3-4《秦时期全图》).地图出版社,1982.。正如《史记》所言: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53)。这说明秦朝比之战国时代,农牧贸易分界线也做了向北、向西延伸。但是这一农牧交界线,在秦汉之际随着南北人文政治实体的变迁,也发生了变化。若《史记》载:“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887-2888)冒顿单于兴盛后,“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郉、肤施,遂侵燕、代。”[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890)而当时中原正处于楚汉之争,故历史上所修长城并非是固定的。各代都有修长城之记载,如描述北魏时期的记载:“八年春,筑长城,距五原二千余里,置守卒,以备蠕蠕。”[3](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P2400)这是北魏抵制北部柔然之举。北朝末与隋朝时,北距突厥而修的长城记载,如史云:“显祖亲御六军,北攘突厥,仍诏斐监筑长城。”[4](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P554)隋炀帝时“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5](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P70)直到近代时,中国境内还留有这样的遗迹,如《清史稿·内蒙古志》载:“东界吉林、黑龙江,西界厄鲁特,南界盛京、直隶、山西、陕西、甘肃,五省并以长城为限。北外蒙古。”[6]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P2396)纵观历代文献,虽然长城成为农牧分界线标示性建筑,但从来没有真正阻挡住过农牧之间的往来。从历史长河来看,这一农牧分界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也是处于南北浮动当中。当然,这分界线同时作为农牧交易的对冲区,也是处在南北起伏流动当中。从文献来看,这一分界线的缘边贸易历代多有记载,如史载:汉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904)。甚至汉武帝与匈奴交恶初期时,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905)。北魏时期,如《魏书》载:“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国,其人大饥,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请台赈给。诏孚为北道行台,诣彼赈恤。孚陈便宜,表曰:……贸迁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汉与胡通,亦立关市。今北人阻饥,命悬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3](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P424-425)这是柔然与北魏缘边的交易。突厥与隋朝的缘边贸易,如《隋书》载:“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3](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P1871)突厥与唐时的缘边互市记载,如《旧唐书》云:“十五年,小杀使其大臣梅录啜来朝,献名马三十匹……上嘉其诚,引梅录啜宴于紫宸殿,厚加赏赉,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P5177)除了正常的贸易,长城缘边也时常成为游牧者对农耕区非正常的物资掠夺区。这类记载也不绝于史。如《后汉书》载:“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会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P2949)《后汉书》云:“五年,鲜卑寇幽州。六年夏,鲜卑寇三边。”[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P2990)《隋书》云:“后数载,突厥寇边。”[2](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P60)
上述无论是何种性质的贸易,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农牧贸易程度,包括数量、内容、频率,都是由北向南逐渐减弱。这则体现了南北贸易“由粗到细”或者说由密集到稀疏的流线性特点。这一流线性随着时代发展,同样处于南北对冲区的起伏当中,东西方向也不例外。
2.东西对冲区的伸缩。
南北有长城作为对冲区,东西方向也有。当然,有些地段是以山川为界限的。因为东部面临大海,所以农牧东西方向对冲区,主要体现于西部。西部对冲区的影响也远大于东部,史书对此也多有反映。依据古文献与历史地图,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点。秦、汉西部就有着巨大的差异。一如《汉书》所载:“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3](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3872)到汉武帝张骞始开西域后,匈奴右地浑邪、休屠王(降汉),“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3](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3873)向西的发展,也造就了农牧的交汇,若《汉书》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3](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P1644-1645)
比之南北对冲区,东西对冲区也尤其显现于草原内部。当然,草原内部东西对冲区并没有长城为界限,只是势力范围的东西伸缩。因为东西方向发展,不仅意味着草原内部贸易,也意味着草原所获南部农耕区物资的东西交流,以及在东西部较远的农耕区所获物资的相向流动。结合地理环境与文献看,一个草原势力的兴盛,首先表现的就是向南推进与东西拓展。东西拓展就意味着东西对冲区的大流动。如《史记》云:匈奴冒顿单于时“东袭击东胡……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4](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889-2890)。这之后在西部有了进一步拓展,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夸耀到:“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4](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896)这意味着草原原有东西对冲区的解体,新区域的建立。这一举动不仅意味着冒顿单于统治下的匈奴掌控了更多草原东西贸易权,也意味着东西贸易线路的拓展。这在后来突厥、契丹、蒙古先后崛起于北方草原之时均有展示。
从经济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农耕区与草原东西对冲区贸易,还是中国北方草原内部东西贸易。整体来说,都是由两边向中心减弱。这是贸易里距、时间与成本决定的。以中国农耕区的西部草原对冲区贸易区来说,就是由西向东逐渐减弱。这在《明史·西域传》中有体现,如其言:“洪武中……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帝不许,令赴京鬻之。”[5](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P8598)这说明东西与南北对冲区贸易类似,草原贸易都是先缘边互市再深入内地。因为贸易里距越长,意味着成本越高,风险也越大。除非,长距离后的利益远大于缘边贸易,如官方的贡赐贸易就是如此。《三国志·仓慈传》对此有展现,如其载:“太和中,迁燉煌太守。郡在西陲……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贸迁……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1](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P512)不难看出,这些西域人的敦煌贸易是西部缘边贸易,若能在这里获得既得利益,就会停止向东去贸易;若此地得不到既定利益,就会远赴京师获取贡赐贸易。这说明缘边贸易是第一波贸易。
古代的缘边贸易发展到近代,表现的就是边境贸易或者说国境贸易,因为真正的国家概念与定型产生于近代。这在《清史稿》有清晰的展示,如其载:“雍正五年秋九月,与俄订《恰克图互市界约》十一条……喀尔喀北界,自楚库河以西,沿布尔固特山至博移沙岭为两国边境,而互市于恰克图。”[2]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P4483-4484)具体地点、贸易路线及管理等,如所云:“互市处在恰克图南买卖城,有路南通库伦,北达上乌丁斯克,与新修铁路接。有俄国领事署。贸易茶最盛。车臣汗、土谢图汗两部事亦归监理。”[2]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P2439)这是一个平等的互市贸易体现。
历史上,除了缘边贸易,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较强贸易区则是政治中心贸易。
二、贸易中心区的流动性
在古代,政治中心也往往决定着经济中心。因为经济实力是政治实力的保障与基础,所以一个政治中心通常也是经贸中心。但是,这一中心区也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草原贸易流动性的第二个表现正是这个贸易中心区的变动。它包括两方面。
1.草原掌舵族群中心区域的流动。
虽然,草原游牧生活处于流动当中,但是这种流动性是具有相对性的。因为族群属部都具有相对的势力范围,所以一般性的流动,也是处于一个相对的范围内。同样,掌控草原的政治中心区也是一个相对稳定区,如王庭所在地。这个王庭所在地,就是草原贸易中心区,或者说贸易集散地。贸易既有自觉自愿的,也有强迫非情愿的。后者最大表现就是,每年属部定期向政治中心区王庭所交的实物与非实物赋税。这是最高政治统治者的权力体现。当然,作为最高统治者,在获得这些“赋税”以及从其他区域或人群获得财物后,除了自己享用与对外贸易外,也会相应的拿出一部分分配给属下,但会有等级差异。这也是维护统治一个重要手段。这可视为是一种上、下的官方“贸易”。史书也多有记载,纳赋税的,如《史记·匈奴列传》:“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3](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2892)在属部的上下关系中,也是如此,若《汉书·西域传》云:“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3](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3874)若不能交赋税的,就会受到惩罚。如《汉书·匈奴传》载,乌桓需“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乌桓距曰:‘奉天子诏条,不当予匈奴税。’匈奴使怒,收乌桓酋豪,缚到悬之。酋豪昆弟怒,共杀匈奴使及其官属,收略妇女马牛。单于闻之,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责杀使者,因攻击之……颇杀人民,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见略者亲属二千余人持财畜往赎,匈奴受,留不遣”[3](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3820)。可见,匈奴对属部乌桓的拒不交皮布税与反叛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不惜用武力逼其就范。当然,正常情况下,如前述最高统治者获得相应财物后也会分配给部下。一个部落内部也实行这样的操作。如《旧唐书》谈及西域突骑施苏禄时云:“有所克获,尽分与将士及诸部落。”[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P6068)若一个首领不能很好执行向下分配,就会出现属部离心离德,甚至是反叛的举动,亦如上引同传之内容:苏禄“先既不为积贮,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其下诸部,心始携贰。有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落,最为强盛……莫贺达干勒兵夜攻苏禄,杀之”[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P6068)。唐初突厥吉利可汗被众叛亲离,也有类似原因。这是造成政治统治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旦解体,草原政治中心区会相继变化,贸易中心区也会出现变化。故结合历代史书与历史地图册来看,草原政治经济贸易中心区,即王庭所在地,也会随着人文变迁而处于一种变化当中。从长时段看,表现出的就是一种流动性。若东汉、三国时的单于庭比之西汉时期,就向西迁移了[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13-14《西汉时期全国图》、40-41《东汉时期全国图》与第三册3-4《三国时期全国图》).地图出版社,1982.,这是缘于匈奴实力的衰弱与东北鲜卑势力的向西发展。与此同时,鲜卑也向南部发展,故而鲜卑庭也向南推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部草原最大两个争雄的族群掌舵者是柔然和高车,二者间的政治中心也在博弈中出现了大移动。突厥兴起后,草原政治中心又掌控于它之手。突厥衰落后,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崛起,使得草原政治经贸中心或者说贸易集散地,从纵向历史角度来看,处于变动或者说流动当中。作为贸易交换的主要对象农耕区,也是如此。
2.农耕区政治中心的变动。
草原贸易一个支撑点源于农耕区物资,其中贡赐贸易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贡赐贸易大部分发生在农耕区政治经济中心,故这个中心的变动也体现着草原贸易的变动性。这个中心,最大体现者就是朝都,即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京师。若东汉、三国曹魏京师所在地洛阳比之西汉京师长安就向东迁移了。这样草原族群向南部的贡赐贸易也会在地点上发生转移。而到魏晋南北朝,这一中心发生了分化,也意味着贡赐贸易的多向流动。若当时的柔然同北朝政治中心有贡赐贸易与南朝政治中心也有贡赐贸易。如《魏书·蠕蠕传》云:延和三年二月“吴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来朝,献马二千匹,世祖大悦,班赐甚厚”[3](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P2294)。这是柔然与都城在平城时的北魏贡赐贸易。又如《宋书·文帝纪》云:“芮芮国遣使献方物。”[4](南朝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P89)这是柔然与南朝宋(建康)的贡赐贸易。当北魏孝文帝改革后,都城从平城迁移到了洛阳,也意味着政治经贸中心向南迁移了。无疑,贡赐贸易中心也会随之南迁。
总的来说,在农耕区统一时期,贡赐贸易大多数是流向一个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分裂时期,农牧贡赐贸易会发散性的向多个政治权力中心流动。
故无论是草原政治中心区,还是农耕政治中心区变动,都会带动草原上、下贸易及与农耕区贸易的大流动。贸易中心在流动,同样贸易辐射区也会流动。
三、贸易辐射区的流动性
贸易中心区周边就是贸易辐射区,政治中心区周边就是隶属或者说属部区。前后两者一般来说,在古代是一一对应的。随着人文群体力量的消长,政治经贸中心区会发生变动,其周边的政治经济辐射区,即下属或者说属部区也会发生变动。从长时段来看,这一相对中心区的贸易辐射区也处在一种流动性当中。这主要表现为这样两方面。
1.草原内部贸易东、西、南、北相向、相反流动。
这方面就是上文所点到的,每年政治辐射区属部会向所属汗庭纳赋,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土特物产。这一举动,表现出的就是物资的“汇流”,或者说东、西、南、北属部向汗庭贸易集散地中心原点汇聚物资的展现。物资体现的是相向流动。当然,作为最高统治者在接收到各种物资后,除了自用与对外贸易外,也会向属下以馈赠方式,给予分配。这一行为,反映出的是物资的“回流”,或者说汗庭贸易集散地中心原点向周边属部散播物资之举。这时的物资流动表现的是反向流动。这一“汇”一“回”就体现出了上、下的“贸易”往来。当然,其中的贸易不平衡,甚至是不平等是显而易知的。但这也正体现了辐射区与中心区的政治、经济地位之差异。但是,辐射区并不意味着是固定不变的。
2.草原内部势力变迁所引起的辐射区变动。
如上所言,草原政治势力的消长,会带来政治中心区的变动。同样,力量的消长博弈也会带来辐射区的变动。一个最高政治中心,就是一个最大贸易集散地,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强盛时期,这样周边辐射区针对的是一个中心。但是当一个政治中心衰落时,属部或者说原有辐射区力量就会逐渐变大,进而出现多个政治中心或者说贸易集散地。当多个政治中心在博弈时,辐射区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动,甚至有些小部落,或者说力量薄弱者,成为两个政治中心区的辐射区,历史上称之为“两属之”。《史记·大宛列传》云:康居“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P3161)这是典型的“两属”现象,是一个处于两大政治势力间小势力的不得已之选择。若东汉时,匈奴衰落,形成南北匈奴的格局,此时鲜卑、乌桓兴起。三国至南北朝时,鲜卑南下,草原柔然、高车相继兴起。当柔然衰落时,其属部突厥兴起。当突厥衰落时,回纥、突骑施、葛逻禄又迭起。当回纥衰落时,契丹又大范围兴起。后继女真、蒙古草原势力,都有类似发展轨迹。故每个掌舵族群衰落时,也意味草原内部势力的变迁,进而也引起了辐射区的变动。无疑,官方性的上、下贸易,在区域间也会发生重大的流动性变迁。同样,贸易中心的辐射区变动也会带动物品流向性变动。
综上,草原生活的流动性是导致草原丝路贸易流动性的直接性因素,若把历史变迁放入其中又增强了其时空维度中的变动性。而历史变迁中人文群体政治势力的变动性,使这一流动性充满了更多变数。但是,不变的是多种形式的人文贸易或者说物产交流,无论是在草原游牧群体自身间,还是农牧间,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