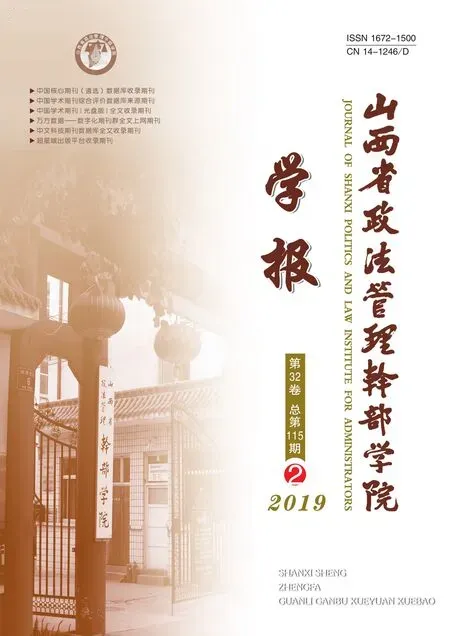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李斯特鸿沟的解决——以陆勇案为视角的刑事政策当代考量
2019-02-19张馨文
张馨文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之关系分析
在晚近以来中国刑法学的研究中,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关系的话题正日益引起关注。[1]在日益引起关注的同时,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凸显出来,如何解决这种紧张关系是当前中国法治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分析
刑事政策是指一个国家应对犯罪所采用的全部方针和策略。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的性质截然不同,刑法规范作为成文的、明晰的法律文件具有较高程度的稳定性与权威性;而刑事政策则是作为一种国家的政治部署出现的,这使得刑事政策自其诞生之时就具有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色彩,而并非价值中立,其承载的是统治阶级对于社会安定与犯罪治理的强烈的价值取向。我国学者卢建平提出了刑事政治的概念,认为刑事政策就是治国之道,刑事政策其实应该翻译成刑事政治,而犯罪问题从来就应该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他指出:“只有将刑事政策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才有可能考虑市民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双本位的二元犯罪控制模式的实现才是可能的,国家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综合治理的政策特色才能充分显示出来,作为‘治道’的刑事政策的本色也才能得到完全的展示”。[2]然而,刑事政策的这种政治色彩恰恰是刑法规范所要剔除的,科学完备的刑法规范追求其自身的体系逻辑、理论根基,而非是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刑事政策必须与一国的政治生态、社会需求、犯罪现状相适应,同时,还要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
通过对刑事政策的概念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一个国家的犯罪治理而言,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二者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却必不可少。正如陈兴良教授所指出的:“完美无瑕的法律是不存在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法有限,情无穷’之说,它深刻地揭示了法的有限性与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3]中国的法律传统并不缺少法内容情的考量,因而在中国当代刑法理论的发展中较为强调的是剔除法中情的因素,让法律更加理性、科学和中立,但是对于刑法规范的科学研究却也因此滑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对于刑法的社会效果的考量正在大幅消减,这一点在陆勇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沅江警方对于陆勇行为的界定刻板地停留在对法条严格解释的层面,虽然我们强调司法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行事,而不能被与案件事实无关的其他因素所干扰,但是如果考虑到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对陆勇所触犯的罪名进行实质解释,就自然能得出无罪的结论。陆勇的拘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刑事政策虽然与刑法规范一样并驾齐驱治理犯罪,但是在刑事司法实务中,刑事政策往往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即刑事政策难以作用于刑法规范这一具有强制力和有效性的法律文件,因而刑事政策在当前中国的司法环境中只能发挥微薄的作用。关于这种尴尬境地,德国学者李斯特在其《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就已经提出了,陆勇案的发生只不过是对这一论断的现实影射而已。
(二)陆勇案中刑事政策的弱势与刑法规范的强势
刑法规范与刑事政策的分立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矛盾,首当其冲的就是刑法规范的体系性与刑事政策个案性难以兼顾的矛盾,陆勇案集中体现出这种矛盾。对于陆勇行为的认定,从刑法规范的严格意义上以及刑事政策的目的解释上来看,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由于我国目前司法的僵化,导致司法人员机械地信赖理论上的概念,而忽视了案件的特殊性。陆勇案虽然最终没有进入到刑事审判阶段,但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对于陆勇行为的认定在本案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还有很多诸如陆勇这样的代购仿制药的人已经被定罪判刑。对于陆勇触犯“销售假药罪”行为的认定,侦查人员显然采取的是严格解释的方法,将陆勇代购的行为或是居中联络的行为认定为是“销售行为”,但是对“销售”这一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时就可以发现,陆勇自身作为病人只是起到了居中联系的作用,其并非以营利为目的,也未承认过对印度药厂进行代理,因此,陆勇的行为达不到“销售”的标准。其次,对于“假药”的认定,侦查人员同样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中对于假药的罗列将确有疗效的印度仿制药认定为假药,若考虑到案件的实际情况,以及这一罪名设立的目的,就不会认为印度仿制药属于假药的范畴。销售假药罪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这一罪名之所以设置成抽象危险犯,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公众的权益,虽然该罪删去了“足以造成人员伤亡”这一危险设定,但是如果自始至终不会对公众的生命健康权造成危险,那么这样的行为不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然而,侦查人员最初并不是依照刑法目的价值进行判断的。
陆勇案集中体现出了在中国刑事司法实务中刑法适用的僵化以及刑事政策作用的薄弱,虽然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是以刑事政策为主导,但是由于前期刑事政策对于司法公正的冲击极强,导致了在依法治国理念下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使得中国当前的司法现状从恣意走向了僵化。
二、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解决路径
(一)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概念分析
未经解释的刑法规范无法适用,因此,刑法解释是审理与分析案件的核心所在。针对某些情况,刑法当然具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刑法规范并不能直接作为逻辑推理的大前提,而是需要经过解释才能与案件事实相契合,这些条款被陈兴良教授称之为“隐形条款”,[4]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就是以这些隐形刑法规范为基础,将外部社会的目标追求、社会决策需要、社会发展变化等因素考虑到解释中来,从而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基础上兼顾社会实效。由于这种刑法解释方法考虑到其承载的任务——社会效果、利益衡量、价值判断等功能性作用,具有功利主义倾向,因而被称之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
我们仍然以陆勇案为蓝本进行分析,如果对陆勇的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进行简单僵化的文义解释,那么刑事政策的精神无法涵射其中。如果对这些刑法条文进行功能主义解释,结果就会豁然开朗起来。以陆勇所触犯的销售假药罪为例,首先是对“销售”这一构成要件的解释,如果从字面含义来理解,销售是一种有偿转让的行为,类似其他罪名中的“贩卖”“出售”等含义,这意味着在本罪中只处罚卖出的行为,而不处罚购买的行为。解释者应该严格按照日常生活中用语的含义进行解释,因为刑法具有指导公民去实施合法行为的功能,这一功能决定了刑法必须以日常含义作为解释构成要件的底线,而不能超越这一底线,否则就会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因此,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要求中,购买行为不能被解释成为是销售行为。有鉴于此,陆勇作为慢粒白血病人其从印度药厂购买仿制药的行为不能被归入销售行为中,否则刑法中所有的销售都包含了购买行为,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退一步说,陆勇虽然实施了居中联络的行为,但是他并非代理,也没有从居间行为中谋取利益。综上,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进行刑法解释时就可以得出陆勇无罪的结论,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自然地将刑事政策所推崇的理念融入到刑法规范中。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之所以可以将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结合起来,是因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自身兼具了刑法规范要求与刑事政策要求双重要求。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归根结底是一种解释,因此,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不能超出文义可能的“射程”,从这一点来看,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符合刑法规范的要求;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在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包含了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这样的功能性作用,这样的目标追求可以与刑事政策相结合,使得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刑事政策的司法化。
(二)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的解决路径
1.彰显刑法的终极价值。刑法的终极价值在于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刑事司法中对某一行为进行出罪入罪研究中自然也不能违背刑法这一终极价值。陆勇案的不起诉决定深刻体现了检察人员在权衡过程中对于刑法这一终极价值的彰显。陆勇代购印度仿制药的行为并没有任何危害他人生命健康的危险,相反这样的仿制药还可以治病救人,并且在高昂的正版药给患者带来巨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这样的仿制药可谓是“救命药”。因此,陆勇的行为不具有法益侵害性,对陆勇作无罪处理,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白血病人的合法权益以及陆勇本人的人权。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可以保障在刑法规范适用过程中始终坚持刑法的价值要求,而不会因为严格按照规定造成误入歧途的危险。严格解释固然坚守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但是这样的僵化司法难以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其虽然可以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但是却无法彰显审判对社会的真正推动和净化作用。
2.凸显刑法的实质内涵。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实质解释,实质解释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限度,超越这一原则的实质解释就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类推解释。因此,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也是在这一限制中讨论的。实质内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我们对案件事实所适用的法条争执不下时,或是当我们死抠法条文本字眼仍然难寻出路时,亦或是当我们发现法条规定无法坚守正义时,实质解释可以让我们重新挖掘出刑法的真谛,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正是用来解决这样的疑难问题。当前,我国刑法学方兴未艾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可谓处在传统刑法解释论与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之争的延长线上。对于陆勇案整体的审视应当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判断而不能停留在形式判断上。对于某些案件来说,形式解释或许可以得出与实质解释近似的结论,但是对于像陆勇案这样的特殊案件,或是有很大解释空间的案件来说,实质解释可以在关键环节坚守刑法维护正义的目标,使得陆勇的行为从刑法认定和道德评价两个角度中得出相近似的结论,满足社会大众对于刑法原有的期待,同时也体现出刑法的实质内涵,维持立法者的本意。
3.落实刑法的预防目的。刑法规范兼具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具体到陆勇案的处理上,一般预防指的是让社会公众不去做触犯刑法规定的行为。如果陆勇代购印度仿制药的行为是犯罪行为,那么这样的有罪认定是否可以促使社会公众不去实施这一行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代购印度仿制药的行为已经成为了部分病人的唯一选择,在利益权衡下,即触犯刑法与治病活命来权衡,大部分人会选择治病活命。事实上,刑法应当是保障人权的法律,而不应该将人们置于上述两难境地。如果是因为刑法的制度设置使得公众面临两难选择,那么这样的刑法显然是不合时宜应当予以修改的。特殊预防是针对犯罪人本身而言的,即防止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如果将陆勇定罪量刑是否可以避免其不去实施“犯罪行为”呢?可能在服刑期间陆勇很难再进行代购仿制药的行为,但是一旦重回社会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因此,从刑法预防角度来考量,对陆勇施加刑罚是不必要的。
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的理论优势
前文论证了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连接刑法规范与刑事政策的重要作用,如果深入到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内部来分析,则可以明晰其特有的理论优势。这些优势区别于传统的刑法解释学,将刑法中关于社会学、犯罪学的研究纳入其中,形成了一种多学科交叉、多因素衡量的与社会现状相适应的刑法解释学。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是一种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之所以能不断发展是因为其能有效解决司法中面临的诸多疑难问题。
(一)兼具目的导向性与实质解释性
目的导向与实质解释是相伴而生的,实质解释首先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解释,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相较于普通的实质解释而言又多了目的导向性。以目的为中心的解释论要求,“法律适用上应取向于储藏于法律概念或规定之目的、价值,在法律适用上主要表现在注重法律规定之目的,亦即其所欲保护之目的,或欲实现之政策,或所立基之法律原则。”[5]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学中,目的解释处于核心位置,并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功能主义刑法学在陆勇案中的作用就在于这种目的导向性,在陆勇案不起诉决定的释法说理书中有这样的论述:“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释法说理书指出这一价值观就是司法为民价值观。由此可见,虽然对于陆勇不起诉的判断完全依照现有法律规定而进行,但是在进行方向取舍时却带有很大的价值判断色彩。或许刑法可以完全将这种价值色彩排除在外,由其本身的逻辑推理和体系的自洽而建构出来,但是司法却无法避免价值判断,甚至司法要有温度,要考虑到为民服务的大背景。因此,司法必须要具有成型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虽然是司法人员自由心证的过程,是根据司法人员自身的经验、理性、知识做出的判断,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对这样的自由加以限制,那就是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这样的解释方法所具有的目的导向性使得司法人员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不会偏离刑事政策的要求。
(二)兼具后果取向性与社会回应性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在解释之前事先考虑作出这样解释的后果与社会影响,以此来判断解释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这就为恣意解释与僵化解释设立了一个底线。具体到陆勇案而言,当陆勇被刑事拘留之后,社会反响强烈,许多慢粒白血病人自发聚集在一起联名请愿,司法人员在处理这样一个刑事案件时必然会考虑到一系列的社会事件以及所带来的后果。一旦将陆勇定罪处刑,所带来的后果是:印度仿制药在国内绝迹,经济困难的白血病人难以得到救治,民怨沸腾,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加剧了犯罪的风险。基于这种恶性后果的考量,在运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时就应尽可能寻找出罪的根据。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于社会的回应性也是极强的,但是这种回应并非是传统中“以民意来断案”的体现,而是在依法治国大背景的要求下,从法律条文中寻找回应社会呼声的内涵。因而,将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可以有效解决刑事政策在具体适用过程中的乏力,并且给稳定的刑法规范注入源源不断的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