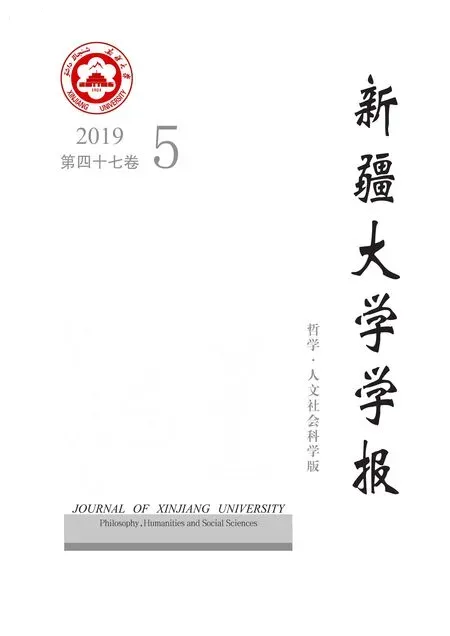伊恩·麦克尤恩小说《黑犬》中的欧洲危机和复调叙事*
2019-02-19王丽云于丽萍
王丽云,刘 巍,于丽萍
(1.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2.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在当代的英国文坛,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与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和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齐名,是英国当代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不仅如此,批评界还常把他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相提并论,因为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都专注于探讨人的本性问题,而且都善于将这个抽象的哲学命题在孩子身上具象化。1978年,伊恩·麦克尤恩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伊恩·麦克尤恩更是藉此被评论界视为贝克特和卡夫卡的文学继承人。1992年,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黑犬》出版,这是一部继承了英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黑色幽默的哲学寓言。在英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上,伊恩·麦克尤恩承继了英国文学的传统,对英国小说在当代的复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黑犬》涉及了宏大的社会主题:战争和文化(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麦克尤恩先是架构了一个回忆录式的框架,然后采用复调叙事从不同的视点切入,多角度展示战争和文化问题。小说由前言和四个各自独立的主体组成。在前言部分里,叙述者杰里米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构建了小说主要声部的发声者杰里米的形象,自然地引出了小说的主题。换句话说,前言向读者交代了一个怀疑论者或者说一个无信仰主义者的生成过程,然后,引导读者跟着这个无信仰主义者去探寻黑犬事件真相,从个体的思想变化切入,展示欧洲文化根基——思想体系的嬗变。在故事主体的第一部分里,作者是以事件亲历者之一琼的视角描述黑犬事件;第二、三部分,从无神论者伯纳德的视角叙述事件;第四部,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尽量客观地、完整地叙述黑犬事件。
小说通过描写一对夫妇的见闻和亲身经历将历史事件融入小说之中,呈现欧洲战后动荡黑暗的局面,探讨战争阴影依旧在欧洲笼罩的原因,解读历史对现在和未来的启示。在结构和人物设置上,小说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努力让三个主要人物脱离自己而存在,成为表现本人思想立场而存在的主体,其在文本中的话语也不仅仅局限于表现其性格特征和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是一种他者的、非作者意识的、具有完整思想观念的主体话语。此外,三个主要人物分别代表了二战后欧洲的三种思想体系:伯纳德的无神论、琼的有神论和杰里米的怀疑论。在追寻黑犬真相的这个统一的事件中,三种思想体系不断碰撞,展现出欧洲思想形态的分裂和坍塌。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一点,伊恩·麦克尤恩在小说《黑犬》中,不仅是设立了三个不同的人物代表不同的思想,而且成功地借用了前苏联文艺学家巴赫金的复调式叙事手法。所谓复调式叙事,是与独白式叙事相对而言。独白式叙事是把多种性格和命运根据作家的统一意识在作品中分别展开,而复调叙事“是把多个价值相等的独立意识以及其各自代表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1]。换言之,作品中的主人公不仅是作家所叙述的客体,更是直抒己见的主体。为了真实地反映现实,保证文本的客观性,伊恩·麦克尤恩在文本中复现了生活本身的对话关系,减弱作者的主观性,让主要人物实现自我意识的独立。《黑犬》之所以被称为复调小说,就是因为它真正地实现了人物自我意识的独立。伊恩·麦克尤恩让每一个人物都具有充分完整的思想观念,并且都各自在小说里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一、多声部才是人类真正的生存形态
在独白式小说中,人物仅是作家描写的对象或客体,是为表现作者的思想观念或感悟而设计的。但是在复调小说中,人物虽然是来源于作者的创作,但却不是为服务于作者的思想而生,是有别于作者的另一种思想观念和世界,是自己观念的主体,是不依附于作者的独立存在。在《黑犬》这部小说中,伊恩·麦克尤恩没有刻意表现自己本人的统一意识,因此每个人物都是独立的,具有同等的地位。小说的这个明显特征具体表现在两点:其一是主要人物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其二是主要人物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不分先后和优劣。因此,《黑犬》是属于典型的复调式小说。
《黑犬》中最先出场的杰里米是一个无信仰主义者,是对话关系的核心人物,代表作者同另外两个主要人物展开对话。对话的内容表面上是在探究黑犬是否真实存在,实际上是无信仰主义者分别同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针对文明出路问题在各抒己见。
杰里米这个人物角色的设置是非常成功的,在文本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是个内视角式的人物存在。法国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历史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 1939—)认为:“叙事作品的叙述视角分成三种:全知视角(零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2]外视角多用于侦探类型的小说,叙述者由事件的旁观者充当;全知视角,即全知全能的作家向说书人一样出现在文本的背后进行讲解,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全知全能,掌控一切。在《黑犬》中,杰里米一身二任,既作为人物之一进入故事和场景,又充当叙事者讲述亲历的事件或转叙见闻。所以,杰里米是读者能够借助的内视角,他的视觉、听觉以及感受都是为了帮助读者领略事件的全过程。不仅如此,杰里米还是整个复调中的一个独立声部。他以写回忆录的目的,与故事中的人物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是整部小说的复调式叙事得以确立的关键。
杰里米是怀疑论者也可以说是无信仰主义者的代表。失去双亲的孤儿杰里米,成长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面对喧闹、动荡、充斥着各种理论,却又思想信仰崩塌的矛盾年代,他在迷茫和失落中挣扎,并且以各种方式填补心灵的空虚。在《黑犬》的第二部分里,杰里米常常去拜访身患绝症、囚困于疗养院中无处可去的琼。通过杰里米与琼的对话,以及杰里米的观察和分析,作者呈现给读者的信息是:琼的人生和容貌都偏离了预定的发展轨道,用容貌变化暗喻信仰的变化,即从最初的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第二、三部分是杰里米同伯纳德的对话。同样,读者再次透过杰里米的视角看到黑犬事件在伯纳德身上的影响。伯纳德的信仰如同他的脸一样,整体格局没有改变,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调整:他虽然在苏联入侵匈牙利时退出了原来的组织,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黑犬》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独立的意识”,代表一个独立的思想观念体系。但是如果仅仅是赋予人物独立的思想,那也只能是一般的心理小说。《黑犬》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的小说一样,给三个人物的独立意识构建一种平等的关系,允许它们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去表述其合理性,而不强加任何来自于作者的价值判断。在独白式小说中,作家把某一社会生活侧面进行诗性的重塑,营造出假定的情境,表现自己的主观褒贬态度。因此,作家势必让文本中所有人物的语言和行动都按照一个统一的、既定的脉络去展开,以使最后的结尾看起来顺理成章。这样的小说常被诟病为是武断地凌驾于文本接受者之上的一家之言。与此不同,《黑犬》的是开放式的,没有依据作者的意志形成固定的结论,只是有三个独立声部围绕黑犬的真相形成一种复调式的和声。但是,这几个独立声部的存在,终极目标不是为了从多个角度去探讨黑犬事件的真相,而是为了展现人类真正的生存方式,即对话性。这种对话性,有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微对话和大对话。首先,人类思维是“微对话”。“人类思维的本质是对话性的。”[3]思维的对话性体现在两点:其一,人物内心的矛盾,具体体现在分裂的人格或者双重人格之间的对话;其二,在内心中与一个对立的话语即他人的意识进行对话。其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大对话”。“生活本身也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常常是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着同一个题目。”[4]一个人的“言谈”是其观点和价值观的外向性表达,并且和他者的“言谈”一同构建出话语的公共空间。在真实的世界中,并不会存在独白小说中常有的某一方的最终胜利,而是多元无限期并存的现象。所以,这样的复调式叙事方式才是表现人类真实生存状态的最佳载体。
二、欧洲战后的文化危机
三个主要人物在自我意识上的独立,目的是为如实复现欧洲战后的文化中的思想信仰分化现象。二战史无前例的杀戮和暴行给人类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而且战后物质生活的匮乏更加剧了精神上的痛苦。战争带来的死亡、贫穷和饥荒等,将人们抛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和思想信仰危机之中,于是一切传统的道德和秩序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思想体系领域里的危机会直接反映在文化领域里。德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1936)于战争期间创作的《西方的没落》在战后的欧洲引发了一股销售热潮,这个文学领域里的事件就标志着欧洲人的思想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西方的没落》能够热销,说明整个欧洲因发达的物质文明而累积起来的优越感已经发生动摇,对曾经引以为傲的文明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形态的文化就象一株花,一棵树那样,都走不出从发生、成熟到衰落的宿命,欧洲正在走向没落。”[5]战后的欧洲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欧洲人开始认真地反思和寻觅自我救赎之路,各种思潮和主张纷至沓来,层出不穷。在众多的救赎理论中,最突出的是理性主义和神秘宗教主义。
从欧洲文化心态的发展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前的主流思想体系非宗教莫属,虽然其宗教流派五花八门,但是究其根本是有神论思想。随后,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进步,逐渐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反基督教主流话语方向的作品,表现人类远离宗教,投入理性和科学的怀抱,并将其认定为发展文明的捷径。然而理性思维和科技进步不仅仅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便利和物质的富足,更是带来了残酷的杀戮,让人类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于是,理性主义构建的信仰体系摇摇欲坠。“理性主义王国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反人性的,那么退回到非理性之中似乎成了可选择的一种途径。”[6]于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再次登上舞台,欧洲大陆坠入了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相互倾轧的漩涡。
麦克尤恩在《黑犬》中用伯纳德和琼在个人信仰上的冲突,指射欧洲意识形态领域里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伯纳德和琼在青年时期都对人生、革命和爱情充满热情和期待,但是随着两人政治信仰的日渐分化,婚姻最终名存实亡。伯纳德虽然崇尚逻辑和理性,坚定地信仰唯物主义,但是在1950年退出了理性主义组织。伯纳德的行为影射的是欧洲人的理性主义崇拜遭遇危机的事实,“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灭了”[7]45。理性主义强调极端的理智,认为理智可以排除人类行为上的冲动和感情用事等非理性因素,能够带来和平、公正、幸福和无尽的创造力。但是,理性主义主导的技术霸权和民主政治没能阻止世界大战的杀戮。于是,欧洲人对理性主义信仰提出了质疑,曾经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伯纳德动摇了。
琼代表的是神秘主义信仰。她在青年时期是一个无神论者,在遭遇黑犬之后,开始信仰神秘主义。琼的变化其实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不解。在目睹了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创伤以及战后欧洲共产主义的极权政治等,欧洲人对倡导科学技术的理性产生了怀疑和否定,转向内心寻找答案,琼是这一类人的代表。她发现理性主义高举的科技和进步大旗没能如期地带来幸福和和平,“即使人人都拥有免费医疗和无所不包的家用电器,可他们还是感到不满足”[7]42。琼坚定地认为理性主义倡导的技术进步只能带来物质的富足,但不足以解释和驱逐深藏于人类心底的邪恶,所以必须实现一场心灵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琼的神秘主义信仰既不是传统的宗教信仰,也不是伯纳德所说的非理性,而是对现实生活和人性本质的重新认识。柏格森曾说:“当代的神秘主义并不是非理性,它是理性的补充,是理性中未被发现、未被探测到的一部分。”[8]理性主义信仰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神秘主义虽然源于宗教,但是却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成为宗教和哲学的综合体,把人和神的关系作为道德修养的核心,关注人的心灵、能力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更加准确地解释生命和世界。
受战争影响的第一代人是琼和伯纳德。他们在价值上的分野和信仰上的冲突不仅让这一代人彼此疏远,同时让他们的后代在信仰上无所适从,而最终成为无信仰主义者。杰里米就是无信仰主义者的代表。他说:“我没有任何信仰,……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或者一条持久的准则,……也没有找到一种能让我信奉的超验存在。”[7]36
社会意识形态和信仰是个人身份和心灵的标志,历史重大事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入侵并改变着个人生活。麦克尤恩反其道而行之,用三个独立的个体把整个欧洲的信仰分裂具象化了。不难看出,在信仰的分化上,战争是关键的触发因素。面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走出中世纪宗教思想的桎梏并投入到理性主义怀抱的欧洲人中,坚定如伯纳德一类,虽然在思想上出现了困惑和动摇,但选择停留在原地,寻找各种方法为理性主义辩护;本就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如琼一类,则投入到了神秘主义的怀抱;背负父辈思想的沉重负担,如杰里米一类的年轻人,面对对立的思想与观念,只能是一个质疑一切的无信仰主义者了。麦克尤恩用文学手法书写历史,成功梳理了欧洲战后的各种思潮和信仰以及他们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态度。
麦克尤恩把传统线性叙事立体化,模糊历史和现实的界限,精准传达二战后欧洲的精神恐慌与焦虑。换句话说,麦克尤恩精心架构了一个复调叙事的框架,用几个独立的声调代表地位平等的意识以及它们各自代表的世界,展现了欧洲战后意识形态的分化。麦克尤恩借杰里米之口感叹:“我不能确定,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是因为有像伯纳德和琼这样的人,还是因为有像我这样的人才遭受祸端。”[7]45究竟是伯纳德信仰的理性主义,还是琼崇拜的神秘主义,哪一个能使人类文明免受战火涂炭?麦克尤恩没有在作品的最后给出结论。《黑犬》中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没有最终答案。可见,作者的目的是呈现矛盾。在《黑犬》这部作品中,麦克尤恩采用了多个独立主体平等对话的模式,巧妙利用人物设计和情节安排,展现自己在信仰方面的困惑和无所适从。或者说,伯纳德、琼和杰里米只是作者割裂的灵魂的代表,是麦克尤恩让自己的多个人格进行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目的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展现整个欧洲思想体系方面的嬗变:从对传统信仰的质疑到思想体系的彻底崩塌,最后到现代人在信仰上的无所依从。
三、复调叙事是呈现思想体系崩塌混乱的最好载体
在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人类活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圭臬,并为此而互相倾轧,与《圣经》所宣扬的博爱产生冲突,人的信仰根基开始动摇。原本坚如磐石的基督教世界里的思想体系出现分裂,导致欧洲人在自我意识和潜意识中,出现割裂的、矛盾的和多重的构造。就麦克尤恩个人而言,其思想意识也是割裂的和矛盾的。在麦克尤恩的生活历程中,曾经有多种思想体系粉墨登场。他出生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时期因父亲的工作调动而辗转于多个海外的海军基地,因此接触到异域的文化和思想。成年后,他与一个神秘主义先验论者结为夫妻,又开始接触神秘主义思想。他本人曾经投身于反文化运动,但是后来对反理性主义的文化运动感到厌倦,开始接受理性主义思想。经历了自身思想变化的作家去表现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是最顺理成章的事情。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这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意识表征找到一个合适的文学载体。经过反复尝试,麦克尤恩最终选择了对话式的复调。
复调的概念本来是属于音乐领域的,指相关但却不尽相同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声部同时进行,使音乐形象更加丰富,气势更加立体,造成震撼的听觉效果。复调叙事的具体理论来自于后现代的音乐,所以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二者的最高美学追求都不是要呈现和谐统一,而是要呈现多元和矛盾。单就这一点而论,复调就比独白更加适合当下的多元化时代表征。
独白式小说是“作者对生活的诗性重塑,有加工过度之嫌,无法表现出生活的真实状态。独白式小说是作家固有的对世界的根深蒂固的原则性态度,是一种观念上的整合和建构”[9]。独白式作家是把人类救赎看成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借文学言说人与世界的关系,围绕自己的理念塑造角色。这样做的结果是:人物虽然也在说话,但他们的声音和意志经过作者意志的过滤,成为作者意志的传声器,因此不契合多种理念并存的时代意识表征。
复调重在多元和矛盾,独白重在统一和归化。首先,复调小说与独白式小说最大的差异是:独白小说的重点是人物和情节,通过描写人物和情节来赋予小说一定的思想性,而复调小说的重点是思想本身。“复调小说是在一个平面的、共时的结构中考量各个意识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故事中的人物以自己的意志、生活模式和标准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个体主体意识的存在方式。”[10]就《黑犬》而言,麦克尤恩用三个人物作为三个不同思想体系的具象化代表,又用杰里米的叙述交代人物背景。三个人物的背景分别代表着三种思想体系的生成过程。其次,独白式小说的结尾是终结式的,由作者给出一个预设性结论。复调式小说的结尾具有未完成性特质,是开放式的。就《黑犬》而言,麦克尤恩没有给文本中对立的信仰一个孰优孰劣式的结局,对立的局面不会因为某一人物的退场而终结,例如琼的死并不意味着她代表的神秘主义的终结。麦克尤恩在《黑犬》中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一切就如生活本身一样,都只是过程。
在工业时代里,人类活动都以利益和金钱为动力,曾给欧洲文明发展提供精神支柱的《圣经》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慰藉人类疲惫的心灵,人的信仰根基不像以往那样统一和坚定,分裂在所难免。在人类自我意识和潜意识中出现的多重构造,已经不适用于古典美学中的单一旋律(独白式叙事作品),因为它无法描绘现代人割裂的灵魂。《黑犬》为现实里多样化的意识和声音,搭建了发言和交汇的场地,这是独白小说做不到的,因为独白小说不给他人话语任何语义空间。综上所述,当下是一个价值多元、观点多元、体验多元的丰富而又真实的世界,复调小说的对话性、矛盾性和未完成性契合了这个世界的多元性状态,是呈现分化格局的最好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