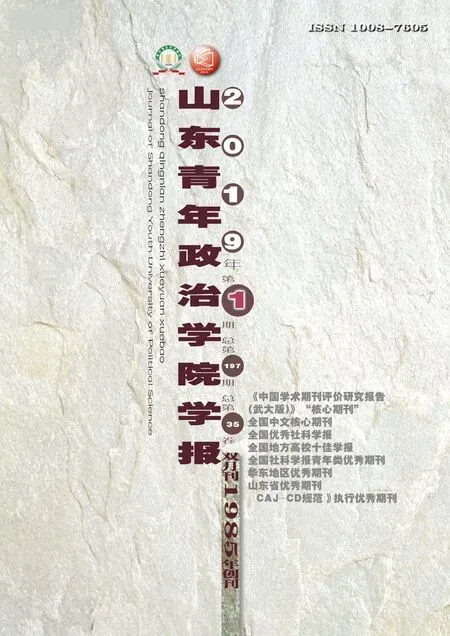告别 追寻 超越
——德格娜电影《告别》解读
2019-02-19王桂青
王桂青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人文社科部,上海 201620)
在2017年9月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中,青年导演德格娜的电影《告别》喜获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而著名演员艾丽娅也获得该片最佳女配角提名。该作品此前还曾荣获第33届都灵国际电影节最佳剧作奖、2015年第九届firs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奖、第28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国际交流基金亚洲精神特别奖”等奖项。
与影片获得众多奖项不相匹配的是,关于这部青年导演德格娜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半自传性电影作品的研究评论并不多见,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这或许和电影的低成本有关,或许和电影的小众性质有关。在当前有限的几篇研究论文中,或聚焦于女主人公青春期的成长,或着眼于都市和蒙古民族文化的表达方面做文章[1][2],却往往忽略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人类共通的生命哲学相互关系的探究。诚然,影片不乏一些蒙古族文化的元素,如片中故事的讲述者山山一家的少数民族归属,山山的奶奶、姑姑和父亲之间时不时用蒙古族语言的对话交流,奶奶和父亲都对山山流露出她不会说蒙古语的遗憾惋惜,等等。这些元素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片中人物对本民族身份和文化的认同,也许还夹杂着大都市中少数民族移民二代民族身份渐趋模糊的焦虑。但是影片不仅仅是这些,它更多的是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状态,表现出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全球化背景下,个体被时代裹挟的尴尬无奈以及人类所面对疾病死亡被动苟且的生存状态。同时在个人的历史怀旧中彰显出个体的精神荣耀和现实的无助,表达了追寻奔放生命与人类梦想的不可遏制的激情和渴望。
确实,如果你期望在貌似反映蒙古族人民生活的电影《告别》中看到某种“马背民族”文化爆棚的恢宏气势和视觉奇观,那肯定是一次失望的旅程。电影既没有辽阔大草原诗意的展现,也没有剽悍民族英雄事迹的呈示,既没有撼人心魄的蒙古音乐长调的宣泄,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化故事情节的演绎。这是一部极具个人化私人化的电影,但又包含着某种人类共同生命体验和生命哲学的思考;这是一部半自传性甚至带有某种纪实风格的电影——女儿在青春期的混乱和迷茫中回顾自己身为导演的父亲,回顾他从病重到去世的一段痛苦而又尴尬的时光,影片的叙述者是托名为“山山”的女儿,其实就是青年导演本人德格娜,主角是父亲、专拍蒙古族题材电影并取得非凡成就的著名导演塞夫(由著名演员涂们扮演)。既有女儿跟临终父亲的告别,也有父亲跟家人的告别,既有女儿跟过去的自己告别,也有父亲与当下的自我告别,如果套用一段流行话语对本片主题进行总结的话,那就是:告别“眼前的苟且”,追寻“诗与远方”。
所谓“苟且”,《现代汉语辞典》的两种解释适用于本文,一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二是敷衍了事;马虎。[3]根据这两层含义,我们可以发现剧中人一家三口都生活在生命的“苟且”之中难以自拔。病痛的折磨、事业的受阻、爱情的失落和迷茫、岌岌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张,等等,都可视为眼前的苟且。
首先,主人公父亲命运“苟且”程度是最为严重的。在观看电影之初,也许我们并不知道青年导演德格那的家事背景,只意识到笼中鸟、骏马图以及马群的隐喻和象征。骏马的像喻应该是自由奔放的生命,笼中鸟使得应该奔放的生命受阻。奶奶曾多次在孙女面前津津乐道其父年轻时自由淘气敢于冒险的生命形态。德格娜的父亲塞夫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蒙古族导演。蒙古族本来是游牧民族,长年策马驰骋在辽阔的大草原,剽悍无比。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形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行为特征,性格格外奔放,不受任何拘束。从他和妻子麦丽丝合作导演的一系列电影中可以看到这一鲜明特色。“从《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到《成吉思汗》,塞夫和麦丽丝不倦地制造着他们民族的寓言——瑰丽的草原视觉,惊心动魄的马背技巧,粗犷憨直的蒙古性格,以及一幅不断丰满、逐渐完整的历史图景。”[4]尤其《悲情布鲁克》“全景式地展现了蒙古族的马上文化, 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充溢着爱与恨、悲与欢、情与仇的抗日故事,集中再现了蒙古民族在‘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关头’时,对抗战的历史性贡献。”[5]该片曾荣获西班牙电影节最佳视觉效果奖,其中有很多骏马奔驰的壮观场景,而那四马并驰、马背上纵情豪饮的华彩段落,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中的经典。而这一切都成为昨日黄花,成为他生命中远去的风景,因为残酷的现实使得他原本奔放的生命受到了拘役。一是自己的身体得了肺癌,而且还是那种非常罕见恶性又非常大的小细胞性质的肺癌,生命正在经受着死亡的威胁。面对死神的召唤一般人都会感到不甘、无奈,无助,想要顺其自然已经非常困难,想要潇洒地行走已然非己所愿,想要奔放的生活更是痴人说梦。困在笼中的小鸟无疑是父亲生活现状的自我投射和像喻。再者,家庭生活成为一种束缚,爱成为禁锢自我的枷锁。他有一般意义上的完整家庭,却不能给他带来温暖和慰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家庭甚至成为他的牢笼。夫妻分居多年,与妻子动辄争吵连绵不断,话不投机半句多;对女儿的行为举止甚至穿着打扮都不能接受和理解,动辄呵斥教训甚至谩骂,跟本来最亲近的妻子女儿彼此之间都有一些壁垒和隔阂,与她们母女的交流往往增添的是不快和郁闷,有时还不如跟自己年迈的母亲和平庸的妹妹甚至老朋友在一起闲聊打牌更让自己能放松一些。作为一个北漂导演,同时作为一个曾经的电影厂厂长,他的事业发展也遭遇到瓶颈。在中国电影市场化之后,国产电影制片厂的纷纷萧条与倒闭,职工连续16年发不出来工资,电影厂制景车间改装成了演艺中心和酒吧歌台。作为热爱电影事业的艺术家,最爱大草原的蒙古汉子,却失去了自己的事业发展的空间,不能像当年那样驰骋草原,拍自己喜欢的电影;作为一个厂领导,也不能给全厂职工带来事业的转机和生活的希望。面对职工们的连连质问,他也无言以对无能为力。因为国企改制后出现的众多问题,也不是靠他一人之力能够解决的。凡此种种,都构成了对他生命的阻隔。在这心为形役的生命状态中,依然想实现带着镣铐舞蹈的梦想,他希望顺其自然,不戒掉抽烟的习惯,想打打麻将,想到处走走,想跟老朋友聊聊天,但在妻子这里总是受挫,不许他抽烟,还要想方设法走后门让他住在医院里饱受身心的双重折磨,以关心爱护的名义对他实行伤害,使得他苟延残喘的生命加速消亡。为了照顾家人的感受,他表面上配合着治疗,吃着价格不菲的药,坚持做放疗化疗,请大师做气功,放生笼中小鸟,而喃喃一句“这样活着为了啥呀”,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切的痛苦。
其次是母亲的“苟且”。在“蒙古族故事里,一说到‘额吉’(蒙语母亲的意思),人们总能想象出草原上蒙古包前那些勤劳善良、忍辱负重的形象。但是在《告别》中,山山母亲‘老艾’却完全和这些词汇不沾边。”[6]当我们在片中见到她的时候,她成为彻头彻尾的生意人,精明能干的女强人,财大气粗的女管家,颐指气使的大家长。她的行为中有很多表演的性质,从机场接从英国回来的女儿回家,一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忙着打电话,遥控着属下给医生买羊绒衫送礼,竟然没有跟女儿任何一句话的交流。不知是为了显示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能耐还是她对女儿的热情,她在她的豪华厨房里对着保姆吆三喝四,并且亲自上阵为女儿张罗了颇为铺张画蛇添足的一大桌菜,然而女儿并没有领情地多吃几口。当年她和丈夫一起合作拍电影,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放弃了拍电影当导演的初衷(从这里也可以反衬出父亲的苦闷)。她从导演转型做起来旅游产业,然而在丈夫看来,她的旅游产业完全受金钱的掌控,商业味道浓烈,而文化气息稀薄:蒙古包用水泥盖的,不透气,好像是桑拿房,吃着炒米把子肉,唱着蒙古歌曲汉语歌词……蒙古草原所特有的民俗风情文化内涵早已变得不伦不类。旅游产业为她挣了很多钱,积累了很多人脉,从而使得她以为钱和关系可以摆平一切。她为丈夫治病舍得花重金给医生送礼,千方百计托关系让他住ICU病房。给他买很贵的药买好多高营养的东西。不能说她不关心自己的丈夫,但她对丈夫的关爱,更像是做给别人看的,总是喜欢标榜她所花费的金钱和价格。有一回她甚至买了一大桶油和一堆需要在厨房加工的东西送到病房,还口口声声说做给奶奶和姑姑看的,足以说明她跟丈夫以及他的家人积怨很深。她非常看重物质的功能,唯独对亲人心灵的需求漠不关心甚至加以摧残。看到丈夫抽烟立刻火冒三丈严词训诫,使得他无以在家存身。她对女儿说起丈夫的病时居然用“生死是正常,要面对”之类的语言,不免让人感到过于现实和冷酷。她表面上似乎事业成功,但在家庭中却众叛亲离,她的一系列做法同样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女儿对她咆哮“全家就你一个人有病!”,她自己也生活在焦虑之中,经常怀疑丈夫的忠诚,坚持认为“外面有他更在乎的人”。
女儿的“苟且”。由于父亲的病,女儿山山从英国留学中途回来。而此时青春期的山山正生活在无所依傍的无序状态中。首先是爱情的混乱,本来现实中有一个男朋友,却又沉迷于虚拟世界的网恋,她像网恋的男友“空气草”的名字一样,她也是无根之草,在生活的河流里没有目的地漂流着,这表明她的精神无所寄托,所爱非人,并没有找到能够给她心灵慰藉的精神伴侣。其次是前途的迷茫。她像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一样,未来的走向都被父母所操纵,而自己却没有主动权。甚至她也像那笼中之鸟,虽然父母放她到国外,但她的留学生活是被父母安排的,而不是自己选择的,父母为了她出国留学在她身上花了好几百万,这对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并不知感恩,甚至心存不快。由于这些不如意,也造成她和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父母不理解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和追求,只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一见面就是批评数落,唠唠叨叨,在一些生活小节上对她横加指责甚至口出恶言,这又加剧了她的烦恼和对父母的反感。山山所经历的烦恼也是众多的青年人在青春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虽然这个过程伴随着尴尬和阵痛,但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逐渐成熟起来。
可以看得出,这个家庭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大潮中的受益者。在改革的洪流中,他们一家成为北漂一族,夫妇俩还成为专拍“马背民族”题材的著名导演;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妻子转型做旅游产业,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为成功的商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还把女儿送出国门,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抵消他们面对苟且生活的尴尬和无助。尤其在父亲罹患肺癌之后,他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人类的悲剧性在于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死期限,即使你有万贯家财富可敌国,即使你位高权重不可一世,即使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即使你心比天高前程远大,终究逃不过命运的苟且。正像《悲情布鲁克》中的主人公所说“人的生死在于天”。这也许是电影对于生命哲学的思考吧。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自由驰骋的骏马,每个人都想成为不受拘束的骏马,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在飞翔的鸟儿。即便是随时面对着死亡无常,也不能在苟且偷生中“束手就擒”。这种向死而生的挣扎或许是一种人类的本能,或许是“绝望的反抗”,就像德格娜在旁白所说的“有些东西是不该在笼子里生活的。”重病中的父亲执意要在留给女儿新装修的房子墙上挂一幅三匹骏马奔腾的油画,这幅画寄予着他和一家三口的梦想和追求。生病期间他还到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内蒙古电影厂走访,在放映间重温《悲情布鲁克》那段策马追奔和悬崖坠马的最紧张激烈片段的胶片。这些都承载着塞夫毕生的事业和追求,承载着他内心的“诗和远方”。迫于他的身体状况,这种追寻只能表现为是怀旧与沉湎。怀旧是对当下生活的超越,是对过去取得荣耀成绩的价值认同,正像老朋友巴音所说的“人一辈子还能怎么样呢,挺荣耀的啦”,父亲眼中的泪光闪闪也表征着他所最珍视的东西就是他的事业。这显然不是像阿Q“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的主观臆想,而是他继续苟延残喘下去的精神支撑。片中有一个场景:父亲夜晚睡不着,坐在床边把玩抚摸着一个玩具小马,耳边却超现实地响起了辽阔大草原万马奔腾和嘶鸣的声音,这是父亲追求奔放生命意义的显影外化,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也许能部分地表达他此刻的心情:“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当年为了拍那一个马坠悬崖的精彩段落,他曾狠心地葬送了一匹马的性命。为了偿前债,女儿终于把象征着父亲新生命的鸟儿放出了笼子,让它在大自然中自在地飞翔。在他看来,死亦不足惧怕,他只是为了家人而配合治疗,既然死亡是迟早的事,也并不想戒掉烟瘾,他似乎超越了生死大限,自在随意,却没有顾及亲人的感受。他有时出口伤人很重,但内里父爱如山,把那套房子的钥匙交给女儿,还去澳门赌场赢了一把给女儿当作学费。然而赌场得意,生活失意。日渐衰弱的父亲在化疗放疗期间,头发落尽,身体衰弱得走路要靠手杖去支撑,他甚至没有力气把墙上的骏马图扶正,夜里辗转不适时,也只有依赖女儿的帮助。眼看着鲜活健壮的生命就这样一日日地消亡下去,伴随着山山和父亲隐忍的眼泪,我们的泪水也悄悄地滑落。
与父亲的怀旧所不同的,在女儿这儿是鞭策与激励,无穷的诗和远方在向她召唤和招手。德格娜回顾“在爸爸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天天陪着他,这是我与爸爸生活最亲近的一段时间,那一段时光对我而言很特别,我第一次开始了解他……那段相处让我重新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转变在我的生命里很重要……”[7]她最终帮助爸爸把骏马图稳稳地挂在了墙上,撕去了包裹在其上的束缚。在陪伴父亲的过程中女儿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追求和梦想,并在为人母后把这梦想传承给了自己稚嫩的女儿:面对骏马图,教女儿模仿骏马“得得”的叫声。片尾,银幕上深沉地推出了父亲引以为傲的电影《悲情布鲁克》最为华彩的无数骏马在辽阔大草原上恣意驰骋的全景画面和四位骑手马上豪饮的片段。这多少让人想起了汪峰演唱的那首《怒放的生命》:“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扑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象飞翔在辽阔天空/就象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确实,理想和梦想就是人类的“诗与远方”。
《告别》是德格娜导演的第一部长片作品,也是她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毕业作品,同时她也在片中出演女主。她表示这部影片是向父亲的致敬。德格娜说,“父亲很疼爱我,对我也很严厉,他总是很忙,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8]真正地了解父亲,是在父亲生病后,德格娜从英国回来陪伴的那段时间。父亲去世几年后,德格娜开始写《告别》的剧本,把它作为自己与父亲的正式告别,也是写给父亲的挽歌,更是献给父亲的礼物。作为新锐导演,初出茅庐便不同凡响,想起了“虎门无犬子/女”的老话,期待她更好的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