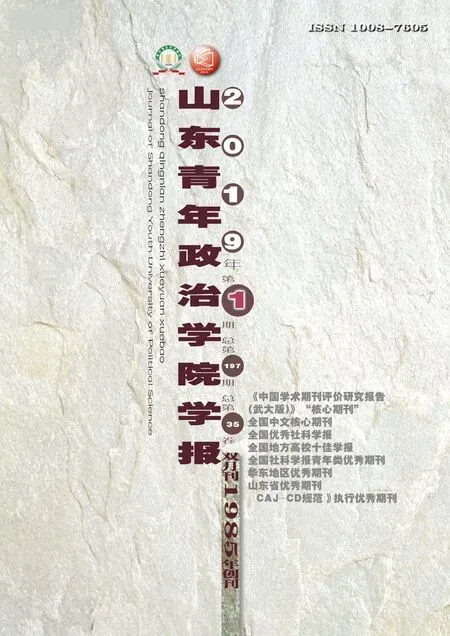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国实践的反思与展望
2019-02-19袁盼盼
袁盼盼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中国实践概述
女性主义叙事学自上世纪1980年代在西方兴起就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它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经典叙事学理论密不可分,一方面克服了经典叙事学在对叙事作品进行意义阐释时只关注叙事技巧本身的文本意义而将作品与包括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在内的社会历史语境隔离开来的弊端;另一方面批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分强调政治化、流于印象化的评论方式;同时它吸取经典叙事学科学严谨的叙事结构模式,借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性别政治批评立场。
本世纪初期女性主义叙事学经由黄必康、申丹、唐伟胜等学者介绍翻译进入中国,中国学者将其运用于对中国女性写作的研究中。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具体文本分析的论文数量很多,涉及外国经典的文学文本、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文本、文学现象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等各个方面。虽然利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进行分析的成果较多的是外国文学领域中对外国文学文本的研究,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的研究中不乏有深度的研究著作,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力有深度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文章一般集中于对八九十年代的女性小说批评,此时的女性作品中因为女性意识愈发张扬而社会语境本身压制形成独特的叙事形式。如陈淑梅《声音与姿态——中国女性小说叙事形式演变》从话语形式的角度研究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小说,将其分为“代言式书写”“个人的声音”“叙述主体的凸显与淡化”三个阶段,认为中国女性小说叙述声音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经历了从压抑到张扬的过程。王侃《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则是没有受女性主义叙事学影响对1990年代女性小说进行叙事分析的论著,它从主题、语言等方面进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依据小说本身的叙事,与利用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批评文章一起构成了中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共同的面貌。而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中利用沃霍尔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方式对十七年小说中男女作家作品中的叙事形式进行分析,从而依据社会语境得出女性当时的话语环境,对女性主义叙事学呈现科学化的方式有启示作用。另外,有一些学者借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一些热门的电视剧与电影,跨学科的态势对女性声音的传播愈加有利。如张兵娟博士毕业论文从女性主义电视叙事学角度入手分析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与电视叙事学结合下的电视研究,随着传播媒介的改变,文学文本的受众普遍低于电视剧电影的受众,现状是很多人都是看了电视剧以后才去看小说或者根本不涉及文本阅读,所以,文学文本本身承担的描绘人性启迪或者净化心灵的功能更多的被新的媒介所代替。对电视剧电影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不仅拓宽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范畴,使得作为一种理念的女性主义更加深入人心,提升了其社会影响力。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国实践的问题
当然,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中国实践也出现了诸多局限与问题。中国学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叙事的理解有一定偏差,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对女性叙事的泛化理解,将叙事学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内容研究;利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进行解读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机械利用西方理论进行解读的模式化形式的现象;研究亦多集中于叙事声音、叙事视角与叙事权威等兰瑟的相关理论,而忽视了其它一些重要的研究方式。
1.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叙事的距离
有些学者指出:“所谓‘女性叙事’就是立足女性立场,以女性主体为主要叙述对象的文学叙事,即讲述女性生命成长的‘故事’。”[1]刘云兰在《论当代女性主义小说叙事策略的转变》中也提出“女性叙事是与男性叙事相对而言带有强烈性别意识的叙事方式,它通过对女性情感经验、欲望经验等的抒写,高扬女性意识,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的审美价值追求,表现女性对社会和人生的独特认识和理解,从而为女性争得社会话语权。”[2]中国学界传统的关于女性叙事的研究侧重分析女性作品中呈现的女性书写内容与女性人物的感觉、情感以及形象以此表达传统学界文学标准下女性作品呈现的对人性、文化、历史等的思考,如分析1990年代女性的“私人化”写作聚焦于身体言说与狭小空间的特征。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则主要是通过女性作品的叙事形式分析女性的叙事姿态与话语权威,这样的阐释使得女性作品逐渐远离传统文学标准建构属于女性叙事的审美标准。只是在中国现有的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是中国学者没有分清女性叙事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区别,只是依循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印象化的分析。有的学者认为“在叙事形式上,女性叙事也由过去女性自我言说的方式转入不注重叙事技巧,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的近乎一种原生态的写作方式”[3](这里是认为女性写作由1990年代的身体写作转入关注底层人物的写作以后的叙事特征)。笔者认为,在这里研究者笔下的“女性叙事”只是分析女性作品中书写的女性欲望、挣扎以及思绪感受等等小说内容层面的显著特征,且只是相较于激进的具有明显女性写作特征的小说与新时代女性写作的内容加以比较,在叙事形式上,女性作品中叙述者的姿态不再像是90年代小说中那样张扬,女性人物也不再是具有强烈女性意识、沉浸在自我经验中的女性知识分子而转向了底层女性的书写或者底层世界的书写。女性写作不是不注重形式而是转变了形式,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是分析女性采用这样的叙事特征如何呈现女性意识以及这种叙事特征是怎样进行身份建构的。
2.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研究未充分展开
笔者经过分析发现,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集中于利用兰瑟的理论,而沃霍尔等人的理论仅在理论研究层面且只是唐伟胜、孙桂芝等少数学者中对其进行探究与传播。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很多方面在中国学界还未展开研究,笔者以沃霍尔的叙事形式与社会性别建构理论为例进行阐释。
唐伟胜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分析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与性别身份建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沃霍尔对女性主义叙事学进行重新定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在承认性别是文化建构的语境下对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研究”[4]。所谓承认性别是文化建构也就是继承了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巴特勒认为性别是在社会环境中不断重复而被固定下来的,是社会文化建构的。放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来说,女性主义叙事学要研究的不仅是性别对叙事形式的影响也要研究叙事形式对性别建构的影响。沃霍尔“关注人的性别气质多元现象,考察性别与言行举止之间的关系,考察社会文化、话语、权利如何塑造、制约人们的行为表现。”[5]她在《痛快的哭吧》一书中研究通俗文化形式对读者性别身份的建构,她认为“通俗文化形式让读者/观众流眼泪,并不是反映读者/观众内心的某种真实情感状态,而是通过让读者/观众流泪来建构和强化这种状态”[6]。她以此分析通俗文化形式如“眼泪文学”的叙事模式和形式特征来观察读者的心理以及如何建构读者心理。
叙事形式与读者性别身份建构的研究在中国尚没有充分展开。笔者分析现有的中国学者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从叙事视角层面探讨性别政治问题,“若聚焦者为男性,批评家一般会关注其眼光如何遮掩了性别政治,如何将女性客体化或加以扭曲。若聚焦者为女性,批评家则通常着眼于其观察过程体现女性经验和重申女性主体意识,或如何体现出父权制社会的影响。”[7]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叙事声音、叙事视角与叙事权威等兰瑟的相关理论,而沃霍尔的关于叙事形式对读者身份建构的研究只是呈现在理论介绍层面,中国的通俗文化尤其是网络小说尤其兴盛,可是关于网络小说中种种的类型如同性恋题材、穿越题材中的大女主甚至是现代言情中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等都会对读者的社会性别建构发生一定的影响。作为受众更广的大众文化具有哪些叙事形式,这些叙事形式如何对读者的性别建构产生影响。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方式进行阐释的,且对建立更加和谐自由的性别倾向会有积极的作用,可是现有成果很少,这是中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一种遗憾。
3.盲目追随西方理论忽视中国语境的模式化解读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本土化成果多是针对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还没有形成体系化,对此孙桂荣教授在《现状与问题: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本土化实践》一文章做过一定阐释[8]。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从目前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成果来看,我们看不到对二十世纪具有年代感的女性主义叙事特征的学理总结,能看到的大部分论文都是对张爱玲、冯沅君等现代女作家单个作品的研究,而且是以内容为主。针对1990年代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形式研究有所增加,但很多论文变成了一种机械利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模式化解读。如《真实的虚构——叙述声音与当代女性“半自传体”写作》这是一篇研究1990年代女性写作的文章,它是从叙述声音入手看1990年代女性话语权威的呈现,这种研究模式是从女性失语与被言说的现状入手,利用苏珊·兰瑟的叙述声音分类,将林白、卫慧等人的小说叙述者姿态进行研究,得出个人叙述声音对女性话语权威的追求。《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下的<饥饿的儿女>》是从叙事本身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颠覆、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声音与感性的女性主义叙事结构三部分解读《饥饿的儿女》,在叙述声音解读的部分,作者在采用兰瑟的个人型叙事声音时指出:“《饥饿的女儿》很明显地采用了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在女性主义叙事学那里,就是一种个人型的叙述声音,即故事的主人公与叙述者为同一人。作者在整篇小说中没有明确亮明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是通读全文后,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作者的叙述对象是广大的读者而非故事内的某个或某几个人物,因此,这本小说所采取的是公开的个人型叙事声音。”[9]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对小说文本的解读完全是依照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研究范式,把它当做金科玉律,研究的结构则变成了某部作品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将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叙述权威等罗列在一起,因为选择的文本在叙事形式上都是较为符合女性主义叙事形式的,所以这些研究文章看起来千篇一律。女性主义叙事学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些学者进行研究的重要方面,凌逾指出“女性主义叙事学不是叙事形式和性别政治的简单相加,需要建构更为扎实复杂的理论话语”[10]
总之,国内对利用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进行研究的论文,没有形成理论增长点,原创性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很少,研究难以形成体系化,呈现在眼前的研究成果都是零散碎片,随着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学者利用其进行的本土化的研究成果需要重新安排,对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衍生与发展,对中国文本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中国学界至今都没有进行整合规划,未来中国女性主义叙事学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三、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展望
随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广泛影响与深入发展,兰瑟等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提出者也在更新自己的观点,她提出了“交叉路口性”理论,主张对现有的资源进行分析以绘制出文本研究实践的新蓝图。中国则应挑选合适的叙事文本,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加入本土性价值批判,构建中国化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理论。
1.交叉路口性
在《我们到了没——“交叉路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这篇文章中,苏珊·兰瑟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交叉路口性”理论作为完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式。她指出:“作为美国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隐喻,‘交叉路口性’任务除性别之外,身份的多方面如种族、国籍、阶级、年龄、身体、素质、宗教、语言以及性征都交叉或汇集,在这个分布着统治、排外、机遇、限制、优势、劣势和特权的世界中产生特定的社会定位。”[11]兰瑟甚至认为对于女性主义叙事学而言即使不再进行新的研究,只针对现有的研究材料也可以绘制出文本实践的图画,“以女性主义叙事学已经完成的工作为数据,可以对我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定位,以弄清不同性别群体(作者、叙述者或是人物)如何在特定社会及再现场景下与身份的其它方面交叉,从而产生了特定的模式与实践”[12]。这样的研究方式将社会身份位置化而不是本质化,研究者要观察特定位置下特定身份组合产生的结构性和情境性效果,避免了预设性的女性主义理性,同时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绘制成一个宏大的地图,可以揭示不同地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特性以及局限性。这是女性主义叙事学庞大的理论目标,是整体性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构建的方式,通过“交叉路口”的特定交通方式辨识特定区域、团体的不同选择与流动方式。这一理论设想中国学者可以借鉴,不仅是根据现有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资料进行整理绘制,更是从本土的研究成果出发建构新的地域性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
2.中国本土扩展
自五四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与民族国家解放发生同构性关系开始,中国的女性主义注定不同于西方。一方面,中国学者应该利用兰瑟的“交叉路口”理论,就现有的女性写作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建构具有民族特性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
第一,加强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研究与建构,随着中国学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专门研究以及利用它进行的文本研究日益增多,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的程度加深。现阶段关于女性主义叙事学本土化建构的研究应该被高度重视,像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到底是如何被利用和解读,如何融合中国学界之前关于女性叙事的研究。还如女性主义叙事学与电视剧叙事的跨学科研究,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进行理论研究的切入点,现在关于电视剧叙事和电影叙事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真正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很少,最有力的研究是电视剧叙事或者电影叙事中对女性意识的遮蔽,但也只是做了揭开问题的工作,没有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语境中真正探讨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
第二,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提出的,在挑选文本的时候应该注意挖掘本土的优秀作品,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挑选张爱玲、严歌苓等作家进行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的解读。但是如笔者在前面所言,在文本解读中多是单篇小说单篇论文为主,且形成了模式化解读的弊病。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可以就一个叙事理论的发展流变进行探析。杨沙君的《个人叙事与女性话语权威的建构》将五四时期的日记体、书信体写作与1990年代私人化写作结合在一起,探讨个人叙事方式在这一历史流变过程中代表的女性自我话语权威的建构。
第三,关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中国建构方面,应该发掘中国本土的价值评判倾向。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同于西方,中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应该将性别研究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性别与国族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最初受压迫被侮辱的国家境遇中,女性更弱势的存在被置换到民族国家惨遭蹂躏的位置,女性的解放变成了一个救国救民的问题,而忽略了一直以来女性被男性霸权压制垄断的处境。后殖民女性主义正是要把这些隐藏于巨大概念角落中根深蒂固的问题拿出来讨论,像宋素凤在《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中论述了后殖民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参考性,提出了“后殖民经验的、后殖民情境的反思”的议题,认为后殖民女性主义因为与性别、国族、家国等有多重牵涉,对国家、民族、乡土话语有进一步反思与开拓,“是寻找一个又一个国家、原乡纯净无沾的梦土,还是进入这个权利话语的游戏当中,以敏锐的洞悉力,借力使力,使居于边缘位置的主体位置仍可以游移进入中心的叙述议题”[13]。中国学界也在利用后殖民女性主义资源拓宽研究空间,如果能与叙事学相联系,探讨女性是以何种叙事方式寻找社会权力、与民族国家话语相对接等对女性文学研究将是一个巨大的开拓。女性写作虽然是文学领域的范畴,但是与社会现实不可能割裂,而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对此亦可以做出自己一份独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