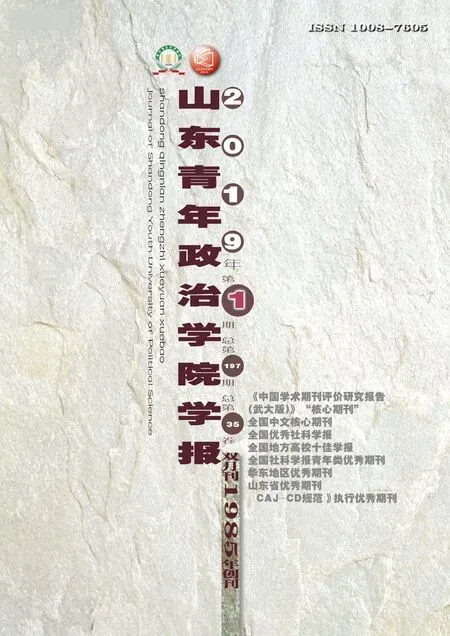叙事学视野下的“女性声音”研究及其中国化建构
2019-02-19孙桂荣
孙桂荣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一、“女性声音”概念的提出
“声音”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1],这是从物理学原理角度对它做的最原始理解。在生活用语之外,“声音”(voice)还引申出了一定的文化、学术含义,目前已被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广泛采用。传统叙事学中也用到“声音”这一语词,“它指叙事中的讲述者(teller),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有人对我说话,向我讲述故事,邀请我聆听他讲故事的声音。”[2]可以说,经典叙事学更多是在讲故事、叙述者/受述者层面使用的“声音”、“叙述声音”这些概念,“叙事文本以其措辞来表示叙事声音,隐含说话者对内容采取的方法,对读者作出的姿态的语气”[3],对“声音”的这种运用增强了文学文本之“叙事性”的辨识度,因为通过叙述人的声音表达出来的文学性描述不同于生活中的现实故事、事件,这奠定了“故事”与“话语”相区别的叙事学基础。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运用方式也产生了一个盲区,即其局限于物理学原理角度的“声音”原意,未能将“声音”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其赋予的权力、身份意涵相联系。像学术论文或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的“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找失落的声音”、“找到另一种声音”等,在这里,“声音”不单单是一个物理学、符号学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是观点、意愿、诉求之意,并往往与身份、阶层联系在一起,被赋予了权力与权利的象征意涵。
可以说,传统叙事学对“声音”的使用体现出了其作为形式主义批评重技术性、符号性分析,轻政治寓意和历史批判的一面。而后经典叙事学则对“声音”的理解从符号学拓展到社会价值层面上。詹姆斯·费伦曾言,声音是叙事的一个成分,往往随说话者语气的变化而变化,或随所表达的价值观的不同而不同,或当作者运用双声时变换于叙述者或人物的言语之间,“我强调声音与价值观之间的关联:就部分而言,聆听叙事就等于聆听与特定谈话方式相关的价值”[4]。将“声音”与价值、权力、意识形态相联系是后经典叙事学的开拓性体现,“女性声音”就是从这个层面而言的,其在后经典叙事学立场上的“声音” 界定中又增加了性别的维度,意在连接、链接、糅合传统叙事学与传统女性主义理念,从性别权力角度理解将叙事形式中的声音属性。也可以说,“女性声音”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是通过叙述形式、言说方式、聆听方式等“声音”层面的叙事学考察来表达女性群体的权力诉求,它是女性主义主义叙事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之一苏珊·兰瑟指出,“叙事技巧不仅应看成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还是意识形态本身”,“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存在状况”[5]。的确,从叙事学上的“声音”意涵出发追求女性权力的表达与释放,这是一种新的女性主义策略,也为重内容研究、轻形式分析的传统女性文学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话语增长点。
二、研究视域与话语指向的突破性
因为“女性声音”位于女性主义与叙事学的交汇处,其对研究实践的启示之一便是为传统叙事学研究增加了性别的维度。像布斯的“隐含作者”概念,“这个隐含作家总与‘现实的人’不同——不论我们怎样看待他——现实的人在创作作品时创作了他自己的化身,一个‘第二自我’”[6],布斯以“他”(he/him)指代其所说的隐含作者,但现实生活中的作者却是有具体性别的人,其在作品中“第二自我”是否也有性别,如果有,这“隐含作者”的性别能否与现实中的真实作者的性别顺应一致起来?显然,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学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女性声音”理论的提出则可以做一些深入探析。
对于传统女性文学研究来说,“女性声音”的提出以其对叙事形式的强调深化与复杂化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话语空间。在詹姆逊、伊格尔顿看来,审美或叙事形式本身就是某种意识形态,是作家与他(她)所面对现实之间的一种关系隐喻。但传统女性文学研究并未像重视“写什么”的内容研究那样去重视“怎样写”的形式分析,像《论底层写作中的女性生存策略》、《从中国文学史看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从新时期女性写作看女性之于两性和谐关系的建构》、《当代职场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困境》之类女性文学研究论文,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其基本是在文学社会学的框架下,将艺术形象等同于现实人物、将叙述情节等同于生活事件,这是对热奈特所言故事与话语相区别的叙事学的有意无视或无意忽略。叙事学理论家申丹教授曾言,“女性主义文评中的‘声音’具有广义性、摹仿性和政治性等特点,而叙事学中的‘声音’则具有特定性、符号性和技术性等特征”[7]。“女性声音”将此二者相结合,可谓形式研究与性别研究的双重突破。
另外,“女性声音”在研究视域上的形式分析并不局限于文学文本,还会延伸到语境层面,将提升公众的社会性别认知纳入自身研究视野,这也是其突破传统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创新之处。相对于性别政治的内容研究,因为“女性声音”研究笃信“文化充斥甚至意味着性别的技术,形式和结构对渗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性别起决定作用”[8],其高度重视读者研究,尤其重视将巴特勒解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叙事学相联系,把对叙事形式的研究演绎成打破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建构现代化与多元化社会性别认知的过程。比如沃霍尔认为波伏娃那句名言改为“一个人不是天生为女人,而毋宁说是被叫做女人的”更为合适,因为一方面社会性别具有历史意识形态长久浸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性别身份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不存在本质的、决定性的性别差异,性别规范本身也处于传播、突破、调整的动态过程之中[9]。在此意义上,由文学类型决定并通过重复性阅读进一步累积、强化的叙事类型与模态,对真实读者性别身份的动态建构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笔者认为其甚至高于写作内容的影响)。像沃霍尔将流行的言情小说、肥皂剧的叙事形式称之为具有性别化功能的“情感技术”(technologies of affect)。这些都是内容中心的传统女性文学研究较少涉及的。
话语指向上,“女性声音”研究因为是通过叙述形式、言说方式、聆听方式等形式层面的叙事学考察表达女性群体的权力诉求,能够有效规避传统研究在界定“女性文学”时纠结于写作者生理性别的问题。根据谢玉娥编纂的《女性文学教学参考资料》所言,目前中国学界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大体有这么三种看法:一是只要女性写的就是女性文学;二是按性别加题材加风格的分类,即女性所写的表现女性生活体现了女性风格的文学;第三种是性别加女性意识,即女性所写的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10]。这几类划分标准内涵和外延各有不同,尽管从第一种到第三种有着越来越精确化的趋势,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强调了女性文学是“女性写的”这一写作主体的生理性别的一面,这在理论上有着性别本质主义的简单化倾向,实践上则窄化、局限了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将女性文学限定成了“只与女性写作者相关”的事。在gender(社会性别)观念在理论上已被女性学界充分熟知、接受的情形下,只从创作主体角度界定的这种女性文学概念有点窄化了,对于研究对象的设定来说甚至无异于某种作茧自缚。“女性声音”研究的倡导者之一沃霍尔曾言,“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文本的差异毕竟不在于所谓的内容,而在于他们的讲述方式、话语的特征(感伤的、反讽的或是科学的等)”[11]。这个说法当然也有诸多可进一步追问之处,像所谓讲述方式、话语特征究竟有没有决然的男女之别,“感伤的、反讽的或是科学的”话语方式是从哪个层面界定的,究竟如何界定“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等等。沃霍尔这种明确拒绝将女性写作只与女性写作者的写作相联系的思维,作为“女性声音”研究的一个学理起点,必将拓展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打破传统的性别经验主义、本质主义思维。
文本资源上,新世纪文学叙事形式的新探索为“女性声音”研究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新世纪以来,先锋文学花样翻新的形式实验表面看来有所降低,但正如青年学者晏杰雄所言,新世纪小说的文体形态精神并未减弱,而是出现了内在化、本土化、混沌化的趋向,“超越既往的社会层面和实验层面,走向文本和人本,走向生活世界,外表老实,骨子里其实是很现代的”[12]。新世纪文学的形式实验不像20世纪末那么张扬、极致、不避极端,而是深入到文学文本的叙事机理,以包容性较强的方式呈现出来。群体性的叙事形式变革可能相对少见了,但作家的个性意识、独立品格在进一步彰显,也能催生某种自觉不自觉的文体创新。比如在“个人化”写作问题上,概念性炒作少了,反而更加回到了其原初意涵——完全遵从个人经验、趣味,而不被时代潮流所裹挟。像最近几年崭露头角的写作者梁鸿、余秀华、付秀莹等可以说都是真正的“个人化”,尽管她们都是以农村题材引发文坛侧目,但风格各异、趣味有别,差异性非常明显,无法进行思潮归类,这必然会引发包括女性声音在内的叙事形式上的“个人化”探索。还如关注民生、关爱弱势群体的非虚构写作所采用的“集体型”叙事形式,是与盛行“个人化”写作的1990年代大异其趣的。还如传统纸媒印刷业的相对衰落与电子传媒的强势崛起所带来的“文学场”各要素构成的变化,及信息时代知识爆炸、共识性破灭所带来的碎片性写作与阅读,共同催生了新世纪文学中醒目的“碎片性”叙事方式。而网络文学中女性社群、女生频道的强势出现则构筑了愈演愈烈的“女性向”叙事形态,这些在电子传媒还不算发达的新时期文学中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些都为从文学形式角度索解女性声音提供了足够的文本与文化资源。
三、“女性声音”研究的中国化建构
当然,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社会历史批评与意识形态分析的强大,“女性声音”的叙事形式研究尚较为薄弱和边缘,笔者在此前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土研究实践中的缺憾与问题[13],这里想从正面强调一下其中国研究的贡献和价值。因为叙事学是西方文学研究界的主流方法,很多叙事学理论也是来自西方,加之女性主义直到如今似乎也没有摆脱“来自西方”的学术出身问题,叙事形式层面的“女性声音”问题,包括其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往往被认为是西方化的产物,相关研究是“以西律中”(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本)的学术殖民。
但笔者在此郑重强调的是“女性声音”研究尽管在中国学界尚相对边缘,但这并不意味这它没有形成一定的知识范式,而且这种知识范式更多是建立在中国文本的形式分析实践基础之上的,比之内容中心的一般女性文学研究,其“中国性”甚至会更鲜明。因为一方面,女性声音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20世纪80、90年代起步,彼时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敏感的中国学者几乎从一开始就关注到了这一理论思潮,并积极参与对话、争鸣,基本不存在其他西方文论那样的接受“时间差”;另一方面,其发生发展的年代正是中国文学创作异常活跃的新时期,中国文本的成长谱系、价值与问题基本左右了中国学者的关照视阈,因此,其并非那种想当然地“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本”的研究路径,具体体现在:
从中国文学语境出发,对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文本分析而得出的概念、范畴进行补充、修正,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像“性别化的干预”理念是沃霍尔从对18、19世纪英美文学研究中得出的,陈淑梅通过对改革开放之初女性小说的考察发现,有的女性写作不自觉应用了“吸引型叙事干预”,但却未增强话语权威感,反而形成了“主体可疑”的叙事话语,也有的采用了“疏离型叙事干预”,但并非性别意义上的女扮男装叙事,而是借用个人言说社会伦理的乔装打扮叙事[14]。这与沃霍尔结论亦大相径庭,是中国学者立足中国文本的分析;而对于苏珊·兰瑟的“话语权威”理论,也有论文提到,新世纪以来部分女作家叙述权威意识的淡化恰恰是其性别观念更加从容淡定的表征,叙述权与性别权未必总是顺承关系,在新的时代与社会语境下会出现新的变体[15]。这些都是已有中国学术成果的创新之举,还有更多新发掘、新阐释,本成果各章节中会有更多详实论证。
与西方理论进行直接对话,指陈其失误之处,像对于兰瑟提出的“公开型/私下型叙述”的说法,申丹指出兰瑟进行文体分析,依据的却是叙事学理论,结构意义上的“公开”与“私下”区分同常识意义上的区分会产生混乱,“兰瑟试图用叙事学来解释这一切,其实就这封信中的不同文本而言,兰瑟进行的主要是文体分析,在涉及连接表面文本和隐含文本的那组语法上的否定结构时,情况更是如此”,她与兰瑟本人当面进行了交流,并得到了其理解和认同[16];而兰瑟所说的集体型叙事只存在于女性写作中的问题,申丹也找出了相反例证认为少数男性写作中亦存在此类型[17],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世界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勘误与贡献。
对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未曾涉及到的一些文学现象进行原创性学理总结。像在“女性向”叙事方面,邵燕君教授挖掘网络社群的“异托邦”性质及其社会性别建构的积极作用,将女性向网络叙事表达的“网络女性主义”称为借助设定虚拟世界而达成的性别心理养成功能的“培养皿”,“从象征界退回到实在界,在那里,没有纯情少女,也没有天生荡妇;没有女神,也没有女汉子;没有全职太太,也没有灭绝师太……一切欲望都可以恣意生长。要想脱胎换骨,必须回到‘子宫’(笔者注:女性欲望的全方位释放),而当新的生命长出来之后,又需要一个‘培养皿’”[18],这些都是西方“女性声音”研究未涉足的领地。还有,在“我阅读”层面具体区分郭敬明等大众化“女性向”叙述与小众化女性网络社群“女性向”叙述在性别建构层面性质的不同[19]等,则是将“女性声音”阐释同大众流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尝试。这些都是西方传统女性主义叙述学甚少涉足之地,体现了中国文论的原创性。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内容研究为主的传统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女性声音的叙事形式研究更鲜明体现了在民族伟大复兴阶段中国学术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