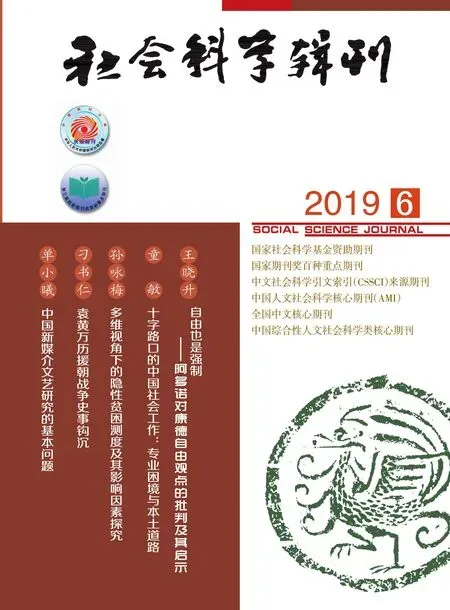《文心雕龙》“物色”说之“感物”新论
2019-02-18张利群
张 利 群
中国古代文论对心物关系的讨论,形成了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感物”说传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一章针对心物关系的讨论,构成“感物”说重要理论支柱,也是刘勰文论体系中的重要篇章;但《物色》在《文心雕龙》体系框架及篇章结构中被列为稍后部分的第46 章,也就是被放在第45 章《时序》到第 49 章《程器》的批评论部分,似乎远离创作论部分。陆侃如、牟世金认为:“不过,其中《时序》、《物色》两篇,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两方面的内容。《时序》从历代政治面貌、社会风气等方面来评论作家作品及其发展情况;《物色》从自然景物、四序变迁方面来评论《诗经》、《楚辞》、汉赋及 ‘近代以来’ 的创作情况。两篇比较起来,《时序》侧重于文学批评,《物色》侧重于文学创作。”另外,《物色》与《时序》排列一起,刘勰也有其“为文之用心”①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2008 年重印。以下刘勰《文心雕龙》引文全部引自此书,不再注明出处。。《时序》侧重文学与时代关系讨论,《物色》侧重文学与自然关系讨论。因而指出:“从现在的《文心雕龙》体系来看,在《时序》之后紧接《物色》是未尝不可的。《原道》中即分论 ‘天文’ 和 ‘人文’ 两个方面,《时序》、《物色》两篇,正是分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两个方面,可见《物色》在《时序》之后,正符合刘勰的原意。”〔1〕此论颇有一定道理。《时序》与《物色》分别从两方面讨论文学关系问题,无论从创作论还是批评论角度而言,都指向文学发展规律及内在逻辑原因探讨。《时序》基于文学与历史时代关系,《物色》基于文学与自然(生活)关系;《时序》侧重于文学发展的时序逻辑,《物色》侧重于文学创作活动的主客体构成逻辑;《时序》侧重于文学发展的时代特征,《物色》侧重于文学创作源泉的感物特征。由此可见,二者相辅相成,具有内在逻辑及学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物色”基于“感物”说之心物关系讨论,几乎贯穿或渗透《文心雕龙》所有篇目内容,尤其体现于《原道》《明诗》《神思》《体性》《定势》《时序》《物色》诸篇,通过“物色”将“感物”说创作观及审美观推进一大步,更为深刻地揭示“心物交感”之文学创作规律及特征,凸显刘勰“物色”对“感物”说创新发展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物色”对“感物”说的传承发展及重构
中国古代文论的“感物”说既是对文学规律与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体系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历代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感物”说传统。刘勰《文心雕龙》不仅传承弘扬“感物”说传统,而且以“物色”说创新发展了这一传统;不仅以“心物交感”夯实了中国古代文论“感物”说理论根基,而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创作论及其文论批评优秀传统。
“感物”说是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对文学创作心物关系的认识与把握,即文艺创作基于文艺与生活(包括自然、社会以及文艺创作对象材料〕关系而在感应、感受、感悟、感兴生活基础上对创作规律特征的理论概括。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对象、资源,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之理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感物”又是基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改造自然、认识自然以及改造与认识人自身的一种必要的行为与活动方式,具有人类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哲学意义,也具有人类存在、生存、发展的人类学本体论意义,故“感物”说带有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论意义。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无论是中国古代“感物”说还是西方古代“摹仿”说,无论是基于对文艺起源发生问题的追溯还是基于对文艺创作源泉问题的探讨,尽管中西理论有所差异,但都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地指向这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艺术审美规律特征的共同认识,并分别形成中西文论批评传统。
中国古代“感物”说在先秦时期发端并形成思想源流。《尚书》“诗言志”作为中国文论批评“开山的纲领”〔2〕,反映出“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对原始巫术宗教之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事象场景的模拟,逐渐生成仪式化诗乐舞形式,以求“神人以和”及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由此生成“感物”基因。《易经》“卦象”将其符号意义与自然物所产生的对应关系发挥想象,姑且不论其中所带的神秘性、神灵性、天命论色彩,但“卦象”所遵循宇宙、乾坤、阴阳、天地万物运行变化之逻辑不无道理,其中孕育“感物”萌芽。《周易·说卦》:“昔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此奠定“感物”说哲学思想基础。《诗经》之“六义”,无论是风雅颂还是赋比兴,从创作方法而言,其中所蕴含的“感物”因素不言而喻,如《关雎》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印证感物而比兴的“感兴”创作方式。儒家思想在“感物”文艺观上有所体现,《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阐明心感于物而动之理。道家思想在“感物”审美观上亦有所体现。《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阐明了基于“道法自然”而“感物”之理。由此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奠定“感物”说思想基础与理论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文的自觉时代”,其标志之一是文学创作“感物”说滥觞,形成这一时代特征及文论批评语境。一方面深化拓展创作所“感”之对象内容,另一方面也深化拓展所“感”之“物”的对象内容,形成“感兴”“感世”“感时”“感事”“感怀”“应感”“感悟”“感思”等范畴内涵及话语空间。刘勰前后,曹丕《典论·论文》从“气”之生命感悟角度,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感慨“夫然则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正是基于万物迁化之“感物”而感悟到光阴及生命流逝之大痛,由此产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追求精神。曹植《与杨德祖书》:“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正是从民间文学“感物”之可取之处感思创作源流的结果。陆机《文赋》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挚虞《文章流别论》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序,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萧统《文选序》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如此等等,形成历代“感物”说线索脉络及文论批评传统。
刘勰在中国古代文论“感物”说建构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对于在他之前所建构的各家学说而言,不仅论证阐发更为具体细致,而且更为系统完整,形成“感物”说思想理论系统,可谓佼佼者与集大成者。刘勰“感物”说贯穿《文心雕龙》全书,是其思想及文论批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序志》在自叙为文动机之志曰:“夫有肖貌天地,秉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有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阐发其“为情而文”而非“为文而文”的写作动机,即有所感而为文,包括感物、感世、感事、感怀、感兴等丰富内容。基于此,《原道》曰:“文之为德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类似论述在《文心雕龙》诸多篇章均有涉及。《物色》篇无疑是“感物”说专论,不仅系统完整阐发“感物”说思想理论,而且有所创新发展,为“感物”说增添新质及新的内容,形成刘勰“感物”说的特点与创新点。《物色》之“感物”说新论在于:一是“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既阐发“感物”从物到容、进而到情、再而到辞的发生过程,又揭示“感物”说涵盖的物—容—情—辞之要素构成;二是“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以此强调感物与想象的关系,凸显感物中的想象要素的功能作用;三是“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坚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阐发创作情感不仅触发于感物,而且原发于感物,由此作家创作成功得“江山之助”;四是“写气图貌,既随物而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提出“心物交感”之论,构成物之会心、心之会物的双向同构、相互交感的“感物”说。如此等等,形成刘勰“感物”说理论系统及基本内容,体现了对以往“感物”说创新发展精神及其特点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刘勰针对“感物”更进一步阐发文学创作所感之“物”的“物色”特征,由此拓展深化对所感之“物”的认知及“感物”说深层内涵与意义,既进一步厘清心与物、物与象、情与景、意与境、形与神亦即文学与生活、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关系,又提供了“心物交感”的内在逻辑及学理依据。《物色》篇以“物色”概念命名,可知刘勰以“心物交感”论创新“感物”说之动机意图及意义,以此创生并聚焦“物色”范畴,使其成为“感物”说的基本范畴及核心范畴。《物色》全篇围绕“物色”拓展深化“感物”说话语空间、理论空间及阐释空间,最后导向“心物交感”宗旨及目的。王元化指出:“刘勰在《物色篇》中采取了当时普遍的说法,从‘物’、‘情’、‘辞’三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去阐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的文学主张,肯定了外境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了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了 ‘写气图貌,既随物而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的看法。这种见解,不仅为陆机、钟嵘等人所未发,而且也是后来的论者所罕言的。”〔3〕在此基础上值得提出来加以强调的是,“物”“情”“辞”三者关系中不能忽略“物有其容”之“容”,亦即“容色”,既在于强调文学感物的特殊性及针对性,又在于深化拓展三者的内在逻辑及“心物交感”的学理依据。由此可见,刘勰提出“物色”是对“感物”说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物色”辨析及其内涵外延阐释
“物色”作为“感物”的重要范畴,不仅使“感物”之“物”对象内容理解更为深化拓展,而且也对从“感物”到“物色”再到“心物交感”的递进层次与结构逻辑进一步丰富完善,形成“感物”—“物色”—“心物交感”的层次与逻辑。由此可见,“物色”正是“感物”与“心物交感”的中介及桥梁,基于“物色”,才能厘清从“感物”说到“心物交感”论的发展脉络与内在逻辑。
其一,“物色”说的基本内容及理论构成。刘勰“物色”说基于“感物”基本内容与理论构成。刘勰“物色”概念贯通《物色》全篇。首先,着眼于所感之“物色”对象辨析。《物色》开篇即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即着眼于春秋代序的四时变化与阴阳之气的浸润影响,揭示出“动物深”“物色之动”的宇宙乾坤、天地万物运行规律与特点,突出所感之“物”的时空运动、变化、状态、形态、气象、容貌等形体特征以及生命、活力、生动、气韵、品质等内涵特征。由此概括出所感之物为“物色”从而触发“心动”“心摇”的观点。其次,着眼于主体所感之情感变化与心理状态辨析。刘勰针对所“感”阐发四时变化与阴阳之气对人的影响及其所引发的心理情绪反应,“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爽;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既提供了主体所“感”之基础条件,又在“感物”基础上进一步触动和激发主体的心理反应与情感活动,触发作家创作感兴、感怀、兴会、会通。最后,着眼于主客体关系提出“心物交感”说。《物色》基于“感物”说提出“心物交感”论,是对文学主客体互动交融关系认识的飞跃,也是《文心雕龙》文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及思维方式。纪评曰:“‘随物宛转,与心徘徊’ 八字,极尽流连之趣。会此方无死句。”〔4〕这一看法颇有见地,归而言之就是“心”“物”交互感应,也就是说“心”可“随物而宛转”,“物”则“与心而徘徊”,阐明文学创作的心与物交互感应融为一体的状态,因而“心物交感”应是基于“感物”之“物色”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心物之所以能够交感,从思想渊源而论,一方面源自于原始巫术、原始宗教遗留的人与自然交感式思维方式影响,通过《周易》而得以传承及流布;另一方面源自于《庄子》“庄生梦蝶”寓言所阐发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也分矣。此之谓物化”〔5〕,即庄周与蝴蝶相互转化,“物化”为一,亦即道通为一,由此感悟及生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刘勰则以“物色”为“心物交感”提供内在逻辑与学理依据,即心物交感于“物色”,或基于“物色”而“心物交感”。因此,《物色》将“物色”概念运用到极致,不仅有“物色之动”“物色相召”“物有其容”“物有恒姿”“物色虽繁”“物色尽而情有余者”等,而且描绘形容“物色”之表现形态的色彩、线条、形状、光彩、状态、情貌等现象也比比皆是。围绕“物色”形成的“感物”“动物”“体物”“物貌”“物容”“物姿”“穷形”“形似”“江山之助”等概念命题,构成刘勰“物色”说基本内容与理论构成。由此可见,从“感物”到“物色”,提供了“心物交感”的基础条件,旨在阐发创作主客体关系的内在逻辑及学理依据,这正是“物色”说创新发展“感物”说之价值意义所在。如果不提“物色”,那么“感物”说就会存在一定的不足,“心物交感”论也就缺乏一定的内在逻辑及学理依据。正是基于“物色”,“感物”与“心物交感”有了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从而使“感物”说导向“心物交感”说,成就了刘勰对“感物”说的创新发展之功。
其二,“物色”之“色”的特征及功能意义。“物”作为客观存在物概念,所指对象固然包括宇宙乾坤、天地万物以及自然与生活现象,应该说对象所指非常明确。但何以又提出“物色”呢?《文心雕龙》确实大量使用“物”这一概念,以之作为相对于创作主体而言的客体对象。刘勰在“物”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物色”,旨在从文学创作角度明确指出客体对象之“物”的特征,以确定“物色”作为创作对象,由此才能构成“心物交感”状态。那么,“物色”与“物”有何区别与联系呢?毫无疑问,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物”是作为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万物。“物”作为客观现象存在,一方面从表现形式看,以其千姿百态之形态、五光十色之色彩、斑斓绚丽之花纹、纵横交错之线条等表现形态与运动方式呈现,故有物之“色”存在;另一方面从现象学角度看,所谓“现象”则是处于人与物关系中的“物化”“人化”现象,亦即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在人的视阈与视角下呈现的物之现象,遂生成意向性存在之物,亦可谓“对象化”及“人格化”“拟人化”之物,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物”,抑或“物化”之物。因此,所谓“物色”固然具有客体作为客观存在物的自然属性,但也具有联系于主体的关系性、间性、互文性,尤其是指涉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物色”,在创作主客体关系中,既含有客体的合规律性,又含有主体的合目的性;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又是基于主客体关系生成的意向性存在物。诚如王国维所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6〕因此,“物色”正是“物”之物性的内涵特质所在,“感物”所感之“物”也正是基于作者创作需要所构成主客体关系中的“物色”,事实上就是“物”之“色”的内涵特质,这正是文学创作对象的内涵实质所在。《说文》释“色”之义曰:“颜气也。从人,从,凡色之属皆从色。”〔7〕故“色”本义为脸颊上的脸色、肤色,以粉敷脸为容色,引申为色彩之颜色、彩色、光色等。“色”与颜、光、容、状、貌、纹、文、美等概念相关,作为元范畴,构词有脸色、颜色、色彩、五色、色泽、容色、肤色、气色、姿色、水色、情色、景色、角色、音色、声色、形色等。“物色”则具体指自然万物之色彩,包括自然现象之景色、山色、水色、天色、光色以及日月星云、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之色彩、线条、斑纹、形态、情状等义的引申与延伸。“色”与“文”联系紧密,“文”通“纹”,线条、斑纹、色彩、形态、光泽之“纹”,正所谓“错画为文”“交错为文”“物相杂为文”。《原道》:“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由此可见,宇宙天地、自然万物之“色”亦可指“天文”“理地”之线条、斑纹、色彩、形状,由此体现“道之文”,即遵循自然之道而显现的自然之“文”,亦即“天地有大美”之自然美、形式美、形象美。“物色”亦如是,所指自然万物之景色、色彩、色泽、光泽、形貌、变化等表现方式与运动形式,亦可谓自然美、形式美、形象美之呈现及显现。
其三,“物色”之“色”的内涵实质。“物色”聚焦于“物”之“色”,表现出物之文(纹)、物之华、物之形、物之光、物之容、物之貌等形象性、绮丽性、审美性特征。《原道》用大量笔墨描绘“物色”特征,凸显“物色”之物的“色”特征,呈现万事万物之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感物”所感对象并非为“物”而是“物色”,亦即所感的是“物色”之“物”,或物之“色”。创作主体之感受、感应、感兴就在有所“感”基础上更为深入地感悟到“物色”的内涵特质,不难发掘其所蕴含、表征出生命、活力、运动、变化、鲜活、生动、气韵之内涵实质。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自然之道”不仅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自然之道”,而且也是“感物”之“物色”生成的“自然之道”,也就是说,物之“色”也具有“自然之道”内涵实质。先秦道家以“道”为名,并将“道”作为宇宙天地、自然万物本体、本元、本源来讨论。《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原生于“道”,遵循自然之“道”才呈现出“物色”之线条、形态、花纹与色彩,可见“道”不仅是“物色”之内涵特征,而且也是“物色”之本体与渊源,故《原道》提出“道之文”“道心”“自然之道”,不仅揭示“人文”内涵实质,而且以之揭示“物色”的内涵实质。所谓“道”,广义而言可指宇宙乾坤本体、天地自然运行规律、万事万物本性,亦即顺其自然可谓“道”。狭义而言,针对“感物”之“物色”而论,即蕴含于万事万物中的自然规律,遵循规律而生成自然美内涵特征。从文学创作“感物”角度而言,“物色”之“色”尽管为物之表现形态与运动形式,但具有“道”之内涵实质,并源自于“道”。“色”之于“道”可谓“道”的表现形式及特征,“道”之于“色”,可谓“色”的内涵实质。从“感物”之“物色”而言,“色”可谓物之形式,“道”可谓物之内容。因此,“感物”从所感“物色”而“原道”,才能发掘“物色”内涵实质,发现“感物”之物—色—道的层次与构成,厘清“感物”—“物色”—“原道”的内在逻辑,真正领悟到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之理,辩证把握创作与生活、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的关系。因此,“物色”不仅呈现万事万物的外观形态,而且蕴涵“自然之道”内涵实质。
三、“物色”之“心物交感”对“感物”说创新发展的意义
《物色》篇主旨为“心物交感”论,厘清“物色”之内涵特质,既为“感物”说传承发展及创新突破提供依据与逻辑,又为“心物交感”论奠定基础与条件。一方面,基于“物色”的“感物”,所感对象是“物”之“色”,亦即色彩、线条、形态、光影、情状、运动、变化等表现方式与呈现形式,以及所蕴含和表征出生命、生机、活力、气韵之内涵特质,故以“感物”之“物色”以达成“心物交感”之目的;另一方面,基于“感物”的关键在于“心”感于“物”,亦即作家以创作的“有色”眼睛观物感物,由此感兴—兴会—会通,进入创作主客体关系即心物关系的最佳状态,即“心物交感”状态。“感物”何以能“物色”,关键在作家之心的意向性与感悟性。以“心”观物,便有感于“物色”而动心与感兴,故“物色”说具有重要的功能作用及深远意义。
其一,“感物”之“感”的主体性功能意义。“感物”一方面指向所感对象之“物”的“物色”特征及内涵;另一方面基于“感”指向“感物”者,即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感物”素质和能力。马克思指出:“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8〕人的眼耳鼻舌身心等感觉器官及其感受功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自身的结果,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不断“人化”与“对象化”的结果,故人类身心及其全部感官对外部世界的感觉都是基于历史建构与文化积淀而形成一定的目的性及一定的主体性视角,亦即具有一定的意向性之感应、感受、感悟。因此,“感物”之“感”不仅具有感应、感受、感悟、感怀、感兴、兴会、会通等含义,而且具有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主体性、能动性、选择性、创造性等功能意义。由此,“物色”可谓创作主体“感物”的“有色”眼光与视角,导致所感之“物”指向“物色”以达“心物交感”的目的。此外,“感物”基于创作行为活动生成心物关系之基础条件与环境氛围,成为创作之“感物”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感物,所感“物色”具有“感物”的特殊性及内在规律特征,提供“心物交感”“神与物游”“情景交融”的理论基础与学理依据。刘勰以“物色”重构“感物”说,其原因及理由主要在于:一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文的自觉时代”,文学独立性与自主性凸显,而且亦是“人的自觉时代”,文学主体性与人文性空前强化,由此将文学视角从客体转向主体,抑或主客体关系,走向对文学自身规律及发展内在逻辑的探讨;二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高潮期,出现曹丕、曹植、陆机、宗炳、葛洪、谢赫、挚虞、沈约、钟嵘、萧统等文论家,刘勰是其中的佼佼者,《文心雕龙》既为文论批评集大成者,亦为文论批评创新发展的标志。“物色”说既是对当时丰富多彩的文学及个性化创作的总结提升,也是文论批评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三是历代“感物”说发展至此不仅需要系统总结与理论阐发,而且需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以“物色”及“心物交感”拓展深化“感物”说内容及研究深度,厘清从“感物”到“物色”再到“心物交感”的发展脉落及其内在逻辑,建构“感物”说生命活力与精神传统;四是刘勰思想中糅合儒道释精神,通过《原道》《征圣》《宗经》等总论体现于“文心”“雕龙”创作论、文体论、形式论、批评论中,文学之“感物”因此而增添“物色”新质,才有“心物交感”的飞跃。由此可见,“物色”说产生不仅具备充足的基础与条件,而且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与内在逻辑。
其二,文学之“心感”的特征及意义。文学创作之心感于“物色”,既强调作家“感物”必须“心感”,即着眼于心灵精神的感应、感悟、感受、感兴、会通,又凸显“心”在“感物”过程中对“物色”的发现、选择、起兴、想象、联想的主体性与主导性作用。在中国古代文论语境中,“心”与“志”“精”“气”“神”“意”“情”“性”“道”等范畴相关或互文,形成“文心”范畴群及要素系统。刘勰提出“文心”说,不仅以《文心雕龙》书名表明“文心”创作观及其文论批评体系核心,而且在《序志》开篇即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文心”含义,一是指“为文之用心”的创作动机意图,形成作家创作原因及文学动力机制运行的原动力;二是指作者的创作主体构成及其中枢系统之“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形成“文如其人”的作者批评论以及“体性”风格论传统;三是文学作品之“文心”,即文之心脏、中心、枢纽、关键。《神思》:“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更为重要的是,刘勰《原道》阐发了“心”的本体论意义,既基于天地人“三才”关系提出人为“天地之心”,凸显人作为“天地之心”的重要地位及价值意义;又基于“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提出人文及文学亦为“天地之心”,“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揭示文学“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之功能作用,凸显“人文”作为“天地之心”的价值意义。由此,“人心”生成“文心”,“文心”建构“人心”,形成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源流关系与同构关系。中国古代所指“心”,一方面指向“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即统摄人体所有感官及其功能的中枢神经系统——大脑,以精神心灵主导的思维系统形成直觉、感觉、知觉以及通感、统觉、联觉,使“心”成为人的身与心、灵与肉、形与神、感与知关系构成的枢纽和源泉;另一方面指向以“心”为内核之人的精神、心灵、思想、情志、意念、人性、人文等内涵与外延,使“心”成为人的存在及意向性之所指。因此,从文学本体论角度而言,“文学是人学”实质上是“心学”。刘勰基于“文心”以“原道”,实质上是从“原人”到“原心”,“因此,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体系的基点的 ‘原道论’,其实质就是 ‘原人论’”〔9〕,故“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从文学主体论角度而言,基于创作之心物关系即主客体关系而生成作家之创作主体,作家创作之心既是“为文之用心”的动机意图,也是创作主体心智结构的才、气、学、习等要素构成系统,形成“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的文如其人特点,创作之“心”正是作者个性、主体性、独创性以及文学风格之源泉所在。从文学创作论角度而言,基于“感物”而“物色”,继而“感兴”以至“心物交感”,故“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原道》),作者触物感兴不仅是心感于物而后动,而且也是“心”有所待而带有意向性所感之结果。
其三,“物色”导向“心物交感”论的逻辑及意义。“交感”指交互感应,即“心”感于物而“物”应于心,指创作主客体关系的互动交融状态及双向交流机制。王元化认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彩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二语互文足义。气、貌、彩、声四事,指的是自然的气象和形貌。写、图、属、附四字,则指作家的模写与表现,亦即《骆注》所云 ‘侔色揣称’、摹拟比量之义。刘勰以此表述作家的创作实践过程,其意犹云:作家一旦进入创作的实践活动,在模写并表现自然的气象和形貌的时候,就以外境为材料,形成心物之间的融汇交流现象,一方面心既随物以宛转,另方面物亦与心而徘徊。”〔10〕由此将刘勰这一经典名句概括为“心物交融”或“心物交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表达文学创作规律特征的重要命题。“心物交感”基于“神人以和”“物我为一”“天人合一”思想,建构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心感于物”“心游万仞”“神与物游”“情景交融”“托物言志”“意与境偕”“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等创作方式及文学传统。由此可见,从“心感于物”到“心物交感”的发展,关键在“感”与“交感”的区别,或者说“交感”是对“感”的深化、发展与突破。创作之“感物”,不仅在于“随物宛转”之心感于物,而且在于“与心徘徊”之物应于心,形成“心物交感”双向交流机制,推动作家创作进入“兴会”“感兴”“会通”的“神与物游”最佳状态,最终获得“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既然如此,那么“心物交感”依据及逻辑何在?《庄子·秋水》中庄子“知鱼之乐”理由主要有四:一是基于“游于濠梁之上”的“游”之环境氛围,营造出可供进入艺术化和审美化之场域空间,由此缔结审美主客体关系,故庄子在“游”之环境氛围中观鱼,故能“知鱼之乐”;二是庄子具备“游”的兴趣和心情,心之乐影响游之乐,进而产生观鱼之乐,由此对应于“鱼之乐”,这可理解为庄子将自身的心之乐移情于“鱼之乐”,“鱼之乐”无形中成为心之乐的表征物与象征物,成为庄子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表达方式;三是基于一定视角的“感物”而聚焦于物之“物色”,即“儵鱼出游从容”之“游”,故能与庄子“游于濠梁之上”之“游”殊途同归,异质同构,庄子正是以“游”之“有色”审美眼睛观照到鱼之“游”的“物色”,故而能“知鱼之乐”;四是基于“游”“观”“乐”之情境、条件、心情,“鱼之乐”与“知鱼之乐”可谓构成“心物交感”机制及状态,庄子之“心”与鱼之“游”,在审美观照之乐视域中交互感应,心感于物而物应于心。庄子“知鱼之乐”而“鱼之乐”可反观庄子之心,故“鱼之乐”实质上为庄子“心之乐”,由此可见“心物交感”主客体交融的审美状态。从这一角度看,“物色”契合创作之心的“有色”眼镜,亦可视为“心物交感”的结果。故《神思》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通过“感物”而激发“感兴”,由此进入“神思”之“神与物游”状态的“意象”创作过程,正是“心物交感”的必然结果。
刘勰《物色》以“物色”作为文学创作对象来讨论“感物”问题,而“物色”对“物”之性质特征的界定与阐发则是紧紧围绕心与物关系来讨论的,其核心命题就是“心物交感”。也就是说,刘勰认定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精神创造活动,因而文学作为作家的创造物,本质上是“人学”亦即“心学”。与“心物交感”相互印证的还有本体论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原道》),创作论之“神与物游”(《神思》),方法论之“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比兴》),鉴赏论之“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知音》),等等,均表达文学活动中的主客体交感状态,揭示出文学规律特征。“心物交感”不仅是贯穿《物色》的中心主旨,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思想和核心观点。因此,文学“感物”的目的旨在“心物交感”,“感物”何以能指向“心物交感”,关键在“物色”。“感物”在于物以“色”而动心,“心感”而见“物色”,由此形成“心物交感”之情理逻辑与学理依据。由此可见,刘勰“物色”说不仅传承发展了“感物”说,而且基于“物色”进一步阐发“心物交感”论,这既是“物色”说价值意义所在,也是“感物”说创新发展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