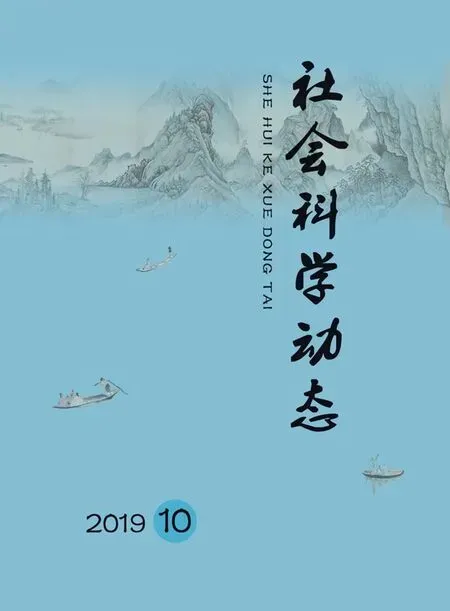杜书瀛访谈:回忆我的老师
2019-02-18李世涛
李世涛
编者按:杜书瀛,山东宁津人,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历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艺理论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论李渔的戏剧美学》《论艺术特征》《论艺术典型》《文艺创作美学纲要》《文学原理——创作论》《文学会消亡吗》等。作为新时期我国文艺学界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文艺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一直坚持在文艺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并敢于结合现实提出自己的学术思想,针对文艺理论原问题作出新的阐释,迄今笔耕不辍,每年都有新著问世。本期刊发由中国艺术院李世涛研究员执笔的访谈文章,让我们跟随杜先生满怀深情的回忆,追寻两代学术大家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
李世涛(以下简称李):杜先生您好!我知道,您最初在山东大学求学,后来又做蔡仪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在您的求学、研究生涯中,您一定有不少学界的师长同事,希望您给我们谈些您们交往的情况。我建议,首先还是从您的求学时开始吧!
杜书瀛(以下简称杜):那就先从成仿吾校长谈起吧。我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最感兴趣的是成老他们创造社的活动以及与鲁迅的笔墨官司,希望他能够给我们讲讲那段经历,甚至奢望能去拜访他,可惜没有机会。有一次晚饭后在校园(山大迁到济南不久的原农学院旧址)碰到过成老与其夫人张琳教务长带着女儿散步,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深蓝中山装,个儿不高,腰板却挺得直直的——后来知道他留学日本时学的是“兵科”,曾任湖南兵工厂技正,国立广东大学理学院教授兼黄埔军校教官、军校兵器处技正及代理处长——此刻仍见当年训练有素的身板儿。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成老,两颗门牙突出,对你一笑,开朗而平易,和蔼可亲。当时我不好意思冒然打扰他,只是给他鞠了一个躬。他很亲切地还礼,还问了我在哪个系读书。
在校期间,我听过好多次成老的报告,遗憾的是,大都与文学上的事不沾边儿。但有一次开大会,大概与纪念鲁迅先生有关,成老忽然讲起了他与鲁迅之间的故事。大体是说:鲁迅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我年轻时幼稚,同鲁迅先生打过笔仗。但后来与鲁迅先生关系很好,还有过合作。1927年4月1日,成仿吾和鲁迅、王独清等人发起,联名在创造社办的《洪水》第三卷第三十期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揭露和控诉英、法帝国主义帮助军阀孙传芳残杀中国工人阶级的血腥罪行,呼吁“世界无产民众赶快起来结合去打倒资本帝国主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当年成老还通过鲁迅先生找到党的关系……成老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于三十年代初从欧洲回到上海,奉党中央之命,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了几年。其间张国焘拉红四方面军主力队伍离我们而去,把根据地四部电台全部带走,从此,鄂豫皖根据地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在这之前,大约是1933年秋,党组织派我向中央汇报工作。那时我身患严重的疟疾,又黑又瘦,从武汉乘船抵达上海,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举目无亲,如何接上党的关系?真是一筹莫展。一天,从报纸上看到有文章骂鲁迅是‘准共产党’,忽然受到触动,脑子里闪现出一线希望,心想:‘何不去找鲁迅?’我通过内山书店老板打听鲁迅消息。内山一见到我,十分惊讶,说:‘你还活着?’我说想见见鲁迅先生。三天之后,按约定在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见到了鲁迅先生,并通过他接上了党的关系。”后来在鲁迅夫人许广平写的《鲁迅回忆录》里面,看到这样的记载,可以印证成老的话:“一般人只知道鲁迅和成仿吾同志有过一次笔墨之诤,但不知道和成仿吾同志之间还有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故事。记得有一天,鲁迅回来,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上眉梢,我忍不住问个究竟,他于是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我才知道他欢喜的原因所在。前不久,我有机会见到了成仿吾同志,问起他是否在上海见过鲁迅?他说:‘是的,并且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这件事情使人非常感动。成仿吾同志和鲁迅有过文学之争,这是谁都知道的,但由于革命的目标一致,思想、政见的一致,他们两人之间的争论终于统一了起来,意见一致了起来,这时看到鲁迅毫无芥蒂地像接待亲人一般地会见了成仿吾同志,真使在他旁边的我,都要为之高兴不已。”成老在鲁迅先生逝世时写过《纪念鲁迅》一文,说:“关于过去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问题,今天已经没有再提起的必要了。自一九三三年以来,我们是完全一致了,我们成为战友了。我们的和好,可以说是团结统一的模范,同时,从此他成了拥护统一的最英勇的战士。一九三三年底我与他在上海见面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什么隔阂了。”然而,不管成老自己如何说与鲁迅“没有什么隔阂了”,“文革”期间,还是有人把他当年与鲁迅的那场论争作为“反对鲁迅”的天大罪状予以讨伐,并往死里批斗。听说,这位七十老翁,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一次,批斗者朗诵毛主席诗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以此为自己壮胆,但是把“罴”读成“罢”(bà)。成老强挣着昂起头,认真地对哪位念错字的同学说:“同学,你读错了,那个字不是‘罢’(bà),而是‘罴’,它音要念‘皮’(pí)的音!”令人感慨不已。
成老当山大校长时,亲自作词,请著名作曲家郑律成谱曲,创作了山大校歌,头几句是:“东临黄海,南望泰山,这儿是我们学习劳动的乐园。”1983年 8月,86高龄的成老仍然登泰山,并题词“岱宗夫如何”。1984年 5月,成老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享年87岁。
李:作为中国著名高校,山东大学以文史系而闻名,这得益于在此任教的著名的文史学者。其中,闻名遐迩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功不可没。不知道您上过他们的课没有?
杜:我上山东大学,最早接触的教授就是陆侃如和冯沅君两位先生。1958年,因为系里分派搬家任务(从青岛迁至济南),让我与另一位同学去帮助两位教授整理和捆扎书籍、用品。我们按时来到两位先生居住的鱼山路宿舍,只见门楣写着“冯·陆”两个醒目的字,两位先生笑脸相迎。我的第一印象:冯先生齐耳根短发,略微含胸;衣着十分普通,上身双排扣列宁装,原来是蓝色,许多地方已经褪得发白。陆先生中等个儿,也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件旧衬衣,罩着袖套,特别和气,细心人也许会觉察出他反右运动后心理上的某种谦卑。冯先生早已在客厅沏好了茶,说是先喝杯水再干活。我们则直奔主题,请先生吩咐,开始工作。两位先生生活简朴,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陈设,而且基本没有自己购买的家具——桌椅、书架等等,都是公家配给。书房里,高高的书架,排排摆放,满满当当。当时他们两人的工资不少,每人月工资都为345元,仅次于国家最高领导人,又有丰厚的稿费,经济上相当富裕。但他们除了教书和做学问,没有其他爱好,生活上更没有什么特别需求,甚至还不如一般职工。他们唯一的嗜好就是购买书籍,据说冯陆两位先生藏书三万多册。令人惋惜的是,他们在“文革”时期的不幸遭遇中被迫卖掉这些藏书的相当大一部分,有的则流失了。
1958年秋,山大搬到济南后,虽然“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但总算可以开课了。我上得最多的课是陆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差不多有一年或是一年半时间。每到陆先生的课,我早早在文史楼角上的大教室前排占好了座位。第一堂课,陆先生穿一套咖啡色西装走进来——这与我在青岛帮他搬家时的落拓样子迥然不同,这大概是他解放前留下来的旧装,每逢隆重场合才穿。那时陆先生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称为“摘帽”右派),他再登讲坛,重获教课机会,心存感激,分外庆幸,内心自然十分珍惜和重视。那年他近六旬,仍然显得那么潇洒。
那天,陆先生首先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说:“同学们大都初次接触古文,难免感到有些困难,我尽量讲得详细。有些古字古词,不但意思要弄明白,而且读音也要准确,开始学,就要打下扎实的基础,不能马虎。课堂上听不明白的,课下还可以问我,我家住得不远,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我年纪大了,睡觉少,夜里十一二点也不睡,找我也不晚。”
这最后几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陆先生给我的感觉是既认真,又谦和,而且特别热情。我虽然没有到陆先生家里去打扰,但是在学校的课余时间,是经常找陆先生问问题的一个。陆先生用的教材是郭绍虞先生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我课堂上听课和课余问问题,恨不得把陆先生的解释毫不遗漏地记下。每次上课前我都把铅笔削得尖尖的,便于写小字——在课本上每一页的页眉和字行之间,我都密密麻麻写上了陆先生的注释和讲解。五十年前的那套课本,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只是有一本书皮儿掉了),之后,每每遇到难解的字词,我还是到陆先生当年讲课的笔记中寻求帮助。
冯先生给学生开的课是“元曲选”和“宋词研究”,可惜的是,她开课的那一年我正好因病休学,没有赶上聆听,这是我遗憾终生的事。冯陆两位先生是当年我们最崇拜的教授之一,因为他们不但才气横溢,而且讲课生动、耐听,一下子就能抓住听众的心。有同学回忆,冯先生有一次讲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按照“三叠”的方式朗诵了一遍,语速很快,像绕口令一样,引得同学们大笑;还有一次讲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咏喇叭》,又朗诵又表演又赏析,活灵活现。两位教授之所以受喜爱,还因为他们对学生特别爱护,教学生特别尽心。两位先生终生没有子嗣,他们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那样疼爱,我们许多同学都有亲身感受。
1971年陆先生坐了三年牢从监狱放出来,系里的负责人到监狱去接他,在从曲阜回济南的火车上,陆先生立即就谈起今后做学问的计划,好像他不是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而是到某地出差而归。陆先生晚年也反了一次“潮流”。那时正是大谈“儒法斗争”的年代,这“潮流”势头很大。陆先生昔日的朋友和同事刘大杰教授为当时“潮流”所左右,修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儒法”划线,强行把杜甫归入法家。陆先生对杜甫1400多首诗歌反复研读,逐一分析,费时两月,写成《与刘大杰论杜甫信》万字长文,论证杜甫并非法家,发表于《文史哲》,被誉为当年《文史哲》最好的论文。可惜,这是陆先生最后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
我从黄元同志写的一篇记述陆侃如和冯沅君生平事迹的文章中,知道两位先生在法留学期间和回国以后,还在翻译方面作出过许多重要的贡献。冯先生翻译了《书经中的神话》、《法国歌曲的价值及其发展——〈法国近代歌曲选〉导言》(1946)、《新法国的文学》、《萨特存在主义》 (1947);译诗有《播种的季节》 (雨果)、《人民颂》、《我曾漫步》 (1947)、《双牛吟》 (杜明)、《工人歌》(1948)等。她的译诗大多附有译者按语,对所翻译的法文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相似的特点一一作出点评,这样读者欣赏诗歌时能够感受到不同语言的魅力。陆先生翻译了《左传真伪考》 (高本汉)、《金钱问题》 (小仲马)、《法国社会经济史》 (塞昂里)。他在1933年6月10日的上海《读书杂志》(三卷六期) 上发表了《恩格斯两封未发表的信》的译作,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女士的信中说:“我以为,写实主义不但要事情的真实,还要在典型的环境中确切地表现出典型的人物来。”这就是影响深远的、著名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创作方法论。
李:听说,您们上学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过高亨先生。当时,他给您们上过课吗?
杜:上过。1963年,大约是初冬时节,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高亨教授终于从北京开会回来,继续给我们讲中断了好几周的“诗经研究”课。以往上课,一打铃,我总是看到高先生夹着讲稿,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教室,站在黑板前面马上开讲,直入正题,黑边近视眼镜后面露出的眼色和面孔,平和静谧而略带严肃;这次不同,他显得特别兴奋,年逾花甲却像年轻人那样步步春风走上讲台,满面红光,笑容似乎忍都忍不住。他第一句话就是:
“同学们,我见到毛主席了!”
原来,1963年10月至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高亨先生作为我们山东大学的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也应邀与会。当时我没有能力和水平、此刻在本文中也没有必要对那次会议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只记得那些天从报刊和广播中感受到那次会议开得特别隆重而热烈。周扬10月26日在会上作的主题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人民日报》大篇幅刊登,洋洋数万言,几乎成为当时学界广泛阅读和学习的经典文献。那时我正准备报考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蔡仪研究员的美学研究生,教文艺理论的老师建议我除了阅读蔡仪先生所指定的参考书之外,一定要把周扬报告作为必读著作。那次会议开了差不多一个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11月16日会议结束那天,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高亨以及范文澜、蒙文通、陈望道、冯友兰、刘大年、周予同等九位著名专家、教授和学者,气氛非常亲热而轻松,规格之高亦前所未有。
高先生开会回来的第一堂课,激动地说:“今天我破个例,讲课之前,先把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情形对同学们说说……”接着,高先生几乎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讲述毛主席如何依次与他们一一握手,会议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报告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如何在一旁为毛主席一一作介绍。
“当主席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一听到周扬同志说出我的名字,立即紧握着我的手,亲切而又风趣地说道:‘你是研究哲学的还是研究文学的?’我回答说:‘主席,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学我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学得都不好。’说起学问,主席兴趣盎然,继续对我说:‘我读过你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
说到这里,高先生嘴唇有些发抖:
“主席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肯定和赞扬,令我既高兴又惭愧,我对主席说:‘我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够,有主席的鼓励,鄙人有生之年,当加倍努力。谢谢主席!’”
我聆听过高先生的“诗经研究”课,领略过他的风采,印象深刻,终生受益。
高先生备课,极为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极富责任心。他不但要学生读懂古词古字的含义,而且要读准古音,一点儿也不许含糊。他的写得整整齐齐的讲稿,做着各种标记,个别字还标出了标准读音,以便给学生详细而准确地讲解。记得在讲《豳风·七月》时,仅第一小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就讲了老半天。他首先解释“七月流火”,说:你们可千万不要误解为七月天热,热得“流火”。这里说的“火”,是星名,又名“大火”,即“心宿”;“流”是向下去。“七月”也不是今天的七月而是豳历(历法的一种)七月。豳历五月黄昏时候“火”星在天空正中,六月里便向西斜,七月更向下去了。他接着解释“一之日”说:豳历一之日,即夏历十一月,周历正月。豳历此月与周历同,为岁始。“二之日”、“三之日”……类推。之后,高先生又特别强调“觱”字的读音,他说:这个字读作“必”(bì)的音,“觱发”者,风寒冷也……对于《诗经》各个篇目中的一些关键词和字,高先生总是强调出来,重点讲解,譬如《小雅·四牡》中的“四牡騑騑,嘽嘽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高先生突出讲这几个字:“嘽”要读作贪音(tān),嘽嘽是喘息貌。“骆”是黑尾黑鬃的白马。“盬”要读作古音(gǔ),停息也。讲到“启”,他连说带比划:启是跪的意思,但是要分辨清楚:古人没有现在的椅子、凳子,而是席地而坐,当臀部贴着脚跟时,那“启”就是坐;若是臀部离开脚跟,那“启”就是跪拜时的动作了。
当他讲《小雅·皇皇者华》时,把有关马的形状和颜色讲得特别有意思:驹,马高六尺名驹;骐,马青而有像黑色棋子样的花纹;骃(音yīn),浅黑色与白色相杂的马。高先生讲得这么细致、清楚,连一些非常微小的意思都讲得了了分明!
高先生不但对《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有着自己独到的解说,而且对古地古名及其沿革变化,也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界定。他认为诗三百篇是按照产生地,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东周)、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雅(即夏,西周)、鲁、宋,共十八个地域来分编的。他把这些地域的位置讲得异常清晰;而在讲《大雅》中的《生民》 (写周人始祖后稷)、《公刘》 (写公刘由邰迁豳)、《绵》 (写文王高祖古公亶父)等几篇周人的史诗时,他把周人的历史沿革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并把历次迁都的名称、地点以及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地方,都做了仔细讲解,随口说来,如数家珍,令我们这些听课的学生惊叹。研究古籍的学人都会知道,像高先生这样的功夫,非数十年兢兢业业治学,修炼不到此等地步。高先生当年为我们授课的讲义,很可惜,我后来几次搬家,丢失了。但是,我在“文革”后看到高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诗经今注》,依稀见出当年讲义的影子,只是注释没有在课堂上那么多。当然,高先生的“诗经研究”,也有那个时代过分强调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痕迹,一些学者曾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高先生的文字考据和研究功夫,没有听到有什么微词;即使学术上有不同见解,见仁见智而已,而谁也否定不了高先生特立独行的敢于独创的学术个性。他在《诗经今注·前言》中说:“我读古书,从不迷信古人,盲从旧说,而敢于追求真谛,创立新意,力求出言有据,避免游谈无根。”我记得高先生在课堂上对我们多次讲过类似的话。
李:山大的萧涤非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汉魏六朝文学史专家、杜甫研究专家,他的学生很多,桃李满天下,也很长寿。您大学时上过他的课吗?
杜:“我的名字叫萧涤非,不是‘萧条非’,‘涤’,这个字发‘迪’(dí)的音,不要念成‘条’(tiāo)!”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山东大学文史楼大教室,萧涤非教授为我们开“杜甫研究”,第一堂课,萧先生走到黑板前,就先写下了“萧涤非”三个有力的大字——当时写的是繁体,他特别指着中间的那个“涤”字,说了上面的话。这是这门课开篇第一句话,课堂上发出一阵笑声。
萧先生中等个儿,脸庞儿稍瘦,双眼炯炯有神。那年他不过五十四五岁,头上已经露出些许白发。他说话,底气很足,声音洪亮,语速稍慢,明显带着江西口音。萧先生说:“同学们不要笑,真有粗心的人把‘涤’读成‘条’,我记得不只一位初次见面喊我‘萧条非’,弄得我颇为尴尬: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咱们山大的同学可不能念错,让人家笑话。”
萧先生是个非常叫真儿的老师,他是绝不允许自己的学生念错字、念白字的,也是绝不允许自己的学生出现常识性错误的——他的课,一上来先从自己名字的读音做起。后来,我记得在他全部“杜甫研究”课中,每遇到杜诗本文和注释杜诗所涉及的其他古文中难懂难读、容易念错的字词,都要格外挑出,重点讲解,不但把它的意思解释清楚,而且把它的读音弄准确。例如他讲的第一首诗是杜甫早年的五律《望岳》,讲到“荡胸生层云,决眥入飞鸟”时,他特别拈出“眥”字,说,这个字不要念成“此”(cǐ),它的音是“字”(zì),去声。“眥”者,眼角也。“决”,是裂开;“决眥”,形容张目极视的样子。萧先生一面解释,一面指着自己的眼睛作张目极视状。
对于两音字的十分细微的区别,萧先生都特别提醒同学们分辨清楚,例如讲到《前出塞》 (九首)之五的第五六两句“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萧先生说,同学们要注意:“骑”这个字,有两个读音,动词如“骑马”的“骑”,《说文》解释为“跨马也”,这时它可以读“奇”(qí)的音;而杜甫这首诗里的“胡骑”,是名词,指骑兵,照以前习惯的读法,应读作去声,发“寄”(jì)的音。
有一次,萧先生说,杜甫是作律诗的圣手。虽然他有时也故意作“吴体”(即“拗体”)诗,甚至自创新体;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很遵循律诗的常规,注意音律、平仄、对仗,“语不惊人死不休”;晚年更是讲究,“晚节渐于诗律细”。例如杜甫757年秋天在夔州所作《登高》,有人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真是律诗的典范,同学们要背诵。说完,萧先生随口背诵出来。萧先生的头随着诗的声律、平仄而微微晃动,抑扬顿挫,了了分明。他接着说,有时杜甫也写出看起来很怪、猛一看不容易理解的诗句,例如《秋兴八首》的最后一首第三四两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就是为了平仄、音律、对仗的需要而写的倒装句。按正常的意思,应该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但是,这样意思顺当了,却乖于音律、平仄,读起来有点儿别扭。对这样的奇怪诗句,同学们也要注意理解。几乎在讲解杜甫的每一首诗时,萧先生都找出特别的关注点,提请同学们精心把握。
“杜甫研究”是一门选修课,当年我之所以对杜甫和杜诗特别感兴趣,那缘由有点儿可笑:原因之一是我和杜甫都姓“杜”,心理上有一种自豪感,不能不对“我家子美”格外了解。但这点肤浅、幼稚、渺小的虚荣促使我听了萧先生为时一年的“杜甫研究”课,却大获收益:萧先生使我认识了一位真正伟大的人民诗人,知道即使我与杜甫是本家,那么杜甫的伟大,也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老杜家”的光荣(那样就把杜甫看小了、看扁了),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全人类的光荣!
当年听萧先生讲《杜甫研究》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课下专门请教他如何学好杜诗。萧先生说了两条:一是知人论世,一是精确理解杜甫的主要诗篇,最好能够背诵。
什么叫知人论世?萧先生说,不但要对杜甫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有深入的了解,而且特别要对生活在那个社会和时代的杜甫本人有深入的了解:他的家庭,他的经历,他的思想,他受了什么磨难,他怎样走向人民……读杜诗,不仅要学他的诗,更要学他的为人。萧先生特别指出,杜甫有一个特点,他的诗往往是个人生活经历的实录,社会重大事件的实录;他的诗就是他的传记,就是时代、社会的传记,你把杜甫的诗依写作时间阅读,就知道了他的生活史,知道了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也知道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萧先生强调,把杜诗称为“诗史”,名副其实,最恰当不过。萧先生的《杜甫研究》讲义,把杜甫一生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的“读书游历时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的十载“长安困守时期”,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的“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四十九岁到逝世长达十一年的“漂泊西南时期”。他选了260多首杜诗来讲解,其排列顺序,也不是像别人那样依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等等体裁,而是按写作年代——后来我读萧先生的《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和《杜甫诗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到都是按创作时间的顺序选注的。
关于萧先生所说要精确理解杜诗的主要篇章、最好能够背诵,我印象更为深刻,因为在我单独请教萧先生如何学好杜诗之后的下一堂课,快下课的时候,萧先生专门说了一段话:“有同学问我怎么学好杜甫的诗,我说,除了知人论世之外,就是要熟读杜诗,达到能够背诵的程度,学习古诗、古文,都应这样,我的老师黄节先生当年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下面,我就给同学们背诵《秋兴八首》。” 本来此刻要立即背诵了,但萧先生说到这里,又特别加了几句话:“《秋兴八首》为杜甫惨淡经营之作,或即景生情,或借古为喻,或直斥无隐,或欲说还休,必须细心体会。律诗本是一种具有音乐性的诗体,诗人完成一首律诗,往往不是用笔写出来而是用口吟出来的。因此,对于一首律诗特别是像《秋兴八首》这样的七律的鉴赏,更需要下一点吟咏的功夫。这倒不是单纯为了欣赏诗的音节的铿锵,而是为了通过抑扬抗坠的音节来更好地感受作者那种沉雄勃郁的心情。前人评《秋兴八首》,谓‘浑浑吟讽,佳趣当自得之’,是不错的。”
萧先生在讲台上抑扬顿挫地背诵,我们在课桌上对照原文有滋有味地聆听,陶醉于杜诗的优美韵味之中。八首七律,每首五十六个字,八首共四百四十八个字,萧先生背诵得一字不差;他的声音,伸缩有致,高低相间,如行云流水,行其当行、止其所止。
背诵完了,萧先生定一下神,对同学们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就像我这样背诵!”
萧先生自1933年来山东大学到1991年去世,前后断断续续执教五十八个年头,可谓山东大学执教时间最长的教授之一。作为学界公认的现代顶尖的杜甫研究和汉魏六朝文学史专家,他与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诸先生一起,并称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四大台柱子,是山东大学名副其实的大功臣。
李:读您的文章,知道您很早就结识了吴晓铃先生,您们也是同事,甚至还有过一段患难的历史。希望您谈一谈您们交往的情况。
杜:吴先生是我的长辈,但是他乐意同我等年轻人交往。我是在五七干校集中于明港军营搞清查运动时才与吴先生成为朋友的。那时我被打成“五一六”,属于另类,与我交往,是有风险的。但恰在这时,吴先生却与我走得很近,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们住的军营宿舍,大得可以做小礼堂用,南北各一排窗户,数百平方米(或许近千平方米)的面积,里面放了四五十张床,每个窗户的两旁,两两相对放四张床,宿舍中间留一个两三米的通道,人们可以窜来窜去。我与陈友琴先生床接床,他靠窗,我的床头连着他的床尾,我的床尾后面,就是人来人往的通道。我的床边总是比较“清净”,可谓“床前冷落人迹稀”,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唯有吴先生不时走过来,同我说说笑话。有一次,陈友琴先生也坐在床上,吴先生走来,指着陈先生说:“你是‘足抵工部’。”又指着我说:“你是‘头顶陈抟’。”听后,略一琢磨,我们三人哈哈大笑。“工部”者,唐代诗圣杜工部、杜甫也,我姓杜,吴先生以此喻我;陈抟是宋初著名道教学者、隐士,有名的“睡仙”,号称“天下睡功第一”,又是有名的长寿老人,据说活了118岁,吴先生以陈抟喻友琴先生。
还有一次,吴先生拿了一张纸过来给我看,上面是他模仿古代“告示”写的一段话:“照得近有不逞之徒,夤夜如厕,靡所弗届,随处乱撒,殃及水房……如有再犯,定当‘杀头’,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原来,我们的宿舍,还有临近的其他宿舍,离厕所较远,冬日天冷,半夜有人小解,往往就近在水房“方便”,弄得臊气熏天,怨声载道。于是吴先生写了一纸“告示”,对我说:“贴在水房,好不好?”不一会儿许多室友围上来看,众人皆谓“妙不可言”,文辞幽默,尖刻风趣,雅中有俗,俗中带雅,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不约而同地说:“好,好!贴到水房去!”
那年春节,食堂为每个人发了一斤白面、一碗白菜猪肉饺子馅,要大家自行过年。傍晚,许多人在自己的床前忙活起来。我是无心过年的——我们宿舍后面考古研究所的张旗,被诬为“五一六”而受到残酷逼供,不堪忍受,不久前在另一水房上吊自杀,死后连棺材也没有,穿了一身蓝色的确良制服埋在附近,第二天即被人扒出来从尸首上脱走那套新一点儿的制服,惨不忍睹;我这个“五一六”在北京隔离时,亦曾自杀未遂……有什么心情过年呢!所以饺子馅放在那里,迟迟没有动手,也不想动手。没有料到,过了一会儿,吴先生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书瀛,我帮你包饺子!”顿时,一股暖流浸透我全身。那个春节我吃的是吴先生与我一起包的饺子。煮饺子用的是我自制的土煤油炉,有时煮个鸡蛋什么的还凑合,要煮饺子,显然火力不够。虽然由于火小,有不少饺子最后煮成了片儿汤,但我还是觉得那是在干校接受清查的冷酷之中,吃得最温暖、最有味道的一顿饭。
1970年代初在河南明港五七干校时,吴先生在附近村子里偶尔结交了一位姓张的农民,还光着膀子与这位农民一起照了一张十分随意的生活照,拿回来给我们看,自以为是遵照党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号召,深入群众,与农民打成一片。不料想,当时领导我们搞清查运动的军宣队和工宣队不知怎么打听到,此农民家庭成分是富农。这还得了!于是把吴先生揪出来,开全所大会批判。军宣队一位负责人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呵斥道:“吴晓铃,站到前面来!”会场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大气都不敢喘。“你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与富农臭味相投,可见你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非常顽固,死不悔改,可以做现行的反面教员……”我们不敢说什么,只暗暗为吴先生叫屈、叫苦。
吴先生人缘好,他乐意助人,人也乐意助他。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后,一次他家(校场头条)的下水道堵了,请几个年纪稍轻有力气的朋友和学生帮忙,于是我们三人——那时正赋闲在家的京剧武生王金璐,文学研究所有名的拼命三郎栾贵明,还有我,去吴先生的四合院,先在他的“双棔书屋”喝茶。我们三人不到半天,活就干完了。中午,吴先生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海阔天空谈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王金璐的遭遇和前途。当时,这位京剧名角正处于人生和事业低谷,后来,我从媒体知道王先生重返舞台,成为“武生泰斗”级的演员,我想这其中应该有吴晓铃先生之力。还有一件与我直接有关的事不能忘怀,他介绍徐大夫为我探亲的妻子治疗十几年屡治不愈的头痛病。
李:您谈的材料很有价值,使我们了解了文论界的不少情况。再次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