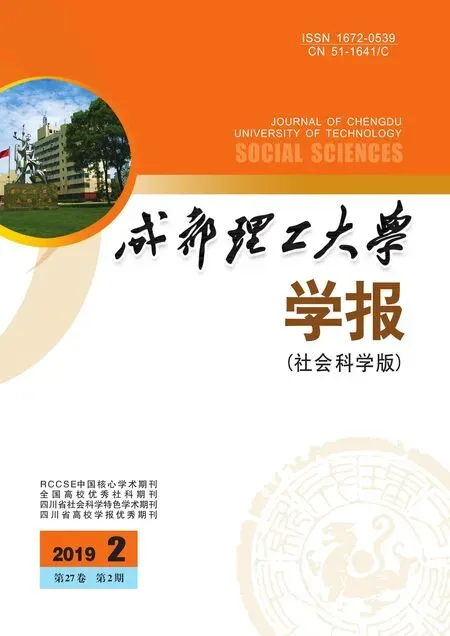司马迁与苏维托尼乌斯传记思想之比较
——以《史记·本纪》与《罗马十二帝王传》为中心
2019-02-16祁泽宇阿孜古丽尔曼
祁泽宇, 阿孜古丽·尔曼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是东西方传记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史记·本纪》(以下简称《史记》)和《罗马十二帝王传》(以下简称《帝王传》)是二者的经典之作。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西方比较研究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司马迁的《史记》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成果丰硕。随着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同为传记文学家的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颇具可比性。本文力图在已掌握的材料范围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研读古典史料的基础上,着力把他们的传记思想同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
一、创作背景
在著作的撰写过程中,创作背景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创作背景既包括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因素,也包括作者自身因素。
(一)时代背景
汉朝建立之初,多沿袭秦朝旧制,但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刑法制度和文化控制,并废除了秦朝制定的“挟书律”,对各派学说持开明态度。面对各种思想在民间的传播,儒学家们开始积极地招收学徒,著书立说。西汉初期,生产工具取得发展,交通便利起来,经济开始繁荣,因此社会日趋稳定。为汉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兴起,中国思想史进入了“经学时代”,告别了思想界战国诸子以来纷乱状态,实现了思想领域的统一。《史记》成书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写道:“上大夫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1]1227。可见,司马迁对今文学家提出的“《春秋》欲代周而作新王,建立后世统治法则”[2]121的写作目的是赞同的。另外在《史记》的十二本纪的写作中,对于历代帝王世系的叙述也体现出了“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念。
《帝王传》成书于罗马帝国早期,当时屋大维掌握实权,建立了元首制统治,开启了罗马帝国时代[3]。在新的官僚机构中,社会秩序得到整顿,进入一个较为安稳的时期。政府奉行不干预的经济政策,随着海外殖民扩张和商业的发展,经济得以复苏。在这稳定政局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产生了一些大财主,他们又促进了大地产的发展[4]。伴随着对外战争的扩张以及财富的与日俱增和海外奴隶的大量流入,享乐主义在罗马社会迅速蔓延。在生产技术进步、商业发展和税制改革的刺激下,罗马小农经济破产,原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遭到破坏。罗马上层社会通过剥削掠夺获得大量财富,他们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生活奢靡。罗马自由民丢失了勤劳节俭,沉溺享乐、拜金主义盛行。《帝王传》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总之,司马迁与苏维托尼乌斯都生活在政局较为稳定,经济取得发展,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这为他们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二)作家背景
司马迁生于汉武盛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西汉思想界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迎来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司马迁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1]2852可见他从小诵古文,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又出游各地,寻访古迹,考察民俗。正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司马迁出游大江南北的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为后来撰写《史记》创造了条件。
苏维托尼乌斯的父亲是一位罗马骑士[5]285,这为他在罗马接受正规的教育提供了经济条件,其先后学习了古籍与演讲术。苏维托尼乌斯并没有留下关于自己的传记,我们只能通过小普林尼《书信集》的资料了解他的生平。“他不喜欢做官。当时骑士阶层人物的升迁通常从军职开始。小普林尼曾帮他张罗谋得一个军官职位,但他把它让给了自己的一个亲戚,自己则留在罗马成为两个祭司团体的成员……”[6]他大段时光都处于隐居状态,并专心投入到写作中。
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的家庭背景都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出生在史官家庭的司马迁以及生活在富裕骑士家庭的苏维托尼乌斯,他们都受父辈的影响而接受正规的学术教育,这对于他们的写作无疑是有益的。
二、写作动机之比较
写作动机是文学家投入到文学作品创作的内在动力,一般是自发的,体现在其创作过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2854司马迁对父亲许诺言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2854可见,司马迁子承父业做史官。笔者认为,“欲论著”是作为史官的一种自觉性,司马迁希望自己能“论著”而不负史官的身份,更要替父亲完成其遗愿,因此父亲的厚望和史官的身份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重要动机来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又提出他写传记的目的是“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说明司马迁并不是单纯地记载历史,而是要提出自己的见解“成一家之言”,流传后世。因此他不满足于单纯地搜集和罗列史料,而是要研究其来龙去脉,并抒发己见。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主观动机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对自身命运不屈的抗争。在遭到残酷的宫刑后,他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备受煎熬,撰写《史记》成了他活下去的动力来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于月宾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因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1]2489司马迁以这些命途多舛却能千古留名的圣人为榜样,发扬坚忍不拔的品质,才能在罹难后坚持著作。
相比较而言,苏维托尼乌斯似乎没有表现出史学家研究历史来龙去脉、探讨国家命运和历史发展的一种自觉性。他著述的主要目的是搜集、整理和记录史料。作为哈德良(Hadrianus)的侍从秘书,苏维托尼乌斯有非常便利的条件完成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他能接触皇家档案,较容易取得大量的资料,但苏维托尼乌斯并不对史料进行辨伪或给予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如他自己在《帝王传》中写道:“我记录这个说法主要是不致遗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是真的或者有这个可能。”[5]244这也导致后人认为他的《帝王传》不具备史学价值,正如罗尔夫说《帝王传》,“既不是历史也不是传记”[5]9。
三、写作手法之比较
(一)史料选取
史学家在史料选取的标准、方法等方面可以影响和反映其写作手法。下文将具体分析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在史料选择和使用上的特点。虽然《史记》是编年体裁,但我们发现列传体裁与《帝王传》的传记体内容也有对应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两者不乏可比性。
1.《史记·本纪》
以《秦始皇本纪》为例,司马迁撰写本纪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古籍。司马迁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古籍中获得了丰富的史料。他在《五帝本纪》中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1]42可见他在保留意见时,也会承认古籍记载的内容。又曰:“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1]62从这些古籍中找到的证据,是司马迁史料的第一类来源。二是朝廷的文献档案。《史记·本纪》中《周本纪》所记录的《太誓》[1],《秦始皇本纪》中的石刻文等都是朝廷管理的文献档案。三是实地考察之所见所闻。他去“禹穴”古迹,游览会稽等地为撰写《五帝本纪》做了准备。《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也是典型的实地考察之作。
关于史料选取的标准,司马迁概括为“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1]2854,即收集天下散失的旧闻用来考订和综述,借以观古今盛衰。对于司马迁取材的标准,学界多同意“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之说法,其中李渊[7]和任刚[8]还分别以《晋世家》和《五帝本纪》为例做了具体说明。班固称赞司马迁的撰史风格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道出了《史记》秉笔直书、言简意赅、文风流畅的特点。
2.《罗马十二帝王传》
《帝王传》以帝王生平事迹为主线,偏重人物叙述而非记述历史事件,属于西方的纪传体史书类型。
《帝王传》取材同样很丰富。一是皇室文献。苏维托尼乌斯在撰写人物传记时多取材于“公报”和“年代记”,而所谓的“公报”和“年代记”[5]156就是典型的皇室文献。二是苏维托尼乌斯的所见所闻。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志向不同,苏维托尼乌斯《帝王传》的史料选取具有显著的西方纪传体史学特征。他既不强调伦理,也不关注政治道德。《帝王传》的主要内容是帝王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饱含着帝王的许多轶事和丑闻。苏维托尼乌斯在记载帝王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时,经常有“据说”“我听说”等字眼,这使得他的史料看起来不严肃可靠。在史料选择方面,苏维托尼乌斯秉承着“有闻必录”的原则,正如他说的“我记录这个说法主要是不致遗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是真的或者有这个可能”[5]193。即唯恐史料记载有所遗漏,而不顾其真伪。
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的史料来源大致趋同,但在处理史料时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大相径庭。相比而言,司马迁更加重视考证史料真伪,而苏维托尼乌斯唯恐有所遗漏,不重视辨别史料之真伪。
(二)编撰手法
编撰手法是传记写作手法的一个重要体现,直接影响传记结构。笔者将分别分析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的编撰手法之特点并比较其异同。
1.司马迁的编撰手法
在传记写作中,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刻画,司马迁选择适当编排史料的次序,在前后呼应中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如司马迁对淮阴侯韩信的描写,韩信初布衣,“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虽志向远大却无处施展,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这一时期的韩信,司马迁简要描写了三件事:怒绝南昌亭长、受胯下之辱、漂母赠食。其后韩信功成名就回乡时,“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1]2609。在寥寥数语的前后对比中,韩信知恩图报、重守信义、不计前嫌、忍辱负重的品质跃然纸上。书中大量描写韩信受到刘邦恩惠,韩信也替他征战各方,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拒绝了蒯通自立为王的游说,最后还为消除刘邦忌惮之心而称病谢朝,都集中展现了韩信的知恩图报。司马迁在史料的次序编排和轻重处理上巧妙地运用了对比呼应的手法,贯穿全文,使得人物性格和形象变得鲜活复杂。最终韩信死于妇人之手的结局表露了人物的悲惨命运,与开篇的三件小事前后照应,构成一部完整的人物史诗。
再从整体编撰来看,从《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是按照编年顺序排列的。 社会历史的各个阶段是互相衔接的,有益于清楚地反映历史的面貌,也有益于人们探索历史变迁的深刻原因。先秦史籍一般都很重视依时序载史事。《国语》《国策》虽是分国记事,但每叙一诸侯国之事,也大致依年代之先后为顺序。先秦史籍的编撰实践为司马迁提供了若干可资借鉴的经验,依时序记事则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史记》十二本纪严格遵循这一原则。秦朝以前,依朝代先后为序,自秦以后,依帝王执政之先后为序。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也大致如此。
2.苏维托尼乌斯的编撰手法
苏维托尼乌斯刻画出来的人物性格可能与读者心中既定的人物性格大不相同。例如,他笔下的凯撒是一个淫乱的帝王形象;克劳狄“身心两个方面都缺乏活力”[5]193,近乎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像是一个国家元首而像是一个仆人”[5]212,胆小怕事。苏维托尼乌斯这种热衷于记录逸事,对罗马皇帝的丑闻、淫乱详细描述的做法,使他被后世视为“造谣者”,正如罗尔夫认为的那样,《帝王传》“既不是历史又不是传记”[5]7。但这种说法是有失客观的,普遍认为帝王的传记应该大量篇幅记载皇位变更、军事政治等,但是笔者认为这不能成为否认撰写皇帝私人生活、逸闻趣事也是传记的理由。换言之,苏维托尼乌斯所感兴趣的帝王的生活细节、逸闻趣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对军事政治史料的补充,这些史料对我们了解传主和其所处时代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另外,苏维托尼乌斯处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和扩张的时代。罗马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自由民沉溺于寻欢作乐,而这些秘史正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可以说,苏维托尼乌斯选取帝王私生活作为传记史料也许是为了迎合当时民众的阅读品味。
再看篇幅的整体编撰,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从凯撒到图密善同样也是按编年顺序排列的。从凯撒到图密善依照帝王执政的先后为序,这样排列给读者理解王位更替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探究历史的演变。
综上所述,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在史料编排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异深层次地反映了两者传记思想之不同。
(三)人物评价
司马迁对史料的处理上力求以严谨的态度辨别真伪,在对人物的刻画上也力争客观,因此他对人物的评价也是尽力做到客观。他用“太史公曰”来阐述自己的评价,例如他在《吕太后本纪》说道:“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宴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318他以当时社会状况为依据评价孝惠皇帝和吕太后,足见他评价人物之客观;他在《高祖本纪》中刻画了高祖的人物形象,详述他从平民走到帝王的生平,对他的评价褒贬具有;司马迁认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劳,同时评价秦始皇:“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1]186,认为秦始皇刚愎自用,不听取群臣的意见。总之,司马迁对人物的刻画及评价体现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在凸显人物命运之性格时,不虚美,不隐恶,评价之客观,班固称之为“实录”。
此外,司马迁对人物评价的着眼点,在于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上,而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他对项羽和陈涉的评价就反映了这一点,他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作世家,从体例的安排上突出了二人的历史地位。《项羽本纪》把项羽写成一个盖世英雄,评论说:“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逐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1]250
在史学的态度上,苏维托尼乌斯难以称得上严肃。在他的笔下,克劳狄是个胆小、软弱、无能的元首;提比略多疑而阴险;凯撒“放荡、玩女人”,等等。但他对上述君王并非毫无褒扬之词,他认为提比略“能对冒犯、毁谤和侮辱他本人和他家人的话语保持自制和忍耐”,并且认为“他依然比较经常地表现出仁慈和对公共福利的关心”[1]131。在指责凯撒私生活淫荡混乱的同时也肯定了其政绩。可见,他对帝王的评价是褒贬兼具的,对昏君并非全无褒扬之词,对明主亦列出诸多缺点。总之,在对人物的评价上,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都力求客观。
四、结语
相比较而言,子承父业的司马迁更有史家的自觉性,他的写作动机也更加明确和宏伟。而苏维托尼乌斯并没有表现出要“成一家之言”的志向,更偏向于为了“不致史料遗漏”而进行传记写作。在史料选取上,苏维托尼乌斯没有像司马迁那样严谨,他像是史料的搜集者,唯恐遗漏。司马迁则注重考证史料的真伪,保持了严谨的治史态度。虽然两者都是编年叙述,但在侧重点上又不尽相同。司马迁对王朝更替、政治、军事给予高度关注,但苏维托尼乌斯对政治和军事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热衷于详述帝王的私生活、逸闻趣事。两者在编撰手法上有着显著差异,但二者在评价人物上又都力求客观,诠释了“人无完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