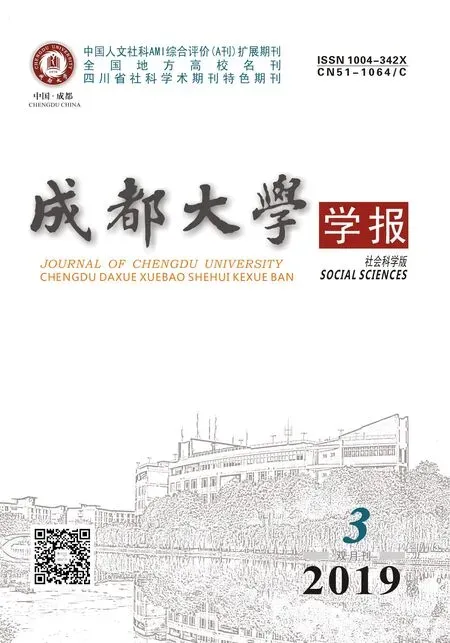上海租界与国民党对左翼文艺审查之关系探究*
2019-02-15苟强诗
苟强诗
(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1845年之后,英、美、法相继在上海设立了租界,但由于英、美、法不断攫取租界地的管辖权、行政权、司法权,致使他们在上海逐步建立的英租界(1845)、美租界(1948)①、法租界(1849),不断成为中国大地上不受管辖的“国中之国”,这种状态直到1945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上海租界后才结束。
20世纪30年代是租界化上海发展的鼎盛时期,它在工业、贸易、金融、交通、讯息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机制,一定程度影响着上海文艺运动的生态环境与生产机制。当时的上海是新闻出版中心、教育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文人提供了较为方便的谋生空间,于是大批知识分子汇聚上海,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审美追求与现实道路选择,上演了左翼文艺、民族主义文艺、自由主义文艺等种种文艺运动,营造了当时上海多元的文艺审美与政治追求的文艺生态。
1927年之后,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共产主义及左翼文艺的宣传与发展,在上海率先实施文艺审查,逐步建立起一套审查制度与体系。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文艺中心,自然成为审查的中心与重心。但由于“国中之国”租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国民党的文艺审查并未能尽心如意,其两者之关系亦因现实之情态的发展而变化,从而使上海的左翼文艺审查产生了多元复杂的历史效果。
一、政法多元——上海左翼文艺发展的历史空间
在近现代上海发展之历史中,英、美、法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存在,使上海租界成为一个可以与国民党当局实施“对抗”的政治力量与法律空间。1919年上海法租界制定并实施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即使如此, 当时之上海租界依然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公共空间。例如,1919年,在面对来自淞沪警察厅命令上海书业领取从业执照的强大压力时,书业从业者便选择迁入租界以此来摆脱北洋政府治下不合理的规章与法律,这实际上是上海书报业对抗政府权力的一次具体实施。而对现代作家开办书店来说,他们同样寻找不同政治力量角逐下的生存空间。
例如,1928年,刘呐鸥出资在上海的“中国地界”开设“第一线书店”因“有宣传赤化嫌疑”而遭“停止营业”后,他们又接着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公益坊,以出版社形式办了第二个书店“水沫书店”。这次因为开设在租界内,不用登记,也没有了华界警察的查问,于是乎开张大吉,一本本书印出来,卖出去,在1929和1930两年中,出版事业办得很热闹。[1]从全国来看,在国民党眼里,其他省市的“反动”刊物多是上海出版,并由上海发往全国各地。1933年国民党调查武汉普罗文学刊物时便指出,武汉市书店,约九十余家,除极少数之线装书外,均系上海出版。[2]而东北的“哈尔滨书店所售之书均由上海运来”[3]。魏斐德在其研究上海警察的著作中指出,上海警察因其司法权的旁落受到租界当局的漠视而感到羞辱,而这种耻辱感即使在1928年1月28日,公安局长主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只能被看作“特区”之后,依然存在。每当公安局警员试图以正式身份进入“特区”,就总是被认为是企图控制租界的借口,而必须获得公共租界警务处的特批。[4]如此情景在黄药眠的文字中有所记录。当时在上海的黄药眠因为要到位于华界的暨南大学附中上课,经常来往租界与华界,在文中他深有感触地说:“那时,上海市有外国租界,什么英租界、法租界等,这些地方由于外国帝国主义者有治外法权,国民党的警察局不能直接去那里抓人的。”而当黄药眠乘火车来到租界地区之外即华界时,“国民党的特务和警察就可以随便逮捕人了。因此我每次去上课都有危险。”[5]
邮政检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实施文艺审查的重要环节与举措。邮检在控制文艺书刊的流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实上,国民党当时的邮检并非畅通无阻。尤其是对租界内的文艺书店及其出版物来说,国民党意欲实施邮检无疑是不能得心应手的。例如,1929年8月,国民党人在致国民党中央常会的笺呈中,对租界邮检大倒苦水,“最近邮件之检查,不能圆满如意,致反动宣传仍流行而从各租界发出之件,占反动宣传中十之七八,在租界不能施行检查,尤为困难一点。”[6]上海市公安局在查禁刊物时同样抱怨说:“本市以有租界之故,共党及反对派,藉为护符,平日各种邪说谬论煽惑人心之种种刊物。已属汗牛充栋,自遭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共党及各反对派,利用各界人士爱国心理,所出刊物更为妄诞不经,肆意蛊惑,以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地方安宁。”[7]在1929年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上,时任上海教育局局长的陈德征在其报告上海市宣传工作情况时,倾诉上海教育局的审查人员在每当租界巡捕换差或逃岗时着手书报检查的无奈,他说:“上海为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点,一切反动势力的渊薮,我们处这二重压迫之下,宣传工作的进行,困难实甚,不得不利用时机,藉以避免帝国主义之耳目。例如每当巡捕换差或逃岗时着手进行,虽然也免不了被其捕捉,然妨碍终可少些。我们受着租界的束缚,感觉到无穷尽的痛苦。”面对此情境,他希望国民党要“不断地宣传‘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还希望各地党部尽力帮助上海市党部作这关系重大的宣传,于最短期间中实现总理的主张。”[8]实际上,陈德征所谓加大收回租界的宣传,并未使上海党部对租界的文艺审查给予实质性的帮助,相反,1929年左右,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官对上海市党部十分敌视,因为在他们开来,上海党部少壮派的政策总是对租界当局充满挑衅与敌对。因此,治外法权②的存在以及上海租界当局与国民党上海党部之间的紧张关系,致使国民党实施的左翼文艺检查遭遇了行政与司法上的困难,这倒给左翼文艺之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空间,左翼文艺借由这样的空间使文艺书刊向全国范围传播。
上海租界与国民党当局间的政法“对抗”,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文艺审判案例中。例如,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月刊③自1933年7月创刊后,很受读者欢迎,但出至第六期后,被上海市党部认为有反动嫌疑,于12月27日咨行公安局会同法捕房前往抄查,并拟予查禁。对此,《申报》载文报道,法捕房抄去《文学》月刊多册,惟捕房经抄查后,并不以反动嫌疑起诉,只以该刊在法租界登记手续未完,故特向第二特区法院起诉。于1934年1月4日上午十时审理本案,由第八法庭庭长审问,当由捕房律师根据法总领事署第一八七号及第一三七条,以被告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未遵令请求法总领事准许,擅行发行《文学》月刊,要求处罚,当由推事向被告质讯,据被告供称,该书店发行《文学》月刊,业经在内政部登记领到登记证警字二三七二号,且该书店亦曾于二年前在法工部局领得执照,完全依法营业。至法总领事署令第一八七号等则以前并未知悉,故发行《文学》月刊未及请求法总领事准许是实,继由被告律师史良、朱章宝、阎世华先后辩护,略谓:被告发行《文学》月刊完全系依照《出版法》办理,内容纯属文艺,绝无政治色彩,至未遵奉法总领事署令,乃系事前并未知有此项命令之故。但发行该月刊之生活书店,业已获得法工部局准许营业,则《文学》月刊兹亦当在准许发行之列,且《文学》月刊出版已历半载,法捕房至上月始受公安局之嘱,前往查抄,可见,法捕房已默认该月刊为正当刊物。今虽偶违租界功令,仍可依法补救,追请准许,决不成立犯罪行为云。当由承审庭长续数语后,即行宣判,罚洋十元了案,并闻所有查获之《文学》月刊业已发还。[9]
二、政治合谋——上海租界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审查
1927年7月7日,在黄郛就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典礼仪式上,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古应芬发言指出当时上海所面临的三点“最困难”:一是人口多而处理不易,二是租界法律问题,三是犯罪管理问题。[10]实际上,这三点无一例外地涉及到上海华界与租界间的法律问题,尤其是租界的治外法权。
租界治外法权的存在使国民党在上海意欲展开的各种计划遇到了阻碍,自然包括上海市政府所辖公安局、教育局等各机关,以及上海党部通过书报审查制度对上海文坛的控制。因此,废除外人在上海租界享有的治外法权,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纳入国民党的司法管理体系之中加以有效管理,以此构建国民党“党治”之下的现代城市管理制度与秩序,便是1927年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成立,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方略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蒋介石于上海特别市成立之日的训词中格外明显:
盖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
这样,在以上海特别市为示范地的治理中,建立公共法律及秩序以证明城市管理的先进性,为收回租界提供合理性基础,成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半个月之后,这一重担落在了上海特别市公安局的身上,因为它的“职责不仅要建立一个强大忠诚的市政管理,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城市环境,作为中国民众和新的国民政府的力量象征,它还必须致力于在上海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恢复失落已久的统治权”,而“从国民政府方面看,他们自己的公安局——上海的华界警察是否成功,将是国民革命成败首要的、决定性的标志。”④
在1927年之后的几年中,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动下,使租界当局感到不安。在一份美国国务院北京公使馆的报告中言及“中国官员有意阻止租界的有效作用的情况越来越多……这种干扰只能解释为是试图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方式取得租界控制权的决心的表现。而这给维护确保租界内生命财产安全所需要的法律和秩序带来了更大的困难”[11]。国民党开始在租界内设立宣传、征税等机构来宣示主权的实际行动。但从魏斐德对上海警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上海特别市政府以及公安局通过上海这块试验地来展示在社会安宁与秩序维持上足以保护居民的财产与人身安全,以达到恢复自己对外国租界的统治权的目的,在1930年左右发生了转向——由将上海租界置于国民党控制的司法系统之下的努力转移到与上海租界当局共同合作对付日益高涨的上海共产党的宣传、游行以及在其领导下展开的左翼文艺运动。
据魏斐德的研究显示,国民党人第一次正式向公共租界巡捕房提出在政治事件上进行合作的要求是在1929年2月20日。而据笔者阅读所见,在1928年5月,国民党上海党部就已经派科员会同上海教育局人员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接洽,前往泰东、光华两书局查禁《短裤党》《战线》《一条鞭痕》等“反动书籍”。[12]
1929年上海临时法院向公共租界巡捕房罪案侦查总部提供了两份文件,其中一份来自上海特别市政府,内容是蒋介石签署的国民政府的命令,要求取缔位于牯岭路132号立群书店出版的共产党期刊《血潮》。11月,上海特别市公安局则直接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联系,向公共租界当局提供有关共产党活动的有价值的线索以换取有助于对付国民党内部和桂系中蒋的敌人的情报。显然这样的合作,符合双方政治安定维持秩序的考虑。因为共产党在上海的外国语宣传业已渗透到租界洋人那里。因此,上海特别市公安局的这次向公共租界的主动联合,很快收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负责罪案侦查总部副处长R.C.艾尔斯的应允,并警惕共产党的活动。而之后上海临时法院院长何世桢奉中央政府命令来文取缔“反动政党”之时,公共租界巡捕房罪案侦查总部负责人回信写道:“11月26日来文收悉。请求公共租界警务处取缔惯于编造诽谤国民政府谣言的反动派活动并禁止此类反动政党所制文字宣传品的散发,均已在注意之中。此奉复。”[13]自此之后,在对付共产党及左翼文艺运动方面,上海特别市政府尤其是公安局不断主动与上海租界当局合作,搜查与查禁有“反革命”嫌疑的书店及印刷品。
例如,1930年9月,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合作”查封南国社,并逮捕了黄芝冈、田寿麟(田沅)等人;同时搜查田汉家。田汉由于得到鲁迅的报警和周信芳的掩护而避居他处。[14]12月28日,法捕房对界内小报展开检查,《申报》报道法捕房政治部长萨利,近来查得界内有多种小报,内容所载文字,类多反动稿件,虽迭经通告禁售在案,奈仍有增无减,昨特将各报名称会查明白,谕令政治部通班探员,一体查获,每日并须特派私人,专往各处巡查,凡遇有兜售下列各报之一者,即将所有报纸及售卖人全拘入捕房,抄录售卖人之姓氏、年龄、籍贯,然后将报纸没收,将人释放。如系再过犯,即须送解公堂罚办。禁售各报计有:苏维埃画报、硬的新闻、上海日日新闻、中华午报、十月评论、国民社员、大晚报、老上海、海上日报、世经、铁报、钢铁钱屑、赤色海员、红旗日报、列宁青年、革命工人、快刀日报、日日新闻、华北晚报、海光日报、战鼓、上海报、小沪报、达报、民声周刊、国民日报、勇士日报、旭光日报、评论周报、上海工人、东方日报、大风日报、春秋战报、朝日新闻、革命日报、武昌革命、穷汉、大小报、摸普耳、沪江日报,共四十种。[15]公共租界巡捕房对于制止共产党宣传品的散布仍然常抓不懈,到1930年,他们向邮电局派出了邮件检查员,以确保邮件不被用来进行宣传颠覆政府的观点。[16]
1931年国民党与公共租界当局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同意在反共运动中提供“完全的帮助与合作”。工部局警务处负责特务股的帕特里克·T吉文斯将这个合作具体化了。[17]1931年3月4日,北新、联合、江南、群众四书局被查封就是公共租界捕房与国民党的又一次“合作”,以代售左翼作家刊物为由将其查封,当时《文艺新闻》报道北新、群众、江南、乐群等店近乎于三月四日被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发封。江南……该店门之封条上系书“查封乐群书店”,江南一家另贴告白于门前,谓“本店无辜被封当于最近依法向当局要求启封”。[18]
上海租界当局通过查禁刊物或查封书店等来压制界内的革命文化,如同他们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一样,或由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之“捕房单独进行,或与中国当道合作”。上海租界当局对革命文字宣传的检查,也不遗余力,其抄获的宣传文字数量也是惊人的。
到1931年1月,公共租界罪案侦查总部已开始依从于一种惯例,即根据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的要求为基础,在不论能否发现其他旁证的情况下,都可以发放不具名的逮捕令,以搜查怀疑出售“反革命”书籍的书店,并逮捕售书者。1932年1月,吴铁城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在其后的5年里,吴铁城与上海租界当局在有关上海中心城区的治安和政治稳定的两个方面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合作。于是,公共租界警务处将同国际共产主义作斗争视为与他们维持租界治安同等重要的职责。
当时一位英国情报处成员H·斯戴普托在他1935年写给公共租界警务处吉文斯处长的信中说:广义地说,共产国际就是对抗国际法律和秩序的非法阴谋活动的渊薮。而警察就是要维护这种法律和秩序,从地区乃至于国际,而且在我看来,如果当地警察无论由什么渠道得到有关共产国际间谍在这儿存在的消息,却没有尽最大努力弄清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是一种很大的遗憾。这样,与法租界和华界警察一起担负的同国际共产主义作斗争的职责顺理成章地演变为帮助国民党当局摧毁国内共产党人的一种义务。[19]
上海租界在为左翼文艺运动在文艺创作、出版、宣传、销售以及人身安全等方面提供便利与安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国民党与上海租界当局站在了一起,即租界当局与国民党出于政治安定维持社会法律秩序而合作对革命文化与左翼文艺运动施以共同压迫。
但上海租界毕竟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自有打算的“地盘”,他们与国民党也并非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上的“警务报告”中,可时常看到租界当局与国民党所发生的种种冲突,对彼此“合作之友谊”的破坏。此外,上海租界当局也并非与国民党政府及党部盲目合作。虽然上海租界当局极其注重维护租界的法律秩序与安宁,但毕竟受到他们母国法律文化观念与价值的影响,在言论、出版自由的裁量上,体现出较大的自由空间。较之1927年国民党政府颁行的控制与压迫“非三民主义”的“反动”出版与言论的法律制度来说,上海租界当局的裁量标准要宽松得多。一方面,除非在书报上出现暴力的杀戮、推翻现有政府等极具煽动人心,破坏社会安宁秩序的言论,对其进行审查起诉惩罚之外,其他言论与出版颇能享有“自由”的便利;另一方面,即使被上海租界当局巡捕房逮捕,他们也基本按照法律程序予以起诉、进行审判,按照西方法律制度进行判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程序正义。
三、小结——魔性空间的多元效果
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之后,特别公安局、教育局等抱怨租界成为共产主义以及左翼文艺等发展与宣传的渊薮,在文艺审查中常常承受着来自“国中之国”之帝国主义的压迫,但为了某些共同的政治目的,国民党亦常常联合上海租界当局对共产主义与左翼文艺进行检查,而租界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安全,除与国民党“合作”对左翼文艺刊物进行压制外,其自身也施行来自租界当局的书报检查。在上海,由于租界的存在,左翼文艺运动虽然遭受了国民党与上海租界当局“合作”下的压迫,但又恰恰因为上海租界的存在,左翼文艺运动才得以在“治外法权”影响下,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与基础条件,为左翼文艺的传播提供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无法给予的便利。被冠以“魔都”之名的租界化上海,对左翼文艺的发展显然发挥着多元而复杂的“魔性”影响。
注释:
①英美租界于1863年合并,称为“上海公共租界”。
②“治外法权”一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解释颇显复杂而又不尽一致。相关研究指出近代外人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已经不具有一般国际法中作为“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涵义,而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概念,它是一种以领事裁判权为主体的非法侵略特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均指在华外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而言。见康大寿、潘家德:《近代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绪论第6页。
③《文学》月刊,1933年7月1日创刊于上海,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第1卷由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十人组成杂志编委会集体负责,从第2卷起主编人改署傅东华、郑振铎,具体编务由黄源负责,从第7卷由王统照接编,茅盾始终是《文学》月刊的编委。刘增人等纂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
④引自【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陈雁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页。为了建立一套适应现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其关键是警察队伍的建设。例如魏斐德认为,“在致力于维持城市不同租界、地区和区域法制的几个执法机构中,这是惟一的中国执法机构。国民党能否建立起一支近代警察队伍,仿效世界上最好的执法机构,”有效地解决上海的公共卫生、工商执照、娱乐业、工会、新闻书刊检查以及吸毒、卖淫和抢劫等问题,同时又推进收回租界的中国主权计划,控制上海华界普遍存在的无序和动荡。《上海警察,1927-1937》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