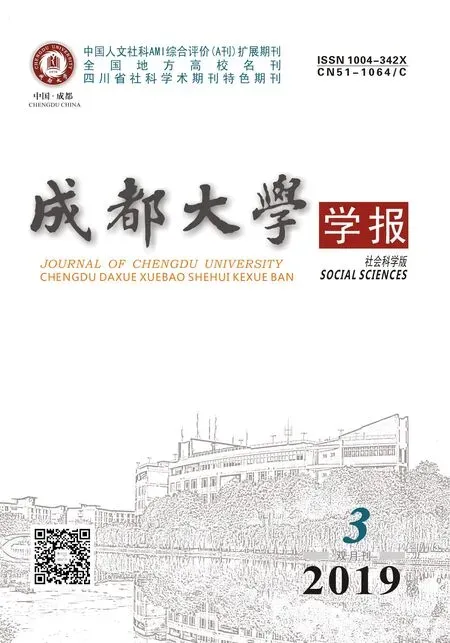阿来的少年情结与藏地少年成长书写
2019-02-15张建锋
张建锋 杨 倩
(1.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2.成都大学 图书馆 四川 成都 610106)
《少年诗篇》是阿来1993年的一篇小说;2015年,阿来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也以此命名。从1987年《旧年的血迹》中名叫阿来的少年“我”,到2015年《三只虫草》中名叫桑吉的小学生,将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中,阿来书写了不同时代的少年生活,刻画了许许多多的少年形象。阿来的少年书写,从记忆深处流淌出来,既是个人的成长记录,也是藏地少年成长的缩影。其成长书写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需要深入研究。
一、阿来的少年情结与成长叙事
阿来的少年情结与其自身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其成长叙事带有明显的自画像或自叙传的色彩,是个人少年生活的想象性再现,体现了阿来对少年成长、少年人生的深层思考。在荣格心理学中,人格作为一个整体被称为“精神”,包括思想、感情和行为,由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个层次组成。“个人无意识有一种重要而有趣的特性,那就是,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簇心理丛,荣格称之为‘情结’。”“当我们说某人具有某种情结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他执意地沉溺于某种东西而不能自拔。用流行的话来说,他有一种‘瘾’。”[1]阿来执着地、持续地、大量地书写童年、少年的生活记忆,在自己的领地里不断开掘。1980年代的《奥达的马队》《旧年的血迹》《孽缘》《守灵夜》《鱼》,1990年代的《永远的嘎洛》《已经消失的森林》《最新的和森林有关的复仇故事》《欢乐行程》《少年诗篇》《格拉长大》,2000年代的《遥远的温泉》、“机村史诗”第一部《随风飘散》,2010年代的《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等,都是藏地传说、历史与现实的书写,留有很深的童年、少年生活的印痕。
弗洛伊德认为情结起源于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荣格进一步提出,情结起源于人性中比童年时期的经验更为深邃的东西即“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人的心理是通过进化和遗传预先确定了的,不仅与自己童年的往昔,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因而,不是人支配着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而情结“可能而且往往就是灵感和动力的源泉”[2]。阿来的藏族血缘、 童年记忆和少年生活是其少年情结形成的基础。阿来曾经说他的心中埋藏着英雄主义梦想的情结,是他的藏族血液中遗传的精神。对于童年、少年曾经的苦难历程,阿来已经是尘埃落定后的淡然和达观,在创作中也是超越自身的冷静思考和客观呈现。“我曾经感到痛苦和迷茫,但是经过时间的过滤,过去反而显得很美好。之所以美好是因为那是对只有一次的青春的怀念,我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3]阿来在自己的出生地、成长地嘉绒藏区深耕,形成独特的藏地世界。
阿来书写的少年故事往往发生在十二三岁这个年龄,在《奥达的马队》中,夺朵是从十三岁开始进入马帮,成长为驮脚汉的。在《格拉长大》中,格拉“今年十二,明年就十三了”。在《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的故事是从十三岁开始的,让他“醒”来的侍女桑吉卓玛成为其终生的情感纠结。在《番茄江村》中,描写的是江村十二三岁时的事情。在《三只虫草》中,桑吉是十三岁,故事发生在桑吉小学即将毕业到升入初中的这段时间里。十二三岁这个年龄,按照正常的情况是小学毕业进入初中学习的时候(若六七岁发蒙,曾经小学五年制,升初中时十一二岁,现行小学六年制,升初中时十二三岁)。但是,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教育状况和教学资源等等的制约,阿坝藏区适龄儿童并未完全正常入学。1969年阿来十岁才入小学,1974年十五岁才读初中,二年制初中毕业时已经十七岁了。这段时间给阿来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阿来书写的少年生活,描写的少年形象无疑是打上了自身的烙印的。在《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后,阿来在回答记者的采访时说:“如果小说拍成电影,自己可以扮演老土司、傻瓜儿子、被割去舌头的书记官中的一个角色,因为这几个形象反映了自己性格中的不同侧面。”[4]这说明阿来是将自己的某些“侧面”融入到了人物形象之中的,甚至于《旧年的血迹》《孽缘》《永远的嘎洛》中的“我”就叫“阿来”。阿来的成长叙事有着个人少年生活的印痕,是回忆与想象的“杂烩”。
阿来(原名杨永睿)1959年出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县马塘村。他的家族属于嘉绒藏区一个从事农耕的家族,他曾经自述自己的境况:“出身贫寒,经济窘迫,身患痼疾”[5]。在阿来书写的少年人物中,无论是夺朵、夺科、金生、呷嘎、洛松旺堆、格拉、次多、江村、桑吉,还是有名无名的“我”,似乎都具有这样的共性。阿来的童年、少年生活是极其艰难的。马塘村地处大山深处,周围几十公里荒无人烟。十五岁去读初中之前,阿来没有离开过马塘村。那时,阿来的家庭正受着极度贫困的煎熬,买油盐酱醋的钱都成问题,上初中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作为杨家的老大,阿来得承担一份养家的责任。倔强的阿来向命运抗争,进山挖药,上山砍柴,拼命挣钱,熬过了两年初中。1976年阿来从卓克基公社中学初中毕业,回到马塘村务农,先后在水库工地扛石头、开拖拉机、当建筑队合同工。恢复高考后,阿来考入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将近五年的乡村教师。阿来在《自述》中写到:“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6]阿来的个人经历是从小学到初中,再到中等师范学校,之后从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中脱离出来。在小说中,阿来往往以“我”来叙事,这当然是一种艺术策略,但不难发现其间包含着对自己童年、少年生活的一次又一次的追忆与怀想。阿来在小说中经常写到“我”与儿时伙伴、小学或中学同学面临的两种人生路向:读书与当兵。在《旧年的血迹》中,父亲要“我”好好念书,离开村子,“考不上学校就去当兵”。其实,父亲也是在十六岁时和村里的三个年轻人参加的志愿军,在成都集训一个月,因草地战事吃紧,转入骑兵团进驻阿坝草原,直到1958年才转业回到家乡任乡文书。在《永远的嘎洛》中,“我”和嘎洛的儿子绛措都在城里念中学,都想摆脱色尔古村贫困、闭锁的生活。绛措作为红军的儿子,想的就是参军提干。虽然嘎洛的红军身份始终无法确认,以致影响了女儿嘉央被推荐上大学,但绛措后来还是穿上军装离开了家乡。“我”和绛措一起参加了入伍的体检,因为“政审”不过关,“我”没能参军,只能离家四处流浪。大中专考试恢复的时候,“我”报名参加了考试,最后离家读书进城里工作了。在“机村史诗”第六部《空山》中,“我”和林军中学毕业回乡不久,林军因为父亲曾是红军的身份穿上了军装,而“我”考上学校离开了机村。在这些小说中,传说与历史、现实与回忆穿插,痛苦与欢乐、艰难与甜蜜、爱与恨、情与仇交织并行,“是拥有了一定人生体验和社会经验的阿来以‘未成年人’的眼光对自己故乡人事的一次次感悟与重新体验。”[7]小说中的成长书写总是留着阿来的身影,虚构的“我”带有“非虚构”的特性。
创作伊始,阿来潜心表现的地域是藏区,特别是他的出生地、成长地嘉绒藏区,着力书写的人是藏族、藏民,特别是嘉绒藏族。他说:“当我书写的时候,我想我一直致力的是书写这片蒙昧之地的艰难苏醒。”他的写作信仰就是“记录这个苏醒的过程”,成为“一个敏锐的同时也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8]。“从娃娃抓起”,曾经是我们的“口头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五四”时代的声音穿越时空,至今仍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阿来的成长叙事自然是“苏醒的过程”的重要环节,寓示着藏地的苏醒和藏族少年的成长。阿来试图构筑一个少年世界,以少年的成长记录来反映时代的变迁与人的命运的沉浮。傻子二少爷是土司时代少年成长的缩影,格拉是红色时代少年成长的缩影,桑吉是市场经济时代少年成长的缩影。综观阿来的少年书写,似乎构成了一个世纪藏地少年的成长史。
《三只虫草》无疑是阿来成长叙事的精心之作。小说以少年桑吉的视角叙事,虫草是叙事的焦点,但不是叙事的重心、核心。人们已经探讨过的关于人与自然及生态、官员腐败等问题是当下的“流行”话题、“热点”话题和“焦点”话题,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不可忽视的是作为小学生的桑吉的成长史及其蕴含的意义。桑吉的成长不只是年龄的增大,更是经历的充实和精神的丰富。桑吉的成长不只是增加个人的经济价值、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人格健全、精神丰富和内心强大。桑吉长大了,可以帮家里挖虫草挣钱,可以给奶奶买骨痛贴膏,给姐姐买李宁牌T恤,给表哥买手套和棒球帽,给老师买剃须泡和飘柔洗发水。这些天真无邪、单纯善良的人性光辉,是“人之初”本色的自然流露。“虫草箱子”“百科全书”事件是对桑吉“原生态”的心灵世界的“污染”。县政府调研员拒还虫草箱子的无赖与无耻,小学校长私占《百科全书》的无情与无理,桑吉进城寻找调研员的无奈与无助,都是对一个少年成长的磨砺、锻造。正是经历了这样的成人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桑吉成长了。
桑吉处在小学六年级至升入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从年龄上说,是十三岁,是阿来书写的少年的大致相同的年龄。在一次演讲中,阿来说到:“文学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人写成一样的人,并不是要塑造一群和全世界不一样的人。”[9]阿来的成长叙事是力图反映共同性、普遍性的,“普遍性是什么?是全人类共同的处境。”“以个别的苦难的经验书写,在全人类中引起良好的共鸣,这就叫普遍性。”[10]少年桑吉的成长与三只虫草的“漂流”交织,虫草的命运暗示着桑吉及其同龄的少年充满偶然性、或然性的未来。阿来试图表现的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下少年成长的共同处境,桑吉的“个别苦难”是启示性的,寓示着少年的成长必然要经受时代大潮的“冲击”、成人世界的“修理”和自我内心的“调节”。时代、社会与自我的“合力”牵引少年们向前,这是少年成长的必由之路。
二、少年的生理、心理与情感书写
伴随年龄的增长,少年的成长首先是生理的变化。“这种生理上的变化伴随着一场心理上的革命”,荣格把它叫做“精神的诞生”[11]。按照荣格的观点,童年阶段是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或性机能成熟之前。婴儿阶段,没有意识的连贯性和自我的认同感,他的全部精神生活都服从本能的制约和支配。童年阶段的后期,自我开始形成。阿来的成长书写是把握住了少年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特征的。在《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的成长在十三岁时经历了重大转折,此前他是蒙昧无知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记事是从那个下雪的早晨开始的,是我十三岁那个早晨开始的。”十三岁的傻子在生理上成长起来,有了性的欲望,十八岁的侍女桑吉卓玛给傻子进行了性的启蒙,并让他走向了性的成熟,让他终生难忘。在傻子的少年生活中,两个仆人尔依、索朗泽郎是傻子“亲密无间”的伙伴,尽管他们之间有着天生的等级的鸿沟。三个少年一起长大,在主仆关系的制约中形成了牢固的、持久的、亲密的情谊,直至终生。在《旧年的血迹》中,十二岁的“我”,对十八岁的彩芹老师产生了莫名的生理冲动或爱恋。“我不敢抬眼,害怕看到彩芹老师那高耸的双乳,……可是她的身躯由于激情难以抑制而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气,……使我感到像没有内脏似的,腹中只有虚空。……她吹拂到我后颈的气息使我一下变得浑身瘫软。胃往下滑,心往外跳。”“刚洗过的头发水淋淋地纷披在她肩头。她把头发在手指上缠绕又松开。我感到我的脊梁上穿过一股暖流。这道暖流把我的背和棱棱的石墙分开。”这是伴随生理的成长而出现的性意识的萌动,具有天生的真实性和天然的纯净性。在《少年诗篇》中,丹泊小表姐一岁,但表姐比丹泊成熟得多。麻风女人总是在舅舅上山时的路上割草,舅舅的身影消失后,她也就收了镰刀下山。丹泊问:“她连一根青草都不带走,又割草干什么?”表姐答:“她想偷走一个男人的心。”丹泊把这句话告诉了母亲,母亲就说:“你表姐能干懂事,我喜欢她。”表姐与丹泊之间瞳朦的爱,是少年成长中美丽的“早恋”。后来,表姐休了学,就完全是个女人了。少年的生理成长必然催生本能的欲求,从而引起心理的变化和情感的躁动。在《三只虫草》中,十三岁的桑吉坐在摩托车上,后面姑娘富于弹性的胸脯不时撞击他的后背,桑吉想:“长成大人后,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让身体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这是一个少年成长中的烦恼与疑惑,来自生理的本能,写得自然而贴切。
在少年的成长过程中,生理的烦恼总是与心理的疑惑、精神的迷茫结伴而行的,而后者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形成,是更为重要的成长的烦恼。在少年的成长中,自我意识的出现与增强,必然引起对自己人生、前途与命运的思考。走出周围的大山,摆脱眼前的贫困,改变闭塞的环境,是特定时期藏地少年朴素的理想愿景。在《欢乐行程》中,格拉和次多这两个乡村的孩子,拉着重载的架子车到刷经寺镇,用胡豆去换大米。“他们感到了故乡村庄的偏僻,宁静,以及和整个世界相距是如此遥远。”刷经寺镇离村子三十里,镇上有电影院、手工作坊、百货公司和公共澡堂。他俩在镇上得到了几本连环画、一支木头冲锋枪和一副乒乓球拍,听说了《洗衣歌》《过雪山草地》《逛新城》等等歌舞,还买了紫竹笛、熏鱼罐头、番茄酱和水果糖。这些都是理想愿景“落地”的切实体现。他俩享受着“走出村子”的喜悦和快感。在回村的路上,在次多的笛声中,人“飞”起来了,车子也“飞”起来了,他俩忘情地完成了这次“欢乐行程”。这种“飞”的憧憬延续到阿来创办《科幻世界》的少年版,取名就叫《飞》,少年情结根深蒂固,无法泯灭。
格拉和次多只是一次短暂的“自我放飞”,理想愿景的真正实现只有通过读书的路径。阿来在小说中反复书写父亲对儿子的要求,就是读书、读书。在《旧年的血迹》中,父亲对儿子说:“你要好好念书。”“长大了要有志气。”“离开这个村子。”后来,当“我”走出那条小山沟时,感到心清目朗,“我没有回头。连回头的想法也没有。”这是怎样的一种“出走”的决绝态度呵,表现出无比强烈的离开村庄的情感倾向。在《孽缘》中阿来写到:“父亲说阿来必须上学。”在《三只虫草》中,父亲、母亲让桑吉和姐姐上学,是为了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桑吉的眼里,牧民定居的新村不如他上学的乡政府所在地。镇上有卫生所、学校,有修车铺、网吧、三家拉面馆、一家藏餐馆、一家四川饭店、一家理发店、两家超市,还有一座寺庙。这也只是一个镇,而不是城。城里有带塑胶跑道和图书馆的学校,有电影院、广场、大饭店、立交桥,有电影里的街头黑帮,有红绿灯和交通警察。桑吉的目光遥望着更远的世界,他经由村庄、乡镇而县城的空间转换,感受到了同一片蓝天下完全不同的现实生活、人生境况。“百科全书”是桥梁,引领桑吉们走向新的人生路。尽管未来的路途还充满艰难曲折,毕竟桑吉上路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若是批评一种创作现象,是可以成立的;若一概而论“少年不识愁滋味”,恐怕不够准确。在《旧年的血迹》中,阿来写到:“少年时代的我俯视那热闹的沉迷于节日气氛的广场,就已经深刻感受到命运的沉重,我敏感的心胸被颓丧与虚无的情绪无情咬噬。”时代潮流汹涌澎湃,敏感的少年难免不被时代潮流激起的浪花所浸染、沾湿,引起心灵的波动,带来情感的起伏,由生活的艰难、人生的沉重和命运的多舛而感到颓丧、悲哀与虚无。在《孽缘》中,阿来写到:“我必须在这里揭示出在一种带着强烈的喜剧性色彩的生存状况下的泛人类的悲哀,人性的悲哀,生命本能与生命追求的崇高品格之间相互冲突的悲哀。”阿来在充满喜剧性的生存状况中感受到了生存的悲剧性,他书写的不只有少年生活的欢乐、喜悦,更有少年成长的磨难、忧伤甚至悲剧。这是少年成长的沉重与困境,令人震颤,发人深省。《环山的雪光》写的是近乎残忍的梦的失落的悲剧。少女金花在学校读书时,美术老师的美的启蒙唤醒了一个体格健壮的姑娘的女性的敏感,给了她“一个习惯”,让她总是沉溺于幻想,“金花的故事是关于她怎样小心翼翼地侧身穿过现实与梦与幻想交接的边缘的故事。”金花的爱的表白在遭到美术老师、同学道嘎的拒绝后,被迫与麦勒生活在了一起,但她觉得闷得慌,“我下山一趟吧,我去看场电影,不然带几本小说回来就够了。”金花频频做那个梦见“眼镜道嘎”的梦,因为道嘎将来要修一条铁路经过村子,在村子那里设计一个全世界最漂亮的车站。金花心中一直有梦想,始终没有放弃梦想。于是,她怀揣着先前的梦想,重新回到原来的中学读书。一个学期后,得知麦勒死了,她主动去作美术老师的裸体模特,最后用刮油彩的小刀捅向了美术老师,她说:“要是没有你,你的笔……”。严峻的现实让金花失望,梦境的破灭使金花绝望,她将悲剧之因归根于启蒙者,她对美术老师说:“你害了我。”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却符合金花“因果报应”的逻辑,在自我意识的萌生、增长中埋藏下了悲剧的种子。在《自愿被拐卖的卓玛》中,卓玛的年龄不明确,但最大也不过接近成人的样子吧。她应该比《欢乐行程》中的格拉、次多要大一些,但他们一样“飞”了起来。不过,卓玛不是快乐地“飞”回村庄,而是悄悄地“飞”出村庄,“飞”过乡镇,“飞”到了她自己都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后来的传说是,她让那个收购蕨菜的老板把她带走,在远处卖掉。”卓玛“自愿被拐卖”的有违常情、常理的行为背后,是她的“梦境”的萌发、蓄积与膨胀,是山梁外的世界的“阳光”对她内心的“照亮”。卓玛从自我意识的萌生、增长迈向了自我实现的行动,体现了藏地少年“跨越性”的成长与进步。金花、卓玛的形象反映了少年成长的沉重、艰难与不幸,揭示了少年心理的焦灼不安和情感的躁动不宁,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
阿来说:“文学艺术最最基本的是诉诸情感,它首先规定的是人的情感状态。它不光是要求我们的作品要写出情感,而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写作某种情感的时候写作者自己必须处于这种情感状态中,自己首先被这种饱满、强烈的情感所控制。”[12]阿来书写少年成长的欢乐与喜悦、烦恼与忧伤、痛苦与悲哀,是饱含情感的,是为强烈的情感所控制的,而情感的抒发没有脱离叙写,“是潜藏在叙写背后情感的流淌律动”[13]。不管是《环山的雪光》,还是《自愿被拐卖的卓玛》,阿来都聚焦于少女游移在“梦境与现实”交接边缘的复杂而多变的内心世界,不露声色地表现少女对梦境的执着和失落的空洞感,对现实的无奈和失望的空虚感。阿来书写少年情感的高超之处在于,他“把人的情感、心理,尤其是把人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那种微妙的联系,生成一个生动细腻的微妙的敏感的表达”[14]。金花在美术老师、同学道嘎和麦勒之间的情感“周旋”和自我思虑,卓玛在村里女人、小伙子和生意人面前的情感“波动”和自我决断,都被阿来“潜藏在叙写背后”,成长的生理烦恼、心灵波动和情感纠结就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在艺术上是一种纯熟的境界。
三、少年成长的精神阶梯与向度
阿来书写少年的成长,有一个细节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对词典或书的反复描写。词典或书是一种隐喻,寓示着少年成长的精神阶梯与向度,阿来特别以此展现少年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在散文《词典的故事》中,阿来非常动情地回忆起自己在小学快毕业时到刷经寺镇买《汉语成语小词典》的难忘经历。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少年往事,从中不难感受到、体会到阿来自身对词典或书的钟爱之情。在《旧年的血迹》中,阿来写到父亲给“我”买了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成语小词典》,仿佛是少年往事的纪实。在《永远的嘎洛》中,“我”被迫离家四处流浪,到处帮人干活“混”饭吃。在许多细雨霏霏的夜晚,“我”借宿在人家的门廊上,就着漏出的灯光,阅读从一家纸厂弄来的准备化浆的废书。在《已经消失的森林》中,罗布(程卫东)把他以前上学用的初级小学课本送给“我”,“我”凭借书上的人民币图案,猜出了“圆”“角”“分”并牢记下来,以后从来没有念错过一次,也没有写错过一次。似乎是调侃的叙写,却是开卷有益、终生受用的直接表达。在“机村史诗”之三《达瑟与达戈》中,达瑟从民族干部学校拉回十几箱书,里面有学校发的课本、参考资料、中国小说和苏联小说。达瑟回到机村,与书为伴,“他真正觉得有用的书是硬皮封面的,是大开本的辞典,是《百科全书》。”小说中还多次写到这本《百科全书》。在《番茄江村》中,阿来借番茄之名的考据,再次写到达瑟的百科全书,并对书的“零落与毁损”发出深深的感慨与叹息。在《三只虫草》中,《百科全书》是一个重要的“道具”,桑吉对《百科全书》的“盼望”“夜读”“追讨”,道尽了一个少年在成长中对书的渴慕、祈求,对知识的渴望、渴求。升入初中后,桑吉在学校图书室“借阅”了《百科全书》,之后他给多布杰老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想念你。还有,我原谅校长了。”《百科全书》是桑吉成长的精神阶梯与向度,虽然走得很沉重、很艰难,但步履却是坚实的、坚定的,刚升入初中的桑吉就“原谅校长”了,心胸开阔起来了,精神世界开始变得宽广起来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个向度的少年成长,比如《孽缘》中的斯丹巴等。他们的词典或书是庙里的藏文、经书,通向宗教,成长为和尚、喇嘛。其实,喇嘛听说桑吉天资聪慧,在学校里成绩好得不得了,就说:“这就是根器好。可惜早年没有进庙出家,而是进了学校。学校好是好,上大学,进城,一个人享受现世好福报。如果出家,修行有成,自度度人,那就是全家人享受福报,还不止是现世呢。”阿来对藏地少年成长的书写,对词典或书的不断强化,体现出对少年成长的精神向度的思考,触及的是深层的文化命题。“本土”与“外来”,“自我”与“他者”,“藏化”与“汉化”,总是在融合与冲突间并行,对少年的成长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词典或书是现代文明的隐喻,暗示少年的梦想与追求。阿来反复书写词典或书,表达的是少年对现代文明的向往,词典或书成为少年成长的动力或加速器。词典或书“藏着思想与知识”,“藏着一个悄声细语冥思苦想的聪明人”。比词典或书更具有广泛性和吸引力的是新生事物。“读”书一般来说是个体行为,而对新生事物的向往却是群体性的、大众化的,更具有冲击力和引领性。阿来在小说中不时写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生事物、新的东西和新的现象等等。在《旧年的血迹》《永远的嘎洛》《孽缘》中,色尔古村出现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红岩》、《青春之歌》、《星星》诗刊、连环画《铁道游击队》、花生糖和饼干。在《鱼》中,柯村出现了汉文学校、汉文报纸、书籍、连环画和文件;河对岸新建了伐木场,工人穿蓝色工装,用鱼竿钓鱼,煮鱼吃;村里的代销点开始出售手电筒、尼龙袜子和农药。在《奥达的马队》中,山沟里住进了公路勘探队,公路四处延伸,卡车沿路行驶,隆洼寺庙用上了自来水。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阿来曾以“新生事物”为题发表了《马车》《报纸》《水电站》等小说,类似的还有《电话》《脱粒机》《喇叭》等。这些新生事物在古老的机村都是第一次出现,成为镶嵌在当代乡村图景上的美丽“花瓣”,标志着生活的变化、乡村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机村史诗”之六《空山》开篇第一句就是:“机村人又听见了一个新鲜的词:博物馆。”新生事物就像一块巨石入水,总是在机村激起一朵一朵的浪花,生出一圈一圈的涟漪。阿来构筑机村的编年史,新生事物成为时代演变、乡村变迁的标志物,少年与新生事物的关系成为少年精神成长的“试金石”。
水电站是阿来反复书写到的新生事物,而且是自觉地作为藏地新生事物的代表来书写的。在《已经消失的森林》中,阿来似乎是以纪实的手法写到了1976年村子修建水电站的事情。阿来写到,这个村子是“哺育我最初全部生命与情感的村子”,但是现在,记忆中的森林、众多的溪流、童话般的气氛、歌谣般的色彩已经消失了,“我下定决心不把故乡村子的名字写进小说,只用村子这个泛称来称谓这个村子。”阿来特意写到:“这也并不意味着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获取作品的典型性意义,虽然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接合部上的大渡河、岷江、嘉陵江发源的地区多的是这样的村子。”这是“欲盖弥彰”的叙事策略,等于告诉读者“我”在挖掘典型。在《少年诗篇》中,居里日岗村有了一所公办初级小学和一座小水电站。“建电站时,小学生们每人背一条口袋排着队,唱着歌去参加劳动。”这个情节在《水电站》中被“放大”了。《水电站》写了地质队员、村民和小学生三组人物。地质队员是“外来”的,他们宣称要给村里修一个水电站。他们的骡子队驮来各种稀奇东西:帆布帐篷,折叠床、桌子和椅子,各种各样的尺子与镜子。而机器、风向标、玻璃容器、记录本、图纸等等,更是机村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显然这是新的文明的象征。村民是由保守趋向文明的人群,他们开始与地质队员是隔膜的,尽力不到地质队扎营的地方去,假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后来才变得有些亲近。小学生是观察者、参与者,成为受水电站影响最大的人群。地质队员的到来,他们的行动、活动与生活,他们带来的东西,他们的工作状态,都引起了小学生们强烈的心理感应和情感激荡。阿来说:“我更关心那些更加好奇的少年,面对生活中的新奇世界表现出来的不由自主的欣喜。”[15]阿来将笔墨落在这群小学生的心理、情感和行动方面,营造了特有的氛围和状态,对小学生的好奇、期待、慌张、激动、欣喜的叙写,表现出了“外来”的新的文明的魅力,表现出了这群小学生对新生事物的向往,这于少年们的精神成长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的。机村少年被邀请去参观地质队,参加“科学主题日”活动。当活动结束离开地质队营地时,好几个孩子伤心地哭了。小说写到:“直到现在想起来,那一天的回忆是多么甜蜜啊!”这是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1974年有几个勘探森林资源的地质队员去到了阿来的故乡马尔康县马塘村,已经十五岁还在读小说五年级的阿来,受到地质勘探队员的影响,产生了“飞出大山”的憧憬。“外来”的文明成为少年们成长的助燃剂和加速器。阿来念念不忘少年时代的“文化哺育”,在小说创作中以自身的经历为原型,给予少年生活想象性的再现,其成长叙事反映了个人的成长之路,成为自己的精神自传。阿来以少年的成长记录来反映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时代与人的命运交响,准确把握了少年成长的生理、心理与情感特征,特别凸现了藏地少年成长的精神向度,成为别样的藏地少年世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恒久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