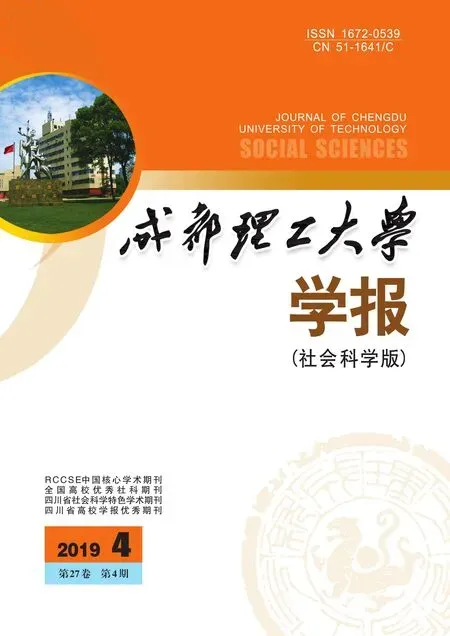走向逍遥之境的层次性
——《庄子·逍遥游》“知效一官”段的现代阐释
2019-02-15万勇华
万勇华
(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逍遥游》作为《庄子》全书的首篇,着重探讨的是何为逍遥之境以及如何达到逍遥之境。在该篇中间一段,庄子特别提到了“知效一官”者、宋荣子(即宋钘,也称宋子)、列子和至人—神人—圣人。这四类人物由于存在规定的不同,导致他们对于逍遥之境的追求呈现出了由远及近的距离差异性,表现出了由低到高的层次递进性。
一、沦为最低层次的“知效一官”者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一方面生产发展、文化繁荣,另一方面政治失序、道德失范。面对混乱无道的社会现实,各国执政者打破陈旧的世袭等级观念,不拘一格地招贤纳士,从而形成了“养士”的社会风气。当时许多有为的国君如齐威王、齐宣王、秦穆公、魏文侯、梁惠王、燕昭王等招揽了数以千计的贤士,另外一些知名的卿相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以及秦相吕不韦等,也笼络了大批人才。这些统治者不仅对士人表现出恭敬的态度,提供优厚的待遇,而且给予很高的地位,委以重要的官职。他们这样做既是为了安邦治国,巩固政权,更是为了称霸诸侯,一统天下。可以说,正是各国统治者的“重士”做法为普通士人施展聪明才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而广大士人把握此等良机,竭力运用自己的知识、才能、道德和品行报效君王,成就功名。
上述士人就是《逍遥游》中提及的“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从世俗的眼光看,这类人已经超越普通民众,跻身成功人士的行列了。然而,此处必须注意“一官”“一乡”“一君”“一国”中的“一”字。这个“一”乃是一偏、一隅,而非大全、整体。具体而言,那些智慧能够担任此地官职的人,未必能够胜任彼地的官职。这就好比今天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专家,往往只是擅长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而拙于其它方面、其它领域。同样的道理,那些品行、道德、能力为这一乡、这一君、这一国所称道的人,并不见得就为他乡、他君、他国所推崇[1]25。例如居行貌似忠信、廉洁的乡愿虽能赢得一乡之人的夸赞,但却因为虚伪圆滑、趋炎附势而遭到孔、孟的批评;还有极具治国才能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虽然于秦孝公掌权期间获得重用、实行变法,但是之后在秦惠文王当政不久由于受到诬陷、猜忌而招致杀身之祸、车裂之刑。所以说,以上这些人看起来声名显赫、成就斐然,其实都是一曲之士、小成之人,根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满的地方。然而,他们偏偏沾沾自喜于获得世俗的功利价值,就如同蜩鸠、斥鴳洋洋得意于腾跃树枝草丛间一样,实在贻笑大方。
从存在论的角度看,“知效一官”者的实践活动主要涉及两大方面:一是政治领域,二是伦理领域。就前者而言,政治才能的施展要以特定的国家和具体的官职为舞台。就后者来说,优良德行的传颂要以一定的伦理关系和明君的存在为背景。进而,个体能否在政治领域获得认可、赏识,取决于在上者(如君主)的立场和态度;能否在道德层面赢得肯定、赞誉,则依存于外在的评价对象和评价标准。一旦离开了存在背景和评价系统这些外部条件,个体的成功形态也就不复存在[2]222。就此而言,上述条件构成了对于个体的外在制约。如果从内在的心理层面加以分析,既然“知效一官”者将世俗的功名利禄视作人生追求的全部目标,那么当他获得这些东西时,自然就会感觉心满意足,反之失去时,难免变得心灰意冷。于是,他的心灵始终受到名利等身外之物的左右,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心为物役”的困境中。为了确保获得的外物不再失去,他必须时刻算计着,提防着,从而内心一直处于紧张、不安中。在此意义上,个体又为内在的欲求、情意所牵累。统而言之,存在背景、评价系统之类的外部条件和欲求、情意之类的内部因素构成了对于“知效一官”者的双重限定。因此,相对于后面几种人,“知效一官”者更加远离逍遥之境,所以只能划入最低层次。
二、处于较高层级的宋荣子
在“知效一官”者后面,庄子隆重推出了宋荣子这个人物。作为著名的稷下学者,宋荣子博采众长,并加以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二重性的思想体系。
一方面,就内在修养而言,宋荣子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道家性。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宋荣子“以情欲寡浅为内”(《庄子·天下》)的见解与老子“少私寡欲”(《老子·19章》)的观点一脉相承[3]。老子目睹世人因为欲求过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为腹不为目”(《老子·12章》)的“寡欲”主张,强调个体仅需最低限度的物质条件即能维持基本生存。与之相近,宋荣子认为人类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荀子·正论》),只要“五升之饭”(《庄子·天下》)能够充饥活命足矣,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物质追求。第二,宋荣子“见侮不辱”说源自老子的“宠辱若惊”(《老子·13章》)、“知其荣,守其辱”(《老子·28章》)思想。在宋荣子看来,“侮”来自于外,体现为负面的言行;“辱”产生于内,呈现为消极的情感。因为外、内不相及,所以“侮”与“辱”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个体若能对于外在之“侮”无动于衷,自然不会形成内在之“辱”,这就是“见侮不辱”说的深层内涵。至于其真正用意,《庄子·天下》篇明言:“见侮不辱,救民之斗。”可见,宋荣子提出“见侮不辱”说乃是为了彻底消除引发争端的思想动机,从而避免人世间许多无谓的争斗[3]。第三,宋荣子“不以身假物”(同上)的观点与庄子“不以物害己”(《庄子·秋水》)的思想具有一致之处。在庄子看来,“己”作为个体形态的自我,具有优越于物的品格。一旦将自我消解在物之中,便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庄子主张“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要求人主导物而非为物所支配。宋荣子认为,“身”作为生命存在的感性表征,其价值远高于名利之类的外部对象。如果将感性之“身”失落于外物的追逐中,势必导致身为物役的后果。鉴于这样的理解,宋荣子提出“不以身假物”,期望世人扬弃个体物化形态,实现自身内在价值。
另一方面,就外在功用来看,宋荣子思想体现出了强烈的墨家性。《荀子·非十二子》篇这样评述道:“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此处,荀子将宋钘与墨翟放在一起加以批判,指明二人学说存在相通之处。具体而言,第一,在平等问题上,宋钘“作华山之冠以自表”(《庄子·天下》)。对此,陆德明解释道:“华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蒋锡昌进而指出:“宋钘以华山之冠自表,似有提倡人类生活平等之意。”[4]872依陆、蒋之见,宋荣子作冠之举旨在表明自己追求平等的志向。因为不满于儒家“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观念,墨子提出了“兼爱”“尚贤”的主张,希望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理想社会,确保广大群众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比较而言,宋荣子只是通过制作帽子的方式隐约地传递出了平等的观念,而墨子则是采用著书立说的形式明确地表达了平等的要求。第二,在战争问题上,宋荣子主张“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庄子·天下》),要求各国统治者停止所有攻伐,熄灭一切战事,从而实现天下安宁、百姓活命。为了达成这样的心愿,他曾在古稀之年不远千里前往楚秦二国,力图说服二王罢兵(《孟子·告子下》)。墨子身处战火连绵、攻伐不断的时代,积极宣扬“非攻”思想,希望消弭战乱,重现天下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曾不辞劳苦步行十日十夜赶到郢都,劝说楚王放弃攻宋计划(《墨子·公输》)。第三,在功利问题上,宋钘强调凡是不利于天下的事情,一概不做(《庄子·天下》)。正是以“利”作为行为的标准,他才游说楚秦二国停止干戈(《孟子·告子下》)。因为在宋钘看来,战争有百害而无一利。墨子认为人类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要求仁人志士致力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而攻伐战争作为不义之举,不仅给交战双方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危及上天、中鬼和下人的利益(《墨子·非攻下》)。因此,他坚决反对大国进攻小国,强国侵略弱国,希望所有国家都能互利互惠,和平共处。第四,在自苦救世问题上,宋钘及其弟子虽然经常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但是依然不知疲倦地“周行天下,上说下教”,只为“救民之斗,救世之战”,所以庄子称赞其为“救世之士”(《庄子·天下》)。墨子及其追随者奉行大禹之道,“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同上)。为了兴利除害,“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同上),即便是“摩顶放踵”(《孟子·告子下》)、“赴火蹈刃”(《淮南子·泰族训》)也在所不辞。这种吃苦耐劳、救世济民的精神,赢得了庄子的好评:“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如果将宋荣子与“知效一官”者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其间的巨大差别:一是后者仅仅局限于一官、一乡、一君、一国,前者则放眼于天下、海内和万民;二是后者孜孜以求于获得个人的成功,前者则全力以赴于“安天下”“调海内”“活民命”(同上);三是后者受到功名利禄的牵累和舆论评价的约束,前者则不受外物的役使和外在评价的左右(《庄子·逍遥游》)。就此而言,宋荣子确实比“知效一官”者进了一层。然而,他也有自身的问题。首先,就是“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同上),亦即区分内与外、辨别荣与辱。而内外之分、荣辱之别本身蕴含着界限,因此执著于上述分别,必然受到它的限制[2]222。其次,宋荣子尽管有着“救世”“救民”的历史责任感,然而由于他的主张违背时代发展的潮流,说教方式又带有强迫的性质(“强见”“强聒而不舍”),因此最终落得“天下不取”“上下见厌”(《天下》)的下场。再次,宋荣子“犹然笑之”显示了自身的欠缺。如果说前文鴳之笑鹏乃是“以小笑大”,那么此处宋荣子之笑“知效一官”者则是“以大笑小”。表面看来,后者之笑异于前者,然其实质不过“自足之见,斯其所得亦浅哉”[5]13,所以庄子断言“犹有未树也”(《逍遥游》)。综上所述,宋荣子虽然没有达到真正的逍遥形态,但是相对于“知效一官”者距离逍遥之境要近一些,因而处于较高的层级。
三、位于更高层面的列子
在宋荣子之后登场的人物是列子。作为道家前辈,列子的思想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显示了多面的性质。
首先,“贵虚”是列子思想的核心。《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云:“列子贵虚。”《吕氏春秋·不二》篇亦曰:“子列子贵虚。”这是对列子思想最为简要的概括。就理论渊源而言,列子“贵虚”思想可以追溯至老子“虚其心”(《老子·3章》)、“致虚极,守静笃”(《老子·16章》)的主张。从具体内涵上看,列子所贵之“虚”可以理解为清虚、虚静、心灵无执等义。其次,“贵正”构成列子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战国策·韩策》记载:“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这里通过史疾和楚王的对话揭示了列子“贵正”思想的内涵与作用。所谓“乌不为乌,鹊不为鹊”是指名不符实,名失其正也。只有乌为乌、鹊为鹊,才算名实相符,名得其正也。可见,列子所贵之“正”,实质上是“正名”的意思[6]。依据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国君必须按照官员的才能授以相应的官职,责令他们“在其位,谋其政”,做到廉洁奉公,胜任其职,这样就能禁止盗贼横行,实现国家太平了。再次,安贫保身也属列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吕氏春秋·观世》篇写道:“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至己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则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且方有饥色之患矣,而犹不苟取,先见其化也。先见其化而已动,达乎性命之情也。”列子尽管生活贫困,面带饥色,仍然谢绝了郑相子阳所赠之粟。因为他深知子阳此举并非真正了解他,只不过是听了别人推崇他的话,那么将来也完全可能因为听了别人诋毁的话而怪罪于他。后来,郑国的百姓发难杀了子阳,而列子却因当初拒收馈赠而幸免于难[7]766。对此,钟泰评论道:“保身必有见于几先也。”[5]673假如列子没有先见之明,苟取施舍,那么在子阳被杀后,必将陷入“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则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的两难境地。令人钦佩的是列子凭着“先见其化”的睿智,去除不义与逆,安贫保身,最终通达性命之情。
如果将列子与宋荣子放在一起对比,可以看出其间的高下之别:一是后者依靠双脚,日夜不休地奔波于诸侯国间,显得异常艰辛疲惫,而前者凭借风力,随意地到处行走,在形式上给人轻盈美妙的感觉(《庄子·逍遥游》)。二是后者虽然没有汲汲营求个人的富贵爵禄,但是依然期望建立泽被天下、惠及万民的丰功伟业,而前者则已完全摒弃世俗的功名福禄(同上),达到了精神超越的境界,从而不再受到人间浮名虚誉的牵累。就此而言,列子确实比宋荣子更进一层。然而,他也有自身的不足。首先,列子“御风而行”(同上)固然飘逸、自在,但是他的行走必须依赖于风,一旦离开风便无法“免于行”(同上)[2]222。况且他乘风行走未能达到游于无穷的地步,不得不“旬有五日而后反”(同上),这个“反”字表明了列子之行的有限性[8]。其次,列子的处世方式具有片面、刻意的特点。《应帝王》篇云:“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文中“三年不出”“一以是终”显示了列子近乎隐者的避世生活。具体到日常行为而言,他表现出了标新立异的性质:一方面,相对于当时男尊女卑、人贵物贱的观念,列子“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另一方面,相对于儒家“亲亲为仁”“克己复礼”的思想,列子“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这样一来,本想避世清静的列子由于与众不同的举动,反而招致了广泛的关注。《列御寇》篇记载,列子出则引人瞩目(“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遣”),入则门庭若市(“户外之屡满矣”)。这种情况说明,列子只知道一味地避世,而不懂得出(世)入(世)自在、无所沾滞;只想着刻意地表现,而不明白和光同尘、随众顺俗。再次,列子尽管“贵虚”,但是并未达到虚之极致。对此,《田子方》篇通过列子与伯昏无人的射箭故事作了生动的说明:“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也,犹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深入分析列子无法实施“不射之射”的原因,可以发现他的内心依然“有己”,仍旧存在生死安危的意识。正因为他的心灵并未虚而至极,所以,当他看到伯昏无人“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展示“不射之射”的时候,吓得匍匐在地,冷汗直流。综上可见,列子显然没有达到逍遥自在的存在形态。不过,较之宋荣子,更加趋近逍遥之境,因而处于一个更高的层面。
四、臻于最高境界的至人—神人—圣人
上述三类人物尽管表现形态有所不同,但在受限定、不逍遥这一点上,又是彼此相通的。那么,如何才能超越限定、走向逍遥呢?庄子提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作了正面回应[2]291。关于“乘天地之正”的含义,郭象有个经典的解释:“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日常语言中的天地乃是万物的总称,而万物则是天地的实体。天地间的每一事物,不管是大鹏、斥鴳,还是椿木、朝菌,都有自身的自然本性(“正”),这种自然本性决定了万物的存在都是自己如此,而非人为使然(“不为而自能”)。由此,“乘天地之正”,无非是要求摒弃一切外在的人为干预,完全顺任万物内在的本然之性(“顺万物之性”)。至于“御六气之辩”,“御”字并非驾驭、操控之义,而是因任、顺遂的意思。“六气”的说法很多,司马彪注为“阴阳风雨晦明”,支道林解作“天地四时”[9]19-20。其实,“六气”只是泛指,不必坐实理解。“辩”之用法,郭庆藩明确指出:“‘辩’与‘正’对文,‘辩’读为‘变’。……‘辩’、‘变’古通用。”[10]21由此,“御六气之辩”即是因任六气的变化。关于“游无穷”,不少治庄者将之理解为心灵遨游于无止境的精神领域,从而使得“游”之主体仅仅限于无形之心,“游”之范围只是拘于精神世界。然而,根据庄子行文的思想脉络,“游无穷”不仅体现为心游,还包含着身游,不仅游于无穷无尽的内心世界,还游于无边无际的外部世界。一言以蔽之,“游无穷”即实现逍遥游的意思。总之,在庄子看来,个体只要顺遂万物的本性,因任六气的变化,就能超越内外条件的限定,达致真正的逍遥之境。
上述“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其实就是下文谈到的至人、神人和圣人。后三者可以说是对前者不同视角的指称。为了更好地做出说明,庄子特别提出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断语。这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无己”说。有的研究者根据字面的含义,把“无己”理解为否定自身,消解自我。然而,如果依照这样的解释,那么,逍遥本身将会成为问题:因为按照逻辑,没有自我,何来逍遥的主体?没有逍遥的主体,又如何落实逍遥的境界呢?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层的语义,而应进行深入地考察。纵观《庄子》全书,可以发现庄子所说的“己”实际上包括两种形态:一是社会化、文明化的“我”,二是自然的、真实的“我”。他反对前者而赞成后者。由此,“无己”的实质乃是超越礼乐文明塑造的“我”,回归与自然为一的本真的“我”[2]293-294。接下来的“无功”并非没有功绩的意思,而是强调摒弃对于功绩的刻意追求,顺任万物的自然天成。对此,庄子通过“姑射山神人”的寓言作了具体的申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逍遥游》)一方面,神人主观上不愿意管理天下的事务,不屑于建立人间的功业,所谓“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孰肯以物为事”表达的即这层意思;另一方面,客观上他又具有奇异的特点,显示了非凡的功能,所谓“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当然,神人的功业并非有意为之,而是遵循事物的内在法则,任其自然发展的结果。总之,无心于建功人世,却意外地惠泽万民,这就是“无功”的真正内涵。最后,“无名”并非没有名声的意思,而是要求放弃虚名的追逐,避免无谓的牵累。对此,庄子通过“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故事作了进一步阐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这里的“名”既可从认识论的角度解作名称、概念,也能从存在论的视域释为名声、名望。与之相应的“实”既指对象、实在,也关乎人的实际生存状态。而“宾”侧重于表达从属的性质。合言之,许由所说的“名者,实之宾也”,就名实关系讲,主要强调事物的名称是第二位的东西,应当符合客观实在;就个体“在”世过程看,意在突出名声、名望相对于实际生存状态,仅仅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因而根本不值得人们去追求。后一观点可以看作“无名”观念的具体发挥[2]295。总的来看,无己、无功、无名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三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至人、神人、圣人所达到的超越境界。
作为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虽然称谓不同,但是精神境界趋于一致,因而可以通用。如果将至人—神人—圣人与列子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后者只能“御风而行”,前者则能“御六气之辩”;后者必须“旬有五日而后反”,前者则能“游无穷”;后者仍然依赖于外在条件(“犹有所待”),前者则已摆脱所有外在制约(“恶乎待哉”)。由此可见,至人—神人—圣人相对于列子处于更高的层次,已经臻至逍遥游的最高境界。
综上所述,“知效一官”者、宋荣子、列子和至人—神人—圣人作为庄子列举的四类存在形态,尽管在存在规定上具有差异性,但在追求逍遥之境上又显示了一致性。如果我们将逍遥之境视为终极的目标,那么至人—神人—圣人则已达成目标,因而没有距离,而“知效一官”者、宋荣子、列子则还没有实现目标,因而尚有差距——具体而言,“知效一官”者离之最远,宋荣子稍近,列子更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上述四者走向逍遥之境的过程表现出了明显的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