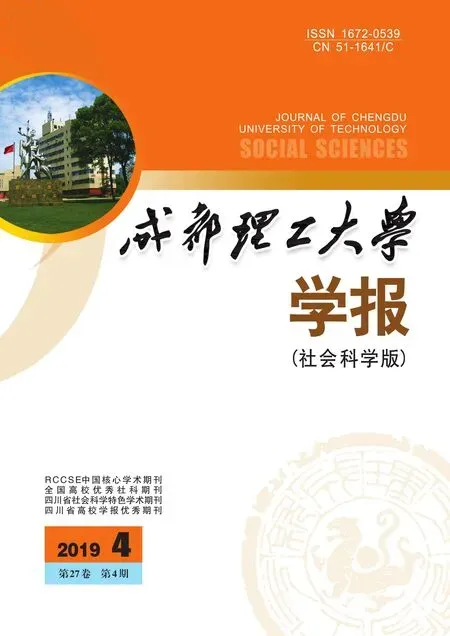从《山木》联系“内篇”看庄子的处世哲学及其演变
2019-02-15赵焱
赵 焱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33)
一、《庄子》的寓言和《山木》
(一)《庄子》的寓言
《庄子》中最具文学特色的便是寓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要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1]2143寓言文体很适合庄子,此文体较为自由,可使其汪洋恣肆之辞藻和无垠诡谲之想象任意驰骋。庄周自称其创作方法为:“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2]1098《寓言》曰:“寓言十九,藉外论之。”[2]948自郭象以来对寓言的说法有很多,正如张洪兴言:“不管怎么说,上述论点都是从‘籍外论之’这一基点出发的。”[3]
(二)《山木》概述
王夫之言:“山木,引人间世之旨,而杂引以明之。”[4]166《山木》第一个寓言故事是庄子和他弟子之间的问答,由大木无用得以存活,而大雁不鸣而遭杀食,叙述保全自身的难处。庄子的答案则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又言:“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2]668
方勇说:“庄子一开始就企图为人类寻找一个不仅摆脱现时社会困境,而且摆脱最终生命困境的途径。”[5]那么这些都需要一些原因和理由,首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庄子要谈论生存方面的问题。
二、庄子生存年代的社会概况
(一)庄子的生存年代
据钱穆《庄子生卒考》中言:
庄子生年当在周显王元年十年间若以得寿八十计则其卒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间。史记又云:“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余推定,周盖历齐威、宣,梁惠、襄,晚年及齐湣魏昭耳。[6]
由此得出庄子生活在战国的中后期,也就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二)庄子的处境
庄子生于周显王之时,是战国时期很重要的节点,其在位之时,诸侯以秦为首先后称王。《史记》记载: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为王。[1]160
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吕思勉是这样概写的:
当是时也,海内分为战国七。曩所谓二等国者,日益陵夷,不复足为诸大国间之缓冲。诸大国则征战益烈,终至由争霸之局,易为并吞之局焉。此盖势之自然,非人力所能为也。[7]
钱穆所言庄子生卒于周显王至周赧王之间,当时诸侯由争霸变为兼并,战争规模日益宏大,冲突革新交相迅亟,昏上乱象,黄钟毁弃,民众倒悬,这近乎就是庄子眼中所见到的世界。
(三)庄子对现实的描写
庄子在《人间世》中描述了你争我夺、互不信任、干戈横行的乱世,无数惨遭戕害的无辜者,充满了无礼的暴戾。庄子揭示了一个血淋淋的、黑暗的人世间。
在《人间世》中,卫国君主“轻用其国”“轻用民死”,国境内随处可见都是死人,哀鸿遍野,普通百姓不知道究竟何去何从。颜回欲干预其政,却得到孔子的种种否定,道出了民众的疾苦与伴君难;又有叶公子高将为使节,写出为统治者办事的疑惧重重,四面为患之难;同时还有身为太子师的忧虑。
庄子在《人间世》中借楚人狂接舆之口对人世间感叹道: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2]183
由此看来,人间上至君臣下及百姓皆不能幸免于水深火热、提心吊胆的煎熬,人世间竟相竞逐,纷争不休。
三、人间纷争的起因
(一)成心
庄子在《齐物论》中最早提出人间纷争的原因是“成心”,“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2]56这句话的大意为:若以个人的成见当成是非的准绳,这样任何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准绳。
有“成心”,就会有自己的成见,有了这种我执就会有人间的争论不休;“百家争鸣”,儒墨相争;就会有君王的无道专横,颜回的“內直外曲,成而上比”[8]113等。
说到“成心”就不得不言“机心”。
在观念形态上,与“成心”相联系的是“机心”。成心表现为已有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定势,机心则既以知识系统与价值取向为内容,又展开为具体的动机意识或目的意识。[9]
那么“机心”具体表现的意志和状态是怎样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9]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机心”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就是“心机”,其实践是以算计和谋划为手段的,所以必然具有很强的功利意识在里面。
《齐物论》第二节中庄子详细地描绘了“百家争鸣”,各个主张派别之间的争论,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争辩者的复杂心理过程。哀乐无常,性情大变,难以适从。他们不安终日,战战兢兢,可是又不知道它们的缘由何在。庄子在这里说:“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2]51而突然顿悟这些情态所发生的根因就是庄子所谓的“成心”。
(二)“名”“知”
在《人间世》孔子与颜回的对话中,庄子提出了天下纷争的根源为“名”“知”。“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2]135
庄子给出了关于因“名”而起纷争杀戮的几个例子。身为人臣,地位在下而修身养德去关爱体恤人君的百姓,若此为之,忤逆人君必遇猜忌,虽其修身养德、爱育黔首,然必身由此事害矣,所以夏桀杀关龙逢,帝辛逼迫比干自剖其心;唐尧攻伐丛、枝和胥敖之弹国丸土,夏禹征讨小邦有扈,小国的辖内变为焦墟,布衣横死,国君身亡,皆因其贪名图利,不断加兵。庄子说这是因为好名求利的结果。庄子又借孔子语颜回警告:“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2]139《德充符》曰:“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2]217运用智巧求取名利是灾孽的起源。
《山木》中庄子借鲁侯问熊宜僚解忧指出统治者的“权”是争的开始,鲁侯的权位成了他的负担、成了他的忧虑;又有狐狸、花豹就算夜行昼居,警惕异常,可还是免不了网罗机关陷阱的祸患,这是因为它们身上的花皮而招至来的灾难,而鲁侯的权势地位与花豹、狐狸的皮毛本质上相同。
在《山木》第八节中,庄子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比喻世间争名逐利、疲于奔命、深陷其中的世人。庄子道:“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2]695物之间相互累害是由于其相互招引谋利贪图所致的。世间无休无止的争乱令人“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意思就是说,求名逐利而忘掉了自身迷失了真性。人为求 “名”“利”“实”,运用智巧不择手段的争夺,事无巨细都很相似,欲望的横流变为杂乱无序的混沌乱世,人们的“争”成了荒谬的开始,由于“争”而丧失了真性,丧失了本我。
四、 庄子的处世哲学及其演变
(一)无用之用
面对人世间的纷争庄子提出了针对性的生存哲学,试图拯救世人。
首先就是针对“于世有用”而提出来的“无用之用”,孔子说:“君子不器。”[10]身为君子应该无所不通。而庄子却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2]186“无用之用”这个观点在《庄子》内篇的不同章节中曾反复出现,每次出现大都是以“劣树”“畸人”为例与世间有才和无才之徒作比,最先出现于第一篇的《逍遥游》。惠子言樗树又大又歪,没有用处。而庄子用狸狌死于机关网罟为例反比樗树臃大而免于斧斤之患。物无害者,正是因为它的“无用”。
在《人间世》中庄子反复提及“无用之用”这一处事方法。如有一个匠人来到了齐国,见到一棵社树,社树难以想象地巨大,来参观的人很多,可是这位匠人却从不看它,匠人说正是因为无用,这棵社树才能生长得如此久并且高大。夜间栎树给匠人托梦,说它历时良久才为无用之木,才保全了自己。又如南伯子綦散游于商丘见一巨树,感慨说道:“正是作为无用之树才能长得如此巨大,圣人也是这样看起来没用的。”稍粗些的树会被人砍来栓动物,再粗些的会被砍去盖房屋,更粗些的会被用来做寿材,故有用的树木皆不得终其天年。另外古时祭祀禳灾的时候不用白额的牛和鼻子朝天的猪,河祭时绝不用患有痔痼顽疾的人,因为在巫祝的眼中此乃不吉,可是在神人、圣人的眼中反而认为是“大祥”。还有支离疏因形体支离怪畸不全而免去了税赋徭役,无干戈之苦,得到政府赈济,凭着打杂工便可养活家人,享尽阳寿。
有的人说庄子把顺其天性、终其天年当作人生的最终目的,认为庄子只为实现自我价值,忽略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否认人的社会价值等,未免有先入为主之嫌,庄子言“顺其天性,终其天年”只不过是打了个比方,并未见有“实现人生自我价值”之类的话,这只不过是庄子对处于乱世的营营众生所提出的处世建议罢了。
(二)材与不材之间
《山木》中,其弟子问庄子,不鸣之鸟被杀,不材之木得终时庄子给出的回答是:“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变,代表庄子因对绝对的否定而转向相对主义,其内心有所动摇导致复杂化,所以有时候会陷入诡辩的泥沼。
在《庄子》内篇中有许多达至材与不材的方法,“心斋”“以明”“虚己”“养生”“充德”等相互联系,而且都是内向的修养方法。何为“心斋”,庄子借孔子之口言: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8]117
气是虚,“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集虚乃“心斋”。何为“听之以气”,“气”又具体指什么?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体味庄子所说的“心斋”是何意了,张松辉有如下观点:
统观古人说的‘气’,仅从哲学的角度讲,大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抽象的‘气’,类似于今天说的‘精神状态’;一类是具体的‘气’,类似于今天说的‘细微的物质颗粒’。[11]
而庄子所谓的“气”则属于后者,就是“精气”,也可以简称为“精”。从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庄子总结的人生生死循环的几个阶段:“无气—气—始聚气为形—降生—死亡—气”,所以当一个人还处于“气”的状态时是没有任何思维能力的,更谈不上任何思维观念,自然也就没有“成心”了,更谈不上有什么追名逐利的算计和功利性企图了。孔子要颜回的心回归至气状,自然就达到虚无的境界、空明的心境,就能去感受无边无际的天地,忘我地散游。
所以庄子说虽然身在乱世之中,但要“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2]148。不为名利诱惑,能则言,不能则去。郭庆藩注曰:“夫子向说心斋之妙,妙尽于斯。”[2]148这也正是庄子所说的“材与不材之间”。
“虚己”就是减少欲望,排除外事对自己的纠缠和困扰,这是《山木》中市南子对鲁侯的回答和劝解。
“养生”也就是养神,庄子通过庖丁解牛把人间喻为牛的筋骨盘杂,提出以有涯随无涯的人生境况,养神的方法在于“缘督以为经”[2]115,顺着牛的肌理自然而然就将其肢解了,也就是顺应自然。
“充德”则是庄子将心灵以及万物全然看作一个不容分割的整体,而不是局限于一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2]217。庄子借许多形体残缺但“德”充的人来进行说明,认为形体上残缺无材但精神完整是有材的,亦是“材与不材之间”。
庄子的“材与不材之间”与儒家中庸之道具有明确的区别。儒家中庸之道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12],也就是说,一个明确的度没有达到预期,或超过了预期都不是中庸。而庄子所说的“材与不材之间”则是代表着两个极端,有用时就尽其所用,无用时则一文不值、仿若无物。庄子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追求的是与万物天地的一体性,而不是将自己与外界对立,所以鄙弃外界的名物,以此来达到一种平衡,一种“材与不材之间”。
(三)一龙一蛇同于大道
庄子的处世思想在最后演变为:“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2]668达到这样“同于大道”的方法就是庄子在《大宗师》中所言及的“坐忘”。
什么是“坐忘”呢?在《大宗师》中颜回告诉孔子自己已“坐忘”。孔子问什么是“坐忘”,颜回是这样说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2]284孔子又言:“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2]285王建疆说:“《大宗师》通过颜回和孔子的对话,阐述从‘忘仁义’到‘忘礼乐’、直到‘坐忘’。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3]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庄子这里所谓的“忘”并非遗忘,而是“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为诚忘”[8]162。《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忘,不识也。”[14]510忘字上半部分是“亡”,下半部分则是“心”。“亡”篆书写作“亾”或“兦”,就是人在隐蔽处,故《说文》中“亡,逃也”[14]634,引申为失或死。《说文》中“心,人心。土藏也。在身之中。象形。”[14]501在古时人们认为心的功能是人意识的本源,所以由此来看“忘”字的本意是意识上隐蔽、意识上舍弃、丧失。与通常的“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庄子的“忘”是一种前往道的途径,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带有不自觉、无意识性的纯属正常生理范围内的“忘”。
总的来说,“坐忘”应该分为四个层次,即“忘外”“忘形”“忘知”和“忘我”(丧我),如果做到了这些就会达到“同于大道”的境界而走向圣人之途,逍遥于世。也就是当忘记了天下、死生、荣辱、形体、名知等,尤其是名知,这是庄子认为人间纷争乱象的根源,所以要“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2]307。能先忘外继而忘形而后忘死生,能忘死生而后能忘争竞,忘我之后见道,得道,走向逍遥无待之境。
“心斋”“以明”“虚己”“养生”“充德”和“坐忘”这些方法都是指向内部的,都是庄子认为可以借此使内心达到一种绝对的平衡,得到“虚”而忘却诸“名”“利”“知”等外在的、内在的招致祸端的根苗来摆脱社会困境及自我的生命困境。
五、“入世”的最高境界——逍遥
在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逍遥游》前言中说:“《逍遥游》篇主旨是说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8]5陈鼓应先生说的是《逍遥游》表面之意,然庄子更有深意。
(一)何为逍遥
物的小大虽然有所差别,可其“各任其性,苟当其分”是谓逍遥,此逍遥的第一层意思。但是物的逍遥是在“有待”的基础上,而圣人可以“与物冥而循大变”达到无待的逍遥,这是向子期、郭子玄释义的逍遥。
庖丁解牛有所待,“虚己”“心斋”“充德”“以明”这些“材与不材之间”的皆是有待的逍遥,而无待的逍遥则是“坐忘”之后同于大道圣人、得道之人的逍遥了。
支遁的逍遥论:“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2]1冯达文把这里的“逍遥”理解为空间和时间:“心灵的通感既不与空间也不与时间构成对待关系,不为空间与时间所限制,自是自由自在,而为‘逍遥游’。”[15]支氏打了比方来批判那些寻觅物质层面充盈的逍遥观,当物质层面的渴望实现时就会觉得无比幸福愉悦,就好比饿的人饱餐一顿,渴的人喝了一瓢水或酒,是不会忘记这些美味的肴核和佳酿的,“苟非至足,其所以逍遥哉”!所以物质上的满足是永远不可能的,故庄子所求的至足是精神上的绝对满足。《说文》中并无“逍”“遥”二字,在《庄子集释》中郭庆藩注曰:“作‘消摇’是也。”又言:“逍遥游者,篇名,义取间放不拘,怡适自得。”[2]2“消摇”我们简单地从字面上看,“消”,《说文》中“尽也”,段玉裁注曰:“未尽而将尽也。”[14]559“摇”,《说文》中“动也”[14]602。将尽而未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是为“消摇”,此亦正契合庄子所谓的“材与不材之间”和“乘道德而浮游、一龙一蛇、与时俱化”。所以“消”就是有待的逍遥,也就是“材与不材之间”;而“摇”就是无待的逍遥也就是“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由此看来,庄子说的逍遥不是一个意思,而应该是包含了两个层次。
(二)“入世”的最高境界
王夫之言:“人间世无不可逃也,而入之也难。既生于其间,则虽乱世暴君,不能逃也。”[4]34《齐物论》言:“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2]66《齐物论》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2]79在庄子的大道中死生如一,天地万物同为一个互为你我的整体,为什么还要相争相轧呢,又有什么必要呢?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来达到逍遥将永远达不到真正的逍遥,所以庄子有待的逍遥和无待的逍遥都强调精神上的满足,精神上最终的绝对满足方达到无我之境——忘我。如果世人都能明了这一点,世人都能逍遥于世,人世间就没有争的因,自然也就没有争和争的果。
既然天地为一,那么存诸于世便没有“出世”和“入世”一说,庄子面对乱世的思考转变为自己心中的诸多矛盾,所以说庄子的逍遥、所谓的“出世”,实则是庄子自己界定的入世最完美的举措——精神上得到绝对的至足。
上文提到的“消摇”之意也已说明,“消摇”是庄子对两种处世层次的总结,这是庄子全书最主要的思想和意向——“消摇入世”,所以庄子要把《逍遥游》列为全书第一篇。由此说“消摇”是庄子对自己及自己处世哲学的总结概括,是“入世”的最高境界。
六、结语
如上所述,庄子由“无用之用”演变为“材与不材之间”“一龙一蛇,与时俱化”,最终总结为“逍遥”。“逍遥”非是逍遥,而是对人间世的无奈、逃避,是庄子对其种种举措的概括,将自我完全地转入精神世界的层面,庄子也知道圣人、古之真人只不过是理想化的产物,两种逍遥的层次是庄子对于精神层面得到至足以处世自保的,并非真地教世人成为真人、圣人种种以及后世的羽化成仙、修身练道之类,庄子所谓的“得道”只不过是想让世人脱离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