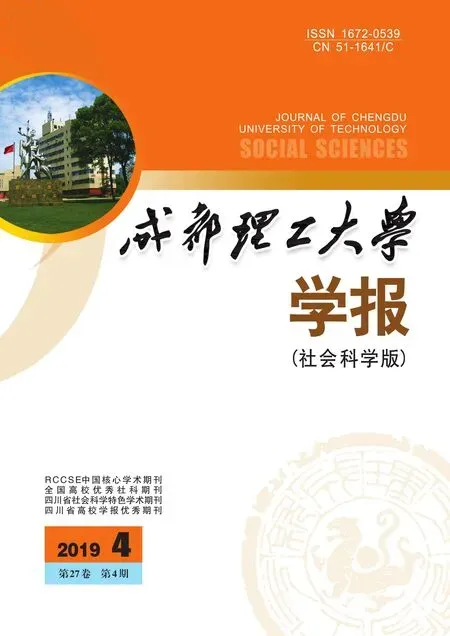《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道路时空体
2019-02-15张少娇
张少娇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一、道路时空体下的不可预测性
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给出了文学中时空体的定义,他这样说道:“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价差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1] 270“时空体”这个数学概念本是用以解释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但巴赫金视其为一个形式兼内容的文学概念,即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这就决定了文学中时空体的决定性因素是时间。在巴赫金给出的几个文学中常见的时空体里,道路时空体与余华的创作有着极为强烈的契合性,从其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便可见端倪。
巴赫金这样描述道路时空体:“道路主要是偶然邂逅的场所。在道路中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点上,有许多各色人物的空间路途和时间进程交错相遇;这里有一切阶层、身份、信仰、民族、年龄的代表。”[1]307发表于1978年第一期《北京文学》上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公认的余华成名之作。整个小说发生在一条山区公路上,这就意味着整个小说都统摄于道路时空体之下。主人公在十八岁时接过父亲递来的红色背包,兴高采烈地出门远行。命运的齿轮从他出门伊始转动,人的积极主动性让位于机遇的偶然性,同时也支配着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是道路时空体的意义之所在,它给了机遇偶然性以最大的主动权。在这条陌生的公路上,见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遭逢什么样的突变都是不可测的,无法在出门时做好任何应急预案。道路时空体在这个意义上,以一种截然的姿态打破了主人公以往生活惯有的程式,将主人公强硬地推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下去历练、体验、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这个时空体也给了读者无限的期待,除了作者,没有人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前途未知的冒险经历抓获了人们的好奇心。
这就使得主人公邂逅的司机身上具有了道路时空体的意义,司机异于常人的非正常、非逻辑的行为举止,正是在道路这个难以预测的场域中发生的,司机本身就是这个道路时空体下的一种不可预测。主人公客气礼貌甚至谄媚的笼络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但是冲司机愤怒地大吼一声,司机反而笑嘻嘻的十分友好。这种违背读者对文明礼貌一贯认知的情节只是稍作铺垫,在主人公遇到哄抢苹果的人群时,这种不可预测性达到了高潮。主人公和司机因为汽车的抛锚而困在了公路上,这时候遇到了一些骑自行车的人,他们非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而是集结了一伙人肆无忌惮地进行了一次抢劫。这个情节的出人意料正是道路时空体不可预测性体现。
当年,李陀在拿到《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作品时曾评价道:“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2]余华说:“李陀的这句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并是他越写胆子越大。”[3]50所以,当余华在此后的作品中使用道路时空体时,就更加娴熟、大胆地对这种不可预测性进行了运用。《古典爱情》一篇中,就能看到这种不可预测性的放大乃至变异。这是一个嵌套在才子佳人小说模子里的故事,柳生在一条黄色大道上赶路赴考,邂逅了贵族小姐惠,两厢生情,继而缱绻话别,落榜归来,佳人不在。余华大胆地给这个传统的模式以一个转折,柳生再踏上黄色大道是荒年时际,他遭逢的菜人市场就将这个悲剧上升到了人性的质问境地,柳生沿着阳间的路走向的却像是阴间的修罗场。在这里,男人卖掉了妻子女儿,屠户活生生地肢解幼童,商人品尝人肉只关注新鲜与否。在道路时空体下,柳生不能预测自己在这条道路上接着走下去会遇到什么,未知让他战栗、恐惧。
余华向来不惮书写暴力和血腥,道路时空体给了他这种创作的自由。路上的风景都是陌生的,未知的环境里藏着的是机遇还是陷阱、是鲜花还是利刃、是善意还是恶语,一切都未可知。甚至在迈出下一步时的心情应该是满怀期待还是惴惴不安都是不可知的。没有尽头的道路就像一个没有尽头的陈列台一样,展示着余华深切体悟到的生活和生命中无尽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道路又是一个命运的集散地,不同命运的人在此时此地相遇,彼此间的命运开始有了纠缠。在余华的道路时空体里,不可测成为了常态,没有定量,一切都是变量,一切都不可预测。
二、道路时空体下的人物形象
巴赫金认为,时空体不是仅仅在讨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作为形式兼内容的范畴,时空体还决定着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时空化了的。”[1]291这就是说,文学时空体会对人物形象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说是限制。采用什么样的时空体相对应会使人物发展出什么样的人物性格、生长轨迹、生长环境乃至人物命运。
而置身于道路时空体下的人物又往往带着强烈的成长色彩,这与道路时空体的不可预测性交相辉映,形成了独属于道路时空体的双重内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主人公“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回家了”[4]1,接着就背起父亲递过来的红书包兴高采烈地踏上未知的道路,甚至在最开始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处。从家里出发时的主人公俨然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稚气、率真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正因为他具有的这些少年人的特质使得他在踏上未知道路时满怀憧憬、毫不畏惧,也正因为如此他在遇到怪异的司机和哄抢苹果的人群时表现的那么冲动而正气凛然。十八岁似乎是一个门槛,门的这边是儿童世界,门的那一边就是成人世界,一旦越过十八岁这个门槛,就无可争辩、无法回头地走向成熟。余华让十八岁的主人公在这条道路上完成自己的成人礼,道路在这里有这一种仪式性的隐喻。
实质上,道路的不可预测性起着将这个世界浓缩的作用,整个世界的偶然性被等比例缩小放置在未知的路途上。初出茅庐的少年不谙世事,用自己稚嫩的三观应对这条道路上发生的一切,换言之,少年是在用自己天真的儿童经验抗击整个世界。而在遍体鳞伤之后的少年还能不能像初出家门时那样的勇敢天真,这个答案可能是不言而喻的。那个怪异的司机和那些参与哄抢的人来自成人世界,他们都是经过“道路化”的,少年与他们的遭遇,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一次交锋,也是“未道路化”和“道路化”两种性格的一次碰撞,何者胜的结果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将主人公初次出门远行所走的道路的现实意义,不知不觉地升华成了隐喻意义。道路在这里不仅仅是小说情节开展的一个地点,更是一种少年成长之路的隐喻。
余华对这种少年成长之路的思考是很深入的,在他的另一个名篇《鲜血梅花》中也表现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没有半点武艺的阮海阔,肩背着名扬天下的梅华剑,去寻找十五年前的杀父仇人。”[4]21阮海阔在二十岁的时候才了解自己父亲死亡的真相,才知道父亲曾经扬名的那个场域——江湖。前二十年的生活里,江湖和他的人生没有瓜葛。突如其来的江湖这个陌生的世界,在阮海阔来说就是那条在前面虚无的延伸着的大道,不知道这条大道通向何处,也不知道这条大道的岔路怎么选择。茫然的少年在离开家时,母亲用自焚的方式逼他上路,从此少年就开始了自己的成长之路。
道路时空体下远行的少年们是在一个极为仓促的节点迈向了大道,他们此前对道路毫无预知、毫无准备,仿佛命运之手在那一刻猛地推了他们一把一样。从踏上大道的那一刻开始就必须迅猛地成长起来,整个世界的世事人情都暴风骤雨般的席来,劈头盖脸的砸向了那些稚气未脱的少年,他们应接不暇甚至疲于应对。少年们在仓皇中不断在大道上向前走,这个大道也就是他们的人生大道,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在夯实自己的人生根基,遇到的人或事,都一次又一次地重塑他们的人生,他们被一次一次地击碎,再重新粘合,愈来愈坚强。
在余华的道路时空体里,少年出发的地点是家,家作为这个道路时空体中的起点是一个固定的位置,而道路则呈现出了一种绵延性、开放性、无尽性。余华给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留下了家,但是一把火烧掉了阮海阔的家,当他“越写胆子越大”以后,他消解了回家的可能,这就让少年们处于一种不停成长的状态,他们会不会被“道路化”成那些遇见的路人?这就是余华的道路时空体下对少年形象的思考与追问。少年们在出门时纯白如纸,在道路上被一笔一划地涂抹,渐渐成长起来。基于远行对人生的意义,道路时空体规约着其中人物形象的成长,人物也因为在道路上而不断地获得锤炼,展现着成长的层次与丰富。
三、道路时空体的荒诞指向
在道路时空体里,依靠道路的独特性使文本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因为这种独特性而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去解构这个世界的深层意义。踏上道路的那一点是起点,从起点开始,前面就有无数的岔路,每一条岔路就是一种可能性,未来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无数种可能性。与此同时,道路唯一终点的意义就被消解了。道路的无尽就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能指,让人生之路、成长之路的意义附丽其上。余华用这种道路时空体特性来构建自己人生本来荒诞的命题,给其笔下的道路时空体赋予了一层新的哲学意义。
《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少年遇见的司机和哄抢苹果的人群,不难看出是人性本恶的一种具象化。司机的欺软怕硬和虚与委蛇,甚至司机在面对降临于自己身上的不幸时流露出看客般的冷漠,但在面对他人的不幸时却不吝加重他人的不幸。同时,主人公也在面对哄抢苹果的人时直面了人性的贪婪和暴力,群体性的暴力会让理智丧失,激起更深程度的暴力。他用遍体鳞伤和鲜血横流为人生的第一课交了学费。面对不幸和暴力时,主人公用文明人的理智来应对,义愤填膺、满腔正义、义正辞严甚至不惜只身与之抗衡,而实际上,理智才是可笑的少数派。这个世界教给人们应该遵循的生存法则本身就是无序的、荒诞的。荒诞才是人生的常态。
最后蜷缩在同他一样遍体鳞伤的汽车座椅上时,“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出门时主人公心里惦记的,就是找一个旅店和搭一辆车,这种希冀实际上是主人公自己对于安定下来的一种向往。初出家门的少年本能地对漂泊有着恐惧,他希望通过找寻安定的场所来存放自己不安定的心灵。现在他躺在车里,发觉这就是旅店。此时找寻的意义就被消解了,找寻骤然变成了无意义的行为,这个黑色幽默笔法的运用,体现了余华希望在道路时空体下展示的一种荒诞性。
余华意识到了道路时空体巨大的包容性和极强的指向性,基于此,他用更深的笔力写下了他认识的社会和世界,这就是《第七天》。这本颇具争议性的小说可谓是余华道路时空体的集大成之作,他别具匠心地选择了“黄泉之路”这个特殊的道路时空体作载体,陈列的却是人世间的世情百态。余华安排杨飞这个亡灵去找寻自己火化的这条路来讲述这个故事,黄泉之路是人的最后一程,这个陌生化的道路时空体就指向人生荒诞的终极命题。
在这个道路时空体下,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生的延续,一种生的变相的开端。“安息之地”依然延续着生的世界里森严的等级秩序,有钱的亡灵坐在贵宾候烧区的沙发上攀比着考究的寿衣和昂贵的墓地,没钱的亡灵坐在普通候烧区的塑料椅子上比较着谁的骨灰盒更实惠。但是他们都在市长的遗体告别仪式前哑然无声。杨飞看到“金钱在权力面前自惭形秽”[5]14。这种现实世界里的潜规则放置在道路时空体之下就显得颇为荒诞,这是连死亡都不能平等的荒诞性。
巴赫金认为道路时空体“揭示和展现的,是这个祖国的社会历史的多样性”[1]308。余华对于道路时空体的这种特性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黄泉之路道路时空体体现出了它自身的独异性和陌生化。他让杨飞作为一个原点,在寻找火化的这条路上不断遇见生前听闻过的人,通过这些人生前的惨死来加重这种荒诞性。无论是被强拆致死的郑小梅夫妇,还是因为发现死婴而莫名遭遇车祸的李月珍,还有为给自己女朋友鼠妹买一块墓地而去卖肾的伍超,等等。这些人在生前被生活逼到了死角,继而没有留一线喘息之机就被碾压成粉,他们的死亡许是昙花一现的爆炸性新闻,许就没有只言片语不被人记忆。在这个道路时空体里,所见的不是刻意的猎奇,而是现实生活的日常。以死写生,死亡拉开了人们与熟悉生活的距离,站在生活的另一侧才发现日常生活原来如此荒诞。
黄泉之路道路时空的独异性和陌生化,也在一定意义上赋予了道路时空体新的内蕴,即强烈的讽刺性和对比性。《第七天》里,余华构建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乌托邦,这是一个“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5]126。的世界,这里聚集着无法去往安息之地的亡灵,这些亡灵都很平和友善。死亡在最大程度上的诗意化,正是对现实世界的无情嘲讽,这种刺骨的对比性直指道路时空体的荒诞性。矛盾和悖论也就再次交织在一起,深层的荒诞意义浮现。权力凌驾于金钱,金钱凌驾于秩序,道德被踩在脚底是这个时代下的人难以摆脱的宿命,无论用多大程度的努力都无法挣脱,甚至连死亡都无法摆脱。这条黄泉之路正是整个当前社会的缩影,它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隐喻。这是余华的匠心,也是道路时空体独异的魅力。
道路时空体的指向,正是现实无序、人生荒诞的终极价值指向,也是因为余华贴近现实,才会有道路时空体这种荒芜的呈现。“现实中人性的残缺在文学审美中得到了修复,现实中心灵的扭曲在文学审美中得到了匡正,现实中的麻木与冷漠在文学审美中得以复苏和温暖。”[6]90这也许就是道路时空体之于余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