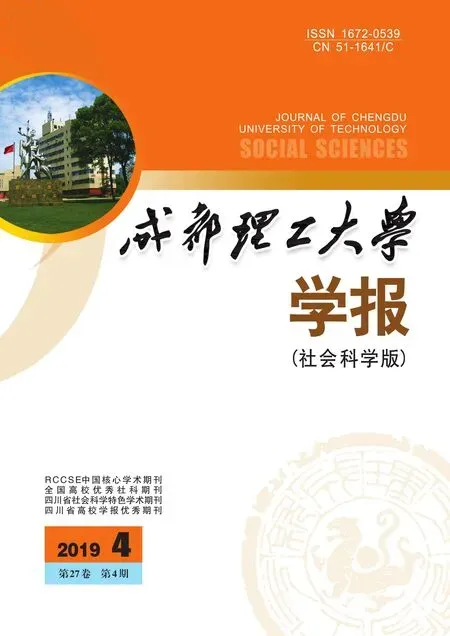哲学与科学的联盟何以可能?
——析路易·阿尔都塞的“联盟”思想
2019-02-15赵睿夫
赵睿夫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631)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联盟”思想,出自其转型时期的重要著作《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年)。具体而言,“联盟”思想包括四重内涵,即阿尔都塞对哲学的新认知;阿尔都塞对科学的新认知;阿尔都塞对哲学、科学、意识形态三者关系的判明;哲学与科学联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联盟”是阿尔都塞对于彼时社会中存在的“跨学科”口号批判的产物,是其意识形态批判在理论境域中的显现。“哲学与科学的联盟何以可能”的问题症候构成了阿尔都塞思想中承上启下的枢纽,要了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与“科学哲学”的独特性,就必须从“联盟”的问题角度进行切入。总体而言,“联盟”思想承续了康德的界限精神与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特质,喻示着哲学与科学摆脱意识形态牵制,走向相互指引、各司其职、各维其位、互不侵犯的理想存在状态。在阿尔都塞的语境下,实现“联盟”的关键枢纽即通过“唯物主义”同时改造哲学与科学:通过“唯物主义”的哲学建构,科学中自发的泛灵论与机械论部分同现实世界相调解,而哲学亦能摆脱科学意识形态的“盘剥利用”。总而言之,“联盟”是一种抗拒垄断性还原的知识体系状态,其所反对的对象即僭越边界的“跨学科”意识形态侵袭,它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的“科学的科学哲学”,是阿尔都塞对现代社会中科学精神与哲学思辨二元归属的最终解释。
一、“联盟”的提出:阿尔都塞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向
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阿尔都塞通常以其“对马克思科学精神的保卫”“对唯物史观的结构性补充”与“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批判”闻名。实际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之外的阿尔都塞哲学,我们的认识是不足的。阿尔都塞有着复杂的思想谱系:首先,阿尔都塞深受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开辟的思辨哲学路向影响;其次,亨利·柏格森、雅克·拉康、乔治·康吉莱姆、吉尔·德勒兹等具有浓厚法国“非定”传统的哲学家为他的主体认识提供了启发;再次,他在巴黎高师的导师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与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等人又使阿尔都塞得到了科学主义的熏陶;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使得阿尔都塞寻找到了“唯一能让我们摆脱混乱”[1]194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路径。总之,阿尔都塞的思想具备四重特质,即思辨哲学的意识性、法国哲学的主体性、科学哲学的体系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
正如张一兵先生指出的那样:“阿尔都塞认为,由于问题式是一种隐性的理论构架,要把它从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深处和文本中挖掘出来,一般的研究和阅读法是绝对无效的,唯一的通道只能是‘症候阅读法’。”[2]63以挖掘问题为中心的症候阅读是阿尔都塞文本诠释学的中心概念,那么以此方法论反推其自身,阿尔都塞哲学的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广泛存在于其哲学思想中的最为普遍的问题内核即“哲学与科学的联盟何以可能”,依据有三:首先,不同于以往的实证主义与结构主义,阿尔都塞反对科学方法论对哲学的渗透,主张哲学与科学的相互独立,认为“哲学不是一门科学,更不是大写的科学;他既不是关于科学危机的科学,也不是关于整体的科学”[3]16。其次,阿尔都塞试图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试图排除意识形态对科学与哲学的双重干预,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社会主义’是个科学的概念,而人道主义则仅仅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4]192。最后,阿尔都塞曾在其1967年的《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一文中明确提出哲学与科学的联盟问题,号召哲学与科学的联合,呼唤哲学与科学“加入这个联盟”[3]98。足可见,“联盟”问题贯彻了阿尔都塞思想的始终,从早期的科学崇拜到后来的科学理性再到晚期的“划界成盟”,阿尔都塞一直所竭力论述的,实际上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具体关系问题,因此,对“联盟”问题的思考是管窥阿尔都塞思想全貌的必由之路。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下简称《自发哲学》)是阿尔都塞对“联盟”问题集中阐述的关键文献,包含了阿尔都塞的哲学观、实践意识形态批判、跨学科批判、“联盟”思想等方面内容。这部论文的前身是阿尔都塞1967年所作的“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系列讲座的讲义,其写作出发点主要是对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雅克·莫诺在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的回应,后经其学生皮埃尔·马歇雷(Pierre Macherey)、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等人协助整理完善后以法语出版。客观而论,《自发哲学》是阿尔都塞著作中的一个异数。不同于其《保卫马克思》《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列宁与哲学》等著作强烈的政治批判与现实观照,《自发哲学》是阿尔都塞“实验思维”的产物,从课程讲述、结构设计到后续的影响分析,他将哲学与科学这两个纠缠交迭的学科领域置于其“观测台”上,并完全以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身份进行“实验记录”。因此,《自发哲学》一文的表述方法显得更为逻辑化、结构化、条目化。总而言之,《自发哲学》中的思想仍存有大量可探讨空间,本文对于阿尔都塞的“联盟”思想探析,也将从此文本展开。
《导读阿尔都塞》的作者卢克·费雷特(Luke Ferretter)将阿尔都塞的思想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1945—1951的早期著作阶段”“1960—1966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阶段”“1967—1975的自我批评转向阶段”“1976—1978的马克思主义危机阶段”“1982—1988的相遇的唯物主义阶段”。作为开启了阿尔都塞思想转向的重要著作,《自发哲学》标志着阿尔都塞开始从前期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向对哲学、科学、意识形态三个向度的反思。有关阿尔都塞思想转向的原因是复杂的:1967年,阿尔都塞主持了“为科学家所讲的哲学课”,开始介入法国科学界;1968年的“五月风暴”事件让他的身体状况快速恶化;及至1968年秋,阿尔都塞的学生阿兰·巴迪欧与他决裂,致使他对于法国阶级斗争的研究遭受重创;随后,由于精神问题的困扰,他在公开场合对莫里斯·梅洛·庞蒂大加谤蔑,个人声望再次滑坡……总之,由于个人发展的变向、阶级斗争研究小组的解散、学界名誉的滑坡,阿尔都塞开始进入了自我批评与理论反思阶段。《自发哲学》中提出的“联盟”思想,其实正是阿尔都塞整个瓶颈期学术渴望的集中体现——他迫切地试图重构自己的哲学观与科学观,从而获得科学界对他哲学成果的认可,并反驳甚嚣尘上的“跨学科”口号。“联盟”问题的提出,标志着阿尔都塞思想向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复归,同时,也正是此时学科讨论中对于唯物主义的再思考,为其后期“相遇的唯物主义”埋下了伏笔。因此,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它们‘开启了’我们研究哲学一般,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转折点。”[3]5将“联盟”思想视作阿尔都塞思想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是毫不过分的。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阿尔都塞思想中“联盟”问题的讨论尚不充分。《自发哲学》中所阐释的哲学观与科学观,乃至在文末发表的对“联盟”可能性的看法,都显示出了一个更为“哲学”化的阿尔都塞。与普遍认知中的斯宾诺莎式、康吉莱姆式的阿尔都塞不同,这个阿尔都塞更像康德。因此,要完善阿尔都塞的思想肖像,绝不能仅将之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块拼图,唯有清晰审视其哲学观、科学观乃至“联盟”思想,我们才能明晰这位思想巨匠真正的内在逻辑。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场域之中,关于跨学科、合并学科、创新研究方法的讨论层出不穷,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愈发处在暧昧状态之中。在此背景下,重读阿尔都塞的“联盟”思想,无疑能为我们提供更富洞见性的时代启示。
二、“联盟”的论证:阿尔都塞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阐释
如果说“多元决定”与“矛盾”范畴是贯穿《保卫马克思》的核心线索、“询唤”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中心概念的话,那么《自发哲学》的行文思路便是由意识形态、哲学、科学三个范畴构成的。在文章开篇,阿尔都塞即清晰地阐述了自身的哲学观:“哲学没有任何对象,只有赌注(enjeu);哲学不生产知识,只陈述论点,等等。针对科学与政治实践的种种难题,它的论点开辟了通向正确立场的道路,等等。”[3]5对阿尔都塞的思维历程有所了解者都可发现,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著作中,阿尔都塞都将哲学描述为“理论实践的理论”,着重强调其实践性与对象性,然而,在《自发哲学》一书中,阿尔都塞的哲学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他开始转向思考哲学与科学的界限与调和,试图跃出科学主义阴影下的藩篱。即是说,从这本著作开始,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发生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嬗变:哲学开始作为纯论点出现,理论与实践、真实与正确、科学与哲学开始发生分离,但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又试图维系这些范畴间的必要联系,因此,阿尔都塞所要构造的解决问题的体系便诞生了——即在文章末尾所言的“哲学与科学的联盟”。下面,让我们回归文本,厘清阿尔都塞在《自发哲学》中的思想脉络。
(一)阿尔都塞的哲学观
在《自发哲学》中,阿尔都塞首先明确了自己的哲学观:哲学将不再具有实质的对象与内容,成为了完全的论点提供装置,除了思维创见、理论预测、界限划定等抽象性的功能之外,哲学不再具有任何现实的、内容性的意义。此外,阿尔都塞重新明确了这两个命题下“哲学实践”的具体含义:“哲学命题总具有生产‘批判性’区分的作用:就是说,它们对各种观念加以‘分拣’和分离,它们甚至锻造出合用的观念,以便使观念的分离及其必然性显而易见……哲学的实践就在于进行这样的划分、区分、划清界限。”[3]8可见,阿尔都塞语境中的“哲学实践”已经不再与现实要素发生关联性,这个意义上的实践是完全“辨析”性的,是对可感与可知、物质与精神、真理与谬误、此岸与彼岸等矛盾范畴的划界。阿尔都塞强调哲学完全纯粹的无对象性与无内容性,因为只有如此,哲学的正误才不具有现实意义上的价值判准。总体而言,阿尔都塞对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可概括为两点:第一,哲学是与科学完全不同的学科;第二,必须揭示哲学与科学的差异,并为之辩护,因为这种辩护本身即“哲学实践”的实现,是哲学家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义务。
(二)阿尔都塞的跨学科批判
在阐明自身基础性的哲学观后,阿尔都塞开始为哲学的特质作出更迂回的补充。他将“哲学没有对象”和“哲学有哲学内在对象”,“哲学没有对错”和“哲学永不犯错”两组矛盾判断并置,目的是为了揭示出哲学发生作用的重要主体因素——“我思”的存在。这种表达显然是受拉康影响的——主体的存续状态被不断变动的大他者所影响,尽管存在悖谬,但却更进一步地表明了哲学的“空中楼阁”性质。
跨学科批判是阿尔都塞联盟思想的另一个理论根基,它尖锐地批判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存在于法国社会科学界的“跨学科”口号。首先要明确的是,这里的“跨学科”并非当代意义下的学科交互与知识创新,它是阿尔都塞用以讽刺学科间盲目同化、科学主义包办一切知识、哲学家过分介入现实等思想病症的反语。阿尔都塞指出,当代知识界面临着三重难题,即“学科内部自身的难题”“学科关系中的难题”与“跨学科产生的新学科的难题”,而“跨学科”作为一种“为创新而创新”的社会风潮,使得大量哲学与文科学者也开始走向“科学化”,但在阿尔都塞看来,哲学未必能与科学形成有效的跨学科,换言之,不同学科通过科学方法的“同化”,是无法实现的。哲学与科学问题路径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哲学对于科学而言是无意义的,正如他所言:“但因为哲学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整体的科学,所以它并没有给那些难题提供解决办法。它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干预:它陈述观点,而这些观点有助于开辟通向关于那些难题的正确立场的道路。”[3]16
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在本阶段的论述中已经初步阐释了《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年)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他将“跨学科”视作一种“意识形态神话”,认为盲动性的跨学科背后潜藏着科学主义对哲学的侵蚀与哲学家对学科界限的漠视。哲学的“整体性”使得哲学学者们拥有了僭越学科差异的盲目性,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哲学家就是要关心与科学实践的难题、知识生产过程的难题、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难题、所有这些难题之间关系的难题本身不无关系的那些问题。他是否有权关心他们,那是一个问题:他就是这样。”[3]16总之,一方面,阿尔都塞预见到了科学发展对哲学研究方式的裹挟,即海德格尔所谓的技术性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工具理性批判;另一方面,阿尔都塞也重新审视了哲学自身存在的问题:太过于相信自身的整体性而忽略与实证科学的根本差异,将干预视作责任,将一切问题包揽上身。这两种意识形态逆流——即“泛科学的意识形态”与“泛哲学的意识形态”——是“跨学科”这一口号的真正本质,必须对其予以坚决地批判与克服。
(三)阿尔都塞对哲学、科学与意识形态三者的关系判明
由于《自发哲学》一文原初是阿尔都塞“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的讲义,因此其着力解释哲学的方法论特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阿尔都塞看来,哲学“为科学的正确性保留了某种可能”,尽管哲学不能切实干预一切现实问题,但哲学的的确确有其自身的作用模式,这种作用模式较之于科学方法的直观性、计量性、实证性、数字理性,无疑是更为不可视的。概括而言,哲学与科学不仅在定义、对象、内容上有差异,在其方法范式上也存在不同,哲学的范畴只能形成哲学方法用以解决哲学的问题,而科学的效用逻辑也有其独特的运作方式,此即阿尔都塞对哲学与科学各自尊严的进一步保留。
承继了上一阶段跨学科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思路,阿尔都塞开始明确地阐述其意识形态理论与哲学、科学的关系。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明确定义为:“一个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向、神话、观念、概念)体系,他在既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5]231依据俞吾金先生的研究,阿尔都塞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实践性、神话性、强制性、阶级性”五重意涵[6]286-288,这一表征在本阶段内得到了初步的建构。在阿尔都塞的理解中,意识形态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厘清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必要中介,他强调:“此前我们看到有两个角色:哲学和科学……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是什么把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区别了开来?”[3]19显然,阿尔都塞将科学、哲学、意识形态三者视作截然不同的事物,如果盲动的“跨学科”口号仍不能停止,科学与哲学将不能免于意识形态的牵制。在这种理论困境中,哲学的现实价值就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即为意识形态与科学划定界限。与意识形态的实践不同,哲学的实践并不要求社会的认同或曰对规则的顺应,依阿尔都塞之见,哲学是自我实践的,这种实践通过产生论题、划定界限完成,并不断提供着科学发展的可能性,此即哲学对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划分作用。
(四)阿尔都塞在PSS(1)问题视域之下哲学与科学联盟的可能性
联盟的可能性问题是阿尔都塞整个《自发哲学》核心思想的体现,一言以蔽之,即阿尔都塞所言的“在每个科学家内心,都蛰伏着一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一有机会就会醒来”[3]57。“PSS”是阿尔都塞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孕育在科学家潜意识中的哲学动因。在阿尔都塞看来,没有纯粹的科学工作者,只有孕育着哲学思想的科学实践者。为清晰解释这个乍闻之下使科学家们难以接受的命题,阿尔都塞列举了科学危机(即胡塞尔意义上的“科学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路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7]13)发生时的三类科学家的应对态度:第一种科学家,即“顽固的科学信仰者”,无论科学基础遭到如何的危机,他们总是相信这只是科学发展的插曲,宗教、艺术、信仰等都无法从根本性上动摇科学;第二种科学家,即“极端的科学背弃者”,他们在唯灵论的冲击下放弃了科学的整个原则,并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为面貌一新的哲学家,但却并未真正从事哲学的工作,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对哲学的盘剥利用”[3]56,以简单的神秘主义否定了科学的价值;第三种科学家,即“居间的科学哲学者”,他们是前两股极端因素的居间态,是保持有科学精神与认识到自身哲学思维存在的具有“科学哲学实践能力”的科学家,在阿尔都塞看来,只有这一类清醒的科学家能够真正实现哲学与科学的和谐统一,将科学家的自发哲学转变为具备了鲜明洞见力的科学哲学,从而真正度过科学危机。
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有谁比科学家本人更适合谈论科学及其实践呢?那便是由科学家所造就的科学的科学哲学。”[3]59阿尔都塞所言的“科学的科学哲学”,即对PSS与科学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富有科学精神、却又不对哲学形成侵蚀的科学哲学。而在最终的对“联盟可能性”的论证环节上,阿尔都塞清晰地指明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关键作用——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使得PSS中自发的泛灵论与机械论被驱除;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取消了哲学中受意识形态钳制的“护教”部分,在唯物主义的纽带作用之下,联盟最终得以成为可能。
至此,阿尔都塞“联盟”的可能性逻辑被彻底阐明:从对哲学与科学分别性质的表述,到对跨学科意识形态的深入批判;从对学科界限不容僭越的申明,到对哲学“划界人”身份的集中表述;从对科学危机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探讨,到PSS语境下唯物主义哲学对联盟的重要作用……无疑,阿尔都塞的联盟思想在其《自发哲学》中清晰呈现。
三、“联盟”的溯源:从康德、马克思到阿尔都塞
事实上,阿尔都塞的“联盟”思想最直接的来源是康德哲学。作为一种试图调和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复合哲学,康德哲学承继了卢梭与休谟的问题之路,开始思考科学知识对人的现实尊严性的影响。在康德哲学的语境中,“知识,尤其科学知识,不是人类的一切,不是人类价值和尊严的最高体现;人类根本的权利并非只是对知识的追求,更有追求‘善’的权利”[8]52。康德全新知识学所带来的哥白尼革命让后世的相当一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到形而上学的不可或缺性,这种由外部转向内部的科学主义再思考构成了整个近现代哲学里程碑式的中心精神。一如齐良骥先生所言:“批判哲学的两大任务,一是用哲学论证科学,保卫科学,一是建立科学的哲学或形而上学,保卫自由。”[9]35康德费尽心思的理念溯源、范畴建构、统觉与“统觉之统觉”的推演,无非是力图展现出哲学与科学的非对抗性——这一点在休谟与卢梭处已经做了良久的讨论——并剔除龋坏的哲学或科学一元论、形成科学与哲学的并置同行。康德曾言:“所以道德学说和自然学说都可以各自维持其地位……我因此就得扬弃知识,以便替信仰留有余地。”[10]25这种各维其位、各司其职、各有余地、相互萃取的科学与哲学状态,构成了阿尔都塞“联盟”问题的雏形。
概括而言,阿尔都塞“联盟”思想对康德哲学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即对科学冲击的深刻认识。阿尔都塞在《自发哲学》中分别描述了“哲学对科学”“科学对哲学”两种“盘剥利用”的形式。所谓哲学对科学的盘剥利用,即哲学利用科学来达成“护教”的目的,以科学实践所产生的成果拱卫“实践的意识形态的价值”[3]67,换而言之,即是哲学通过科学发展的危机、科学实践的难题来维护自身泛灵论的部分。而所谓科学对哲学的盘剥利用,则是指现代科学的总体颠覆性。一如海德格尔“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11]885的技术化批判,阿尔都塞认为现代社会的科学主义正在试图“破坏整体性”,这种科学意识形态正在反过来作用于人自身,并力图消灭人的洞见与创想能力——或言之曰哲学。与康德不同的是,阿尔都塞不仅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冲击,还认识到了哲学对科学技术的利用与意识形态浸润下社会病症的形成。因此,在对科技危机的认识上,阿尔都塞具有更为全面的认知。
第二,即对主体精神的充分论证。尽管在阿尔都塞的哲学范畴内,“主体”并非是一个意味着自由与独立的存在,相反,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揭示出“体制、仪式、实践、言语行为”的主体询唤链条[12]38,瓦解了现代社会独立主体的迷梦。但在“联盟”思想的意义上,阿尔都塞仍然延续了康德哲学所开创的那种“我思”的有限度性的主体精神——一如物自体的不可知但可实践,阿尔都塞的哲学不与现实相关但却具有现实干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阿尔都塞对哲学功能的界定——即前文所言的“划界”——是对康德哲学主体精神最大的致敬:在肯定哲学理性的经验无涉的同时,阿尔都塞也间接承认理念存在的必要价值,其哲学所提供的非经验性的论点仍然为科学实践与自然改造提供了可能性范本。足可见,阿尔都塞在《自发哲学》中表述的主体精神尚非拉康式的虚假独立主体,相反,他已经通过对哲学功能与科学实践的阐述完成了对康德哲学的补充。
第三,即对界限精神的强烈呼唤。界限精神从启蒙运动开始就一直是西方哲学探讨的重要问题,从卢梭所言的“我自谓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忠诚对于善人要比博学对于学者更可贵得多”[13]5到霍克海默、阿多诺指出的“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它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14]2,西方哲学的界限精神一直在逼问科学与哲学、道德与技术、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边界与尺度。此即阿尔都塞视角下“联盟”形成的必要性。如果说康德的界限精神是启蒙长夜中打破黑夜的星火,那么阿尔都塞的界限精神便是在技术理性批判大潮中冷眼静观的烛光——康德使人们意识到科学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而阿尔都塞则让人们明白,不仅是科学,即便哲学本身,也不能成为那个主宰一切的上帝,唯有实现“联盟”,才是实现康德、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海德格尔等人哲学诉求的终极路径。
阿尔都塞在《自发哲学》的末尾清晰地描绘了“联盟”的现实图景:“科学家什么时候得到过这样一种联盟呢?它确实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它尊重科学自身的领域;因为它请求哲学的帮助,只是为了去干预那种对科学进行盘剥利用的哲学;因为它没有许诺什么奇迹,而是号召进行一场自觉的斗争,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因为,与其说它在谈论一种完成、完善了的哲学所进行的干预,还不如说它在告诫着我们:哲学本身就是通过干预才建立起来的。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这样的哲学,它提供服务的方式是如此的谦逊?”[3]98
对于这段充满浪漫色彩的描述,我们很难不联想到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经典描述[15]297,实质上,阿尔都塞的“哲学与科学的联盟”,从本质上包含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因子。类比马克思而言,阿尔都塞所追寻的“联盟”状态将是如此的:在联盟中,作为完成了的哲学=科学=科学哲学,那是一种非拒斥性或者非相互消灭的和谐统一,是各类知识自然而然地为人类文明演进而服务的思想联盟。在联盟的状态下,科学不再试图消灭哲学的思辨性,哲学也不再试图强行介入经验现实——此即阿尔都塞联盟的本质,一种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哲学继承。
对比青年马克思呼唤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同盟,阿尔都塞的“哲学”与“科学”的联盟更偏重理论性而非现实性。尽管他并无马克思那般崇高的历史寓意,但其哲学思想的结构必然包含马克思总体性辩证法的灵髓。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16]105尽管阿尔都塞强调他的出发点是唯物主义哲学,但其“联盟”所要反对的那部分错误的哲学并非广义上的唯心主义,而是“独断论”与“泛灵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之所以与列维-斯特劳斯、索绪尔、乔姆斯基不同,是因为在阿尔都塞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之外,还包含一个对总体性与多元性的召唤,即其“有机理性”。潘志新认为:“在阿尔都塞那里,物质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决定与超决定、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处的一种模糊的、混沌的‘即此即彼’或‘非此非彼’的状态,就是‘有机理性’。”[17]1这种有机理性同马克思的总体精神发生了深刻的思想的交互——此亦阿尔都塞着力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多元辩护的思想导因。
在《列宁与哲学》(1971年)中,阿尔都塞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哲学诞生于柏拉图的数学大陆,后由笛卡尔的物理大陆所改造。今天,他正在被马克思的历史大陆引入一场开放性的革命。我们称这场革命为‘辩证唯物主义’。”[18]4马、恩所开辟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路径,无疑是阿尔都塞“联盟”思想的重要基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使得阿尔都塞认识到科学与哲学形成联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亦使得阿尔都塞开始关注哲学的划界功能与实践意识形态的影响。总而言之,阿尔都塞的“联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历史性、辩证性的综合反映,亦是共产主义理想在理论场域中的生动显现。
用雅克·德里达在阿尔都塞葬礼上的一段发言作结:“终结的东西,路易带走的东西,不只是我们在这样那样的时刻将会分享的这里或那里的这样那样的事物,它就是世界本身,是某个世界的开端——当然是他的世界,但也是我在其中生活过的世界,是我们在其中经历过独一无二故事的世界,这个世界无论如何是无法补偿的。”[3]509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之一,德里达的话语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阿尔都塞所构建出的思想世界,或许不是一个臻于完美、能免于一切批评的世界,但其中蕴涵的独特的“开端”价值,是我们必须去认识与感知的。“哲学与科学的联盟”或许难免流于乌托邦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萃取跨时代的力量——在阿尔都塞诞辰百年之际的当代,对于阿尔都塞的思想遗产,我们能做的、需要去做的,还有很多。
注释:
(1)PSS为阿尔都塞对“科学家的自发哲学”的简称,他试图使这个概念成为一个专有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