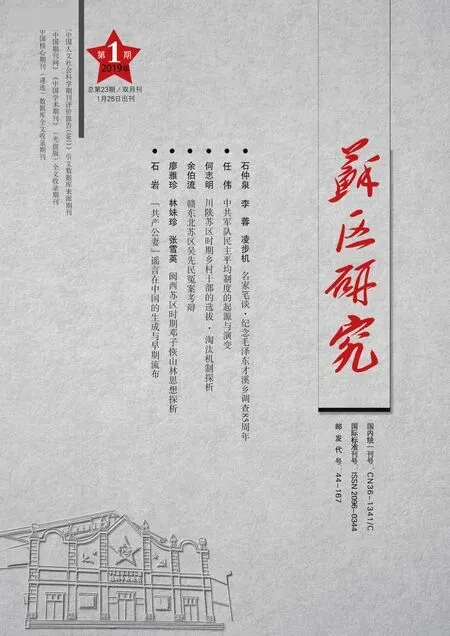中共军队民主平均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2019-02-14
提要:提及红军,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民主与平等。不可否认,草创时期,红军的确有过比较理想的实践,但那一过程极为短暂。随着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革命队伍被重新结构化、等级化,军官与士兵的物质生活也因而出现差距。虽然中共在制度上一直倡导平等,但是随着官僚制度日益成熟,居于上端的革命者无疑更容易摄取资源。虽然中共党人的理想与奋斗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平均主义的实践——尤其是相较于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的贫富分化并不算严重,但是从制度与历史趋势上看,平均主义走向破灭实属必然。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讲,“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所谓“军内民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物质分配上,官兵待遇平等;第二,在权力关系上,“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有民主讨论的空间。[注]《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虽然现存研究对红军的这两个特点已多有关注,但仍有可论述的空间。[注]于潇:《论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建强:《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
首先,既存论述往往止于表面现象罗列,未能深入分析民主制度的成因。按常理说,军队中最应讲究等级秩序,最不应实行民主。中共反其道而行之,是何道理?其次,既存研究过于重视文本条例,没有深入到实践层面一探究竟。红军草创时期,自由民主的气氛浓郁,但若把时间段稍稍拉长,就不难发现,红军集权趋势很明显。这既与中共的革命体制有关,也是战争的内在要求。
与民主类似,平均主义也有一个限度问题。随着革命政权趋于稳定,层级化的官僚体制逐步成熟,“平均主义”在多大层面上发生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现存研究多注重阐发“民主”与“平均”的正面作用,较为忽视其局限和消极影响。其实,就战争而言,民主未必是好的选择。研究者对那些耳熟能详的制度,也许应该保持某种必要的反思。
军队中的民主权利,涉及横、纵两个方面。从纵向上看是官兵关系,从横向上看是政委与军队主官的关系。这两对关系牵涉到红军中很重要的两个制度,即士兵委员会制度和政委制度。过往研究通常把他们分开来讨论,但若把这两个制度的变迁过程合而观之,能够非常明显地发现中共军队的集权趋势。因此,本文讨论这两个制度,更多是从权力结构上着眼,或说更注重人事变动和政策文本背后的东西。就叙述策略而言,本文将采取“察其言”“观其行”的方式进行论述,希望可以呈现出革命的双重面向,即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张力。
一、平均主义的起源、效用与蜕变
中共军队起源于朱毛红军,因此,平均主义也最先体现在这支部队中。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经济完全公开。军费拨发分为计划、执行、监督三部分。预算计划由军队委员会负责制定;各级士兵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军需处每月公布收支情况,士兵有权审查或提问,军需处长出席答复。若发现问题,则处罚负责人。制度公开透明,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即如毛泽东所言,“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注]《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9页。据陈毅称,红军中的军官若不介绍,最多以为是一个火伕头。朱德当时的诨号就是“火伕头”。红四军中有一幅联语,最典型地体现了平均主义,即: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注]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5页。
关于平均主义的景象,革命回忆录中多有描写,现存研究也多有提及,本文不拟复述。但需要追问的是,中共军队为何会在初期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军队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官兵平等。自晚清、北洋、国民党以来,军队中的等级差序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官还是兵都习以为常。中共革除旧俗,别出心裁,难道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的理念吗?除此之外,有没有更为关键的现实因素呢?关于红军践行平均主义的缘由,现存研究大都注意到了中共主动选择的那一面,但却相对忽视了其不得不如是的那一面。其实,平均主义之践行,既是缘于理念,也是基于现实。
中共军队初建时,面临双重困境:其一,被四处“围剿”,没有安稳的居所;其二,中央经费紧缺,部队没有稳定的外部供给,一切全靠自筹。1927年底,中央明确告诉朱德:你们队伍一切的给养,均应从地主豪绅、官吏财主身上想办法,“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这不但事实不可能,而且原则所不许”。[注]《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军给养筹措的意见》(1927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养兵、练兵本来最费钱,中共中央却分文不出,全让部队自筹。这与国民党军队有很大区别。军费自筹,实际上就是要让士兵自己动手找粮食。可以想见,在这个过程中,军官没有任何优越于士兵的地方。若是军费从外部供给,意味着军官掌握财源,财富分配呈现等级性特征;但当士兵自己找粮食时,官兵实际上处于同一境地,军官没有超越士兵之上的权威凭借。这应该是平均分配的最根本原因。极端贫困状态下,平均主义是凝聚人心的强大武器。
平均主义的制度基础是供给制。北洋及国民党军队普遍实行薪饷制,主要按人数与等级发放薪俸。照常理讲,薪饷制应该被正规军队普遍采用。但游击时代,红军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所以中央建议朱毛废除薪饷制,实行志愿军制,只发必要的生活费用。[注]《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4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应该说,这个决定相当明智。因为若是按薪饷制,司令部肯定发不出钱,拖欠军饷,必引起士兵不满。近代以来,士兵哗变,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拖欠军饷。事实上,中共中央当时也已经考虑到,如若不改变军需制度,恐怕将来很难维持军队稳定。
不难发现,中共之所以变更军需制度,最关键的原因是没钱发饷。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救急”举措,后来却引发巨大反响。薪饷制最大的弊病是容易导致军官贪腐。因为按等级和人头发钱,一方面会诱使军官虚报人数,赚取外快;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借机克扣士兵薪俸,中饱私囊。这些弊病在北洋及国民党军队中非常普遍。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官兵贫富悬殊巨大,心理隔阂严重——士兵眼见军官敛财,既羡慕又嫉恨。而且,薪饷制隐藏着另一风险——军费充足时,官与兵尚可相安无事;但若遭遇军费危机,军饷发不出时,兵与官就很容易冲突。士兵哗变闹饷、逼迫长官给钱等事例在北洋及国民党军队中很常见。中共颇为大胆地废除薪饷制,实行供给制,一切财物按需配给,这就几乎杜绝了任何舞弊空间。此外,官兵待遇一律平等,也就意味着军官没有任何优越于士兵的地方。
供给制度一方面缓解了军费危机——因为只保障最基本的吃穿,没有额外薪饷,可省去一大笔开销;另一方面对士兵心理影响极大。在薪饷制下,官与兵实际上是两个阶级,思想上比较隔膜;但在供给制度下,官与兵是连为一体的,他们同甘共苦。因此,即便遭遇困难,也不容易出现官兵对立的情况。粟裕回忆,井冈山的生活虽然苦,有时连续几个月发不出钱,但因为长官与士兵生活一个样,所以“从来没有闹饷的”,士兵“也不怨恨谁”。[注]《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1929年滕代远也报告称,官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钱时就多发,没钱时,两月之久,一文不发,部队上下生活同苦,“亦没有如何的了不得”。[注]《滕代远向湖南省委报告(节录)》(1929年1月12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30页。不难发现,供给制加上平均主义,不仅能节省军费,而且还能凝聚人心。当部队遭遇困境时,士兵不但不会向军官发难,反而会采取抱团取暖、共度难关的态度。陈毅对此有明白的表述。据其称,因为废除薪饷制,实行供给制,所以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时,士兵可以多分零用钱,经济困难时,则少发或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注]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458页。红军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仍能够维持不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不会向军长要钱”。
放置在近代以来的官兵关系中看,士兵不闹饷是很少见的。比较而言,国军士兵的待遇远好于红军,但国军仍然不满意,经常闹饷,官兵之间离心离德的情况严重。红军士兵虽然经常饥饱不均,但很少有闹饷举动。过去总习惯于用“革命精神”一类的抽象话语对此进行解释。实际上,国共士兵都来自工农群众,就思想认识而言,基本上属于同一层次,几乎不存在谁革命性更强的问题。真正影响官兵团结的,其实是物质分配。只有官兵的生活水平较为一致时,思想与情感才会趋近,士兵才会把军官视作“自家人”。一旦贫富悬殊扩大,不公平现象加剧,再好的政治教育,都很难弥合军队的整体性裂变。马克思讲“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或许就是这个道理。过往研究在诠释中共官兵关系时,过于重视宣传、组织、政治工作等“言传”的一面;相对忽视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革命能吸引那么多人投身其中,绝不仅仅靠言说。“言传”之外,“身教”更为重要。
官兵平等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因为平均主义思想自古以来就有,容易引起士兵共鸣;另一方面,晚近以来,军队中等级制度森严,平均主义的实践非常稀缺,无论是北洋还是国民党军队都不曾有过。中共适时推出平等举措,一下子就抓住了士兵们的心理。据陈毅报告,俘虏兵见红军的军官那样“芒鞋草履”,“莫不诧异”。[注]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455页。黄克诚也回忆称,当他初次见到毛泽东提出军队不发军饷,要搞供给制时,非常吃惊。因为在其看来,“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但打破惯例,竟然大受士兵欢迎,黄克诚为此感慨到:“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注]《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干部带头”确是平均主义能够实行的根基。
平均主义的影响固然很大,但不要忘记,它是与绝对贫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效用的限度问题。平均主义能够有效促进军队团结,这无可置疑。但是,如果长时间地处在绝对贫困状态下,那么即便实行平均主义,是不是就能保证士兵群众死心塌地干革命?抑或说平均主义是否可以被无条件地当作万能药?第二,持续性问题。平均主义产生的大背景是军费不足,那么,一旦红军有了稳定地盘与收入,平均主义还能延续下去吗?或者说,即便在制度上能持续,但在实践上会不会发生变异?过去关于“平均主义”的论述,基本上都忽视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平均主义固然可以促使官兵同心同德,但也只是在部分程度上缓解窘境。从长时间段看,平均主义维持军心的效用或不可高估。红军游击初期以及苏区后期,军需食粮都严重不足;在饥饿的威胁下,即便严格地实行平均主义,也仍然难以避免士兵动摇。1929年2月,湘赣特委书记杨克敏报告称,最近两个月来,红军每人每天只发三分钱的伙食费,三分钱的小菜,仅能买得一斤南瓜。虽然官兵一致,但士兵仍然动摇起来,“有开小差的,拖枪跑的”,甚至“下级干部也深感不安”。杨克敏提醒称,如若红四军不下井冈山解决经济问题,“大多数的群众,有不能领导了的危险”。[注]《湘赣边区红军后勤状况》(1929年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第24页。可见,平均主义并非万能药,其作用是有限度的。但后来的革命叙述,过于夸大了平均主义的作用,刻画出一种“民主平均”可以战胜万难的错觉。其实,一旦处在绝对贫困线以下,任何制度与动员都没有太大作用。
苏区后期,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经过几年的战争蹂躏,苏区一片凋敝,人力、物资都极端匮乏,扩红成为相当棘手的问题。黄道炫等人对此已做过深度描述,本文不拟重复。[注]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339页。但与本文相关的是,造成逃兵严重与扩红困难的原因,除战争不利、人口不足外,部队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因素。1932年底,萧克即报告称,因为经济困难,红八军曾一天只吃一分钱,甚至有一个时期,一分钱一天都接济不到。“现在农村生活,比军队高得多”,“所以农民有很多不愿当红军”;尤其是催促逃兵归队,比什么都感困难。[注]《红军第八军的给养情况》(1932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第199页。萧克此言,清晰揭示出平均主义的限度。与此相似,1933年11月湘赣省委也报告称,因为“给养完全没有保障”,“以致去年四、五月扩大的数目到年底已减少一半以上”。[注]《政治决议案——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1933年11月30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5页。在琼崖,也是经济困难,“使红军许多战斗员,每从医院出来便就不愿意回到红军中去”。[注]《琼崖红军第二师党委报告》(1932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第106页。不难看出,在绝对贫困状态下,即便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也难以挽救危局。或许可以这么说:平均主义与绝对贫困是一对七巧板的关系,如果一端的负担过于沉重,另一方其实无力回天。
其次,关于平均主义的延续与蜕变问题,也值得放在一个长时间段内考察。虽然在制度上,整个红军时代都实行平均供给制,但这不意味着井冈山时期那种绝对平等情形一直没有变化。井冈山时期的平均主义之所以能得到较好的执行,有两个不可忽视的条件:一是部队规模小,管理结构简单,军官没有中饱私囊的空间;二是军队一直处在流动状态,没有相对稳定的地盘,因而也没有税收、田租等稳定的军费来源,所有财物都是士兵打土豪得来的,他们直接参与分配,对物资多寡了解得比较清楚。所以,有时连一个鸡蛋都要闹着平分。[注]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但这两个关键性背景,随着红军的壮大而有所改变。
首先,苏区稳定后,红军军费已不全靠自筹。田赋税收、群众慰问等占了很大比重。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要求地方苏维埃准备军费,转变军队靠打土豪为生的局面。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建立统一的财政部门,要求各机关将所收入款项上缴中央财政部,由该部统一分配。[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1931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第97页。如1932年7月,红军一、三、五军团,每月给养至少需要30万,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支出”。[注]《红军的财政、给养、后方工作动员及军委后方工作计划》(1932年7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第156页。在游击时代,红军队伍规模小,经费自筹,士兵可直接参与分配;但到正规军时代,红一方面军已有几万人,不可能每个人都再直接参与分配。士兵只能等待发饷。中央通过税收、发债、打土豪等,将财物集中起来,再由后勤部门层层拨付,士兵不再直接参与分配体系制定。虽然中革军委规定:各级经理机关,每月造出决算账目后,须经过审查委员会审查。但是这个审查程序已经和井冈山时期不同。因为后来的审查委员会只有很少数代表参加。例如,师审查委员会,由各团选派士兵代表2人,师直属队1人,及师部、政治部、军经理处各派1人组织之。军审查委员会由每师选派代表1人,军直属部队选派士兵代表1人,及军部、政治部各派1人。审查委员会若发现经理机关有舞弊事宜,“得提到上级经理机关或高级军政机关惩办之”。[注]《中革军委关于经理工作的训令》(1932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第124、125页。很明显,这个审查制度已经是集权化的结果,士兵人数极少,监督效果有限。井冈山时期的平均分配,是全体士兵直接参与,而苏区时期的平均分配已经呈现出体制化、集权化特征。表面上看,平均主义制度一直延续,但其实践方式,实际上已经从“全民民主”转向“集中制民主”。
其次,实行集中经费、统一分配制度之后,官僚管理机构开始变得复杂化。1932年1月,中革军委指示军队建立统一的财政机关,共分4级:中革军委、总经理部、军或军团的经理部、各师的军需处。[注]《中革军委转发临时中央政府规定整个财政系统的训令的训令》(1932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第104页。此外,各部队中又分士兵伙食费、马干费、办公费、擦枪费、技术人员的津贴费、特别费等。[注]《中革军委关于各项费用的性质、数目及限制规定的训令》(1932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第111页。据统计,部队各项费用共有10类、130多项。[注]蒋胜祥主编:《杨立三年谱》,金盾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五花八门的费用背后,必定要有对应的管理人员。数量庞大的财物集中后,又经层层转手,如此一来可操纵的空间大大扩展。虽然红军在制度上仍然规定官兵平等,但实际上,军官的可支配权大幅度提升。权力增长并集中,意味着贪腐风险上升。
需要说明的是,军费集中管理和官僚机构复杂化,并不是制度错误,而是革命的必然趋势。革命要摧毁不平等制度,但当革命本身壮大之后,仍然需要一套差别有序的官僚体制维持运作。官僚体系确立之后,权力的等级差异必然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平均主义的实践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就是为什么井冈山时期的平均主义被很多革命者追忆与怀念,而到苏区后期,就很少有人再提及平均主义。当然,若是横向比较来看,整个革命时代,中共军队的贫富分化其实都不是很严重。毕竟,作为参照物的国民党实在是太腐败。但若是纵向来看,从井冈山到苏维埃共和国,再到后来的延安时代,中共关于平均主义的理想虽然未变,但在具体实践上,其实已经日渐松动。而这个松动,最早正是萌芽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
苏区后期,军官生活已然有特殊化的迹象。陈伯钧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观察范例。1933年,陈伯钧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的参谋长、第十三师师长。当时部队供给已极端困难,士兵每天一角钱的生活费都很难维持。如1933年7月26日,因敌人经济封锁,十四师午餐断炊,到晚上才领少许款项,以解燃眉之急。[注]《陈伯钧日记·文选》上,1933年7月26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虽然军队总体面临困境,但陈伯钧个人的生活似乎未受影响,他日记中经常有喝酒吃肉的记载。例如,1933年6月13日,吃红烧肉及玫瑰酒;6月18日,吃鸡肉下面条;6月28日,肉烧茄子;7月4日,“大肉小菜”;7月5日,两毛钱的猪肉,两毛钱的茄子,“弄了一餐烧茄子”;7月10日,吃团鱼、鸭子;7月27日,吃鸭子。[注]《陈伯钧日记·文选》上,1933年7月26日,第21-32页。很显然,陈伯钧的这个生活水平,一般士兵绝对不可能达到。当时士兵的生活费用大约每天一角钱,而陈伯钧一餐“烧茄子”就花去4角,是一个士兵4天的餐费。更何况,陈伯钧隔三差五都能来一顿类似于“烧茄子”的大餐。9月23日的一个细节,更能充分反映出陈伯钧平时食不厌精的生活情形。当日,部队供给实在困难,作为师长的陈伯钧也只能“中饭吃稀粥,晚饭吃番薯”,但陈伯钧并没有抱怨,而是感叹到:“吃餐把番薯,也还新鲜”。[注]《陈伯钧日记·文选》上,1933年9月23日,第45页。可见,平时他是很少吃番薯的。师长陈伯钧的生活细节充分说明,中共关于平均主义的理想和制度虽然留存,但随着新秩序、新等级体制的确立,平均主义在实践上已经开始有所变化。
关于平均主义蜕变的另一个极端例证是李德的“奢侈”生活。作为共产国际顾问,李德1933年到达苏区。为照顾其生活,中共中央极端用心。据其秘书王智涛回忆,李德到来之后,军委供应局局长宋裕和专门负责其生活。尽管当时苏区物资极端困难,但军委供应局还是想了很多办法保障其特殊的生活待遇。例如,派遣曾在大饭店掌勺并会做西餐的师傅当炊事员,并经常从战利品中搜罗好烟、好酒、奶粉、咖啡、白糖、巧克力、各式罐头等供应给他。此外,李德还单独就餐,由专门的师傅在军委食堂做好后端到其住处。一日三餐以烤馒头代替面包,再配上自炼的牛油、咖啡,还有鸡鸭鱼肉、青菜、水果等。总之,李德的生活相当优越。[注]《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无独有偶,另一位担任过李德秘书的伍修权也有类似记载。据其称,当时根据地的经济不富裕,普通工作人员每天只有十两粮食,“根本吃不饱”。吃菜不仅没有油,常常连盐也没有,只能把青菜用白水煮了吃。但组织上对李德却额外照顾,苏区自产的鸡鱼肉蛋等源源不断的供应,打仗缴获和从白区弄来的香烟、咖啡等高级食品也优先供应给他。[注]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虽然李德的事例比较特殊,不能代表当时中共党内高层的普遍情形,但从中也能看出,当官僚体制建立之后,核心权力机构所能调动和分配的资源大大增加。龚楚有一个回忆,可与李德的事例相印证。1933年,龚楚在红军大学高级班学习,此班共有20多人,全是师级以上干部。据其回忆称,“我们的给养很好。每星期一次肉食,每人有四两猪肉或六两鱼。平日的菜蔬也丰富,比较红军士兵要好上几倍。”[注]龚楚:《我与红军》,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版,第387页。从这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上层人员生活特殊化已经具备相当的制度基础。至于“奢侈之风”是否会蔓延开去,其实只是时间问题。毕竟,上层机构掌握着那么多资源,既然能够优待李德,也就能够在某个时间段开始优待自己。以后见之明观之,这个分化的道路,随着革命的成功,正一步步加剧。
平均主义被打破,一方面是因为体制性因素——处在官僚体制上层的人员拥有权力,并适当将资源向上层倾斜,这实际上是被默许的。如陈伯钧、李德等人的“优越”生活是被体制许可的,他们喝酒吃肉不算违规。但另一方面,随着官僚体制膨胀,以及权力失去约束,贪污腐化现象大量滋生,这就不是正常现象。1932年底,湘赣军区批评地方武装称,因为经常独立行动,军区和政府不能很好地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因此,贪污腐化非常严重,如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不归公,“经常不顾一切革命工作,专门干那贪污腐化的事情”等。[注]《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军区总指挥部训令》(1932年12月),《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独立第十二师中有烟鬼十多名,打土豪时“经济手续不清楚”,“各个人都可以收款”。连长、指导员各自支配经费,“拿公款私人买金戒子金手表”,而“士兵生活苦到万分”。[注]《中共湘赣省委报告》(1933年2月),《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297页。大约同时期,南广县委也批评称,地方武装无统一指挥,将打土豪所得任意分配,中饱私囊者众多,“嫖赌吃大烟更是普遍的”。[注]《中共南广县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报告》(1932年10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2),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92年,第98页。与此相类,宁化游击队中“吃大烟、嫖姑娘的”也很多。[注]《霍步青给稼蔷同志信》(1932年11月8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年),第273页。地方武装贪腐严重,实际上是整个苏区风气的一种反映。当时苏维埃政府的贪腐程度并不弱于游击队。如在赣西南,“一般同志在较好的环境生活特别表示腐化,金圈子、金戒子带起;还有藉党招摇向乡人讹索钱财酒食,造成党内新土豪新劣绅”。[注]《中共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1930年5月18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第133页。麻城、黄安一带的各级指导机关和区委,“每天总是吃鸡吃肉,常常是一餐一个鸡。许多同志非肉不饱”。[注]《何玉林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7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鄂东北特委、豫东南特委文件1927-1934年),第126、127页。兴国、于都等模范县也都出现过严重的贪腐窝案。如兴国县主席,借国家商店,吞没公款,假造账目等[注]《苏区开展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斗争》,《红色中华》1932年3月2日,第7版。;于都县,从县苏主席到各部部长,几乎无官不贪。[注]朱钦胜:《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158页。无可讳言,苏区后期,政府人员利用权力分肥的现象非常普遍。[注]《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四个月(一月至四月)工作总报告》(1932年5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第153页。为打击贪腐,苏区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并制定过严厉的惩罚条例,如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500元者,处2-5年的监禁。[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六号》(1933年12月1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即便如此,贪腐的风气并未得到彻底根治。
以上所论是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府的情况,至于正规红军,情况虽稍好,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受影响。贪腐享乐风气最先盛行于地方,而后向军队蔓延。如巡视员郭树勋报告称,在鄂豫皖三十二师中,“一个号长可以发大财,副官更是贪污极了”。[注]《郭树勋巡视河南商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19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鄂东北特委、豫东南特委文件1927-1934年),第325页。1932年11月,湘赣省委也批评“红军中军阀残余与贪污腐化现象”非常严重。[注]《红军与地方武装问题决议案》(1932年11月),《湘赣革命根据地》,第400页。苏区后期,一边是士兵群众食不果腹,另一边是上层人员利用权力造成党内的“新土豪”“新劣绅”。毫无疑问,这对平均主义的实践必然造成沉重打击。革命者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等级分化悄然出现。
其实,等级分化不仅表现为贪腐,当官僚体制稳固下来之后,资源沿着等级秩序往上流动。居于上端的权势者,必定会占得先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傲慢”表现,也足以让平均主义黯然失色。如秦基伟回忆,1934年初,他在红四军中当团长就很有派头。据其称,“当团长的时候,身边有一大帮人,有一个专门文书,有警卫员,有公务员。团部有一个骑兵排,团长一出门,就有一个班跟着。每人三大件,一把盒子枪,一支马枪,一把大刀,盒子枪和大刀的柄上都系着红绸子,漂亮得扎眼”。当他在前面策马扬鞭时,后面有十余匹随从。众人策马奔腾时,马蹄铁踏在鹅卵石的街面上,“嗒嗒嗒,火星子乱迸”,景象颇为壮观。秦基伟自己都感慨称:“那真叫八面威风”。[注]《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无可讳言,秦基伟的这个“威风”与后人常言的“官兵平等”很不一致。其实,“官威”在红军中早就有表现。1929年,巡视员何玉林报告称,“红军中的官长出外,必带着勤务兵,许多同志出外带着手枪、电筒”,“工作非常夸张,态度非常骄纵”。[注]《何玉林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7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鄂东北特委、豫东南特委文件1927-1934年),第126、127页。这与秦基伟的回忆或可遥相呼应。官僚体制形成后,“耍威风”其实是权力在实践中的自然表现形式。
总体上看,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官僚管理体制确立,等级分化便随之凸显。井冈山时期的那种绝对平等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中共关于平均主义的理想固然值得赞颂,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新秩序、新体制逐步确立,资源的差异化配置无可避免。当然,比之于时代,中共的问题绝对不算严重,只是从内部看有所松动。
二、战争阴影下的民主及其走向
除却平等,红军的另一个特质是民主,也就是毛泽东讲的“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注]《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0页。民主与平等,一个关乎权力分配,一个关乎物质分配,二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政治运作角度看,资源分配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分配。红军中权利民主,最重要的体现形式是士兵委员会制度。
士兵委员会起源于苏俄。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中有过短暂实践。[注]王建强:《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国共分裂后,中共中央指示南昌起义部队组织士兵委员会,但共产国际内部有争议。如瓦西里耶夫认为:在南昌起义军中提倡士兵委员会的口号“是冒险的”,因为起义军不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党支部”,通过支部和政治工作掌控军队。瓦西里耶夫害怕一旦搞起民主,士兵就不服从指挥。然而布哈林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是否建立士兵委员会,应取决于共产党人拥有多大权力。如果中共有足够的组织力量,则可以不要士兵委员会;如果不能够从组织上领导士兵,“那么设立士兵委员会还是合适的”。[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速记记录》(192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4页。他们二人的意见虽然相左,但有一点是相通的,这就是把士兵委员会与中共的领导权对立起来。只是在布哈林看来,士兵委员会可以帮助中共取得领导权,等到军权稳固以后,再取消;而瓦西里耶夫认为,士兵委员会增添麻烦,应该越过士兵委员会,直接掌控军队。不难发现,不论哪一种看法,共产国际实际上都只是把士兵委员会作为一个过渡性手段。
从中共后来的实践看,布哈林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秋收起义部队最早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关键原因正如布哈林所言:领导者实际权力有限,不能有效控制军队。秋收暴动失败后,起义部队分崩离析,士兵、军官逃跑者甚多,原本5000余人的部队,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只剩下几百人。毛泽东为重振旗鼓,1927年9月底进行三湾改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成立初期,权力极大,凡重要事务都须经其讨论,官长亦须接受其监督。[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61页。军队中向来都是官长命令士兵,中共骤然改弦更张,士兵地位空前提高,这带来相当大的震动。
据陈士榘回忆,“三湾改编”给工农革命军带来的最大变化不是“支部建在连上”,因为以前部队里也有党代表,只不过一般都建立在营以上单位,但营、团的党代表经常下到连队来,士兵们见到党代表并不困难。“三湾改编”给工农革命军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这个组织类似于监督院,可以监督官长。若是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士兵们就不敢讲话,或者讲了话也没有作用。但是有了士兵委员会,情况便大为不同。士兵委员会规定:官兵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政治民主,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力与自由;经济公开,士兵监督执行。[注]陈人康口述,金汕、陈义风著:《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在这个制度下,士兵个体被充分尊重,民主气氛浓厚。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军队中实施大民主,除革命理念外,更现实的原因是,作为主帅,他没有任何可以控制住士兵的物质手段,只能依靠“平等”“民主”等精神力量来凝聚人心。这与稍前布哈林的论说非常一致。
士兵委员会的运作主要靠选举。在组织体系上,士兵委员会分为三级。首先,由全体士兵选举出代表会成员;其次,再从代表会成员中选举出执行委员会,最后,从执行委员中选举出常委会。关于士兵委员会的选举方式,陈毅有过详细描述。据其称,红四军中的军、团、营、连都设有士兵委员会。连一级的士兵委员会,由全连士兵选举,人数为5到9人,推选主席1人。营一级的士兵委员会,以全营人数总和为基准,按每5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同时又在士兵代表大会中再选举出11到13人组成执委会。团一级,每10人选一代表,并在其中推选17人至19人组织执委。军一级,每30人或50人举一代表,择其中19人至21人或23人为执委。从营一级到军一级,除执委之外,还设有常委。军一级的常委,由执委中选5或7人;团一级也是5或7人;营一级为3或5人。连一级无常委机关。[注]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456页。可以看出,士兵委员会制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参与层面,全体兵士都有投票权;在执行层面,又通过金字塔体系,将权力集中化,最终使“民主”落到实处。当然,红四军规模小,是便于实行直接民主的重要因素。
士兵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同时也做政治教育工作。罗荣桓谈到士兵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时称,军官都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是制裁。例如,连长、排长犯错,士兵委员会就有权决定打其手板。当时九连的连长,就是因为违反群众纪律,而被士兵委员会打了屁股。[注]《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聂荣臻在1942年谈及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也称当时的红军是用最高的民主方式,来根除旧军队的习气。许多事情并不是靠命令,而是与士兵商量解决。这主要是因为“部队首长与党代表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权力”。当时,士兵委员会是连队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问题都要经过它的决议才能执行,没有通过就不能执行。士兵委员会甚至可以决定干部的处罚。[注]《从现在去认识过去,从过去来了解现在》(1942年8月1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士兵委员会的强势,中共官兵平等的传说才深入人心,流传久远。
士兵委员会制度不仅使官兵在物质生活上趋于平等,而且在权力上也实现了共享。由此,士兵的革命主动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湘赣特委书记杨克敏曾报告称,“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监督经济公开、制止长官体罚士兵等。除此之外,在士兵委员会的督促下,士兵写标语、发传单、组织群众工作等都比较积极,“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3页。士兵在近乎于自我管理的体制下,做事明显更积极主动。对此,滕代远也有类似的观察。据其称,“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以代表士兵利益参加军队管理,维持军队纪律,发展群众运动。如若本身健全,很能够起作用”。[注]《滕代远向湖南省委报告(节录)》(1929年1月12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29页。传统军队通常采用命令与打骂方式进行管理,士兵虽然也做事,但心里有芥蒂。新制度下,士兵内在行动意愿就比较强烈。这在俘虏兵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毛泽东曾不无得意地讲:俘虏兵在民主的氛围中很受震动,感觉与国民党军是“两个世界”,昨天在敌军中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就很勇敢。[注]《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0页。毛泽东的讲法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是红军别具一格的管理方式的确是其他军队所没有的。例如,旧军队中,官长动辄打骂士兵,但在红军部队中,因为有士兵委员会的存在,体罚相当程度上被制约。1930年熊寿祺向中央作报告时就提到,起初要废除打骂制度时,许多官长都说:““不打人看怎样能够管理?”但后来事实证明,在士兵委员会的帮助维持下,士兵自觉遵守纪律,比打人有效得多。士兵委员会一方面教育士兵;另一方面也制止长官打人,因此“士兵都感觉像这样当兵才值得,这才真是自己的军队!”熊寿祺讲,“每次捉来的俘虏兵不用长官去宣传,我们的士兵都争先恐后的很热烈的去告诉他们红军官长不打士兵!士兵的宣传力比官长的宣传力要大得多,因此目前下级官长也不十分反对废除肉刑了。”熊寿祺最后总结称:“士兵的确比以前打人时代还好管理了”。[注]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1927年10月-1930年4月》(1930年5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很多革命者,如罗荣桓、聂荣臻、宋任穷等都对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念念不忘。可见,那时的民主氛围的确是一代人的记忆。
回过头来看,民主平等虽然让士兵欢欣鼓舞,但也不是没有问题。通常来讲,军队最应该集权,因为战争情势瞬息万变,必须当机立断;若事事都要民主讨论,必定贻误战机。军事作战,尤其是战略部署,将领的天才通常起决定性作用,民主讨论未必能得出最优决策。民主的最大优点是可以防范最坏结果,因为它有“试错”机制,一旦发现错误,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推翻重来。但战争中是没有“试错”机会的,一旦出错,就意味着死亡与万劫不复。古往今来的战争中,都只有英雄,而没有民主。可见,战争需要的是“超人”与集权,而不是民主。中共别出心裁,一方面让个体士兵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但一方面,从整个军事作战角度看,民主与平等也带来诸多问题。
首先,战争最重指挥与服从,而民主极大地削弱了这种上下级的服从关系。士兵委员会权力太宽,即便是战略决策,也要提出主张,但士兵们通常眼光狭隘,只见眼前利益,难以照顾到大局,最终往往导致惨剧。如红四军的“八月失败”,就与29团士兵执意回湘南家乡有关。据欧阳毅回忆,当时有一些军官从战略角度分析,认为回湘南凶多吉少,但立即被士兵咒骂“怕死”“家乡都不要了,没有良心”等。士兵委员会提出“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的口号,符合士兵个人利益,极具煽动性,导致士兵一哄而起。欧阳毅感叹:“农军回乡情绪太普遍,太可怕,不赞成回乡的遭到孤立”。[注]《欧阳毅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58、59页。结果29团回到湘南遭遇彻底溃败,这一事例典型表现了民主在战争中的局限。战争需要集体奉献、需要个人牺牲;而民主在本质上恰恰是追求个人权益。因此,民主与战争其实格格不入。
其次,民主与效率是相冲突的,越是广泛的民主,越难以达成共识。士兵动辄有意见,很不利于军事行动,因为军事作战往往需要迅速决策与统一行动。1929年朱毛之争时就涉及到民主与集权问题。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到军队民主化的弊端,因而力主集权,但他的看法未被接受。红军七大上,毛泽东被选举出局,朱德领导红军继续进行民主化实践。可是在红军八大上,众将士七嘴八舌,会议开了几天都没一个结果。军队没有主心骨,肯定打不好仗,朱德后来南下失败,就与此有关。
朱毛争论爆发后,中央明确支持毛泽东的集权主张。1929年底,红军九大,即古田会议上,红四军正式开始“纠偏”。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并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求“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各级机关在讨论问题时“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90页。军事民主必须受严格限制,这是古田会议的重要内容。
古田会议上的急剧转向,一方面与毛泽东加强个人权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整个战争态势有关。井冈山时期,队伍规模较小,而且人心散乱,用民主来维持团结是很好的选择。但1929年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队伍规模急剧扩大,军费粮草相对充足,红军面临的问题开始转变,即从如何维持队伍转变到如何指挥作战。总体来讲,民主在军队力量薄弱时能够发挥最低限度的笼络作用,而一旦形势不稳,它就必须退出。否则,将有碍于军队的进一步整合。这是战争的内在要求,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集权主张正是历史意志的彰显。
古田会议之后,中共军事民主日益萎缩,集权趋势明显。由民主转向集权的突出性标识是士兵委员会的取消。前文已论及,士兵委员会的权力范围从日常生活到军事作战,无所不包。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军官几乎随时都会受到挟制,“八月失败”是典型事例。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有意识地限制士兵委员会权力,让其只管生活,不得过问军事问题。应该说,这样一种取舍是比较得当的,军事作战与日常生活分离,使得民主与集权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
然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并不认可毛泽东的策略。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称士兵委员会起初可能起着团结士兵的作用,但是由于委员会与党组织平行存在,他们试图履行监督、指挥和进行政治工作的任务,所以他们隐藏着最坏意义上的“委员会至上”因素,潜伏着对抗党组织的危险,同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共产国际因此建议:首先要使士兵委员会“在政治上不起领导作用”;其次,应伺机将其取消。[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67页。从井冈山时期的实践情况看,共产国际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彻底取消民主的做法无疑有些矫枉过正。共产国际只注意到士兵委员会的“分权”弊端,似乎没有重视其在军队生活中的黏合剂作用。
中共中央接共产国际的通告后,很快有所行动。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军委会议上明确指示:上层的士兵委员会组织要完全取消,“连的兵委组织要逐渐减少他的职权,一直做到取消”;并提出“反对军队民主化的倾向”,“一定要采集中权力的原则”。[注]《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1930年9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1133页。这显然是紧跟共产国际步伐。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及士兵委员会问题,强调“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做到消灭”。[注]《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此后,红军各部队遵照中央指示,开始逐步限制与取消士兵委员会组织。截止到1932年,“士兵委员会”一词在红军文献中基本不再出现。[注]王建强:《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回过头看,从1928年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到1930年开始对其进行限制,其实有保障的民主只有两三年而已。
压缩民主、集中权力,是红军迈向正规化的必然趋势。在队伍规模较小时,民主可以有效维持部队团结;但当部队规模达到几十万之众时,就必须集中统一指挥,不适宜再搞民主。布哈林早期说:如果党组织的力量足够强大,则可以不要士兵委员会。实际上,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当组织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民主便可以退出。总体而言,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士兵委员会的兴起与消逝,可算作一个例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士兵委员会制度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度有所恢复。1948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接此通知后,斟酌情形,在各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以几个月作为试办时期,以便在试办期中产生办法、工作范围及内容等”。3月8日,周恩来签署命令,要求各部队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重振军队民主。但恢复后的制度相较于“原典”有很大变化,最关键的是增加了很多限制性条款。例如,首先规定士兵委员会必须在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其次,士兵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再次,上级的命令,士兵委员会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最后,士兵委员会如欲对其上级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并且要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注]《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1948年3月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1页。很显然,解放战争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其性质与井冈山时期已无法相提并论。
三、从民主到集中
“官兵平等”“民主讨论”是井冈山时期的特征。红军转战到赣南闽西后,随着规模扩大,等级秩序重新建立。平均主义被打破,表面上看是物质生活分化;实际上,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权力被重新结构化。1930年后,中央红军朝着正规化、集权化方向迈进。井冈山时期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草莽形象一去不复返。中共强化军事集权有两个重要表征:其一,是政治委员制度之贯彻;其二,是政治保卫局的发展与膨胀。
先谈政治委员制度。红军从党委制向政委制的转变历程,现存研究已有清晰论述。[注]王建强:《红军由党代表制度到政治委员制度的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这两个制度的重要区别在于,党委制领导下,重大问题是由党委委员集体讨论决定;而政委制,则是个人专权独断,政治委员一人可以凌驾于党组织之上。1930年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并明确规定:一、政治委员制度在军队中与党组织是平行存在的,并且高于这些组织之上。二、连、营、团、师、军的政治委员对于党支部和他下属的政治委员具有上级党组织的一切权力。三、如果支部工作中出现反党倾向,政治委员可以解散支部。四、对于下级政治委员,有奖惩权。五、政治委员作为党的代表,与指挥员享有同等权力。他监督指挥员,使指挥员的作战符合革命利益。指挥员“一旦有叛变嫌疑”,“政治委员有权将指挥员送交审判,如有明显的叛变行为,政治委员有权处决”。指挥员的命令如无政治委员的签字和该部队加盖印章是无效的。共产国际最后声明,中共对于这些指示可以有所变通,但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即:明确的、有组织的形成以政治委员制度为领导的党的组织体系。[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966页。可以看出,这个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将政治委员等同于党。党本身是很抽象的东西,其职能必须由具体的个人来承担。党与政治委员黏粘在一起,在实践中,容易造成组织与个人不分,形成政委独裁。
强化军事集权,提高政委的地位,符合中共中央的意图。三十年代以后,中央与毛泽东等军事将领的分歧与争论愈来愈大,红军俨然有挣脱中央管控的危险。因此,接苏俄指示后,中共中央很快有所行动。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军委会议上进一步诠释政委制度,强调“提高政治委员的权威,建立政治委员的作用,完全是巩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注]《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1930年9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1131页。12月,中央给各红军部队发出训令,明确指示:“党部书记和政治委员的职位是不同的,党的书记是在选出后要得到政治委员的批准,而政治委员则居于政治指挥的地位,政治委员对部队的情状负完全责任,自然对党的组织的情状也要负责”。[注]《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1930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16页。政治委员被赋予绝对领导权,这就进一步压制了民主空间。如果说取消士兵委员会,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被终结;那么,政委制度取代党委制,则代表着横向民主也遭到严重挤压。
政委权威迅速提升,除去政策指示外,也与另外两件事情有关。其一,富田事变。1930年底,红二十军公开分裂红军,不论当时他们有多大委屈,但这一举动都让中央极为震动。此事加速了中央派遣政治委员去控制军队的步骤。1931年3月,中央通过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最能表明此种态势。决议称,二十军暴动的事实告诉我们,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是每个党团员第一步的基本任务。“不执行命令,批评这种命令和行动计划,批评上级指挥员的战略,都是绝对不能的”。中央同时强调,各级政治委员,不但有权停止队伍中党部所通过的削弱红军战斗力与纪律的决议,并且有权解散该支部,以及开除支部中的个别同志。[注]《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3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1543页。富田事变虽然比较偶然,而且领导者谢汉昌、刘敌等也是被逼无奈。但不言而喻,此次事变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促使中央加强对军队的集权化管理。政委集权制度正当其时。
政委权威提高的第二个现实原因,与外来干部有关。1930年后,中央“钦差大臣”大量进入苏区。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白色恐怖”下,中共在大城市的活动空间日益缩小,只能转移人员;另一方面,“钦差”大批进驻苏区,实际上也是中央意欲控制红军的一个体现。“钦差大臣”到苏区后,大都担负政治工作。中央权威正是通过政委得以体现。统计1934年2月红军各军团司令官和政委的履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政委都是1930年后才进入苏区。
1934年2月红军各军团的司令官与政委分布情况:

总司令部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七军团红九军团江西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官朱德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寻淮洲罗炳辉陈毅叶剑英政委周恩来聂荣臻杨尚昆朱瑞乐少华蔡树藩李富春万永诚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序列表》(1),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
政委权力提升,体现了中央对军队的纵向控制,虽然政委专权引起司令官的强烈不满。但是随着毛泽东等人被打倒,外来“钦差”基本上成为军队的主导力量。
中共军队集权的另一标志是设立政治保卫局。中央政治保卫局成立于1931年,前身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特务大队,是肃反的主要机关。[注]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红军在肃反过程中冤杀、枉杀等事例数不胜数,现存研究已有详论,本文不再展开。[注]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227页。政治保卫局横行无忌,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固然要谴责,但从权力控制角度看,集权体制之建立,恰恰需要暴力与恐怖。可以说,政治保卫局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集权体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帮手。
首先在权力架构上,政治保卫局完全是垂直式管理,与各级军队和政府只发生横的联系。“地方政府及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如有异议,只能到人民委员会解决。[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1932年1月2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政治保卫局若逮捕政府机关、红军与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时,只需拘捕前通知该机关的最高负责人,“该机关最高负责者即使不同意亦不得阻挠其行动”,只能向上级抗议。[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1932年1月2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第165页。可以发现,政治保卫局是一个非常封闭和独立的体系,对“反革命分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对此,长期在保卫系统工作的李一氓有深切体会。他讲,地方保卫局直接由同级党委书记领导,军队里面的保卫局(方面军和军团保卫局)自成建制,不属于政治部系统。政治保卫局在军队和地方上都形成一个非常独立的建制。在军队上政治部管不了,在地方上政府管不了。长征以后,政治保卫局才归属到政治部里去。解放后,地方保卫局转化为公安系统。李一氓感慨称:“至于地方公安工作,从现在来讲,其内容要比从前复杂得多,规模也比以前扩大得多了,但是就其权力来讲,确实比以前缩小得多了”。[注]《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正是因为没有制衡机关,政治保卫局专权独断,所以很多冤假错案难以得到有效纠正。
其次,在权力行使上,政治保卫局非常蛮横。处理“反革命”案时,这一机构可以任意严刑拷打,甚或是直接枪毙。暂且不论它制造了多少冤案,仅只是此种行事方式,就完全窒息了民主空间。政治保卫局一手遮天,任何反对或不满的言语行为,都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据彭德怀回忆,肃反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压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与政治部平列,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注]《彭德怀自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1932年1月,闽粤赣省委总结肃反教训时也有类似的反省。批评政治保卫局把一切现象都看作社党、托派,严重压制了民主批评与讨论。[注]《中共闽粤赣省委反社党托派及一切反革命政治派别斗争的决议》(1932年1月20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年),第34页。政治保卫局专权独断,稍有不满者即被视为反革命。受害者没有申辩的余地,正是集权主义的特征。1932年江西省委的一段批评很有代表性,在其看来,“省保卫处自认为是代表党,代表政府的,一切问题独断独行,形成一个超党、超政权的组织”。因为它的权力毫无约束,所以在打击反革命时,也往往出现陷害异己、假公济私的行为。如粤北区一个村的肃反委员,与苦力争野老婆,便将其捉来,诬陷成AB团,严刑拷打,“并用香火将肚子烧烂一块”。[注]《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四个月(一月至四月)工作总报告》(1932年5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第175页。如果连争“野老婆”都可以被牵连到肃反案件中,那么可想而知,政治保卫局的权势已经张狂到何种地步。
无可讳言,肃反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这固然要谴责;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肃反本身对士兵与民众构成一种巨大威慑力。在这种威慑下,不同意见很难被表达出来。对此,欧阳毅有过精彩回忆。据其称,肃反期间,他亲眼看到一同参加革命的老乡彭琦被逮捕,当他路过时,彭琦向其呼救。然而,欧阳毅连声都不敢应,因为一应声马上就会被当做“同党”。欧阳毅只能“别过脸,低下头,装作不认识”,迅速走开。[注]《欧阳毅回忆录》,第119页。无独有偶,萧劲光也有类似记述。闽西肃反时,政治保卫机关大杀“社会民主党”,导致人人自危。萧劲光感叹称,“在那样的形势下,谁也不敢提意见,谁提了意见就是同情‘社会民主党’,就可能被立即打入另册,甚至遭杀身之祸”。结果是,一听到某同志有问题,大家都避而远之,不敢往来。[注]《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无可讳言,肃反激烈化严重窒息了民主空间。
结语
提及红军,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民主与平等。不可否认,草创时期,红军的确有过比较理想的实践,但那一过程极为短暂。随着革命队伍壮大,民主的局限越来越突出。毛泽东等军事领导人不得不做出调整。古田会议上所谓反“极端民主化”,正是调整的开端。纯粹从作战角度看,适度压缩民主是有道理的。毕竟,对战争而言,英雄人物的专权独断可能更为有效。但问题是,即便是英雄专权也得有个“度”,一旦走向极端,极易导致不可挽回的灾难,苏区时期的疯狂肃反,便是一个显例。然而,“度”的考量只是后人的理想期待。因为,集权一旦开启,就很难停歇。
生活平等与权力分配紧密相连。革命权力重新结构化、等级化之后,军官与士兵的物质生活日渐分化。虽然在制度上中共一直倡导平等,但是随着官僚体系日益层级化,居于上端者无疑能更容易摄取资源,其生活水平慢慢超出一般群众。虽然共产党人的理想与奋斗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平均主义的传统——尤其是相较于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的贫富分化并不算严重。但是从体制与实践上看,平均主义走向破灭实乃必然趋势。红军后期已经呈现出的分化现象,正是平均主义走向破灭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