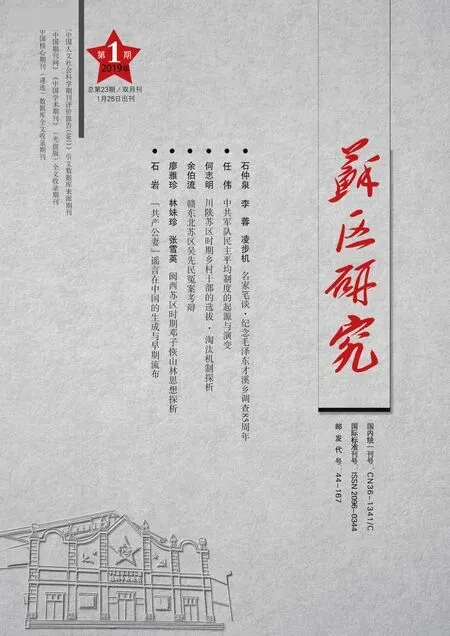赣东北苏区吴先民冤案考辩
2019-12-15
提要:党的历史有辉煌,也有曲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赣东北苏区和红十军内,发生过一幕真实而又可怕的惨剧:赣东北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始人之一吴先民,在“左”倾肃反政策的淫威下,被残酷杀害。惨剧的制造者是“左”倾“中央代表”、后堕落为叛徒的曾洪易。方志敏为之抵制、抗争过,但无力回天,爱莫能助。从历史的深思中,应当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获得有益的当代启示。
党的历史是辉煌而又曲折的,有的时候还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本文论述的,就是发生在赣东北苏区和红十军内一幕真实而又可怕的惨剧:赣东北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始人之一吴先民,在“左”倾肃反政策的淫威下,竟被残酷杀害!
方志敏为之抵制、抗争过,但无力回天,爱莫能助。
惨剧的制造者是“左”倾“中央代表”、后堕落为叛徒的曾洪易!
让我们回首这幕惨剧的始末。
一、“横峰有了吴先民,不愁天下不太平”
赣东北上饶,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信江之滨、灵山耸立。这个素有“富饶之州”、“信美之郡”的地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出了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一代英杰,他们领导创建了毛泽东誉之为“方志敏式”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
吴先民,江西横峰县青板桥人,是跟随方、邵、黄革命“起家”、浴血奋战的一员虎将,素来性情耿直,刚正不阿。青年时代他在南昌大同中学投入反帝浪潮,后来毅然弃学,潜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参加黄道组织的横峰“岑阳学会”,1926年由黄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先民入党后,获得政治上的新生。他常说:“吾名先民,就是先为人民。”他在青板桥领导农民运动,成绩显著。大革命失败后,吴先民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参加了方志敏主持秘密召开的赣东北五县党员会议——“窖头会议”,随后同方志敏(化名汪祖海)、邵式平(化名余艳王)潜回横峰,做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7年冬,吴先民同黄球、铁壁、项春福、吴先喜等领导千余名农民革命团员,以青板桥为中心,参加发动了著名的“弋横暴动”。暴动胜利后,组织“农民革命团”,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一跃成为横峰县的革命领袖人物。当时,弋、横人民流传一首歌谣:
弋阳方志敏,横峰吴先民,领导共产来革命,都是为穷人。
在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军创立的战斗中,年仅20几岁的吴先民身先士卒,出生入死,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他先后担任中共横峰县委书记、上饶县委书记、信江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代政委、红十军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后被调任赣东北赤色警卫师政委,当选为中共信江特委委员、赣东北省委委员,成为赣东北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始人之一。他赢得了赣东北广大军民的尊敬和爱戴,当时苏区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我们的民崽”[注]《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5页。,并流传着一句民谣俗语:横峰有了吴先民,不愁天下不太平。
然而,硝烟中突现一片乌云,“左”倾中央派遣的“钦差大臣”——中央代表曾洪易来到赣东北。
二、苏区“肃反”的背景与起因
1931年1月,王明依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支持,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推出了两项“左”倾纲领,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夺权,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共中央的统治。
其时,赣东北党和红十军正在方志敏、邵式平的领导下,应对国民党军的“围剿”,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回师赣东北苏区。时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的吴先民,则奉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赣东北苏区的军事斗争。赣东北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从弋阳芳家墩迁至横峰葛源。随后,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任特区军委主席。从此,葛源这个阔大、幽美的山村,成了赣东北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个时期的赣东北苏区局面红火,发展势头很好。
同年4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委派万永诚、倪宝树来到赣东北苏区。5月,在葛源召开了赣东北特委扩大会,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中央代表指责赣东北党“是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者”,“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认为“赣东北三月来的主要危险是右倾”,“要审查和调换各级党部的干部”等等。[注]中共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之二《关于党的组织问题》(1931年5月9日),江西省档案馆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随即,会议改组了赣东北特委,由万永诚任特委书记,倪宝树任红十军政委。中央大员特别关注“肃反”,对“肃反”作了相应的布置,提出“建立肃反委员会的独立工作”,“准备各级政治保卫局的建立”等。[注]中共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之三《关于苏维埃工作》(1931年5月9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85页。
由于万永诚等初来乍到,对苏区各方面的情况还不了解,加之特委组织和红十军的领导没有大的变动,所以尽管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对苏区的实际工作影响并不大,王明“左”倾政策还未完全贯彻下去,肃反工作也没有真正开展起来。这个时候,赣东北的党和红军仍然保持以往的工作计划和传统,一面发展和巩固老苏区,一面进军闽北,攻克崇安重镇,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正因为如此,“左”倾中央认为赣东北党执行四中全会精神不彻底,万永诚等不得力,故加派曾洪易以“中央全权代表”身份来到赣东北加强领导,掌控局面。同期到达的还有聂洪钧、杜石公、关英、吕振球等人。
曾洪易等1931年7月中旬到达赣东北苏区。
曾洪易,又名曾宏义,江西万安人,资历颇深。大革命时加入中共,曾任江西团地委书记,后赴苏联留学,同王明等人结识,回国后受到“左”倾中央的青睐,派赴赣东北苏区。
曾洪易下车伊始,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在葛源主持召开了赣东北特委扩大会,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全盘否定赣东北党的工作。8月14日,曾洪易即向王明中央呈报一份关于赣东北苏区“整个的详细报告”,指责以方志敏为首的赣东北“苏维埃政府工作中的富农路线和富农影响特别厉害”,党在政治上“有许多还依然是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当然还是右倾”,突出表现在没有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党内的地方观念、封建关系、小派别的斗争,也是党内目前极严重的危险,因此决定要深入开展“反富农路线的斗争”,对赣东北的党和苏维埃政府“必须厉行一次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的彻底的改造”,“在斗争中将一切腐化机会主义的分子从苏维埃机关中彻底的肃清出去”,在“深入反立三路线、反富农路线的斗争中去改造党的阶级基础及其领导成分”,并声称要“在最短时间内”将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成立起来”,等等。[注]《曾洪易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14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版,第348、351-352页。
曾洪易慑于方志敏在赣东北苏区的威望,不敢放肆,就把眼光盯在邵式平(军委会主席)、黄道(组织部长)等人身上。他胡诌红十军“军委会的领导还依然是很弱的”,“党特委的组织部并不能在实际上起中心的组织作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等,进而向中央表示“我们现已决计要有计划有组织的改造这些领导成分”。[注]《曾洪易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14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349、350、348页。
为此,曾洪易指令“改组”赣东北特委。他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在特委扩大会上指定万永诚为书记,聂洪钧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这样,黄道、吴先民、方志纯等被排斥在特委之外。在红十军内,则撤销了舒翼的红十军参谋长、吴先民的红十军政治部主任职务,指定杜石公、吕振球接任。于是,王明指派的“钦差大臣”们,都被安排进了赣东北党和军队的领导班子中。更有甚者,曾洪易在特委之上,增加了一个“有权决定一切”的中央全权代表——曾洪易,又说红军是中央的,应直属中央代表曾洪易指挥。此外,又在特委常委内组织了一个由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组成的“三人主席团”,“三人主席团”有重大问题须向中央代表请示,由中央代表曾洪易拍板定夺。这样,就把赣东北党和红军的创始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等排斥于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之外。方志敏虽然还保留有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头衔,却被剥夺了对赣东北党和红军的指挥权。曾洪易则俨然成了赣东北党与红军的“太上皇”。
改组特委和红十军领导机构以后,曾洪易继续双管齐下,一手抓“改造”,一手抓“肃反”。曾洪易在赣东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声称:“最近在苏区内又破获了反动[派]的活动,如横峰、贵溪都破获AB团的组织。”“AB团”的所谓“罪行”,“主要是利用村乡工作上个别的错误与弱点,鼓动群众反对村乡苏维埃与企图打入红军,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注]《中共赣东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1931年9月20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371页。曾洪易所说的“AB团”,实际上是吴先民领导组建的“农民革命团”等革命群众组织。
1932年3月,鄂豫皖苏区的“肃反经验”传到赣东——张国焘奉“左”倾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身份到鄂豫皖苏区“加强领导”,在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杀害了同张国焘有工作意见分歧的军长许继慎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
曾洪易闻之,立即加快了“肃反”的步伐,拉开了“肃反”的铁幕!
1932年3月27日,曾洪易指令赣东北省委颁布了《肃反宣言》,提出“肃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的口号,发出“肃反”紧急通知,规定从5月24日至30日为“肃反运动周”,进行“肃反突击”。通知竟提出破获反革命组织时,“可交群众审判”,反动首领“可交群众大会举手枪决”,从5月11日发出的《团赣东北省委关于肃反运动周工作通知》中还可见及,对于所谓在政治保卫局的要犯,可以“动员青年群众公审和处理”,这就是为了肃反积极性,竟然把生杀大权“下放”到了“青年群众”,真是荒唐至极!
于是,一批干部进入曾洪易的“肃反”视线。
赣东北苏区“肃反”的起因是肃所谓“健康会”。
这时,恰逢一批从上海派到苏区来做文化工作的潘务行、做工会工作的何东樵,做互济会工作的罗子华,以及余一之、徐文壁等知识分子来到赣东北苏区。他们到来后,对苏区工作多有歧见,喜好议论。尤其“对曾洪易及省委领导不满,曾便对他们怀疑”;“他们在闲谈中提倡健康,要洗脚、爬山等,曾认为是以‘健康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活动”。[注]邵式平、汪全祥、胡德兰等:《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1945年3月),《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曾洪易还诬指潘务行等“企图利用健康会的组织,拉拢改组派、第三党于一炉,进行其反革命的活动”。[注]《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肃反工作的决议》(1932年7月10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452页。于是,肆意罗织罪名,逮捕逼供。曾洪易进而于5月在葛源主持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以“健康会”的莫须有罪名,将潘务行等上海派来的知识分子处以极刑!
从此,惨痛的赣东北“肃反”开始了!
为了造成“肃反”的声威,曾洪易还制定颁布了《赣东北省委关于肃反工作的决议》、《反革命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自首案例》等文件,层层传达、贯彻。随后,赣东北民间中的兄弟会、姐妹会、红枪会、大刀会、同心会等封建会道组织,都被视作“反革命组织”,受到严厉处置,被关押、滥杀者相当多。
三、吴先民葛源罹难
赣东北苏区的肃反运动,在中央“九月指示信”的政治旋风中,掀起肃反的高潮。
1932年9月25日,“左”倾中央给曾洪易和赣东北省委发来一封指示信。
这封信非同小可!
指示信表彰了曾洪易的“肃反”成绩,说中央“审查了你们寄来的一些文件,认为你们在执行过去中央所给与你们的指示上,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同时指出,“然而,我们认为在赣东北苏区反革命组织的总的领导机关,还是没有破获。……我们不能相信在赣东北苏区内没有像闽西、中区、鄂豫皖、湘鄂西各苏区那样总的领导机关,零星的破获固然需要,然而我们必须从这种零星的破获,一直追踪到总的领导机关。”[注]《中共中央给曾洪易并转赣东北省委的信》(1932年9月25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上,第470页。“左”倾中央还指示赣东北党“特别应该注意——要把追踪反革命“改组派”、“AB团”的“总的领导机关”,同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结合起来。
根据中央这一指示,首先映入曾洪易“肃反”眼帘的是吴先民。
如前所述,吴先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军的优秀指挥员。这个性情耿直、刚烈的男子汉,在担任红十军代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赤警师政委期间,就对曾洪易的所作所为甚为不满。他目睹曾洪易等“钦差大臣”来到赣东北后,在政治、组织、军事、肃反等方面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政策,造成根据地领导不和、环境恶化、军事失利、干部消极、群众动摇的局面,忧心忡忡,不时在同志间有所议论。
吴先民都说了些什么呢?这里有当时的省委文件记载为据:一是说过“第一次成立东北特委”(即曾洪易到赣东北后7月改组特委)时,“地方干部参加的很少”,提出“要黄道参加特委”,不然的话,“这个特委不能领导东北的革命”;二是批评了曾洪易的持久围攻国民党军坚固的堡垒的决策,认为“持久围攻堡垒是冒险攻坚,是碰钉子的战略”;三是反对排挤和架空方志敏、邵式平对赣东北苏区的领导,提出了“拥护方、邵”的口号;四是议论过“中央派来的同志谈谈理论是可以,实际斗争不及地方干部”等。[注]《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肃反胜利中的经验教训》(1932年10月23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39页。这就是吴先民的全部“罪状”。
吴先民的这些坦直的言论和意见,有的是在会上直言不讳提出的,有的是在高压下与同志私下议论的,不料被人告密,反映到曾洪易那里去了。
曾洪易一听,大动肝火。尤其是吴先民说“中央派来的同志谈谈理论是可以,实际斗争不及地方干部”,认为是直接针对他这个“中央派来的同志”,遂怀恨于心,决意在“肃反”中拿吴先民开刀。当时在苏区的邵式平等人回忆说:“吴先民同志亦因对曾洪易的领导与路线不满而后有议论,曾认为是反革命的派别活动,捕捉吴先民,实行逼、供、信。”[注]邵式平、汪全祥、胡德兰等:《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1945年3月),《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2-33页。
尤其是曾洪易为了进一步确定吴先民的“罪行”,还不惜罗织、编造其所谓犯罪事实。
1932年8月中旬,红十军与赤警师组织部队曾夜袭贵溪周坊国民党驻军。战斗开始后,曾毙敌三四百人,后因战场联系不畅致使周坊夜战未获全胜。据时任红十军政委的聂洪钧回忆,“在贵溪地区的一次作战过程中,原定作为预备队的一个营不见了,吹号也调不来。到战斗结束后才在一个很远的山沟找到这个营。于是我和建屏同志(周建屏,红十军军长——引者注)当即决定撤营长的职,送葛源审理。”[注]聂洪钧:《关于闽浙赣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几个问题》,《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49页。
曾洪易在葛源接到周坊夜战的报告后,认定“此事有反革命破坏”。于是,他布置肃反委员会审理此案,并居心叵测地暗示要审出赤警师政委吴先民与此事有牵连,是反革命“改组派首领”。肃反委员会领旨即对这个营长严刑逼供,这个营长招架不住,“在讯问中,他承认自己是个反革命,并供说吴先民(赤警师政治委员)也是反革命。”[注]聂洪钧:《关于闽浙赣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几个问题》,《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49页。
于是,吴先民被撤去赤警师政委一职,降任上饶县委书记。
9月底,即中央“九月指示信”到达后,曾洪易即以此为“尚方宝剑”,诬陷吴先民是“改组派省委书记”,下令在上饶县坑口将吴先民逮捕!
吴先民被捕后,关押在葛源军校杨家祠堂。曾洪易指使肃反委员会对吴先民施用酷刑,大搞逼供,吴先民始终威武不屈,拒不认罪。
吴先民有个工作笔记本,上面记着赤色警卫师干部和上饶县各区区委书记、区苏主席的名字。肃反委员会从吴先民身上搜出后送给曾洪易看,曾洪易断言这是“改组派”名单,下令将这批干部通通抓起,指名逼供。在审讯时宣布:“只要说出一个名字,就可以宽大”。拿到口供以后,就把这些人杀掉了。
吴先民笔记本中的这批干部,成了“九月旋风”中的肃反对象!他们临死前,谁也不知道“改组派”为何物!
吴先民被囚后,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闻讯,大吃一惊。他立即来到曾洪易住地,质问曾洪易说:“为什么逮捕吴先民?”曾洪易说:“我们在审讯上饶县的‘改组派’时,犯人供认吴先民是赣东北‘改组派’省委书记!”方志敏立即严正指出:“吴先民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实党员,不可能是‘改组派’!单凭口供,不能乱抓人!”
曾洪易立即摆出“中央全权代表”的架式,气势汹汹地说:“乱抓人?中央九月指示信你难道没看过?现在有人指控吴先民是‘改组派’省委书记,不抓吴先民,怎么追踪、破获反革命‘总的领导机关’?中央指示还执行不执行?!”
善良、正直的方志敏忧心如焚。这时,他正值痔疮发作,天天流浓血,步履艰难,坐凳只能坐半边,本来已和红军医院医生说好,准备立即做切除手术的,但一想到吴先民被捕,他立即打消了住院治疗的念头。他后来在狱中回忆此事时写道:“我想在肃反紧张的时候,我个人却睡在医院里去割痔疮,心里怎么会平安下去?仍回复医生暂且不割,等有暇时再来,泻剂也退还医院了。我也常到保卫局审问提来的‘反动派’,在审问时,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这时,方志敏不顾痔疮造成的痛苦,抱病来到囚禁吴先民的地方探监。吴先民见到方志敏后,感激涕零。随即,他怒斥了曾洪易的诬陷,说:“曾洪易这帮家伙,逼我承认是‘改组派’省委书记。真是天大的笑话!我连‘改组派’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志敏同志,你是了解我的呀!……”
方志敏强忍住自己的情感。他深知这位老战友是赤胆忠心的好干部。可眼下,肃反是曾洪易直接掌控、单线联系的,他方志敏无权过问。他心里很痛,充满难言之隐,挥泪而去。吴先民望着方志敏远去的背影,不禁潸然泪下。
在吴先民的问题上,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同曾洪易几次在省委常委会上争论。方、邵认为:“吴先民等是在长期斗争中考验过的忠实党员,不会是什么‘反革命’、‘改组派’。”“有人招供他是‘改组派’省委书记,难免不是反革命的诬陷。”曾洪易则认为方、邵对肃反“动摇”,是“调和主义”和“机会主义”,竟对方、邵强制隔离、写声明书,要在群众中“公布”。
是年10月23日,曾洪易就吴先民的问题,专门作了一个《赣东北省委肃反胜利中的经验教训》的决议,在决议中一方面认定吴先民是“反革命的首领”,是红十军中改组派的发起者,在开赣东北省中共代表大会是吴先民组织了改组派的省党部,到上饶时又作为改组派的特派员企图把上饶造成改组派的根据地,在赤色警卫师是企图将其完全变成为改组派的武力,“实行反革命暴动的阴谋”,“来破坏党破坏红军破坏苏维埃”;另一方面,点名批评了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声称:“现在如果谁还对反革命的吴先民表示怀疑,这不仅是简单的思想上的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活动的错误,而且他的本身事实上都是自觉的反革命。”[注]《赣东北省委肃反胜利中的经验教训》(1932年10月23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38页。换句话说,谁怀疑吴先民是反革命,谁本身就是反革命。这就是曾洪易的逻辑!随后,曾洪易决定“广暴公审”,即在广州暴动五周年之际,杀害吴先民。
1932年12月11日这一天,寒风呼啸,阴霾满天。
葛源,这个秀美的大村庄,本是赣东北苏区大本营,闽浙赣省委、省苏的所在地,苏维埃政权的红色首府,这一天却笼罩着阴暗、萧瑟的恐怖气氛。
吴先民被五花大绑,赤膊捆在葛源枫树村的大樟树下。苏区干部和父老乡亲们,聚集在大樟树四周,人山人海,万头攒动。
公审大会开始时,曾洪易宣布:“吴先民是一贯反对中央、反对省委,在赤色警卫师和上饶县分裂党的反革命,AB团、改组派的骨干分子。”省委决定公审后“处决”!
这时,“方志敏上了一下台,下台眼泪都落出来了,随后他回村去了。”[注]徐大妹:《闽浙赣苏区斗争忆实》,《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00页。
方志敏深知:这是“太上皇”掌控的省委常委不可改变的决定,曾洪易是竭力要执行“公审”处决的。他已多次据理力争,无力回天。他满含深情地看了吴先民一眼,便与他泪别了!
被绑在樟树下的吴先民,在曾洪易等人的淫威下,面不改色,大义凛然。他大声呼喊:“乡亲们!我不是AB团、改组派,更不是反革命!我是冤枉的!冤枉的!!”。吴先民怒气冲天,还用一句土话骂了曾洪易。曾洪易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动刑。随后,吴先民被梭标、乱刀活活捅死、砍死!吴先民临死不屈,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注]徐大妹:《闽浙赣苏区斗争忆实》,《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00页。
吴先民死时,年仅27岁。
四、“永远记取这惨痛的一幕”
吴先民被错杀之后,如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汪金祥所言:“以曾洪易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为了向中央报功,便不分青红皂白,刑讯逼供,捕了又捕,造成肃反扩大化,以致冤枉死了很多好人,造成惨痛的损失。”[注]汪金祥:《对赣东北根据地几个问题的回忆》,《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23页。许多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群众斗争领袖和重要干部,以“AB团”“改组派”“第三党”“罗章龙派”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捕杀。
他们当中有:弋、横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余杰、洪坤元、甘广平;红十军参谋长舒翼;共青团省委宣传部长汪明、副部长胡仁辉,组织部长张天松;红军总医院院长邹思孟,省苏政府秘书、《工农报》总编辑徐跃;闽北苏区创造者陈耿、赤卫军军长徐福元、区苏秘书长徐常、党校校长熊祺等。还有,“县、团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出身的负责干部大部被杀掉。弋阳、德兴、乐平的整个县、区、乡、村干部也大部被杀掉了。甚至把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干部和交通员也调来根据地,加以杀害。……弋阳全县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一个。”[注]《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104页。
在肃反狂潮中,赣东北团省委书记、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竟被吊了三天三夜,赣东北军委书记邵式平也受到审查。……
曾洪易及其推行的“左”倾肃反政策,给赣东北的党、军队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极为深重、无可挽回的。
邵式平等在延安回首往事,谈及“惨痛的闽浙皖赣肃反”时,沉痛地说:“由于乱捕乱杀,大伤了党的元气,造成干部动摇逃跑,人人自危,使党内产生一种严重的恐怖现象。”“这完全是曾洪易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与宗派主义危害党和革命的罪恶。”[注]邵式平、汪金祥、胡德兰等:《闽浙赣(赣东北)党史》(1945年3月),《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3页。
赣东北的肃反惨剧,是在方志敏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对此,方志敏后来在狱中进行了严肃的审思。他在遗著中写道:“我现在肯定的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很明显的我们是犯了‘肃反中心论、肃反扩大化和简单化’的错误。”“我与式平同志为吴先民问题,同时也就是为‘肃反需要慎重,不应刑讯’问题说话,就受到党的处分。”[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全集》,第75-78页。
可见,方志敏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的处境有多难啊!
铸成赣东北肃反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王明“左”倾中央的错误肃反政策所致,而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曾洪易的倒行逆施。
正如方志敏在狱中批评曾洪易时所指出的:“党的主要负责同志(指曾洪易——引者注),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庞然自大的以为自己什么都是正确的。”[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全集》,第75-78页。
曾洪易这个人,确实“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他自恃是中央代表,处处以“太上皇”自居,庞然自大,专横跋扈,心狠手辣,陷害忠良。后来,他在赣东北苏区斗争最危急时刻逃到南京,投靠国民党,沦为可耻的叛徒。
中共七大时,赣东北苏区及红十军吴先民等同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当年被错杀的一大批烈士的忠魂,可告慰九泉之下了。
江西省革命前辈、省长方志纯,生前撰文悼念吴先民烈士时,满怀深情地告诫后人说:“让我们永远记取这惨痛的一幕!”
赣东北苏区当年“惨痛的一幕”,是要永远记取的。但最重要的不是挥之不去,而是要从历史的教训中吸取智慧与定力,牢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经典论断,推进我们党的伟大事业永远沿着正确的航道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