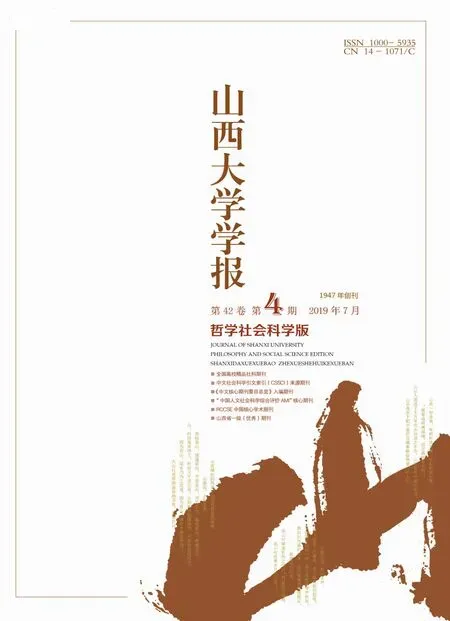舍勒的人格自律理论辨析
2019-02-12陈清春
陈清春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是现象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以下简称《形式主义》)是现象学伦理学的奠基性著作,其学术地位不亚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在《形式主义》中,一方面批判了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一方面建立了自己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或者说人格主义的价值伦理学。在“人格的自律”一章,他在批判康德理性主义自律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格主义自律观,即人格的“双重的自律”思想,从而完成了他“对伦理学的人格自律之概念进行奠基”[1]的现象学工作,即完成了他对人格自律概念的现象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本文拟将舍勒人格自律思想的主要内容、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犯的错误进行分析与辨析,并指出其完整的人格自律理论实际上包含着“三重的自律”。
一 双重的自律
舍勒的人格自律概念不同于康德的理性人格自律,因为他的人格概念是一个包括所有意识行为在内的精神总体,而理性仅是所有意识行为中的一种意识行为,理性人格也仅是人格总体中的一个方面,所以康德的理性人格自律仅是理性的一重自律,而舍勒的人格自律却是人格的双重自律。舍勒说:“所有真正的自律并不首先是理性的一个谓项(如在康德那里)以及不是作为分有一个理性法则性的X的人格的谓项,而首先是这个人格本身的一个谓项。但在这里必须区分双重的自律:对自身是善和恶的人格明察的自律以及以某种方式作为善和恶而被给予之物的人格愿欲的自律。与前者相对立的是无明察的或盲目的愿欲的他律,与后者相对立是被迫的愿欲的他律,它最清楚地包含在所有的意愿感染和暗示中。”[1]603-604即:自律是属于人格总体的一个属性而不仅仅是属于理性或理性人格的一个属性,所以人格的自律不只是理性的一重自律而是人格自身善恶价值的明察与愿欲的双重自律,与之相对立的人格他律则是无明察或盲目的愿欲和被迫的愿欲。
康德的自律观认为,纯粹理性本身,一方面作为“原则的能力”,是给意志提供一个普遍道德法则的立法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实践的能力”,是使意志的每一个行动都遵守普遍法则的守法能力,而纯粹理性的立法和守法能力就是意志的自律,所以康德说:“就理性能够规定任性而言,意志就是实践理性本身”[2],既然意志的本质就是实践理性,那么意志的自律就是实践理性的自律。可见康德的理性概念不仅取代了价值感受的原理功能,而且也取代了意志的选择与决定功能,这样的理性在实践中不仅起着指导的作用,而且还起着主导的作用,即是说,不仅指导着实践的善恶价值方向,而且还决定着实践的善恶价值属性,从而使得理性成为决定一个实践行为是否是“道德的”或“善的”唯一要素,由此他将除理性之外的其他一切实践要素都归之于质料性的他律。
舍勒指出,康德的形式主义是“把善的观念建立在一个愿欲的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上”[1]598,或者说是“把善的观念不是回归到一个质料的价值之上,而是回归到一个合法愿欲的观念之上”[1]257;如此一来,“伦常明察和伦常愿欲不再被区分,同时善和恶这两个词的意义被回归到理性人格所自身给予的一个规范法则上(‘自身立法’)”[1]605;因此,“他对‘伦常明察’的事实也是一无所知”[1]84。即是说,康德的自律观只有伦常愿欲的自律而没有伦常明察的自律,因为他对伦常明察的事实一无所知,即不懂得人格自身价值感受的直观明察是善恶价值的最终根源,从而没有将伦常明察和伦常愿欲区分开,把它们都回归到一个理性的合法愿欲之上,或者说回归到理性人格的自身立法所给予的一个普遍法则之上。舍勒认为,理性人格所立的普遍法则如果没有建立在人格自身的伦常明察之上,就不是真正的道德法则,因为真正的道德法则是价值感受的先天秩序原理,而不是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因此,人格价值感受的自身明察才是人格自律的价值基础,它决定了愿欲的自律。
舍勒的双重自律是康德以来最重要的自律理论,它与康德的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人格自律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理性的自身立法,而是价值感受的自身明察,从而一方面剥夺了理性对于人格自律的单一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区分开了感受、意愿与理性之间的本质界限。
第二,人格自律的普遍道德法则不是形式化的绝对命令而是质料性的价值秩序原理,从而将理性思维所给予的一个可普遍化的形式法则转变为价值感受的自身明察所给予的一个普遍性的质料原理。这两点就是舍勒的双重自律观在人格自律问题上所取得的最大理论成就。
二 明察的自律
舍勒将自身明察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自身是善和恶的人格”的一般性的明察,与之相对立的是“盲目的愿欲”;一种是对“每一个特殊的人格而言都有一个自在的善”[1]598的特定性的明察,与之相对立的是“价值的欺罔”。
在第一种情况下,自身明察是对人格自身的善恶现实属性的明察,即这个人格的现实属性既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但这种自身明察却不是相即的和真正的自身明察,因而建立在其上的“自律的人格本身绝非已经是一个善的人格”[1]604。即是说,自律的人格并不等于就是善的人格,它只是相对于“盲目的冲动”而言一般性的明察自律,在这种自律的情况下,恶的人格越是自律,其恶性也就越大。所以舍勒说“自律仅仅是人格的伦常重要性的前提”[1]604,而不像康德那样认为自律是伦常必然性的前提,即自律的人格就是道德的人格,他律的人格就不是道德的人格。在第二种情况下,自身明察是对人格自身的至善本性的特定性明察,即对每一个人格都先天固有的价值感受原理的自身明察,只有这种至善本性的明察才是真正的和相即的自身明察,并且只有建立在这种明察自律之上的自律人格才是善的人格。与此相反,“价值欺罔”则是作为人格至善本性的先天价值原理被后天的经验习性所遮蔽、颠覆或扭曲的价值感受状况,而对这种价值感受状况的自身明察其实就是第一种不相即情况的自身明察。但是,建立在价值欺罔之上的人格绝不可能会是一个善的人格,因为这样的自身明察并没有明察到人格的“自在的善”,并不具有自身明察的自律。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明察到人格自身的至善本性才具有明察的自律,才有可能是自律的道德人格;反之,任何不相即的自身明察都不具有明察的自律,都没有可能是自律的道德人格,所以都是人格的他律。
可是,舍勒却试图论证建立在不相即自身明察之上的人格也有可能是善的人格,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阐明所谓“总体人格”的“共同责任性”以及所谓“顺从”的德行。但他所发明的“总体人格”却是一个基于宗教信仰而不是一个基于现象学明察的错误概念,况且,“顺从”的行为无论所顺从的是什么,“顺从”本身都是一个典型的他律。
舍勒十分重视对“顺从”的道德论证。他说:“在所有‘顺从’的行为那里都没有那种自律的、直接的明察是被给予的,即那种被诫令须待实现的价值状况的伦常价值内涵的明察……尽管如此,‘做出顺从’的愿欲可以是一个完全自律的愿欲。”[1]609即是说,“顺从”的行为没有直接的自身明察的自律而仅有愿欲的自律。但舍勒认为,“顺从”也是双重自律的一个类型,否则它就不是自律的而是他律的“顺从”或“盲从”了,所以“顺从”虽然不具有直接相即的自身明察,但却具有另一种类型的直接的相即明察,即与“自身明察”相对的“异己明察”:“服从行为是一个自律的意志行为(不同于被一个暗示、传染或仿效趋势所征服),但它同时是异己明察的结果;但它也是一个明察行为,只要我们明察到,发布命令者所具有的伦常明察之标准要高于我们的伦常明察。”[1]97即是说,异己明察是对他人(即发布命令者)的伦常明察的明察,即直接明察到他人的道德水准要比自己的更高。
具体地说:“在伦常上有价值的顺从就在于,即使所有的顺从都描述为缺少对被诫令的价值状况的伦常价值的明察,对愿欲以及愿欲着的人格(或它们的‘职责’)的伦常之善的明察仍然是明见地被给予的……在这种情况中包含着对诫令行为之伦常价值的自律的、直接的明察,对被诫令的价值状况的伦常价值的间接的、他律的明察,但同时也包含着做出顺从的愿欲的完全自律。”[1]610即是说,尽管顺从者对所顺从的命令内容只能拥有间接的和他律的伦常明察,但他对所顺从的人格发布命令行为的愿欲(即行为的动机)却拥有直接的和自律的伦常明察,所以,“顺从”行为也是同时具有明察自律和愿欲自律的道德行为。也就是说,“顺从”行为虽然没有直接明察到自己本性的善,但却直接明察到了他人意愿的善,所以“顺从”他人意愿的行为就是一个善的行为。然而,异己明察也有可能是一个不相即的明察,“如果对做出诫令的权威或人格的善良的明察并不是完全相即的明察,亦即可能是一个受欺罔的明察,那么听从者对被诫令的价值状况的实现便有可能展示为一种对伦常的坏的实现”[1]611,但舍勒却认为,尽管这个行为“是坏的和有罪的,但招致这个坏的实现的却不是他,而是这个命令者,而他的顺从的伦常价值在这里始终没有受到损害。”[1]611这就是说,无论所顺从的诫令是善的还是恶的,“顺从”本身始终都是一个善的行为。
很明显,舍勒对“顺从”的道德论证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无论人们所顺从的诫令是权威的命令、传统的习俗还是宗教的诫令,无不是出于对权威、传统、宗教的信任、习惯或者迷信的结果,其中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道德明察。他所谓的“异己明察”也是一个难以成立的概念,因为人们不可能对他人的意识行为有任何直接的相即明察,或者说直观性体验,因而对他人的善良意愿的明察都不可能是直接的自律的明察。因此,既然“顺从”缺少了明察自律这个必要前提,那它就不可能是一个人格的自律行为,也就未必是一个道德的行为。
一般认为,康德的自律观是西方“主体性道德体系的诞生”[3]的标志。舍勒的双重自律观就是为了反对康德的主体主义。他说:“康德曾赋予他的自律概念以一个主体主义转向……唯有这个主体主义转向才会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一个以前的自律人格行为的价值内涵对个体而言他律的转递形式。”[1]605他认为,外在的他律原则也是以前人格自律行为的产物,其中包含着以前人格自律行为的道德内涵,但康德的主体主义否定了外在他律原则的道德内涵,因而也就否定了顺从传统、恪守律令以及追随榜样等他律行为的道德价值。舍勒反对康德的主体主义是为了论证他的“总体人格”或者说“伦常共同体”的总体主义思想。他把“总体人格”设定为一个“共同体的每个个体都具有的、在所有人中都同一的人格性”[1]607,即在一个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共同拥有的一个同一性的人格,但这个人格却不是一个个体人格的总和,而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立本质的个体性的总体。他以此来解决自爱和他爱、自身责任和共同责任之间的本质关系,即:自爱和他爱都奠基于神爱,自身责任和共同责任一起直接地被给予,一个人在自身负责的同时也对总体人格以及对其中的每个成员共同负责。[注]事实上,他爱的伦理实践就是最高类型的自爱,他爱的共同责任就是最高类型的自身责任,因此没有必要设定一个神学的前提以及设定一个独立的共同责任;而且也不存在具有独立人格性的总体,因为一切总体都是由个人组成的人格共同体或人格群体,人们在共同体的群体生活中相互负责,共同承担群体的善恶与功过。但是“总体人格”概念的错谬在他对“顺从”的道德论证中可见一斑,因为他认为“总体人格”也是一个独立的伦常价值载体,而且它是使“顺从”行为成为一个自律行为的前提。因为舍勒认为,“明察之路完全可以是由权威、传统和追随所提供的”[1]611,在这些外在的异己明察中,既有对诫令内容的他律明察也有对他人意愿的自律明察,但这些明察如果没有“总体人格”的理论设定,也就在理论上得不到有效的论证了。
在理论上,舍勒将人格自律区分为伦常明察和伦常愿欲的双重自律,同时又将伦常明察的自律区分为四种:
第一,对本己“自在的善”的相即的自身明察,其人格的自律是善的自律。
第二,本己“价值欺罔”的不相即的自身明察,其人格的自律是恶的自律。
第三,本己明察是不相即的但异己明察是相即的,其人格的自律是善的自律。
第四,本己明察是不相即的而异己明察也是不相即的“价值欺罔”,其人格自律是恶的自律。
其中,后两种就是舍勒所谓“顺从”的人格自律,他荒谬地认为,即使“顺从”的自律行为是恶的实现,也无损于“顺从”的道德价值,无损于它是一个美德。可是,如果一个人格的自律并不一定是善的,人格的他律也不一定是恶的,那么自律和他律在伦理学上的地位也就无足轻重了。在实践中,如果“顺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一种美德的话,那么就会为那些打着国家利益或宗教信仰的旗号所犯下的集体罪恶免除了追随者个人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而这些集体罪恶才是人类迄今所曾遭受过的最大灾难。
因此,只有对本己“自在的善”的相即自身明察才是真正的道德明察,才是真正的自明自律,因而才有可能是人格的道德自律。此外,所有不相即的自身明察都不是真正的道德明察,都不是真正的自明自律,其行为无论自愿与否都是人格他律,因而都不是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自明自律与自愿自律的双重自律才是人格的自律,其他都属于人格的他律。可见,由于舍勒不适当地扩大了明察自律的范围,从而就扩大了自律的范围而缩小了他律的范围,将他律只限于“无明察的或盲目的愿欲”和“被迫的愿欲”等比较特殊的情况。这是其双重自律理论的不足之处。
三 理性与双重自律
在人格自律问题上,我们应当肯定康德的主体主义而否定舍勒的总体主义,但同时也应当否定康德的理性主义而肯定舍勒的人格主义。舍勒的人格主义将明察自律和愿欲自律区分开,前者是感受的自明自律,后者是意愿的自愿自律,两者都不属于理性行为的领域,从而取消了理性在道德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他并没有忽视理性在实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以观念认识的形式指导实践的主观意愿与意志选择。因此,人格的自律是在理性认识指导下的自律。
首先,理性与自明自律之间是认识关系。人格的自身明察不同于理性的观念性认识,而是价值感受的直观性体验,但它以直接判断的形式反映在理性认识中就是“观念的应然”,即“所有具有肯定价值的东西都应当存在,所有具有否定价值的东西都不应当存在”[1]249的应然原则。舍勒将应然原则区分为两类:“在应然以内,我已经将‘观念的应然’区别于所有其他那些同时展示着对一个追求的要求和命令的应然。但凡谈及‘义务’或‘规范’的地方,指的都不是‘观念的’应然,而已经是它的这些向某种律令之物的分类化。这第二种应然依赖于第一种应然,因为所有义务始终也都是一个意愿行为的观念存在应然。”[1]245-246即:一般意义的观念应然和特殊意义的义务与规范的应然,而义务与规范的应然是观念应然在追求或意愿领域的命令化或律令化,属于次一级的观念应然。[1]258
根据舍勒对人类群体生活的“凝聚原则”和“契约原则”“共同责任”和“义务”以及“规范”的本质区分,我们可以把应然原则区分为责任原则和义务原则两类,而律令则是义务原则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形式。责任原则和义务原则的区别主要是:
第一,责任原则是他爱原理的直接反映,是出于自然情感的凝聚原则,而义务原则是他爱原理的间接反映,是出于理性人为的契约原则。
第二,责任原则的价值内涵是人格价值和自身价值,而义务原则的价值内涵是实事价值和后继价值。
第三,责任原则是自明性的自觉原则,是基于自身明察的自律原则,而义务原则是经验性的强制原则,是基于理性认识的他律原则。
第四,责任原则是面对群体中各个成员的原则,而义务原则是面对群体中各类组织机构的原则。总之,责任原则是自明自律的原则,义务原则不是自明自律的原则。
然而义务原则及其律令的最终价值根源仍然要回溯到人格的自身明察之上,正如舍勒所说“唯有当一切律令(也包括绝对律令,倘若有这种律令的话)都回归到一个观念的应然之上时,并间接地回归到那个从属于它的价值之上时,这些律令本身才是有正当理由的律令”[1]258,即所有义务原则及其律令的正当性都直接地奠基于责任原则并间接地奠基于他爱原理。也就是说,义务原则及其具体化律令的正当性理由最终来源于人格的自身明察。另一方面,从责任原则和义务原则的价值内涵上看,由于实事价值从属于人格价值,后继价值奠基于自身价值,这就决定了两类原则之间是从属与被从属、奠基与被奠基的关系。
但是人格的自律与他律并不取决于两类原则的不同本质,而是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本质关系是不是自明自律的。人格自律的首要条件是人格至善本性的自明自律,而人格至善本性的自明自律首先直接地体现为责任原则的自明自律,其次通过责任原则间接地体现为义务原则的自明自律,这就是责任原则与义务原则之间的从属关系或奠基关系的自明自律。在这种情况下,义务原则的强制性、他律性本质特征就相对地具有责任原则的自觉性、自律性特征,也就是说,对群体中各类组织机构所承担的强制性义务就被上升为对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自觉性责任了,这种现象可称为“义务的责任化”。所以舍勒说:“只要我们自身明见地明察到,一个行动或一个愿欲是善的,我们就不会谈论‘义务’”[1]231,因为义务已经被“责任化”了。与此相反的是“责任的义务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义务原则不具有任何自身明察,而且责任原则也丧失了自己原有的自身明察,其自觉性、自律性的本质特征就被异化为义务原则的强制性、他律性特征,也就是说,对群体中每个成员所担负的自觉性责任就被下降为对群体中各类组织机构的强制性义务了,而这种责任被“义务化”的情况就是人格的他律。因此,人格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区别首先在于其理性应然原则是“义务的责任化”还是“责任的义务化”,而理性应然原则的区别又在于理性对他爱原理的认识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直观的还是经验的,即是不是建立在人格自身的道德明察之上。
其次,理性与自愿自律之间是指导关系。意愿是客观的价值追求或意欲在理性中的主观反映,前者的意向对象是价值图像,后者的意向对象是前者的价值图像反映在理性中的价值观念;而理性则是以观念应然的形式指导人们判断自己的某个意愿是否应当成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或者在多个意愿中判断哪一个更应当成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事实上,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其实践活动无论是日常的饮食起居还是为人处世的人际交往,除了舍勒所谓“盲目的冲动”“暗示、传染或仿效”等较为特殊的非理性意愿,一般都是在理性意愿指导下的自愿行为,即意愿(或愿欲)的自愿自律。但由于理性用以指导的观念应然有人格道德价值的自身明察与非自身明察两种情况,自愿自律也就有自身明察的自愿自律与非自身明察的自愿自律两种情况。舍勒说:“完全相即的、自律而直接的对什么是善的明察,必然也设定了对那个作为善的而被把握到的东西的自律愿欲;但反过来自律的愿欲却并不也共同设定了在它之中作为‘善的’而被意指的东西的完全直接的明晰性。”[1]609即是说,凡是自明自律的都必定是自愿自律的,但并非凡是自愿自律的都必定是自明自律的。其中,只有前者才有可能是自律的人格,即只有自明与自愿的双重自律才有可能是人格的道德自律,此外都属于人格的他律。
总之,尽管理性不是人格自律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却是人格自律必不可少的前提,一方面它以观念应然的形式直接反映了人格道德价值的自身明察,另一方面它又以观念应然的形式指导主观意愿的价值方向,所以舍勒的人格主义伦理学并不会走向非理性主义。
四 人格的三重自律
仅有自明与自愿的双重自律只是具备了人格自律的可能性条件,还不是人格自律的现实存在。人格自律除了要具备价值感受的自明和意愿追求的自愿两个条件外,还应当具备意志做出选择与决定的能力条件,亦即意志的自能自律,所以完整的人格自律应当包含着自明、自愿和自能的三重自律。
事实上,康德的自律本身就包含实践理性的立法和守法两个环节,即已经包含着双重的自律:立法是“意志”(Wille)的自律,守法是“任性”(Willkür)的自律。在康德那里,意志的含义有广义、有狭义,广义的意志包括立法和守法两个环节,狭义的意志即立法环节。首先,立法环节的“意志”作为被理性所规定的意志,其本质内涵实际上指的却是理性的意愿。例如康德说:“假如根本没有充分规定意志的纯然形式的法则,那么,也就没有任何高级的欲求能力能够得到承认了。”[4]即:被理性法则所规定的意志就是高级的欲求能力。而高级的欲求能力作为理性法则所规定的欲求就是理性的意愿。如他说:“如果欲求能力的内在规定根据,因而喜好本身是在主体的理性中发现的,那么,这种欲求能力就叫作意志。”[2]220即:作为理性的高级欲求或者喜好的“意志”的本质内涵实际上是低级欲求或者喜好反映在理性中的观念形式,即理性的意愿。其次,守法环节的“任性”是意志在行动中根据“意志”所立的普遍法则做出选择与决定,而这个与行动相关的“任性”环节才是意志的真正本质。康德说:“意志就是欲求能力,并不(像任性那样)是与行动相关来看的。”[2]220即:作为理性欲求能力的“意志”(Wille)实际上指的是意愿,而作为行动的“任性”(Willkür)指的才是意志。因此,康德的立法环节是意愿的自律,守法环节是意志的自律。
舍勒认为,康德的自律观在立法环节上没有将伦常明察和伦常愿欲区分开,只有伦常愿欲的自律而没有伦常明察的自律。由此他提出伦常明察和伦常愿欲的双重自律,伦常明察属于价值感受的直观体验,伦常愿欲属于理性的意愿。可见,舍勒在这里的“愿欲(Wollen)”概念与康德狭义的“意志”概念一样实际上指的都是意愿,即意欲(Wollen)的观念化。[注]“Wollen”,倪梁康通常译为“意欲”“愿欲”,有时译为“意愿”。但是,只有道德的自明与自愿的自律还不是完整的人格自律,还应当有做出选择与决定以及付诸行动的意志能力的自律。康德的观点是“他之所以能够做某事,乃是由于他意识到应当做这事”[5],即是说,一个人如果意识到他应当做什么,那么他就能够做什么。舍勒指出康德的思想逻辑是:“我们必须首先聆听‘实践理性的声音’,它使我们断言地承担起一个做的义务,而后才假言地达到这个设想:我们也能够做我们应当做的”[1]286,即是说,我们能够做的是从我们应当做的假设中推导出来的。舍勒反对康德从“应然”推出“能然”的观点,同时也反对大多数古代哲人从“能然”推出“应然”的观点,认为两者都是独立地被直观体验到本质事实。他说:“对观念应然的体验与能然是同样原初地并互不依赖地建基于最终的直观之中,因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把一个回溯到另一个之上。”[1]287其中,“应然”的原初直观体验就是人格道德本性的自身明察,而“能然”的原初直观体验则是“意志力(Willensmacht)”[注]倪梁康译为“意愿力”。的体验,亦即意志能力的自能自律。与“能然”相对的是意志的“无能”或“无力”的体验。
意志的“无能”或“无力”的情况通常是:我们已经自身明察地认识到应当去做(或不去做)某件事,也愿意去做(或不去做)这件事,但意志却“无能”或“无力”去做(或不去做)这件事。这不是因为缺乏身体运动的机能而是因为缺乏意志做出选择与决定的行动能力,所以即使我们已经具备了自明与自愿的双重自律,但我们的人格仍然不是自律的。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我们的意志“无能”或“无力”抵抗他人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外在压力而被迫地去做(或不去做)自己不愿意(或愿意)去做的事。显然,这种既“不愿”也“无能”的被迫情况也不是人格的自律。
可见,舍勒虽然没有把“能然”问题放在“人格的自律”章来讨论,但它显然是人格自律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环节。所以,只有具备了道德认识的自明、道德追求的自愿和道德选择与决定的自能的三重自律才是完整的人格自律理论。除此之外,都是人格的他律。
五 结语
康德所创立的自律概念既是其伦理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概念。如果说康德的自律观是西方伦理学主体主义的转向标志,那么舍勒的自律观可以说是西方伦理学人格主义的转向标志。这个转向主要表现在:他将决定善恶的普遍道德法则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所提供的一个意愿的可普遍化的形式法则转变为人格价值感受的自身明察所提供的一个普遍性的质料原理。这是其人格自律理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他出于宗教的理由却试图将顺从某种外在因素的人格他律也转变为人格的自律,从而提出了缺乏现象学本质明察的所谓“异己明察”和“总体人格”的概念。这是其人格自律理论的主要失误。然而从总体上看,舍勒的三重自律理论毫无疑问是目前结构最为完整、内容最为全面的人格自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