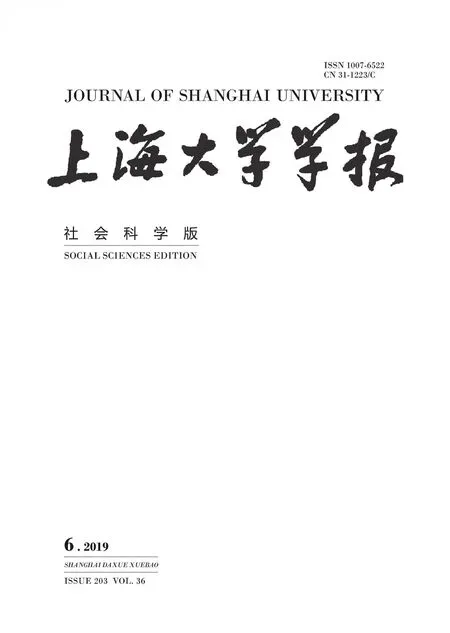英国文学批评学科的谱系学
2019-02-12陶水平
陶 水 平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昌 330022)
一、英国文学批评学科的前史:近代古典语文学及其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先声
众所周知,西方文学批评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诗学和诗艺,它们构成了西方文学批评学科的文化原型,当然亦成为英国文学批评的文化原型。但本文不拟讨论古希腊罗马的诗学和诗艺,也不拟讨论英国近代诗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理论,因为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极为丰富。本文将学术目光置于英国文学批评学科的前史,即近代英国大学人文教育机构中的英国古典语文学研究,探讨英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是如何既直接脱胎于古典语文学又如何超越古典语文学的。然后,探究英国文学研究是如何从英国大学近代人文教育的边缘走向中心,英国文学批评是如何学科化或如何构型自己的现代学术形态的。最后,简要探讨英国文学批评如何受到随后的英国文化研究之挑战,英国文学批评如何走向文化批评的。本文希冀通过上述英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谱系学追溯,获得对文学理论学科发展规律的某种认知和镜鉴。
古典学(Classics Philology)是一门以研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对古希腊罗马文明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综合性研究的学问,在西方教育、文化和学术传统中具有崇高地位。直至20 世纪早期,古典学一直是西方最主要的人文学科,时至今日仍然是西方人文学科的基石。[1]与欧洲其他各国一样, 近代英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中心不再是神学教育,而是以古典语文学教育为核心的自由博雅教育。在英国文学批评兴起之前,英国学术界对于文学的研究依附于或寄存于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这种学术形态之中,尚未取得独立的学科形态。因此,本文的探讨就从英国近代大学的古典学或古典语文学研究开始。笔者不是外语专业出身,借鉴并综合有关的研究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古典学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或称古学、古代通学、(1)张弢先生在《溯源与辟新——略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载于《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一文中将“Altertumswissenschaft”译为“古代通学”,传达了古典学的通义(整体义),有相当道理。古典语文学或古典文献学(英文为Classics、Classical Studies、Philology或Classical Philology;德文为Klassische Studien、klassischephilologie或Altertumswissenschaft),指的是对古希腊罗马文献的考证、校勘、修复、考古、整理、释义等,以此获得对古代世界的把握。其中,Classics、Klassische一词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意为“最高等级的公民”,引申为“高级、权威、典范”等。Pzhilology、Philologie则源自古希腊语,由“philos”(喜爱)与“logos”(言语)复合而成“Philologia”,最早见于柏拉图的《斐多篇》,本义为“爱语言、爱文字、爱文献、爱知识”等,其实也即是语文学。(2)本文对古典语文学的学术史考论资料主要借鉴和综合了以下论著:维拉莫威兹著《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约翰·埃德温·桑兹著《西方古典学术史》(张治译),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克拉夫特著《古典语文学常谈》(丰卫平译),华夏出版社,2012;雷蒙·威廉斯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威廉·汤姆逊著《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凌曦著《早期尼采与古典学》,中山大学,2012;以及我国当代学者刘小枫、甘阳、黄洋、张弢、张巍、沈卫荣、刘皓明、赵敦华等先生研究古典学的部分论文。
德国著名古典学家维拉莫威兹在其《古典学的历史》一书开篇就给古典学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古典学“从本质上看,从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看都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该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切地描述这种文明的起点与终结;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由于我们要努力探寻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方法也是浑然一体的。把古典学划分为语言学和文学、考古学、古代史、铭文学、钱币学以及稍后出现的纸草学等等各自独立的学科,这只能证明是人类对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种折中办法,但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这种独立的东西窒息了整体意识”。[2]1-2德国当代古典学家克拉夫特指出,直到19世纪,古希腊罗马时期及其文化都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研究领域,该领域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学科,即古代史——研究古希腊罗马及其他相关民族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史;古代考古学——研究古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古典语文学——研究保存下来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古典语文学的兴趣不局限于“美”文学,也包括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专业文献(哲学的、专门科学的、纪实学的),从事古典文献的修复、笺注和阐释。[3]在作者看来,古典学的核心是古典语文学。毫无疑问,古希腊罗马文献及其语文研究本身是古典学的源头,但是,古典学不是古典文献本身,而是对古典文献和文化的研究。在西方世界,古典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其源头可追溯至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学者们对古代希腊文献的校勘和整理。但是,古典学的真正发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和崇拜,进而热衷于研习和传播古典文化。换言之,古典语文学的雏形虽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时期就出现了,但毕竟被中世纪基督教和圣经研究遮蔽了近千年。因此,古典学真正发端于作为近代序幕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不仅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更是一种近代人文主义文化的新生,在这里,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复兴是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的世俗主义社会思潮的。可见,古典学或古典语文学的兴起应当直接归因于文艺复兴对西方古典人文传统的再次发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试图用复兴古代世界的文化来打倒封建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他们渴望将古代希腊和拉丁文化同化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古典学或古典语文学因而实际是近代西方诞生的一门综合性极强的现代性人文学科。(3)参见聂敏里:《古典学的兴起及其现代意义》,《世界哲学》2013年第4期;聂敏里《古典学的新生: 政治的想象,抑或历史的批判?》,《世界哲学》,2017年第1期。与“古典学”对举的是“东方学”(德文为“Orientalische Studien”,英文为“Orientalism”(或“oriental studies”)——近代西方学者对东方古代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古典语文学在近代意大利复兴之后,接着由意大利播撒于法国、荷兰、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集大成于18、19世纪的德国。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古典语文学进入所谓的“德国时期”,并开始有了一个规范和统一的学科名称。由于有众多人文主义者、新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推动,有众多作家、艺术家、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家以及考古学家的合力参与,德国古典语文学后来居上,古典语文学进入其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即“德国时代”, 以至于人们把古典学或古典语文学与德国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起的德国以古希腊为师,掀起了对古希腊文化的仰慕和研究的热潮,以求追赶师法古罗马的法国,先后涌现了多位举世闻名的古典语文学家。例如,温克尔曼在其《古代艺术史》一书中提出,希腊艺术的美在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4]此后的莱辛、歌德、席勒、赫尔德、施莱格尔、荷尔德林等德国作家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都有一种追慕古希腊的文化乡愁。作为学科的德国古典学的正式兴起始于18世纪后期的沃尔夫时期。“第一个以studiosus philologiae自况的人,是现代德国学派的创始者沃孚(通常译为“沃尔夫”)F.A.Wolf,1777年4月8日,他在哥廷根大学的入学考试表单里这么形容他自己(译者按:他入学时填报了一个大学并不存在的语文学系),从此即有‘语文学之诞日’一说。”[5]鉴于当时德国大学尚不存在这一专业,学校乃为此专门设置了这个新的古典学专业(studiosus philologiae)——正是沃尔夫沿用了“爱言”这个古希腊文的词语。沃尔夫遂被视为现代古典学学科的创始人,他研究的问题正是希腊化时代学者们特别关注的荷马史诗,其著作《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也成为现代德国的古典语文学学科的开山之作。时至1807年,沃尔夫对philologiae顾犹怅怅,盖因此名被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的同好们限定于仅文献研究一域,排除文艺鉴赏,而近代又屡屡被视作与语言研究之科学同义。沃尔夫因而创造了一个新词即 (Altertumswissenschaft,或译为“古学”“古代通学”),以取代传统语文学的“klassischephilologie”这一名称,意为“古代事物之科学研究”,这个新词遂成为德国古典学更为通行的学名。沃尔夫不仅力主古典语文学与神学分离,正式确立了古典语文学在现代德国大学中的学科地位,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历史科学(尤其是精神史、文化史、心灵史)的学科特性;同时将实证科学方法引入古典学研究,使之更具系统性。正是这种历史科学精神和实证科学精神滋养和哺育了几代德国学人,并产生了像赫尔曼、蒙森、维拉莫维茨这样的古典学大师。1809年,语言学家兼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被任命为普鲁士教育部长,改革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建立了以古典文化学习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进一步推动了德国古典语文学的发展。洪堡所创办的柏林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的蓝本,也是19 世纪德国古典语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正因为此,有论者指出,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西方古典语文学研究在19世纪的德国攀上了其学术史上的巅峰。[6]从19 世纪一直到20 世纪前期,古典学都是西欧乃至北美中高等教育的基础,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大学生乃至中学生的必修课程,当时很多西方学者和思想家都具有深厚的古典学素养,掌握这两门语言更是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必要条件。例如,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之差异》,而尼采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希腊悲剧的《悲剧的诞生》。后来居上的德国古典语文学又反过来影响了欧美各国,使之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学科。总之,西方古典语文学虽以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却并非一门古代学术,而是一门随着人类心智进步而发展的、以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现代属性的人文学科,它在近代西方人文教育中的地位,一如神学曾在西方中世纪所处的地位,具有现代性、整体性、语文性、历史性、实证性、人文性等特点。
英国近代文论虽然肇始于英国近代诗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的诗论。但是,近代英国诗论主要是以诗人作家的诗论文评和报刊评论文章的形式出现,进入大学学术机构的英国近代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是19世纪伴随着古典学的确立而出现的。西方18世纪中期出现了美学、艺术学,而且它们都进入到大学人文教育体系之中,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则晚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诞生,比美学、艺术学学科整整晚出一百多年。换言之,19世纪英国大学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尚无独立形态,而是借鉴德国古典语文学,依附于古典语文学研究之中。此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学于16世纪传入英国。1540 年英王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分别设立五个王室钦定讲座教授席位,钦定古希腊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便是其中之一。而经由德国人重建和振兴的古典语文学则是于19世纪进入英国的。“到19世纪末期,当英国的各个大学为古典学术设立了学位考试之后,古典学术的地位在课程中的位置凸显了。”[2]导言6古典语文学作为一门研究古代语言、历史、文学、哲学、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和考古的综合性研究,其中本就包含了语言与文学研究,并与其他研究交织在一起。但是,古典语文学范式下的英国文学宛若一位“戴着镣铐的缪斯”(The Musein Chains),隐匿在拉丁文和欧陆古典语文学强光投射下的阴影之中。以19世纪的马修·阿诺德为例,其文学研究仍包裹在古典语文学的学术形态之中,尽管阿诺德的文学研究开启了英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先声。马修·阿诺德曾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重视古希腊荷马史诗的教学,并取得了19世纪英国古典语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2]导言22在谈及当代语言学与历史学分离的学术态势时,有当代西方学者重申了古典语文学的学术特点,指出:“古典学联合各门学科的崇高理想几乎不能废除,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语言学似乎会陷入仅仅纯文学而已;同时,如果语言学不能与时代同行并从中获得新的动力的话,就是古老意义上的语言学概念也几乎难以维持。”[2]导言30
在此,本文选取马修·阿诺德作为英国近代时期的古典语文学研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加以深入分析。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盛期的著名诗人,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教育家和文化批评家,出生于文化世家。父亲托马斯·阿诺德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和公学校长,在古籍学阐释和德国传统史学的当代史意识方面开风气之先。阿诺德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属于中等阶层,但就文化地位而言属于有深厚古典学养和时代意识的上层文化贵族阶层,具有古代贵族般的精神旨趣和济世情怀,堪称一位不穿袍的贵族。马修·阿诺德主张向古人学习,认为荷马翻译者的职责应当是重建荷马的影响。他对荷马史诗深有研究,盛赞荷马史诗具有贯穿始终的崇高性和激扬性。而且,他还高度评价柏拉图,认为柏拉图是一位诗性哲人,《理想国》具有最高的诗性。马修·阿诺德于184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期间经常聆听纽曼主教讲经布道)。阿诺德的文化理念深受纽曼神父所发起的牛津运动宗教思潮的滋养,阿诺德在牛津读书时,正赶上这场史称牛津运动的天主教宗教改革运动。尽管阿诺德(及其父亲)不完全赞成这场宗教改革运动,而主张复兴以希腊罗马以及希伯来文化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宗教(以诗和艺术的“甜美与光明”为新的信仰核心,而非以上帝为信仰核心);但阿诺德仍高度激赏牛津运动,认为它代表了人类对于和谐完美理想的不懈追求。阿诺德认为,牛津运动的真谛在于深刻体现了牛津精神的基本品格,那就是对优美文雅的完美性的追求。它败北于中产阶级的庸俗的新教教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却虽败犹荣。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充满深情地写道:“当我坚持这样说的时候,我是完完全全浸淫在牛津的信仰和传统之中。我要大胆地说,我们对优美文雅的热爱,对丑恶粗鄙的憎恶,我们的这般情怀,才是我们靠拢许多失败了的事业、也是我们反对那么多成功了的运动的根本原因。这感情是虔诚的,它从来没有被整个地摧毁,它虽败犹荣。政治上我们没有成为赢家,没有能使我们的主要观点获得赞同,没有能阻止对立面的前进,没有成功地与现代世界同步行进。但是,我们已于不知不觉中对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我们培育起来的感情洪流冲蚀和削弱了对手们似已占领的阵地,我们保持着同未来的沟通联系。”[7]23,24数百年来,牛津和剑桥一直是为贵族子弟进行高雅的古典文化教育的最高学府。阿诺德以牛津精神传人的姿态表示,牛津运动虽然夭折,但其英魂永驻。他认为,纽曼博士所倡导的牛津运动及其文化精神之深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这场运动所滋养的追求美与雅的愿望,它所表露的对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之苛刻庸俗的反感厌恶,它那照得中产阶级新教教义的丑恶怪诞无处遁迹的强光,瓦解了自信的自由主义的地基,而为未来铺平了道路。牛津精神与文化朝着同一目标努力,牛津的美与雅的情操正是以这种文化的方式取胜的,而且还会长期地取胜。
马修·阿诺德处于牛津、剑桥等英国传统顶尖名校人文教育由古典语文学教育向英国文学教育转型的历史时期。据说,马修·阿诺德曾于1887年投票反对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切顿·柯林斯向牛津大学校务评议会提出在牛津设置英文学院的提案,因为他预感到,英国文学教学进入牛津,将会削弱古典语文学的权威。[8]但是,马修·阿诺德又是牛津历史上第一位用英文讲授古希腊诗歌的诗学教授(1857—1867),他还关注凯尔特语言,著有《凯尔特文学研究》(1867)。阿诺德盛赞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文学,而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颇有微词,认为其逊于当时的法、德两国的文学——根源在于当代英国学术和法德学术的差距,前者流于怪癖和任性,后者致力于从神学、哲学、历史、艺术和科学等各方面探究事物的实际。[9]阿诺德认为,希腊和罗马的古学绝非一种装点门面的浮浅的人文知识,而是一种探究事物真相的科学真知。他明确表示,完全赞同德国古典语文学家沃尔夫的观点,认为古典文化研究是一门严谨系统、追根溯源、探求真知的人文知识。[10]61,62阿诺德明确以古希腊文化标准来评价当代文明,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1869)一书的开篇即指出:“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7]11阿诺德主张以“美好与光明”的希腊精神来救治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技术崇拜与物质财富崇拜的非利士主义。阿诺德把当时的英国社会阶层分为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这三大阶级均有不满,指出他们各自的阶级陋习,分别称之为“野蛮人” (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即市侩)和“群氓”(populace),因而主张以文化精神来提升和改造英国社会各阶级。阿诺德批评其同胞只能感觉到头上的天空是铜铸铁打的,而不能更高远地仰望星空(没有更高远的精神追求)。尤其批评英国中产阶级只知现实功利的欲求,而缺乏高远的理想理念,缺乏对下层平民的同情或不能为他们指路导航,使社会面临无政府主义的危险。[10]168阿诺德提出了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思想和语言的精华,文化是智性和美德的统一,文化即是对内在完美与和谐的追求,文化是无私的、普遍的价值,文化是与物质文明截然对立的精神力量。文化即是让天道和神意通行天下。他主张效法法兰西学院,确立牛津、剑桥的文化权威,并由国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
作为英国近现代转型之际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化巨擘,阿诺德把文化提到极其崇高的地位。阿诺德在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这部最重要的文化批评著作中,常常用以下美好的词语来指称文化,诸如:“美好与光明”“追求完美”“人的精神在整体上的成长”“优秀的自我”等等。阿诺德所谓的文化,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知识与思想”,其核心是西方古典文化,同时也包括近代以来优秀的英国文学及欧洲各国文学。他重视西方古典学传统,倡导古典文学教育,使国民有机会接触古希腊罗马的优秀思想和文字。阿诺德在西方学术史上最早提出“两希文化”或“两希精神”说,认为希腊精神(Hellenism,亦译为“希腊文化”“希腊主义”)和“希伯来精神”(Hebraism,亦译“希伯来文化”“希伯来主义”)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两个重要来源,进而以此为线索描述了西方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并以此诊治英国近代以来非利士主义盛行的社会病因。阿诺德认为,“和一切伟大精神传统一样,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无疑有着同样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人类的完美或救赎”。[7]111他指出:“希腊最优秀的艺术和诗歌是诗教合一的,关于美、关于人性全面达到完美的思想,结合宗教的虔敬,成为其充满活力的运作的动因。唯其如此,希腊的优秀诗歌艺术对我们至关重要,能给我们以重大启示。”[7]17可见,马修·阿诺德的文学研究仍属于古典语文学范畴,尽管其古典语文学同时具有创新意识,强调希腊诗歌艺术精神的当代性。阿诺德高度重视古典文化的当代价值,他一方面强调要用两希文化精神(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尤其是追求“美好与光明”的希腊精神)来诊疗现代英国的文化病症,同时又对两希文化精神作了富于时代精神的新阐释,反复强调以两希精神为代表的“文化”即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7]147,208提出了一种以自由的、智性的希腊文化精神来提炼智慧和融会德性进而克服非利士主义的文化宗教理想。因而,其古典语文学堪称一种重视艺术审美和人性完美的新古典主义语文学,开启了英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新声。
阿诺德对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传播美好与光明的文化理想,英国就仍大有希望:“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是一个民族生命中的标志性时代,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天才的创造力流光溢彩的时代。”[7]31阿诺德所倡导的文化宗教乃是牛津追求美与雅的精神传统的发扬光大。阿诺德坚信,文化是一种高尚的理想,弘扬文化价值将使整个社会提升到一个美学境界和文化境界,从而使整个社会充满真善美。总之,阿诺德的古典语文学已然是一种既有深厚古典人文情怀又具有审美现代性品格的文化批评,开启了英国近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先声。19世纪下半叶,经过维多利亚时代马修·阿诺德等人的学术努力和知识建构,一种审美的文学观念已经开始在英国高校流行开来。正是阿诺德从根本上确立了一个具有很高文化价值的、审美化了的主导概念——大写的“文学”(Literature),并一直影响到后代。贯穿其所有著作中的,不乏一些这样的词语,诸如:“好的文学”“当前的英语文学”“法兰西和日耳曼文学”“伟大的文学作品”“文学名著的创造”。[11]37可见,与那些保守的古典语文家有所不同,马修·阿诺德既重视古典语文学,又认识到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特殊审美价值,成为从古典语文学研究转向英国文学研究的先声。阿诺德的这种新古典主义批评的学术传统甚至直接影响了T.S.艾略特,艾略特同样重视古典文化,尤其重视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马修·阿诺德在西方文化伟大传统的书写史以及现代文学观念和文化批评的确立过程中影响至巨,在英国文学批评学科发展史上起到了学术先知、文化导师和思想领袖的作用。
二、从古典语文学走向英文研究:英国文学批评学科兴起的四个历史契机
回眸英国文学学科形成史,不难发现,“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泛指对英语语言、文献、文化、历史、教育和文学的研究,与西方古典学或古典语文学(Classics、philology)相对而言,是19世纪英国兴起的一门近代人文学科,“英文研究”通常又译为英语学、英语研究、英国研究或英国文学研究。“英文研究”涵括英国人文研究的各个领域,但其核心是英语语言和文学研究。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作为现代英国“国学”的英语研究,在英国只有大约一百年的历史。英语研究的兴起和英国的“国运”是息息相关的。[12]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术语,“英文研究”大致是在19世纪末伴随英国文学的兴起及其学科化历程而兴起的。到了1895年,英国高校基本都设置了英语语言文学的学位。1917年正式成为剑桥大学学位课程乃至学科专业体系。特雷·伊格尔顿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英文研究发端于维多利亚时代,其前身为比较语文学,而比较语文学研究旨在从语言比较中探寻种族或民族精神的演化规律。[13]186
回顾英文研究的历史,对于理解英国文学批评学科的兴起大有裨益。依据韦勒克的考论,近代英国文学自18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民族化和审美化的双重过程。[11]36近代英国文学的日益审美化和民族化,扮演了一个宗教衰微之后精神替代物的重要角色。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剑桥英文学院高材生彼得·威德森教授所言,文学“被看成是迫切需要的建设中的一种构成因素,即在一个新的而且是异质的工业、都市、阶级社会的背景中能够凝聚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的建设中的构成因素”。[11]37彼得·威德逊还在《英国文学教育的危机》一文中指出,在英国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形成史上,有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和节点:一是19世纪马修·阿诺德的文化和教育观念及其对艾略特、利维斯产生的影响(后两人也都书写了英国文学及其伟大传统)。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文学批评学科化的深刻影响。[14]128-129这个论断已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细究起来,英文研究或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有其特定的时代机缘和历史语境。英国文学研究是英国大学教育体制现代转型的结果,也是欧洲近代古典语文学和比较语文学学术交流的结果,同时还是英国现代民族文学研究高涨的产物,以及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即用文学的精神价值填补18、19世纪宗教衰微所留下的空缺以拯救国民灵魂的需要。以下试逐一论之。
首先,英文研究是英国大学教育体制现代转型的产物,最突出的事件是英语学院的成立,它为文学批评进入英国大学殿堂铺平了道路,英国文学及其批评得以在英文学院的学术体制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英文教育经历了一个从研习古希腊罗马文化向研究英国本民族的近代英语和英国文学嬗变的过程,换言之,英国文学研究既脱胎于古典语文学又超越了古典语文学。19世纪之前英国大中学校的人文教育为古典语文学(philology)教育。占据大中学校人文教育中心的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及其文化教育。英语则是下层语言,英文教育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副产品,文学批评是贻笑大方的不入流的职业,不为知识阶层所重视。以至于在19世纪50年代,牛津大学曾经极力反对一项由皇家学会提出的建议,即将英语教学列入教学大纲的建议——显然牛津大学当时恪守古典语文学传统,对英语教学还不以为然。据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雷纳·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一书中的考证,还有英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剑桥英文学院毕业生彼得·威德森的考证,以及我国学者陆扬援引伊格尔顿的考证,尽管英语研究和英国文学批评早在17、18世纪就孕育在当时伦敦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咖啡馆及流行杂志之中,这些报刊文章成为英国近代文学的早期文体,报刊读者也相应成为英国近代文学的早期读者,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英文研究和文学批评出现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此时正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期,长期主导英国人文教育的古典语文学正逐步让位于现代意义上的英国语言文学研究。最早提供英语语言文学教育的是19世纪20年代的伦敦大学学院,该校于1828年首次设立英国语言文学教授岗位。第一部题为《英语语言和文学的历史》的学术著作是由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撰写的,出版于1836年。到19世纪末,都柏林三一学院、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等高校陆续设立英语和英国文学教席。尽管海外殖民地英文教育、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客观上都促进了英文研究的发展,但牛津和剑桥依然坚决抵制设置英文研究这门学科。1870年的教育法案的颁布,使得英国社会对英语教师的需求激增。1885年,牛津大学才设立英国语言文学的莫顿教授职位,被委任的却是对文学毫无兴趣的语言学家A·S·内皮尔。到了1893年,牛津大学开始建立授予英语硕士学位的荣誉学院(honours school),这相当于可授予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院。1894年,牛津大学建立了英语学校。1902年牛津聘任瓦尔特·拉雷(Walter Raleigh)爵士为第一位英国文学教授。1904年,牛津大学将莫顿教授教授职位分为英国语言和英国文学两种,瓦尔特·拉雷又受聘这个新的英国文学教授职务。剑桥设立第一位英国文学教授则更晚至1912年,首位剑桥英文教授是阿瑟·奎勒·考奇(Aather Quiller Couch)爵士(此人即利维斯的导师)。剑桥的英文学院则成立于1917年。1919年,英国文学被列入剑桥大学学士学位考试系列, 正式成为剑桥大学的学士学位课程。[15]英文研究在20世纪初终于正式进入英国高校最后的文化堡垒,成为英国现代大学人文教育体制真正转型的最重要标志。1921年颁发的《纽伯特报告(Newbolt Report)》(即《关于英国文学教育的报告》)更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优秀的英国文学足以担当宗教人文主义曾经担负的伟大使命,宣告英国文学学科体制化的正式确立,极大促进了英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和建制化。尤其是瑞恰兹所创立的“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代表了利维斯主义之前剑桥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平,对利维斯学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其次,英文研究的崛起也得益于19世纪文化人类学和比较语文学的兴起,激发了当时英国文学批评家的文化观念、人文精神和学科意识的自觉。长期以来,英语是拉丁语的仆人、古典语文学的仆人。尽管自17世纪以来,英国评论家开始表现出弘扬本民族语言的倾向,但是英语和英国文学教育仍长期从属于古典语文学和古典文学教育,尚未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直至19世纪末期,英国牛津、剑桥仍在就“英国文学”的课程和教席问题争论不休。“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就要不要在牛津设立一个英语语言文学教授职位曾有过激烈的争论。”[16]一次争论的结果以失败告终。而在剑桥,直至1883年,英国文学仅以选修课的身份进入本科教学,“且从属于中古和现代语言系,其教学深受日耳曼语言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大多从语言学、语文学的角度考察英语语言的演变和发展”。[17]“英国文学的早期教学方法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学教育那里复制而来的,文学附属于语法学、词源学、修辞学、逻辑学、演讲术等所有被后人埋怨的东西,唯独没有真正的文学研究。”[18]直至19世纪末,英国正规大学文科教育仍以古典文学和古典语文学为圭臬,英语教育处于边缘或仅在成人教育之中。老牌的牛津、剑桥长期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正宗,英文教育地位较低。即便在利维斯就读于刚成立的剑桥英文学院时,英文学科仍处于筚路蓝缕时期。但是,19、20世纪之交,古典学在英国各高校逐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人文学科即英国语言和文学学科的兴起。随着拉丁文、希腊文和古英语等古典语言实用性下降,英国文学作为一门人文教育的新型学科迅速取代古典学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正是经过剑桥大学英文学院教师的努力,英文教育一改旧日的语文学传统,变驳杂的古典语文学习为主要面向英国本民族文学的专业批评。剑桥英文学院的成立和发展,奠定、巩固和提升了英文研究在英国最高学府的学术地位。剑桥英文研究以文学批评为核心,注重文本的细读和实践批评,训练学生的语义分析和文本细读能力,训练学生对生活肌理和道德思想感情的分析能力。致力于提高学生的鉴赏力和辨识力,培养其情感和悟性,养成对生命的感悟和珍爱,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代人文价值。经过剑桥英文学院的学术洗礼,英文研究和英国文学批评终于成为现代英国大学人文学科教育的核心学科。
再次,英文教育的发展史反映了英国民族的崛起史,把英国文学设立为学科的时代正是英国进入高度帝国主义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直接成为英文研究高涨的一个外部契机。英文教育可追溯至伊丽莎白时代这个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到了19世纪初,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这位学术领域里的英语之父,更是将文学说成是“一个民族的自传”;到了1835年,在确定了教授印度人英语而使他们文明化的需要之后,麦考利爵士确立了这样一个前提,即英格兰文学现在远比其他的古典遗产更有价值”。[11]37-38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满足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教育之需,英语课程在英国高校开始普及,旨在使帝国海外殖民地原住民受到一种有效的文明教化。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英语学术地位的真正提高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使英文教育或英国文学教育崛起获得了时代的契机,使之摆脱了德国古典语文学传统的影响,那种移植过来的德国古典语文学模式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和批判,进而促成了一场英文研究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英德两国之间的尖锐矛盾,消解了德国古典语文学、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文化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公正、理性和崇高的学术形象。同时,大战也使得英国朝野对于民族认同的意识空前高涨,英国文学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一战的结果是,“它造成了一种需要去颂扬‘英语文学’这一份民族遗产,而目的是铸就一种民族认同感”。[11]47战争本身强化了那种铭记在英国文学中的爱国热潮,促进了牛津、剑桥的英语学科超越日耳曼语文学。既然英国文学研究的对手即古典语文学与德国的影响密切相关,既然英国正在与德国进行一场大战,那么就应当抵制古典语文学这种蠢笨的“日耳曼胡说”,任何一位自尊的英国绅士都不应与之发生联系。牛津大学教授瓦尔特·雷利当时甚至放出豪言:“我想率领百名教授组成的一队人马向一百名德国佬教授发起挑战。他们的死对人类有好处。”[13]186总之,英文教授们从各个角度批判和反思德国文化,增进了对英文教育之于强化民族意识、唤起民族使命、促进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性之认识。英文研究和英国文学批评因而成为提升英国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表征。英国文学研究终于实现了对古典语文学的胜出,长期占据英国大学人文教育学术核心的古典语文学终于被英国文学研究所取代。20世纪初期,英语文学批评被视为增强英国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举措,成为英国最正宗的“国学”。
最后,英国文学批评学科的兴起满足了近代社会传统宗教式微之后现代人文教育和现代意识形态建构之需要。正如特雷·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如果有谁被要求对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研究的增长只给出一个解释,他的回答也许勉强可以是:“宗教的衰落”。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一向行之有效的传统宗教这种意识形态陷入深刻的困境。它不再能赢得群众的感情和思想。而在科学发现和社会变化的双重冲击下,它那无可怀疑的统治正处于消亡的危险之中。幸而有一种极为相似的话语就在身边:英国文学。伊格尔顿引用了牛津大学早期的英文教授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在其就职演说中的一段名言:“英国正在生病……英国文学必须拯救它。由于(我所理解的)教会已经衰落,而社会补救方法迟迟不来,英国文学现在具有三重作用:当然,我认为它仍然要愉悦和教导我们,但是首先它应该拯救我们的灵魂和治疗这个国家。”伊格尔顿进而明确指出:“当宗教逐步停止提供可使一个动荡的阶级社会借以融为一体的社会‘黏合剂’、感情价值和基本神话的时候,‘英国文学’被构成为一个学科,以从维多利亚时代起继续承担这一意识形态任务。”[19]21-23随着宗教在现代社会的衰微,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出现某种空虚和危机,而英国文学和英文研究正好可以填补宗教衰微之后的空缺,发挥疗救现代英国人的灵魂的重要作用,给人以因应社会挑战的精神力量。早在19世纪后期马修·阿诺德就已经开始倡导文化宗教,以代替日渐式微的传统宗教。阿诺德在《诗歌研究》《文学与教条》《上帝与圣经》等著作中,即强调今人越来越需要用诗来阐释生活,宗教和哲学将被文学所取代。对于传统的宗教和圣经,阿诺德也首创性地进行文学性研究,主要阐发其对于人性完美的德性精神价值,并主张用诗性精神贯通圣经文本和宗教教义。再比如,在20世纪初期,著名的《纽伦特报告》也明确提出:英国文学所能提供的精神价值足以代替宗教曾经拥有的地位。到了利维斯那里,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更是建构人性价值的文化事业与有效手段。利维斯认为,在个人与艺术的反应特点与其对实在的人性的相符程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通过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所描述的本质生活重新建立联系,人类的本性便可以避开大众社会的破坏性力量而流传下来,人的主观意识就重新获得了明辨是非的理解力中的人道特性。[14]153-154从阿诺德开始的以文学代替宗教的精神文化建构过程,至利维斯时代终于取得了成功,文学研究已然起到了宗教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利维斯主义成为以剑桥批评学派为标志的英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学术精神和文论精神的真正代表。
特里·伊格尔顿则在其《英文研究的终结》一文中以犀利的语言对作为学科的英国文学研究做出评价和阐述,他指出:“‘英国文学’是维多利亚帝国中产阶级的东西,它迫不及待地要用物质性的书写躯体表现精神同一性的结晶。……‘英国文学’作为道德戒规和精神膏药,在战后的剑桥得到迅速发展,绝非偶然,它是给精疲力竭、加速没落中的帝国民族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替代性身份。……重要的文学生产大规模地从帝国中心移向殖民或后殖民的边缘地带,宗主国的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对象,只能向后折回,远离低贱而异己的现代主义,回到想象性的本土的过去。……于是便有了《细绎》喧嚣一时的种种含混和歧义,既是精神前卫,又是反动余党,对当下事务做出热切回应的同时却竭力退回到理想中的过去。”[13]211比如,莎士比亚作为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于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阅读、批评和教育,增进英国人民对所谓“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
三、 从边缘到核心:“英语学”的崛起与“英国文学研究(英国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历程
英国是一个有着复杂历史谱系的国家,欧洲西部的凯尔特人、罗马人,中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法国的诺曼人等许多欧洲民族都曾依次统治过英伦三岛。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不列颠群岛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远不是一个由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统一体。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不列颠群岛见证了一个个血腥王国间的战争与轮替, 还有众多的封建采邑、殖民者的图谋、种族仇恨、语区的分裂和文化的纷争。”[20]因而英国的语言谱系极为复杂,凯尔特语、拉丁语、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维京语、法语等都曾成为或进入英国的官方语言,国内又有苏格兰语、爱尔兰语、威尔士语、英格兰语、康沃尔语等多种方言英语。随着文法学校的出现,中世纪英语开始出现方言之外的共同语。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城市扩张、教育普及、报刊普及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促进了英国近代语言的统一或“标准英语”的形成(即便是各地的英语方言也在共同语言的背景下衍生和变化)。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发端于伯克、柯勒律治、卡莱尔、纽曼、马修·阿诺德等人的英国近代文化观念形成史。威廉斯还在《漫长的革命》第二部分第四节专门讨论了“标准英语”的发展问题,指出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书写英语的标准化起了决定性作用。至19世纪,崛起的英国中产阶级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同语言,标准英语也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当然,标准英语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英语发展的一成不变,发表和变异仍将以不同方式延续。[21]在英语发展史上,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作家对于英语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在英语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还有:1611年英王詹姆斯一世下令翻译的英译本《圣经》出版并颁布通行,1755年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以一己之力历时九年编撰的《英语大辞典》出版,1884年由英国著名诗人、学者柯勒律治生前主编的《牛津英语词典》第一册出版,等等。英语的发展不仅为英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语言基础,同时也促进了英语学(English Studies,Anglistics)的形成,或者说,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正是伴随着英语学的兴起而发展的。
英国文学研究起始于乔治四世和威廉斯四世时期,而迅速发展于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六十余年,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英国从一个普通的地区强国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全球性强国,海外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所谓大英帝国的快速扩张的客观形势,对人才培养和文化发展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了适应工人阶级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和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教育之需,英国文学研究取得长足的发展。但初创时期的英文学院学术地位仍然很低,处于英国学术机构的边缘。19世纪英文教育在那些技工学院和成人教育中得到较快发展,许多工人群众因为有受英文教育的机会而有了获得感和归属感。对此,特雷·伊格尔顿和彼得·威德森都有过精辟论述。特雷·伊格尔顿指出,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技工学院、工人院校和大学附属夜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英国文学实际上就是穷人的古典文学——它是为处于英国公学和牛津剑桥这些迷人的小圈子之外的人提供最便宜的‘人文’(liberal)教育的一种方法。从一开始,在莫里斯(F.D.Maurice)和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iley)等‘英国文学研究’开拓者的著作中,强调的就是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团结、‘更大的同情心’的培养、民族骄傲的灌输和‘道德’价值标准的传播”。[19]26彼得·威德森也认为:“恰恰是在那些机械学院、技工学院以及从大学里向外延伸的巡回讲座中,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里,‘英语’才得到了最有活力的发展,而这样的讲座获得成功又要归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福音传教士,例如莫里斯(F.D.Maurice)和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这样也就明显地在工人群众中培育出一种民族归属感和‘博大的同情心’。并且在他们与其他阶级之间创造出一种‘同类情感’。许许多多的工人的确因为有了‘文学’上的收获而产生了一种解放感。”[11]43英语专业主要为那些无法进入正规名校接受古典学教育的中低阶层子弟提供了廉价的、准入门槛低的受教育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英语文学’就变成了道德教育的工具,变成了廉价的和可接受的‘穷人的经典’。”[11]44文学成为急剧衰落的宗教精神力量的替代者。通过向工人群众提供充满福音的或自由人道的文学教育,文学发挥了在一个阶级分化加剧的社会中将那些潜在的分裂因素加以人性化、文明化的积极作用,英文教育履行了道德教育的意识形态职能。
早期英国文学研究除了在技工学院、工人学院和大学附属夜校中得到最初的发展之外,还在女性教育中得到发展。由于女性受教育人数的增多,加之为了培养民族未来的儿童之需要,对作为教导本民族青年一代的“教师加母亲”的妇女文化培训提上了议程,英语文学的教育也因此派上了重要用场。一位皇家调查团的证人在1877年指出:英国文学是“妇女……以及去当教师的二、三等公民”的合适科目。英语文学教育所具有的个人直觉的特性使之成为妇女培训最好的方式。正如查尔斯·金斯利在就任皇后学院英语教授时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阅读英语文学非常适合于妇女天然的兴趣,这也将有益于在妇女中形成对“英语精神”(English spirit)的理解,使之成为妇女文化教育的根基。[11]44相对于理工科和古典语文学,英国文学研究的学习显然更为轻松,且富于柔美的情感。对此,特雷·伊格尔顿有精辟阐述,他指出:英国文学的“软化”(softening)和“人化”(humanizing)效力——这是英国文学早期倡导者反复使用的字眼——在当时的关于性别的意识形态观念中显然是女性。这种性别观念在当时的英国文学教学课堂上都有所反映。阿瑟·奎勒·考奇爵士(Sir Arthur Thomas Quiller Couch),剑桥大学第一位英国文学教授,居然会用“先生们”一词来开始一堂听众大部分为女性的英国文学课程。[19]27后来,伊格尔顿在就任牛津大学沃顿英文教授职务的学术演讲(1992)中,再次回顾了早期英文研究被视为女性化、女人腔的课程这一早期现象。他指出:从性别看,剑桥大学现代语言学校里女性占了三分之一。剑桥英文系正是由现代语言学校发展而来的,牛津大学英文系在头五年里有六十九名女生,男生只有十八名。第一次世界大战重铸了剑桥大学英文系的阳刚之气和发达的肌肉及其强大生命力。[13]192
早期英文教育或英国文学教育也是英国面向海外殖民地的文化教育,换言之,海外被殖民的对象是早期英文教育的第三个主要对象。印裔美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英国文学系教授高瑞·薇思瓦纳珊( Gauri Viswanathan)甚至考证出,英国文学的学科化最先出现的地方并非英国本土,而是英属殖民地印度。她以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思考为理论切入点,精细剖析了英国文学是如何服务于英帝国在印度攫取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工程的,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作为一门学科的英国文学在殖民地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英国本土。”[22]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关键不在英国文学而在英国文学:英国民族的伟大诗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可以培养对于英国有机的民族传统的认同意识,海外殖民地的新应征者可以通过英文学习而被接纳到这一传统和认同中来。为了方便英国实施殖民统治,英国文学知识还作为考试内容进入了东印度公司公务人员考试 (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的范围。特雷·伊格尔顿援引的一则研究资料表明:在维多利亚时代,一旦由方便地包装过的本民族的文化财富即英国文学武装起来,大英帝国主义的政府官员就可以怀着对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安全感而冲向海外,并且还能够向羡慕他们的殖民地人民炫耀这种文化优越性。[19]27-28
值得指出的是,与经典化的古典语文学学科相比,初创时期的英国文学教育尚处于英国大学人文学科教育的边缘。早期英文教育及批评方法大多显得随意而缺乏严谨性,颇显业余作风而缺乏经典化和科学性。其内容多半是讲述作家的生活轶事,缺少作品解读和结构分析,因而流于一种印象式、趣味式批评,往往被认为是关于文学趣味的无稽之谈。可见,英国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并不是一门高贵、典雅、精致的人文学科,而只是古典语文学的低端代用品,被视为“半瓶醋的学科”,因而很长时期被牛津、剑桥等古典学重镇所抵制。即便是被勉强接受的初期,英国文学研究也不受待见。例如,牛津大学的第一位英国文学教授瓦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本人即对自己的学科表示出蔑视态度,视之为女性的事情或女性的幻想而非男人的事业,以至于“一战”爆发后,他立即放弃这份教职而奔向前线从事战争宣传。[19]28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英国大学开始快速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普选权、公共教育和公民识字普及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小资产阶级大批进入英国教育与知识生活的更高等级,英国的文化教育快速发展,英国文学学科化和科学化进程加速。在英格兰,伯明翰大学不但率先把英语设为正式学科,而且于1894年任命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位英国文学教授——积极倡导英语教育的约翰·切顿·柯林斯(John Churton Collins,1848—1908)——柯林斯曾在1885年竞聘牛津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教学的莫顿教授职位失败。英国教育部继1902年颁布教育法案之后,1907年又在纽波特爵士倡导下成立了英语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推动和提升英语语言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适合于每一位英国儿童的基本课程。这一阶段,英文教育或英国文学教育也日渐精致,又出现了将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的新趋势,使文学教育获得了方法论意义的特色,使文学在培育均衡成长的公民、使他们得到充分发展方面具有核心地位而受到尊重。[11]47可见,曾经占据英国牛津、剑桥等名校传统人文教育主流的古典语文学终于受到英国其他更多高校英文教育的挑战而出现了衰落,取代它的是作为新的人文研究的“英语语言与文学”。牛津、剑桥对古典语文学的固守已是难以为继,不得不将英文教育纳入其体制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加速了英文教育的崛起,促使英国文学研究最终成为英国高校人文教育的支柱,彻底挣脱了德国古典语文学的枷锁。即便是在曾经作为古典语文学重镇的牛津和剑桥等老牌大学,德国文化也遭受指控。相反,原先不受重视的英文研究或英国文学研究却日益成为民族认同的对象。英国知识界普遍希望借助于英文教育来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建构起英国文化的英国性 (Englishness),促进战后英国社会的复兴和英国民族凝聚力的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文研究”或“英国文学研究”成为牛津大学的正式课程。1917年,剑桥大学引进关于“文学、生活与思想”的荣誉学位考试制度,英国历史上第一份英文独立考试大纲随之在剑桥诞生。同年,区别于传统的语文性(philological)教学并以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为主要特征的英文学院(English school)也在剑桥大学正式成立。英国文学研究进入牛津、剑桥等老牌名校并成为一门正式人文学科的历史,也就是小资产阶级进入英国顶尖名校的历史。原本体现中下层阶级文化需求的英国文学(English Studies)课程不再处于边缘,而是逐步取代了古典语文学曾经的位置,成为英国大学自由人文教育的核心。以1917年剑桥大学英文学院的成立为标志,宣告了英国文学研究在英国高校体制化的完成,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已开始取代古典语文学的地位,成为挣脱了镣铐的缪斯,从学术边缘进入学术中心。
1921年,在著名诗人、教育家亨利·纽伯特爵士(Sir Henry John Newbelt,1862—1938)主持下,由剑桥大学第一位英文教授阿瑟·奎拉·库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 Couch,1863—1944)与青年诗人和批评家瑞恰兹(A·Richards,1893—1979)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题为《英格兰的英文教学》的研究报告,并由英国教育部颁发,史称《纽伯特报告》(Newbolt Report)。《纽伯特报告》的问世,是英国文学学科化历程中的一个重大学术事件。该报告字里行间回响着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提出的有关文学肩负重大文化宗教使命的文化理想。该报告明确肯定了英国文学在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濡化普通人的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品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提出了英国文学在世俗社会所能提供的足以取代传统宗教的精神价值。报告还明确把莎士比亚誉为“最伟大的英语作家”,盛赞莎士比亚对建构英国民族文化共同体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纽伯特报告》突出强调了英文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报告宣称:建立在“英语”教育基础上的自由教育“应该构成民族团结的新成分,将所有阶级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更为确定的是,应当为民族文学起到这种黏合剂的作用而感到自豪和愉悦”。[11]48至此,随着英文专业作为一门学科在英国高校的兴起并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当年阿诺德倡导由国家来兴办人文教育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
英国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在20世纪前二三十年走向成熟、走向经典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和英国文学批评教授不再是过去的上层贵族精英,而是中下层资产阶级,后者以英国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文化资本,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全部的生命精力。例如,F.R.利维斯是乐器商的儿子,利维斯夫人Q.D.罗丝是绸布商的女儿,而瑞恰兹则是一位工厂经理的儿子。英国文学研究在他们心目中,不再像早期英国文学教授眼里那样只是一种业余性、印象式的活动,而是一门严格或严肃的学科,是一项值得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事业。20世纪20年代,时任刚刚成立的剑桥大学英文学院教师的青年批评家瑞恰兹曾邀请艾略特担任一些学术工作,但被艾略特婉言谢绝。尽管如此,两人却成为亲密朋友。这也是艾略特第一次与剑桥英文学派建立的联系。瑞恰兹成为艾略特诗歌的批评家和阐释者。“艾略特的批评文章为一种‘传统’观念下了定义,而他的作品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其广泛、复杂的文学联想范围。日益壮大的英语研究界需要可供‘解释’和‘研究’的现代课题,而这两者对它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正像艾略特需要学术界的注目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地位一样,‘英语文学’研究最终只有借助于文化巨人艾略特才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问题甚至是道德问题的学科。”[23]随后出现的瑞恰兹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与利维斯主义更是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以瑞恰兹、利维斯等人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或剑桥英语学院批评家们将文学批评从绅士的外行趣味转变为需要系统训练的实践批评专业。这种批评实践既是文本细读和美学教育的实践,又是心智和道德培养的实践。利维斯还进而主张,大学英文学院是走出文化衰退、振兴英国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英国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在现代人文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肩负着培养和提升社会大众鉴别力和洞察力的重要使命。为此,他创办《细察》杂志,开展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将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推向更大的社会文化领域。利维斯认为,英国近代乡村有机社会虽被工业文明解体,所幸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得到保存。因此,文学教育和批评的意义也就更为重大。利维斯明确指出:“文学——作为英文荣誉学位考试而学习的文学非常重要,它对文明至关重要。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的现实,一种人类精神的自治。”[24]利维斯极力强调英语性(Englishness)和“英语学院”(English school)的重要性。利维斯吸收了瑞恰兹的实践批评和细读方法,并使之与阿诺德的文化批评思想相融合。利维斯等人将文学批评视为恢复和重建传统文化秩序的先锋,建立了一个影响长达四十余年的利维斯主义。正因为此,有论者高度评价了利维斯的美学,肯定其对建立英国文学批评所做的重要贡献:“在英国历史上,英国文学并没有学术地位,从未成为考生的科目,因为所有这类‘关于雪莱的杂谈’纯属个人的情趣和爱好。然而,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教师和学生都赞同的并且行之有效的文学价值标准,那么就可以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的‘鉴赏’能力。利维斯主义的主要成就之一在于把一种可以通过考试来检验的教学方法建立在一种将有价值的文学与没有价值的小说严格区分开来的美学基础之上。”[25]总之,英国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及其批评标准的确立是经由柯勒律治、阿诺德、艾略特、纽波特、库奇爵士、瑞恰兹、利维斯等几代人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剑桥学派的形成标志着英国文学批评学科的成熟。正是在20世纪前二三十年,剑桥大学的英文教授摈弃了早期英文教授作为上层绅士的那种轻浮的业余态度,把早期英文研究的趣味性、印象性、随意性的趣谈,改造提升为重视文本细读、富于美学精神和文化理想、注重批评技巧的文学批评学科,进而取代了古典语文学在英国现代大学人文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与传统的古典语文学相比,英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学科具有诸多新的学科特点:古典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而英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是近代以来的英国文学。古典语文学的方法是浑整性的,包含文献考证、语言释读、历史考古等多种方法,英国文学批评则主要为文本细读、语义分析、鉴赏批评和生活批评。古典语文学企图复活古代世界,以期提供对现代社会的镜鉴,英国文学批评则通过文学经典的解读和接受,培养读者敏锐的感受力和健全的心智。 英国文学批评在经历四十余年的盛期发展之后,受到了更为新型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挑战。伯明翰学派早期主要理论家、曾经的左翼利维斯主义者霍加特、威廉斯等人不满于剑桥文学批评的文学精英主义,主张打开文学和文化,扩展其边界。例如,威廉斯认为,文学固然极其重要,因为文学的确是重要的、正式的生活经验记录,而且每部作品都是文学与以不同方式保存下来的共同语言的契合点。但是,威廉斯拒绝了利维斯主义固守精英文学的狭隘性。威廉斯认为:“让文学担负起,或者更精确地说,使文化批评担负起控制全部个人与社会经验品质的责任,这将会使这个重要的立场受到有害的误解。英语的确是所有教育中的一件中心大事,但英语显然不等于是整个教育。同样,正规教育无论如何高尚,也不是我们所获得的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经验的全部。[26]在威廉斯看来,利维斯以文学代替文化,固然有其卓见之处,但文学经验不等于文化经验,更不等于全部的社会生活整体经验。因此,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应当予以打开和扩展。我们必须不断地扩展文化观念,直至使之几乎等同于我们整个的共同生活。正是出于对剑桥文学批评学派的不满与超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旅程。(4)对此,笔者已有五十余万字的《“文化研究”的历史语境与理论建构》一书深入探讨这一重要课题,该书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