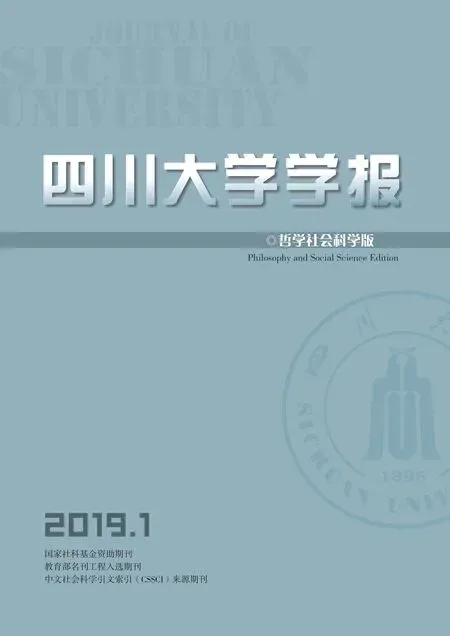历史性: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2019-02-12
历史究竟是什么?这是长久以来人们都极为关心的话题,因为这关乎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在对这一问题的诸多探究中,澄清“历史性”的问题又是关键之所在。那么,究竟何谓“历史性”呢?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的一段经典论述中获得一定的启迪: “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注]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83页。海德格尔在这段话中提及的“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指称的即是“历史性”。在他的阐释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历史性理解为事物作为“历史”事物的本质性,即事物的“历史”的特征,或者说,事物在“历史”中现实地存在的特性。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海德格尔坦露出的对马克思的高度赞誉中进一步体会他的深意。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牢牢地抓住了“异化”这个在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性,换言之,这个最根本的历史特质,并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因此真正开启了深入历史的那个本质性维度中的正确路径。应当说,海德格尔的上述评价的确要言不烦地揭明了马克思思想的超群之处。本文将着力探讨马克思相较于黑格尔对“历史性”的理解与把握,经由这番探究以充分揭示和印证海德格尔对马克思高度赞誉的恰当性。
一、黑格尔的“历史性”
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历程当中,黑格尔之前的人们都将世界的基础视作是非历史的。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真理存在于超时间的不朽的理念之中。及至近代,康德首先提出了先验性是理性自身的逻辑的主张。尽管如此,历史的真实内容与理性的先验本质,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事实上始终呈现为一种外在的关系。
黑格尔开始系统地探讨有关历史的本体论问题,例如:历史的基础、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目的等问题,并力图在认可康德的先验性的同时也把历史性原则融合进来,将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这种努力的成果即是其历史哲学思想。1830年《历史哲学》一书的问世标志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诞生。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对象、性质、作用等方面都作了深入而全面的阐释。他提出了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历史本身,研究它的根本目的在于把握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充分发挥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和康德先验的自由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了人类理性之于历史的根本意义,这可以从总结而来的他的几个分论点中得以说明:
其一,理性精神是历史的真正的基础,历史就是理性精神自我意识的历史,黑格尔说:“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换言之, 精神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种意识是不依赖外界条件的意识,被黑格尔称之为“自由”,自由是精神的本质,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即呈现为实现自由。因而,人的这种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自由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基础。
其二,人类理性不仅是人类精神自身的而且也是客观世界的内在本性,理性所具有的辩证本性必定在自身诸环节的范畴中展现其具体内容,因为客观世界的每个事物都是按照理性的辩证法而展开的,从而构成呈现理性的具体环节。换言之,理性的内在逻辑决定着历史的逻辑。
其三,一切历史都是精神的历史,自然界没有历史。自然界永远呈现的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不会产生新的事物,因而,“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6页。但与此不同的是,历史上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它们都是精神的创造。
其四,理性需要通过热情、利益等非理性的力量达到自身的目的,因而,这些非理性的力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杠杆。“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使这个目的具有意识,并实现这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6页。
由上述可见,归结起来,黑格尔主张将历史解读为理性的自我外化、自我否定、自我复归的过程。质言之,他的这一思想体系的基本观点是:“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9页。这样,黑格尔在理性精神的辩证运动当中,将先验性与历史性融合在了一起,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思辨的表达。在这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正是他所创造出的辩证逻辑。通过辩证逻辑,他才能尝试着将“历史”置于本体论的境域之中,从而得以建构历史性的原则。恩格斯曾经针对这一点给予了黑格尔高度的肯定,他称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与其他哲学家相比,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以“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页。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也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哲学功绩,他这样说道:“他把时代历史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同时把永恒与短暂、永恒与现实等联系起来,进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哲学的特征。”[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尽管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思想中力图将历史性纳入到本体论当中,但是,也恰恰是他的这种着力的方向,使他的建构最终流于以虚假的历史性收场的结局。因为黑格尔努力朝向的是将各种社会历史现象都追溯到精神之上,以之作为它们的本质,而精神的发展史就是概念的发展史,它只存在于思想之中。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黑格尔把人类史描述成了概念运动的历史:“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9页。这样一来,他所领会到的历史就“仅仅是哲学的历史, 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他这是从理性精神的辩证法来把握事物在历史中存在的特性,“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用理性的逻辑牺牲了现实的历史,达到的只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而他所领会的“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7页。一言以蔽之,在黑格尔这里,历史性之所以成立根本在于理性具有辩证的本性,而理性这个辩证法的本体论的根基远离了真正具体的现实的生活,因而,历史性依然是虚假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恩格斯给予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页。的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深受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扬弃黑格尔历史哲学固有缺陷的基础上才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对它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在于马克思确立了真实的历史性原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观不再是历史哲学之任意一种,它“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不再沿袭对历史的思辨探讨的路径,而是将“历史”纳入到存在论之中,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历史本体论即历史存在论。
马克思的这一历史性原则的确立,首先是从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入手的,而这一批判坚持的立场是自然与历史的相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不能撇开历史谈论自然,同样也不能撇开自然谈论历史,人类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事实上是同一部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0页。本雅明一语道破了这一点:“如果说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物质自然同样也侵害世界历史’,那么马克思则从一开始就是从社会范畴上认识自然的。”[注]汪民安:《生产》第一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1-342页。
再从马克思以下这段论述中来具体分析他是如何在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的视域下分析并戳穿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的,他这样说道:“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这种历史哲学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一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在以上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指出,这一唯心主义历史观之所以是“唯心”的,其根源就在于它对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性关系的割裂和对立。这样导致的后果是,从历史的本源性的存在之外来审视历史,人们现实的生活过程反倒成为了非历史的存在,纯粹的精神、自我意识却变成了历史的核心,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并支配一切的主导力量。因此,历史要么是他们眼中具体的政治历史事件这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要么是抱着时代幻想、将历史视作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就前者而言,历史事实上是由细碎的日常经验的累积而构成,这些日常经验经过范畴的规定上升为科学研究的事实,它归属于不同的“事实领域”。然而,这些经验事实却远非“事情”本身即现实生活及其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不过是是思辩唯心主义所讲的“意识的空话”,换言之,这同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与实际发展过程脱离的”。总而言之,马克思认为,这种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就其本质而言,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3-174、153、153、153、153、175、173页。
三、马克思的“历史性”原则
与这种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主张,“‘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页。它是人们的“能动的生活过程”,这个“活动”指的即是感性活动之劳动。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这个现实的个人不在理性范畴的规定性之中,而是包括了人类的感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亦即“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3、146、146页。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在臆想中撇开的现实的前提出发去理解历史。由此,人类的历史是感性活动的历史,即劳动的历史,这是人与自然在这种活动中被改变的历史,是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同时又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同一部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2页。
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之中,无论是基督教的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二元结构中,还是近代启蒙思想的人与自然界的二元对立中,自然的价值皆在于其被人类所需要。面对自然,人是认识与改造它的主体的存在,而自然仅仅是人类征服的对象。但是在马克思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脱离了过去的关系框架。人成为置身于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社会两者彼此不可分割:“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与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没有脱离自然的人,也没有脱离人的自然,只有人和自然的统一,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注]夏巍:《马克思哲学意义域中劳动概念的当代批判透视》,《南通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26-32页。由此立场出发,马克思进而论证了割裂两者会导致的唯心主义的后果,“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57、89、92页。马克思恰恰是洞悉了自然与历史在存在论性质上的相统一,才能够将黑格尔的客观的理性精神落实到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当中,由此改变了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理性为根基的哲学路向,开辟了转向以感性为核心的真正的历史本体论即历史存在论的先河。
下文进一步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历史性原则的具体论述当中,呈现其历史性原则的四个方面的重要内涵,同时揭明他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新主张。
其一,“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在上面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主张历史是理性精神的历史针锋相对的观点: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生产物质生活之于历史的重大意义不只是表现在它能够生产出人类的生命活动所需的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感性存在和感性生活的生成,换言之,是对人的社会性的创造和生成。马克思提醒人们,上述事实的意义和范围是任何历史观都必须加以注意和重视的,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错误恰恰就在于忽视了这一点,他说:“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8-159页。
其二,“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阐明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力量的问题。黑格尔的看法是个人的思想行动中蕴藏着的热情、意志和欲望是理性精神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使这个目的具有意识,并且实现这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6页。与此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所说的“需要”指的既不是自然所设定的动物的天然的需要,也并非黑格尔所谓的激情、欲望一类的非理性的精神,而是具有人的社会属性的需要即“感性需要”。不同于具有个体特质的非理性,感性需要是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需要,它并不存在于人们精神的建构活动当中,而是只有扎根于感性劳动建构社会关系的活动中才会生成与发展。当人们对社会关系的需要获得了满足之后,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感性活动的创造中会进而生成新的感性需要,由此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这样说道:“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0页。
其三,“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关系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在关于历史性原则的第三个阐述中,马克思首先提出了家庭关系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以及家庭、社会、劳动是一同诞生的观点。家庭关系之所以能够诞生,在马克思看来,是人们具有了对于与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的感性意识。家庭是个体之间交往关系的开端,当具有了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家庭伦理这种感性联系的感性意识,人类才走出了群婚制,建立起这一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也说过,“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这一表述不仅表达了意识是对社会关系的发现和需要的意识的观点,而且,马克思更想强调的一点是,意识绝不是现成地被给予的,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意识,归根结底,意识是被劳动生产出来的。所以,他接着论证道:“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围绕着这一点,马克思还提道:“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这时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像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161、160、159页。也就是说,马克思进一步重申了一定要从现实的前提出发思考历史问题的观点。
其四,“此外,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明白,把它们看作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160页。马克思在这一阐述中明确指出,以上所考察的原初的历史的这三重关系并不是独立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它应被视为社会活动的同时展开的三个方面。
以上对于马克思的历史性原则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的“历史性”通过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这一社会存在的本质性内核定位其本质规定性。用他自己的表述来总结其思想即是:“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172页。
四、余 论
马克思是在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的关系中,在人类的感性实践活动及其历史运动过程这一“存在”中指认出了事物的“历史性”,这就使得其“历史性”奠基在深厚的现实基础之上。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不单单成就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更是建立在感性活动之历史性基础上的存在论的新视域,成为海德格尔所称颂的真正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之中的崭新的思想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