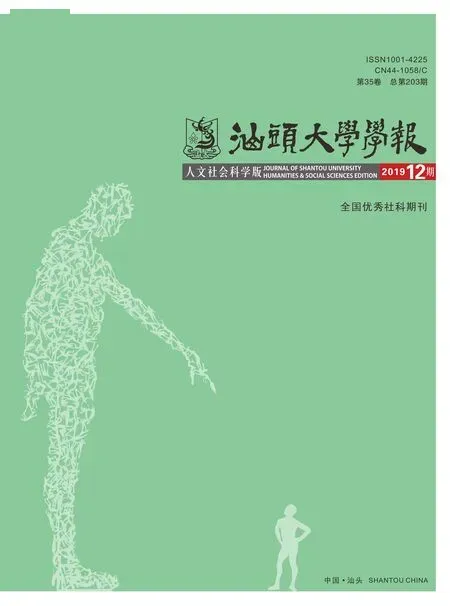我与互联网的33 年:从使用到研究使用
2019-02-12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香港 999077)
我不是做互联网技术的,但应该算是第一代的用户和用户行为研究者,用网33 年,研究20 年。
一、初识互联网
1969 年互联网诞生时,我还在上海读中学,与其他国人一样,从不知道世上已有这个神器。1986 年,我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U)读博士,见到很多新东西,其中包括BITNET,可以给全世界发电子邮件,更重要的是收发免费(当时美国国内长途电话每分钟1 美元、国际长途每分钟3-5美元),所以狂给美国各地的新朋旧友发电邮,很爽,只恨当时还发不到中国。此外,我还常用TELNET 远程登入办公室电脑、用USENET 来收看新闻包,等等。
1990 年,我从IU 毕业去康乃狄克大学(UCONN)任教。第二年网上有了GOPHER 服务,我们可以从办公室电脑浏览全美各大学图书馆的书刊资料,高效而又便利。再过两年(1993),第一代的WWW 浏览器Masaic 问世,比GOPHER 更神奇,不仅能显示文字而且还可以看图像、听音乐、播影片(当然先要花几个小时下载,然后几秒钟就播完)。学校里顿时流行起用HTML 写个人网页,学生们热衷于贴照片,我们教师则多半用来贴课件。1995 年,商业版的浏览器Netscape 诞生,但很快被微软的Internet Explorer 超出。互联网从此走出大学和研究所的象牙塔,成为易用而且免费的信息工具(这是当年对互联网的主流定位)。
二、理解互联网
互联网当然是信息工具,而且它提供的最好服务至今仍是信息(如搜索引擎、Wikipedia 等)。但是,互联网不仅是信息工具,更是大众媒体。后者除了信息,还包括新闻、娱乐、广告等。这些服务应该并非在互联网之父们的计划之中,但如果没有它们,互联网至今恐怕还是象牙塔里精英们的玩具。
我是从几次偶遇的聚会中逐渐意识到从信息工具到大众媒体的必要和可能。1995 年,我在UCONN 升为终身教职,随后到香港城市大学访学。不久接待了一位来访的老朋友,刚接手一家杂志,亟需在海外华人中扩大其读者群。他问我有何方法?我反问,几千万华人散布在世界各地,推广、销售、收款等成本极高,很难盈利。他回答,我们不需盈利,只求低成本地扩大影响。我脱口而出,那就容易了,办个互联网版,不花什么钱但能被全世界看到。这位资深老记者立刻意识到互联网就是他们踏破铁鞋无览处的神器,不久第一份网络版中文杂志就诞生了。
其实当时我只是灵机一动。然而,IU 的Christine Ogan 教授(曾教过我)则已经在探索互联网的定位问题。1996 年,她在传播学顶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Internet as mass medium”的论文①Morris,M.,& Ogan,C.(1996).The Internet as Mass Mediu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6(1),39-50.,文中并未提出博大宏深的理论,但其标题一语破的,提醒世人(至少是传播学界),互联网不仅仅是信息工具,更是大众媒体。2000 年,北京的一个跨世纪新媒体研讨会上,新浪新闻的一位副总讲道,“互联网是什么?互联网是媒体。是媒体就要按媒体的规律办,我们还不太懂媒体的规律。”我在听众席里听了很高兴,大家终于有了共识。
三、研究互联网
互联网从信息工具变成大众媒体的意义何在?首先是更大了,同时也不纯了。新闻涉及政治、娱乐涉及文化、广告涉及资本,远比搜索引擎和维基百科更具挑战。因此,更加需要加强研究。
作为长期研究媒体受众的传播学者,我的关注点是网民的使用行为。2000-2008 年间,我每年都在香港对一千多名市民(包括网民与非网民)进行一次电话抽样调查,询问其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或不适用的原因,九次共调查了上万人。随着网民日益普及而非网民减少,我改用网络挖掘技术来研究网民行为,既快速、又省钱。
20 年来,我们通过线下(电话调查)和线上(网页抓取)的追踪研究,发现和积累了一系列网民行为的特征与规律。其中与今天话题最有关系的是,网民通过使用(包括善用、误用和滥用)而改造了互联网,以满足其高尚(或者低俗甚至卑劣)的需求。社会各色机构,如“蓝”(技术界)“黄”(资本)“红”(政界)“黑”(地下社会)等,无一不是为了服务、利用、应对这些需求而介人互联网,从而推动其发展或变化。
四、展望互联网
今天,互联网50 岁了。我的前辈(互联网之父们)和同辈(第一代用户们)回顾它的诞生和演变,无不感慨万千。大家既惊叹互联网50 年来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又遗憾它的异化,与初衷渐行渐远,越来越商业化、中心化、噪音化。我亦有同感。但鉴于上述研究心得,我建议大家无须大喜大悲,用平常心坦然对之。
互联网的上半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局面,既充满了各种偶然事件,但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当年的INTERNET(包括我提到的BITNET、TELNET、USENET、GOPHER、WWW 等等系统),如果不在1995 年前后由于电信、软件等商业公司的介人而演化成商业化的大众媒体,自然会有其他系统出来填补这个市场。事实上,美国的传统媒体(如大型报业集团和有线电视网)纷纷从1970 年代开始研发各种联网或互动的媒体系统;1980 年代推出了联网信息系统(如ViewTron),但并不成功②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ewtron.;1990 年代推出了150+个频道的互动电视系统,如果当时没有WWW 网及其浏览器的竞争,我们也许现在还在通过光纤连接、在16K 大屏幕上使用500+有线电视网提供的搜索、新闻、娱乐、广告、社交等服务呢。当然,这种系统同样充满了商业化、中心化和噪音化。
同理,如果互联网在下半场里变本加厉地商业化、中心化和噪音化,超出用户的容忍度极限,我相信自然会有新的替代网络出现。会是基于生物技术的网络吗?我不知道,但我们应该不需要再等5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