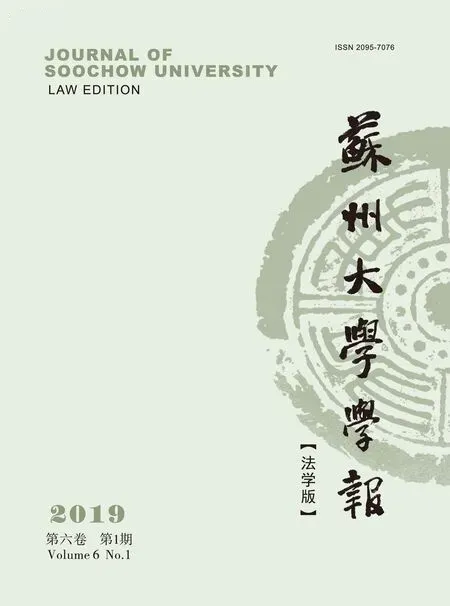违法合同的效力评价与无效类型
——《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释论
2019-02-11蔡睿
蔡 睿
一、引言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在奉行意思自治的民法之下,人们可以自由地缔结合同,为自己“立法”。[注]明确合同具有法源地位,最典型者为《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1款: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具有法律的效力。然而,自由亦非没有边界,限制个人自由以实现人人自由之并存,亦为自由题中之义。此外,现代国家为保障公共利益、社会秩序以及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也会对合同自由加以干预,其手段是在法律中增设强制性规定,将公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引入私法,使之产生私法上效果的,即是民法中的法律行为适法规范。[注]《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和第1133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343条、《奥地利民法典》第879条、《瑞士债法典》第20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1条、大陆《民法通则》第58条第5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
我国民事立法过去十分注重“公的管制”,法律行为适法规范也贯穿于我国民事立法的始终。1981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无效;1986年《民法通则》则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彼时的法律行为适法规范未区分强行法与任意法,更未区分强行法之类型,且不少判决将该项所称“法律”解释为包括规章在内的广义法律,导致司法实务中许多违反任意法或取缔规定的行为被认定无效,损及交易安全和当事人权益。[注]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的号角响起,在这一背景下,1993年《经济合同法》将“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修订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1999年统一合同法更进一步限缩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更进一步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限缩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放松管制、扩大自治,逐渐成为我国合同立法的趋势。
2017年10月1日正式生效的《民法总则》集全国民众之智慧,开启了中国民法典时代的到来。《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规定的法律行为适法规范,继承自《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而又增加但书规定,实为一大亮点。这一目的保留条款的引入,增大了违法合同效力认定的弹性,扩大了私人自治的范围,但也加大了法官适用法律的难度和责任。如何看待《民法总则》的这一转变,如何把握立法变革背后带来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突破,值得法律解释者予以深入思考。笔者不揣知识浅陋,在此做出一些努力,就教于方家。
二、违法合同效力评价路径之转向
(一)《合同法》时代的评价标准:规范分析进路的迷雾
对于法律行为适法规范,《德国民法典》第134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1条均设但书规定,因此,学界公认以上条款除具有引致规范的功能外,兼具有解释规则的性质。[注]Vgl.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14f.与之不同,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未设但书规定,在文义上给人以一经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就归于无效之感,显得过于绝对。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限缩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而使后者具有了解释规则与概括条款属性。[注]参见韩世远:《民法的解释论与立法论》,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3页。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15条更进一步以“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相对,违反后者法院应认定合同无效,违反前者则“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注]需指出的是,司法解释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作目的论限缩,意在强调仅在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方才无效,但根据《指导意见》第15条的说法,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合同也有可能无效,其立场似已发生游移。实际上,在司法裁判中,因违反市场准入条件,而被认定合同无效的案件大量存在,如违反特许经营的规定订立的合同,被法院较为一贯地认定为无效。参见陈允斗与宽甸满族自治县虎山镇老边墙村民委员会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81号民事判决;李晓吉与杨春艳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上诉案,(2014)辽民三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
司法解释引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一对概念,并非其独创,史尚宽先生在其著作中就有效力规定与取缔规定的区分,史先生认为,强行法得为效力规定与取缔规定,前者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注]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据考证,史先生这一区分,又源自于日本学说,[注]参见苏永钦:《以公法规范控制私法契约——两岸转介条款的比较与操作建议》,载《人大法律评论》2010年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在日本,将民法内的强制性规定称为强行法规,而民法外的强制性规定则称作管制法规,管制法规常常未就违反法律行为的私法效果作出规定,需要通过解释以决定之。[注][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第248-249页。违反将导致私法上行为无效的,被称为“效力规定”,不产生私法上效果的被称为“(单纯的)取缔规定”。[注]参见[日]大村敦志:《基本民法Ⅰ 总则·物权总论》,有斐阁2007年版,第66-67页。转引自韩世远:《民法的解释论与立法论》,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在司法层面,带来的进一步问题是如何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此,实务界人士提出正反两个标准。在肯定性识别上,首先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其次,若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无效的后果,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为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否定性识别上,若强制性规定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或纪律管理的需要,一般不认为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资格。不过,该人士又话锋一转,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判断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注]参见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正是因为区分不易,上述《指导意见》第16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但这样一来,实际上使这一区分虚化为一个分析的框架,从这一对概念本身,并不能推出合同违反某一具体强制性规定的法律效果。
与区分标准的模糊相对应的是司法裁判论证思路的分歧,在有的判决中,法院会整理多个涉及规范内外的理由,得出相关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或“管理性”的结论,进而作为合同效力评价的前提。[注]例如在(2013)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53号案件中,法院认为虽然涉案承包合同未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8条第3项经村民会议同意,但双方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故该“民主决议原则”仅为“管理性强制规范”,违反该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在实践中,也有判决省略区分说理环节,径直认定某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或“管理性”规定,进而认定合同有效还是无效。例如在中建六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诉沈阳永来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7条规定的:“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使被申请人永来房地产公司在涉案建筑工程开工前没有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也不影响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477号民事判决书。还有的判决,是在认定相关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后,再结合其他规范内外的理由,认定违反强制规范的合同是否无效。[注]例如在(2014)皖民二终字第00114号判决书中,二审法院除了认定《公司法》第16条第1款非“效力性”强制规范,还从该条未明定担保合同无效仅为决策程序之规制,如果认定担保无效有害交易安全等角度论证涉案保证合同应为有效。有学者将前一种思路概括为描述型进路,将后一种思路概括为要件型进路。前者将论证的结论又作为论证的前提,实则是循环论证、同义反复;后者将“效力性”与“管理性”规定的区分仅作为得出结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实则是使“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变得名不副实。[注]参见姚明斌:《效力性强制规范裁判之考察与检讨——以<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实务进展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综上而言,以强制性规定属于“效力性”还是“管理性”作为决定合同是否无效的标准,实则是将判断重心放在强制性规定性质的甄别上,可称作是一种规范分析进路。然而这种规范进路存在的问题在于,效力性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是先定的,而是以合同违反规范的效果为标准作出的区分,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导致无效的则可归入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反过来将之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原因,无疑从逻辑上存在倒果为因的问题,正如苏永钦教授所言,这实际上是在“以问答问”。[注]参见苏永钦:《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的法律行为》,载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因此,这一对概念的区分除了提示裁判者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或者随着审判经验的积累,这一对概念可作为速记符号在审判中快速认定合同效力之外,对裁判的指导功能实际上非常有限。
(二)《民法总则》的新起点:基于规范目的的个案衡量进路
在《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中,从一审稿到三审稿,草案均吸收了司法解释的做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注]《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第155条、《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第147条、《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第155条。但在最终颁布的《民法总则》中,立法者却改弦更张,删除了“效力性”字样,而增加“但是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这一但书规定。从这一转变可以看出,立法者没有接受在司法实践中已被广泛应用的“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这一对概念,而是选择了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类似的规范目的保留模式,这对我们在违法合同的效力判断问题上,走出规范分析进路的迷雾,转而求助于具体规范目的的考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可能。
由于但书规定的存在,从《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规范本身,并不能得出违反某一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毋宁说他只是对法官作出了授权,让其在具体个案中予以分析判断,而判断的依据则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申言之,取决于对具体强制性规定的解释,而具体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则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从比较法上看,规范目的说(Normzwecktheorie)也是现今德国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的无效只在同“法律的旨意和目的”相符时才予以考虑。[注]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就违反法律禁令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倾向于个案考察,并明确强调法律禁令的意义和目的(Sinn und Zweck)始终是起决定作用的,而每条规定的意义和目的各不相同需个别考察。[注]Vgl. 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11.在具体的解释原则上,正如梅迪库斯教授强调的,还应使法律制度不存在评价上的矛盾,如果法律禁止人们从事某项行为,那么,就不可能通过法律行为为人们设定从事该项行为的义务。例如,根据第134条规定,使一方当事人负有实施某项刑事犯罪行为的合同是无效的。如果一项行为既为法律所禁止,同时却又可以成为合同约定的要求,那么这就会使法律制度变得自相矛盾,令人难以承受。[注]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页。
规范目的保留条款的引入,为违法合同的效力判断提供了一个基于规范目的的分析思路,但这一思路如何在实践中展开,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尽管有学者主张法律行为适法规范中的 “强制性规定”不限于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尚应包括私法上的强制性规定;[注]耿林:《论中国法上强制性规定概念的统一性——兼评金可可教授<强行规定与禁止规定>》,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47页。但不容否认的是,法律行为适法规范的主要功能仍是沟通公法强制与私法自治的管道,即通过它在民法中引入公法强制性规定,作为对合同效力的评价依据。[注]参见谢鸿飞:《合同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7页。公法上的规定并非以法律行为为规制对象,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命令或禁止当事人为特定行为,而对违反这些规定的效果也多以公法上的制裁为主,因此,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间接的、计划外的影响。如同行政行为应坚持“谦抑性”原则一样,公法上的规定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也应有所适度,职是之故,通过引入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作为评价违法合同效力的依据,自然也是顺理成章,这点也已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注]参见黄忠:《比例原则下的无效合同判定之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
一般认为,比例原则包含三项子原则:其一为妥当性,要求国家措施必须适合于增进或实现所追求的目标之目的;其二为必要性,就是要靠以往的经验和学识的积累,对所追求的目的和所采取的手段之间的相当比例进行判断,保证所要采取的手段在诸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中是最温和的、侵害最小的;其三为法益相称性,要求干预的严厉程度与理由的充分程度之间要非常成比例,要求以公权力对人权的“干涉份量”来断定该行为合法与否,要使人民因公权力的行使受到的损害比起公权力由此获得的利益来讲,要小得多,要合算的多。[注]参见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5页。具体到违法合同无效的判定,在比例原则下,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对此不妨参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的规定,该示范法第3.3.1条第3款就确定合理救济的考量因素予以了列举,这些因素包括:被违反之规则的目的;该规则旨在保护的人群之类别;依被违反之规则可以施加的制裁措施;违反的严重性;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项违反;是否合同的履行必然导致该违反行为以及当事人的合理期待。[注]如何通过比例原则分析违法合同的效力,另可参见黄忠:《比例原则下的无效合同判定之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
比例原则为实践中的法官判断违法合同的效力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路径,然而在利益衡量的思路下,何种利益为重、何种利益为轻有时并非清晰可见,若诸种利益难分伯仲,法官依据比例原则仍然难以得出确切结论时,该如何决断?这就涉及第153条第1款的规范性质问题,即适法规范本身是否提供了一个解释规则?依弗卢梅教授的见解,《德国民法典》第134条“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该条并没有规定任何在“有疑义时”可以基于其认定违反禁止性法律的行为无效的推定规则或解释规则。[注][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02条。与之相反,卡纳里斯教授则基于公法优位的观点,认为第134条清晰地表明了原则——例外的关系,在有疑义时,违反禁令的法律行为无效。[注]Vgl. 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17-19f.对于该问题,我国民法学者的立场可谓鲜明一致,均倾向于维护私法自治,认为在违法合同有效还是无效所保护的利益孰轻孰重难以权衡时,应认定合同有效。[注]参见胡智勇:《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法律强制性规范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关系之分析与构建》,载《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宁红丽:《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反思与优化》,载《法学》2012年第4期。考虑到我国缺乏私法自治的传统,并且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干预仍然太多而不是太少,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倾向性意见确是值得赞同的。
三、基于具体强制性规定和违法行为的类型化整理
以规范目的为准绳在个案中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不过不容忽视的是,这一路径实际上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破坏司法裁判稳定性的危险。因为当法官进行利益衡量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法官的个人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生活环境等,这些“前见”使得法院判决的不确定性成为必然。因此,在利用个案衡量思路保持违法合同效力认定的灵活性的同时,找到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指引法官裁判,增加判决的稳定性,也是必须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经由案例的积累而对强制性规定以及违法行为做类型化整理,或可提供帮助。以下结合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各种方案,就违法合同的效力判断做出类型化的尝试。
(一)基于强制性规定的类型
对于广义的强制性规定,学说上有处分界限规范与狭义强制性规范之区分,前者多出现于私法,而后者多出现于公法。[注]对此种划分的介绍,可参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对于私法上的或称处分界限的强制性规定,如《物权法》第211条关于流质的规定、第185条第1款关于设立抵押权的书面法定要式的规定等,其规范内容往往针对法律行为,违反这些规定往往在私法之外并无其他公法上的制裁措施,自规范目的而言,如果不否定违反这类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则这类规定将缺乏任何制裁后果,也就失去了强制本身的意义。与之不同,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通常都有相应的公法上的制裁措施,民事制裁只起配合作用,所以在公法制裁手段可以实现规范目的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对该行为施以民事后果上的制裁。[注]参见耿林:《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为中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职是之故,对于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应倾向于行为私法上的后果不受影响;对于私法上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则应倾向于行为私法上效力的否定性评价。
(二)基于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利益
在法律规定的背后,都蕴含着很多价值观念,在利益法学者看来,法律规范总是体现着特定的利益冲突,立法者通过法律规范公开他们的利益评价。这种立法上的利益评价对法律的适用是有约束力的。因此,法律适用的主要方法也就是去发现这种法律规范背后的原因利益。[注]Bydlinski, Franz,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echtsbegriff, Springer-Verlag, Wien, 2. Aufl. S.115ff.循此思路,违法合同的效力评价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衡量问题,即维持合同效力的利益与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利益何者优先的问题。
就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利益,可依不同标准予以划分,例如从利益主体的不同划分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还有学者从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影响后果上的差别,把利益区分为绝对公共利益维护型、弱势群体等多数人利益维护型、民法理论制度维护型、当事人利益维护型以及形式要件维护型。[注]耿林:《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为中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保护利益的探明方法,可从法律的目的条款中寻得,如《建筑法》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有时候,一部法律的立法目的既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也在于保护特定当事人的利益,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地产的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时,一个具体强制性规定的保护利益就需要具体分析,例如该法第45条关于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的规定就主要关系当事人利益。由规范保护的利益出发来决定违法合同的效力,较为一致的共识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于合同自由,违法合同有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认定为无效,若违法合同仅涉及当事人利益,则一般不认定其无效。[注]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32页。
(三)基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对象
以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还是双方来决定合同是否有效的做法来源于德国判例,[注]Vgl. RGZ 60, 273, 276f.亦得到部分德国学者的追随。[注]Vgl. Schricker, Gesetzesverletzung und Sittenverstoss, 1970, S.64.在这种类型划分下,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都违反了法律,则这种情况应当导致无效。相反,如果只是一方当事人违反了法律上的禁令,则通常不导致无效。[注]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70页。于此最为常见的例子是买卖合同因出卖人的欺诈而成立,该法律行为违反了《德国刑法典》第263条,然而,该合同并非自始无效,而只能通过买受人基于恶意欺诈进行的撤销使之无效。这一划分的正当理由在于,当只有合同一方违反法律禁令时,无过错的相对方的利益也应当被考虑,例如在缔结承揽合同时,经营者违反了《德国打击非法劳工法》,但顾客对此并不知情,守法顾客的利益要求他仍享有履行以及保障请求权,因此该合同不因《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而无效。[注][德]汉斯·布洛克斯、[德]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33版),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
(四)基于强制性规定的禁止内容
1.弗卢梅教授的观点
在弗卢梅教授看来,应当对那些因直接涉及法律行为而使其“不法”的法定禁止,与那些涉及法律行为之实施行为的禁止性规则予以严格区别。就后一种禁止性规则而言,它仅直接使法律行为之实施行为不法,至于法律行为是否或在何种前提条件下也会因法律行为之实施行为受到禁止而间接具有不法性的问题,应当分别予以考察。[注]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05页。
一般来说,那些直接涉及法律行为的禁止性规定以禁止法律行为为其内容,典型者如一般法定让与禁止。在这种情形,禁止性规范的效力仅仅取决于法律行为本身违背禁止性规范,而无须考虑法律行为实施者的行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特别是,不取决于法律行为实施者是否明知或应知法律禁令。[注]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05-406页。
如果禁止性法律仅直接涉及法律行为之实施行为,则该禁止性规定完全有可能也间接涉及法律行为。如刑法中的规定一般仅针对事实行为,而间接的波及作为该事实行为原因的法律行为。此时,只有当法律行为的实施完全满足犯罪构成要件时,也即,不仅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前提条件,而且满足其主观前提条件时,禁止法律行为实施的刑法规范才能作为禁止性法律规范适用于业已制定的法律行为规则。[注]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页。
2.卡纳里斯教授的观点
卡纳里斯教授将违反法律禁令的法律行为整理出四种类型:因其内容被禁止的法律行为;因缔结环境而被禁止的法律行为;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身份而被禁止的法律行为;因其后果而被禁止的法律行为。[注]Vgl. 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20-53f.
在“因其内容被禁止的法律行为”的类型中,卡纳里斯教授又划分了四个子类型:第一,在法律行为违反针对合同双方的禁令的情况下,合同原则上应无效。第二,在违反仅针对一方当事人的禁令时,如果单方违法是内容性质的,则另一方当事人必然一同从事了单方违法行为,因为他参与了法律行为内容的形成,内容违法也因此原则上落在双方当事人的风险范围内,此时,合同也应依据第134条而被宣告无效。[注]例如国家颁布了某出口禁令,尽管通常只是针对国内的出口商,然而要实现其目的,就必须使合同无效。第三,在单方违法时,应小心地检验它是否真的影响到法律行为的内容,如果合同内容与违反行为无关,则该违法不应影响合同的效力。[注]例如在受托人违反《德国刑法典》第226条将信托物出卖时,买卖合同和所有权移转通常都和背信的要件无关,而只是完全正常的法律行为,其内容和其他法律行为无异。因此,此处的违法只是信托人领域内的内部事务。Vgl.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27f.第四,在法律禁令恰恰是为保护另一方当事人时,卡纳里斯教授提出此时的合同应单方部分无效的观点。[注]例如违反《经济刑法典》(WiStG)第5条和《刑法典》第302a条的租金暴利,卡纳里斯教授认为此时可以对租金请求权施以完全无效的制裁,但维持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取代暴利租金请求权的是不当得利请求权,根据《民法典》第812条第2款,该请求权的内容为使用租赁物的价值赔偿。Vgl. 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28f.
在“因缔结环境而被禁止的法律行为”类型中,卡纳里斯教授认为法律行为原则上有效,其典型例子为违反《商店关门法》而缔结的买卖合同。[注]Vgl.RGZ 60,276; 103,263.不过,作为该项原则的例外,当违反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禁令时法律行为应无效。例如违反禁止在流动经营(Reisegewerbe)中提供借贷合同中介和缔结借贷合同的法律禁令,此时,根据《工商管理条例》第56条第1款第6项,该禁令只针对一方当事人,且仅针对缔约环境,但是本条的理由在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免受诱导和压力,因此违反禁令之合同仍应被宣告无效。[注]Vgl.BGHZ 71,358,360ff. 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37.
在“因为当事人一方之身份而被禁止的法律行为”类型中,卡纳里斯教授又划分了三个子类型:若是针对双方当事人的法律禁令,则法律行为无效,其代表为联邦最高法院在违反《赌场条例》(SpielbVO)案中的判决。[注]Vgl.BGHZ 37, 363,365f. 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41.若是禁令只针对一方当事人,则此时与上一种情形并没有本质差异,合同仍应无效。若违反的是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禁令,则上文处理内容违法时提出的单方部分无效的方案能再次解决这个问题。[注]Vgl. 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40-47f.
在“因其后果而被禁止的法律行为”类型中,卡纳里斯教授认为此类法律行为原则上有效。如在不动产买卖中为了“节省”不动产交易税而在公证书上写了过低的价格,此时,并非法律行为本身违反法律禁令,因为相关的税法规定并未禁止所涉合同,而是仅仅针对其附带的计划偷逃税行为。合同本身是预备行为,尚不足以使其违法。[注]Vgl. 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48f.不过,当法律行为与违法特别紧密相关时,如在偷漏税案中,当偷漏税构成合同的“主要目的”时,合同应为无效。[注]Vgl. 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49-50f.
(五)小结
若将以上类型的划分作为认定违法合同无效的原则和标准,无疑是不合格的,因为这些“标准”要么过于笼统,要么不够周延,可以找到许多例外。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标准”的角度而是从“类型”的角度去审视这些划分,那么我们仍然会发现其价值。实际上,类型化思维是建立在案件的整理积累之上,其并非是为了取代规范目的在个案衡量中的“标准”作用,而是为了辅助审判,使法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其目的在于保证判决的稳定性。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个类型的划分并非相互隔绝,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进行综合的归类,例如对某个强制性规定的分析,可以使它同时归入“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公共利益保护型规定”“双方当事人违反型”“法律行为内容禁止型”等类型,若其落入的无效类型越多,则法官据此认定合同无效的可能性越大,判定合同违法无效的准确性也越高。
四、违法无效之对象——以“对赌协议”为例的说明
法律行为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在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立法例下,须追问无效者究为负担行为还是处分行为,这就涉及强制性规定的规制对象。
一般而言,强制性规定通常所针对的是合同的内容,违反该强制性规定原则上仅导致负担行为无效。为履行无效的负担行为所实施的处分行为仍是有效的,不过由于欠缺给付原因,可以根据不当得利的规定要求返还。[注]如在德国,某人通过事务处理合同被委托处理他人的法律事务,则尽管他未根据《法律咨询法》第1条第1款第1句得到许可,但无效的仍只是事务处理合同以及必要时被授予的意定代理权,而非报酬的转让。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德]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33版),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有些时候,强制性规定也会同时禁止负担行为的内容与特定物品的转让,那么除负担行为外处分行为也会同样无效,最典型者要数禁止违禁品交易的法律。[注]德国《麻醉药品法》第29条第1款第1项对交易麻醉药品的禁令,从中不仅可以得出买卖合同无效,而且对药品以及作为价款被支付的金钱的转让行为同样无效。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德]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33版),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146页。还有的时候,强制性规定仅针对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并不会因违反该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如我国台湾地区旧“土地法”第30条规定:“私有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为限,并不得移转为共有,但因继承而转移者,得为共有。违反前项规定者,其所有权之移转无效。”[注]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页。
我国法律是否承认物权行为(sachenrechtliche Rechtsgeschaft),在学界存有极大争议。[注]参见柳经纬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民商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不过不容否认的是,接受“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作为分析范畴,在对一些法律问题的解释上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注]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227页。在违法合同的效力评价问题上,亦是如此,通过明确强制性规定的禁止对象,使法律行为的无效精确限缩在负担行为或处分行为上,或可收到缩小无效合同范围,扩大私法自治的功用。下文以资本市场近来频繁出现的“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为例展开说明。
“对赌协议”(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又称“估值调整机制”,其实质是投融资双方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一种约定,根据约定事件的出现与否,来安排投融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融资方利用“对赌协议”可以解决融资难问题,投资方则借由其来规避自身投资风险,常见的“对赌协议”类型主要有:股权对赌、优先权对赌、现金对赌和股权回购式对赌。[注]参见韦祎、崔蕾:《“对赌协议”司法第一案的评析与启示》,载《天津法学》2013年第2期。实践中,由于“对赌协议”涉及违反《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的强制性规定等问题,其效力一直存有争议。[注]相关文章可参见罗文峰、李明致:《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载《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唐英:《甘肃“对赌协议案”判决之评析——以法律方法的运用为视角》,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1期;华忆昕:《对赌协议之性质及效力分析——以<合同法>与<公司法>为视角》,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抛开“对赌协议”涉及的复杂问题不谈,这里仅就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之于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的问题进行说明。
实践中存在投资方与目标股东之间的股权对赌协议,[注]例如浙商创投与普路通之间签订的对赌协议。参见“【IPO业务】近期企业境内IPO涉及对赌条款的案例总结”,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3760f0100ou5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6月13日。假设目标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而参与对赌的股东又为公司的发起人或者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此时有可能与《公司法》第141条的强制性规定发生抵触,于此,“对赌协议”是否因违法而无效?若不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则“对赌协议”将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从效果上看这否定了公司的一条合理的融资渠道,对公司并不有利。然而,若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则从“对赌协议”的内容上看,其实质上并不会导致股权的转移,而只是为相关主体设定负担,应属于负担行为的范畴。而《公司法》第141条禁止的是特定主体在特定时期内的股权转让行为,其禁止的是股权的“转让”,属于处分行为的禁止。上述“对赌协议”在签订时并不会导致股权的转让,只是设定了在特定条件下转让股权的负担,因此“对赌协议”本身并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141条而无效的问题。
另一例子是股权回购式对赌,例如在被称为“对赌协议司法第一案”的“苏州海富诉甘肃世恒案”中就存在这样的条款。实务中,“对赌协议”中约定由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司法部门一般不承认这样约定的效力。[注]参见黄占山、杨力:《附“对赌协议”时股东承诺回购约定的效力》,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0期。然而,从裁判效果上看,这样的处理方式却并非合理,因为“对赌协议”往往涉及一揽子交易,除股权回购条款外,往往还有投资条款以及各种担保条款,若一概认定此类“对赌协议”违法而无效,则只能要求恢复原状,这既不符合尽量维持合同效力的鼓励交易原则,也不能适应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因此,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缩小违法无效对合同整体的影响。笔者认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对于违法“合同”无效范围的限缩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首先,投资人与目标公司签订的股权回购式“对赌协议”并不会导致股权回购的即时发生,它只是为目标公司设立了一个负担,并且这一负担行为的生效尚取决于特定条件的成就。其次,《公司法》第74条与第142条虽然分别就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自身股权(股份)作出限制,然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其仍可通过“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方式回购股东的股份,法律并没有堵死股份有限公司落实股份回购条款的道路。即使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虽然采取封闭式列举的方式,禁止公司履行股权回购条款,但是考察该条的立法目的,其主要在于贯彻资本维持原则,保护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然而需注意的是,违背资本维持原则的实际是股权回购的履行,而非回购股权的负担,申言之,该条真正禁止的其实是处分行为而非负担行为。因此,作为处分行为禁止的强制性规定并不会导致作为负担行为的“对赌协议”无效。当然,由于强制性规定的存在,这种股权回购式“对赌协议”可能最后不能履行(法律上不能),投资人只能据此要求目标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注]需说明的是,合同当事人双方对合同可能不能履行的风险均是知晓的,因此这里相对人的违约责任可以考虑过失相抵原则的适用。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在于,由于“对赌协议”仍然有效,那么附随于“对赌协议”的各担保条款也同样不失去效力,因而投资人可向其他股东或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通过“对赌协议”的例子可以发现,对强制性规定禁止的对象进行精确定位,区分是负担行为的禁止还是处分行为的禁止,可使法律行为无效的范围得以限缩,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意思自治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无效的对象,《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以“民事法律行为”代替《合同法》第52条的“合同”,为上述区分扫除了解释上的障碍。
五、合同违法无效之类型
(一)《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之“但书”功能再审视
对于法律行为适法规范中的但书条款,传统见解认为其功能有二:一为指示法律本身规定有其他效力的情况;二为提示法官注意观察强制性规定的目的,不应将违法合同全部认定为无效。[注]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对于传统的第一种见解,适法规范既然立于《民法总则》之中,当其他法律对违法合同的效力另有规定时,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适用特别规定即可,自然没有再叠床架屋适用该规则之必要。因此,“但书”之功能主要在于第二点,它授权法官考察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以判定违法合同是否应归于无效。然而,“但书”的功能是否止步于此,仅在于“规范目的说”的证明,还是有进一步挖掘其功能的可能,换言之,违法合同除了“无效”及其相对的“有效”之外,是否还包括其他的效力瑕疵类型?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多数学者仅将第134条的“但书”作为“规范目的说”的证明,并没有把法律行为是否违反禁止规范与违反禁止规范是否当然无效二者截然分开,而是笼统地视为一件事,依各禁止规范的目的来决定法律行为是否“因违反禁止规范”而无效。[注]参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例如韦斯特法尔教授认为法院不可以再进一步对“违反”法律的法律行为效果加以调整,即不认为“但书”为另一独立的价值补充过程,而径认此一规定为赘文。[注]Vgl.Westphal, Zivilrechtliche Vertragsnichtigkeit wegen Verstosses gegen gewerbrechtliche Verbotsgesetze, Berlin, 1985, S.132.不过,与多数学者的认识不同,卡纳里斯教授却认为第134条这一解释规则具有双重功能:一是有疑义时,违反禁令的法律行为无效(unwirksam),而非有效(wirksam);二是作为无效的特别形式,在有疑义时为完全无效(volle Nichtigkeit),而非诸如部分无效(Teilnichtigkeit)、效力待定(schwebende Unwirksanmkeit)、相对无效(relative Unwirksanmkeit)或类似的无效。[注]Vgl.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16-17f.卡纳里斯教授通过对合同无效类型的区分,在第134条的传统功能外拓展出一层新的功能,赋予“但书”规定的另一层含义,即通过规范目的的考察可将违法合同评价为部分无效、效力待定与相对无效等类型,可谓颇具启发意义。
实际上,在德文中,描述无效的词汇并非单一,除第134条所使用“nichtig”外,尚有“Unwirksam”,一般认为,前一个词表达的是绝对无效,而后一个词使用的范围更广,在不同情境表达不同意义。据王宠惠先生考证,“unwirksam”在《德国民法典》中主要在三种意义域中使用:“它有时意指(绝对)无效(如德民第111条);有时意指法律行为并非在绝对意义上无效,而只是在某些方面或对某些人无效(如德民第135条、第161条);有时又意指法律行为尚未满足,但随后可能满足一项或数项有效要件之情形(如德民第108、174、185条)[注]The German Civil Code,Translates and Annotated by Chunghui Wang,Stevens and Sons,Limited, 1907, p.600.转引自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230页。。根据现今德国学者的通说,一般将“Unwirksamkeit”作为所有无效形态的上位概念,而“Nichtigkeit”只是“Unwirksanmkeit”中的最强程度。[注][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页。在我国法中,依多数学者见解,合同效力瑕疵除存在绝对的“无效”之外,也存在“效力待定”(《合同法》第47、48、51条)、“部分无效”(《民法通则》第60条、《合同法》第56条后段)等样态。《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若将这里的“无效”理解为自始、当然、确定、绝对的不生效力,则从该款但书的“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除可得出违法合同可以有效的结论外,还可得出违法合同存在其他效力样态的结论。
上述结论可从比例原则中获得正当性支撑,根据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公权力对私人自由的干预应适度,不能超过实现行政目的的需要。在法院依据强制性规定评价合同效力时,除要考虑私法上制裁的必要性之外,还应该对私法上制裁程度的必要性进行论证,也就是说,即使根据规范目的得出合同效力应受否定评价的结论,法官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合同效力受否定评价的程度,是彻底否定合同的效力,还是仅仅有限制的否定合同的效力。
综上而言,笔者认为《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的但书规定,除为违法合同预留有效的可能外,还为违法合同预留了除“自始、确定、当然、绝对、完全无效外”的其他效力样态的可能,这使得违法合同的无效类型得以丰富化,可让法官根据需要在诸多无效样态中选择最为合适的方案去认定合同效力,以最大程度保证合同自由。本文以下部分结合司法解释和实务中的问题对违法合同可能存在的无效类型进行简要的分析说明。
(二)与绝对无效相对之无效
一般认为,无效为绝对无效,那么与之相对的自然就是相对无效。实际上,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这对概念在比较法上即已存在,不过在不同法域对其内涵存有不同理解。在德国,相对无效是指某项行为仅仅相对于某个特定的人不生效力,而对该特定人之外的其他人则是有效的,最为典型者,即是《德国民法典》“物权编”中规定的违反预告登记的处分。[注][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与之不同,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这对概念在法国有完全不同的意涵,现代法国法学理论一般从无效事由以及可以主张无效的主体来区分二者。比如,当合同因违反保护社会利益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时,是绝对无效,当合同因违反保护个人利益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时,是相对无效;对于绝对无效,任何利害关系人均可主张其无效,而对于相对无效,只能由法律规定意在保护的特定人主张。[注]参见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244页。我国学理上,有学者认为任何人均得主张,并得对任何人主张之无效为绝对无效,而一定之人或对于一定之人不得主张无效者,谓之相对无效。[注]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这一理解从无效主张之主体和无效之效力范围来界定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似乎同时吸收了德国和法国的区分标准,不过又有所不同,德国的相对无效是在强调相对于特定人无效,而我国似在强调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注]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相对无效在我国法中不乏其例,如《合同法》第80条规定的债权转让的事实未通知债务人时,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再如《物权法》第194条第1款规定的抵押权顺位变更协议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的,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注]参见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将相对无效引入违法合同的效力评价之中,作为合同无效的类型之一,可以起到软化无效制度的僵硬性的作用。例如《物权法》第191条第2款规定:“在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尽管有不少学者从法政策的角度对该条立法提出尖锐批评,[注]参见许明月:《抵押物转让制度之立法缺失及其司法解释补救——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91条》,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但在法律既成的情况下,如何运用解释方法缓和该条的僵硬性,最大程度地矫正立法的弊端,也是值得思考的方向。该条作为强制性规定,并且直接指向法律行为,对违反它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应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即是如此,亦可通过两种途径尽可能地消除其负面影响:其一,正如有学者正确认识到的,该款对抵押物转让的影响只及于处分行为,当事人之间的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应受到影响;[注]参见陈永强、王建东:《论抵押物转让的法律效果——以对我国<物权法>第191条的解释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9期。其二,即使处分行为的效力需受该条的限制,但从该款之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而非涉及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处分行为的无效限定于相对无效范畴,唯其不得对抵押权人主张,但在买卖合同相对人之间,转让行为仍然有效。
(三)与全部无效相对之无效
我国《民法通则》第60条、《合同法》第56条后段、《民法总则》第156条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制度。依学者解释,民事法律行为一部无效时,原则上应全部归于无效,例外情形,以无效部分除去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为条件,可以认可其他部分为有效。所谓一部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主要情形有:其一,民事法律行为标的之数量超过法律许可范围;其二,民事行为之标的,由数种不同事项拼合而成,其中一项或数项无效;其三,民事行为非主要条款,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公序良俗而无效。[注]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实务中,存在不少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部分无效的案例,如2008年第5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崂山国土资源分局与青岛乾坤木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定未经政府批准的131亩土地使用权出让无效,但合同中经过政府批准的84亩土地使用权出让有效,其他合同条款仍然有效。[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不过需说明的是,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被评价为部分无效,此项评价的依据并非仅在于部分无效的一般规定之中,还在于适法规范的但书规定之上。[注]参见耿林:《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为中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342页。认定合同部分无效在某些场合可起到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如须经审批方能生效的合同,可能存在一方当事人恶意不办理审批而使合同无效,从而逃脱合同义务的情况,此时,准确认定合同部分无效而部分有效即可实现公平正义。对此,正面的例子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条第2款的规定:“合同因未经批准而被认定未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的效力。”此时,认定履行报批义务条款部分先行生效,促使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防止其恶意抗辩,可谓十分合理而正确。
不过,这里应区分合同部分无效与合同给付内容的变更。根据民法理论,法律行为部分无效的前提是行为成立的一体性(Einheit des Zustandekommens)和行为的可分性(Teilbarkeit),对于后者,在通常情形下,只要涉及某项给付的范围或者排除责任的范围,就不能认为存在可分性,因为对过高的给付或过度的排除责任进行“维持效力的限缩”,不会使合同部分有效,而是要对合同作全部变更。[注]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页。例如在民间借贷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年利率超过36%的,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规定初看之下是合同部分无效的规定,然而当事人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实则是一个整体,认定超过法定利率的部分无效与其说是合同部分无效,不如说是法院行使职权变更合同内容,以使借款利息控制在法律许可的上限。由此带来的进一步问题是,这种依职权的法定变更是否合理?正如卡纳里斯教授在解释违反租金暴利的合同时所说,如果出租人仍然可以要求获得法律上限所允许的租金,则无疑法院将帮助暴利者获得最佳后果,且免除了他形成正确和经济上最为有利的合同内容的风险。因此,卡纳里斯教授认为此时应认定合同为“单方部分无效”(halbseitige Teilnichtigkeit),出租人的租金请求权被认定为无效,其只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但是承租人仍享有获得租赁物的请求权。[注]Vgl.Claus-Wilhelm Canaris,Gesetzliches Verbot und Rechtsgeschaeft, Heidelberg 1983, S.28-29f.卡纳里斯教授的这一建议颇具启发意义,当强制性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合同一方当事人时,法院依职权调整合同内容至法律所允许的上限,也许并不能很好地贯彻规范目的,这种单方部分无效的效力评价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并且,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的合同效力评价结果的出现,当事人在订约时就会慎重考虑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而法律规范的指引作用也得以彰显。[注]从笔者在基层人民法院实践中了解到的情况看,司法解释对超额利息进行职权调整而不是宣告利息条款无效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高利贷者,高利贷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规定超高利息,只要不被起诉就可以获得暴利,即使被起诉至法院,法院也只是将利率调整至法定上限,该司法解释所期望达到的保护借款人的规范目的不能说完全得到实现。
(四)与自始无效相对之无效
关于自始无效,可于不同层面上理解:一为以无效原因之发生时间,可区分为自始无效与嗣后无效,前者指法律行为成立当时即有无效原因者,后者则指法律行为之成立与其效力之发生并非同时,而于其间发生无效原因者。[注]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二为以无效的溯及力之有无,可区分为自始无效与向后的无效。这里所指的自始无效是在第二个层面上使用。
《合同法》第56条前段与《民法总则》第155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拘束力。因此,当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被确认无效时,合同当事人应相互返还各自取得的利益。然而,基于强制性规范的目的,这一效果可能并不符合被保护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对于禁止使用童工的强制性规定,考虑到其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促进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注]参见《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1条。,若认为招用童工的雇佣合同自始无效,令双方返还已经取得的利益,可能对童工更为不利。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有限制合同无效的溯及力,而使其仅向后发生的必要。对此,有学者主张雇佣童工合同应“自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并处罚招用童工行为之时无效”。[注]朱广新:《合同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页。从比较法上看,为解决特别是在继续性债之关系中溯及自始无效的弊端,学者们提出了“事实合同”“自我矛盾行为禁止学说”等理论。参见耿林:《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为中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345页。这一立场值得赞同,在《民法总则》生效后,其依据可来自第153条第1款的但书规定。不过这里需要额外指出的是,在上例中,合同被宣告无效之前的这段期间内,承认合同完全有效可能也对未成年人不利,因为雇主同样可以基于合同享有履行请求权,并且单纯依靠向后无效可能导致雇主存在侥幸心理,有诱使其躲避查处的问题。因此,更加完满的做法是,在合同被宣告无效之前,合同也只是单方部分有效,即只有未成年人基于其劳动享有报酬的这部分请求权有效。
(五)与当然无效相对之无效
一般认为,合同无效为当然无效,所谓当然无效,即无待主张,也不必经由一定程序使其失效。[注]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可见,当然无效蕴含两层意思:首先,不需要任何人主张,法院得依职权认其为无效,进而也没有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其次,不需要经过任何程序,则法院或行政机构对合同无效只是“确认”而非“认定”。不过,现实中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五花八门,并非所有合同都会被起诉到法院,当事人可能私下里已经对合同履行完毕,法院也无法知晓这些合同的存在,而去主动宣告其无效,如此一来,所谓的当然无效必将造成选择性执法,造成现实与理想状态分离的尴尬境地。[注]参见谢鸿飞:《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强制性规定都会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有可能在纠纷发生时无效事由已经消除,这时不分情况地一概认为违法合同当然无效可能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因此,不妨认为违法合同在当然无效之外,还存在非当然的无效类型,这种非当然的无效或是需要特定当事人主张、或是排除特定当事人的主张、或是需要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或是需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判决方才无效。笔者认为,承认违法合同非当然无效这一类型至少有以下两点好处:
第一,可以防止特定当事人的恶意抗辩。在不少案件中,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原告往往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其起诉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自己的合同义务,但实际上,在签订合同时,他是知道合同无效事由存在的,这种现象在工程承包领域尤其常见。此时,法院若对合同按当然无效处理,则无疑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使一方当事人“援引自己的不法而获利”。因此,在合同违反的强制性规定无涉社会公共利益时,应驳回一方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请求。事实上,禁止恶意抗辩的思想在司法解释中已可见端倪,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7条[注]《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7条:“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的承包人与总承包人、分包人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当事人以转包建设工程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不予支持。”就已突破《合同法》第272条的规定,限制一方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此外,从审判实践来看,对只涉及双方当事人利益和特定第三人利益的一般无效合同,法院也会考虑时效的问题。[注]参见隋彭生:《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相关案件可参见“万通实业公司与兰州商业银行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
第二,可以维护私法自治,维持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合同订立于当事人之间,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安排,原则上与他人无涉。有的强制性规定,特别是私法上的处分界限规定,其目的并非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自我解决的规则,违反这些规定,法律不赋予其强制力即可,让当事人自己去选择,国家没有主动干预的必要。例如未达法定婚龄或一方患有严重疾病的婚姻,法律不承认其法定效力即可,若当事人反悔而提起确认无效之诉,法院就予以确认无效。若当事人没有提起诉讼,而是安于现状,法律就没有主动干预的必要,同时也没有让当事人之外的其他好事者干预他人生活的理由。对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7条对确认婚姻无效之诉的诉讼主体的限制,以及第8条无效事由消失后,对宣告无效请求的否定,可谓这一无效类型的规定,堪称允当。
(六)与确定无效相对之无效
一般认为,合同的无效是确定无效,不会因为无效事由的消除或特定事由的发生而使合同“死而复活”。[注]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56-657页。不过正如拉伦茨教授所言,法律规则将特定法律效果归属于特定构成要件乃是一种“适用命令”,法律之适用既然属于规范世界,则法律效果之归属,不能以自然因果关系理解。[注]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34页。职是之故,无效合同甚至可以再被撤销,[注]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而令无效合同再“死而复生”,也就并非没有可能了。
在民法理论上,与确定无效相对的,有“未决的不生效”(schwebende Unwirksamkeit),它是指将某项两个人之间订立的法律行为是否发生效力的问题,交由某个第三人来决定。[注]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374页。我国有学者以“效力待定”来指称这种“未决的不生效”,认为它在法律行为本身之外还欠缺某种生效要件,一旦事后具备了该要件,它就可以有效。在我国法上,《合同法》规定了效力未定的合同,依多数学者解释,以如下三种为典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第47条)、无权代理订立的合同(第48条)以及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第51条)。[注]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由此可见,合同“未决的不生效”状态往往存在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某种能力或资格欠缺的情形。与之类似,我国法上存在许多对合同当事人的资质要求的规定,或者是合同须经审批才能生效的规定,比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18条、第25条对勘察、设计、施工单位的资质要求;《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35条对外资企业转让土地使用权须经批准的规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10条第3款关于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须经批准的规定;等等。当事人违反关于资质或合同审批类的强制性规定订立合同,也应该比照行为能力欠缺或无权处分的情形,认定合同属于“未决的不生效”,其并非没有发生效力的可能。实际上,这一认识现已得到司法解释的普遍遵循,如法释〔2009〕11号第2条[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法释〔2005〕5号第11条[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1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法释〔2003〕7号第2条[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法释〔2004〕14号第5条[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5条:“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等规定,对于这类合同,若当事人能够在一审辩论终结前、起诉前、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资质或获得批准的,则合同将会被认定为有效。
与“未决的不生效”这种效力悬浮状态不同,不确定的无效类型下还应有一种类型,合同本来已无效,但却因合同履行完毕而被承认为有效,使当事人得以保有给付。违法合同之所以可以因履行完毕而承认其效力,其理论基础主要在于结果考量的导向功能和法律的安定性,前者要求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能忽略通过对已有的行为结果的评估方式,来体现对法律规范的目的含义的理解和把握;后者则要求法官考虑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法律利益安排期待的保护。[注]参见耿林:《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为中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268页。正如梅迪库斯教授所言,合同一旦执行完毕,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既然合同已经执行完毕,说明法律禁令并未能够有效地制止执行合同的行为。因此,这时只能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即:坚持合同继续无效能否在其他方面促进立法目的的达成。[注]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页。无效作为一种私法上的制裁手段,其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遵守强制性规定,若除去这种制裁手段,则法律的预防性作用将会消失,则即使违法合同履行完毕,也不能承认其效力。反之,若私法上的制裁对于履行完毕的合同没有意义,甚至将会悖于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则无效之制裁应被除去,合同应被承认为有效。对此,梅迪库斯教授举出了违反《商店关门法》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是将买卖合同作为即时结清的现金交易为履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希望相互返还。并且《商店关门法》的立法宗旨在于保障雇员的休息权利,若认定商店关门之后的交易无效,而令当事人双方相互返还已经获得的给付,恰恰将有违立法宗旨,因为这样一来,雇员还得在店堂工作更长时间。[注]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485页。在我国,法律对承接建设工程的一方当事人往往提出相应的资质要求,若承包人未取得相应的资质,则其订立的建设工程合同应被评定为无效。不过,对从事建设工程的资质要求,其目的在于保证工程质量,若无资质者在订立合同后,已完成施工,并且所完成的工程质量也通过质量验收,从资质要求限制的目的上看,显然其目的已经达到,已没有再以缺乏资质而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此时,不妨承认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效力,使合同当事人能够获得履行利益。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上述司法解释虽然没有明确承认此等场合下合同的效力,但从承包人可以请求支付合同约定价款的规定上看,最高裁判机关显然已经意识到合同履行对违法合同效力的影响,而在实质上承认了这类无效合同因履行完毕而得以恢复效力。
综上所述,《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的目的保留条款,为司法者提供了一个判定合同效力的弹性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裁判者可以根据规范目的、利益状态以及具体的合同情势,灵活地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类型,如合同相对无效、部分无效、向后的无效、非当然的无效、不确定的无效等。需进一步说明的是,上述合同无效的类型并非穷尽式列举,现实情形的复杂性决定了合同效力样态的多样性,这方面的空间有待法官在司法实务中去进一步开拓,此其一。其二,上文所述的各种合同无效类型并非相互区隔,而是相互交错的,一个违法合同,其效力样态可能同时满足其中数种形态,如上文提到的单方部分无效与向后的无效的组合。
六、结语
民法虽为私法,但其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王国,公法规范对私人生活的干涉从来有之,随着“社会国”思潮的兴起, 公法对私法的“入侵”更甚从前,在此背景下,如何使公法管制顺利进入私人领域而又不失其妥当限度,即是考验立法者智慧的问题。《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仿照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的立法成例,引入目的保留条款,明确违法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可谓契合了“扩大自治、放松管制”的民事立法潮流,值得肯定。
《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通过但书规定,实际上赋予了具体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在违法合同效力评价中的核心地位,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法官的目光应在规范目的与违法合同之间来回穿梭,以比例原则为指引,审慎地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同时,法官也应充分利用该条规定为其提供的弹性空间,以必要性原则为指导,妥当认定法律行为无效的对象及无效的类型,以实现对私人自治最大程度的维护。
法律行为适法规则搭建起沟通私法与公法的桥梁,善用这一规则可禁止自由的滥用,维护社会秩序,进而实现人人自由之并存的理想,但滥用这一规则也可能导致公权力吞没个人自由的恶果。因此,法律行为适法规则的适用如同“针尖上的舞蹈”,考验着我国裁判者的智慧和能力。诚如德国利益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黑克所言:“在所有的改变中,方法的改变才是最大的改变。”作为概括条款,《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赋予裁判者更大的权力,但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它要求我国裁判者改变以往机械适用法律条文的惯性思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目的解释与利益衡量等法学方法,使概括条款在个案中得以具体化,最终实现私人自治与公共利益的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