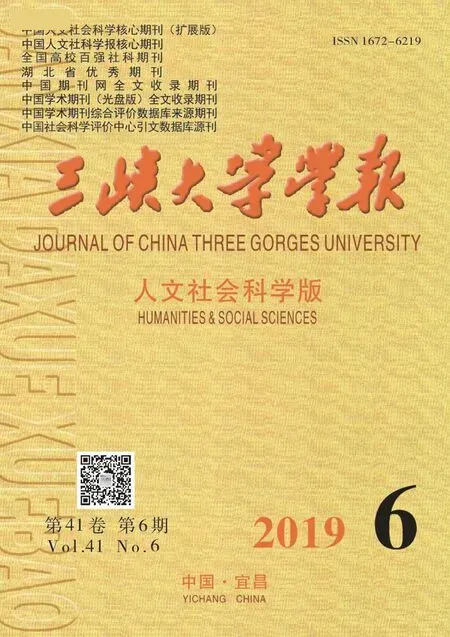论孟子“道性善”的“情气”背景及其根据
2019-02-11黄意明
黄意明
(1.上海戏剧学院 人文社科部, 上海 200040; 2.上海戏剧学院 图书馆, 上海 200040)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性善”论的思想家,并将“性善”论作为其伦理思想、政治学说的基础。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孟子的最大特点是“道性善”,影响最大的是性善说。然而,关于“性善”的真意,及“性善”说与孔子思想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学者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性善说与四端之心、清明“夜气”是密切相关的。四端之心其实是一种道德情感,构成了人性善的心理基础,而“夜气”及其发展“浩然之气”,则形成了人性善的生理基础。认清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孟子思想,发掘孟子思想中蕴含的价值,是非常重要且必需的。
一、“性善说”的提出及其根据:恻隐之情与清明夜气
在孟子时代,关于人性的讨论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话题,这不仅在先秦的典籍中能找到根据,而且在《孟子》文本中也有所反映。孟子言性以前,已经有三种“性”论流行,“性”已经从一个普通的话语逐渐变成了一种哲学术语[1]。更有甚者,当时的墨家、道家甚至以人性自然的概念来反对儒家的仁义,以为仁义之道违背了人性。(“生之谓性”的传统承认生命的各种本能与欲望为性)针对这种挑战,孟子不得不做出回应,以证明儒家仁义礼智的合理性。另外,孟子自称私淑孔子,然而孔子罕言“性”与“天道”①,所以孟子言性,多有不得已处,正如他自己所说:“予岂好辩,予不得已也”一样。葛瑞汉指出:“除了在与告子争论时,以及在回答他为什么不同意所有三种当时流行的学说的一个门徒的提问时,孟子自己决不说‘性善’”[1]。葛氏的说法,虽有些绝对,却不无道理。这样,孟子在对“性”作解释时,必须要说明仁义礼智对于人性的必然合理性。如此,孟子的性善说对于过去的各种人性论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创造。同时,孟子“道性善”的理论依据仍然不可能脱离儒家的学术资源。从文本上看,孟子是从“情”和“气”两个方面来说“性善”的,所以他的创新,乃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以下,我们通过考察《孟子》的文本,来说明这一观点。孟子“道性善”,有两段文字是必须注意的: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2]79-80(《公孙丑上》)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为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2]259(《告子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两段文字中,孟子提到了“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实即恻隐之情。关于“怵惕恻隐”,《说文》云:“怵,恐也。”“惕,《易乾释文》引郑玄云:惧也。”可见,“怵惕”为恐惧义。“恻”,《说文》云:“恻,痛也。”“隐”,赵歧《孟子注疏》云:“痛也”。朱熹《孟子集注》谓:“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杨伯峻先生谓:“隐即‘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之隐。”[2]78-80可知“恻隐”为哀痛义。因此孟子所谓的“怵惕恻隐”,乃是指人的恐惧哀痛悲悯之情感,此情感常在人面临突发事件时被激发出来,它以自己与他人的身心交感为基础,接近于同情心一类。除了恻隐之心以外,“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或恭敬之心),也与情感有关,或者说就是人面对外在人与事时的情感态度和意愿。“是非之心”,与人的判断能力有关,属于“知”的范畴,然而在先秦儒学中,特别是在孔、孟思想中,“知”虽表示一种分界,有认识的作用,但也和“仁”相关。孔子之“知及仁守”,即强调仁对知的贯通作用,故冯友兰先生说仁能包知。而仁与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情感有关,钱穆先生云:由其最先之心言,(仁)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也。而冯友兰先生以真性情释“仁”[3]。这样,知也可统一于仁,也与情感相关。在《孟子》中,四端以恻隐为中心,相贯为一。朱子说:“恻隐是个脑子,羞恶、辞逊、是非须从这里发来。若非恻隐,三者俱是死物了。恻隐之心,通贯此三者。”[4]可见,“四端之心”皆与人的善良情感有关。
孟子又进一步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四种德行之“端”,“端”本作“耑”。《说文》云:“耑”,物初生之题(题犹额也,端也)也。段注:“古发端字作此,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朱子《孟子集注》曰:“端,绪也。”可知“端”有端绪、起点之意,在这里作萌芽、萌蘖讲。孟子认为四端之情,即是仁义礼智四德之萌芽。并进一步申论,人有四端之心,就象人有四肢一样,是与生俱有,当下现成的,而非后天灌输或外在强加。
另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一句中的“情”字的解释。赵岐注曰:“若顺也,性与情相为表里。性善胜情,情则从之。”[5]将情释为情感,然性里情表说,恐受到董仲舒思想影响。朱子《孟子集注》云:“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6]朱子根据《中庸》,把心分为未发已发,未发为性,已发为情。他说:“仁,性也,恻隐,情也”[4],“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乐未发则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心是做工夫处”[4],“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4]。故按朱子之理解,此处之情,也为情感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释此“情”,“情犹素也,实也”[7]则认为此处的“情”字当做“情实”讲。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也据此将此“情”字译成资质。一般而言,先秦时代之“情”字,实兼有情实与情感意义,而此两种意义又有联系,不可截然二分。以此处而论,“四端之心(情感)”正是情实的重要内容。因此这里的“情”字,也可兼有两种意思。孟子文中的四端之心,正是从人类的共通情感处立论。孟子认为根植于人心的“仁义礼智”之性,乃是有人类共同的情感作为根据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乃仁之端,也即仁之起点,仁之萌蘖。仁之起点与萌蘖当然也属于仁,这正像树之苗也是树一样。故又说:“恻隐之心,仁也”。以此类推,有四端之情则可知人有仁义礼智之善性。关于四端之情与仁义礼智的关系,历史上的学者误会颇多。朱子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6]238。朱子根据“心统性情”来说性情关系,“有这性,便发生这情,因这情,便见得这性。因今日有这情,便见得本来有这性。”[4]又云:“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见他恻隐,辞逊四端之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4]清儒程瑶田《通艺录·论学小记》说:“孟子以情验性,总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晓人。仁义礼智之性,其端见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者,虽下愚者,未尝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说,以情验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义疏矣。情其善之自然而发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无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8]这些观点,其理路都是由“情为性之动”而来,因四端之情为善,以情验性,情善故知性善,而在性、情、才关系上,则是性善故情善才亦善。这种理解由于朱子之学后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逐渐变成儒家对孟子性善说的一个较权威的理解。但是这样一种理解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人之所以有此四端之情,乃是由于先天所具的仁义礼智之性的活动。另一方面,人之具有仁义礼智善良之天性,乃从四端之情见出。这就难免会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有循环论证之嫌[9]。细察《孟文》之文本,笔者觉得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应该重视孟子讨论“性”的文化背景与时代氛围,因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会凭空产生。孟子言性善是对当时以生言性,以自然本能与生理欲望言性的回应。所以孟子言性乃是首先肯定人先天具有恻隐等善良的情感,由此善良的情感即说明道德情感先天具备,当下现成。以此来证明人不仅有可以为善的先天资质,而且,由于道德情感是在乍见孺子入井的突发情境时产生的,所以能够摆脱世俗的利害计较,更具根本性,是人情中更为本质的部分,而人性的善,即表现在此道德情感上。这样孟子的“道性善”,不应仅仅理解为“以情验性”,而是“指情为性”或“因情而性”,情即是性的内容。由情之善,乃知人有向善之可能与倾向,仁义礼智皆建立在此善良情感之上。这一思想是传统儒家人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罕言人性,却重视发自于血缘亲情的孝,并将仁建立于其上。郭简《性自命出》等篇屡言性,走的是以“情气释性,因情定性”的理路②,其中的情虽仍属于“喜怒哀悲”的自然情感,然特推重“美情”③。相对于“孝悌”之情,美情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更为宽泛的道德情感。这明显地可看出其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挥。由此,孟子是在这一以情言性、以情为性之进路上,更进一步将人类的道德情感提升为优先的、具本质意义的情感。正如前面提及的,许多论者注意到孟子有以心善言性善的特点,而此心乃四端之心,也即四端之情。这一点,明代大儒刘宗周看得很明白,他说: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只为性字不可指言也。盖曰吾就性中之情蕴而言,分明见得是善。今即如此解,尚失孟子本意,况可云以情验性乎?何言乎情之善也?孟子言这恻隐心就是仁,何善如之?仁义礼智皆生而有之,乃所以为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言性也。即心言性,非离心言善也。后之解者曰:“因所发之情而见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见所性之善。岂不毫厘而千里乎?[10]
四端之心,即四端之情。有此四端之情,故知良知良能生而有之,仁义礼智皆此四端之情的自然发展。故恻隐等四端就是仁,就是性。由此,谓之性善。清儒焦循也持以道德情感言性的相同观点。
严格说来,四端之心,都从恻隐之情而起,恻隐之心,孟子又称之为“不忍人之心”,实即不忍人之情。《孟子》一书中,屡屡提到“不忍人之心”。齐宣王不忍以牛作为牺牲来衅钟,孟子即赞扬宣王有不忍之心,是一种仁术。对牛尚知怜悯,何况人乎?劝说齐宣王推广不忍人之心,认为不忍人之心是实行王道,保证四海安宁的基础[2]15-17。不忍人之心,即怜悯心,同情心,也即仁道的开始。“人皆有所不忍,达至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至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而此种不忍之心,尤在对亲人的态度方面表现得明显,因为恻隐之情,不忍人之情正是从孝亲开始。
盖上世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蔂埋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滕文公上》)
这个关于丧葬起源的推测,极好地表达了孟子的“不忍心”命题。上古时代,人民并无人死埋葬的概念。亲人死后,将之委于沟壑。然而他日过之,看到狐狸在咬食亲人的骨肉,蚊蝇在吮吸着亲人的身体,不禁全身冒汗悔恨交加,惭愧之情油然而生,马上拿起锄头簸箕把亲人埋葬了。
孟子通过这个故事,极具说服力地阐明了人的孝悌亲情也与人的恻隐不忍之情有关,具有天然合理性,同时也说明了礼(丧礼)的出现也有其人情的基础。
另外一则对墨子薄葬的批评,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肤亲,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公孙丑下》)
此段讨论的是厚葬还是薄葬的问题,孟子认为“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不可惜物薄亲的理由,是惟有如此才能让人心安宁,“快然无所恨”(朱子语),也即是尊重人的不忍之情。“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滕文公上》)丧礼正是对此感情的满足。
准此,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美好的情感(恻隐孝悌之情),或曰在自然情感中有合目的性的“善”,此“善”即道德情感。而一切礼乐政治的建构,也必须以此天然道德性的情感为基础。
正是在此四端之情的基础上,孟子以情为性,建立起他的“性善论”。恻隐为仁之端,为仁与善之萌芽和开端,因恻隐还不是仁的全部、仁的完成,而只能说是仁的开端。实现仁、完成仁是需要有一个践履的过程。从成仁尽善的角度而言它还只是一个依据,一个开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但作为善的根据而言,它却是当下现实的。正像“形色天性也,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一样,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还必须经由人为的努力。然而君子为何要将这种可能性变成必然性。为何必须要“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将成仁成圣作为唯一的选择,却也有其不得不然之原因。孟子将恻隐等称作四端,其实已经暗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人性之善,就像植物之萌芽,泉水之始涌一样,虽还未成材成流,然而其向着最终目标进发的趋势却是不可违逆的。“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公孙丑上》),造成人性由善端向纯善完成的内在动力,是“乐”,一种与情感相伴随的快乐。在现实四端之心向纯善之境的进程当中,君子体会到了乐。用孟子的话来说,叫“可欲之为善”。孟子认为,天下人对于美好的品德美好的情感,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之情,这来自于人心深处的道德之欲,就像所有人对于美味美色有一种共同的爱好一样。
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孟子》用“理”字极少④,“理义”两字连用,仅有此段。蒙培元先生认为“理义”和“仁义礼智是同一层次的范畴”,是有道理的。由于“仁义礼智”来源于道德情感,以自然情感为依据,因此“理”可看作情理,义可看作情义。如此,依孟子,一方面人心对仁义礼智为代表的德性义理,会有一种伴随快乐的向往之情,所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另一方面,所悦的对象(义理)本身又是情感(情理)的。如果将这种心悦理义的美好情感不断扩充深化并付之于实践,则人人有成为尧舜的可能。“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这样,孟子的结论是:道德价值、道德理性来自于人内在的道德欲求(体现为道德情感,或曰道德情欲),同时人们追求道德价值,又有感情之悦安作为心理基础。
《孟子》一书中,论“乐”处甚多,多与德性有关: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下》)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尽心上》)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离娄上》)
快乐一旦发生,就会无休无止,不可遏止。以至于手舞足蹈。所以在孟子看来,人之践履仁义,向纯亦不已之善境进发,乃有不可已己者。
通过以上这些论“乐”片断,不难发现,孟子所谓君子之乐,乐的都是仁义忠信之类。这样孟子的理路不难揭示。以人人情感中都有的四端之心、悦理义之心,从而说明道德情感有向善的目的性,也就是道德情感天生具备,当下现成。而从人人都有悦理义之心,进一步说明人有完善道德的自然欲求。这样,在善的萌芽与纯善之境之间,正如植物之由萌芽至成材,有一种自然的势能潜伏着。葛瑞汉在谈到道德之乐的时候曾说过:“虽然道德教育必不可少,但他像身体的给养一样是自发的养育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展开就是加速度,像火之燃烧,因为我们从中发现了乐趣”[11]。
孟子以道德之乐来说明善性的成长,这种说法与西哲休谟之人性论也有可会通之处。休谟认为:恶和德总是使人产生一种实在的痛苦和快乐。“德的本质就在于产生快乐,而恶的本质就在于给人痛苦。……不快和愉快不但和恶和德是分不开的,而且就构成了两者的本性和本质。”[12]休谟的观点,注意到了道德和快乐之间的关系,然说快乐是道德的本质,则有发挥过甚之嫌。
以上我们讨论了孟子由情善定义性善的理路。但如要进一步理解性善说的内涵,笔者认为还须结合孟子的“气”论,才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孟子文本中常爱用举例的方法,来揭示人性的成长,其中最经典的一个是通过“牛山之木”的隐喻,以清明夜气来说明性善的道理。而性气关系,也是此前《郭店竹简》着重讨论的一个话题。“气”在先秦哲人话语中,既是万物之基,也是性情的基础。研究这个著明的隐喻,对深入理解孟子的性情论,是有帮助的: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息,雨露之所润,无非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者也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告子上》)
牛山在齐国郊外。牛山之木材质甚好,然而由于其生长在大城市外围,因而砍伐者甚众。随着草木资源的匮乏,牛山便逐渐荒凉。但天地之大德曰生,树木虽屡遭砍伐,牛山之生意仍在。日夜之间,其生气仍在不断恢复充实,加上阳光雨露之照耀滋润,树木仍有新的萌芽,但不久,人们又将牛羊放牧于此,于是仅存的一点生机也荡然无存,最后只剩下一座光秃秃的荒山。路人经过此处,看到一座荒山,就以为牛山本来就是濯濯童山。牛山之喻是一个象征,它有几方面的喻义。首先,牛山恰如人的本性气质,其生机正如人的善性美情,树木之萌芽,就像人的善端(四端),时有萌发。然而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人为的戕害。所以牛山之木,无法成材践形。人的美情善质,也是如此,由于受到后天种种因素的影响,最后终至良心放失⑤,天赋的善性无由实现。孟子牛山之木的比喻,形象地阐明了他试图表达的主旨,即人都有“本然之善心”(四端、良知良能),之所以不能成长,乃是由于后天遭到了戕伐斫伤,如果能保证先天善性的正常成长,则人人可为尧舜,而斫伤戕贼善良天性的,除了人的耳目之欲外,就是积习和外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思想,孟子引入了“夜气“的概念。就某些不善的人而言,身上也存有仁义之心,他在日间夜里发出来的善心,他在早晨未与外物交接时身体内积累的清明之气,这些在他心里所激发出的好恶跟一般人也有一点点的相近。然而一到第二天的白天,其所作所为又不断损害夜间积累的清明之气以及相伴而来的善念,终于“至于夜气之生,日以寝薄,而不足以存其仁义之良心,则平旦之气亦不能清,而所好恶遂与人远矣”[6]。人的养气与养心(情),道理是一致的。这里想说明的是,孟子此处的“夜气”之说,其实是以气说性传统的延续。《论语》强调为仁由己,较少说到性与气⑥。孟子以心说性,重视自然情感中的善端,引而申之为道德情感,与孔子从孝悌亲情说仁是一致的理路。然而“夜气说”,却显然是对《左传》和《管子四篇》等旧有以气释性及“生之为性”的资源的改造生发⑦,其进路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之“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相同,这是从生命的角度,说人禀赋有天地良善之气。而由此最初之良善之气,即可证人性之善。在这里,又可说即气为性,因气说性。
根据以上所述,孟子将情、气结合而论性,特别是将善端(四端之心)和清明夜气结合论性善,是一种综合新说。在孟子以前,有以气论性的传统(如前述《左传》等),有以情和气论性的理路(《性自命出》以情气为性,偏重于从情上说明,气乃情之生理基础)⑧,孔子则以仁(道德情感)接通天命。孟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原初的道德之情与作为道德之情生理基础的良善之气说明人的善良天性,两者结合以论证“性善”为人之本质,其理据更为充分,思路更为清晰。
关于孟子养气说的讨论,历来论述稍嫌不足,这里再稍作补充说明。孟子曰: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者;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公孙丑上》)
这一段文字,说的是养气,同时涉及到了心与情。孟子认为,“气,体之充也,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此处志与心连用,当为心志或情志,接近于道德意志。“气”,杨伯峻先生释为“意气感情”,注意到了气与情的关联性,是较为准确的。在这里,孟子提到了意气感情与道德意志的交互作用。故既须养气,又须以心志控制调节意气感情(此处之感情是兼自然和道德感情而言)。这两者是相与为一,无分轻重的。所谓“夫志至焉,气次焉”。赵歧注云“志为至要之本,气为其次。”毛奇龄《逸讲笺》以“次”为舍止,言“志之所至,气即随之而止”[2]70。应该说,毛奇龄的说法更为合理。感情意气与道德意志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虽然意志能够控制情气,但就生命本身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主次的问题。因此,一方面须以思想意志引导情感意气,不让情气自由驰骋;另一方面又须培养情气中的夜气,以使意气专一从而坚定心志。这种经过培养的气,孟子称之为“浩然之气”。这种气,伴随着正直的情感,配合着道义,伟大而不可限量,培养它而不加伤害,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缺少道义的积累,则这种气就会没有力量。同时行为亏欠,有违良心,违背道德情感,也会没有力量。从这一角度,不难看出,养气即所以养心、定志。所以,这里的浩然之气,不仅仅是清明夜气,而是夜气的一种合理的发展。这种发展必须伴随着道义与情感之培养的过程。所以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操之则存,舍之则亡。”朱子说:“浩然之气,是养得如此。”“浩然之气,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说浩然,便有个广大刚果意思,如长江大河,浩浩而来也。富贵、贫贱、威武不能移屈之类,皆低,不可以语此。”[4]说浩然之气比清明之气更为广大刚果,是极有见地的,不过浩然正气也正是从清明之气培养而来。心志坚定专一,情感正直美好,意气充实刚健,则善性也从而得以体现。
孟子以气论性的思路,对后世的人性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对此“存夜气”说,有一重要的发挥:
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义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便常做个羲皇以上人。[1]
王阳明以夜气来说明良知,也是以气善说明性善,可谓深得孟子之深意。然对于孟子的养气说,阳明此处却未予以进一步的阐明。
当然,就情气比较而言,孟子言“性”,更偏重于从情上立论,恻隐之情,可随在而体认,而清明夜气之理则需思索而得,这也与情显而气隐有关。
二、性、情、气一体中的“道德情感”
据上节以情论性、以气论性的理路,孟子从人的生理(夜气)和心理(四端之情)的角度,顺理成章地推出了他的结论:人性善。
不过,这里仍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既然善的根据可以从生理与心理方面找到,那么如何看待身心中的不善。第二,以情感而言,四端之情,固然人人俱有,此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前提。然而同样必须肯定的是,富贵荣华、佚乐食色,也是人之所欲,又孔子曰:“富贵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孟子自己也说:“生亦吾所欲”、“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之类的话,可见这些要求也是情感之必然,而此类情感既不具有道德意义,也非不善,对这种情感孟子又持何种态度呢?
针对第一个问题,孟子认为相对于不善和生物本能状态,人性的善是更为本质的,现实中的人所以为不善,“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他说:
今天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
相同的麦种,在合适的季节播种,遇到适宜的气候,至收获季节都会成熟。最后麦实之间如有不同,那就因归结于地力、气候、人事等外在因素。“善”性的成长也是如此,“良知良能”有完成自己的自然趋向,而有些人之所以甘为不善,乃是因为“耳目之官不思”,甘于受外物引诱而放失良心的缘故: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2]70(《告子上》)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2]271(《告子上》)
由于“今之人”不能首先确定作为其大者的良知良能的主导地位,并将其扩而充之,因此常常顺着各种本能、欲望的驱使,过分追逐生物本能的快乐,逐渐遮蔽了人所独有的良善天性,孟子称之曰违禽兽不远。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引之”,人的本能与欲望无所谓善恶,但情欲被无限引发,人倘为求其实现满足,无所不用其极,则成为不善,于善良天性反成一遮蔽状态,即所谓良心放失。
对于一个放失良心很久的人,孟子认为,一方面应该找回放失的“良心”,确立其良知良能。故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另一方面找回以后,则要不断培养其善性美情,扩充清明之气,使人能尽其才。由“性”“情”“气”一体论出发,则锻炼培养善良的天性,应从情、气、两方面入手,并以理性来扩而充之(知皆扩而充之)。从情上说,是培养扩充道德情感;从气上说,则为集义养气;而从性上总说,是坚信并确立良知良能的优先地位。这是从发展上说性。
对于第二个问题,孟子以为,自然情感,和人的感官生理心理相联系,因此是一种纯感性情感,且实现与否决定于外,决定于命运,况且,此类情感乃人与动物所共有。孟子认为不具备道德意义,不具备向上提升,以接近于纯亦不已之天命的可能性。而道德情感则求之在我,且具备向上之可能,因此是更为本质的情感。如能先充实培植此道德情感,则自然能明乎义利之辨,达到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中和⑨。下面的论述,进一步反映了孟子对道德性情与自然性情关系的看法: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梁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告子上》)
观此几节,则知孟子并未贬低否认人的自然之性、自然之情。要求满足口、目、耳、鼻以至身体等感官需要,也是人的天性。不过既然此自然之性,自然之情,或曰人之自然情欲的满足,有待于命运,受到外在条件的制约,受到自然生命的限制,故君子又不称之为“性”,赵歧曰:“(五者)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乐者,有命禄,人不能皆如其愿也。凡人则有情从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则以仁义为先,礼节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谓之性也。”[5]393而仁义礼智能否实现,虽也为自然生命及命运所限,却为天性之必然,且为之在我,只要我之生命尚存,即可努力增益其德性,因此是更为本质的存在。故又称其为“大体”。“大体”相对于“小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与超越性。
这里,可以澄清孟子的一种思想。孟子并非反对基本的人欲,这从上面孟子也把人基本的情欲看作性,便可明了。孟子经常告诫统治者要“治民之产”,要以“百姓利为利”,这是要求统治者不要放纵情欲(寡欲),穷竭民力,以便让人民能满足基本的食色需要。且孟子还认为统治者只要能与民同乐,世俗的享受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孟子更认为,人的感官满足、生理欲求,求之在外,命运的因素相当多,而且驰骋人欲,纵耳目之官的结果,必定是违背礼义,违背法律,造成混乱的结果,这样,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同时,放纵耳目之欲,必定遮蔽人的仁心善性,道德情感得不到安立与扩充,从而求之于内的“性善”便无从实现。所以孟子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欲之间,更注重道德情感,使之首先确立。在道德情感得以安立,即天命之性得以展开前提下,控制自然情感,使之得以合理地实现。一个正常之人对于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每方面都会竭力爱护、保养,但最终评价他养得好不好,是看他总体上保养得如何。就像饮食,每个人都需要,但饮食的目的是保证人体生存发展的需要,如果为饮食而饮食,甚至为纵口腹之欲而损坏身体,则这样的人就是“饮食”之人、“狼疾之人”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养其小体虽也必须,然应该随时警惕这一行为中所暗藏的异化力量。故孟子一方面说:“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另一方面又强调“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告子上》)。
这样,道德情感和自然情感其实都与人的生理心理密切相关,因此,也可以说都有遗传学上的根据。在当代西方也不乏知音,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人的层创进化的一个全新之处,就是进化出了一种能与(只关心同纲同门利益的)自利主义同时并存的(关心同纲所有动物的)利他主义倾向,进化出了一种不仅仅指向其物种,而且还指向生存于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物种的恻隐心”[14]11。(接近儒家所说的一体之仁)也许是出于同样的思路,华霭仁认为:孟子的意图是用一种更宽泛的生物学主义,这种更宽泛的生物学主义在人的遗传学特征或者“性”之中包含了道德心本能[1]236。 这些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道德本能的遗传学的根据(也有人认为是长期进化中的集体无意识),相比较而言,孟子是从道德情感的与生俱有、当下现成来说明道德(性善)的主导性和优先性的。
注 释:
① 本文论孔子义基本以《论语》为基准。
② 《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参考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性自命出》云:“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行善者也。”
④ “理”字仅二见,此处而外,另有一处谓“稽大不理于口”(《尽心下》),释为“顺”。
⑤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1页。
⑥ 《论语》中“气”字共六见,与生理相关者如“血气方刚”。
⑦ 《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 《管子四篇》:“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⑧ 《性自命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又“喜怒哀悲志气,性也。”
⑨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情感也是自然的,也是一种自然情感。但孟子“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一语,则将道德情感与顺耳目口鼻的自然情感作了区分,将之从自然情感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