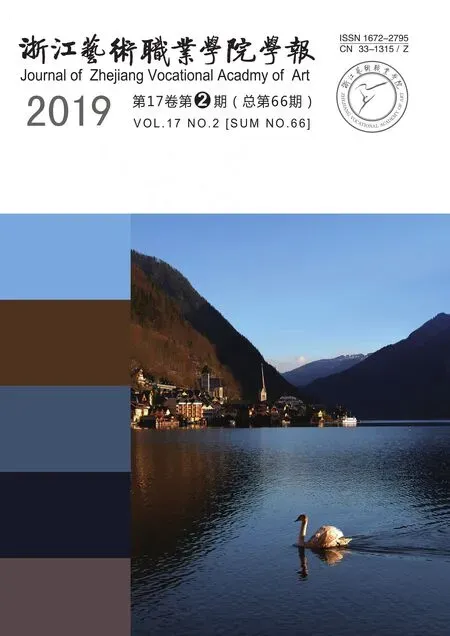《桃花扇》接受与研究在日本*
2019-01-29王亚楠
王亚楠
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近世戏曲史》中称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并为清代戏曲双璧,为艺苑定论”[1]283,这也代表了近现代中日戏曲研究者的一致看法。戏曲作品的跨文化、跨语际传播、接受是戏曲接受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自江户时代中国的戏曲剧本输入日本,戏曲作为兼具文学性、音乐性和舞台性的综合艺术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戏曲研究也是近现代中日学术研究现代转型和成果积累的重要体现。被目为经典名剧的《桃花扇》在日本的接受和研究,是中日文化交流、学术影响的一个具体而典型的案例,具有多重的价值、意义。日本学者对《桃花扇》的接受、研究前后之间有影响和承传,借此可窥见日本近现代戏曲研究进展的一些线索;中日的评论、研究之间也存在借鉴和互渗,共同推动了《桃花扇》的现代研究。
江户时代——东传日本
相对于《西厢记》和《牡丹亭》,《桃花扇》问世既晚近,流传时间也较短,但问世之初便大受肯定和欢迎,康熙、雍正年间又盛演于全国各地的舞台之上,同一时期《桃花扇》西园本的梓行,都使得这部剧作备受关注,使其地位、影响超越了一般的明清戏曲作品,所以也较早地传入日本。据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所收《商舶载来书目》,有文献记载、时间确切的《桃花扇》最早东传日本是在宽政十一年(1799,清嘉庆四年),即其问世整百年后,共一部六本,具体版本情况不详[2]。
据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所载日本各公私图书馆等藏书机构收藏的《桃花扇》的情况,可知江户、明治时期有多种《桃花扇》的版本流入日本,其中无论版本种类,还是单本数量,多数都为西园本及其翻刻、重刻本。《桃花扇》的康熙间介安堂本和康熙间刻本到了乾隆初年便很少流传,书坊为满足读者需要和借以营利刻印了西园本,实为康熙间刻本的翻刻本。西园本流行既广,又有了它的翻刻和重刻本。因为常见,所以传入日本、为公私所收藏的《桃花扇》也多为西园本及其翻刻、重刻本。如东北大学藏道光十三年(1833)刊的西园刊本便是重刻本,纸张劣质,字体呆板。除西园本外,传入日本的还有其他一些比较罕见、特殊的《桃花扇》的版本。如十行二十字、康熙四十七年序刊本、九州大学滨文库有藏的《桃花扇传奇》二卷,据其书名页书影和行款等特征,可知实为嘉庆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同一版本,原为吴梅所有。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九行二十字的“西园刊本”实为西园本的一种重刻本,为沈默、沈成垣父子刻于乾隆初年。大阪图书馆所藏康熙四十七年序刊本《桃花扇》的书衣题签下有木记:“书业德自在江浙苏闽拣选古今书籍发兑”[3]178。“书业德”是清代山东聊城规模颇大的有名的刻书铺子,在全国有很多分号,创办于康熙年间,光绪年间达于极盛。书业德刻书种类范围广泛,但都比较通俗。有时还从南方刻书业发达地区购买书籍,转运到山东等其他省份发卖,并在书籍之上特加说明。上述带有木记的《桃花扇》即为一例,可见这种刻本原是刻印于南方。西园本流行既广,便被认为是较好的《桃花扇》的版本,以至于铃木虎雄在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据以校正本国出版的排印本[3]183。这种排印本共四卷,又有“首一卷”,所以所据的底本可能是兰雪堂本。
明治时代——评论与讲授
《桃花扇》刻本的输入,是其在日本被接受的基础。该剧篇幅宏大,文辞典雅,传入日本后,也应主要在通晓汉文的部分文人学者中接受、流传。明治时期,在维新的大背景下,随着西学东渐和汉学转型,戏曲、小说等以往仅供消遣娱乐的俗文学作品逐渐得到重视。一些思想先进的文人学者展开了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介绍,而且开始在大学课堂上进行讲授,讲授的具体内容主要见诸课堂讲义和据以编辑、出版的最早的“文学史”著作。其中领风气之先,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明治汉诗坛的重要人物——森槐南(1863—1911)。而森槐南对《桃花扇》情有独钟,这在他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等都有明显的体现。他也对于《桃花扇》在日本的评介、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森槐南喜爱中国戏曲作品,又曾自作短剧,十七岁时即撰有《补春天传奇》,写清代文人陈文述因感于梦,而为冯小青、杨云友、周菊香三位著名女性修葺坟墓,并建兰因馆祭祀故事,有明治十三年(1880)东京三色套印本。卷首有沈文荧和黄遵宪的《序评》,两人都指出森槐南有意模仿《桃花扇》,文辞风格也相接近。沈文荧谓:“此曲于孔、洪为近,‘幽隽清丽’四字,兼而有之。”[4]黄遵宪谓:“以秀倩之笔,写幽艳之思,摹拟《桃花扇》《长生殿》,遂能具体而微。”[5]对于第二出中的[过曲]【绣带宜春】曲,沈文荧的眉批指出:“大似孔云亭《桃花扇》。”[6]沈文荧还评价第四出《余韵》的下场诗“秀雅,是全仿《桃花扇》”[6]。其实《余韵》的出名也借自《桃花扇》,该出的结构也摹仿了《桃花扇》的续四十出《余韵》。可见森槐南对这部名剧的熟悉和喜爱。
他又先后作有多篇诗歌咏叹《桃花扇》,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明治十二年(1879)二月,森槐南在其父森春涛(1819—1889)创办的《新文诗》第四十六集上刊出《读〈桃花扇传奇〉题其后》,凡五首:
秦淮柳色莫愁村,旧院繁华记泪痕。欲向春风问遗事,桃花扇底最消魂。
月前和影坐吹箫,流水桃花旧板桥。犹记六朝金粉地,伤心花月又南朝。
玉树歌残不忍闻,草萦枯骨泪纷纷。水声呜咽人来吊,春月梅花阁部魂。
英魂一片付空谈,暮气消沉恨不堪。从是年年风雨夕,有人偷哭左宁南。
干戈满地叹兴亡,征召谁登选舞场。犹是深宫人不识,《春灯谜》里月昏黄。[7]
同年八月,他在《新文诗》第五十一集刊有《重读〈桃花扇〉得二律》(录一):
桃叶歌残古渡头,夜乌啼断媚香楼。当年轶事悲纨扇,前辈风流吊玉钩。
真个寡人元有病,可怜天子是无愁。胭脂井畔旧时泪,洒向秦淮烟雨秋。[8]
后附小山春山评语:“五十六字,善写一代兴亡,何等才笔。起结补圈。”[9]
同年九月,他在《花月新志》第八十二号刊出《又赠圆朝演义》,也是咏叹《桃花扇》:
烟雨南朝梦未醒,桃花红委土花青。美人扇上兴亡恨,都付泰州柳敬亭。[10]
明治十三年(1880)六月,他在《新文诗》别集第十集刊出《集〈桃花扇传奇〉句》八首:
井带胭脂土带香,六朝兴废怕思量。今晓灯影纱红透,明日重来花满床。
——余韵、听稗、眠香、访翠
春在秦淮两岸边,天空不碍月团圆。谁家剩有闲金粉,一树桃花似往年。
——传歌、会狱、孤吟、题画
大江滚滚浪东流,怕有降旗出石头。歌舞丛中征战里,当年烟月满秦楼。
——哭主、修札、余韵、逮社
锦瑟消沉怨夕阳,天涯烟草断人肠。笙歌西第留何客,别姓人家新画梁。
——题词、访翠、余韵、听稗
江带春潮坏殿基,烟尘满眼野横尸。从来壮士无还日,一曲歌同易水悲。
——听稗、移防、草檄、守楼
山高水远会相逢,往事南朝一梦中。无数楼台无数草,斜阳影里说英雄。
——栖真、题词、听稗、修礼
玉树歌终画殿凉,一枝带露柳娇黄。美人公子飘零尽,剩有残花隔院香。
——余韵、访翠、题画、听稗
竹西明月夜吹箫,书到梁园雪未消。古董先生谁似我,桃花扇底送南朝。
——和战、寄扇、先声、入道[11]
其中的“题词”即《桃花扇》刻本卷首所载孔尚任同时的文人所作的题辞,“锦瑟消沉怨夕阳”出自田雯的题辞,“往事南朝一梦中”出自吴陈琰的题辞。
森槐南的父亲森春涛是明治初期日本著名的汉诗人,也曾作诗咏叹《桃花扇》。明治十四年(1881)一月,小永井八郎评点的《新评戏曲十种》(乙)出版,森春涛题诗八首,其中涉及《桃花扇》。森春涛曾选编张问陶(1764—1814)、陈文述(1771—1843)和郭麐(1767—1831)的绝句成《清三家绝句》,森槐南参与了校勘。森春涛还摹仿三人的诗作而作“艳体”,森槐南也曾作有“艳体诗”,如《青山》(载《新文诗》第四十九集)、《怜春词》四首(载《新文诗》第八十一集)等。上引《集〈桃花扇传奇〉句》八首也属艳体诗。森槐南受其父的影响,自小便倾慕陈文述的诗歌,故将陈文述谱入自己的剧作。而陈文述集中有《秦淮访李香故居题〈桃花扇〉乐府后》组诗,第三首作:
湘筠小阁画帘秋,惆怅前朝吊玉钩。读到婵娟长庆体,夜乌啼上媚香楼。[12]
对比上引的《重读〈桃花扇〉得二律》(录一),可知森槐南的这首咏剧诗受到了陈文述诗的影响,其中“夜乌啼断媚香楼”“前辈风流吊玉钩”更直接借用原诗词句。此外,张问陶集中有《读〈桃花扇〉传奇偶题十绝句》诗。由此可见森槐南选择组诗形式咏叹《桃花扇》所受的影响来源。
森槐南还在日本近代第一次将中国戏曲引入大学课堂的讲授。明治二十三年(1890)九月,森槐南受聘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讲师,所讲课程为“杜诗偶评讲议”,而实际讲授涉及戏曲,其中便包括《桃花扇》。据记载,森槐南讲授时,学生们在非常陶醉,竟至无法记录笔记,讲授结束时,还顿有茫然之感[13]。由自作诗歌评论到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不仅是个人兴趣向公共空间的延伸、扩展,也不仅是传播、接受形式的迁移、转换,更重要的在于这意味着对《桃花扇》的评价、研究开始进入近现代学术体系。
森槐南的讲授还对他的学生接受、评论《桃花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他在东京专门学校的学生、曾在课堂上听其讲授过《桃花扇》的柳井絅斋(1871—1905)作有《读桃花扇传奇三十首》,刊载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三月的《栅草纸》第三十号(选录四首)和同年七月的《栅草纸》第三十四号(选录16首)。
另外,日本《自由新闻》记者宫崎宣政(字晴澜)作有《读〈桃花扇〉》诗十首,刊载于《辽东诗坛》1926年第15至18期和1927年第21、22期,也应是受到森槐南的影响。森槐南曾为宫崎宣政的《晴澜焚诗》(有明治书院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二月版)撰作题词,并分别为集中每篇诗歌写有评语。
尽管《新文诗》系列可谓明治初期刊行时间最长、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汉诗文杂志,但毕竟传播范围仍有限制,大学课堂讲授和汉诗评论一样也不能更大、更广地促进体裁特殊、曲辞文雅的戏曲的普遍接受,并扩大其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于是,别种著述形式开始介入戏曲的评介。如柳井絅斋受森槐南讲授《桃花扇》的影响,应刊物之约,为该剧撰写“梗概”,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评价,发表于明治二十五年八月的《早稻田文学》“名著梗概”栏,自总第21期连载至十一月第28期,对全剧每出剧情详加介绍。第一篇前有记者识语,第一篇的副题作“《桃花扇传奇》的由来、大意及价值”。识语和第一篇中都转述了森槐南对《桃花扇》的评价,谓《桃花扇》是“中国院本中屈指可数的作品”,可见森槐南心目中《桃花扇》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第一篇中还转述森槐南的话:“又篇中之诗,清新婉丽,颇可表见清朝的诗风。当时诗宗王渔洋亦称其能,宜乎《桃花扇》成,王公贵绅,争相誊写,以致一时纸贵也。”[14]但目前未见王士禛有评价孔尚任的诗歌或者《桃花扇》的文字,而且《桃花扇》的曲辞和诗歌不是其风行和获得高度评价的主要原因。
明治三十二年(1899)六月,森槐南受聘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讲师,主要讲授词曲,其中也包括《桃花扇》。明治四十五年(1912)十月,森槐南在东京帝国大学授课的讲义残稿《词曲概论》,经整理在《诗苑》上陆续刊出,凡十一章。“曲”的部分其实是关于元明清戏曲发展的简史,最后一章“清朝之传奇”将《桃花扇》置于中国古代戏曲演变历程中进行论述,给予了高度肯定,称为“曲中巨擘”,对其剧情、结构和艺术创新等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多能切中肯綮。其中的部分观点和描述明显借用自他书,可见森槐南的阅读范围和取资对象。如谓《桃花扇》的曲辞“艳处似临风之桃蕊,哀处似着雨之梨花”[15]70;评价结尾的“余韵悠然,有余不尽之意,置于烟波缥缈之间”[15]70,均直接借用自梁廷楠的《曲话》卷三。森春涛、森槐南父子推崇明清诗风,森槐南也读了不少清人别集,在阅读中还特别留意到“名家之集中,读《桃花扇》传奇或观演之诗,累至百余篇,皆有可观”[15]70,可见他对《桃花扇》的强烈爱好和兴趣。森槐南第一个提及清人集中有大量咏叹、评论《桃花扇》的诗歌,虽不及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卷十四“《湖海集》十三卷”条详细,但在时间上早了近百年。
处于近现代学术转型时代的森槐南,先以汉诗文创作蜚声文坛,后又登上大学讲坛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他重视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观念和以多样形式对这类作品进行的评介、研究引领了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他堪称现代学术意义上中国戏曲研究的真正开创者。而在他对中国戏曲的评介、研究的活动和成果中,《桃花扇》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的存在。
森槐南之后,更多的日本学人参与到中国戏曲研究的活动中来,产生了更多的成果。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受到西方民族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研究观念和著述形式的输入和影响,有日本学者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这包括文体专史和通代的文学史。地位处于上升态势的戏曲小说进入文学史演变的历程中,并占据了比较大的分量,《桃花扇》也成为了其中必须论及的一部重要戏曲作品。
明治三十年(1897)六月十日,笹川种郎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出版,这是最早的中国小说戏曲专史。全书凡四篇,第四篇论述“清朝”文学,凡五章,后三章所述分别为金圣叹、李渔和《桃花扇》,可见作者对《桃花扇》的重视。不过,书中仅是对剧作进行了梗概介绍。明治三十一年(1898)八月,笹川种郎又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史》,戏曲小说首次被列为专章进行论述。其中第九期“清朝文学”的第二章“小说和戏曲及其批评”论述了《红楼梦》、李渔、《桃花扇》和金圣叹,《桃花扇》继续获得了强势的存在。他在论述由于儒学制约,戏曲小说多以道德劝化为主旨,因而发展缓慢时,引用了孔尚任《桃花扇·小引》为例。
笹川种郎对《桃花扇》有较为特别的关注和重视,熟悉该剧,并有较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明治三十年六月,他发表《中国的戏曲》一文,在论述中国戏曲的多个方面特质时都举了《桃花扇》为例。除前面提及的重视道德劝化外,还包括缺少真正悲剧,谓《桃花扇》“虽是悲剧,然其结局仍是成山中仙”[16]59;重词采,引孔尚任《凡例》。明治三十二年(1899)四月,笹川种郎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学所表现的女性》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出中国的戏曲小说中有一个特异之处,便是女性通常较男性出色,所举例证中也包括名士侯朝宗不及歌妓李香君远甚,这一结论自然是从他对《桃花扇》的接受中获得的。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他的学术论集《雨丝风片》出版,收入了《中国文学所表现的女性》。同年十月,《帝国文学》“杂报”栏刊出的书评中说:“《桃花扇传奇》出,王渔洋在《秦淮杂志》上转用‘雨丝风片’四字以夸其巧,今临风用作书名,不难见其宿癖嗜好。”[16]56笹川种郎对《桃花扇》有较为特别的关注和重视是事实,但书评中的其他论述则是错误的。首先,《秦淮杂志》当作《秦淮杂诗》,共十四首,第一首便是“雨丝风片”的出处:“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17]其次,此诗并非评价《桃花扇》,因为诗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而《桃花扇》完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
久保天随(1875—1934)作为日本从事中国戏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因受到森槐南的影响而走上戏曲研究之路的。久保的主要研究实绩主要体现在于中国文学史的撰述和《西厢记》研究上。明治三十六年(1903),久保天随撰成《中国文学史》,其中“第四期 近世文学”第三编“清代文学”的第七部分论述了《桃花扇》与《长生殿》。他的后来多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也都论及了《桃花扇》。此外,明治四十二年(1909)他还特别为卧病在床的校友田冈岭云撰写了《桃花扇传奇》一文,刊于同人杂志《千波万波》。
明治三十七年(1904)秋,宫崎繁吉(来城,1871—1933)在早稻田大学的讲义录《中国小说戏曲文钞释》出版,对《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和《桃花扇》四部作品的内容加以引用和译注。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他又在《太阳》上连载发表了《清朝的传奇及杂剧》(第十一卷十四、十六号)一文。1908年3月,该文被翻译、刊载于中国的《月月小说》杂志第十四号,改题《论中国之传奇》,译者“滨江报癖”称赞其“于吾国传奇之优劣,月旦甚详”[18]11。文章评价的第一部剧作即为《桃花扇》,称此剧“当之无愧”为“清代传奇中之白眉”“洵足称为逸品”[18]12。文章主要介绍了剧名之由来、创作缘起、曲白的特色及形成原因和成书后的反响和上演情况,内容都出自孔尚任的《本末》。
明治四十一年(1908)十一月,另一著名的中国戏曲研究学者、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的幸田露伴为《日本百科大辞典》陆续撰写有关中国戏曲小说的“解题”条目,其中有《桃花扇》。在《桃花扇》的解题中,他从结构、成书、剧名之由来等方面对该剧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戏曲,清孔云亭著。全四十出,传奇,非短制也。以奇笔写明亡清兴之际,以东京才子侯朝宗和南京名妓李香君成一部之针线。作者腹藏十余年,及作,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成书,忽流传于王公贵绅间,终入内府。香君以身守节,以侯所馈之诗扇,打欲逼己之人,终于倒地,花颜崩解,面血溅扇。杨龙友见其血迹红艳非常,添画枝叶,成桃花之图。此乃“桃花扇”名之起因也。然此传奇,与寻常作者以描摩男女缱绻之满足者大异,观之虽以朝宗、香君为主人,但实为叙明末全体而成一大画幅。结构雄大,笔路健硕,意气宏盛之《西厢》《红拂》类,均成其鞋底泥也。盖作者壮时,从其族兄方训公及舅翁秦光仪等诸老,而详知弘光之遗事,由此而成篇,可谓中国剧中之一佳作也。[19]239-240
结合他在其他解题中对《西厢记》的评价,更可见他心目中《桃花扇》的文学价值和地位:《西厢记》“于中国戏曲中所占地位很高,与《琵琶记》一起最受推崇”[19]235;《西厢记》与《琵琶记》“一起被尊为中国戏曲两大明珠”[19]236。
大正年代——多种译注本的出现
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在大正年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表现之一是翻译了中国的很多戏曲作品,有些作品还有多种译本。《桃花扇》便至少有盐谷温、山口刚和今东光分别翻译的三种本子,译文的语体形式各有不同,但将长达四十四出的原剧完整译为日文实属不易,能够使更多读者了解和认识《桃花扇》的全貌,促进了对剧作的接受和研究。
盐谷温(1878—1962)曾在东京帝大开课,讲读和演习多种小说戏曲作品及研究著作,其中包括《桃花扇》。他特别重视读曲和翻译,“将翻译注释看得比个人著述更重要”[20],曾先后翻译了《琵琶记》《长生殿》《燕子笺》等剧作。盐谷温译《桃花扇》被收入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的《国译汉文大成》第十一卷,共四册,前三册为日语译文,第四册为剧作原文,大正十一年(1922)十一月印行。卷首依次为《〈桃花扇传奇〉解题》、原剧中的一些附录文字(如《小引》《小识》《本末》《凡例》《纲领》《砌末》《考据》《李姬传》等)和正文。正文首页署:“国译桃花扇传奇 清云亭山人编 文学博士盐谷温译并注”。盐谷温《解题》对剧作的文学背景、历史本事、剧情等做了简要的绍介、评述,包括以下几部分:“清朝之戏曲”“作者之略传与作剧之由来”“明末史之概要”“本传奇之梗概”和“概评”。日语译文每页并附有注释。
山口刚译《桃花扇传奇》,大正十五年七月由东京春阳堂印行,全一册。该译本每出的出目不沿用原剧的双字出目,而是使用意译作为新的出目。全书最后附有《〈桃花扇〉解题》。今东光(1898—1977)译《桃花扇》,大正十五年由支那文学大观刊行会印行,共上下两册。卷首有盐谷温的《〈桃花扇传奇〉解题》,删去了“清朝之戏曲”的部分。每出的出目与山口刚译本相同,使用意译。正文分上下两栏,上栏为注释,下栏为原剧文字,原剧文字旁有译文,对加注文字之外的其他词句进行翻译。
昭和时代——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
昭和年间,日本学者研究《桃花扇》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是青木正儿(1887—1964)的《中国近世戏曲史》。青木正儿的这部著作接续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首次较为全面和详细地描述了元代以后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出版后收获了众多好评,对后世影响深远。这部著作也首次对《桃花扇》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评论,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青木正儿没有采用常见的政治社会史的标准对戏曲的发展进行分期,而是注重突出各个时期占优势地位的主要的戏曲形式和演剧类型,将明清戏曲的历史分为“南戏复兴期”“昆曲昌盛期”和“花部勃兴期”三个相续的阶段。而《桃花扇》属于第二个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即“昆曲余势时代”的作品,而且应该是青木所谓的“比诸极盛时代之作家毫无逊色者”之一[1]278。这首先确立了《桃花扇》在明清戏曲发展脉络中的一个大致的位置。具体到康熙年间,《长生殿》和《桃花扇》都在问世之初即备受瞩目,清代即已出现“南洪北孔”的并称美誉,后来同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戏曲的经典作品。《长生殿》先于《桃花扇》十年问世,但无论中国和日本,青木正儿之前的评论者很多在论述两者时都先《桃花扇》,而次《长生殿》。其中有时带有一种价值和地位的评判,但不免会使读者产生误解,颠倒两者成书的时间先后。青木正儿在评论“康熙期诸家”戏曲作品时,则先《长生殿》,而后《桃花扇》,主要排列依据应是两者问世的先后顺序。尽管他提到《长生殿》“极脍炙人口,论者多以之为清曲第一”[1]278,但这不代表他自己的看法。
青木正儿引用丰富的材料,依循全书评述具体作家作品的一般格式,介绍和评论了《桃花扇》多方面的情况。首先是考订作者,主要包括孔尚任的生平、履历,并特别考证了孔尚任的生卒年,不过因所见材料不足,对其卒年的考证止于大致的推断。另,孔尚任又号“岸堂”,而非“肯堂”,至此书最近的2010年的中华书局版,这一明显的错误仍未得到改正。其次,简略介绍该剧的主要内容和成书情况,从中可见青木正儿所据以评论的版本为“暖红室重刻本”的《桃花扇》。再次,较详细地介绍全剧情节梗概。第四,评论剧作的艺术特色和得失,包括结构佳妙、体例创新、曲白新警、宾白生动和音律欠妥等。青木正儿在提出自己的观点后,间或引用前人和时人的相关评论,又借肯定或否定这些评论来加强自己论述的合理性。展开具体的阐述时,他以自己广泛的阅览、敏锐的眼光、深入的考察,做出平实、确切的判断,多能言前人所不曾言,而予人启发。如对于试一出《先声》中老赞礼独特的“副末开场”,青木正儿注意到冯惟敏的《不伏老》杂剧和万树的《念八翻》传奇已有类似开场,而《桃花扇》更胜之。他还联系作者生平,指出孔尚任借老赞礼之口歌颂特别年份为太平盛世,“不外致感激破格殊遇之微意耳”[1]286。青木正儿在注重戏曲作品的案头阅读和研究之外,也重视实际的演剧,注意从剧场搬演的角度分析、评价作品。如从长篇传奇的分卷、分日上演的特点,肯定《桃花扇》中加二十一出《孤吟》的存在。又如关注该剧在民国时期的上演情况:“而《桃花扇》至近日,剧场内演之者渐稀少焉”[1]287。最后,介绍《桃花扇》的流传和改写情况。
青木正儿在论述中多次引用吴梅《中国戏曲概论》(1926年初版)中的观点,而且都是用来佐证自己的意见。吴梅在为王古鲁译本所作序文中也说其书“间有征引鄙议者”[21]4。两人平生并无交往,但可见青木正儿对吴梅的戏曲研究及其著作的重视和肯定。这主要有以下原因:一,两书的主要论述对象相同。《中国近世戏曲史》之作,是青木想要“继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原欲题为《明清戏曲史》”[22]1,实际成书的主要内容也是叙述有关明清戏曲的发展演变和作家作品。而与王国维有些轻视明清戏曲不同,吴梅对不同时期的戏曲发展做同等重视,其《中国戏曲概论》名为“概论”,实为戏曲史,而且是《宋元戏曲史》之后第一部以明清戏曲为主体内容的较完整的戏曲史。青木氏之著作晚出,自不免受其影响。二,两人的研究兴趣有重合之处。吴梅作为近代的全能曲家,不同于王国维的“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22]1,而是既能制曲、谱曲、度曲,又曾亲身参与演戏,这使他在从事戏曲文本和戏曲史的研究时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更重视对作品音律和搬演的考察,且多切中肯綮。青木正儿也将戏曲视为综合艺术,既重视案头文本及其文学性的研究,又关注戏曲的音乐性和舞台性。他在游学北京期间,观赏戏曲演出,便是“欲以之资书案空想之论据”[22]1。
结 语
《桃花扇》作为经典名剧在日本的流传、接受和研究是近现代中日文化融通、学术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我们通过考察近现代日本学界对这部名剧的接受、研究状况,不仅可以梳理出不同时期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的大致脉络,而且可以窥见中日戏曲研究互相影响的途径和效应。《桃花扇》在近现代日本的接受和研究,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几个阶段,由诗歌评论、梗概介绍、全本译注到学术研究,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浅层走向深层,从模糊走向清晰,使日本学人和普通读者对该剧有了更全面、深入、客观的认识、理解。日本学者对《桃花扇》的接受、研究前后之间有影响和承传,中日的评论、研究之间也存在借鉴和互渗。如清人以诗词文体评价戏曲催生了森槐南的多首咏剧诗的创作,森槐南在研究中对梁廷楠《曲话》的借用,还有日本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戏曲史被译介到中国促进了我国学者的文学史观念的现代转换和文学史著述写作潮流的兴起,具体到《桃花扇》来说,这些方面多是潜在和隐性的。而到了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论述《桃花扇》时引用梁廷楠,特别是吴梅的观点,则是直接和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