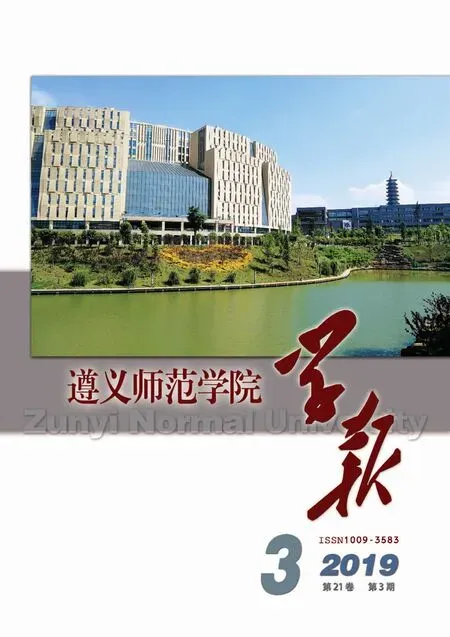浅谈信息时代的新型“公民不服从”
——以“维基解密”事件为例
2019-01-29郝波
郝 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一、“维基解密”及其政治面相
“维基解密”(WikiLeaks),是2006年以朱利安·保罗·阿桑奇(JulianPaulAssange)为首建立的、为要让组织、企业、政府在阳关下运作的、无国界非盈利的互联网媒体。这一组织专门公开匿名来源的文档和网络泄露的机密文件给公众,但又能确保告密者不会因为发送这类机密文件而被捕入狱。任何人都可以在“维基解密”上发布消息,不需要任何技术性操作,并且解密者可以匿名粘贴文档而不留下踪迹,阿桑奇将其视为一个能保护告密者的中间组织。
孩童时代的阿桑奇就善于黑客入侵,并且到了以此为乐趣的程度。年仅16岁的小阿桑奇,就组织建立了“万国颠覆”这一黑客团体,专以黑客入侵唯是,可见阿桑奇对黑客入侵的热衷程度。1997年,阿桑奇在他自己著的一本书中(《地下:黑客与疯狂的传奇及对电子前沿的痴迷》)描述了这段经历,这段经历的叙述,也成为阿桑奇在“维基解密”之后遭受诟病的一个来源。阿桑奇在书中还阐述了有关黑客的法则:“不要损坏(包括崩溃)你所侵入的电脑系统;不要更改那些系统中的信息(除了修改日志掩盖自己的踪迹);分享所获得的信息。”[1]这些都为2006年“维基解密”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或者说是创立“维基解密”的前兆。“维基解密”是阿桑奇个人思想的凝聚,阿桑奇称他创办“维基解密”的动机是:“为了彻底地改变政权的运作方式,我们必须认真并大胆地思考。就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政权本身并不想要发生改变。我们必须要超越前人的思维,追寻技术上的改变,查找出对我们有用的且前人没有机会用到的技术。”[2]除此之外,阿桑奇还曾经在他的个人主页上发表过这样一段话:“某个组织越是隐秘,越是对事件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信息的泄露就越能引致组织内部、小圈子的惊惶与无端的恐惧……因为,不公平的系统的产物一定是众多的异议人士。与异议者相比之下,组织的操控者还常常占寡数和劣势。这种情况下将系统的大量秘密信息泄露,会使这一不公正的系统,在其他更加开放的系统面前,显得更加的脆弱与不稳定。”[3]阿桑奇想要实现的是“透明公开”的公平公正的社会文明。
然而,不管阿桑奇创立“维基解密”的目的和宗旨何在,这都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违法的行为。自“维基解密”创办以来,公布了相当多的机密文件,包括美国的数十万机密外交文档,所以不仅美国政府对其发起诉讼,就连他本国澳大利亚也对其进行调查,称其违反了澳大利亚的法律。阿桑奇这一行径还遭受到了很多批评,有的称这一行径会导致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生命威胁,其工作方式并不透明,其追求的并不是信息公开化,而是肢解美国政府,有的甚至直接将其称为美国政府和民众的敌人。这一结果已经与阿桑奇所预想的目的与宗旨大相径庭了。
其实“维基解密”并不单纯是一个泄密事件,也不单纯是现代信息社会出现的一个现代性事件,它还是一种“公民不服从”的反抗行为。只是,这一“公民不服从”已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而是带上了大数据时代的“染色体”,是一种新型的“公民不服从”行为,而且产生了新型的“政治主体”。
二、传统“公民不服从”与新型“公民不服从”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在西方引起争议的炽热期。雨果·亚当·比多(Hugo Adam Bedau)在1969年和1991年,都写过有关“公民不服从”的书籍,时隔二十几年还在谈论这一话题,可见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对这一话题都十分感兴趣。直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维基解密”事件,又激发了人们对“公民不服从”这一理论进行新的探讨,这一时期的“公民不服从”已然不同于之前传统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下面先来谈谈传统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
有关“公民不服从”的文献记载中,柏拉图的《克里托》篇,通常被认作是有关“公民不服从”的第一篇相关文献。《克里托》记录了囚徒苏格拉底与好友克里托在狱中的对话,对话主要是围绕着苏格拉底是否该逃狱这件事情而展开的。苏格拉底受到了雅典官方的不公正判决被捕入狱,以克里托为首的朋友们花钱买通了狱卒,想借机帮助苏格拉底逃出去。然而,克里托却遭到苏格拉底的劝解性拒绝。苏格拉底拒绝的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苏格拉底必须考虑朋友们的这种解救是否正当,如不正当,则难以从命;其次,苏格拉底还从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层面来考虑不经官方开释而逃狱是否正当,而不是从普通大众的现实功利出发。他认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坏事,即使是被冤枉时也不能以恶待恶。再者,苏格拉底以城邦和律法的口吻反问自己:“苏格拉底,你这是想做什么?你如此图谋,岂非在竭尽全力,来败坏我们——败坏法律跟整个国家?难道你还能想象,若是法律判决无法生效,倒能被私人取消破坏,城邦竟还能存在,不给翻个底朝天?”[4]P10“是什么竟至于你反对国家和我们,必欲试图破坏了我们?首先,不是我们给了你生命?你父亲不是通过我们,才娶了你母亲,生了你下来?告诉我们,你对我们处理婚姻的法律,何抱怨之有?”“对处理儿童养育和教育的法律——你也是如此长大成人的——你又何抱怨之有?”“你又何能否认,你和你的先人,都是我们的子嗣和奴仆?”[4]P11“若你不满意我们,或觉得这契约不公平,你有七十年时间可以离开这国家。……可你并未选择去那里……显然得很,你比旁的雅典人更其喜欢这城邦,喜欢我们法律。……而今,难道你不欲恪守你的约定?”[4]P13-14在一系列发问中,苏格拉底同样从城邦和法律的角度反问式的得出结论:“你难道聪明到忘记了,比起你的父母,以及旁的先人,你的国家可是远更宝贵,远更可敬,远更神圣,神人共仰,智者皆伏?你难道不晓得,国家一怒,岂不比你父亲一怒,更应令你肃然求饶?你难道不晓得,若你无法规劝国家,便只能噤然而从,甘心接受惩罚——鞭策就鞭策,监禁就监禁?”[4]P11-12通过以上苏格拉底反问式的自问与对答,我们发现,此时的苏格拉底顺服至死反倒成为了一种最好的抗议,这一举措可能是当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正当且影响深远的“不服从”了。
“公民不服从”这一思想,是经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之后才从宗教的桎梏中独立出来的。1849年,梭罗发表了有关“对公民政府的抵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这一论题的演讲。奇怪的是,后来这一演讲的题目被改成了“公民不服从”(civildisobedience)。然而,这一事件发生于梭罗死后的第四年,所以,这便并不能证明是梭罗首次或直接使用了“公民不服从”这一术语。有据可考的是,最早把这一术语归之于梭罗的是甘地。梭罗通过决绝向政府纳税来实践他的“不服从”,并且因这一行为被捕入狱一夜,后来因为他姑姑为他缴纳了税款就被释放了。他的这种“不服从”是一种个人性的反抗,这种个人性的单独反抗比置身群众运动中的暴力行为更为冒险,也需要更大的勇气。梭罗的拒交税款是一种典型的“公民不服从”行为。
“公民不服从”这一理论是通过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事件而公开化的,这一抗议事件是一场非暴力的直接行动。路德宣称他领导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就是以非暴力为旗帜的,他在《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谈到了非暴力的四个阶段:收集事实,以判定不公正是否存在;谈判;自我净化(self-purification);直接行动。[4]P62虽然在伯明翰已经经历了这些非暴力阶段,种族歧视已经席卷了整个伯明翰,黑人们的非法占领和游行最终还是激起了暴力,引发了动乱,还是一种违法行动。
“公民不服从”理论经过苏格拉底与克里托的“良知不服从”、梭罗的“良心拒绝”、路德的“非暴力不服从”、甘地的“消极抵抗”和德沃金的“善良违法”的发展,到约翰·罗尔斯才发展成为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公民不服从”理论。1971年,罗尔斯在西方政治哲学式微的情势下,出版了《正义论》一书,向西方政治哲学的深潭中掷下了一巨重石,打破了西方政治哲学万马齐喑的局面。在这本书中,罗尔斯阐述了“公民不服从”的定义、论证了“公民不服从”的合法性并阐述了“公民不服从”的作用。罗尔斯称“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出于良知又属于政治性的违法行为,往往旨在带来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的改变。靠这一种行动,人们诉诸社会多数的正义感(senseofjustice),并宣布依其所考虑的看法,自由平等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为能得到尊重。”[4]P158-159由此可见,公开性、非暴力性、违法性和政治性是“公民不服从”这一思想的核心定义阐释。之后,罗尔斯还论述了“公民不服从”的合理性,认为如果抗议的对象确实有悖正义,或者政治的多数呼吁无效,或者由于“公民不服从”的正义范围被加以限制时,是可以决定“不服从”的。因为适当和健全的“公民不服从”是民主法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它有助于纠正非正义,将不法分子重新拉回到正义之中,从而维护社会正义。
真正典型的“公民不服从”是建立在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多数人的正义感之上的,而且“不服从”者仍被视为公民,并且拥有公民权。然而,纵使是在正义居于主流的民主法治社会中,也并不能完全保证“公民不服从”者的安全,毕竟“公民不服从”确实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虽然这种“公民不服从”是以公开、和平以及甘愿受罚来表达对法律的忠诚。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的决定是否“不服从”,但他们应当做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准备,无论是法律上的,亦或是道德上的。
通过以上对传统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梳理,再来看阿桑奇“维基解密”一事,我们会发现,阿桑奇作为大数据时代的公民,他透过泄露国家机密文件而采取的“不服从”,已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了,是一种新型的“公民不服从”。阿桑奇与苏格拉底在对待国家和法律时的反应完全不同,苏格拉底遭受不公正的审判入狱,他自己并没有主动反抗这一审判,更没有逃跑,而是以一种“顺服”来“不服从”。苏格拉底以“顺服”致死保住了他的公民资格,又由于至死也留在雅典城邦便带有强烈的精神民族性。阿桑奇的“维基解密”不服从与梭罗的个人性拒绝纳税和马丁·路德·金的反抗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性不服从相比,虽然都带有违法性质,但对待犯罪后的惩罚态度却不尽相同,所以带来的后果也各不相同。虽然阿桑奇“维基解密”事件带有传统意义的“公民不服从”特征,即违法的、政治性的、公开的和非暴力的,但是这些传统性特征却不足以概括大数据时代发生的“公民不服从”。
三、新型“公民不服从”产生的新型政治主体及其主要特征
阿桑奇“维基解密”一事,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了现代信息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从政治层面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对有限国家的强调,二是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从政治层面来思考维基解密事件是对现代人自身政治处境的一种观照,正是在这种反思中见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概念,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主体。
在信息时代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概念,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的政治概念。传统的政治概念主要是区分敌友,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在《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一书中详尽地阐述了以敌友为核心的政治概念。施密特认为政治的基础就在于划分敌人与朋友,且在此基础上强调了政治具有独立性,“朋友与敌人的划分表现了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或分裂。它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独立存在,而无须同时借助于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划分。”[5]P106-107只是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主权性决断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这种主权性决断,也就将没有政治的存在。这种政治概念是以民族—国家的主权政治为划分标准的。而到了信息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划分界限的传统政治概念发生了改变,不再仅仅区分敌友关系,更多的关注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新的政治概念体现为个体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新型反抗。
一是新政治主体具有匿名性。匿名性,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德国的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是这一术语的最早提出者,他说:“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会逐渐产生各种不同的类型格局,这些类型会随着生活中与他人相处的经验和接触程度等不同,渐渐地由面对面的情境逐渐远离到匿名的情境,也就是指互动的双方对彼此并不是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产生了匿名性。”[6]P135而网络匿名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网络参与者可以隐藏真实身份,以匿名或别名的方式进入网络;二是指网络参与者可以拥有多个ID身份,这种多重身份使网络参与者无需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是变革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交往方式,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形态。通过网络平台开创的虚拟空间,拓宽了物理空间,为更多的人参与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人们虽积极参与,却多是匿名流动。阿桑奇就是以这种匿名的方式掀起了维基解密风波,揭露了美国及其同盟瞒着全世界把网络这个曾经预表着前所未有的民主与自由的工具变成了全面监视公民的空间的惊天迷津。公民不再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公民资格被剥夺,真正进入民主与自由的途径发生了变化。以匿名的方式“发声”成为信息时代捍卫真正民主与自由的有效途径,从而这种匿名性成为信息时代新政治主体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是从政治的归属到逃离。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归属感基于政治认同感,罗森堡姆(walter A.Rosenbaum)曾在《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书中指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7]P69在古希腊时期,“人是政治的动物”,公民是政治生活的有机体,国家是公民生活的集合体,无论从参政度还是地理空间上说,公民都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高度的政治认同感和浓郁的政治归属感。而近代以来,霍布斯和洛克从假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认为自然法的约束力仅仅是道德层面的,还需要公共权力的制约,为此达成了契约,建立国家来维护公民的权利。到了罗尔斯和诺齐克时代,他们开始反对契约论,主张个人权利至上。国家契约论也好,个人权利至上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此期的公民深受国家保护,即使犯了罪,也深信国家会伸张正义,不会逃跑流亡,有着强烈的政治归属感。但到了网络信息时代,情况则变得更加复杂,最明显的特征是网络信息在形式上变得更加隐秘化,随之公民犯罪手段的隐秘性也大大地增加了,合法公民的利益受到危害的风险无形之中就加大了很多,从而导致公民以往的那种政治归属感变得岌岌可危甚或荡然无存。同时,网络的出现打破了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冲击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并且无形中改变了对政治惩罚的态度。维基解密东窗事发后,阿桑奇获政治庇护,这种政治行为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惩罚了,主要表现为政治逃离而非乖乖接受法律制裁。这种逃离与政治归属感的变化正是信息时代新型政治主体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是公民资格被剥夺。“公民资格”作为一项制度,有其自身发展的悠久的历史,现代学术界所讨论的“公民资格”理论,主要是以马歇尔(ThomasHumphrey Marshall)所阐述的相关理论为基底。马歇尔对“公民资格”的释义是:“赋予共同体的完全成员的一种身份,所有拥有这种身份的人在由这种身份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方面是平等的的。”[8]P28-29究其根本,公民资格的实现是建立在将每个社会成员都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平等待之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公民资格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将社会权利与公民身份结合起来,追求平等的公民资格,从而彰显公民身份。对于公民资格嬗变的历史分期,学术界的主流分法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道德至上的公民资格,处于嬗变和过渡时期的中世纪公民资格,现代物质主义取向的公民资格,以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公民资格。”[9]P9在古希腊时期,公共空间就等于民主空间,公民积极参与到政治事务,就像伯里克利曾经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这里,每个人不仅关心个人事务,而且关心国家事务:即使那些总是忙于自己事务的人也熟知一般的政治生活——这是我们的特点。”[10]P132但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公民人数的激增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古希腊时期那种全民面对面的民主参政已变得不再现实,公民也不再将政治看作生活的中心,公共空间与民主空间发生了断裂,所谓的民主成了少数人的“民主”。而当下正处于全球公民资格时代,但由于网络大肆“侵入”人们的生活,可以说,当下正处于“全球监控”状态,公民资格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侵犯。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假借反恐名义加强互联网监督机制,全面监控公民生活,大肆践踏人权。阿桑奇维基解密事件就暴露了美国政府滥用职权剥夺公民资格的这一事实。这种或显或隐剥夺公民资格的现象也是信息时代新的政治主体的一种体现。
四是精神的非民族化。精神的非民族化主要谈及的是一种新式的想象共同体,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关于民族化问题,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起源与散布》一书中阐述了关于民主化的问题。安德森否定了原生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些充分条件,比如出生籍贯、生活环境、种族血统等因素,将民族主义看作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的,提出了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民族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想象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想象”贯穿于民族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始终。与原生民族主义强调现实当下性相比,安德森所阐述的民族主义更突出“想象”性特点。这种“想象”性主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尤其是印刷术在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促进了将民族视作“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说法。安德森曾在“美洲大陆上欧裔海外移民想象的民族主义”这次民族主义的散布浪潮中讲述到,那些移居到他乡的人们,在异地缺少归属感,对母国怀有深切的渴望,当这些移民接触到来自其他地域与他们有相似情况的人时,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亲近感与认同感,尤其是想象到远在大洋彼岸的家乡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会将现居的殖民地想象为自己的民族。尤其是当印刷术传入时,通过报刊及书籍等媒介更是深化了这种民族归属感。在这种“民族想象”的过程中,“欧裔海外移民官员与地方上的欧裔海外移民印刷业者,扮演了决定性的历史角色。”[11]P62至此,可以说,这种精神认同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界限。在信息时代,由于网络的出现与普及,对距离、界限及亲疏等问题都已有了新的界定,延伸了物理层面的空间,较之传统的公共空间更加多元化,毕竟网络是一个跨越全球多地域、多种族、多文化的交往平台,交往范围大大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通过网络人们可以了解各个国家的大小事件,且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无疑加剧了跨民族—国家精神想象的认同感,形成了一种精神的非民族化。
四、结语
通过对新政治主体的匿名性、逃离与政治归属感、公民资格被剥夺和精神的非民族化这四个方面的分析,这些特征区别于传统的“公民不服从”和传统的政治概念,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公民不服从”和一种新的政治概念。“维基解密”之事表面看仅是现代信息社会出现的一个现代化问题,但却为我们深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情况掀开了重要的一隅,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