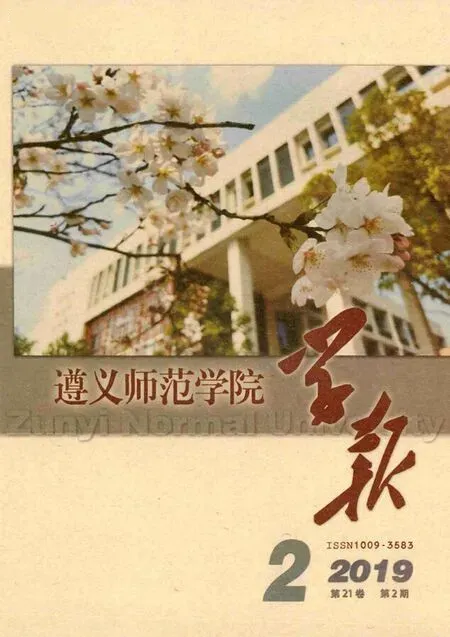论清代移民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开发之功
2019-01-29魏登云
罗 进,魏登云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包括重庆东南部和贵州北部,东与湖北、湖南毗邻,南与贵州南部及广西相连,西接云南,北依四川,流域总面积87920平方公里,世代杂居着土家、苗、布依、彝等40余个少数民族。此处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加之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内地民众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为了谋求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历代王朝都有大量内地民众远离故土,迁居于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清代也不例外。自顺治元年(1644)明朝降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经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分三路进入贵州,至翌年(1659)吴三桂率清兵攻占云南,进而管控整个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以来,内地人口急剧增加,从而使其人地关系变得极不和谐。对此,康雍乾三代帝王都曾发出过相同的忧叹。康熙帝忧心道:“今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地亩并未加增。”①《清会典》卷一百五十七《户部六》雍正帝亦忧心道:“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1]P18乾隆帝同样忧心道:清朝自建国以来,时间长达100多年了,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和平时期,从而造成了“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①《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四十一面对严重的人地关系不和谐,清朝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向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移民是解决内地人多地少矛盾的最佳途径。为此,清中央政府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清王朝诸多惠政的刺激下,大量内地民众纷纷以不同形式进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而且还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新的农作物品种,借助其辛勤劳动,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开发建立了不朽之功。
具体而言,清代移民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开发之功,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大量军士驻守乌江流域,维护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为了加强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管控,清代推行了富有特色的驻军制度。顺治十五年(1658),清朝在贵州首创绿营兵制,“设贵州提督,标兵分左、右、前、后四营,左营设将领八,余三营将领八”,其绿营兵共计3000人。[2]P2667翌年(1659),“定云、贵官兵经制。设云贵总督,标兵分中、左、右、前四营,中营设将领八,余三营将领八”,其绿营兵有4000人。[2]P2667“设大定、黔西、镇远、威宁四镇总兵官”,绿营兵有三营,每营分别带兵2000人,合计6000人。一直到光绪年间(1875-1908),贵州绿营兵合计多达42905名。[3]P687另外,针对流域中贵州地区军粮供应不足的问题,清廷特允许部分驻军就地垦荒屯田,当时,“有屯兵者惟湖南、贵州”。[4]P213部分绿营兵就地垦荒屯田,其双重效果明显,既维持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又保障了其驻军粮食供应,稳定了军心,不失为切实可行之举。
除了保持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绿营兵之外,为了进一步加强驻守的军事力量,清代还驻扎其他军队,最为常见者有三种:一是防军。防军初为招募而来,属于地方军,其兵员人数多少不确定,分布在各地郡县,如果遇上敌人入侵,就由专征将帅统领出征反击。到了清末,因为绿营兵战斗力大为削弱而多次被裁减,这样,各省守卫工作主要依靠防军,防军地位凸显,其人数有增无减。光绪二十四年(1898),仅贵州防军就多达16940人。光绪三十年(1904),贵州防军继改编为24营后,在此基础上又增募了19营。[3]P712二是乡兵。乡兵创始于雍、乾两朝,与防军一样,同属地方军。流域中贵州苗疆地区的乡兵有夷兵、土司兵、黑倮勇丁数种。但乡兵建立之初,还不是常设之师,旋募旋散,极不稳定。不过,后来由于乡兵在维持地方治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也随之提升,因此,流域中贵州苗疆地区的乡兵出现不断增加之势。雍正八年(1730),云贵总督鄂尔泰顺乎历史发展之趋势,在滇黔川相连之地,大刀阔斧地推行改土归流,为了配合该政策的有效实施,调用官兵10000余人,其中乡兵就占了约一半,足见乡兵人数之多。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云贵总督岑毓英完善乡兵建制,进一步扩大其规模,将“黑倮勇丁,编为六营”,“西南土防,编为二十五营”,调兵2000人,与原有防军及乡团土司,协力警备九隘以外“野人山寨”。[5]P886为了解决某些驻防地区军队口粮之需,清廷也令乡兵就地垦荒屯田,嘉庆时期(1796-1820),流域中的贵州苗疆地区,官府就拨出乡兵7000人令其从事垦荒屯田,这些乡兵利用平时军事训练之空闲,开垦荒地达数十万顷。[3]P687乡兵开垦荒地如此之多,其屯田效果不可谓不显。三是土兵。土兵为云南、贵州、湖广等西南边地各长官司所独有,通常由当地少数民族组成。[3]P687与乡兵不同,土兵常被征调远离本土参加对外作战,“调征西南,常得其用”。康熙年间(1661―1722),“莽依图战马宝于韶岭,瑶兵为后援。傅弘烈平广西。亦籍土兵义勇之力”。乾隆年间(1736-1795),朝廷讨伐廓尔喀,征调金川土兵5000人参加平叛,“讨安南,以土兵随征”。[6]P41倘若平时无征调任务,土兵接受土官和土司管辖,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与乡兵一道镇守险关要隘。
由于流域中苗疆地带少数民族叛服靡常,历代王朝以维护国家大一统为圭臬,对其实行剿抚兼施之策,清朝也一样。康熙三十八年(1699),朝廷考虑到镇筸地处苗疆军事之要地,将沅州镇改为镇筸镇,设总兵以下各官职,增加兵力1000人,加上原有驻军,其兵额多达2100人,以防红苗之反叛。[2]P2793乾隆元年(1736),杨名时“锐意治苗”,依据流域中贵州苗众分为生、熟二苗,生苗在南,熟苗在北这一情况,在流域中的贵州腹地安排重兵屯驻,在靠近苗族的各交通要道,增修防御工事,使民有所归,兵有可守。[3]P713-714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康雍时期(1661-1735),在黔东南原土司领地,置古州、清江、台拱等6厅,共计驻军达8656户,若以每户平均5口计,即迁来移民43000余人。[7]P56在六厅附近的凯里卫,领有13屯堡,另有14塘、10铺,共计军户为9692户,若以每户平均5口计,即迁来移民48000余人。[7]P56嘉庆初年,乾嘉苗民起义(亦称石柳邓苗民起义)被镇压之后,为进一步根除后患,清廷在苗疆修复“边墙”150余公里,建碉堡、哨卡、关口1100余座,招屯兵7000人,备战练勇1000人,实施“屯田养勇,设卡防苗”的政策,从而使南接铜仁府,北连湖南永绥厅,百里之中顷刻可达。[7]P56其军事管控何其严也。
有清一代,大量绿营兵、防军、乡兵和土兵驻守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成为军事性移民,其中部分军队就地垦荒屯田,部分军队重点镇守险关要隘,从而产生了双重效果:既保障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驻军的粮食供应,稳定了军心,又未削弱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管控。《清史稿》云:“沾边台卡,亦内外兼顾,盖边防与国防并重焉。”[8]P160尤其是对乌江流域的大片苗疆地区,军事防范更严,“环苗数百里”的湘桂黔边界,修筑汛碉、炮台,屯堡共1209座,“烽燧相望,声息相闻,……防守兵丁,有警则荷戈,无事则秉来,进攻退守,为持久计”,[8]P161-162从而将流域中各少数民族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完全置于军士移民的严密监控之下,维护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为其大规模开发创造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二、内地农民纷至沓来垦荒种地,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清军入关之后,由于大规模的战争致使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田地抛荒、百废待兴,特别是追剿南明残余势力和平定“三藩”之乱,造成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当进入17世纪80年代战乱结束之时,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人口密度相当低,其开发程度亦不高,这对人多地少的内地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去处。随着内地人口激剧膨胀及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对内地农民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大。鉴于此,清廷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顺乎民情民意,允许内地农民到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垦荒种地,从而出现了垦荒性移民。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云贵总督赵廷臣奏请清廷户部:“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对于赵廷臣这一切实可行的提议,清廷户部做出了积极回应,支持云、贵当地民族和汉族移民一起开垦荒地,各州、县发给他们印票,所垦土地“永为己业”。[7]P56其惠政力度不可谓不大。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户部断然驳回了在两广、江西、福建等地招民垦荒之议,而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招民垦荒之议却另眼相看、关爱有加,“仍准照例议叙。”[9]P155雍正时期(1722-1735),云贵总督高其倬充分肯定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移民垦荒之举,他说:移民垦荒“可以充实地方,可以移易倮习”。[3]P731乾隆六年(1741),清廷户部又针对贵州山地多且山石混杂这一实际情况,规定:凡是依山傍岭及贫瘠之地,“悉听民垦种”,并永远免征土地税。一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实行新的垦种政策,允许自由开垦国有山头地角的零星土地,并实行免税。其新政规定:流域中贵州的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俱不论顷亩,概免升科,以广地利而厚民生”。[10]P41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此优惠诱人的垦种政策,极大地吸引了大量内地农民纷至沓来,加入移民垦荒大军的队伍。就在清廷诸多惠政的刺激下,借助内地垦荒移民的辛勤劳动,大量抛荒的原屯田及无主荒地很快就被垦种。另外,清廷还教给内地垦荒移民最佳垦种方法,即先垦种熟水田、次垦种生水田、最后垦种旱田。雍正十年(1732),云贵总督高其倬即以此法招募内地农民至乌江流域上游的乌蒙府垦种,并允许所垦水田6年后、旱田10年后,按照普通田地收税条例征收钱粮。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移民垦殖活动。
随着内地垦荒移民大军纷至沓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汉族人口迅速增加,从而使其民族人口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由“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就拿流域上游的黔西州来说,乾隆十五年(1750),即有“汉庄二百四十六,计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九户、共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五名口”;“附居苗寨客民一千一十九户,共五千二百六十名口”;而苗寨仅“二百有九,计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三户,共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三名口”。[7]P57-58其“汉多夷少”的状况不可谓不明显。流域中部的修文县同样是“汉多夷少”,其民族人口结构为“汉民多于苗户十之八九,苗民不及汉庄十之二三”。[3]P769就连地广人稀的普安县,其土目大姓招佃耕种,从而使得“流民凑聚,滇蜀失业穷黎,携妻挈子而来者,踵相接也”。[7]P56这些以“客籍”身份进入贵州的垦荒移民,有的很快就在农村置宅购产,有的住在城镇而在农村购置田产,豪富者竟至购买“全庄”或“全寨”土地。有人曾做过统计,清代“贵州人口约1121万人,普安向东至镇远一带为人口稠密的地区”。[11]P209-210另据《清实录》统计,康雍乾时期,流域中的贵州地区新开垦的农田三朝合计 183824亩,其中,“康熙时仅为66657亩;雍正时为25200亩,乾隆时为91967亩”。[12]P79不可否认,新垦田地的不断增多在很大程度上皆归因于外来移民的辛勤劳动。此外,垦种熟田所占比例快速攀升,清初,遵义府“原额熟民田地共556877亩,康熙二年(1663)增至563534亩,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增至913128亩,乾隆五年(1740)以后大致稳定在895964亩”。[13]P98由于田地熟化程度日益提高,农作物产量也不断增加,食用之余,“尚多盖藏”。[13]P110
内地农民迁移至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有清一代,流域中的某些地区已广泛使用筒车、龙骨水车和铁犁等先进农具,还能根据土壤性质给农作物施肥,推广汉族地区先进的育秧插田法。当时,流域内的农作物灌溉主要采用三种方法:其一,拦河筑坝提升支流渠道水位,随地势高低造堰分而灌之,又“相田之高,卑为小沟,轮日泄闭,灌无不均”;[13]P100其二,充分利用各处地下泉水,并根据地下泉水水温冷暖情况,掌握好冷暖水量的合理搭配,因为“泉水有冷热,热者丰,冷则谷迟,迟病秋风”;[13]P100其三,根据田地高低不同,利用水车等提水工具分配用水,“一轮之水常输五十石谷田,岁一补,三岁一新,逸不及拦田之美,俱无忧水旱”。[14]P5其农作物灌溉方法不可谓不科学,亦不可谓不先进。在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流域内的农作物栽培技术也得到了提升:一是盛产水稻等粮食作物。清人许缵曾说:流域中的贵州各属“产米精绝,尽香稻也,所酿酒亦甘芳入妙,楚中远不及。”[15]P209仁怀直隶厅土田最高者为箐地,气候较冷,“宜稻、菽、粟、稗、高粱、玉蜀黍”。[16]P1421二是栽种耐旱高产作物。流域中的黔北婺川县“产米不多”,但有“包谷杂粮等项,足敷民食,无须他处接济”。[17]P198松桃直隶厅,“乡民”勤俭垦殖,同时“栽桐茶诸树及种包谷、番薯等物”。[17]P198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黔江等地土家族、苗族地区遭受大灾,粮食十分紧缺,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黔江知县翁若梅从福建引进番薯,并翻印了农书《金薯传习录》,向当地百姓宣讲此书,“告以种植之法和种植之利”,从而加速了番薯的推广种植。[18]P438三是栽种经济作物。清乾隆八年(1743),遵义知府陈玉壂新开致富之门,“携其蚕种山佐来,教民种橡以养之,取丝为帛。至今衣被甚广”。[14]P90仁怀直隶厅土田下为花厂,“地低近河,居民多种棉花”。[16]P1421
在清中央政府各种鼓励垦荒政策的刺激下,大量内地农民不辞艰辛、远道而来,构成了规模庞大的移民垦荒队伍,补充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人口结构,推广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新的农作物品种,开垦了大量抛荒的原屯田及无主荒地,从而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三、外来客商侨居乌江流域,推动了民族地区商贸繁荣
随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各种经济的大发展,地方官府为增加商业税收,积极支持外来客商往来各地,从而出现了商业性移民。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在上疏中说:“兵后整理抚绥,其要在垦荒芫,广树蓄,裕积贮,兴教化,严保甲,通商贾,崇节俭,蠲杂派,恤无告,止滥差。”[2]P7747并要求各地州县官吏以这10件大事作为殿最。不难看出,“通商贾”一事也成为了各州县官吏必须重视的大事之一。由于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外来客商怀揣致富之梦,纷纷进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选择各交通沿线的城镇、屯堡、村落作为其长期经商和定居之所。如流域中的省会贵阳,“五方杂处,江左楚南之人为多”,“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籴贱贩贵,相因坌集,置产成家者今日皆成土著”。[7]P59水陆交通便利的镇远府城,“居民皆江、楚流寓”,“湖南客半之,江右(即江西)客所在皆是”。[7]P59临近的普定县,“黔、滇、楚、蜀之货日接于道,故商贾多聚焉”。[19]P241甚至不少偏远地区也不乏外地客商移民。流域中的大定府,“关厢内外,多豫章、荆楚客民”。[20]P98威宁州,其地盛产铜、铅,又是京铜外运的必经之地,吸引外地客商汇集,“汉人多江南、湖广、江西、福建、陕西、云南、四川等处流寓”,有4502户,占大定全府客商总数的45%。[7]P59流域中的铜仁府,其汉民“多来自江西,抱布贸丝,游历苗寨,始则贷其赢余而厚取其利,继则准折其土地、庐舍以为值”;[7]P59松桃厅的城市乡场,“蜀、楚、江西商民居多,年久便为土著”。[3]P770距黎平府府治二百余里的“内三江”茅坪、王寨、卦治,因为盛产杉木,又通船只,水运方便,“商旅几数十万”。[7]P59外来客商往来川流不息、人山人海,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商业图景。
大批客商往来和侨居,必然会带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商业贸易大发展、大繁荣。俗语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也不可能例外,流域中的贵州地区出产葛和兰麻,各地大多以之为纺织原料生产葛布和兰麻布,贵阳、黎平、思州等地生产的葛布和兰麻布闻名遐迩,十分畅销。有些地方以棉花为纺织原料生产土布,都匀、镇宁、永宁等地生产的土布,因布质细致洁白颇受消费者喜爱,人们争相购买。尤其是遵义地区,棉织业最为发达,不少居民多以织布为业。贩者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远赴湖南常德大量收购棉花,然后在遵义列肆坐卖,纺者买棉花以纺线,织者买棉线以织布,并将产品投入市场销售,从而形成了从原料购进到产品销售,其专业分工十分明确的整套生产流程。[13]P150受此刺激,流域中的蜡染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尤其是苗、仡佬、瑶等少数民族制作的蜡染布匹,质量上乘,销路好,其市场前景广阔。黔西北气候寒冷且多雾,为了抵御严寒,各民族大多畜养绵羊,以绵羊毛为纺织原料生产毛毡,因此,用羊毛织毡发展成为其传统手工业。当时,毛毡产量很大,是各地集市交易中较为常见的商品。[3]P722
为了更好地融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体之中,许多外来客商不但开设作坊,就地生产市场所需产品,而且还招收雇工学徒,传授先进技术,一方面满足少数民族群体日常生活之需;另一方面确保民族地区传统民族工业经济的繁荣。仅流域中的贵州地区,乾隆年间(1736-1795),贵州全省有“贸易、手艺、佣工客民二万四千四百四十户”,其中,贵阳府尤多,共有“贸易、手艺、佣工并无苗产客民”2177户,具体包括贵阳府亲辖地312户,贵阳县281户,新贵县498户,罗斛州判241户,大塘州判171户,定番州391户,广顺州271户,开州12户。[13]P148贵阳城内,铁业发达,成行成市,出现了“铁匠街”“铁局巷”[13]P149。清代中叶,仁怀城西茅台村酿造的茅台酒远近闻名,有“黔省第一”之美誉,并远销滇、桂、川、湘等省。光绪年间(1875-1908),安顺出现了名扬遐迩的“三刀”,即剪刀、菜刀和皮刀。铁剪分花剪、布剪和桑剪三种,钢口坚利而耐久,远销本省及云南,从事刀剪生产的居铁工的十分之四,获利甚丰。[13]149
随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外来客商的日益增多,他们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基于此,不少地区的外来客商为了保护其共同利益,解决同乡生活、生意上的困难,实现更好的发展,以同乡或同行关系为纽带,广泛建立会馆。当时,会馆数量的多少可以反映出外来客商势力的强弱。有清一代,仅流域中的贵州各地外来客商会馆即达214处,其中江西会馆74处,四川会馆、湖广会馆各54处,秦晋会馆10处,江南会馆5处,福建会馆13处,广东会馆4处。[3]P770毫无疑问,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外来客商中,江西客商占据了明显优势,其势力最大。而以会馆为依托的商品集散地就自然成了临近地区商贸的重要场所。比如,来自江、楚、蜀等地的贸易客民多在省会贵阳“籴贱贩贵,置产成家”[3]P724。黔西普定县,“场市十三,各有定期”。[21]P53黔东北松桃厅,“贸易以赶场为期,场多客民,各立客总以约束之,场以五日为期”。[22]P154黔东胜秉为“苗夷互市处”,每月逢三、七附近居民赶场,一年共有七十二次集市。[3]P728黔中开州因盛产朱砂、水银,“江右之民麇聚而收其利”。[23]P317可见,清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商贸不可谓不繁荣。
四、占籍仕宦热心开办学校,促进了民族文教日益兴旺
选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仕宦到地方任职,是历代封建王朝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控制的重要举措,清代也不例外。清代职官制度,在继承明朝的基础上而稍有变化,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其主要官职都由省籍不同的仕宦异地担任。有清一代,仅流域中的贵州省就有“省级文职官员567人,其中总督79人、巡抚124人、布政使123人、按察使153人、提学道(提学使)88人”。[24]P45与明朝相比,并无二致,连同各地府、厅、州、县官署,长期保持着大量外省籍流官。鉴于清朝统治者实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到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任职的各级地方官员,均能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积极有效地执行中央的文教政策,热心教育,革除旧习,纷纷创办各类学校,其中主要有三类:一是官学。清代的官学,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制度,不过,还是有所发展,有所改变。康熙初年,贵州提督学政田雯鉴于明末清初战乱,许多学校被毁这一现实情况,奏请在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永宁、独山、麻哈3州以及贵筑、普定、平越、都匀、镇远、安化、龙泉、铜仁、永从9县设立学校[25]P459-460。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廷又设贵州清浪卫学教授一员,开州、广顺、永宁、独山、麻哈5州学学正各一员,普安、余庆、安化、普定、平越、都匀、镇远、铜仁、龙泉、永从10县学,训导各一员。[26]P53清代贵州官学在明代47所的基础上,增加到了69所,其中,府学12所、直隶厅学3所、直隶州学1所、厅学6所、州学13所、县学34所。各官学的廪生、增生学额共3000余名。教育的普及面比明代大为拓展。二是书院。与官学相比,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书院则更多,其最有名者为贵山书院、正习书院和正本书院,时称“贵阳三书院”。[4]P216其中,贵山书院于雍正十三年(1735)由贵州巡抚元展成在阳明书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正习书院和正本书院都于嘉庆五年(1800)由布政使常明创建于省城贵阳。康熙三十五年(1696),毕节知县李曜修建的松山书院(又称毕阳书院)也很有名,以“立教以存心、立品为本,以储经济、达时务为用”为办学宗旨。[27]P169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流域中的贵州共建书院133所。其中,贵阳府14所,遵义府15所,黎平府20所,大定府11所,安顺府11所,兴义府10所,都匀府10所,石阡府2所,镇远府11所,思南府12所、思州府3所、铜仁府2所、镇安直隶厅1所、仁怀直隶厅2所、松桃直隶厅3所、平越直隶州7所。[28]P659不难想见,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书院文化教育事业的兴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代移民所带来的先进文化的厚积薄发。三是社学。雍正之前,流域中的贵州社学,仅在离城较近的巨乡大堡创办,“凡汉人在乡之学,总曰社学,所以别于府州县在城之学也。各乡离城远近不一,岂能尽人负笈来城?故于巨乡大堡另立社学”。[29]P257其办学进展不是很大,直到雍正年间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雍正十三年(1735),贵州巡抚杨名时上奏称:“驭夷之道,贵在羁縻;服贰之方,务彰诚信;止戈为武,德可感人;未有怨毒猜疑而能久宁帖者”[30]P311。在杨名时看来,集权统治离不开“德化”教育,而实现“德化”教育的最好方式就是兴办地方学校。在此治国理念的指导下,清政府不仅放宽了对社学的限制,而且还从办学经费、学制诸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自此以后,贵州社学逐步从巨乡大堡向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延伸,出现“苗地遍立社学,并择内地礼师教训”[31]P94的景象。乾隆二年(1737),礼部议准“社学之设,著有成例。其黔省地处偏僻,或有未经设立之处,应再行文该督,遵照雍正九年定例,饬令州县官酌量奉行。至量加廪饩,动何钱粮?令该督随地酌办”。[32]P704自此,社学便广泛地在贵州边远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开办起来。乾隆五年(1740),礼部又议准:“贵州总督兼管巡抚张广泗查复贵州学政邹一桂条奏,黔省设立社学一款,应如所奏,贵阳府属之长寨、定番州属之大塘、大定府属之水城、都匀府属之都江、独山州属之三脚屯、自粤改隶黔省之荔波县、清平县属之凯里、铜仁府属之松桃、永从县属之丙妹……又镇远县属之邛水、天柱县属之柳霁等处,准各设社学一所,永从县在城在乡,准设社学两所,于附近生员内,择文行兼优者,令其教导,照例以六年为期,果能教导有成,文学日盛,将训课生员,准作贡生。如三年尚无成效,发回另选。仍令驻扎地方之同知、通判等官,不时嵇查,至修建社学,应令该督转饬地方官,酌量办理,其社师修脯,每年各给银二十两。”[26]P154自此,社学设立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贵州社学发展出现高潮。
在占籍仕宦的热情倡导和积极鼓励支持下,通过各类学校的教育熏陶,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名流,如流域上游毕节地区的张氏和路氏就是典型:张氏家族是一个文化家族,该家族人才辈出,闻名于黔西北,以“祖孙五进士,叔侄三翰林”闻名于世;[33]P315路氏家族是以耕读传家的成功典范,该家族在清代出现了10多位文人,均能写诗作文,大多有诗或诗集传世,如路元升、路同升、路璜、路瑄、路朝霖、路承鋆、路承熙、路秀贞(女)、路孟逵、路邵、路斯京、路斯亮、路斯云等,其中“进士5人,举人5人”[33]P307。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除科举止,清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贵州辖区,“共录取举人3110名,武举1704名,进士611名,武进士103名,状元3名,其中武状元1名。”[34]P7其民族文化教育的成效不可谓不显著。
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熏染,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安顺府“侬家(龙家)居府东北,性和平,衣尚白,近时有读书入学者,礼节与汉人稍同。婚姻以牛马为聘,迎娶之夕,其女即返母家。”[35]P523镇远府“峒人即土人,风俗与汉人同,妇女亦汉妆,惟足穿草履,所织之布曰峒布,细而有纹,婚丧俱循汉礼,耻居苗类,称之以苗,则怒目相向云”;[36]P266黎平府“洞苗向化已久,男子耕凿诵读,与汉民无异,其妇女汉装弓足者与汉人联姻”;[36]P266贵定县境内的苗族“衣服言语与汉人略同。知同姓不婚。遇亲丧,长子居守七七日,期满乃敢出,名曰放鬼,如贫不能守,必以次子或长孙代为之守”。[35]P635清嘉庆初时的松桃厅,“苗皆剃发,衣帽悉仿汉人”“婚姻丧葬,与汉人渐同”。[37]P183可见,清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其社会风俗习惯日益汉化。
综上所述,整个清代,鉴于内地人多地少,人地关系不和谐,清中央政府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刺激内地民众迁徙到地广人稀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正是在朝廷各种惠政的激励下,大量内地民众以不同的形式远道而来,通过辛勤劳动,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开发建立了不朽之功,这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仍不乏现实意义: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其中,“依靠科技进步、培养人才”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保障。这就要求必须有大批掌握高科技的高素质人才投入到西部大开发中来,而西部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经济较为落后,对高素质人才缺乏吸引力,因此,作为中央政府在为政决策方面,必须从二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大规模进行交通、水利、电网、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另一方面从工资待遇、生活补助、项目投资、税收政策等方面加大优惠力度,吸引高素质人才主动放弃东部优越条件,积极投身于西部大开发,从而实现新时代知识性移民,为建设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再立新功。